汉代神学政治的危机与生机
2018-06-01杨清虎
杨清虎
(安顺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
美国人类学家魏乐博(Robert P. Weller, 1953)认为高水平的宗教信仰与政治健康、经济成功并行不悖。[1](P1)反之,是否意味着低水平的宗教与政治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导致政治统治的危机与衰退呢?从汉代社会发展的走向来看,正是因为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低水平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才使汉代政权统治走向末路。国家是基于社会文明和世俗权力的产物,政府的社会控制需要依赖各种国家机器方能维系下去。民间信仰具有原始、草根和散漫的个性,与体制化宗教的强大的控制力不同,民间信仰虽是基于神权与原始宗教神学的产物,却无组织,无体系,易于被政治权利操控。这种控制力较差的信仰与政治结合,为汉代神学政治社会的发展埋下隐患。
一、神学政治思想理性的堕落——儒术还是巫术?
汉代建立起来的人本社会并非一个纯粹的理性社会。由于信仰上杂而无序的聚合收纳,致使汉代神祇信仰复杂,既有对先秦和秦代神祇的沿袭,又有汉代新造的各种神祇。从神祇的继承上来说,长安设置的祝官、女巫大多照搬秦朝,长安到处都是巫者。当然,林富士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巫官员额极少,整个汉代官僚组织中所占地位和分量极为微小。[2](P43)巫觋官职数量的减少,一是由于分工细致化,巫的职能范围缩小,专业从事祭祀的人员大为压缩;[3](P179)二是汉代建国以后,随着儒生地位上升,巫觋受到排挤,相对数量有所减少导致。但总体上,汉代沿袭了秦代的巫觋制度是肯定的,说明官方信仰依然受到民间信仰的干扰,甚至有融入民间信仰的现象。
在官方宗教祭祀和神学体系之外,民间社会流行着大量的神秘主义信仰、神鬼之道,这些民间宗教风俗极为兴盛,大行其道。牟钟鉴等人将汉代的民间信仰归纳为以下几项:一是以易学为基础的占卜预测之术,二是在巫术基础上发展来的求雨禳灾之道,三是由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思想而延伸出来的神秘主义,四是由神仙传说引发的神仙崇拜,五是由于宗教观念所产生的禁忌。[4](P193)可以说,汉代民间信仰内容庞杂,体系凌乱。同时,汉代政府对民间信仰的管理也不严格。如《史记·封禅书》载高祖十年(前197)春天,有官员以猪羊祭祀社稷神,民众也争相以财物前去祭祀,出现“民里社各自财以祠”[5](P1380)的现象。这说明从汉初开始,由于汉代政府对民间信仰态度上较为放纵,存在着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相互共存的现象,理性与信仰似有融合。
儒学与政权的结合,形成了儒术。儒术就成了“为官之术”,或“权术”。鲁迅在民国时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儒术》,表面上是对元遗山为前朝叛将崔立写碑文史实的考证,实际上是以史来揭露元遗山、王若虚之流的儒术狡猾虚伪,善于玩弄权术,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6](P133)所以有些人就对“独尊儒术”的“儒术”产生了质疑,认为“独尊儒术”不等于“独尊儒学”。[7]无论是“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也好,还是儒学与儒术有别也好,汉武帝以后儒学地位提高则无质疑,且这时的儒学已影响至人们的生活。窃以为,儒术之所以称为“术”,与方术、道术等一样,有某种“技能”特征。儒学的这种“技能”可以理解为“为官之道”,即儒家对政治权力的崇拜。儒术改变了儒学纯粹地追求学术和科学之路,走上了搬弄权术与利用神学而形成的理性与信仰融合发展的道路。
以神学政治为主导的汉代儒家思想到底是儒术呢,还是巫术?说是儒术,是因为神学政治说到底仍处于政治层面,是国家的权力构成,儒家思想反映的是国家意识形态;说是巫术,是因为神学政治是以神学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国家体制,一切国家事务都在神学的驱动下完成,权力运作常常带有巫术特征,这时儒术等同于巫术。说到底,要么是儒学借用了巫术,要么是巫术异化为儒术,形成似巫似儒,巫与儒相通的汉代神学政治权力架构和文化模式。神学政治理论本身而言,又是儒术与巫术的结合,或者兼而有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巫术无异于儒术,儒术也带有巫术色彩。
儒术是政治需要的产物,还是儒学服务于政治的政教化变革?说到底,儒术还是一种权力信仰,这种信仰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存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还是向往用儒学理念来治理政治国家,是希望得到他人对自己的执政理念予以支持与肯定,不然也不会以“众星共之”来阐述德政的效果。退一步讲,在儒家的思想里,即使不入仕,也要做“素王”,也要“众星共之”,以达到道德修养超越政治权力的境界。这种试图以自我束缚和修身养性营造理想社会的个人状态,看似远离权力,实为对政治权力追求到极致的另一境界。所以,所谓的“儒术”就是把信仰,把宗教观念拉入儒家思想体系,形成一种神学政治理论,让儒家膜拜权力。这种方式近乎民间信仰对神祇的崇拜,只不过“儒术”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对“素王”的崇拜形式罢了。
汉代所形成的这种神学政治,是天人为中心的信仰与政治的结合,是低水平的宗教与政治融合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携带了太多的原始宗教色彩,以此为思想基础构建起来的社会政治架构必然难以适应历史的发展需求,只能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
二、神学政治文化的信仰调和——正祀与淫祀
宗法确立以后,长幼有别,尊卑有序已成为传统。《白虎通义》载:“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8](P79)这说明,国家规定的祭祀是自上而下逐渐降低档次的,祭祀对象越神圣,对应的祭祀者地位也就越高。天地祭祀成为天子独享,是天子的特权,除了天子其他祭祀天地的行为就是一种僭越。处于金字塔底层的普通民众,也就只能祭祀祖先亡灵了。地位更低一点的“异族”,恐怕就只能祭祀淫祀了。《曲礼》曰:“天地四时山川五祀,岁遍;诸侯方祀,山川五祀,岁遍;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当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8](P79)祭祀有着严格的仪式和制度,不是什么都可以祭祀的。故《汉书》言:“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9](P1194)淫祀就是除了名山、大川、五岳、四渎、五祀、祖考之外的信仰对象,淫祀不能祭祀,不在官方信仰之列。
(一)儒学影响下正祀与淫祀的融合
祭祀划分为正祀与淫祀,实际上是权力控制者为了维持官方信仰的稳固而对其他异端思想的排斥,不是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区分的标准。因此,祭祀代表了官方和民间两种信仰的融会。不过,从整个社会的礼治发展来看,有人就认为民间信仰与官方信仰分别对应为乡间习俗与正统礼制,代表了民间舆情与官方信仰。风与俗是雅与礼的源泉,正统文化几乎都是对风、俗改造和加工的结果。[10](P5)儒学以国家政权对信仰试图化名成俗,来规整混乱不堪的民间风俗。这个过程其实并不那么容易,风雅之间,礼俗之间,儒家虽有归仁之心,却难以驾驭庞杂的社会信仰舵轮。
汉代整个社会弥漫着巫鬼之风,民间信仰的泛滥,使得正祀与淫祀本应泾渭分明的信仰社会没能呈现出来。相反,正祀与淫祀趋于融合,并表现为几个趋势:一是淫祀融入正祀。泰山信仰是民间信仰中最为重要的信仰,在民间信仰中一直有较高的威望,其后被官方接纳,列入祀典。二是正祀范围急剧膨胀。《礼记·曲礼下》载:“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郑玄注:“五祀,户、灶、中霤、门、行也。”[11](P1268)祭祀何其之多,天子、诸侯、大夫、士以及平民各有所祭,非常复杂冗繁。三是正祀与淫祀的界限相当模糊。郑玄注《礼记·祭法》道:“今时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门、户、灶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厉也。或者合而祠之。”[11](P1590)谁是谁应该祭祀的,没有严格的说法和记载。尤其是庞大的神祇群体,没有专门的官员给予一一划分,至少在汉代管理并不规范。四是正祀与淫祀有时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载汉元帝时崇尚儒学,因而有一大批儒生如贡禹、韦玄成、匡衡等担任要职,后来韦玄担任丞相,与贡禹等人有意见冲突,官职被罢免。“后元帝寝疾,梦神灵谴罢诸庙祠,上遂复焉。后或罢或复,至哀、平不定。”[9](P1253)借助祭祀的合法性,权力斗争不断。五是淫祀不见得就一定“无福”。《风俗通义》载:“高后崩,诸吕作乱,欲危社稷,章与周勃共诛灭之,尊立文帝,封城阳王,赐黄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阳,今莒县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12](P394)私自“立祠”一般是民众为了纪念死者,让亡者魂有所归而专门搭建的庙堂,虽为淫祀却是人情感自然地流露。
正祀与淫祀之所以趋于融合,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汉代民间信仰本身的多样性和杂乱性,也与汉代统治阶层对正祀的管理不严有一定关系。
第一,祭祀对象是人为的划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官方祭祀什么,不祭祀什么,完全是根据统治者和国家的利益需求而定,并没有具体标准。汉代的道家思想在民间广为流传,对道家神祇的崇拜,在当时都属于淫祀范畴。蒲慕州就认为,王莽信仰鬼神与武帝相比并不更甚,但《汉书》却不以“淫祀”称武帝,与其地位不无关系,因此“淫祀”的认定常常要受主观态度的影响。汉代以后的道教,就常常用“淫祀”二字攻击一些不为道教所承认的民间祀祠,所谓“正统”,原本也只是类似的祀祠而已。
第二,统治集团对鬼神的迷信,主动祭祀淫祀。《汉书·郊祀志》载汉成帝喜好鬼神,常常召见一些祭祀和方术之人,针对这种虚耗国家财富的行为,谷永说上书极力劝谏,曰:“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9](P1260)并且举出了苌弘、楚怀王、秦始皇,以及汉代的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一大堆例子,进行反复劝说,仍是无果。皇帝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居然笃信鬼神。汉文帝就相信了新垣平的“望气之术”,以至于大张旗鼓按其所指进行封禅。到了汉武帝,对鬼神的信仰有过之而无不及。武帝崇信巫鬼仙术,常常听信方士妖言惑众,先后有李少君、齐人少翁、栾大、齐人公孙卿以长生不死、神仙方术等迷惑武帝。[13](P147~156)武帝效仿秦始皇,到处“求仙人”“采芝药”,大肆建造宫观楼台,接受公孙卿的谣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5](P1401)先后建了柏梁台、建章宫。班固《西都赋》云:“前唐中而后太液,览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滥瀛渊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14](P211)统治集团的错误引导,致使官方的信仰极其不纯,“非其所祭而祭之”,就是祭祀“淫祀”。
第三,汉代官方祭祀本身过于庞杂,过于随意。汉代国家祭祀庞杂,从天子到地方,大大小小的神祇不计其数。这些祭祀,既有对前代祭祀的继承,又有一些新的神祇出现。国家祭祀虽然仍然是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系统,但也充斥了各种神仙鬼怪,出现了复合型祭祀,信奉的神祇远比周代杂驳。[15]
第四,民间信仰本身就是官方信仰的延伸。祭祀社稷,属于民间信仰,但也是官方认可的祭祀。《礼记·郊特牲》载:“社,所以神地之道也。”[11](P1449)《白虎通义·社稷》载:“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8](P83)也就是说神祇太多,不是官方不祭祀,而是根本祭祀不过来,所以留给民间祭祀。《吕氏春秋·孟秋纪·怀宠》载:“问其丛社大桐,民之所不欲废者,而复兴之。”[16](P418)社稷之神主要是保佑农业丰收,禳灾除疫,对于大部分以农业为生存基础的民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灶神、水神、火神、瘟神等等这些关于生存、生产、生活的神祇都会受到祭拜,同时也是官方提倡并祭祀的天神、地祇、祖先的延伸。
第五,整个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还没有摆脱巫鬼信仰。儒学是以理性为起点,社会的整体走向也趋于理性。但是汉代的大统一不仅统一了政治和版图,把信仰也给统一进来。《风俗通义》载:“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12](P401)就整个社会而言,崇鬼信巫的宗教神学思潮几乎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了大部分社会空间。儒学在汉代继续发展,不得不采用包容性的思维理路接纳神学思潮,以迎合普通民众的精神需要。在这种儒学发展作用的驱使下,才导致了儒学与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的融会。可以说,正祀与淫祀之所以交错,源于儒学的兼容并包。
(二)儒学影响下的正祀与淫祀的冲突
孔子把祭祀鬼神称为“谄”,且“谀”与“谄”互释。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盲目崇拜现象,与民间信仰的功利性极其相似。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态度较为明确,祭祀不该祭祀的淫祀,就是谄谀,就是不分是非。儒家的“淫祀无福”由来已久,从孔子的态度以及后来荀子“法施于民”来看,先秦儒家态度更多倾向于反对淫祀。
究其原因,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与社会因素。汉初,黄老之术在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虽然形式上适应了社会重建与发展的需要,但其中弥漫的道家鬼神等神秘主义却因此大行其道,迷信思想得以放任和肆意滋长。西汉中期,董仲舒所推行的儒家思想又融会百家学说,从阴阳家和道家学说中汲取营养,甚至对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某些信仰方式也有接纳,这种改造逆转了儒学纯粹的理性化发展导向,而导致神学化色彩浓重。“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9](P3194)董仲舒、京房、刘向、谷永等等,都是当时为神化儒学做出贡献的佼佼者。成帝时的刘辅说:“臣闻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9](P3251)这可以说是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最简明的概括。儒学和儒家学派的神学化、宗教化,是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极大的一个变化,也是汉代迷信盛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20](P59)东汉以后,整个社会笼罩在神学思潮的氤氲之中,官方有谶纬流行,一度神化圣贤;民间迷恋淫祀,官府禁而不绝;宫廷巫蛊横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宗教大行其道,民间宗教肆意扩张,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整个社会弥漫的是巫鬼神魔,地方政府又肆意推脱,对于群众基础极好的民间信仰,一时的查禁不能够完全杜绝,终致淫祀泛滥成灾。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淫祠在民间有大量的信仰者支持,有广泛的信仰基础,因而才终禁不止,生生不息。
汉代的淫祀之风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汉末。《搜神记》载有广陵人蒋子文,生性嗜酒且好色,无所拘束,汉末任秣陵尉时,被盗贼所杀而殒命。到了三国时,东吴一带为其立庙,摇身一变成了杭州一带的土地神,且非常灵验,“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19](P57)“蒋侯神”成为东晋南朝时期最普遍的神灵之一,也是政府所说的“淫祀”之一,但在民间却香火鼎盛。在曹操担任济南国相大力禁绝“淫祀”之后,“淫祀”现象并没有根除。《风俗通义》载“惟乐安太傅陈蕃,济南相曹操,一切禁绝,素然政清。陈、曹之后,稍复如故”。[12](P395)可以说,从汉代开始,淫祀与正祀之间的对立就广泛存在,这种对立是民间信仰与官方信仰的对立,而官方信仰多为儒学所支配,本质上还是民间信仰与儒学的对立。
三、神学政治文化的衰落与民间信仰的兴起
朱玉周认为,董仲舒杂取诸子各家,在儒学中糅入神学思想,推动了儒学的神化,《白虎通义》又以儒家神学政治理论作为主导,才使得儒学真正完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建构。[21]然而,这种政治与神学结合的文化和社会形态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神学无法成为支配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特别是民间信仰作为神学思想资源无力引导社会走向前进,因此这种神学政治思想建构起来的体制与文化必然面临问题与危机。
(一)神学政治文化背后的社会信仰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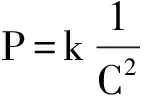
天人理论是儒学维系其神学政治理论的基石,但却并不牢固。高祖刘邦立黑帝祠,借用民间信仰完善五帝祭祀。这也意味着,利用五行之说把天神的唯一性破坏,上天一分为五。周代天帝观的天是统一的,但群雄并起诸侯割据,天的信仰土崩瓦解。从五帝信仰来说,这种分治本身就是一种王权的衰落和分化。到了武帝时期,董仲舒又聚合所有的天观念,重塑天的至上和超越。这种神学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灾异祥瑞本身是为了限制王权,但由于这种“灾异”极不确定,神学政治理论也就显得脆弱和不堪一击。东汉以后,谶纬流行,以《白虎通义》为代表的神学政治思想对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依然有所继承。这种理论在维护王权的同时也威胁王权,以“神学”构建的政治理论就显现出了巨大的危机性,为东汉王朝的衰亡埋下隐患。汉代儒学背离原儒开拓的理性之路,全面倒向神学。神学政治主导的思想文化走向衰落,主要表现在:
第一,严重依赖谶纬理论,使得儒学丧失政治吸引力。谶纬之说过多依赖民间信仰,理性主义被湮没。但社会进步更多需要与此相反的科学力量来推动,一味强调信仰,只会让政治抛弃儒学。东汉后期,社会动荡,政治危机加剧,单纯依靠谶纬之学无法抑制社会的剧烈动荡与信仰的严重撕裂。儒学谶纬化,直接导致了汉代儒家精心构建的神学政治文化与社会体系的倒塌,儒学前途未卜,令众多儒生陷入迷茫甚至绝望。
第二,汉代后期,经学队伍异常庞大,儒学发展支离破碎。汉代通经致仕,注经之风大盛,五经博士到了东汉太学愈千,“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9](P3620)儒学过于功利和烦琐,要么是当官的敲门砖,要么是登堂入室的装饰品。东汉后期的儒学已经失去活力,儒门臃肿,鱼龙混杂,经学杂而不精,基本无法为社会进步和政治的改革提供对策。
第三,儒学转化为做官的敲门砖,使得儒学自身名声极坏。严彭祖为宣帝博士,不事权贵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9](P3616)儒门不再是高不可攀,反而是名声极差。儒学的核心是“仁”,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是知识阶层寻求内圣外王的精神出路。汉代儒生则放弃了这种信仰,转而寻求一种外在的神学体系来支持儒学。儒家的理想人格、伦理道德、治世之道统统都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官场的尔虞我诈,深陷党锢之祸的无奈。可以说,汉代儒生在政治漩涡中逐渐迷失,难以自拔。
截至2016年,我国已建成城市焚烧厂249座,焚烧处理量为2.02×105t/d,年焚烧量为7.37×107t,较2006年增长550%[1]。飞灰作为垃圾焚烧副产物,由于大量富集如Pb、Cd、Cr、Zn等多种重金属,国内现有的环境法规已将它归类为危险废物。一般地,焚烧飞灰产量约为垃圾焚烧量的3%~5%,GB 16889—2008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中规定,达到浸出标准的飞灰可以豁免进入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分区填埋。
第四,社会动荡和危机加剧,让儒学信仰极其脆弱。儒学的天人神学观在太平盛世可能尚有信仰的支撑,但到了东汉一个普通人在连吃饭都成问题的社会环境中,谁还会去相信什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转而寻求能够慰藉个人心灵的信仰,高大上的天人神学自然被抛弃。《管子》载:“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22](P924)如果一种治国理念不能让人安居乐业,还有谁去信仰它?东汉儒学走向末路,不受百姓重视,表面上与佛教、道教大兴有关,实际上还是儒学自己的不可一世与神学政治理论的缺陷导致。究其根本,神学政治思想其实还是儒家试图把儒学宗教化,并利用宗教化的儒学来维系自身在政治中的合理地位。何以如此?
天人神学是儒学宗教性的表现。制度化的宗教在成教之路上一般都会建立一个至上的神,比如基督教,至上神就是上帝。儒学也以同样的方式塑造了这样一个“上帝”,可这个“上帝”却表现得极不纯正,是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世俗、道德与义理等“聚合”的产物。且这种外生的宗教化过程吸收了太多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的信仰方式,带有鲜明的入世功利色彩,加上儒学学术理性与政教色彩过于浓烈,使得以儒学为基础构建的神学政治文化生态在信仰层面上非常脆弱。
神学与政治的急速整合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至少与战国以来儒家的社会预想不契合,但却是儒家对此的一次尝试。汉代神学思潮延续了原始的宗教,是信仰传承的产物,有向宗教发展的趋势,而政治和道德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行为文化”。这种“行为文化”不是人最高价值取向的产物,或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而是人与神相处的规则,也就是吕大吉所说的“一概被归因于天之所命”。[23](P565)比如《尚书》被视为经典,实际上是以一套天命观念来制定人的“行为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观念。汉代儒学所倡导的神学政治不是把神学与政治割裂开,而是采用“天人合一”的方式试图让宗教与政治合二为一。这是一种类似于中世纪宗教神权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的政教合一,但汉代神学却又没有西方制度化宗教的权威,使得汉代的神学政治文化显得过于早熟。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这种政教合一逐渐退出历史,政治以自由、民主、平等之名脱离了神权的掌控,真正独立出来,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天人神学难以走向制度化的宗教。杨庆堃研究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发挥的功能时,综合了约阿欣·瓦哈(joachim Wach, 1898~1955)的结构性视角和保罗·蒂利希(田立克)(Paul Tillich, 1886~1965)的功能性视角,将宗教定义为:“信仰体系、仪式活动和组织性关系,其目的是处理人生面对的终极关怀的问题。”[24](P19)从援神入儒的汉代儒学来看,神学政治思想是基于儒家“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双重价值取向的中和,乃儒学竭力融会宗教的尝试。理性之学渐渐遭受儒学嫌弃,终致儒学丧失权威。可以说,作为儒生是困惑的,“信仰”之“度”稍把握不当,就易陷入价值判断上的迷失。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学者也绝没有想着把儒学发展成为宗教,对宗教的态度无非是急功近利的政治诉求和饮鸩止渴的儒学自救。东汉政治危机爆发,儒学依靠的权力支柱轰然倒塌,势必会主动抛弃神学这层外衣,回归理性。魏晋儒学理论化的发展走向证明了这种趋势的必然性。可以说,汉代天人神学绝对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制度化的宗教,也无可能让整个社会发展到神学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的局面。神学政治体系无非是儒学在汉代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维持其存在的一种手段罢了。
(二)整个社会信仰的急剧变化
从两汉社会信仰来看,神学政治理论体系的确立不但没有强化儒学对信仰控制,反而加剧了儒学自身的危机。孔毅认为,儒学之“道”的迷失,生存忧患以及形上困惑等等因素,导致了儒学信仰的危机。[25]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以来,其实不仅仅是儒学维系的信仰变化问题,实则为整个社会“信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不幸的是,由于儒学沾染权术而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趋势一,“信仰”急剧下移。从西周到两汉初期,信仰都是由国家主导,由上层社会进行认定和选择,祭祀谁,不祭祀谁,怎么祭祀,什么时候祭祀等,一系列信仰相关的事物和制度是由国家政权特别是君主说了算的。到了东汉,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官方参与修订的《白虎通义》看似权威,实则毫不严谨,是妥协了儒家各派的产物,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结果。官方信仰借助神学外壳也就丧失公信力,民众信仰转向底层,譬如来世轮回的佛教、修道成仙的道教、揭竿而起的民间宗教,等等。董仲舒创立神学政治思想体系本意是为了巩固儒学,借力政治来宣扬儒学,但过度吸收神学,把儒学引向神秘主义的泥潭反而动摇了儒学之本。事实证明,靠神学信仰来维系的儒学不可靠,难以长期稳定发展。
趋势二,“信仰”的多元化。信仰的多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信仰对象的多样,一个是信与不信的对立。东汉以来,社会信仰分崩离析。如崔寔热衷典籍文献,其思想偏向于法治。仲长统放荡不羁,主张“德主刑辅”,《后汉书》评“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26](P1644)马融会通儒道,不仅注四书五经,还对《老子》《淮南子》也有研究。东汉儒生也有立足于现实,王充与王符针砭时弊,王充有论“四失”(人、事、理、物),王符以潜夫而论“边议”(救边、边议、实边)。整个东汉儒家无法主导信仰,社会信仰是纷乱的,没有统一的认识和精神追求。儒学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局面,百花齐放的儒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阻击与挑战。
趋势三,道、佛信仰对儒学精神的超越。社会危机四伏,民众忍受着痛苦和罹难。宗教的产生都是在人们寻求现世的解脱中诞生,汉代的社会困境为宗教流行大开方便之门。儒学对整个社会控制力的大为削弱,让佛教、道教有了生存空间,也为其拯救民众的心理诉求提供了其他的选择。佛教、道教在传播初期,借助民众熟悉的民间信仰,使其融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不断填补儒学缺失留下的信仰间隙。而儒学一直试图利用民间信仰为自己的政治服务,这显然有悖政治理念初衷,最终儒家的神学政治思想被宗教意识极强的佛道超越,而儒学依然停留在一个原始的低级宗教信仰构架之内。
汉代整个社会信仰的变化说明,儒学倡导的神学政治思想体系已经危机四伏,不足以维系汉代社会多元的信仰需求,神学政治思想微弱的信仰控制力反而加剧了整个社会走向解体。同时,在东汉社会危机的推波助澜中,儒学自身岌岌可危,亟待拯救和迎来蜕变。
(三)民间信仰的顺势崛起
汉代中晚期,儒学异化,一味神化政治,大兴谶纬之学,导致儒学自身信仰危机重重,潜伏在社会底层的民间信仰随着社会的动荡和信仰的需要,开始大行其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间信仰成为道教产生的重要信仰来源。道教与民间信仰渊源极深,一方面,道教信仰与民间信仰都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来;另一方面,汉代儒学独尊,道家思想淡出国家意识形态,道教借助道家理论,在形成初期多以民间信仰的方式流传,并以此形成道教组织和教义制度。因为这种关系,民间信仰的大量神祇被道教吸收,致使早期道教信仰体系中的神祇显得杂乱无序。
第二,民间信仰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借鉴对象。两汉之际,佛教东来,佛教传播初期,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唯一可以借鉴的,只有民间信仰。佛教要融入中国社会,势必对其借鉴。佛教初期的发展模式,与民间信仰是一致的。他们在民间四处传播信仰,佛教教徒因此被称为“苦行僧”。当然,由于佛教和道教有完备的宗教理论和经典的指导,又有专业化的神职人员,很快就能脱颖而出,在具备了一定的信众以后,就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三,民间信仰成为慰藉个人心灵的重要支柱。在一个儒学信仰流失,佛道信仰并不强势的特殊时期。民间信仰离民众最近,是“唯一”的可取信仰。加之民间信仰散乱、多功利性,很容易被普通民众接纳。在东汉这样一个战争不断、食不果腹的社会里,民间信仰成了老百姓唯一的精神食粮。社会动荡,民众病急乱投医,佛教也好,道教也罢,民间信仰也行,只要能够得到心灵慰藉,都愿意去尝试。民众看似信鬼神,却又与鬼神保持着一定距离,这与儒学的理性思想影响不无关系。
民间信仰以其独有魅力,开始替代儒学成为社会主流信仰。第一,儒学信仰的极度强势与神学政治理论自身的隐患。儒学作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自汉武帝以来一直是整个社会信仰的基础和精神支柱,一直是支配着汉代民众的生活、生产、为政、为人。普通百姓从一出生,都会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道德上需要遵守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规范,生命中的大事,包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加官晋爵、出生入死等一系列的生活都需要遵从儒家一整套的礼学制度。然而东汉末年,社会危机加剧,土地兼并、统治集团的明争暗斗、生产停滞等问题日益严峻,民众信仰由此陷入一片混乱。儒学的衰落带来了整个社会信仰的危机,形成了信仰真空,信仰的争夺引起民间信仰的巨大波动。第二,民间信仰长期受到意识形态压制,但一直存在。儒学作为官方推崇的主流社会思想,不可能面面俱到。汉代是一个宗教开放和信仰包容的社会,民间信仰只要不危害他人,无损政府利益,一般都能长期存在。蒲慕州认为,在我们所了解的汉代官方宗教系统中,主要关注的是天人和谐和国家福祉,但有一项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就是人死之后的去处。秦皇、汉武、王莽之所以不断地在原有的官方宗教系统之外求长生之术,就是由于官方宗教不能为他们解决一个最大的希求——不死升仙。[27](P166~167)民间信仰复杂而多元,是一种多神信仰,官方找不到的不死之术,民间信仰则轻易就能解决,因而民众求神问卜,求仙求道绵延不绝。可以这样说,儒学填补的是国家的精神世界,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仰诉求,而民间信仰服务的是个体的期望和理想,表达的是个人的一己之私。比如,国家追求统一、富强,不受外族奴役,个人则追求财富、多子、多福,长生不死。儒学为大道大智慧,民间信仰则为小利小恩惠。
从西汉到东汉整个社会信仰发展的轨迹来看,儒学吸收民间信仰却又服务政治,两者的有机结合形成神学政治国家体制,这种政治模式有悖理性和法治理念,让民众信仰迷失,导致汉代政治衰落,却刺激了思想的多元化,引发了民间信仰的大行于世,为社会信仰的持久进步注入了生机。
[参考文献]
[1]李向平.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林富士.巫者的世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3]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4]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陈鸣树.鲁迅批孔反儒的斗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
[7]任怀国,范秀美.独尊儒术与儒学独尊是一回事吗?[J].管子学刊,2009,(4).
[8]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齐涛.中国民俗通志(江湖志)[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1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姚胜良.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M].济南:齐鲁书社,2009.
[14]龚克昌.全汉赋评注(后汉上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15]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2004.
[16]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陆贾.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贺科伟.淫祀之禁与汉代地方社会[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8).
[19]干宝.搜神记[M].中华书局,1985.
[20]丁毅华.汉代的类宗教迷信和民间信仰[A].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古代史论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1]朱玉周.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J].北方论丛,2008,(2).
[22]黎祥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3]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下)[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10.
[24]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5]孔毅.汉晋之际儒学信仰的危机与演化[J].云南社会科学,2005,(5).
[2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7]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