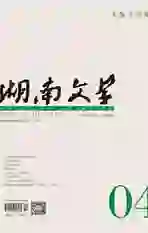天地任逍遥 河山重修行
2018-05-31凌之鹤
凌之鹤
学群的散文作品引我关注和追读久矣。
在小说为王的当代,在我们这个素以“诗国”与“散文大国”自矜的国度,散文这种向来尊贵有加的盛行文体,前因“文化”强势附体致其魂魄大乱,流行一时的大散文读来虽有“文化”知识实无文学情趣;后因“泛鸡汤化”风行遂使其形象与情怀畸变,小散文读之固有小聪明惜无大智慧,如今分明显见失宠或式微了。作为文学“先王”的散文,无论感觉派抑或说理派,在创作和阅读方面,现在似乎均颇欠人气了。学群的散文作品——尤其是那些关于天地遨游,山水行吟的美文,居然还能持续激起我的阅读热情,不仅说明散文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文体之雄魂未散,而且还有照亮我心灵的文学光芒在焉:学群散文里处处流溢的自然人文气息和思想力量,让我看到时光的样子如逝水般和着我的呼吸静静地流淌。
一、在学群散文里邂逅惊艳销魂的人性长江
某個清晨,刚从梦中醒来,我就在《散文》杂志上幸运地邂逅了学群的《长江》,并在枕畔追随着那绵延不绝的滔滔江水,痛快地流淌了一个表面平和宁静,内心却波涛汹涌、风云激荡、山水相送的上午。其实,岂止数小时?时光一闪,把酒临风,大江东去,弹指间长江一泻已是千秋万代;潮起潮落,日升月沉,花开花谢,人生的起伏跌宕,只在一念间,快意恩仇,生命已完成涅槃的传说。
这是一个人的长江史诗。这是壮美雄阔的长江。诚然,同样面对长江,古往今来的诗人、政客和寻常之辈,都会有不同的审美感受,都可能产生异样的情怀。这是长江的魅力,也是一切近于神秘的大自然造化的伟大魅力。滚滚长江,从圣洁雪山上悄然滑落的一滴,静静地形成峻峭的冰川一脉,将世间最清朗的阳光、最明媚的月光和最洁白的云朵,凝聚、淬炼而融化为一缕至性柔情,涓涓成溪,汩汩涌流,汇成一路或婉约缠绵的清唱,或豪迈狂放的劲歌。
学群的语言文字节奏舒缓,他饱含深情的叙述,宛若长江动人的自白。弦波震颤,水文靓丽,我们发现,河流与江湖卓绝而缓慢的流动成长,在漫长曲折的历险中始终获得了生命无私的温情滋润。生命之水不绝,是因为水不停地流动或变幻。江水欢快地向下奔流,江鱼却奋勇逆流而上。
是的,这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长江。这是曾经无数次打湿过中华民谣、诗歌、词曲和鸿篇巨制的长江。而这流经散文中的长江,却与俱往的文化长江趣味迥异。同样是真情流淌的长江:在学群散文的长江中,没有丝毫呆板单调,没有庄严大词,没有高谈阔论,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教科书式空洞无物的苍白说教;有的只是纯粹干净的自然情趣,以及柔美丰润的哲思颖悟。那是处子之俊逸风姿,也是处女之丰腴神美,那分明是天然一段风骚!这奔流不息的长江,在学群跌宕起伏的文思里,是水文与人文浑然相融的激昂交响,是滔滔不绝的中华文脉和千古风流人物的动人长卷,是从老子、孔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一脉相承的智慧源流,她与那从天而降的黄河一起,汇聚众多河流,在激荡中孕育了雄浑深邃、澎湃浩瀚的中华文明。江水回旋八百,源远流长的长江文化,暗藏着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玄机?人性的长江里,即使一个小小的水湾,也是如此惊艳,如此销魂:
水在这里转了一个湾,一个多美的弯,美尽天底下的曲线!要不是少妇丰满的臀,就一定是她的乳房在人的细软处扫了一把。
读着这样感性的文字,你有没有感觉到,自然原是如此性感而富有生命力?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到了学群这里,我则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是肉做的,她生机勃发,魅力无穷。
学群多次书写过长江,虽然每次书写的情感基调未变,但由长江激起的情感波澜却决然不同,其思想新意迭出,情感高潮迭起。《长江》开篇颇为诱人:“它是深海里的一滴水。”起句语气平淡却神秘自在。作家不动声色,以小说的情节和散文的自由笔法,耐心地从一滴水徐徐展开高远辽阔而深邃幽曲的叙述,一个宏大的寓言由此产生。这一滴水非凡的历程端然令人动容:它源自雪山,因风化为白云,随风雨又回归江河,有时潜入大地,惊回首,又神奇地以露珠之态挂在草尖;它或让动物喝进腹中,动物被人食后,它便融入人的血液里,或被草木吸收,涵养于绿叶碧枝。这哪里是说水之秘密,分明是借水喻人,写的是人的命运和人生的诸多变相!生命源于水,终以水的方式回归于水。我们油然感受到,在学群朴素唯美的自然生态哲学里,万物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敌我共生,物我互育,山水相依,天地相接,宇宙生命和谐同生。生命在变异中不断地以新的容颜、新的形式、新的姿态和新的物种复活或呈现:生命旋律永恒,死亡不过是假象,是一种更为神奇的诞生。生命绵延不绝,生命一直葆有伟大而壮丽的历程。贯穿万物命运的水,让人随着它时而显见时而隐匿的神秘运动,获得了千变万化的机缘。这是作家对生命的诗意礼赞和哲学慰藉,读来令人心安神远,万虑俱消。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这一滴水也可以折射出丰富多彩的人生。水土养人,水土即人。只是,因为“人是站立的泥土”,人生的结局未免过于恐怖而悲凉,“你本是尘土,终归于尘土”。
街道上尘土累积了一千年。沿着街道向前走,每迈出一步,差不多都踩在先人身上。一脚踩下去,说不定就有一只秦时的蹄印,带着战国的一段历史升腾起来,落在裤管上衣襟上,进入我们的肺和胃,成为我们的一部分。那头站在坡地上的驴子,说不定就一脚踩在哪一个王位上。一阵风顺手抓起一把,那撒播开来的,又是哪一个王妃的玉体?弥漫在空气里的,不知有多少年代多少人的衣冠……千千万万人繁浩的生活,就这样成了泥土!
——《走进时间深处》
耶和华令人绝望的谕旨确实残酷无趣;帕拉塞尔苏斯曾宣称,上帝的创造并未完成,应该呼唤人类将其未竟的创造完成——也许,凡胎肉体的人,作为造物主“创造未竟之事业”,我们已然继承造物主的意志和抱负,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一种豪迈而温和的口吻说:生命源于水,终将归于水。至少中国的诗人有如是自负。毕竟,水滋养生命,生命在于运动,“精子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那里,生命在它形成的时候就是流动的”“一个人只是一个云粒子一个水分子”。
是的,正如学群所说,一条长江,把多少东西放在里头奔流!天与地,还有时光。阳光,那是在它开始流动时候就已经融进血脉里的。从源头到江尾,再到大海,阳光一直在浪尖上闪耀。云朵曾经在雪山那里,后来又潜入水底。星星也是,萤火虫在屁股上打一盏灯笼,常常跑到江边来同它们相会。地面上站立的,飞扬的,游走的,也来到江中,在那里流淌。大地和江水一起在流。仰天长啸的李白,是被波浪高高举起的一道月光。他知道,酒无非是发过酵的月光,那里头其实收藏着阳光。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生命这么明亮。苦吟的杜甫,江水在他那里回旋八百。苏东坡自己也说过,他只是江上漂过的一张苇叶,那上面载着酒和月亮。
二、天真浪漫的“中国梭罗”,洞庭湖畔的行吟诗人
一八四五年三月底,意气风发的亨利·大卫·梭罗孤身一人,提着一柄借来的斧头,到远离人群的瓦尔登湖畔森林里建房辟地,随后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几乎与世隔绝的“完美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小屋写下了传世之作,一部崇尚和追求简朴生活的诗性散文经典,一部关于重建美好生活和探索生命秘密的沉思录。瓦尔登湖作为一种书写自然的象征,具有强烈的实验性与探索性,正如作家唐诺所指出,颇具开拓精神的“美国颜渊”梭罗本意不是为了完成文学创作而离群索居(并非隐居),而是为了探询人的生存绝对底线或别样可能。
学群显然研读过梭罗。在《马原的选择》这篇短文里,当学群置身于马原栖居的云南南糯山原始森林中,面对千年古树感慨历史变迁时,如是提到梭罗:“他住在林子里,写了一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我字用得特别多。他知道用一千种简单的方法测定生命。比方说,同一个太阳,它使我种的豆子成熟,同时照耀整个太阳系”。我注意到——学群的散文中非但“我”字用得多,“我们”也用得不少:他不仅带我们一起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我们从壮美的风景中领略中华文明,而且强有力地将“我们”带进他所面对的环境(困境),让我们和他一起感悟、反思、检讨“两栖人生”的意义,一起提升灵魂,进而抬高“生命的海拔”。
学群也曾有过自己的“林间小屋”,并以自觉的原始姿态尝试过梭罗式的野外生活。但“中国梭罗”学群的野外生活抱负并没有美国梭罗的那么宏大,目标也没那么明确。唐诺认为,梭罗所为不是止于个人而是有着普遍可能、带着某种社会工程企图的实验,他设定了目标还设定了时间,时间一到就走人;他只想验证个人独自生活的可能和人类生活(生存)必要的最低成本,所以他将生活所需之物资降至最少。在我看来,梭罗所做乃是今天社会学者们常用的田野调查,任务完成即可全身而退,归来就可能发表赢得名利的论文或报告。而学群的荒野放逐则是因其神往过上不用“算术”(算计)的生活,只想“换个环境,换种活法”,他的自我流放只为在辽阔宁静的天地和无边的孤独中寻找“天性”;他只想用“阳光、空气、水和草木”,顶多只靠简单的采果捕鱼来谋生,并且不拒绝与心爱的女人一同来“体验”这种神仙眷侣似的桃源生活。所以他远比梭罗要单纯浪漫得多,当然,也天真可疑得多。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出他如是浪漫如梦幻般的生活选择意义何在,也看不清其前景如何。在《湖洲》这篇颇具先锋小说气质的长篇散文中,学群以回忆的口吻叙述了自己的一次“自我逃亡”:我自己从自己那里逃了出来,从过去的生活中逃了出来。“我是谁,过去的生活如何”?——读着这篇寓言或童话气息浓郁的散文(故事),我们很难想象并接受它的真实性。一个来路不明的年轻男子,花了几天时间跑到一个“野生的”湖洲中央,用石头、泥巴、树木、芦苇砌了一幢屋子,然后欣然住下来,白天听鸟观云看风戏水,夜里数星星玩月亮,其意只为“摆脱在那座城市里久住的空间感”:
在无边的寂静中,我感到一下彻悟整个世界,天空、大地和其间的生命。受到大自然的神启,我开始向自己聚拢,从喧闹中分散出去的事物上向自己回归。由动物到一株植物,生命收归自身,向根部回流。我从头到脚就在我面前。我的灵魂在辽阔而悠久的宁静中慢慢发育。
这似乎是哲学家或修行者的生活。梭罗说:野地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学群也许是相信梭罗的野地救赎观的,他不仅跑到青藏高原寻求救赎,而且一度扎根于野地自我救赎。学群写道,“孤独是现代人的宗教”,“我就是我自己的宗教”。这个只知季节变换而不知今夕何夕的男子(如希腊神话中自然神一样的存在),在人迹罕至的旷野独居中“完成了自己身上的好些感觉”,后来又和一个不期而至的名叫阿欢的女子——他的梦中情人,通过元气丰沛酣畅淋漓狂野不羁的身体叙事,“完成了各自身上最重要的一道感觉”。就在那伊甸园般神秘宁静的湖洲水泽,这个周身毛孔都充满荷尔蒙的男子和他心爱的女人自由而欢悦地跨越了亚当和夏娃的原罪禁区,而且无需蛇的引诱,当然也无须神的恩准,他们似乎就是神,所以他们完全是自己做主:
在地面上,我是一棵走动的树。湖洲上四通八达的路,是我发达的根系。而她,她来的时候还是一朵花,现在,这里的地面已长进她的身体,她成了一座湖泊一块生长的土地。我把这里的春天栽种在她的里面。
《湖洲》无疑是我们(不止是学群)青春期冲动的野性投影和神圣纪念,是一个关于身体和精神孤独成长的非凡寓言。青春本身就是神话,青春期的种种怪异奇想和离经叛道都应当获得原谅。尽管我不大喜欢其中过于张扬的情欲描写,但我还是感觉惊艳:失樂园的神话在此彻底终结了,在永恒而神秘的大自然中,无须神的启示或魔的诱惑,天性未泯的男女即是乐园之主,在水一方,恍如世外的“湖洲”竟成为我们重建“乐园”的圣地;学群以诗性的语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散文的书写不动声色地越界而进入到小说的领域,——我以为,《墙》《茅草铺》《修堤》《唯有杜康》这些散文故事都可以当小说来品味。
对人生、生命和命运同样满怀强烈好奇的学群,他的书写与洞庭湖密切相关。这个远古曰“云梦”,春秋时代即称“洞庭”的大湖,无论从地理版图、史学和文学视野还是从现实存在的象征意义考察,都远比梭罗笔下过于功利和世俗化的瓦尔登湖要浩大、深邃很多。这使得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带有双重隐秘的溯源使命和探求归宿的哲学取向:一者是探寻水之源头何在,水最终流向了何处;二者则是要追问人(生命)从哪里来,死后将到哪里去。这两个问题,前者稍具理化知识即可从科学的角度解答,如今好像已达成普遍的共识(常识)。后者作为伟大的“天问”,一直是人类社会至为关切,人类也一直在运用各种智慧和诸多学科理论去探索,——但无论自以为是的远古神话、哲学、宗教甚至异端邪说,还是任何先进的前沿科学,迄今依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生命之秘密,天才或可感知一二,却不能明白畅快地说出来——天机不可泄也。活在自己不可知的伟大秘密中,这也许就是人生而存在的最朴素之价值和意义所在?
作为幸运而超脱的书写者,学群不必像梭罗那样跑到异乡僻壤的湖畔开荒盖房。他从小就生活在洞庭湖边,听着洞庭湖的风浪长大,在洞庭湖的哺育下成家立业;除却出差或壮游,他大半生都行走于洞庭湖周边,面对洞庭湖的秀美风光,在历史文化坐标岳阳楼下,仿佛一个湖畔散步的思想者,用文学的方式不紧不慢地追逐着他的自由梦想。学群熟稔洞庭湖滋生繁育的鱼虾草木,对它们的生长习性一清二楚。他对洞庭湖心存敬畏,就连到湖畔散步也要换上休闲鞋——不单是为了脚的舒适,主要是怕踩痛湖滩上的花草,伤及在湖滩上活动或产卵的小动物。他甚至会饶有兴致地观察湖边吃草的牛群,并且以《牛粪本纪》这样看似不着调实则庄重的文题,为城里人敬而远之的牛粪立传。从循环论说,他相信“牛粪是有生命”的,“一头牛的世界观,就在它的牛粪上”“牛粪是牛最伟大的作品”。
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边,学群就这样以三闾大夫的豪迈情怀和范仲淹的忧思笔调,执著而从容地书写着他特意或偶然游历过的人间繁华盛景,写下他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人生求索。这种逍遥而丰饶的游历过程,在他既是孜孜以求的修行游学,也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审美验证。他不是“归去来兮从此犬马相伴”,也不是装模作样去寻找灵魂,因为他自己一直带着灵魂。就像我的偶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中写的,关于人生这门课,每次走这段路都比在学校学得多、学得好。每次旅行都是重要的人生课。倘或不信,你不妨回头看看周遭,滚滚红尘中,有钱且闲的狂热驴友并不少见,他们怀着冒险倾向,呼啦啦阅尽名山大川,兴哄哄看遍天下美景,但他们只以“征服”为荣耀,只以“游历”为谈资,他们和自然风光相遇却不相通,他们贫瘠的精神世界里只有物欲的享乐与享受,他们任性的冒险只图一时的感官刺激而不求长远的精神磨砺。而学群是行者,也是写作者,他的写作,纯属有感而发,完全缘情而生,其行止境遇可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概而言之:“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学群的行走,有修行意念在焉,他与其说是旅游,勿宁说是游学:以天地万物为师,以壮丽河山为师,甚至以沙砾草木为师。在他眼里,雪山圣洁,江山如画,但所见诸美中,还是那些性情纯善,热爱生活的人最美。他一路悠悠走,一路细细看,一路慢慢思索。他实则在大自然中重塑自我,让自我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他就这样成为了宁静的大自然中行走的一道人文风景。
学群的写作,是斯多葛派哲学的修行之道,他用写作来修行,所以他实质上是一个行吟诗人,一个逍遥的修行者,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一个健行的思想者;就像他所赞赏的行为主义诗人冯春发:“他用他的双脚,用整个的生命在大地上写诗”。他用散文向自然致敬,对世界说话。
三、学群散文艺术的缓慢之美与思想之魅
说实话,就时间和效率而言,在这个凡事追求“跨越”,仿佛满地破镜似的“闪”“碎”时代,阅读学群这样节奏缓慢的纯文学作品,就像游览壮阔的风景——波澜不惊的大海或苍茫雄浑的群山,心不在焉仓促走过,那是无法欣赏的。好风景就在眼前,你可能熟视无睹,习焉不察。也许有那么一天,疲于奔命的你忽然停下来,安静地面对周遭的一切,你就会惊奇地发现,动人心魄的美景其实从未稍离:凌乱的书桌也有混乱的秩序,桌上的文竹宛如绿烟缭绕,窗外云淡风轻,震耳欲聋的高分贝广场舞原来竟是老年生活中的嘹亮高音,远处传来的建筑噪音竟然也洋溢着摇滚乐的品质,……原来,我们的人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不堪,生活并非永远一地鸡毛。彼时,你已成为了一名虔诚的生活修行者。
然而,期望“悦读”学群的散文是有困难的。正如汪惠仁先生所言:学群着力看取并记下的地方,不一定是别的人生可得“陶冶”处;节奏也不一定是别人能适应得了的,学群是缓慢的实践者——他在苍茫间缓慢甚至是迟疑地移动着。
汪之灼见乃知音之论。学群的散文,总体上叙述节奏是舒缓的(那是相当的慢,性急之人估计读不大痛快),表象上一如风平浪静的洞庭湖,内里却是深水潜流,波涛汹涌,有时星光闪烁,令人神逸思远;有时风起云涌,一如隐秘的激情突然暴发,使人遽生“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之幻景。
捧读学群的散文,无疑可以让人慢下来:那样细节历历在目,语气平和舒缓一如聆听佳人耳畔朗读性情文字(有些精妙的文字是纪录片风格的,是高清慢镜头式的特写)——不是疾驰的轿车,也不是一闪而逝的高铁动车,甚至不是风中兰舟鞭下快马,它们只是闲庭信步的散漫姿态,是让灵魂跟得上脚步的行走。学群提醒我们:人生很长,何必急走狂奔?人生又很短,不宜走太快。快是偶然,是非常态,慢是自然,是常态。在世俗中行走,只有与灵魂同行,才能行稳致远。
学群的散文是纯散文,是雅正的非文化非鸡汤美文。他走的是中国传统散文的正道,叙事清晰畅达,说理明白易懂,抒情性和思辨性水乳交融,婉约与豪放如山水自然相间,赞美或批判,强调的是“我”的内心感受,书写的却是“我们”共有的情怀与经验。学群的感情丰厚而诗意缠绵,化为笔下“三叩九拜”的曼妙文字,恰如漫天细雨飘忽,又似满眼落英缤纷,细腻绵密,甚为可观。那字里行间,有人的呼吸,有草木滋生的声音,有天地的辽阔,有江河奔流和群山蜿蜒,有星光闪烁。
阅读学群,最好在晴朗的早晨(以班得瑞音乐为背景更妙),打开窗子,能看到辽阔的原野和远方的群山,这样才能回应他散文里的天地气象;星光灿烂的夜晚,也适宜读学群,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文字里的水声、风声,蛙鸣虫吟,牛羊吃草的声音或它们慵懒的喘息,还有作家热烈的心跳,——他的感慨,诚能唤起我们心底幽闭的同情与叹息。作为凡人,我们的心灵疼痛或幸福原来如此相似,只是,這千年一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固然都轻轻地发出过,却不能像作家那样自然而优雅地诉诸于文字。
对人生和生命满怀热情的学群,有着格外独到的敏锐和睿智。他知道这不是一个英雄时代,这更像一个灌木时代(其实是一个野草丛生的时代),存活与发展,都不必过于高调,相反,要学会降低一点高度。所以,他坦承,“我是一只思想的蚂蚁,在寻找食物的途中停下来,思想一会儿,又接着匆匆忙忙往前爬”。在面对横贯宇宙的巨大寂静面前,学群也碰到了无数先哲大贤追问的人生难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学群意识到,人类已经到了好好问一问自己的时候了。人凭借技术创造了丰盛的物质,人甚至进入了创世主才能进入的领域。问题是人还没准备好。尤糟糕的是,这个时代的人很少有信仰,我们不再相信来世,不再拥有星空、大地,也没有闲暇和宁静。“到处都是物资,到处都是物资带来的堕落。”学群不无偏激而愤怒地说,“技术使人类的鄙陋和罪愆成倍地放大,人类的精神比任何时候都要鄙陋不堪!”“我们是精神上的爬行类,还远没有完成自己的进化”。他多次感叹,“人是一种会背叛自己的动物”,“我们与自己之间,相隔了太多的东西,许多人终其一生无法横渡,一生也抵达不了自己”。他在《两栖动物》一文中抱怨各种人际网络对我们的野蛮牵扯,“……有时你不得不让人拉着,去做一些明明毫无意义而且了无生趣的事情。为了生存,为了在人群中活着,你得忍着”。他因此甚至情愿尝试着像野兽一样自由行走:
人的痛苦莫过于自己的生命不能归于自己,不能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头野兽就是它自己,人却很少这样。人似乎更多的是别的什么,甚至根本就不是他自己。
——《生命的叩问》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活在名缰利锁下,活在一群亲友和熟人中间,被各种名义挟持着,假装欢喜地干着胜任却不愉快的事情,费时耗力地表演着无聊透顶的人间喜剧,成天疲于奔命,陷在一大堆人情世故中痛苦地挣扎。我们眼下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什么时候,我们已温驯如斯,不敢也不愿意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我们宁愿让愚蠢的权威牵着鼻子在危险狭窄的荆棘小径上爬行,也不肯往宽阔的大道上望一眼。我们每天一本正经地做着无用功,像西西弗斯用力将巨石推上山头又无奈地看着它滚下来。我们假装服从假装拥护,活得如此卑劣如此反讽!人啊——还不如像动物那样真实地活一回:
真的羡慕那些在这里游走的生命:不用开会,不用呼吸污浊的天空,不用忍受噪音,不用在不想哭的时候做出一副笑的模样,不用去做那些你不想做的事情,坚守简单而纯粹的生命。真想变成一头羚羊,一匹野驴,或者哪怕一只兔子,用博大的心脏从这里走过,走过自己的一生。饿了,就低下头,伸出舌头撩起一把草,用嘴唇捉住,一扯,把大地,把季节,把遍洒阳光和雪花的天空一起扯动。
——《天地有大美·可可西里》
学群的每次行走,都是耐心地阅读自然之书,是虔诚地唱诵自然的圣经。他数次走进腾格里沙漠,只为从大地的童年找回自己孩提时代的星空;他登临珠穆朗玛峰,只想接近天空触摸灵魂;他在极高处,在亲近神灵的地方看月亮、数星星,看风自由吹过红尘的样子,看雪山看流云,只为让灵魂皈依自然。置身于辽阔、深远的大自然怀抱中,学群无数次地慨叹,无数次地反省,人的一生(生活)所需诚然不多,最基本的无非是“面包、水和盐”;人的生活其实可以简洁干净:
再没有一种屋居像窑洞一样深入大地,使人与土地融为一体。人像植物、像穴居动物一样,把家栽进了泥土。走进窑洞,就像回到了人类的根部。进门就是炕,泥土做的床,足可以睡下一家人。炕过去是土灶。炕灶是连在一起的。吃饭、睡觉和做爱,人生所必需的几样东西,全都在这里了!从半坡村到西周汉唐,繁华与轰轰烈烈从黄土表面漂过,最本质、最核心的几样东西,在这里在地层上扎下根来——人类几千年的生活就这么简单,一桩桩算下来,用不了五根手指!
——《黄土》
面对图像统治的虚无和世间惊人的相似,眼看车流滚滚,在这个信仰和诚信稀见,宗教失效的时代,学群更多的时候则是自我省悟。多少年来,我们追捧的是权势、财富和声誉,却忽略了一直身处其中的大自然。一些只会买卖土地的官僚,将良田沃野和植被丰美的大地,从国家战略红线保护区里巧取豪夺出来,用钢筋水泥建大城小镇,建高楼豪宅,建广场大道,将稻花香和蛙声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彻底驱除,将森林和草地、水泽从我们眼前活生生填没。身陷都市的学群,对此深感郁闷却毫无办法,他固然曾发出响亮而近乎“天行健”的豪言:
不要以为这是些无关的事情,正是她们的美丽把我们打动,我们一下觉得世界是这么美丽,我们不再甘于日复一日地碌碌无为,我们得走很远的路,做出很大的事情来,对得住这个世界,对得起她们的美丽。
——《一个人与一条河》
让人扼腕者,一番书生意气的慷慨激昂过后,他却选择将自己关起来:
大白天我去上班,白天就像是我的黑夜。在这里,我有些像鬼,我只是我的异己,我的另一个版本。夜晚就像是我的白天。回到我自己的房間,我才是我自己。只要关上门,我就生活在云端。在桌上,在床头,随手翻开一本书,就可以跟一些伟大的人物在一起。抬起头来,我可以看得很远,透过墙壁,穿越车流和人群,我看到长江在辽阔的大地上奔流,星辉在亿万年的时空闪耀。
——《两栖动物》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典型的后浪漫主义者或“两栖动物”,一个和学群一样经常沉沦于现实梦魇中的修行者,我并不赞成学群带有意淫取向的乌托邦式生活。我想对学群说,既然相信写作可以拯救自我,那么,写作也应当可以拯救他人(至少读者)。天地任逍遥,河山重修行。一个乐于在天地间逍遥修行的写作者,他的抱负不可以止于“桌上”“床头”的美妙遐想,他确实应当而且必须勇敢地引领有心人(至少读者)走很远、做大事,最终对得起读者,对得起带给自己美好生活的“写作”。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