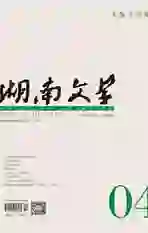送葬记
2018-05-31黄孝纪
黄孝纪
二月初五
没想到岳母走得竟这么快。
晚上八点刚过,我的手机响了,妻子的号码。“大哥打来电话,妈妈死了,就刚才。”妻子喉头发涩,我也一下愣了。此时,妻子在湖南永兴县城,我在浙江义乌市,大妻嫂在深圳伺候才几个月的外孙,二妻兄一家人在广东中山市打工的出租屋,只有大妻兄大妻姐二妻姐仨在北岸村一间旧瓦屋里,陪着刚刚离世的他们的生母,我的岳母。
妻子下午才从北岸村返回县城,她原本也想陪着住一晚,但同去的涯儿闹着要回家。妻子向我描述当天看到的状况,我觉得岳母应该还不会很快就走。她一大早火急火燎到菜市场买了一大包肉鱼蔬菜,又到超市买了两大包成年人纸尿裤,约了她大姐,一齐从县城出发,坐公交,搭出租摩托车,两个小时后,赶到了村里。其时,母亲躺在床上,面色如常,像熟睡了一般,不能言语,不能进食,偶尔右边的手脚能动一下。妻子俯身喊了几声妈妈,涯儿连喊了十几声外婆,一溜泪水倏然从岳母眼角滑下。他们兄妹给母亲擦洗了身子,换上干净的衣服,撬开牙关,喂了几调羹温开水。
岳母是昨天突然出的事。那时我刚吃过午饭,接到妻子电话,说妈妈摔着了,是邻居发现的,情况很严重,景和二妹已经赶过去了。
岳母正月十七在县城刚过了七十七周岁。三年前,岳父去世。他们一共有两儿三女五个子女,老大景和早年从县烟草公司买断了工龄,现已办理退休;老三二妹从煤矿职工医院退休多年。他们两家与我家都在县城买了房子,住县城。老二细妹前些年从农村来到县城,找了份环卫工的活,租住在她所清扫路段的一间民房。只有老四景亮,带着老婆孩子常年在广东打工,在县城郊区煤矿沉陷安置区买的一套指標房,打算今年装修入住。岳父原是国营煤矿工人,在世的时候,他的退休工资足够老两口在农村生活的日常开支。他去世后,我们五家一合计,用他的积蓄为岳母买了一份煤矿职工配偶政策性保险。这样,做了一辈子农活的岳母,在晚年还拿上了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这三年来,岳母大多数日子一个人居住在村里的老屋,她说住村里习惯些,四处走走,跟老人聊聊天,弄了三顿饭,晚上大门一关,一天就过去了。为了随时了解她的状况,我们给她买了一个老年手机,她不识字,好不容易才学会了接电话。过节过年或者有病痛,她才会来到县城,在我们三家住上一阵。这次摔倒,她从县城回村还不足一个星期。
我电话询问景和哥。“这次可能不行了。”他说:“妈妈现在是左边手脚不能动了,不停呕吐黏液,屎尿在身上,不得了。”发现岳母摔倒的是前排老屋的一个老人,早上九点多钟,岳母吃了早饭,下来跟她聊了一阵。十一点多钟,她上去找岳母,喊了几声没答应。进屋一看,吓了一跳,岳母靠墙瘫坐在卧室门边,耷拉着头,已不省人事。她慌忙喊来了周边的老人,七手八脚把岳母抬放在床上。住在后排老屋六十多岁的堂兄景晴哥,赶紧打通了景和哥的电话。
我把这一情况,电话咨询了我的一个医生同学,又向我的做了几十年乡村医生的大姐说了,他们一致的判断是脑溢血,已导致半边瘫痪。“严重的话,难挨过三天。否则,就是救了过来,也是瘫痪。”我的大姐甚至下了断语。
我将了解到的告诉景和哥,他说刚才叫了村医来看了,村医摇摇头走了,不肯打针用药。我问是否考虑叫救护车到县城去抢救?他担心妈妈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了,那样的话,死在外面进不了村,更麻烦。“先观察两天看看。”他说。他是家中长子,主见自然由他来拿。
事后谈起二月初四夜里的事,二妹可吓坏了。二妹今年五十岁,这栋残破不堪的瓦房,是她十几岁时建的。这些年来,好在岳父母一直居住在这栋老屋,偶尔维护一下,安全尚无大碍。与之相邻的两栋瓦屋,因户主带着家人多年在外打工不曾回来,已经坍塌得不成样子。村里夜晚黑得早,周边都是老房子,黑咕隆咚,人声静寂。她和大哥临时在母亲卧室隔壁房里铺了一张床,两人轮流看护,一盏昏黄的白炽灯下,她值下半夜。“妈妈的右手不停地往空中挥舞,好像要抓什么一样。我当时想,是不是爸爸来喊她了?全身一下就起了鸡皮疙瘩。”二妹说,妈妈的手又朝头上摩挲,竟然还在鼻梁上夹出了一条红痧。这些昏迷状态下的奇怪动作,令二妹吓到瑟瑟发抖。
我想,这一定是岳母在本能地挣扎,她脑袋里血管破裂,痛苦不堪。
春节前后
几姊妹有点抱怨大哥景和,说要是他早几天能及时定下来陪护母亲的事情,让邻村那个老人过来,与母亲吃住一起,就不会发生这个事了,至少,即便摔着了,也能及时发现,呼救。
除夕前大约一个月,岳母从村里打来电话,说手脚无力,病了。景和哥将她接了来,送到县中医院住院治疗。经检测,内脏正常,没有大碍。岳母享受医保,需个人承担的那一部分医疗费用不成问题,医院乐于接受这样的病人长住,每天上午测测体温量量血压挂几瓶盐水葡萄糖液这类营养药物。作为家属,也愿意当做疗养一样,让她住着,尽量恢复健康。只是几天后,岳母就闹着要出院,原因是她跟同住一室的老太太发生了吵架。听妻子说,那老太太是个很慈祥的人,这些日子她去探望,老太太都很有礼貌,多半是妈妈小心眼。
岳母出了院,妻子将她直接带到了我们家。妻子这么做,自有道理。这个时候,景和哥只是他一人在家,大妻嫂新燕一直在深圳,帮着她大女儿带不满半岁的外孙,他的二女儿也在深圳工作,儿子在昆明读大学。二妹的独生女刚生了儿子才几天,她正忙着护理。细妹租住的是旧房,简陋狭小,既不便,岳母也不愿意去。考虑到这些因素,元旦节回家的时候,我就与妻子特地买了一张1.2米宽的实木新床,靠窗安放在我的书房,将电脑桌移到了阳台。往年春节前后,岳母来我们家住,儿子就要让出他的床铺,跟他姐姐挤在一床。如今女儿大学快毕业了,儿子也上初中了,姐弟不愿再睡一床。而岳母睡过的床铺,有一股浓烈的老人味道。
岳母已经十分迟钝。我春节在家的日子里,感觉她比去年又老了不少,偶尔摘下毛线帽子,头发已然雪白。她原本身材高大,现在走路的时候,左手往后靠在腰间,背驼得像一把曲尺,脚步细碎。她不爱活动,早上起床后,除了洗脸和上厕所,就坐在沙发中央,掀起电烤火桌上的罩布往身上一拢,整天不会起身。有时我们上街,妻子顺口喊一声妈妈你去不去?她就笑着说也想走走。下楼梯,走路,她都需要搀扶着,驼着背,走起来十分吃力,缓慢。她时常说,腿没有力,拖不动。这一年来,听说她已经摔倒了好几回。妻子说,前几天在我们家上厕所的时候,也摔过一次,坐在地上起不来,听到喊声,才赶紧跑来拉起她。她的记忆力严重萎缩,刚刚发生的事,说过的话,一下就忘了。
除夕前几天,景和哥原本冷清的家,又热闹起来,全家人都回来了,而且大女婿、外孙也来过年。景和哥来到我家,把岳母接了去。
正月初一,按照往年的惯例,我们在城里居住的两家,一同到景和哥家拜年。酒席间谈到,过了元宵节,新燕嫂依然要去深圳带外孙。景和哥也想去,毕竟他退休无事,家人又多在那边。但岳母的安置不解决,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这些年来,景亮哥身体差,做了两次心脏搭桥手术,每月要药物维持,如今好不容易在广东进厂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要他家照顾岳母,显然靠不住。细妹也困难,一个儿子身体有严重缺陷,常年吃药。她一个人从农村进城,孤零零地多年坚持这份辛苦卑贱又薪水微薄的环卫工,就是冲着这工作买养老保险,指望老来有一份生活来源。平时,岳母有病痛,需要摊派费用,我们也从不让她承担。说来说去,方案有三个。其一,由我们在城居住的三家轮养,一家一月或一季;其二,进县城养老院;其三,依然回村,在瓦房里砌一个卫生间,从村里雇一个人专门照顾。后两个方案所涉及费用,除细妹外,四家平摊。我提出并赞同第一方案,他们更倾向后两者。吃过午饭,太阳晴好,我拿出相机,建议大家到楼下的草地上照张全家福。刚站着拍完,岳母一个踉跄,又在草地上摔倒了。扶她起来坐在花池边,她揉着膝盖,表情痛苦。
接下来的日子,岳母有开心,有笑容,有满足,她看到了儿孙满堂,家道兴旺。让她牵肠挂肚的二儿子景亮也带着家人来看她,得知他如今不打牌赌博了,有了三千元的月工资,她无比欣慰。岳母也有忧伤和落寞,在短暂团聚的日子里,她嫌大儿媳新燕整日泡在牌桌上,或者出门打牌至深夜方归。她心疼钱,爱唠叨,数落,以至于婆媳间相互看着不顺眼。在她的二女儿家,她抱怨不跟她说话,让她一个人嘴闭得发臭,要么一说话就噎她。在我家,她说住着安逸,可我的儿子又不爱叫她。但她似乎从未反思过,我的几个儿女,自出生以来,她从未带过一天,也从未吃到过她主动买上门哄他们嘴巴的哪怕一粒糖果,以致缺少了婆孙之间骨子里的亲热。她渴望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宠着,顺着,可每一家都不能令她完全满意。为此,她偶尔会扯起衣角擦眼,说老人呢,还是早点去了好。
我是元宵节几天后,在义乌上班时,接到妻子电话,说岳母去了县养老院。早几天,他们兄妹几人同去考察过,生活设施挺完善,环境也幽静,每人一间居室,住了不少老人,有的甚至是老两口。每个月的生活护理费是一千元左右,用岳母的那笔“退休工资”刚好可以支付。据说岳母居然被做通了思想工作,愿意去住一两个月试试看。我当时把妻子数落了一顿,我说这是你们兄妹最不该做的一件事,会让老人多么寒心!果然,当天午后才交了费把岳母送去,傍晚养老院的电话就来了,说岳母死活不肯住,闹着要走。没办法,景和哥只好把岳母接回了家。
经过这次倒腾,岳母坚持要回村居住。担心她生活不便,有个闪失,几兄妹最后决定平摊出资,在村里雇请一个身体健康年轻一点的老人同吃住。起初,本村一个老太太愿意干,工资是一千五百元一个月,隔天后,可能是在她家人的阻止下推辞了。最终,细妹从她村里找了一个老人。那老人六十多岁,十分乐意,并几次打来电话希望尽快说定这事。景和哥犹疑着,说过几天他回村里一趟,顺带找人在瓦屋砌一个卫生间。
二月初三,妻子给岳母打了一个电话,问吃了饭没有,交谈了一阵。这一天,是岳母从县城回村的第五天。
隔一天,岳母已是阴阳两隔。
二月十一
我们一家人乘坐的两辆出租摩托车在北岸村一条水泥巷道停下。从通乡公交终点站三塘乡政府门口到这里的车费一共是十六元。我拿着伞形的花圈走在前面,妻子女儿儿子后面跟着。两旁是墙体剥落的红砖旧瓦房,前方一眼就能看到那栋熟悉的房屋。二十多年来,这块被称为永兴县的西伯利亚的高寒山区贫瘠边地,我不知来过多少次。就在去年的中秋节,我们还一同来到这栋熟悉的老屋,与岳母一同过节,分享阳光下柴火做的饭菜和欢乐。不同的是,此刻,屋前的街檐搭建了塑料布雨棚,扎了白色纸花,有戴着白孝的人在门口进出。
大门两侧贴了白纸黑字对联。厅屋被分成前后两堂,隔着用木头临时搭建起来糊了白纸的屏风,上面写着诸如“音容宛在”之类的毛笔大字,挂着大小不一的纸花,两侧留有门洞。岳母站在屏风前旧方桌上的相框里,她戴着那顶旧毛线帽子,眼光平和,皱纹分明。她的身边是一盆沙土,插了五色彩纸做的古装小人和幡旗,面前一个小香炉,青烟缭绕。方桌两旁,条凳上各坐两个师公,中老年人。他们是附近村庄的农民,此刻身份转变,戴着黑色道士方帽,外套一件脏兮兮的红色团花长袍,一人吹喇叭,一人拉二胡,一人敲小鼓,一人拿着话筒,翻着桌沿上的手抄书,嘴里长一声短一声唱经,如同戏台班子。嘈杂的声音将屋子塞满,通过扩音喇叭,撒向整个村庄和天宇。
我手上的花圈已被人接去。跨过门槛,我们在桌前地上的稻草蒲团跪下,三叩首。起身,走进后堂。岳母的黑棺木瘦长,搁在两张条凳上,竖放厅屋中央,棺盖上骑一只白纸扎的大凤鸟。厅屋一角放一大盆,里面满是黑色的纸灰。我们蹲下,燃烛点香焚纸。火光烟尘之中,妻子在小声地招呼岳母岳父来多领钱,并告诉他们,我和女儿昨天分别从浙江和天津赶来了,女儿刚考上了研究生。
厅屋里人来人往,十分拥挤。南侧两间房子原是岳父分给景亮哥的,他一家人经年在外,关门落锁。不过此刻,屋门敞开,里面生了火炉,摆了桌凳,开了床铺,箩筐碗筷热水瓶水桶摆了一地,一派凌乱。二妹从门口出来,笑着向我们招呼了一声,抱怨随即脱口而出。她说大礼堂的厨房是今天才进场,早两天一直是她在屋里弄几桌人的饭菜,她们两妯娌又不管,天天为着钱的事,为着请人买东西的事情争吵,烦透了。
我們来到北面的房间,这是分给景和哥的,岳父母在世时一直住着。外面一间摆了一张方桌,放着墨水毛笔。堂兄景维正在折裁白纸,他是村里毛笔字写得最好的人,也是刚从广东打工的厂里请假回来。地仙侯道松老哥戴着老花眼镜在翻看一本毛了边的旧书,他是隔壁侯家村的,是新燕嫂的亲长兄。我们径直走进里间,新燕嫂正在裁剪白布,或长或短,用来戴孝。她是王熙凤式的人物,性格开朗,善于交际,这场白喜事,她是总管。见我们一家人都来了,她很高兴,拿了孝布,给我们一一戴在头上。并笑着告诉我们,她是二月初六从深圳赶来的,她的三个子女丽丽平平卫卫,要今天下午才到。
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见我们还没吃,二妻嫂小英带我们去村礼堂。一路上,她叽叽咕咕,说新燕嫂事事专断,听不进她的意见,很多东西买得贵,尽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礼堂在村边,毗邻村小学,宽敞明亮,是前几年集资兴建的。里面摆了几十席空位,一律是暗红的八仙桌,几个老人在收拾。我们潦草吃了一点剩饭剩菜。
北岸村如今宗族思想严重,各房族不团结。一个房族的白喜事,别的房族一概不参与。除了师公、地仙和乐队需要请外村的专业人士,包括厨房、礼客、放鞭炮、抬棺材种种事务,全靠本房出工出力。岳母的这场白喜事,由本房的雄英哥为首担任礼客师,堂兄景晴哥的儿子海勇做他的助手。雄英哥多年来在郴州做着防治白蚁蟑螂的生意,这次他和老婆特地开了车回到村里。
下午,我们几个稍懂文墨的人,围坐一桌,专门商量明后两天主宴席及接待岳母外家人的礼仪。雄英哥说,他从没搞过这样的事。海勇是年轻人,更加不懂。他们一致要我出主意,说我来自大村,礼仪之乡,懂得的。我自然不能推脱,将我们村沿袭下来的那套接客仪程凭记忆列了出来,又参考了大家的共识,进行增删调整,力图周全简练又符合乡俗。最后誊写清楚,让雄英哥反复演练了几次,并提醒他声音洪亮,语速平稳。雄英哥十分满意,他笑着说,以后这套仪式,要作为规制在本房族中固定下来,传承下去。
二月十二
像一个巨型棋盘,又像智力游戏书上的迷宫,村前月塘边的小禾场上,石灰线画出的这个招魂道场充满了神秘。四方各一入口,里面回环往复,每个转折处另画一小三角,内置一个蜂窝煤球,插一面三角小旗,由五色彩纸做成。中央一张旧竹椅,端坐岳母的替身,她是稻草扎的人形,穿了过于宽大的衣裤,戴着帽子,白纸蒙面,画了眉目,粗略一看,令人心惊。
上午的这场仪式,村人叫窜黄河,据称是为亡人解罪,主角自然是那四个师公。为首者手执一面绣有阴阳八卦的金黄长幡,在前面引路,一面唱经。另三个师公也各执法器,敲小锣,唱经应和。大妻兄景和双手抱着岳母相框紧随其后。我们一干后裔子孙数十人之众,头戴白孝,手拿一根或两根糊了细丝白纸的哭丧棒跟着,从道场的一个开口处鱼贯而入,低头徐行。师公在替身前稍停,作揖,我们也一一如法炮制,表情肃穆。一些三五岁的孩子,觉得有趣,嘻嘻哈哈地笑着,甚至拔小旗,用脚踩踢煤球,被父母牵了手警告,或者带到场外玩耍。转圈,循环往复地转圈,不明就里地转圈,逐一从四方开口入,从不同的开口出,小小的禾场上摩肩接踵,首尾相连。道场外的老瓦房檐下,站着几个形容佝偻的老头老太,他们与池塘边仅存的一棵枯了主干的老柏树一道,木然地看着我们漫长的表演。
临近中饭,我摘下头上的孝布,带着家人来大礼堂吃饭。礼堂门口的公路边上,站了一群人,在大声吵闹。雄英哥显然正生着气,满脸通红,他大步走向那辆贴着灭杀白蚁蟑螂广告彩纸的黑色轿车,拉开了门,嘴里气呼呼地说不干了,要走。他的老婆,一个穿着时尚的中年妇女也在大声数落:“七十多岁的老人,都在厨房里做事了,还要怎么样?他们都在说了,别人家有事,你们家一个人也没来厨房帮过忙。”旁边,新燕嫂子也火气正旺,高声说话:“塑料碗就不得买!不是小气几百块钱的事。那么好的不锈钢碗,摆着几好啊,就硬是要另外买。厨房里二十多個人,两餐饭的碗也洗不出来吗?”
我们走过去,好言相劝。这时,来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在大家的劝解下,生气的几个人都平和了下来。事后我问新燕嫂子是怎么回事,她说,村里的大礼堂,本身就配置了几十桌公共碗筷,饭碗一律是不锈钢的,厨房里的人嫌难洗碗,要求今晚和明早两餐正餐用一次性的塑料饭碗。房族人少,连七十多岁的老人都来做杂事,确实辛苦,但是厨房里已安排了那么多人,洗两餐碗还是没有问题的。“雄英两口子闹着要走,他们走就是了。他们家也还有老娘,我看他们以后一家人能把老娘背上山不?”新燕嫂显然余气未消。
下午两点十八分,是地仙选定掀棺的时辰。我以为,掀棺是一项需要革除的陋习,极不卫生。这项旧习的起源,据说是为了给远道赶来的亲人见亡人最后一面。根据地仙的推算,对猪马两个生肖年出生的亲人有冲克,需要回避。我让女儿和儿子也到一边去,在我看来,让孩子们在记忆中保存外婆生前的形象,比记住一具逝去多日的遗体要好。黑色的棺盖被几个成人掀开,抬放在墙边。众人围拢过来,岳母的三个女儿扶着棺木号啕恸哭。岳母躺在狭小的棺木里,戴着那顶旧毛线帽子,身上盖着一床绿缎,嘴唇收缩,露出几颗惨白的门牙,已略显狰狞之状。新燕嫂探手扯了扯绿缎,盖住岳母的嘴巴。我刻意嗅了嗅空气,庆幸的是,这里地处高寒山区,尽管岳母去世一周,尚无明显异味。棺盖重新盖上,钉上铁钉,缝隙处刷了浆糊,贴了白纸条。
乐队班子也请来了,厅屋内外更加喧闹和拥挤。明天是出殡的日子,远近的吊客正陆续来临。鞭炮声,喇叭声,锣鼓声,哀乐声,不时响起,经久不息。雄英哥带着他的礼客班子,形色匆匆,忙里忙外。吊客来了,引至灵堂前行跪拜礼,扶起长跪灵柩旁的孝子孝孙,之后到账房上礼金,领取纪念毛巾,安排妥住宿的人家和床铺,带往礼堂就坐。
岳母外家人的到来,迎接的礼数最为隆重。孝子、礼客班子、乐队要出村口候迎,一路鞭炮不断,乐鼓齐鸣。岳母虽然是独生女,外家人依然来了数十人之多,花圈开道,抬着三牲奠仪。一时间,灵堂里人头攒动。举行祭奠仪式后,一行人被引领到礼堂,在那里,礼客班子还要专门为他们摆开联席,举行敬酒和挂红仪式。
开餐的礼炮在礼堂上空炸响,夜色里开放着一串串夺目的焰火。礼堂里灯火通明,座无虚席,人声嘈杂。
突然,扩音器里传来洪亮的男高音:“肃静!”我一听,正是雄英哥。
“奏乐!”
“白鹤仙师升座——请!”
……
雄英哥正按照昨日制定的那套仪程有条不紊地司仪,中气十足。
晚餐菜肴丰盛,野猪肉,刺猬肉,羊肉,牛肉,全鸡,全鸭,肘子,团鱼,墨鱼,草鱼,泥蛙,十几个荤菜,碗大量足,堪称奢华。
夜里九时许,灵堂里举行家祭,行三献九跪之礼,献香献酒献牲。此时,暴雨大作,雷鸣电闪。
二月十三
冷寂的深夜突然传来礼花的鸣响,“嘭,嘭,嘭……”急促,震撼,直捣梦境。
我从床上爬了起来,穿了衣裤,拿着手电和雨伞,出了借宿人家的门口。此时是凌晨二时许,距离出柩的时辰还有十几分钟。暴雨已经停歇,漆黑的夜空飞着毛雨,空气潮湿,独自走在没有鸡鸣狗吠的旧村巷还真有些胆怯。
灵堂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睡眼惺忪的人,有的在拆屏风拆雨棚,扯掉白纸纸花白对联,将一根根卸下的木头堆在厅外街檐下。香案木桌已经撤下,花圈一律移到了门外。厅堂一下子宽阔了许多,高功率的电灯泡将浓密的黑夜驱逐出门,阻止在街檐之外,单将岳母黑亮的棺材突兀呈现。众人在棺材两端套上了手臂粗大的棕绳,随着地仙一声吉时已到,将棺材抬上了肩膀。
鞭炮开道,鼓乐齐鸣。棺材缓缓出了厅屋,在曲折逼仄的村巷里移动。手电,矿灯,停电宝,发出惨白的亮光,一同撕开浓墨的夜幕。转折,下台阶,再转折,淋湿了雨水的石板小径,小心翼翼引导着嘈杂的队伍,向着月塘边画了招魂道场的小禾场行进。
棺材在禾场的中央放下,稳稳地搁在两条长凳上。此时毛雨已无,夜风浩荡。喧嚣与灯光渐渐散去,黑夜裹着黑棺材,将孤独的岳母紧紧包裹。
早晨,隆重丰盛的早宴端上最后一道菜,孝子在哀乐中拄着哭丧棒已逐桌拜毕。在村礼堂通往月塘边的路上,吊客络绎,他们来送岳母最后一程。
出殡的时辰定在九点多钟,墓地就在村庄对面的小山包,中间隔着一垄水田一条溪涧,一两里路的样子。这是村前最热闹的时刻,礼花炸响,鞭炮不息,鼓乐雷动。灵柩已绑扎了粗大的抬杠,众人簇拥,高声喧哗。前后四人抬着,甩开手脚,三进两退,抬着摆丧,脸上满是兴奋或笑容。灵柩一左一右一沉一浮不住地摇晃,与抬杠棕绳相摩擦,发出叽咕叽咕的响声,纸扎的大凤鸟,张开一双大翅膀,修长的颈脖频频点头。一溜长长的子孙后裔,头戴白孝,在灵柩前且跪且行。前方泥泞的田埂上,撒纸钱开路的,举花圈的,挑着箩筐放礼花的,放鞭炮的,各自尽着职责。田野上空,硝烟弥漫。
在溪涧小石桥上举行路祭仪式后,走的是一段上坡土路,抬棺的队伍明显加快了步伐,一鼓作气,将灵柩抬放在了墓坑边。之后,在择定的时辰,下葬,掩土,圆坟。众人陆续下山回村。
厅屋大门口已贴上了红纸对联,堂上清扫干净,摆了四桌联席,放了糖果饼干红枣。众人围桌而立,密密匝匝,端着一次性塑料酒杯。雄英哥指挥他的礼客班子,拿了一条长长的红布将众人围起来,祝酒四杯,吉言四句。禮成,各自散去。
岳母的相框放置在堂前神台上,与岳父靠在了一起。在二老的注视下,兄妹五家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新燕嫂子口头通报了这场白喜事的开销,总共花了五万多元,接到包括我们三个女婿在内的礼金三万多元,加上岳父去世时由她家保存的一部分存款及三年来岳母“工资”剩余,基本上收支相抵。至于今后从国家领取的安葬费,看大家的意见怎么分?各人心里都有一把秤,意见不尽相同。为免引起争执,我率先亮明观点:“财产的事情,你们两兄弟处理好,没有矛盾就行了,我不介入,也不需要,这也是乡俗。”新燕嫂子笑着说:“既然你们三姊妹高姿态不要,那就由我们两兄弟分。”
我和家人收拾行李准备当即回县城。我和女儿买的是明天的火车票,我去浙江,她去天津。
景和哥说,他按照村里的习俗,守孝三天后,也将去深圳。
景亮哥说,他已经超了假期,要赶紧回厂上班,明天上一次坟就走,当做清明节扫墓。
此刻,岳母在黄土里安睡,她是地府的新人,她的名字叫邓友莲。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