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身体与秘密的异托邦
2018-05-28邵泽鹏
邵泽鹏
雾,是近地气层中视程出现障碍的一种独特的天气现象,这种天气现象是由于大量悬浮的微小水滴或冰晶造成水平能见距离变小所致。当代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1959— )曾经在其小说及散文作品中多次提到雾,从他描写雾的频率以及这些描写本身,可以看出作家有一种雾的情结。在弗兰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纯洁》(Purity,2015)中,多次出场的雾,更是由一种单纯的天气现象化身为与日常空间迥然不同的异托邦(heterotopia),成为书中人物隐藏身体与秘密的庇护所。
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将异托邦描述为“在一个‘大量分裂的可能世界的‘一个不可能空间的共存,或者简单地说,是互相并置或者附着的没有共同尺度的各种空间”。《纯洁》中的雾,为书中人物构建了这样一个与日常生活 “没有共同尺度”的空间,这一空间的首要功能,不是承载人的身体,而是隐藏它。

在《第二性》中,法国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说过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为自己身体的存在而感到羞耻,因此人们想要躲避其他人的目光,想要阻止身体为他人存在,想要否认身体。而《 纯洁》中的安娜贝尔·莱尔德,正是法国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的这些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的男女中最敏感,最想要阻止它为他人存在,最想要否认它、隐藏它的一位。“我的身体又背叛我了,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一生就只是一个身体背叛的过程”。刚跟女儿打过招呼,左眼皮直跳的安娜贝尔就发起了牢骚。显然,左眼皮直跳只是一个引子,她对自己身体的不满由来已久。背叛感产生的根源在于身体的可见、可感。青年时期,身为艺术家的安娜贝尔计划摄录一部以自己的身体为对象的电影,通过对身体进行从下到上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摄录,“她更大的雄心是要从男人和肉那里一点一点地取回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十年之后,她将拥有全部的自己。”然而,她隐居后的名字——珀涅罗珀·泰勒——预示了这个艺术作品正像是珀涅罗珀的织物(The Web of Penelope),永远不可能完成。
最让安娜贝尔感到失望的是,在她开始摄录自己的身体之前,这具身体不属于她;在此之后,她不仅没夺回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同时也失去了对其的掌控力。于是,安娜贝尔选择了逃离父亲、丈夫的视线,以隐藏自己的身体。在隐居生涯中,作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安娜贝尔将自己的食谱严格地局限于非动物制品;作为一个离家出走的隐士,她将自己的活动范围、交际范围划定在一个极小的圈子内;作为一个离了婚却仍旧守着最初婚姻诺言的人,她将自己的欲望紧紧锁在肉身之上;作为一名艺术家,她将身体献祭给一个永远完不成的作品。在其女儿普瑞缇(皮普)眼里,“作為一名诗人,你不必非得写诗,作为一名艺术家,你不必非得创造什么东西。她妈妈精神上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一种看不见的艺术。”遗憾的是,安娜贝尔身体的可见性,并没有因为她的种种精神努力消弭。远走他乡、隐姓埋名的安娜贝尔,为了生存,不得不在新生活中建立、维系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将自己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而雾的遮蔽,给了感到羞耻的安娜贝尔以安慰。此时,雾是她藏身的危机异托邦(crisis heterotopia)。在雾中,被看的物质的身体消隐了,感知的身体却放大了。在《盒外之情》(“Emotions outside the box”)一文中,德国哲学家赫尔曼·施密茨指出,“物质的身体归属于具有表面的空间,而感知的身体则归属于没有表面的空间,就像声音、天气或者静寂。”从某种程度上说,感知的身体与其所属的没有表面的空间共同建构了其自身。当没有表面的雾与感知的身体遭遇时,就像瑞士雕塑大师、画家贾科梅蒂的某些人物画一般,在人物与环境的接合处,有模糊了界限的别样光晕,这光晕既是环境的一部分,也是人的一部分,将人与其所处环境完美结合起来。当雾与身体的这种融合真正完成时,为身体而感到羞耻的安娜贝尔终于再次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完备自足。因此,安娜贝尔彻底喜欢上了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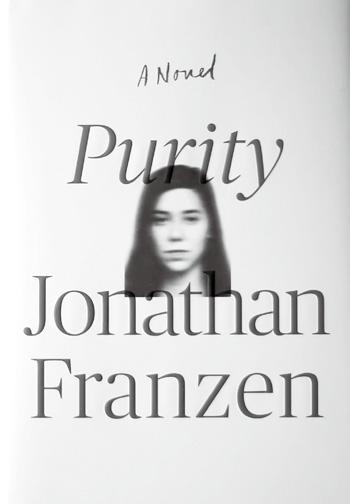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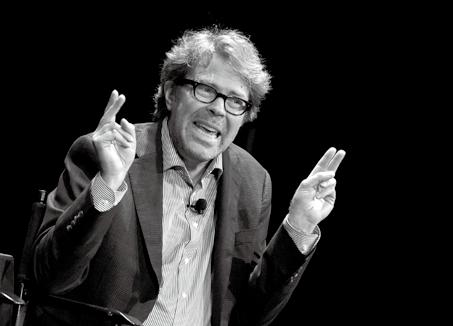
在同样的雾之世界里,不同的人,表现出了不同的心态,安娜贝尔变得轻松惬意、舒缓自如;《纯洁》一书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安德烈·沃尔夫则放开了对邪恶念头的压制,成为恶的化身。“这蒙蒙细雨下得这么细密、美好,几乎成了薄雾。……薄雾开始让位给更温暖的雾,这一转换让白天到来得古怪突然。雾不是件坏事。”蒙蒙细雨向薄雾转化之时,正发生在安德烈与安娜·格雷特合谋杀死对她图谋不轨的继父霍斯特·沃纳·克兰霍尔兹之后;而薄雾变成雾天则发生在安德烈送别安娜·格雷特,将要清理犯罪现场的时刻。雾的在场,建构起了一个法外的异托邦,将谋杀的现场隐藏,同时也将整个谋杀事件中最大的证据——尸体——隐藏。与安娜贝尔藏身其间的危机异托邦不同,安德烈身处的雾之异托邦,是一种偏离异托邦(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最初人们将行为异常的个体置于其中,渐渐地,法外之徒们,将这一法外之地变成了为非作歹的秘密场所。堪称反讽的是,因为试图掩盖自己的秘密,安德烈开始搜集其他人的秘密,并逐渐成为一个致力于揭露秘密的人,而这,显然有违他的初衷。长期深陷矛盾之中的安德烈,直到身体被雾遮蔽之时,才能有短暂的放松。然而,就像雾天终究是短暂的一样,他所能求得的解脱始终只是暂时的,将一生耗在守住一个秘密上的他,终于发现了存在的空虚和无意义。在被内心藏着的秘密压垮而自杀的前夕,他向世界吐露了这个曾经想要用一生来守护的秘密,获得了真正的解脱。
除安娜贝尔、安德烈外,《纯洁》的主要人物中,明确表示喜欢雾的还有皮普。“像她妈妈一样,皮普开始喜欢上蒙蒙细雨和浓浓的雾,因为它们毫无怨责。”毫无怨责(absence of reproach,怨责的不在场),归根结底,皮普喜欢的还是雾隐藏一切,將人与物的在场尽皆消弭的能力,而这,也即雾对于人的庇护。与法国思想家加斯东·巴什拉曾于《空间诗学》中考察过的“幸福空间”(espace heureux)意象一样,除正面的庇护价值外,雾之异托邦还有很多附加的想象价值。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描述异托邦的几大特征时也称,“异托邦有创造一个幻象空间的作用”,作为异托邦的雾,往往可以为身处其中的人创造诸多幻象。弗兰岑在《不舒适地带》中这样阐述雾的这一优点:“‘这是雾优异的方面,这个女人评论道,‘你能看到任何你想看到的东西。”这个女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弗兰岑将雾中的鱼鹰看做游隼。作为一名资深观鸟者,弗兰岑误将一种鸟看作另一种,除了雾这一客观原因,观察主体的主观意愿也在发挥作用——观鸟者大多期望自己能看到更罕见、更珍稀的品种。弥漫于林间的雾恰恰以其特性变相满足了他们的这种预期。或许,弗兰岑雾的情结,就源自他多年观鸟的经验——观鸟无疑需要云开雾散、天朗气清,然而能见度高的晴朗天气固然有利于观察、拍摄鸟类,却少了像雾中观鸟时那般发挥想象力的机会。《纯洁》中的雾,之所以能被视为异托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为身处其中的人物创造的种种幻象,而其为他们创造的最大幻象,那就是如家般的温暖。它就像是深夜旷野中一座亮着孤灯的茅草屋,为人及其秘密提供庇护,外面越是寒冷黑暗,越是让藏身雾中的人感到温暖。安娜贝尔的真实身份、皮普的父亲是谁、安德烈杀人……在《纯洁》一书中,这些雾曾经帮助隐藏的种种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雾慢慢消散,都将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但雾之异托邦带给安娜贝尔、安德烈、皮普们的温暖和庇护不会随着雾一起消散。


弥漫于天地间的雾,轻而易举地将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虚无化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雾既是一切,也消解了一切。在消解的同时,雾也参与了世界与人的重建。雾参与建构的异托邦,为人的身体与灵魂提供栖息地、庇护所;雾参与建构的人,比以往更加敏感、深情,充满爱意。通过遮蔽一切却又给人以温暖幻象的雾之异托邦,弗兰岑创造了一个神秘不安、变动不居,却又带着异样温暖的世界。尽管雾中也曾发生过争吵、凶杀、荒淫、放纵、欺瞒,但这些正像是该书摘自《浮士德》的那句题词——“我是总想做恶的力量,却反把好事促成”——反而成全了雾之温暖。《纯洁》中描绘出的雾之异托邦,就像是文末那场雨,将爱与信任等美好的情感,以及感受到这些情感的感知身体,统统笼罩起来。即便雾消散,感到羞耻的身体,以及各种秘密展露在世人面前,雾带来的爱与温暖仍将长久留在人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