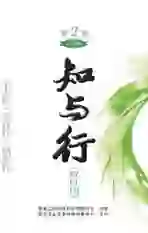生命伦理中道德冲突问题探析
2018-05-14钟纯
钟纯
[摘 要]生命伦理是应用伦理学的重要分支,它引起人们对生命道德的思考,尤其是对某些特殊情况下所出现的道德冲突进行反思。在现实生活中,尽管道德冲突的出现使得人们束手无策,但是,我们只要遵循康德的道德原则去剖析道德冲突,就可能找到可行性的解决办法。不难发现,康德在道德哲学中关于“道德价值”的论述是在告诉我们出于义务、合乎义务的行为才是具有道德价值的,同样在道德冲突中,人们要想作出具有价值的行为,那么,就要求其行为是合义务的。此外,康德还讲“人是目的”这一原则是可以应用到解决道德冲突的,其认为只有掌握这一法则的义理,才能对“难产时保母保子难题、安乐死”等问题作出合理的判断。由于各种理论(德性论和后果论)都给道德冲突提供了指导,但是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然而,康德道德哲学却为解决道德冲突提供了新的视角:一方面,康德的道德哲學的“义务论”能够给道德冲突带来启示;另一方面,其“人是目的”能够直接应用到生命伦理中,这些理论能够让人们在面对道德冲突这种两难的处境时,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为人们更好地处理生命伦理中所出现的道德冲突问题提供可行性方案和指导。
[关键词]生命伦理;道德冲突;道德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2-0145-06
生命伦理在国内兴起不久,但是迎面而来的挑战却很多,出现的各种道德冲突问题,如孕妇难产时保子还是保母、医生该不该为病人安乐死以及克隆人道德问题等。面对问题时人们尝试了无数种办法,但都没能使这些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当然,尽管此问题难以解决,我们还是可以从理论的视角去分析与探讨,从而找到合理可行的解决方式,达成共识。本文从康德的道德哲学这个理论基点出发,探讨如下问题: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冲突有联系?如果有,是必然联系还是偶然联系?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如何发挥其理论的作用使得生命伦理中的道德冲突有解?如果能够对以上问题作出回应,那么,以康德的道德哲学作为理论指导,必然会给我们在解决道德冲突的问题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启示。
一、道德冲突与康德道德哲学
生命伦理作为应用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以尊重生命和人格平等为价值取向,注重实践领域并为解决道德冲突提供理论支撑;而康德的道德哲学则是以义务、德性、人三个方面为主,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理论性指导。虽然,两者看似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都是在人的精神层面——道德伦理层面,来寻求冲突的解决路径。
(一)道德冲突理论和道德价值理论分析
道德冲突并非道德要求本身的冲突,而是主体在特殊情况下,很难同时履行道德要求,进而产生的困境,这种困境也叫“准则冲突”。那么,什么是准则?所谓准则就是主观异化成了一个原则,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当这个道德原则被他人接受或认可时,就能成为他人的一条准则,即原则的普遍化便成了准则。相反,当个体形成他人的准则,很容易变成自我准则,于是客观准则便带有主体性,因而在道德冲突境况下,这种准则会让他不知所措,如此一来,自我准则就容易与准则发生冲突。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一种行为符合了这种准则的同时又违背另一准则。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在道德的要求下进行抉择,要么遵守其中一条准则,要么违反另一条,从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法则。如果主体对两难的情形进行选择,会让主体陷入情感上的焦虑、痛苦和不安,但是,在两者之间选择,就很有可能失去自己的道德价值,任凭他人进行裁决。因此,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就必须忍受痛苦,自主地去解决冲突,以凸显自身的价值。
当准则发生冲突时其表现相当的复杂,既可以是由于社会和他人对同一角色期待不一致造成,也可以是由于改变个人的角色而造成新旧角色与所承担的义务之间的冲突。从价值选择的角度来看,准则冲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由于自身限制而导致在价值选择上出现的冲突,例如,家庭、事业、友谊、尊严,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构成幸福的要素,缺少任何一项都会让幸福不完满,可是“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尽管做出选择很痛苦,但主体又不得不进行相应的取舍。第二种,准则冲突可能是基于道德原则的冲突或矛盾,比如忠孝不能两全,再比如电轨难题:列车行驶到一个分叉路口时,只有两条轨道,一条绑有一个人,另外一条绑有五个人,而且列车来不及刹车,这时司机应该怎样选择?此外,准则冲突还可能是你面对邪恶势力时,要求你对生命的价值与自由、尊严与信念进行选择。例如,你家被恐怖分子绑架,他们逼迫你杀死你的所有亲人,就把你给放了,否则就把你杀害,这时你是选择大义灭亲,杀了他们来保全自己呢,还是舍弃自己而维系你对亲人的爱?由此可见,准则冲突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通过正当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价值抉择,另一种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进行道德判断。很显然,以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必然要侵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成正当的目的呢?或者说,正当的目的是不是可以为不正当的手段来辩护呢?
(二)康德义务论在道德冲突中的作用
道德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价值冲突。当人们在某种实践或行为当中遇到道德与生命的抉择时,是以生命的价值作为结果导向,还是更加的倾向于道德?再进一步说,两者本身都具一定的价值时,是按价值的大小计算吗?显然,如果这样必然会导向功利主义,但是换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从合乎道德、合乎义务的道德哲学角度来做出选择,这样会更加合理。康德的道德哲学在解决道德冲突时能够提供合理的理论指导。
那么,什么是康德道德哲学呢?康德曾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下简称《奠基》)中指出:“一个出自责任的行为的客观必然性就叫作义务”[1]448。从这句话中,可以得知义务具有必然性和客观性,因为要使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就必须要出于义务,这样人类的意志才是理智的。换言之,意志就具备了有为自身制定行为准则的功能,通过这个功能,准则就有利于我们认识客观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盲目的改造和创造规律。所以,康德对人的理解就是人作为一个立法者,必须具备理性,使之行为合乎义务,否则就不具备立法的资格。同样,在道德规律中,人只有通过理性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最终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不然就会受到主观臆断的影响。所以,义务在行为上具有必然和客观两种属性,如果在道德行为上不能满足必然性的话,那么,这种行为就不是出于义务的道德行为,也不具备道德价值。也就是说,出于义务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这样的理论才能够有效地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
作为行为动机的“义务”称之为出乎义务,因为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而任何出于其他意图的行为,例如,带有不良动机、恶、利益以及情感偏见的行为,都不具备道德价值。这些不合乎义务的行为的产生不够纯粹,同时还带有很强烈的主观情绪,例如,当一个人快乐时,他可能会欣喜若狂,甚至也可能热情奔放,而当一个人痛苦时,他可能愁眉苦脸,还有可能会做出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因此,由于主观情绪支配的道德行为都无法保证它的道德价值,也就无法保证道德行为的必然性。这样,康德就对义务作了明确的区别:一种是出于义务,另一种是合乎义务的。出于义务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准则,同时合乎义务又是在道德法则之中。康德指出:“一些行为尽管在这种或者那种意图中可能是有用的但已被认识到是反义务的,我在这里统統予以忽略;既然它们甚至是违背义务,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有是否出于义务的问题。”[1]404这表明,那些符合义务的道德行为是没有任何的偏好,也不会受偏好的影响使行为符合义务,所以,合乎义务的行为是出于义务的。例如,商贩卖东西,如果他把东西定价太高,就很少有人过来买;如果他把价格定在大家都能接受的范围,那么都会来买。换言之,每个人都有对商品的一个共同价格认知,这个价格普遍被人们所接受,那么,这就是合乎义务的。如果商贩怀有自私的意图,受利益的驱使,将商品定高价再以打折的方式进行销售,看似商品的价格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其中的“猫腻”商家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商贩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既没有出于义务,也不符合义务的。
接下来,康德进一步强调出于义务的行为,才能称之为义务,其又对义务进行了分类,最基本的是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法权义务是完全义务,是绝对的且没有条件的。例如,他在《奠基》中说道:“你不应当说谎,这条命令不仅仅对人有效,其他理性存在着就不能放在心上,其余一切真正的道德法亦复如是。”[1]396这里,康德把“不要说谎”当成对他人的义务,不带其他任何目的,就相当于我们在商业中要讲诚信一样。一个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不卖假货的老板往往让人值得尊敬,因为他的行为是具有道德的,这才是康德认为的道德行为。在康德看来,这样的道德行为只能在先天的领域中去寻找,因为,它不是置于人的本性之中,而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概念。如果这种概念不具备普遍的规范,而是一部分,甚至很小的一部分都是依据经验而存在,那么,它就不能是一种道德法则。而德性义务则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义务是有条件,有选择,有对象的,因此,又可以根据对像的选择不同划分为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康德在《奠基》中说道:“在行动者的自身身上发现一种才能,这种才能经过若干培养,就能够使他成为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很有用的人。但是发现自己处在舒适的情况中,而且宁可沉溺于享乐,也不愿努力去扩展和改善自己幸运的自然禀赋。但是仍然自问:他荒废自己的自然天赋的准则除了与他对欢娱本身的癖好一致之外,是否还与人们称为义务的东西一致。”[1]430一个有自然天赋的人如果不能够利用好自己的才能而选择自甘堕落的话,就会与义务背道而驰,整天无所事事,甚至一事无成。但是,发展自己的才华也是有条件的,假设一个不健全的人,去发展一个不适合自己的才华,往往会导致功亏一篑。例如,你要挑选一个没有双腿的人去发展他踢足球的才能,这可能吗?显然自身条件不允许。同样的道理,“帮助他人”也是一种对他人的义务,但这种义务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我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或意图,然而一旦动机带上自私的目的,这种帮助也就变成了非义务的了,因为它变成了人自身的一条准则,带有了主观的情感在里面。
二、康德道德哲学在道德冲突解决中的启示
近年来,生命伦理成为应用伦理学中讨论的热点,它涉及政治、法律、社会、道德等各个层面。此外,对生命伦理与道德决定进行讨论时需要许多学科的参与。因此,从康德道德哲学的视角来剖析生命伦理中关于人工流产、安乐死等问题时,出现的道德冲突就显得很有必要。尽管人们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德冲突中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却能从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得到启示,从而在道德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寻求最佳的途径。
众所周知,理论是可以指导我们实践的。同理,“出于义务,合乎义务”作为康德道德哲学的道德原则,也可以给我们在生命伦理道德中如何解决道德冲突作出指导。随着人们的思想水平和觉悟的提高,一般的风俗、习惯也就慢慢演变和发展成为道德。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古到今,无论是对道德哲学的研究还是对道德的实践,都产生出许多相关的哲学理论。在中国先秦时期,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孟子则用“仁义礼智信”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道德学说;而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德性来论证道德就是人们最高的生活技艺,既要求有节制、勇敢、智慧、正义的美德原则,又要追求好生活的同时与善的目标达成一致。而在当代,讨论最广泛、最热烈的是罗尔斯的“正义论”,正义是道德所涵盖的范围。那么,究竟什么是道德?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可以作为评价人们行为的准则,又可以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突然常常也作为善恶、是非、对错的评判标准。然而,在康德看来,尽管道德有评价的功能,但是,这种评价的功能包含着个人情感、偏好等主观因素在里面,它就不是一种纯粹而又普遍的道德。所以,他在《奠基》里如此说道:“一个出自义务的行为具有自己的道德价值,不在于由此应当实现的意图,而是在于该行为被决定时所遵循的准则,因而不依赖行为的对象的现实性,而仅仅依赖该行为不考虑欲求能力的一切对象而发生所遵循的意欲的原则。”[1]406所以,要使我们的行为是道德的,就必须做出“为道德而道德”的行为,也就是要出自于我们对义务本身的道德行为才具备道德价值,一旦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带有情感偏见,那就不是道德的。例如,我们在路边看到一个乞丐,如果你是出于怜悯、同情、恻隐之心而去行善,那么,这种行为是不具备道德价值的,因为行善这个行为是被情感所要求的,行善是为了满足内心中出于对乞丐的可怜,并非纯粹而自然的。在康德看来,要使行善这个行为具备道德价值,那么,行为就一定要出自义务本身,不应该受到偏好或情感的驱使,是一种自发自觉的行为。
所谓道德冲突是行为主体在特殊情况下碰到的两难情形,其很难实现多种道德要求的困境。在这种情形下,他不可能满足两种道德或义务,只能做出二者选其一的决定,这就意味着要忽视其中一种义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道德冲突很常见,例如,医学上的安乐死问题。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但却要帮助那些毫无希望的病人,让他们结束病魔折磨的痛苦,在安详、宁静中与世长辞。安乐死问题一方面会造成价值选择的冲突,另外一方面会混淆医务工作者的角色,是治病救人还是置人于死地?这无疑会让医务工作者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同时也会让患者失去对医生的信任。就安乐死问题既要医生愿意执行,又要让患者接受,是两难的困境,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那么,康德义务论在解决道德冲突时是何以可能的?康德认为,安乐死不看重结果的本身,而是出于义务的行为使安乐死完全不带医生和患者的偏好,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才能形成一个普遍的法则。因此,在《奠基》中,康德得出一个结论:“义务就是出自对法则的‘敬重康德对敬重与情感进行了区别,他说:“尽管敬重是一种情感,它也毕竟不是一种通过影响而接受的情感,而是通过一个理性概念而自己造成的感情因而与前一种可以归诸偏好或者恐惧的情感的区别。因此,敬重是意志直接为法则所规定以及对此的一种意识。”的一个行为的必然性”[1]407。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如果他采取行动带着他对患者悲悯或同情的情感色彩,那他的决定不会是康德所说的“敬重”。因为安乐死仅仅只是意志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意志的活动。同样,对于患者的家属来说,他们都希望自己亲人能早点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那他们也不可能是“敬重”,而是情感的表现。因此,安乐死既不让患者家属带着解脱的情感,又不让医生对自己行为产生内疚,那才是“敬重”。所以,在道德上我们说这种行为是善的,这里就包含着此行动者的人格,因为,只要人格被他人敬重就能说明此过程是具有道德价值。在患者安乐死的过程中,他依然享有生命权、尊严、人格以及生命的内在价值,任何形式都不能剥夺。
在道德价值方面,康德着重强调了“敬重感”。他认为,“敬重感”只存在于善的意念或德性之中。因为人为自然立法,是由于人作为理性者本身来说是自由的,要参与到普遍立法的过程中来,这样的法则才具有价值,否则就不具备价值。康德在《奠基》中谈道:“因为除了法则为之规定的价值之外,没有任何的东西具有一种价值,但正是因为这一点,规定一切价值的立法本身就具备一种尊严,亦即无条件、无与伦比的价值;对于这种价值来说,唯有‘敬重这个词才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理性存在者对这种立法的评价。因此,自感律就是人的本性和任何有理性的本性的尊严的根据。”[1]444由此可见,康德的“敬重感”就源于立法的原则,也就是说,普遍的法则一定是带有必然性并使之产生敬重感。而道德的价值就在具有尊严的敬重感之中,这点我们无可厚非。对于能够想方设法去履行自己义务的人,就有一种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尊严。之所以说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尊严,是因为他既是立法者又是理性的存在者。所以,康德說:“既不是恐惧,也不是偏好,而仅仅是法则的敬重,才是能够给予行为一种道德价值的那种动机。”[1]448就我们自己的意志仅仅在一种因其准则而可能的普遍立法的条件下才去行动而言,这个在理念中对我们来说可能的意志是敬重的真正对象,而人性的尊严正在于中国普遍地立法的能力,尽管是以它同时服从这种立法为条件。
当我们的准则能够成为“普世伦理”的时候,就具备了道德价值。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为例来说,儒家的道德准则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基础上的,通过“推己及人而利天下”难免不会带有“人情”的味道,一旦利用人情到达了自己的目的,那么,道德这样的准则就可以弃之不管了。这样的准则成了一个结果的导向:由于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不应该把它施加给别人。如果我做到了这条准则,那么,我也希望或者期盼他人跟我一样,这样的行为也不具备道德价值。所以,康德在《奠基》里说道:“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它出发期待的结果,因而也不在于任何一个需要从这个被期待的结果借取其动因的行为原则”[1]408。一般而言,我们所期待的结果常常带有情感爱好或偏好在里面,这就与康德所说的“敬重”一词相区分,尽管“敬重”是一种感情,但是,它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概念来区别于情感,这就意味着理性使我们的情感去服从一个法则的意识。前面我们提到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成为一条法则的话,那么,就只有具备以人格为目的且带有“敬重”的条件,这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道德的法则。准则究竟要如何才能成为法则呢?康德说:“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准则作为一个法则的普遍有限性必须是我们的行为的限制条件呢?我们归于这种行为方式的价值应当如此之大,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有更高的兴趣存在,但我们要把这价值建立在什么上面呢?人唯有因此才相信自己感觉到其人格的价值,相对于这种价值,一个适意或者不适意的状态的价值就不值一提了,这是发生了什么呢?对此,我们无法给他令人满意的答案。”[1]457这表明,康德把人格作为人的价值属性,认为人的价值是内在的人格在起作用,如果人格都得不到尊重的话,那么,所谓的法则或普遍的准则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康德认为,我们行为的动机不应该建立在行善之后所产生的感情之中。而恰恰幸福论者将情感上的愉悦作为我们行为的动机,认为先有某种情感才去行善的,借此来证明情感是受利益支配的(获得情感上的愉悦也是一种利益)。这与康德的观点截然相反,幸福可以作为安乐死这个道德冲突的出发点,但这只会让冲突更加的锐化。真正要调和安乐死这样的道德冲突,“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用道德的方法去调和,需要康德道德哲学来发挥作用。总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对一个行为进行道德评价:一方面,这个行为本身是否符合客观的道德法则,只有符合道德法则,才能说是“合法的”;另一方面,做出这个行为的主体动机是不是出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当一个行为具有两个方面时,才能说此行为是道德的,才具备道德价值的。如果仅仅是满足第一个方面的话,那不足以称之为道德。确切地说,对道德律“敬重”的行为就已经具备道德的属性,因此它是一个道德行为。
三、“人是目的”原则在道德冲突中的应用
康德是德国哲学家中最深刻、最完整地表达人是具有尊严的并把人归结为目的的,而不是一种手段的哲学家,他说:“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同时当作目的,而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在他看来,人是具有人格、尊严、平等、自由意志的存在体。要理解人就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人的存在是带有尊严、人格等属性的存在;第二,作为目的的人,不能把人当作工具或手段;第三,这里的人,既包含单个的个体,也包括人类这个整体;第四,人是目的,是内在的目的而不是外在的目的,不是单方面的物质或利益的追求。内在目的,并非没有利益,它所追寻的利益是正当的、合法的,正如康德说道德行为要具有道德价值一样,这样它必定是道德法则的“合法性”。如果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所追求的利益损害了人类整体的利益,那么,就有违“人是目的”的价值理念。
康德的目的和目的论是不尽相同的,康德的目的强调根据自身法则所确立的目的,而不是“目的论”即单凭感性而确立的目的。同时,他还把义务也作为目的,因为义务既是本身的目的,又是行为的目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常常以利害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法则,因为幸福是受利益的制约和支配的,从而具体的道德行为也要把利益作为权衡的标准。在康德看来,幸福和利益是有一定关系的,因此,他要喊出“德福一致”的口号,其中他所认为的利益并非物质利益,而是利益渗入道德律之中,只有依据道德法行事,才会带来好的结果,这种结果就是自然利益。所以,他认为的道德行为是不需要考虑利害得失的。一旦道德行为带有利益目的,就很有可能失去自由意志,从而影响意志对行为的准确判断。在生活中,当人们知道应该如何去做的时候,那就是道德法则的具体化,这完全是出自义务的一种行为。换句话说,义务就是成了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有着强大的信念,必定会给他人或社会增加福祉。因此,当“人是目的”参与道德活动的评价时,无论行为的结果如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都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一个道德的行为。
当我们遇到两难的情形时,无论是德性论、后果论、契約论还是义务论,都无法完满地解决问题,但毕竟它们在解决道德冲突时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其中义务论的作用最大。接下来,就义务论在解决道德冲突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看下面一个例子:一个孕妇在难产的时候,只能保全一条生命,是保母亲还是保胎儿,这是个两难抉择。有人认为保母亲,因为母亲具有再次生育的能力,可以再次的繁衍,这显然是从功利主义的方面得出的结论,要让效益最大化或痛苦最小化。假若这个母亲就只有这一次生育的机会,又会怎么办呢?也有人认为,应该保胎儿,因为胎儿已具人形,有生命权,具有更广阔的发展、成长空间。不管做出什么抉择,这个冲突也不可能得到完满地解答,也不能得出正确答案。但在康德看来,人既然是目的,那孕妇、胎儿也必然都是目的,不能牺牲任何一方来保全另一方。但从作为尊严、人格、内在价值的人的内在属性来看,保全孕妇会更加的恰当,因为尽管胎儿已具人形,但他的尊严和人格属性还不够完全。换言之,胎儿仅仅是具有了生命权,对于尊严、人格的概念属性还不够完备。针对这个棘手的两难问题,想要完整、正确地解决是不可能的,但行为的价值判断需要道德哲学作为指导。如果在两难中,一定要两者选其一的话,以“人是目的”这条法则来指导,会使结果更加合理。因此,在道德哲学中,康德的义务论思想无疑在道德冲突解决中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四、结语
综上所述,康德的义务论在道德冲突的解决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尽管没有给面对道德冲突情形下的主体提供正确答案,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提供了有效的指导。面对科技快速发展给人类留下来的难题,无论是安乐死问题、堕胎问题还是克隆问题,都离不开伦理学,都需要道德哲学来为它们寻求一个答案。因此,本文对道德冲突问题进行了伦理学的探讨,当人们陷入这种两难境地时,康德的义务论思想无疑给人们带来了及时雨,这种思想不仅能指导人们如何有效的、正当的面对冲突,而且还能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总之,康德的道德哲学在解决道德冲突问题时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曙光和新的视角。
[参 考 文 献]
[1]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上海:中华书局,2006: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