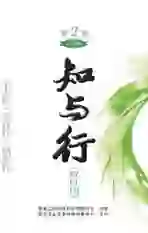《论语·宪问篇》隐士的孔子观考辩
2018-05-14张仲广
张仲广
[摘 要]《论语》作为记述儒家核心理论的基本典籍,除了记载了孔子传道授教及与时人弟子应答之语外,亦有多处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与道家隐士交往之事,其中《论语·宪问篇》记载有知隐(知识分子型隐士)微生亩、吏隐(底层官吏型隐士)晨门和商隐(手工业商贩型隐士)荷蒉三人三事。从这些记述中能够梳理出先秦时重视天道自然的道家者流的隐者对重视世道人伦的儒家者流的孔子的基本认知与态度,亦即隐士的孔子观。这些隐士虽然与孔子志趣有异,但除却处世观亦即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立场上的差歧外,他们对孔子的基本认知与态度并不像后世某些《论语》注疏家所描述的那种纯粹的讥孔、贬孔甚至还有一丝反孔,而是知孔、谏孔甚至还有一丝爱孔。隐士的孔子观在本质上反映出了当时道家对儒家关怀、赞赏与希望其能超越人道而感悟天道的基本态度与认知,同时也反映出孔子对儒者出处的基本态度并不是单一式的,而是进退结合式的且以进为主以退为辅,整体是圆融的,也进一步表达出儒道思想互补的必要性,儒家经世济民的“实理”恰能弥合道家消极遁世之流弊,道家空灵超拔的“虚理”恰能弥合儒家喜好声名之流弊。
[关键词]《论语》;隐士;儒家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2-0027-05
《论语》作为“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 [1]1的儒家元典,其不仅重点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之言行外,还记述了一些隐士与孔子及弟子相遇相交之事。其中《论语·宪问篇》记载有微生亩、晨门和荷蒉三人三事,这些记述虽着笔运墨不多,但却是先秦时期道家与儒家两大学派相互交流的直接记述,极为珍贵。从中我们能够梳理出当世之时的隐士对孔子的基本认识与态度,亦即隐士的孔子观。
平心静气的来品读《论语·宪问篇》中关于隐士的三则记述,可以得出这样的审见:当世之时隐士的孔子观并不是讥孔、贬孔甚至反孔,而是知孔、谏孔甚至爱孔;隐士的孔子观不仅能反映出当时儒道两家的交流情况,亦能反映出孔子对儒者出处问题的圆融看法和儒道思想的互补关系。
兹按《论语·宪问篇》相关章节次序逐一考辩如下:
一、微生亩的孔子观:孔子乃苦心救乱之徒
《论语·宪问篇》载:“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2]198
(一)微生亩的隐士身份
关于微生亩的隐士身份,《论语》并没有明文提及,但按照刑昺“微生亩,隐士之姓名也。”[2]198的注疏和朱熹“微生,姓;亩,名也。亩名呼夫子而辞甚倨,盖有齿德而隐者。”[3]157的见解以及康有为“亩名呼夫子,盖耆老之隐伦,亦创教者。”[4]219-220的解读,我们可以推知微生亩应为当世之时年长有德且对人与社会关系有着自己独到理解的隐居之士。其人职业不详,无论《论语》本文,还是注疏中皆未有只言片语的透露,康有为以其为“创教者”,似言过其实。但从其与孔子的问答中可知微生亩年龄耆硕,可能本身已经不直接参加谋生活动而由子孙赡养,或是与孔子一样,以授徒为生。加之,其人所关注的乃是“佞世”与“疾世”之事,亦即知识分子所最为关注的人格尊严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由此,大致可以推知微生亩应属于知识分子型的隐士。
(二)微生亩的孔子观
按后世注疏家的看法,在此则记述中,微生亩因直接讥讽孔子为邀名逐利之佞徒,并且奚落孔子凄惶的现状处境而被认作冥顽固陋之流。然仔细品味与思量孔子之所答所应,此说未然。如曰微生亩直讽孔子,孔子自然可以本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篇》)或“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篇》)的态度置之不理,或可以本着“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篇》)的态度反唇相讥。可孔子两举同弃,而是选择了“圣人之于达尊,礼恭而直言如此,其警之亦深矣。”[3]157的姿态,敬心敬气的将自己“以道济天下,拯救生民,故东西南北,席不暇暖,哀饥溺之犹己,思匹夫之纳隍,……数十年羁旅之苦,车马之尘”[4]220的良苦用心和真實情意进行申说剖解。
今按,以事后的维度观照,固然知道孔子并非邀名逐利之佞徒,夫子当时驾车列游并非为己之功名利禄,却是为世道苍生而劳心劳力。对此,范祖禹曰:“夫子疾世之衰,欲行其道而反之于尧舜三代,此岂微生亩所得知哉?”[1]502以此为原点进行推演,自然会得出微生亩误读孔子的结论。然探究微生亩的基本认识是不能以后世维度观照的,而应该以当时之世的维度来观照。平心而论,微生亩虽言辞倨傲,但其身为年长有德者,实并不为失礼,所以,孔子并未默而不应或反唇相讥而是据实回答。再者,从二人问答的言语中,似乎夹杂着微生亩对孔子的一丝爱怜与激励之情,其看到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仁义,而却落得凄凄惶惶,心有不忍,故出言批评之、教育之,恰似禅宗当头棒喝之举。既给孔子提出警醒,周游列国,推行仁义是存有危险的,事实上孔子推行自己学说之时确实遇到了类似厄于陈蔡之类的事情(与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向青年传道却被判有罪,饮鸩而逝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同时,也是在告诫孔子不要放弃仁义正道,而谄媚有权且居上位的人。谄媚当权者固然容易获得富贵,博取功名利禄,但那不是君子之所为与之所求,是君子人格的自我折损与阉割。故而,士人君子不可侫世。微生亩恰恰是懂得这一点而向孔子发问的。另,微生亩用“栖栖”二字亦不应解读为讥孔。《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5]764从中可见,孔子对别人评判他栖栖惶惶不但不介意,反而觉得比喻很形象。细心品读,郑人并不是在讥讽孔子,而是在赏赞孔子之才德,慨叹孔子之遭遇,替孔子抒发怀才不遇的感伤之情。如微生亩讥讽孔子在郑人讥讽之前,则从孔子对郑人讥讽的反映可见孔子并没有将此种行径当作讥讽,微生亩讥孔也就徒具其形而不具其实;如微生亩讥孔在郑人之后,则与郑人情出一辙。
故而,在微生亩眼中,孔子并非邀名逐利之佞徒,而是救世无成之徒,本着对孔子的关爱与激励,应当给予孔子以善意的提醒:孔丘,你如此凄惶,是不是佞世媚俗?孔子回答:不敢佞世俗,是嫉世恨俗!从中可见二人对世俗的态度是一致的,以嫉不以佞,以恨不以媚。从这种维度上可以说微生亩是知孔与爱孔的,在微生亩的眼中孔子是一位苦心救世却落得凄凄惶惶之贤人德者。
二、晨门的孔子观:孔子乃慈心救世之辈
《论语·宪问篇》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2]200
(一)晨门的隐士身份
关于晨门的隐士身份,《论语》亦没有明文提及。按刑昺“此章记隐者晨门之言也。”[2]200的注疏和朱熹“晨门,掌晨启门,盖贤人隐于抱关者也”[3]158。的见解,晨门不是隐于山野之隐士,而是隐于微官小吏之中的隐士。掌管晨时城门开启乃之职分,故杨时称其为“抱关击柝”的“禄隐者”[1]509。其人职业从注疏中可以得知,乃是以按时开关城门为职分来获取微薄财物的守门人。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晨门应属于底层小吏型的隐士。
(二)晨门的孔子观
关于晨门对孔子的态度,后世《论语》注疏家主要有两种见解。一种以胡安国和范祖禹为代表,认为晨门不知孔而讥孔。胡安国认为“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故以是讥孔子。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3]158按照胡安国的看法,晨门不知孔子,并以自己的认识作为衡量标准来评判孔子,讥讽孔子愚蠢,认为孔子是在做无谓之事,是在做不可能做成的无意义之事。范祖禹认为:“知其不可而不为者,晨门也;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也。此所以异于逸民也。夫可不可在天,而为不为在己。圣人畏天命,故修其在己者以听之天,未尝遗天下。圣人亦不敢忘天下,虽知其不可,得不为哉。”[1]508-509在范祖禹看来,孔子和晨门是属于两个不同生命范畴之内的人,孔子是圣人,圣人做事不谋求外在天命,只问人事当为不当为,并不计个人利害得失;晨门是逸民,逸民做事则谋求外在天命,天命可为则为,不可为则止,人事要以天命为转移,计较个人利害得失。故而逸民是不知圣人的,只能以逸民之心度圣人之腹。这种思路基本上是套用了小人不知君子的思维范式,并无创新之处。同时,似有先入为主之嫌,先将孔子定为圣人,其余皆是非圣。另一种以刑昺、黄式三为代表,认为晨门知孔而赞孔。刑昺认为:“时子路宿于石门,夙兴为阍人所问曰:汝何从来乎?子路曰:自孔氏者,子路答阍人,言自孔氏处来也,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者,晨门闻子路云从孔氏,未审孔氏为谁,又旧知孔子之行,故问曰:是知其世不可为,而周流东西,强为之者,此孔氏与?意非孔子不能隐遁辟世也。”[2]201按照刑昺的看法,晨门是听说过孔子救世救民之事的,对孔子很是关注,故而向子路问起孔氏何人。但他认为孔子是在强为,这种强为并不是除此别无所为、不得不为的强为,而是能避世而不愿避世,为世而甘愿为之的强为,亦即为他人为社会甘愿牺牲自我的强为,是高尚且悲壮的强为。此中体现的是晨门对孔子的赏赞之情。而黄式三认为:“是夫子周流在外,使子路归鲁,值莫而宿于魯之城外,故有此问答之辞。曰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指圣人周游列国,知道不行,而犹欲挽之。晨门知圣也。”[6]在黄式三看来,晨门虽未与孔子谋过面,但却对孔子之所行所为颇为关注并有一定了解,而且用“知其不可而为之”对孔子的救世情形进行了生动准确地描绘。进而得出晨门人乃是知圣并在知圣基础上钦赞孔子之辈的结论。
今按,刑昺与黄式三的晨门知孔赞孔说为是。细品“宪问晨门章”文本,不难看出其大意当为,晨门得知子路来自孔氏处,不禁问此孔氏是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试想一个人通过素未相识的第三方想确认另一人的身份时,应举被确定人最杰出之事方是人际往来之正当手段。从对话中可见,晨门与子路并不相识,由此逆推,可知晨门举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之事,应是赞美之意。在晨门的眼中,“知其不可而为之”恰恰是孔子最为可爱和可贵的地方,可爱之处在于孔子心中依然对世道人心抱着希望,可贵之处在于孔子心中依然对救世救民充满信心。在晨门看来,孔子不失为一位对世道饱含热忱、不辞劳瘁的慈心救世之辈。
三、荷蒉的孔子观:孔子乃悲心救民之人
《论语·宪问篇》载:“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2]201
(一)荷蒉的隐士身份
关于荷蒉的隐士身份,《论语》亦没有明文提及。按刑昺“此章记隐者荷蒉之言也。”的注疏和朱熹“此荷蒉者,亦隐士也。”的解读以及尹焞“晨门荷蒉,皆隐者也,其亦微生亩之流欤?”[1]510的见解,基于《论语》中相关记述,可以推知,荷蒉乃精晓音律且精通诗书的隐居之人。其人职业《论语》中直接提及,乃以买售草鞋等生活杂物来获取微薄财物的手工业商贩。由此,大致可以推知荷蒉应属于手工业商贩型的隐士。
(二)荷蒉的孔子观
关于荷蒉对孔子的态度,后世《论语》注疏家主要有二种见解:
第一种见解认为荷蒉不知孔而讥孔,其主要以刑昺和张居正为代表。对此刑昺曰:“孔子闻荷蒉者讥己……言未知己志便讥己,所以为果敢。”[2]201可见刑昺将“果”释为“果敢”,然此种释义是站不住脚的。因“深则厉,浅则揭”根本就不是“果敢”范畴内的事情,孔子自不会用“果敢”来回应荷蒉,此释义和解读与文意不合,当不取之。张居正则认为:“盖圣人心同天地,天地不以闭塞而废生物之心,圣人不以时之衰乱而忘行道之志,诚上畏天命,下悲人穷,非得已也。彼荷蒉者之流,何足以知之。”[7]在张居正看来,孔子是心同天地的大圣人,其待人接物皆同天地一样,是不可能忘却情世道人心的。而荷蒉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精神境界与道德涵养,其人只想洁身自好,并以此为高明。故而,出语讥讽孔子。张居正发表此说时,正是身居侍讲时,教导未成年皇帝是第一要务。其解经往往采取“六经注我”的方法。他在讲解时是将《论语》当作经来看待的,其更多的是关注孔子万世师表层面的内容。故而对荷蒉采取了以偏衬正的态度,认为其人不知孔而讥孔。
第二种见解认为荷蒉半知孔而讥孔,主要以朱熹、程颢与《日讲四书解义》为代表。对此朱熹说“圣人之心未尝忘天下,此人(荷蒉)闻其磬声而知之,则亦非常人矣……(荷蒉)讥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适浅深之宜。”[3]159对此程颐说“孔子击磬,何尝无心于世,荷蒉知之……不知更有难事,他所未晓,轻议圣人”[1]509。从中可见朱熹与程颐皆认为荷蒉知孔子有心于天下,但其人不知孔子为圣之深意,故而讥讽孔子。细考之下,不难发现此说所犯之错与刑昺并无二致,亦是错解“果”字。
《日讲四书解义》对隐士荷蒉与孔子相遇一章解说如下:“适有隐士荷草器而过孔氏之门者,闻磬声而知之,……盖人心之感往往托之乐音,隐士乃贤者,自能审音而喻其微也。既而讥之曰:何其鄙哉!识之不达。……用世者乃不自度量,人不己知而不止,毋乃不如涉水者之随遇而能通乎?……故圣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万物,彼荷蒉者何足以知之?”[8]在《日讲四书解义》看来,孔子是大圣人,荷蒉虽能从磬声中听出孔子心声,还从中能体会到孔子的忧世苦楚,但其人不同意孔子的出处之道。荷蒉认为君子处世应该按照《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中“深厉浅揭,随时为义”(《后汉书·张衡传》)的原则,而不应一意强为,故而讽刺孔子不能随遇而通。然话锋一转,又赞孔子德比天地,不忘天下。这一层深意是荷蒉所不知的。按《日讲四书解义》的解释,荷蒉对于孔子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并在此基础上对孔子进行讥讽。
今按,荷蒉的表达无非是“以为人既莫己知,则当为己,不必更为人。”的人之常情常理而已。其并没有讥讽孔子之意,反而劝说孔子勿要逆势而为。从其能于磬声中听出孔子心声并能够引诗论说和孔子对其的评价“果哉!未之难矣。”(确实啊!我没什么能反驳他的啊。)可以推知荷蒉不失为孔子知音知心之人,其人是了解知晓孔子之“慈悲心肠”与“木铎本分”的,其对孔子的所言包含着知孔谏孔甚或一丝爱孔之意。对此蒋伯潜的解说是可取的,其文曰:“明君子于道可行则行,不可则止,人莫己知,不必悲观也。……按‘果哉犹今言‘果然这样吗?‘末之难矣之‘难,当读去声,言我亦无以难之也。孔子于避世之士,向以尊敬的态度对之,故闻荷蒉者之言,仅如此云云耳。”[9]由此可见,在荷蒉眼中,孔子是一位不避世事险恶,直道行事的悲心救世之人,只不过缺少一点超脱的气质罢了。
要之,《论语·宪问篇》中的三位隐士并没有讥讽与嘲笑孔子的用心与行为。他们关注关心孔子,对孔子热肠救世的本愿初衷给予肯定和赞赏,对孔子全心全意救世而世人皆不应答的遭遇给予同情,对孔子大用心世道而小用心天道的人生观给予谏劝,希望孔子能够对世道人伦进行超越,超越世道善恶而达于“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庄子·大宗师》)的境界,亦即超越尧善桀恶之二分,而达于天地大道一体无别之中。
四、隐士的孔子观所反映问题探析
《论语·宪问篇》隐士的孔子观所反映的基本问题有三:
(一)《论语·宪问篇》隐士的孔子观反映了先秦时儒道交流情况
关于《论语·宪问篇》中隐士的学术流派所属问题,历代关注者并不多,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如清代学者王夫之就曾在《读四书大全说》中明确指出“微生亩,看来亦老庄之徒”[10]。从中我们能够推知,《论语·宪问篇》中隐士应当属于道家学术流派,他们对孔子的基本看法,可以代表当时道家学者对儒家的基本看法。从以上微生亩、晨门与荷蒉对孔子的观点中我们能够看到,以隐士为代表的道家学者对儒家是持正向态度的,是知孔而赞孔的。这种孔子观与《史记》上所记述的孔老(儒道)的交流情况极为相符。《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5]756从中可见,老子对孔子的态度并不是冷淡的,而是以一位阅历丰富的老者身份对孔子进行悉心教导的。从“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的情况来看,孔子的确按照老子的教诲做了,而且效果良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了孔子对老子的态度,其文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孔子去,谓弟子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5]943从中我们能够明确看出,孔子对老子是很尊敬的,视老子为“乘风云而上天”的龙。《史记》中的这些相关记述正与《论语·宪问篇》中隐士的孔子观相呼应,亦可作为先秦时隐士的孔子观的别样诠释。
(二)《论语·宪问篇》隐士的孔子观反映了儒者在乱世中的出处问题
儒者身处乱世究竟是如何,似乎并不是像《论语》注疏家所认为的那样阳刚无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通观《论语》,孔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篇》)的话,也赞同过曾点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志趣。可见,夫子内心深处不仅存在阴柔有退的一面,还存在着洒脱浪漫的一面。对此,钱穆早有发现,其在《四书释义》中说:“孔子虽有志用世,而亦深有取乎隐者。”[11]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孔子出处观中出与处或进与退并不是对等的,而是以出为主,处为辅的,亦即以进为主,以退为辅的。其整体上是圆融,刚柔进退皆存的。也正因如此,当时的隐士们才三番五次的直接或间接地劝诱孔子归隐。
(三)《论语·宪问篇》中隐士的孔子观反映了儒道互补的必要性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主张美善刺恶,主张圣王治世与王道化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种经世济民的“实理”,其优长在于古道热肠与奋发勇為,并且强调颠沛造次必于斯;其流弊则在于会被王道仁义所异化,走上追求声名的道路,所谓“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庄子·人间世》)对于儒家思想可能异化生出好名求名的这种流弊先秦道家最有发现。《庄子·齐物论》中尧欲伐三国的寓言故事正是对此的生动诠释,其文曰:“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12]在这个寓言故事中,尧作为儒家的代表,他虽为圣王,但心中容不下三个偏远小国,意欲征伐,使归王化,心中对此念念不忘。舜作为道家代表,他告诉尧,那三个小国就像蓬蒿艾草一样,存在于天地之角,大可不必讨伐它们。之所以心中不释然,那是好圣王之美名的心理在作祟。从中可见,道家的超脱空灵的“虚理”正好能弥合儒家这一流弊。
道家主张超然出世,主张超越善恶,主张道法自然与圣人无名,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49章)这种空灵超拔的“虚理”,其优长在于逍遥洒脱与心无挂碍,并强调“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人间世》);其流弊则在于会被空灵自然所异化,走上一条消极遁世的道路,所谓“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对此孔子看在眼里,思在心中。孔子曾面对道家代表长沮和桀溺的谏劝时,表明过自己立场和心迹:“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篇》),孔子认为一味地空灵避世与躬耕山野并不是高明的选择,反而有消极逃遁的嫌疑与迹象,身为圆颅方趾之辈不应该与鸟兽为伍,而应该在人類社会中实现人的价值。从中可见儒家经世济民的“实理”正好能弥合道家这一流弊。两相对比,儒道思想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论语·宪问篇》中隐士的孔子观正是这种互补关系的一种隐性体现。
五、结语
基于以上考辩与探析,可见孔子所处之世的身为道家者流的隐士对孔子的基本态度并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般的冷漠,更不是“汝之不惠,甚矣!”般的揶揄,而是“心有灵犀,希其有所善归”般的赞许与关爱。在隐士的眼中,孔子是一位苦心救乱、慈心救世、悲心救民的热心人杰。他们希望孔子能够在“尽人道”的基础之上有所超越,达到“知天道”的境界,孔子内心深处亦是有所戚戚焉。
从当时隐士的孔子观中,我们能够看到春秋战国之际儒道两大家学派在实践交融的同时所展现出理论上彼此互补的基本状态与趋势。儒家的“实理”有喜好声名的流弊,洽需要道家空灵穿越“虚理”的弥合;道家的“虚理”有遁逃消极的流弊,洽需要儒家奋发勇为“实理”的弥合。同时,也能看到儒道两大学派在理论建构上的发展趋势——“实理”与“虚理”相结合。
[参 考 文 献]
[1] 朱熹.朱子全书第7册·论孟精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 刑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朱熹.四书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康有为.论语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 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出版社,2012.
[6] 黄式三.论语后案[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422.
[7] 张居正.四书直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215.
[8] 库勒纳,等.日讲四书解义[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2:162.
[9] 蒋伯潜.四书读本[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559.
[10]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5:417.
[11] 钱穆.四书释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2.
[12] 王世舜.庄子注译[M].济南:齐鲁出版社,20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