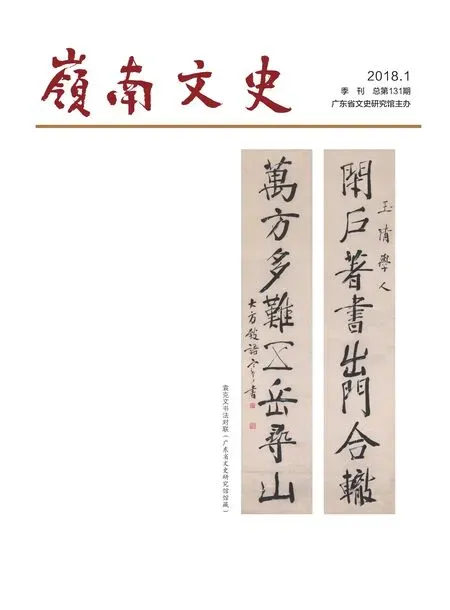虎门海口事件与林则徐外洋执法
2018-05-11唐立鹏
唐立鹏
林则徐在禁烟之外,同时还肩负着其他重要使命,也曾在外洋周密部署,与各国武装商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海口事件”之辨析
林则徐赴粤是奉旨行事,谕旨全文为:“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1]谕文中用了“海口事件”,而不直接说“鸦片事宜”,不禁令人产生疑问。紧接着在发给两广总督邓廷桢的谕文中作出进一步解释,说派遣林则徐赴粤是为了“专责以查办鸦片以及纹银出洋”,[2]这一表述似乎表明,“海口事件”除鸦片走私外,还存在白银外流问题。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鸦片走私的主要恶果是白银外流,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可并陈述之,亦可相互代称。究竟哪一种解读更为恰确?考察林则徐赴粤的前期背景以及后续态势,可以得出如是结论:所谓海口事件,不只是鸦片走私那么简单,至少还应该包括如下情形:
1、白银外流。早在清嘉庆朝时期,这一问题就已经引起关注。不过,当初并没有将其与鸦片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是归因于两点:一是夷商通过贿赂广州行商,将内地纹银偷运出洋;二是内地民人贪图交易方便,以足色纹银兑换含银量较低的洋钱。[3]清廷要求广东官员彻查此事并制定严禁纹银出口的章程,主要应对措施是严格遵照以货易货的原则进行交易,尽量减少现银支出。道光初年,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就白银外流与鸦片输入问题同折上奏,但并没有指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清廷也分别按两件事进行定性,一个被视为民生问题,另一个则被视为风俗问题。[4]道光九年(1829),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在奏报中第一次把白银与鸦片直接联系起来,认为由于鸦片大量输入,导致每年漏银数百万两,“非寻常偷漏可比”。这一奏报引起道光帝的重视,谕令两广总督李鸿宾制订《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将禁烟作为防范白银外流的重要举措。[5]然而,据此将鸦片走私与白银外流视为“一体两面“的同一问题则有失妥当。在当时人眼中,导致白银外流的原因有多重,除鸦片外,洋呢、钟表等其他洋货以及逃避关税之夷船等,均会造成大量白银流失。[6]成因的复杂性,决定应对措施的综合性,绝非禁烟一途所能彻底解决。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在禁烟的高潮阶段,白银问题亦经常被清廷作为一项专门议题、甚至是优先于鸦片的议题进行讨论。有鉴于此,鸦片走私、白银外流二者的关系可一言以概之:有交集的两个独立事件。正因为有交集,故共同归列于海口事件交由钦差大臣一并处理;正因为独立存在,所以必须区分对待。更有说服力的是,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专责海口事件期间,除全力以赴禁烟之外,还积极筹划如何防范白银外流问题。如他在复议御史骆秉章关于“内地洋银与纹银一律严禁出洋”时,曾详细阐述自己在广东的做法,并表示形势已初见好转,“此时外来洋银实见旺盛”,银贵钱贱现象得以极大缓解。[7]这充分表明,防范白银外流是林则徐处理海口事件的应有之义。
2、夷船窜越。有清以后,该问题一直纠缠于中英交往始末。众所咸知,英国凭贸易立国,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令英国对海外贸易的依存度日益加深;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度,按照乾隆帝的说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何需借助贸易互通有无?[8]英国千方百计想扩大对华贸易,而清廷则尽量将与西洋的贸易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既彰显怀柔远夷的天朝气度,又不致影响国内统治秩序。正因如此,在此前近200年的中英贸易史上,限制与反限制的争斗此消彼长,从未间断,窜越与反窜越正是这种争斗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清初海禁解除,开放了广州、宁波等4个通商口岸,实际上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仍主要集中在广州一口进行。后来由于赴宁波的外国商船逐渐增多,引起清廷警觉。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式宣布,宁波“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9]这就是清代影响深远的“一口通商”谕令。英国政府先后两次派使团访华,要求增辟通商口岸,未果;来华英商不顾禁令,非法窜越它口贸易的弊案时有发生,清朝当局加强防范。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扩大对华贸易,派胡夏米等人乘坐“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考察了粤闽浙苏鲁等沿海要地,历时半年之久。胡夏米事件令清廷大为震惊,传谕沿海各省严防外国船只非法窜越,一场大规模专项整治行动拉开帷幕。[10]然而,随着鸦片生意日渐兴隆,来华外商不惜铤而走险,窜越夷船不降反增,严打行动不得不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林则徐抵粤前夕,广东当局正在整顿粤东洋面;林则徐抵粤后,当即会晤总督邓廷桢,表示要将该项工作“核实办理”。[11]在收缴鸦片期间,林则徐一面主持虎门缴烟现场,一面清理分窜到粤东洋面的夷船,“以冀断绝根株,不使稍留余孽”。[12]同时需要说明的是,防范夷船窜越虽与禁烟息息相关,但不应仅仅视为禁烟过程中的一个具微环节,它更是清王朝为维护一口通商贸易体制而长期执行的一项政策性举措。当缴销鸦片完竣后,林则徐继续主持打击夷船窜越专项行动,此际追缴鸦片已不是重点,整顿通商秩序方为重中之重。正如林则徐所言,“有牌照而行中路者,则为经商之船”,“无牌照而窜东西各路者,即为偷渡之船”,偷渡之船皆系“有莠无良”,无论是否贩运鸦片,均在打击之列。[13]这也充分表明,防范夷船窜越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的另一项重要使命。

二、广东水师外洋执法之弊
道光帝登基元年(1821),就在广东发起一场严厉的禁烟斗争,许多外国鸦片船被逐出珠江。为了对付这次行动,英国东印度公司鼓动英商远离广州内河与黄埔,在外洋建立新的据点,即以伶仃岛为中心,聚泊大量趸船作为浮动仓库,“纹银之出,鸦片之入,洋货之偷越漏税,其交易多在趸船”。[14]如此,趸船成为藏污纳垢之所,外洋则成为奸逆横行之区。
究竟何为外洋?其法律地位如何?是否如英人所宣称的那样,外洋即公海?其实,清代的“外洋”是特有所指。清朝开国之初,沿袭明朝制度,将沿海水域划归各省管辖,各地方又根据洋面的远近,依次分为内洋、外洋、深水洋。凡靠近陆地的洋面为内洋,稍远为外洋,最远为深水洋。关于外洋与内洋、外洋与深水洋之间的界线,亦即外洋的范围,并无统一标准,各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界定。就珠江口而言,外洋的水域为(如图一所示):北面以龙穴岛为界,“过龙穴而北,由此入内洋”;[15]南面以老万山为界,“老万山以内洋面,是为外洋”[16];东西界线较为笼统,东侧的淇澳岛属内洋,九洲岛属外洋,西侧的赤腊屿、磨刀岛均属外洋,据此可大致勾勒出其轮廓。如此划分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行政与军事上的管理。内洋由地方政权和水师官兵共同管理,“内洋失事,文武并参”;[17]外洋由水师官兵专门负责巡哨,“外洋失事,专责官兵,文职免其参处”;[18]深水洋“非中土所辖”,[19]类似于现代意义的公海。由引可见,清代所称的“外洋”,并非中国之外的公共海域,它与内洋一样,皆在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图1 清代珠江口外洋水域示意图
珠江口外洋不靖,广东水师责无旁贷。水师基本职能有二:军事作战与维护治安。自清初收复台湾以降,除几次大规模清剿海盗行动外,军事作战任务寥寥,维护治安成为最大量、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引发外洋乱象的主要是来华外国商船,对这些商船的治理整顿应归属司法执法范畴,虽其间难免出现擦枪走火的状况,但与两国军队正式交战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起初,广东当局按照“欲绝来路,先堵去路”的方针,[20]要求水师官兵在内洋与海口处密集巡缉,但收效甚微。两广总督李鸿宾(1826-1832任)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外洋,因而加强了对外洋的管控。他在《章程》中专门加入“巡洋舟师梭织外洋,查察最为切近,应责成舟师分段查察”这一条款。[21]广东整治外洋,引发夷船向闽浙等省洋面窜越,两广总督卢坤(1832-1835任)重拾旧例,督令水师官兵在粤闽交界洋面落实“巡洋会哨”制度,鉴于夷船窜越线路复杂、单凭粤省一己之力难以奏效,他还提请闽浙当局共同协防。[22]两广总督邓廷桢(1835-1840任)任内,鸦片走私泛滥成灾,外洋情势愈发严峻。前期阶段,邓廷桢与弛禁派沆瀣一气,污称“逐趸船“、”拿快蟹“是沽名钓誉之举,主张放弃外洋执法,“专在隘口稽查“。理由是:隘口为纹银之出必经之地,只要守住隘口,“不虑其飞渡外洋“,若允许水师官兵出洋,”则散漫无稽“,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滋生事端。[23]当道光帝明确严禁立场后,邓廷桢的态度发生逆转,对外洋执法变得积极起来。他委派水师提督关天培驻扎在虎门海口的沙角炮台,督率附近水师协营将备,“无分雨夜”,加大出洋巡查力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最终总结出“驻洋守堵之法”,即:以水师提督负责总协调,将负有守洋之责的水师提标左营、香山协、大鹏营组织起来,打破陈规旧制,重新组合人员武备,分成三批次轮流驻守外洋,周而复始,不留空档。此外,他提出的沿海诸省“一体巡防”的倡议,亦得到朝廷肯复。[24]
令人遗憾的是,广东当局兴师动众,外洋诸弊却积重难返。追根溯源,不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思想上“怕”。清朝水师废弛已久,平时多在近海巡缉,对于外洋执法颇存畏难心理。正如卢坤奏述:“虽各省均有巡缉舟师,而重洋浩渺之中,番船乘间出没,势难防堵无遗”,[25]此为一怕。英船高大坚厚,安放炮位较多,师船无法与之相比,一旦在外洋发生冲突,彼强我弱,“难操胜券”,这也是广东官员最为担心的。此外,还涉及到政策因素。清朝对待来华夷商历来奉行“怀柔“政策,凡事以安抚为主,即使进行惩戒,也必须做到“不失国体而免衅端”,[26]这就使令地方官员在处理夷务时畏首畏尾,顾虑重重,广东外洋执法面临同样尴尬。二是行动上“软”。针对外洋趸船,广东水师计出千条,均是在如何禁止内地匪船前往接应上下功夫,没有一项措施是直接针对外夷趸船的。如李鸿宾时期制定的相关章程中,仅规定“无论商、渔船只,一经拢近夷船,即行拿究”,以及“严查有无匪艇运销鸦片、运送纹银”,对于如何处理趸船未置一词;邓廷桢推行的“驻洋守堵之法”亦是如此。在外洋执法的水师官兵不仅不敢对趸船实施搜查、缉捕,连简单地驱逐也做不到,清廷一再催令也无济于事,托词竟是:趸船混杂商船之中,难以分辨;如果强行驱逐,恐其向他洋分窜。[27]至于防堵非法窜越的夷船,广东水师也仅是走走过场、敷衍了事而已,“遇有夷船驶至,不过循例催行,如其任催罔应,亦即莫敢谁何。甚有桀骜夷船,胆敢以枪炮恐吓,而官船因未奉明文,转不变使用火器”。[28]执法者畏缩不堪,被执法者飞扬跋扈,执法成效不论可知。
三、林则徐外洋执法新举措
林则徐首次外洋执法源起于驱逐胡夏米间谍船事件。道光十二年(1832)6月,胡夏米等人驶抵江苏洋山外洋,[29]新任巡抚林则徐与两江总督陶澍会晤,两人很快达成一致,共同主持驱逐事宜。与闽、浙督抚尽快将夷船驱离本省洋境不同,陶、林二人首先想到的是“设法截阻”其北上,以免事态持续恶化。为此,部署巡洋师船,三面迎住,使之不得近岸,“兼断其北驶之路”;委派苏松镇总兵关天培京自押送至浙省洋面,拟移交该省水师,再由其押送至闽境继而返粤;为防范夷船探窥内洋情形,专门选择风险较大的外洋路线进行押送。当然,由于“未得浙洋接护”等因,该夷船驶至浙江洋面逃窜,后又折返北上。[30]但从整个事件的处理看,林则徐顾全大局、办事缜密的风格彰显无遗。
林则徐抵粤后,将外洋视为全部工作的重心,外洋执法活动从未间断。禁烟时期,林则徐的首要目标是将外洋趸船上的鸦片悉数清缴,考虑到如果直接出动水师,于洪涛巨浪之中“未能确有把握”,决定将矛头指向广州商馆的夷商,通过拘禁人质最终实现了这一目的。同时,在伶仃外洋加大水师巡查力度,密切关注趸船动向行踪;在粤东洋面展开专项清理行动,阻截分窜至此的外夷商船。善后时期,粤海中路事态暂缓,大量夷船驶向粤东、闽浙等洋面,堵截夷船窜越成为当务之急。林则徐一面整顿水师,实力防堵,一面与闽省密商,共同采取行动。封关时期,中英贸易断绝,在华英商被勒令回国,但在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的唆使下,它们拒绝离去,仍滞留外洋伺机作奸犯科。林则徐果断采取措施,多次派出水师、水勇出洋攻剿,烧夷船、捕内匪,功绩累累,直至中英两国正式爆发战争,方告一段落。
与此前历任广东督抚相比较,林则徐外洋执法呈现出两方面显著特征: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
首先,敢于斗争。从整顿水师营伍入手,林则徐毫不留情地惩处一批在外洋执法中“因循不振”的水师官兵,其中包括南澳镇总兵沈镇邦、参将谢国泰一干人等;[31]同时举荐、提携“廉明勤干”、“防截有功”之人补任水师将领。针对违禁夷船以枪炮相恐吓而师船不敢使用枪炮的情形,林则徐据实上奏,声称对那些违禁夷船仅空言驱逐无济于事,“惟有严行惩办,乃可震慑其心”,提请允许水师官兵可以枪炮还击甚至火攻。清廷一方面同意林的请求,但同时强调“亦不至骤开边衅,方为妥善”。 为彻底打消朝廷的顾虑,林则徐专折奏陈“英夷非不可制也”诸项事由,力主严惩英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2]针对师船从不敢主动攻击、一味被动应对的作法,林则徐亦深不以为然,“英夷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向来师船未与接仗,只系不欲衅自我开,而彼转轻视舟师,以为力不能敌”。[33]他主张应该主动出击,以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效果。当英人公然挑衅并引发九龙之战后,林则徐决定还以颜色,密派水兵、水勇攻袭停泊在潭仔洋面的趸船“丹时那”号并将其烧毁。事后,林则徐通告闽省当局,除重申粤闽两省一体严防外,还提出“将夷船烧毁一二”的建议。[34]这一事件开启了水师官兵主动攻剿夷船的始端。
再者,善于斗争。在策略上,以守为战与以战助守相结合。“以守为战”是清代应对海上威胁的基本策略,即不在外洋与敌交锋,而是固守内洋与陆岸,待敌人进入内洋或登陆再将其制服。该策略与清朝水师实力疲弱、不善远涉的状况较为切合,如果部署得当,亦不失为扬长避短的好方略。林则徐忠实履行相关指令,精心筹备口岸防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近口门”,并得以阻断内地匪船对外海夷船的接济。然而,仅凭“近守”终究无法从根本上靖除“远患” ,甚至一度成为一些官员逃避外洋执法的借口。林则徐没有死搬教条、墨守成规,而是审时度势,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主动出击,从而使外洋执法变得灵活而富有成效。在人力上,正规水师与团练水勇相结合。过往经历表明,水师外洋执法不力不仅仅是实力问题,还存在深层次的腐败原因,重振水师虽势在必行但绝非短期内所能奏效。林则徐的解决之道是借助民力,他相信民心可用,动员沿海乡民团练抵御,他还亲自招募5000名水勇,[35]经过培训后加入到水师队伍,成为外洋执法的中坚力量。在战法上,以正御敌与出奇制胜相结合。一方面,林则徐要求水师官兵继续执行之前的“驻洋守堵之法”,以保持正面防御的态势。另一方面,他深切认识到英夷“船坚炮利”,在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而师船“木料不坚,未便穷追远蹑”,以短御长,实非明智。根据“夷船最畏焚烧”的弱点,[36]总结出“偷袭火攻”之法,即准备大小火船若干,每船由一二兵弁领携水勇多人,先赴外洋各岛澳分头埋伏,候至夜深夷船睡熟之际,察看风潮皆顺,即令一齐放出,乘势火攻,如能烧得夷船,倍加重赏。[37]经过多次偷袭火攻,对外洋夷船已然形成“惊慑”之势。[38]值得一提的是,林则徐在外洋执法方面的突出表现,除自身具有较高智识外,不得不说与其主动获悉夷情的难能可贵的品行息息相关。在当时“华夷之辨”根深蒂固、甚嚣尘上的社会背景下,林则徐勇于突破陈腐观念的束缚,通过翻译西文报刊、探访夷人侨眷,搜集了大量第一手夷情资讯,为他了解国内外情势并进而作出理性研判、正确举措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与同时期其他官员对夷情闭目塞听、一无所知,应对夷患主观臆断、章法全无形成鲜明对照。
林则徐外洋执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它直接打击了海上作乱的外国船舶,维护了外洋正常的通商秩序,最终促成海口事件的成功告罄。第二,它向西方国家宣示了中国的领海主权。清代中国虽无领海之名却有领海之实,“外洋”即类似于西方的领海。来华英人罔顾这一事实,大肆宣扬伶仃外洋“如荒弃地方”,可任由外国人停泊;[39]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罗便臣索性将办公地点搬迁到伶仃外洋的一艘船舶上,声称这里“在中国人的权力范围之外,完全不受中国人约束”,[40]并妄图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殖民据点。而此前广东水师不敢到外洋执法、不敢针对夷船执法的作派更是助长了英人的狼子野心。林则徐在外洋采取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不啻再次严正声明:外洋绝非“法外之地”,而是隶属中国主权管辖下的海域,展示出维护领海主权的坚强决心。第三,它为后来的军事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如鸦片战争之初,清廷根据林则徐的建议,大规模召募水勇作战,水勇的战时表现令不堪一击的正规水师相形见绌,成为一支无可替代的抗英武装力量;再如,林则徐总结出的火烧夷船的原则和做法,被其他沿海诸省仿效,在战争实践中屡建殊功,尤其是战争末期,奇袭火攻一度成为清军赖以御敌的唯一战法,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争颓势,亦不失岌岌危殆中难得的一丝亮色。总之,林则徐外洋执法的经历深刻影响着历史时局,在鸦片战争史乃至中国近代海防史、军事史上均应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1][7][11][12]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224-225、4、27页,1988。
[2][6][14][2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台北:文海出版社,第336、121、90、51-52页,1966。
[3][4][5][10][20][21][22][24][25][26][27][3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第9、38-39、55-60、137-138、65、69、134-135、347、426-427、166、150、159、722页,1992。
[8]《乾隆致英王第二道敕谕》,《华东续录》乾隆朝一一八卷。
[9]《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七日上谕》,《华东续录》乾隆朝四六。
[13][28][31][32][33][36][38]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第155、155、156-157、186-188、194、381、305页,2002。
[15]《清史稿》卷一三八《兵九·海防》。北京:中华书局,第4115页,1976。
[16][19](清)方浚师:《蕉轩随录》卷八《海洋记略》。北京:中华书局,第38页,1995。
[17][18]《钦定大清会典则律》第一一五卷,第48页。
[29]清代江苏洋山洋属外洋。见王宏斌《清代前期江苏内外洋与巡洋制度》。《安徽史学》2017年第1期,第27页。
[30]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稿》,第83-84、118-119页。
[35][清]魏源:《圣武记》卷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版,第459页。
[3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二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第27-28页,1992。
[39]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十册《译编》,第265、331页。
[40]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第91页,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