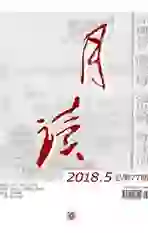唐德宗初年的改革
2018-05-09张国刚
张国刚
上一期讲到了宪宗朝裴度铲除藩镇之事。关于唐朝的藩镇割据,还应从安史之乱以后的政局说起。
公元763年,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结束。但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之以节度使的称号,由其分统原安禄山、史思明所占之地。于是,朝廷任命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嵩为相卫等州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部分地区,共四镇。其后,薛嵩为田承嗣所并,四镇变成了三镇,史称“河北三镇”。这三镇名义上虽服从朝廷,实际则属于独立状态,军中的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为了防范河北的藩镇,朝廷在中原建立了很多藩镇,边疆地区设置的藩镇同样不能撤掉,因为边疆形势也很严峻,于是就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所以我们说从唐代宗初年到唐德宗末年,是藩镇割据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一、德宗即位
唐德宗李适,是代宗的长子,母亲睿真皇后沈氏,天宝元年(742)生于长安大内之东宫。李适的整个少年时代,正值大唐帝国昌盛繁荣的辉煌时期,但好景不长,他14岁那年即755年的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变迁中,李适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他做过天下兵马大元帅,封鲁王、雍王,后因讨平安史叛军有功而兼尚书令,广德二年(764)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即位,时年三十八岁。
代宗对藩镇采取姑息的态度,当时还是太子的李适对此就非常不满。所以,他继位以后很想在藩镇问题上有所作为。
德宗首先要解决的是朔方军过大的问题。平定安史之乱,最重要的一支军队就是朔方军(治所在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那么当时的朔方军统帅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子仪。郭子仪担任的职务,史书记载为“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可谓“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因而“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a。德宗继位后,尊郭子仪为尚父,胡三省对“尚父”一词解释说:“太公望为周师尚父。说者谓可尚可父,天子师也。”b这是给予郭子仪极高的尊荣。此外,还“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壻迁官者十余人”。朝廷给了郭子仪这么高的待遇,换来的是将其“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并把他所领的军区一分为三:“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a
除了解決郭子仪的朔方军问题,德宗还要换宰相。当时的宰相常衮,“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b。有一个叫崔祐甫的官员,对常衮有一些不满,两人于是发生争执,“声色陵厉”。常衮不能忍受,就说崔祐甫“率情变礼”,要将其贬为潮州刺史。德宗以为惩罚太重,便将崔祐甫改贬为河南少尹。
这个时候正赶上郭子仪等人入朝。郭子仪也是宰相,但他是使相。什么叫使相呢?就是凡担任节度使、枢密使、亲王、留守的重臣,其检校官兼三省长官(侍中、中书令、尚书令)或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为使相(出使在外的宰相)。使相不在中央为官,而是在地方处理政务。按照此前的规矩,凡是宰相提出的报告,由首席宰相签名,并且代使相签名,就是说不需要通报使相,因为使相在地方上,那时候也没电话,通报起来很麻烦,容易耽误要事,因此代签字就行了。
对于崔祐甫贬官一事,郭子仪等人入朝时“言其非罪”。德宗觉得很奇怪,就问道:“你们自己不也是同意的吗?为什么又说他不该被贬呢?”郭子仪等人回答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原来,当时常衮独居政事堂,他代郭子仪等人签了名来弹劾崔祐甫。
德宗刚继位,认为常衮欺罔,大骇,觉得你身为宰相怎么能这么做,怎么可以没有跟别的宰相商量就以个人名义贬逐崔祐甫。当天德宗便下旨,贬常衮到潮州当刺史,而将崔祐甫提拔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对于这件事,“闻者震悚”。德宗大骇,“骇”的是什么?就是常衮“欺罔”。德宗这种人不容许别人欺骗他,很有点神经质的紧张,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从这件事上可以表现出来。应该说,德宗分了郭子仪的权,表现出了他的魄力;而他换宰相一事,则表现出了他的敏感。
二、德宗的改革
德宗继位后还着手治理的一个弊病,就是宦官问题。肃宗、代宗优宠宦官。宦官到地方出使,向地方官员索要东西,皇帝也不禁止。有一次,代宗派一个宦官到一位妃子的家中送赏赐。回来之后,代宗问宦官,这家人给了你多少回礼?回答是给得很少。代宗听后很不高兴,认为这是看不起自己的使者。这个妃子得知此事,十分害怕,赶紧把自己的珍宝送给这个宦官。从此以后,宦官更加猖獗,到哪里出使都公然索要礼物。到宰相那里,也照收不误,因此宰相的办公室必须经常存点钱,宦官来了,就要送上,不能让他们空手回去。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就是公开鼓励贪腐啊!德宗素知其弊,所以他继位以后就用严厉的手段加以纠正,受贿的宦官将被处死,这使得当时出使的宦官纷纷把接受的礼物扔掉。宦官索贿、受贿之风由此得到遏制。
与此同时,德宗还剥夺了宦官的兵权。神策军是当时一支重要的军队,统领者王驾鹤是个宦官,德宗让一个叫白琇珪的朝官来替代王驾鹤的职位,担任禁军的大将军,而让王驾鹤做东都园苑使,照看皇家园林,就是让他去做宦官应该做的事。
德宗还对财政进行了整顿。他让刘晏来做转运使。转运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央派到地方去的财经官员,主要负责盐铁的专卖和漕运的事务;盐铁专卖和漕运,是当时税收的主要来源,占到全国总收入的一半。德宗让刘晏对征收体制进行了改革。
另外,就是改革国库制度。此前,国库和宫中的用度是分开的,就是说国家的钱是国家的,皇帝私用的钱是皇帝自己的,二者不相掺和。可是安史之乱期间,这个制度被破坏了。当时负责财政的官员,顶不住那些军将不断地向他索要军饷,所以财政官员干脆把赋税送到皇家的内库里,由宦官来掌管,这就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到后来,财政部门的人根本不知道天下收了多少钱,支出多少钱。而“宦官领其事者三百余员,皆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a。
德宗继位的时候,宦官不仅掌军,还管财,这都是肃宗、代宗惯下的毛病。当时,一位财经官员叫杨炎,他跟皇上讲了一段关系国家命运的话:“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岁用几何,量数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后可以为政。”b就是要求皇帝把国库的财政交给国家的财政部门掌管,宫中每年需要多少,确定数字之后留下来,绝对不敢有缺。皇帝当天就下诏,所有的财富归左藏库,完全按照安史之乱前的旧规矩,从中挑三五千匹绢,绢就是钱财,纳入大盈库。这个杨炎对税收还做过一个改革,就是推行两税法。两税法其实酝酿于代宗时期,但成就在德宗时期。两税法就是把过去按人头征税,变成按财产征税,每年分两次征收,这反映了一种新的财产关系的变化,是一种进步。两税法对后来明朝的一条鞭法,乃至清朝的摊丁入亩都有很大影响。人头税逐渐减少,财产税逐渐增加,这是比较合理的税制改革。
对于财政的改革,还有一点。在代宗的时候,遇到皇帝的生日,或是过年过节,都鼓励地方上给皇帝送礼,送得越多皇帝就越高兴,所以地方官员经常以这个名目进行加税。德宗继位后,把这种送礼之风也给废除了,反映出了一种新气象。
对于官员的腐败,德宗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但在反腐败方面,却也暴露出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史书记载:“大历以前,赋敛出纳俸给皆无法,长吏得专之。”a朝廷不反腐败已经有二十年了。现在,德宗对那些腐败的官员,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加以惩处。可是,在反腐的过程中,德宗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刚继位的时候,疏斥宦官,亲近朝士,像“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但后来他发现这些朝士先后因腐败被弹劾。于是,宦官和武将们就有借口了,他们说:“你看这些文臣动不动就贪污这么多钱,还说是我们把天下搞乱了,这不是欺骗蒙蔽皇上吗?”史书中用了“欺罔”一词,对于这个词,我们应该不陌生,前面德宗对常衮的批评就是说他“欺罔”,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就是说皇帝此时心里有些犹豫了,我到底应该信任宦官呢,还是武将呢,还是文臣呢?他刚继位的时候,一心想疏远宦官武将,现在发现自己亲近的文臣也这么贪腐,于是开始举棋不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德宗虽已是不惑之年,但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幼稚。文官有贪腐的,也有不贪腐的,惩治贪腐不能靠文官、武官或者宦官来决定,而是要靠一套反腐的措施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