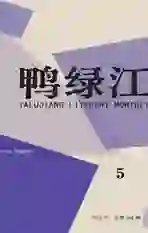燕园吾师严家炎
2018-05-08吴宝三
吴宝三
1984年春,严家炎先生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我当时在辽宁兴城林業疗养院工作,曾去信祝贺,很快接到他的回信。信中说:“虽然好久没有联系了,偶或看到你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的诗,总感到非常高兴,给我带来很大的温暖与安慰。就像又回到了往日促膝谈心的那种境界里,那么亲切,那么令人神往。”
“你不该向我祝贺,而该为我一哭。搞上这个工作,每天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几个小时泡进去,有时连星期天也不得安宁,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写东西(近年发表的,都是前两年写成的稿子,或是利用节假日赶出来的),实在苦不堪言。如果我作出牺牲,能换来全系面貌大改观,为全系师生创造较好的条件,那也值得。问题是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们的许多设想,常常被碰回来,手脚被捆得紧紧的,简直动弹不得,怎么能打开局面呢!再过半年若还是这样,那就只好要求辞职了!”信中引用了《庄子·大宗师第六》中的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动情地回顾了我们开门办学,在密云县穆家峪公社前栗园大队朝夕相处结下的情谊,然后无可奈何地说,尽管鲁迅不赞成庄子的话,但到了江湖也有江湖的难处,社会兼职太多,有许多想要做的事做不了,心甚不安。同时寄来了他新出版的论文集《知春集》,扉页上端写了一行书小草:宝三学弟指正。他生于1933年,长我一旬,虽同属鸡,却是我的恩师,几十年来,对我总以学弟相称。手捧这本论文集,我沉思良久,心潮难平。可以说,在燕园,严先生是我最亲密、最知心的师长之一。
文艺界许多人不会忘记,1961年,严家炎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多篇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文章,并引起一场大论战,后来导致全国公开点名批判所谓的“中间人物”论,邵荃麟、严家炎首当其冲。挥舞大棒的急先锋不是别人,正是其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文元。那一年,严老师只有27岁。1972年在密云乡下,我俩躺在一铺大炕上闲聊,我问严老师:“你那时认识姚文元吗?”他并没有感到意外,语气极平和地说:“开文代会时,我们见过面。我和他父亲姚篷子先生更熟悉些,姚父总是称其为竖子……”说罢,淡淡地一笑。粉碎“四人帮”之后,严老师把几篇关于《创业史》的评论文章收入《知春集》中,他在“后记”中写道:“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关于《创业史》的几篇评论均未做改动。今天读来,这些文章在某些观点上也许不是没有问题,有些措辞似嫌轻率,现在读起来有几分吃惊。”他只字未提自己和“四人帮”如何斗争,也没有标榜自己是反对“四人帮”的勇士,这种客观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多么难能可贵!翌年,他出版了另一本论文集《求实集》,获北京市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88年与唐弢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获全国第一届优秀教材奖,1992年专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教材奖。曾荣获五一劳动奖章。
严家炎先生,笔名稼兮、严謇,上海人。15岁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北大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提前毕业。历任该校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系主任,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员,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他名如其人,文如其人,无论做学问还是为人处事,一向严谨缜密,严上加严,一丝不苟。这些年来,他给我写过三十几封信,每封信的信封上,省市单位街道门牌号无一省略。邮票一律贴在右上角,无一破例。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小事:在密云乡下时,一次吃过晚饭,天已尽黑,我俩从食堂摸黑回住地。路上,听到大队部正广播通知开会,严老师说播音员是房东家的何姑娘,我说大概不是,何姑娘的声音要标准些。他坚持说是,我坚持说非,于是我俩打赌,谁输谁买一斤糖请客。我以为不过说说而已,孰料他竟一个人跑到广播室去核对,回来后满头是汗,一边从兜里往出掏糖,一边连说:“我之错!”
“文革”期间,系里组织批斗“五一六”分子。我做梦也未料到,严老师竟被打成“五一六”头子,依据是,全国大大小小的作家几乎都认识他,无疑是“五一六”分子的总后台。第一次批斗有百余人,只见他从一辆破旧自行车上缓缓下来,从容不迫地走进会场,摘下口罩放在上衣兜里,平静地坐在批斗席上,不管主持者和革命群众如何狂轰滥炸,他总是那么两句话:我实事求是地讲,我不是。声音很轻、很慢,口气不像是在分辩,似乎在向学龄前儿童讲清楚一件事。毫无疑问,严老师当然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我真不敢相信,军宣队、工宣队怎么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误导学生呢?!在这次批斗会上,我一言未发,倒不是不相信军宣队、工宣队,而是直觉告诉我,像这样一介书生(严先生自己也这样说),只知埋头勤奋做学问,怎么会成为组织什么打砸抢的“五一六”分子呢?散会后,我把他穿的旧棉猴大衣递给他,他向我微微点了点头,眼神里颇含谢意,彼此的印象恐怕就是这样留下的。我钦佩他面临这样巨大的压力,心境平和,从容镇定,以至由此我联想到革命者的视死如归。后来严老师当了文学专业的支部委员,还是我的入党培养人。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似乎接受过什么反面教训,少了一点年轻人的锋芒。他不会知道,我也同他一样被造反派批斗过,有几分棱角似被磨光。在严老师的培养帮助下,我于1972年2月在校入了党,党委批准之日易记,那一天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达北京。
1984年,我在《北方文学》发表了一组诗,名为《海滨抒情》,严老师读后立即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辽宁的一家报纸上。没想到,这篇评论在我所工作的兴城引起强烈反响,县委书记将此文批转给主管领导和部门,主管文化的副县长苗会田连夜给我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千言长信,邀我参与为宣传兴城——第二个北戴河造势。这之后,名人纷至沓来,郎平任队长的中国女排来兴城集训,乔羽、王酩、凯传、晓光等为兴城而歌,艾青、杨沫、峻青、王扶林等为兴城鼓与呼,范曾、王遐举、魏哲等为兴城挥毫泼墨……著名评论家黄益庸先生在他主编的《北方文学》上,转载了严老师的这篇评论,而我则把此文作为赞颂兴城第一部诗集的序言。
毕业后,我每次去北京都要去看看严老师。他请我吃饭,大都选在北大对面的海淀饭庄。边吃边聊,不知唤起多少对艰难岁月的回忆,其中有欢乐,亦有悲伤,提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禁不住黯然神伤。
那年盛夏时节,严老师从美国哈佛大学作学术讲演归来,专程来兴城看我。那时我的三个女儿还小,他给孩子们买了玩具,当提起孩子的名字时,严老师还记得,他一本正经道,我写给你的信说过,吴为、吴非,名字起得很有一点道家的味道。在兴城,我俩无话不谈,谈得最多的还是在京郊乡下那段日子,因我有胃病,可谓同病相怜,我感谢他给我买苏打饼干,给我邮寄胃药猴头菌片,他说记不得了,只轻描淡写地轻轻带过,而提起兴城却兴奋不已。谈明代古城保存如此完好,令他流连忘返;谈乾隆皇帝,诗多好的少;谈努尔哈赤攻打宁远(兴城)唯一的一次败北;谈降将祖大寿成了英雄。回京后,他写了一篇散文《祖氏牌坊》,刊发在《人民日报》上。同年秋天,我携妻带女去北大看望严老师,在他家里做客,他亲自下厨,弄了十五六个菜。最让我们夫妻俩难为情的是,两个女儿从海边来,对海鲜并不格外喜欢,可在严老师家里,拌海蜇皮却被一扫而光,严老师看孩子们喜欢吃,又去做了一盘。这个菜是否做出了上海菜的风味,现在也不得而知。最让女儿惊叹的是,严老师的家里,满屋子满桌子满地都是书,没有回身之地。严老师的夫人卢晓蓉称先生是“书虫”,或许再贴切不过了。
【责任编辑】 宁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