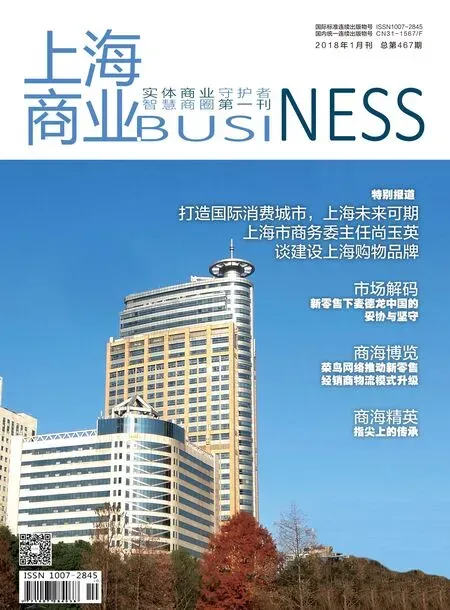网约车平台法律地位探析
2018-05-05何彦辰
文 /何彦辰 汪 琴

伴随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颁行,我国网约车市场已从无序的雏形期走向了规范化的成熟期。尽管我国对网约车这一新兴产业的包容性和开放态度超过其他国家,但是囿于法律的滞后性和不周全性,网约车新政实施一年多来,关于网约车的社会问题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特别是因网约车平台法律地位不明确所引起的纠纷甚为突出。鉴于此,为了保障我国网约车市场稳定有序发展,有效保护网约车乘客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就网约车平台的法律地位作一深入探讨,冀望对建立健全我国网约车平台管理法律制度有所裨益。
一、我国网约车发展现状及其面临的困境
网约车利用互联网技术,打破传统出租车信息不匹配、管理制度僵化等缺点,最大化的利用社会交通资源,解决乘客出行难题,符合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网约车行业从萌芽到成熟,从法外之地到合法地位,经历数个阶段。网约车平台的发展则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2010年-2012年,这一阶段以出租车接入网约车平台为主。出租车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与乘客端的信息匹配度,改善传统巡游揽客方式空驶率高的问题。其次,2013-2015年,网约车行业开始呈现井喷式发展,市场出现了数十款打车软件。网约车市场开始急剧扩大,并成为独立业态。最后,2016年至今,网约车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2016年7月28日,网约车《暂行办法》发布,并于同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网约车平台取得合法地位,并需要负承运人责任。
通过对网约车平台三个阶段发展规律的总结,发现随着网约车市场规模的扩大,网约车平台法律地位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网约车新政以来,随着平台合法地位的取得,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网约车平台的具体法律地位仍不明确,平台行为规范缺失,相关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二、我国网约车平台运营机制遭遇困境的根源
网约车平台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出现了政府的监管、交通事故的责任分担、乘车价格的变动等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网约车平台自身的技术特点导致其法律地位不明确
网约车平台是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支撑下产生的。信息的处理能力是其核心竞争力。网约车平台自身的技术特点使得用户认为平台为居间人。
平台是乘客和司机之间客运合同的桥梁纽带,乘客与司机的承诺和要约以数据的形式在平台的数据处理器上进行交换。当乘客将乘车的要约以数据形式发给司机,而司机将承诺同样以数据信息形式发给乘客,并出现在乘客的手机屏幕上时,客运合同就已经达成。而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只是提供数据传送的服务,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客运合同的达成中。并且乘客的给付具有不确定性,乘客可能中途取消订单或延迟给付。网约车平台依靠提供信息和信息服务获取收益,并且对信息进行绝对的支配。根据“利益管控”和“风险运行”理论,平台实际上参与了乘客与司机之间的客运合同的订立过程中。乘客在与司机之间的订立合同的过程离不开平台,平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现行法律法规关于网约车平台地位规定的缺失
首先,《暂行办法》在网约车平台公司这一章中,对平台的法律地位没有做出特别规定。笔者认为,由于平台不是承运人,所以就规避了许多承运人的义务。新政下,网约车的经营要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三证齐全。但是实际过程中三证并不齐全的司机照样继续营运。由于网约车平台辩称自己只是合同的居间人,只为乘客与司机订立客运合同提供信息,并不直接参与到运输过程中。平台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放任这种行为。由于政府执法难,细则很难落实到位。正是由于平台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对网约车的监管陷入了平台暗中违法、政府难以执法的尴尬境地。
其次,网约车平台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主体,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明确,有关的网约车平台行为规范尚未出台。
笔者认为平台对司机和车辆的监管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当平台能够对人和车实施有效监管,政府对平台的监管才能发挥作用。
最后,《暂行办法》第16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但是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中受伤的乘客或者第三人在对平台的索赔比较艰难,平台与司机常常互相踢皮球,都不承认自己是承运人。
(三)网约车自身的特点导致网约车平台法律地位不明确,平台、乘客、司机之间责任分配不清
非自营模式下网约车的车辆和司机来源较为复杂,使得法律关系也较为复杂。在不同情形下,网约车平台的法律地位不同。车辆可能来自于汽车租赁公司或者私家车,司机可能来自劳务派遣公司或者私家车主。通过正常组合,可以形成“汽车租赁+劳务派遣”、“私家车+私家车主”这两种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下,司机和车辆是分开的,运输服务由“平台+汽车租赁+劳务派遣+司机+乘客”共同完成,涉及到五个主体,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在该种模式下平台不是承运人,而是双方运输合同的促成者和交易信息的提供者,因此对交通事故不承担承运人的责任。在第二种模式下,司机和车辆是合二为一的,运输服务由“平台+私家车主”及其“车+乘客”完成,法律关系就比较简单。在该种模式下平台是客运服务的组织和领导者,也是事实上的承运人,需要承担承运人责任。
(四)网约车平台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
网约车服务的出现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网约车平台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网约车与传统的出租车有着本质的区别。出租车受到严格的政府监管、价格管控和牌照限制,交通管理部门中有专门部门对出租车进行管理。网约车作为一种新业态,准入门槛低,服务性价比高,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发展起来的。由于网约车和出租车发展所处的环境不同,对它们的监管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但是,现实中监管者乃至立法者都没有明确网约车的市场主体地位,赋予网约车平台主体地位应有的权利。
三、美国关于网约车平台法律地位的立法例及对我国的借鉴
网约车在2009年起源于美国。开创该业务的Uber已在全球220多个城市开展业务。美国在对网约车平台法律地位的处理上对我国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明确网约车平台定义和创新监管模式
美国许多地方的监管和立法机构都在探讨如何界定网约车平台的法律地位,希望能够明确平台公司在运输服务中的地位,从而为政府的监管提供法律上的支持。2013年9月19日,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CPUC)做出决定,承认网约车服务的合法性。
笔者认为加州模式下网约车平台地位明确,即交通服务提供者。同时政府监管平台,平台再监管司机的方式责任清晰,不易出现平台借法律地位不明从而逃避责任的现象。
(二)运价的市场化,确立网约车平台市场主体地位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法案解除了出租车预约服务的运价管制。法案实施前,特区的出租车运价都受政府管制,乘客和司机之间信息不对称。但立法过程中,立法机构认识到,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技术的发展,这种信息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平台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掌握定价权,从而使价格能够反应供需关系,有利于交通资源的合理配置。
四、明确网约车平台法律地位,加强网约车平台监管的建议
网约车平台法律地位的明确,事关乘客合法权益的维护和网约车市场的有序发展,对加强政府监管和相关矛盾的解决有重大意义。
(一)明确网约车平台在客运合同中的法律地位
网约车若继续发展,前提是明确网约车平台的地位。网约车法律地位主要有居间人和承运人之争,其判断的标准是网约车平台是否实际参与了运输合同的实施过程。上文中提到,美国加州地区在网约车合法化的过程中,将网约车平台称为交通网络公司,并认为其提供交通服务。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加州的做法,将网约车平台定义为客运合同中的承运人,有利于增强平台的社会责任意识,促使平台加强对所属司机及其车辆的监管,极大减少不合规车辆和人员的存在,从而保障乘车人的安全。《暂行办法》虽然规定了平台要承担承运人责任,但是没有直接把网约车平台作为交通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这对乘客的维权不利。笔者建议完善《暂行办法》,对各方承担的责任进行具体规定,明确网约车承运人地位。
(二)政府应赋予网约车平台相应的监管职能
网约车是一种新业态,不能用传统方式进行监管。加州地区政企合作的监管方式值得借鉴。政府行政资源有限,对网约车司机和车辆的有效监管需要平台合作。我国的监管模式实际上参考了传统出租车的模式,对平台、车辆、司机三方都进行监管。笔者认为这种监管模式既浪费了行政资源,又难以实际解决问题;既没有考虑到网约车发展的特点,又没有有效实现监管。因此不妨借鉴加州政企合作的模式,政府将对车辆和司机的条件审核权赋予平台,平台对车辆和司机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发给许可证。笔者认为这种模式至少有两点优势:其一,减少行政成本的同时提高监管效率;其二,通过对监管的创新,根据网约车市场和技术应时而变,为网约车的发展提供了开放包容的环境。政府监管路径的创新实质是对网约车平台法律地位的创新,通过委托的形式,将政府的监管权授予平台。有权必有责。为了规范平台的监管权,必须强化政府对平台的监管力度,政府加强对平台条件的审核,符合条件的发给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及时取缔。同时平台在对符合条件的车辆和司机发给许可证后应及时向政府报备,政府为了乘车安全,应当定期检查,对违规的平台进行处罚。同时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网约车平台行为规范》,将平台需负的责任明确化。

(三)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指导涉网约车交通事故案件的判决
随着网约车用户的增加,涉及网约车交通事故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前文中笔者认为网约车平台在客运合同中应为承运人。运输合同生效后,承运人负有将旅客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 对于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使得旅客生命,财产遭受的损失,平台应当负损害赔偿责任。司机与平台在运输过程中紧密联系,谁也离不开谁,两者共同为乘客提供客运服务,成立“准合伙”关系。司机和平台在对外承担责任上具有一致性,即共同对外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对内则应按过错比例分担责任。现实中,由于个别司机经济能力有限,无法及时给付赔偿,此时应由平台先行赔付,平台有权向司机追偿。为了统一案件审理标准,需要两高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将案件担责原则明确化。应当注意的是,顺风车、拼车等合乘行为不属于平台的经营活动,属于民法上的好意实惠行为,笔者在前文中并未涉及。关于这类合乘的事故处理,笔者认为应将平台认定为居间人,具体处理原则仍需讨论。
(四)确立网约车平台的市场主体地位
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网约车的价格变动应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暂行办法》规定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除外。网约车并非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完全没有必要实行政府指导价。这反而导致地方政府出于各种利益考量,对网约车价格实行干预,不利于网约车健康发展。参考美国华盛顿地区对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化,尊重网约车市场主体地位。笔者认为网约车的出现是市场发展形成的,网约车的运价也应由市场来决定。让价格充分反应供求情况,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助于解决公众出行难题。笔者建议尊重网约车平台市场主体地位,由乘客与平台决定网约车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