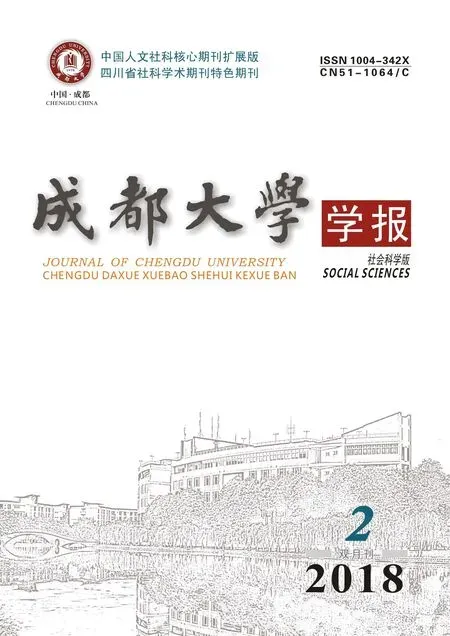《三国志补义》的内容与特色*
2018-04-28刘治立
刘治立
(陇东学院 历史与地理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一、《三国志补义》的内容
《三国志补义》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在字词释义、时间、地点辨正、典章制度索隐、诸家说法比较等方面均有阐发。
(一)注释音义,勘正字句
(二)阐释地理,辨析时间

(三)解析典故,阐发制度
典故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故事或传说,以及由此形成的有具体出处的词语。而制度指历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所指定和推行的政策、法规及具有法律效力的习俗等。康发祥在《三国志补义》中注意揭示典故,如《刘二牧传》“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台访‘物故’之义,高堂隆答曰:‘闻之先师:物,无也;故,事也;言无复所能于事也。’”康发祥引用了裴松之的注解,进一步认为,“今人谓人死曰‘物故’,本此”[1]750。《魏延传》记载,魏延与杨仪不和,“有如水火”,康发祥说:“按时人以不相能为水火,语本此”[1]758。
各个时代的货币单位变化比较大,康发祥以丰富的知识对其进行梳理。《吕蒙传》记载,孙权给吕蒙“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一亿到底有多少,康发祥做了详细的解释:“按亿有大数,有小数。十万曰亿,乃小数也;万万为亿,乃大数也。孙权于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余年铸当千大钱。荆州之定在建安二十四年,未有当五百、当千大钱。所赐之钱,乃泛用之钱耳,以黄金五百斤准之,则非小数之十万,必为大数之万万可知。”[1]826三国时期,蜀汉的许多官职只是遥领,法正之子邈官至奉车都尉、汉阳太守,当时汉阳郡(治今甘肃甘谷县)并不在蜀汉的辖区,康发祥注解:“按汉阳时已入魏,此盖遥领之耳。张翼领扶风太守,亦犹是。”[1]755
(四)比较诸说,说明原委


基于对三国正统的判定,《三国志补义》在编次上不按陈寿原书的次序,采取先蜀汉而后曹魏的编排顺序。卷一首篇是《先主传》,其次是《后主传》和《二主妃子传》,其后才是《刘二牧传》。对于这样的安排,康发祥解释说:“按陈《志》以二牧列昭烈、安乐之前,殊觉不合夫《蜀志》,以焉、璋列二主之前,何不以董卓、袁绍诸人列曹氏父子之前乎?今从《前汉书》陈胜、项籍、张耳、陈余,《后汉书》刘元、刘盆子、隗嚣、公孙述俱列帝纪后之例,移置于此。”[1]749康发祥以两《汉书》的史例为根据,做出这样的顺序调整。这种观点刘知几已经提出,“陈寿《蜀书》首标二牧,谓益州牧,即焉、璋也。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刘知几提出了问题,而康发祥将之付诸实施。由于帝蜀而抑魏,对三国志的原有标题也做了改写,如《先主传》和《后主传》下分别注以“陈书曰先主、曰传,今当改正曰《汉昭烈帝纪》”,“陈书曰传,今当改为纪”[8]35。而曹魏四卷帝纪,也做了改正,《武帝纪》下注明“陈志曰纪,今当易曰传”,在《文帝纪》《明帝纪》和《三少帝纪》下则注“陈志曰纪,今易同前”。

二、《三国志补义》的特色
康发祥的“补义”,最突出的成就不在字词的解释,时间、地名的考证等,这是清代考据学者注释《三国志》的共同目标。对三国志的解读、对裴松之注的研判,以及对《三国志》体例的讨论,是其书的不同于其他注本的特色。
(一)对《三国志》及裴注的独到见解
以“义”为名的注述,汉以前多是说明经学典籍的义理,其体式和古代传注相近。六朝以后,则专以解注者为义,与义疏同意。作注而说其义,是义的内涵,何宴《论语集解序》:“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疏曰:“谓作注而说其义。”这种注释在作文字训诂的同时阐发原作之义理,在经学一统学术的地位动摇的背景下,为许多经史注释者所采用。以阐释所解书籍的要义的义体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盛行起来,出现了许多义体注本,如南朝梁时崔灵恩有“《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9]677。康发祥将其著述命名为“补义”,表明其书主要是要阐发自己的见解,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三国历史的看法,二是对《三国志》的见解,三是对裴松之注的认识。
1.对三国历史的看法


2.对《三国志》的见解


康发祥深受正统儒家思想的浸润,对春秋笔法非常赞同,对于《三国志》中的“书法之妙”也很注意发掘。陈寿在《吴书·濮阳兴传》中揭露丞相濮阳兴身居宰辅,虑不经国,勾结宠臣张布,“与休宠臣左将军张布共相表裹,邦内失望”。康发祥评价说:“按堂堂之相,与宠臣比周,宜其死也。曰丞相曰宠臣,此书法牵连之妙。”[1]836陈寿有意溢美曹操,但有些地方还是体现了直笔,曹操率军进攻陶谦,“所过多所残戮”,康发祥说:“按承祚作魏志,每多曲笔回护。兹言多所残戮,此直笔也”[1]768。司马昭指使成济袭杀曹髦,《三国志》仅言“高贵乡公卒”,对死因只字不提,历来为史家诟病,刘知几在《直书》中对“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杜口而无言”[8]69予以谴责。梁章钜也发出了质疑:“前此幸太学、幸辟雍皆称帝,至此忽改从旧号。且明系刺死,而但书卒,不可解”[12]277。康发祥愤怒地指斥:“按司马昭之心路人知之,云龙门之变,昭假手于成济,抽戈犯跸,遂成恼恶。史不能大书特书,暴其罪恶,乃假以皇太后之令,多方掩饰,以欺万世,可谓悖矣。且于帝髦之死,祗书曰卒。夫即以髦帝制不终,仍从旧爵,亦当以薨书,不应以卒书。何物鬼魅,操此史笔。亮哉,黄东发之言欤!按《晋书·天文志》于彗星见角下,大书曰高贵乡公为成济所害;于客星见太微下,大书曰高贵乡公被害;于日有蚀之下,亦大书曰有成济之变。《晋志》不讳言,承祚之史何悖谬如此。”[1]773康发祥痛斥这种回避真相的历史记述为“悖谬”。
3.对裴松之注的认识


裴松之征引材料是很审慎的,对于一些记述还表达自己的看法,如《诸葛亮传》摘引了有关空城计的记述后表示,“举引皆虚”。《文聘传》记载,“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裴松之引用《魏略》的材料做补充,“孙权尝自将数万众卒至。时大雨,城栅崩坏,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补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虽然裴松之也表示“《魏略》此语,与本传反”,但对这一则“空城计”没有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论断,“按《魏略》实属不经,岂有大兵临城而可以卧而却之乎!况孙权雄才大略,岂肯不攻而去,竟如小儿之可欺乎?吾观魏臣诸传,每多虚誉,而《魏略》尤甚,识者鉴诸。”[1]794《魏略》所记述的文聘卧舍却敌,显然是低估了雄才大略的孙权的智商,这种虚誉可谓荒诞不经,不可轻信。
三、对《三国志》的体例的卓见

由于特殊的身世和经历,历史人物往往有多个名字,如马忠“少养外家,姓狐,名笃,后乃复姓,改名忠”[2]1048,陆逊“本名议”[2]1343。在叙述中应该前后一致,不要诸名杂用,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李严于建兴八年改名为平,《李严传》中前半部分称“严”,后半部分则呼为“平”。康发祥认为,“李严既于建兴八年改名‘平’,传中不应前后异名,宜始终以‘平’名之,以从马忠、陆逊诸传之例。否则《马忠传》何以不前曰‘狐笃’,后曰‘马忠’;《陆逊传》何以不先曰‘陆议’,后曰‘陆逊’也。”[1]758
在《吕布传》中,突然插进一大段张邈的事迹,虽然与下文有一些联系,但还是显得很突兀,康发祥说:“按《吕布传》中夹张邈一传,既非合传,又非附传,其体例特奇”[1]780。虽然没有明确否定,但还是将其点出,暗示这种离奇的做法很不合规范。《阎温传》文字又少,而作为其附传的《张恭传》却相对详细,称张恭父子“著称于西州”。从叙述的内容看,张恭的影响似乎要大于阎温。康发祥指出:“按温传附张恭及子,就传甚详,而温传颇简,何如作张恭父子传,而以温传附之邪。即以岁时考之,恭事亦在温前也。”[1]794按照康发祥的意见,与其称《阎温传》,还不如称为《张恭传》,这样更符合实际。

四、《三国志补义》的不足
康发祥生活的时代,与陈寿相隔一千六百多年,形势完全不同。在分析《三国志》的许多问题时,康发祥没有充分考虑特定的时代局限,而是囿于清代的思想局限,以自己所处时代的观念(如正统观)来苛求古人,不能像钱大昕所提出的护惜古人之用心,因此,在一些具体论断中也存在不恰当之处。
(一)政治伦理化准则压倒了事实依据
庞德本为马超的部将,曾跟随马超投奔张鲁,后来又随张鲁归顺了曹操。在与关羽作战中,庞德对督将成何说:“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2]546最后兵败被杀。对于庞德的豪言壮语,康发祥站在蜀汉正统的立场上,提出激烈的批评:“按庞德身为降将,不死于马超、张鲁,而死于曹操,犹五代时周臣韩通不死于汉而死于周也。虽时作壮语以死,君子无取焉。”[1]794以庞德不死于马超、张鲁,而死于曹操,特别是与康发祥所仰慕的关羽对抗而死,就否定其死节,表示“君子不取”,缺乏历史公允。
(二)偏重发义而忽略了知人论世


(三)时间考辨带有臆断

关于刘放和孙资任光禄大夫的时间,康发祥说:“《齐王纪》,正始元年乙丑,加侍中、中书监刘放、侍中、中书令孙资为左右光禄大夫。正始元年始加光禄大夫,则前此未为光禄大夫也。青龙初年恐是但加侍中耳,光禄大夫四字疑衍。”[1]791对于这一论断,卢弼提出驳议:“本传明言正始元年更加放、资左右光禄大夫,金印紫绶,仪同三司。曰‘更加’者,明前已加也(《齐王纪》并未言‘始加’,‘始’字康氏所增)。且汉制,光禄大夫属光禄勋。此则变更官制,位次三公,与特进同为加官,故再加任命,特书《本纪》。传文不误,康说非是。”[11]1343
(四)注解词语偏离本义
康发祥凭其管窥,对字词做出解释,也出现偏离词义的地方。《和洽传》:“太祖令曰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顺,臣道益彰。”[2]656句中“屈笮”的含义是困苦危难。康发祥根据《说文解字》做出解释,“按《说文》,笮,迫也,篇海急也,屈笮,或是褊急之义”[1]805。“褊急”意谓气量狭小,性情急躁。虽然加上“或是”,表明只是一种推断,但确实还是背离了词义。汉高祖在创建基业的过程中多次陷入困苦危难,但萧何、曹参等人却恭敬顺从,始终追随不舍,周守昌征引经籍注例,解释更加达意,“屈笮是委屈急迫之意,《史记·大宛传》徐广注,屈,抑退也;《荀子·荣辱》篇:屈,竭也,笮,《说文》,迫也;《汉书·王莽传》:迫笮青徐盗贼,即此意。”[15]855
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三国志补义》的成就还是很重要的,其认识上的局限和个别论断的瑕疵并不能掩盖其在《三国志》注释中的贡献。发掘《三国志补义》的成就,对于全面认识清代学者的史注活动,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康发祥.三国志补义[M]//二十四史订补·第五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2]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3]潘眉.三国志考证[M]//二十四史订补·第五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汪文台.七家后汉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6]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刘知几.史通[M].长沙:岳麓书社,1993.
[9]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11]卢弼.三国志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2]梁章钜.三国志旁证[M]//二十四史订补·第五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13]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5]周寿昌.三国志证遗[M]//二十四史订补·第五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