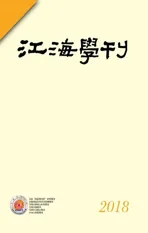从《魏风》《唐风》军礼、嘉礼类诗歌看河汾文化区的孝道观*
2018-04-14郝建杰
郝建杰
内容提要 《魏风》《唐风》中“军礼”“嘉礼”类诗歌,既反映了春秋时期河汾文化区礼仪制度规范层面礼制的发展趋势,又反映了伦理道德规范层面礼制的基本状况。这一文化区春秋时期的孝道观,是自尧、舜历夏、商、西周孝道观的延续和发展,具有深厚久远的经济与文化渊源。尤其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发生嬗变的大环境下,不同社会阶层孝道观呈现出极为相反的状态:一方面是贵族阶层氏族家庭内部大宗与小宗之间的权利之争,使得孝道观念逐渐淡化,并开始由宗亲之“孝”向君臣之“忠”转化;而另一方面是庶民阶层个体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孝道观念得以强化,且对父母双亲之“孝”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责任。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所引发的经济基础的渐次变革,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家”“国”一体观念开始形成;于是,在礼仪制度规范层面的礼制与伦理道德规范层面的礼制共生互动进程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孝道观逐步整合为一,逐渐形成以“孝”为体、以“忠”为本的“忠”“孝”一体的孝道观,并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一种社会风尚。
《诗经·魏风》与《唐风》产生于今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一带,属于最典型、最珍贵的河汾文化区的艺术产品与文化遗存。①其中,《魏风》之《陟岵》《硕鼠》《伐檀》与《唐风》之《鸨羽》《杕杜》《有杕之杜》等,属于军礼与嘉礼类诗歌。我们可以从这些诗歌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窥视出先秦时期河汾文化区孝道观的发生、发展与流变的历史轨迹,进而揭示周代礼仪制度规范与伦理道德规范演变的历史规律。
《魏风》《唐风》中军礼、嘉礼类诗歌基本状况及其所透露的孝道观信息
《魏风》《唐风》作为河汾文化区的艺术产品,既是春秋时期魏国与晋国礼乐文化的艺术载体,又是先周与西周时期这一文化区的文化遗存,自然最能够展现当时“国人”的精神世界。就其与该文化区孝道观的发生、发展与流变关系而言,军礼与嘉礼类诗歌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最丰富,最能够反映礼仪制度规范与伦理道德规范的基本状态与演变规律。
1.《魏风》《唐风》军礼类诗歌所透露的孝道观信息
所谓“军礼”,是指与军事活动相关的礼节仪式,其基本功能是“同邦国”,即震慑僭越礼制者以使诸侯和谐共处。具体内容包括“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②(《周礼·宗伯·大宗伯》)。其中,所谓“大师礼”,亦称“征战礼”,是指与军队征伐行动相关的仪节,像出师祭祀(军队出征前祭天、祭地、告庙、祭军神等)、誓师(祭祀礼毕后出征军队举行誓师典礼)、军中刑赏、凯旋、饮至与论功行赏、师不功(军队打了败仗回国后国君以丧礼迎接吊死问伤,慰劳将士)等;“大均礼”,指“均其地政、地守、地职之赋,所以忧民”(《大宗伯》郑《注》),即定期均分邦国土地以平赋税,避免因土地不均而赋税繁重使民致贫;“大田礼”,亦称田猎礼,指天子与诸侯通过定期狩猎方式检查平时训练与备战状况,如“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明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卷八)之类;③“大役礼”,指根据民力强弱安排修建都邑城郭、营造宫室、修筑堤防等土木工程;“大封礼”,指勘定封疆、沟涂,树立界标,以合聚其民。另外,还有马政礼,即养马之政教,包括牧地、交配、执驹、医疗、祭祀等。像《陟岵》(大师礼)《伐檀》(大田礼)《硕鼠》(大均礼)《鸨羽》(大师礼)《杕杜》(大师礼)等,皆属涉及军礼类信息的诗歌。
比如,《陟岵》为魏役人写出师行役在外而思念父母兄弟之作。④全诗三章,其首章曰:“予子行役,夙夜无已。”次章曰:“予季行役,夙夜无寐。”卒章曰:“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由来无止。”此所谓“上者”,是“谓在军事作部列时”(郑《笺》)。则所谓“行役”,非指一般的服劳役,而是专指“从军行役在道之时”(孔《疏》)。足见诗中的“行役”者,不仅是魏国国人中响应国君号令出征士卒中的一员,而且是这个国人家庭中出生的最小的儿子。则诗歌自然为描写作为礼仪制度规范中“军礼”类中征战礼的作品。又,首章开篇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次章开篇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卒章开篇曰:“陟彼冈兮,瞻望兄兮。”通过描写登上“岵”(草木较多之山)“屺”(无草木之山)“冈”(山岗)来遥望居家的父母与兄长的情境,在场景的不断转换之中,不仅表现出自己对父母与兄长的思念之情,也表露出父母与兄长对自己的关切之情。诗中所写“行役”,通过“国迫而数侵削,役乎大国”(毛《序》)的环境描写,展示出“君臣”人伦关系,彰显的是“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我“瞻望父”“瞻望母”“瞻望兄”与“父曰”“母曰”“兄曰”,通过“父母兄弟离散”(毛《序》)的情境描写,展示出“父子”“兄弟”人伦关系,彰显的是因国事“行役”在外而不能在家“尽孝”的人文情怀。足见诗中隐含的役人——季子与小弟,是一位既“忠君”又“孝亲”的武士。又,《礼记·祭义》曰:“孝弟发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军旅,众以义死之而弗敢犯也。”孔《疏》:“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则孝之次也。”则对父母有孝心,是能够对兄长有敬心的基本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兄友、弟恭”之“悌”,属广义之“孝亲”。足见此诗正是从广义“孝亲”角度,反映出魏国人的“孝道观”。故宋黄櫄《毛诗李黄集解》卷一二评之曰:“仁杰惟能孝于事亲,故能忠于事君。学者于《诗》而三复之,则知其所以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矣。”⑤
再如,《伐檀》为魏伐木者刺不劳而获的君子之作。其中,诗之三章间隔反复咏叹“不狩不猎”者,言魏国的“君子”们——上层贵族不再行田猎之礼以检阅全国兵车徒众,暗示其出现了军备废弛的衰败现象,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因不能自强而亡国的原因。又,《国语·晋语四》载晋大夫狐偃(子犯)对文公问曰:“民未知礼,盍大蒐,备师尚礼以示之?”⑥《公羊传·桓公四年》:“诸侯曷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何《注》:“已有三牲,必田猎者,孝子之意以为己之所养,不如土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足见诸侯亲自参与田猎所获猎物,以供宗庙祭祀、燕享宾客与充君庖厨之用,为是否“尚礼”的重要标志。其中,充君庖厨者,首先在于尽“孝亲”之道。那么,我们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胡瞻尔庭有县特兮”“胡瞻尔庭有县鹑兮”的反复质问之中,可以看到诗人在刺“君子”不劳而获的背后,实际上兼有刺其不能“孝亲”的用意。《硕鼠》与《杕杜》的情形与此诗大致相同,不再赘述。
2.《魏风》《唐风》嘉礼类诗歌所透露的孝道观信息
所谓“嘉礼”,是指与饮宴、婚冠、节庆活动相关的礼节仪式,其基本功能是“亲万民”,即通过培养尚善社会风气来和合人际关系而使不同社会阶层和谐共处。具体内容包括:“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大宗伯》)。其中,所谓“饮食礼”,亦称宴饮礼,通常专指宗族兄弟合族宴饮之“族宴”,属“宴饫之私”,主要有逢祭而宴与以时而宴两种形式;“婚冠礼”,即昏姻冠笄之礼,主要有婚姻“六礼”、冠礼(男子成人礼)、笄礼(女子成人礼)等;“宾射礼”,即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所举行之射礼以及大射礼(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所举行之射礼)、燕射礼(平时燕息之日所举行之射礼)、乡射礼(地方官为荐贤举士所举行之射礼)、投壶礼(以箭矢投入壶中为胜);“飨燕礼”,亦即饮宾客之享宴礼,飨礼在太庙举行,燕礼在寝宫举行;“脤膰礼”,是一种把社稷宗庙的祭肉(生曰脤,熟曰膰)分赐给同姓之国以表示同享福禄之礼仪;“贺庆礼”,指改元礼(帝王告殡宫而即位)、朝礼(帝王与大臣上朝办理政务之礼)、贺礼(节日庆贺)、寿礼等;另外,乡饮酒礼、养老礼、优老礼、尊亲礼、巡狩礼以及“观象授时(天文历法)”“体国经野(地理)”“设官分职(官制)”、学校、科举、取士等,亦属嘉礼。像《伐檀》(饮食礼)《鸨羽》(养老礼、饮食礼)《有杕之杜》(饮食礼)等,皆属涉及嘉礼类信息的诗歌。
比如,《鸨羽》为晋国人刺五世之乱时期君子下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之作。⑦全诗三章,首章曰:“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次章曰:“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卒章曰:“王事靡盬,不能艺稻梁,父母何尝?”《礼记·王制》:“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祭义》:“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乡饮酒义》:“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足见诗人所谓“父母何怙”“何食”“何尝”者,所指正为养老礼与饮食礼,反映的是晋国人的孝道观。那么,“父母”何以不能“怙”、不能“食”、不能“尝”呢?诗人在三章中采用间隔反复方式咏叹道:乃“王事靡盬”之故;正由于“我”为“王事”而征战不休,难以实行“春行秋反,秋行春来”之行役古制(《盐铁论·执务篇》)⑧,故踰农时,以至于“不能艺稷黍”“不能艺黍稷”“不能艺稻梁”;既然连“黍”“稷”“稻”“梁”之类的基本食用谷物都无法按时播种,自然难居家养老以孝亲了,更不要说可以举行合族宴饮了。故诗人在每章结句以呼告修辞方式连续发出慨叹:“悠悠苍天,曷其有所”“悠悠苍天,曷其有极”“悠悠苍天,曷其有常”,强烈地表达出自己“怨天尤王”的愤懑之情。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晋国因征战频仍、违背农时而嘉礼制度崩颓的情形。
再如,《有杕之杜》为晋大夫美武公好贤求士之作。首章曰:“彼君子兮,噬肯适我?中心好之,曷饮食之?”“彼君子兮,噬肯来游?中心好之,曷饮食之?”此“饮食”,即以“亲宗族兄弟”为目的的“食宗族饮酒之礼”(《大宗伯》郑《注》),亦即宗族兄弟合族宴饮——饮食礼;则所谓应邀参加族宴之“君子”者,乃“宗族兄弟”;族宴之“主人”,自然或为“人君”,或为“大夫士”(《大宗伯》孔《疏》),此则指晋武公。故此所谓“招贤纳士”之“贤士”,乃与晋公室之曲沃小宗具有血缘关系的贤能之士,当然包括像栾氏始祖“靖侯之孙栾宾”(桓二年《左传》)之类血缘关系较远的“宗族兄弟”。武公称虽尊称“曲沃伯”,实则曲沃邑大夫。其祖父公子成师与父亲庄伯鱓一直有并晋之心而未遂,之所以能够在即位后的三十七年间(前715~678)吞并大宗而以小宗为君,就是能够通过像饮食礼之类的方式来亲和宗族兄弟,形成自己以宗族兄弟为核心的政治力量。如此一来,饮食礼便成为一些有政治野心者凝聚力量的工具,自然偏离了设计的初衷,礼义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参与“族宴”的“宗族兄弟”,自然包括同宗族中的栾氏、韩氏之类的长辈,则此诗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孝道观”,即孝敬同宗族之长辈;而非狭义的“孝道观”,即孝敬父母。故宋李樗《毛诗集解》卷一三论之曰:“盖能亲亲者,必能用贤;不能亲亲,未有能求贤者也。”⑨《伐檀》的情形与此诗相类,不再赘述。
要之,从上述所论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河汾文化区的“孝道观”呈现出一幅鲜活图景,其大略包括如下内涵:一是同姓宗族之“家”内部大宗与小宗之间“尊亲”观念开始淡化,而同姓氏族之“家”内部“亲亲”关系逐渐加强;二是同姓氏族中庶民阶层之“家”对上层贵族之“家”的“尊亲”观念开始淡化,而同姓氏族中以家庭为单元的个体之“家”内部“亲亲”关系逐渐加强,子辈对祖辈、父辈的孝行孝德得以坚守与传承。
河汾文化区“孝道观”发生的经济与文化渊源
观念是礼制的内在本质,礼制只是观念的外在形态。就“孝道观”而言,实际上反映的是广义或狭义的“父子”人伦关系,体现的是一种道德伦理规范,从发生学视角来看,自然有着深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渊源。
1.早期农业经济生产方式是催生河汾地区孝道观念的根本动因
《左传·哀公六年》引逸《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孔《疏》曰:“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此所谓“平阳”在今临汾市西南,“蒲坂”在今永济市蒲州老城东南隅,“安邑”在今运城市夏县东北。足见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三代(相当于考古学中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其统治中心就在今以临汾市、运城市为中心的晋南地区。这一地区位于黄河与汾河流域相交的三角洲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宜农耕。故《书·夏书·禹贡》有“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之说。足见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原始农业较其他地域更为发达。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父系社会逐渐代替了母系社会。于是,这一地区很早就产生了与当时高度发达的原始农业相应的、以男性为主体的氏族部落家庭结构,并开始了与之相应的国家治理。这些以经营原始农业为主的家庭中,剩余产品开始逐步出现,为以氏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孝道观的产生的经济和婚姻前提已然具备。⑩
西周时期,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促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合理分工,进而催生了氏族家庭的孝道观。《书·周书·大诰》所谓“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诗·豳风·七月》所谓“同我妇,馌彼南亩”,虽指周人氏族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协作生产的情况,但也适用于河汾地区。足见在以氏族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生产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男性劳力之间,已经具有大致分工。
春秋时期,这一地区农业更为发达,随之出现了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个体家庭结构形态,男女分工开始明确起来。像晋大夫郤芮(冀芮、子公)被杀后,其子卻缺(冀缺、郤成子)流落民间,沦为庶人后“翼缺耨,其妻馌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反映的正是这种个体家庭结构形态与家庭成员内部分工状况。家庭形态逐渐由氏族家庭向个体家庭演变,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必然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这便是孝道观形成的重要基础,也是以“孝”为标准的伦理道德规范层面的国家礼制形成的前提。
2.早期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是河汾地区孝道观念逐渐成熟的内在因素
河汾地区作为虞夏商三代的中心区域,其亲孝观念发生的早期文化基因,正是虞夏商的孝道观。《礼记·祭义》曰:“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则虞、夏、商、周四代,虽有“贵德”“贵爵”“贵富”“贵亲”之异,但有“尚齿”之同,足见“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礼记·礼器》)。当然,这也表明不同的政权对于以年齿为尚,不是一种简单的传承,而是一种创造性传承与创造性发展。于是便催生了周人以“贵亲”为基本前提“尚齿”的“孝道观”,以“孝”为标准的伦理道德规范层面的国家礼制得以持续进步和不断完善,国家礼制建设由萌发到成熟,孝道文化的枝叶也日益繁茂起来。
虞舜时期的孝道观经历了一个由个人孝德衍及民间孝道而终至于国家礼制的过程,是河汾文化区孝道观的发韧期。《尚书·尧典》:“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上博楚竹简《容成氏》第十三简:“尧为善兴贤,而卒立之。昔舜耕于鬲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足见舜不仅以个人奉孝德而和合家庭,成为“邦子”——同姓宗族子弟的典范;而且大力推行以“父义”“母慈”“子孝”为基本内容的孝德之教。由此可见,舜的孝行已经由其家庭伦理功能,逐步扩展到整个宗族的道德建设,孝道便进入了国家礼制系统;同时,孝道观礼制化达到了使“百姓不亲”到“敬敷五教”的良好效果,孝道文化便由此产生。
夏后氏孝道观详细情况史料阙如,然其“贵爵而尚齿”,则“尚齿”文化风尚自然上承虞舜而来。而殷人孝道观亦直承于虞舜:“契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荀子·成相篇》),此正与《舜典》舜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说相合,说明商民族始祖契早就力倡孝道。商人立国后,商王更是以身作则,奉行孝道:小乙之子武丁即位后,“乃或亮阴,三年不言”(《书·周书·无逸》),即为先父守丧三年,不言国事,孝心可鉴;武丁之子孝己“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战国策·秦策》),即率先垂范,笃行孝道,孝道遂大行于世。
殷商覆灭,天命归周。周初立国者为国家长治久安计,将孝道与礼制紧密结合,作为治国理政方略。文、武、成三王均笃行孝道,而周公旦在理论表述与制度建设方面用力尤多。《书·周书·康诰》载周公对康公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君陈》:“王若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足见周公认为不孝是首恶,故应对不孝之行施以刑罚;同时,将推行孝道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颁布政令的前提,委官任职的条件。正是他们以宏大气魄进行顶层设计,将孝道观纳入礼乐制度之中,逐步实现了孝道观念的礼乐制度化。上引《礼记·王制》等礼书中关于养老礼等,可见一斑。
魏、晋两国作为周初姬姓封国,上承历史,下顺时势,自然会非常重视以孝道观为基本元素的礼制建设。一方面,上承前代孝道礼制化遗绪,效仿前代“不迁居,不易民”而“不出河东”之法(《诗谱·魏谱》孔《疏》引服虔《注》),即通过稳定土著族群以维护文化基因,从而保证了本土孝道文化建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分封者以新主身份入驻河汾地区,必然大力推行王朝礼制,从制度文化上蕃屏周室。于是,土著族群的孝道文化与外来周人的孝道文化便顺势媾合,河汾文化区的孝道观由此而形成。
要之,自尧、舜以降迄至春秋,魏国、晋国所居的河汾地区,孝道文化一脉相承,孝道礼制化绵延不绝,这正是河汾诗歌中孝道观的深厚渊源。
春秋时期河汾文化区孝道观的传承、演变与转化
春秋时期,随着政治生态由“有道”向“无道”渐次演进,孝道观及礼制化情势不断演变。就河汾文化区而言,孝道观出现了贵族宗族家庭与庶民个体家庭之分野。
1.贵族宗族家庭由宗亲之“孝”向君臣之“忠”转化
《逸周书·谥法解》:“五宗安之曰孝,协时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虑行节曰孝。”则西周时期之“孝”,就其范围而言,主要存在于五世之内的宗族之间,即血缘关系在“五服”宗亲之内;就其功能而论,主要是使宗亲和谐、祭礼协调、家庭和睦。足见在西周礼制系统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尊尊”“亲亲”为核心的宗法制,是这种尊亲孝道观存在的基本前提。故其在血亲基础上有效地调节了贵族宗族家庭内部的利益关系,作用至大,功劳至伟。
《礼记·祭义》载曾参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又曰:“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则春秋时期之“孝”,就其范围而言,不仅存在于宗亲之间,也存在于君臣与朋友之间;就其功能而论,不仅要协调宗族关系,而且要调节君臣与朋友关系。足见在宗族与政治趋于一体的政治体制中,“孝”的内涵开始泛化,即孝道观开始由宗亲之“孝”向君臣之“忠”转化。于是,“忠”“孝”一体的泛化孝道观开始形成。
造成贵族宗族孝道观嬗变的主要原因是王族与公族大宗与小宗之间矛盾的不断加剧。自西周穆王时期诸侯小宗开始不亲睦天子大宗事件开始,终至幽王废太子宜臼而立少子伯服,表明王族宗法制开始动摇,“尊尊”“亲亲”之道已衰,王室的孝道观自然也由此落魄失路。于是,上行下效,各诸侯国破坏宗法制的事件时有发生。而晋国则是宗法制较早失守的国家。西周晚期,晋穆侯卒,穆侯弟殇叔自立,穆侯太子仇出奔,此即诸侯公室小宗取代大宗嫡长子自立为君者;春秋前期,周王使虢公命武公(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此即诸侯公室小宗灭掉公室大宗立国者。特别是武公子献公即位后,灭桓、庄之族,诛杀群公子,逼杀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出奔,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君,自此晋无同姓公族。由于晋国宗法制被严重破坏,甚至同姓公族不存,血缘关系已不为所重,“亲尊”观念大大动摇,孝道观受到强烈冲击,社会上弥漫着宗亲溃散的悲观气氛。像《杕杜》《有杕之杜》正是这一系列变故的真实反映。我们从“不如我同父”“不如我同姓”这些留恋宗亲关系的言语中,看到的是公室宗亲关系受到严重削弱的基本状况,贵族孝道观正是经过如此异常阵痛之后逐渐开始淡化,公室贵族自然会放弃对同姓之“孝”的信任,而转向对异姓之“忠”的倚重了。
魏国的情形与晋国有所区别,其孝道观的沦丧主要表现在贵族与庶民之间。我们从《汾沮洳》中赞美“彼其之子”“殊异乎公路”“殊异乎公行”“殊异乎公族”的言行以及《园有桃》中“心之忧矣,其谁知之”的忧叹,似也可嗅到宗法制动摇的味道。宗法制动摇的大氛围,再加上生产发展导致的履亩税的实行,魏国贵族与同姓庶民之间的血亲关系也逐渐淡化,终于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像《伐檀》《硕鼠》就尖锐地揭露了统治者的刻薄寡恩和对庶民的不亲,在此情况下,出现“适彼乐所”“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强烈愿望和实际行为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可见,正是由于“尊尊”“亲亲”观念的淡漠甚至丧失,贵族孝道观不再限于“父子”之间的家庭伦理关系范畴,而是泛及“君臣”之间的政治伦理关系范畴,并成为政治人物评价体系的重要标准。正如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所言:“就本质而言,宗法制是两条线拧成的绳索,一条线是氏族时代以来的血缘关系,一条线是自封建以来的政治需要。在宗法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前一条线虽然始终未曾断绝,却逐渐削弱;后一条线逐渐增强,渐次处于主导的地位。”
2.庶民个体家庭孝道观在逆境中得以传承与强化
与贵族孝道观日渐淡化的情形不同,河汾地区的庶民孝道观则是在冲击之中坚守不弃,呈现出另外一番图景,这在《鸨羽》《陟岵》等诗中所见甚明。这些诗歌显示出鲜明而强烈的亲孝意识。为说明其原因,我们需要澄清庶民孝道观的礼制基础。
首先,庶民阶层在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参与程度与贵族利害纷争的情况迥异,从而保证他们的家庭孝道观虽然备受冲击却基本稳定。政治上,庶民作为周代社会的基本阶层,被排斥在贵族权力体系之外,因而也无需参与贵族内部的政治角力。经济上,庶民是“隶属于诸贵族封建主的附庸之民(一般亦应多是土著居民),生活于与贵族家族居地相分隔的各家族的封疆土田内”。庶民家庭虽拥有自己的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但无权参与土地分封,也无权享受卿大夫的食禄权力。他们除承担贵族征发的兵役、力役和缴纳税赋外,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方面。春秋时晋国内外战争多发,即使国土狭小的魏国也常被大国胁迫而屡与争战,庶人服役势必频仍,孝行难以施行,养老礼难以为继,但是相对单纯的处境和生活抵消了来自贵族集团的压力,保证了庶民家庭孝道观的稳定。
其次,庶民宗法制的存在是其孝道观得以坚守的重要保障。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以为:“在西周初年,宗法制首先在周天子和诸侯间施行,随后,随着封建制的发展和贵族等级的确立,宗法制也及于中、小贵族,以至于士与庶民之间。”一方面,庶民宗法制的存在使得他们产生了远近亲疏之分。《左传·桓公二年》载春秋初年晋大夫师服曰:“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春秋中期晋大夫师旷曰:“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另一方面,即使庶民社会的宗法制不像贵族一样严格,等而下之的“尊尊”“亲亲”意识也凝聚了同族的人心。有尊亲则有孝道,庶民孝道观的延续正得益于宗法制的完整。再次,春秋时期庶民聚族而居的基本居住格局,维持了庶民社会族群的稳定,从而保持了宗法制的稳定,进而保证了其孝道观的稳定。基于上述制度性因素,他们的孝道观在贵族孝道观堤防崩溃后的洪流冲刷下基本上得以保全。
总之,《魏风》《唐风》中“军礼”“嘉礼”类诗歌,既反映了春秋时期河汾文化区礼仪制度规范层面礼制的发展趋势,又反映了伦理道德规范层面礼制的基本状况。这一文化区春秋时期的孝道观,是自尧、舜历夏、商、西周孝道观的延续和发展,具有深厚久远的经济与文化渊源。尤其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发生嬗变的大环境下,不同社会阶层孝道观呈现出极为相反的状态:一方面是贵族阶层氏族家庭内部大宗与小宗之间的权利之争,使得孝道观念逐渐淡化,并开始由宗亲之“孝”向君臣之“忠”转化;而另一方面是庶民阶层个体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孝道观念得以强化,且对父母双亲之“孝”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责任。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所引发的经济基础的渐次变革,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家”“国”一体观念开始形成;于是,在礼仪制度规范层面礼制与伦理道德规范层面礼制共生互动进程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孝道观逐步整合为一,逐渐形成以“孝”为体、以“忠”为本的“忠”“孝”一体的孝道观,并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一种社会风尚。
①汾河为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发源于忻州市神池县太平庄乡西岭村,流经忻州市、太原市、吕梁市、晋中市、临汾市、运城市等6市的28县,在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汇入黄河,全长713公里,流域面积39721平方公里。故我们将该领域称为“河汾文化区”。
②本文所引《周礼注疏》《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尚书正义》,俱见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清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1815~1816)江西南昌府学刊刻阮校十三经注疏本,不再逐一标注。
③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二年(1639)叶培恕刻本。
④关于本文所涉作品的作者、诗旨与创作年代,详见邵炳军师《春秋文学系年辑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不再逐一标注。
⑤⑨李樗、黄櫄:《毛诗李黄集解》,江苏广陵书社1996年影印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第7册),第335、343页。
⑥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4页。
⑦晋穆侯夫人姜氏生二子:嫡子文侯仇,庶子公子成师(曲沃桓叔);公子成师生二子:嫡子庄伯鱓(曲沃庄伯),庶子韩万(别为韩氏);庄伯生武公称(曲沃伯)。晋昭侯元年(前745),昭公伯封其叔父公子成师于曲沃(即今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原为晋行政都邑,时为祭祀都邑),逐渐形成了“大都耦国”的政治局面,遂出现了孝侯平、鄂侯菥、哀侯光、小子侯、晋侯缗等五君凡六十一年(前739~前679)的所谓“五世之乱”。事详见《左传·桓公二年》《史记·晋世家》。
⑧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92年版,第455页。
⑩参见李根蟠《中国农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