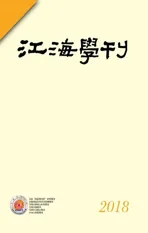“位重任隆,击钟鼎食”
——论入梁元魏宗室人物之境遇与影响
2018-04-14王永平
王永平
内容提要 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因北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不断激化及社会动乱日益加剧,间有失意之元魏宗室人物南奔萧梁以寻求避难;也有一些戍守沿边交界州镇之元魏人物叛魏入梁。对于元魏宗室流亡人物,梁武帝“方事招携,抚悦降附”,采取了诸多优遇政策,以致“位重任隆,击钟鼎食”。对元魏宗室人物之任用,主要表现在以之为将,用兵北方,一些人“数为将领,窥觎边服”;特别在北魏后期混乱状态下,以元氏宗室人物为“魏王”“魏主”,助其北伐,其中以元颢北伐影响尤著。侯景乱梁,对流寓萧梁之元魏宗室人物也加以利用,封王者众,或委以三公之位,或利诱其叛梁助乱。入梁元魏宗室文雅化程度较高者,明显受到南朝学术文化风尚之熏染,其中返归北方者,其言行举止、音韵风采,无不为“朝野师模”,“后进所归”,成为南学北传之载体。
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南北朝之间交往日渐密切。在这一过程中,南北流亡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以往人们对南朝北奔人士及其相关活动颇为重视,所论颇丰,而对由北而南之流亡人士则少有关注。其实,当时这类流亡人士不少,《梁书》卷二一《王份传附王锡传》载:“普通初,魏始连和,使刘善明来聘,敕使中书舍人朱异接之,预宴者皆归化北人。”这些所谓“归化北人”,皆为由魏入梁且具有一定地位者。梁武帝统治时期,一度国势强盛,文教发达,南趋入梁之北人颇众,其中既有经学之士和旧族士人,也有武力豪强。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北人群体,即北魏皇族宗室流亡人物,《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载北魏宣武帝赐元禧死,“其宫人歌曰:‘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虽富贵,弦管奏之,莫不洒泣”。咸阳王元禧死,“北人在南者”心存悲戚,伤感之情难抑,他们自然与北魏宫廷关系密切,其中当多有元魏宗室成员。由于当时入梁之元魏宗室人数颇众、影响突出,《梁书》卷三九特为其代表人物设传以彰显其事迹,其传末史论指出梁武帝优遇北魏宗室亡人,以为“高祖革命受终,光期宝运,威德所渐,莫不怀来,其皆殉难投身,前后相属。元法僧之徒入国,并降恩遇,位重任隆,击钟鼎食,美矣!”这一评论基本上概括了梁武帝对待元魏宗室流亡人物的政策。有鉴于此,本文细究南北朝相关史籍,对入梁之北魏宗室人物及其活动加以考察,从一个侧面透视南北朝后期之军事、政治冲突与文化交流。
入梁之元魏宗室人物考
北魏宣武帝、孝明帝时期,其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争夺不断加剧,后又发生北部边镇暴乱,得势的尔朱荣一度残酷屠戮迁洛的鲜卑上层。在这一系列政治斗争中,一些遭遇迫害和失势的元魏宗室人物间有南奔入梁者。根据史籍所载,对其可考之具体代表人物,略叙述于下。
元翼、元昌、元晔、元显和、元树兄弟。《梁书》卷二《武帝纪中》载天监五年(506)三月“癸未,魏宣武帝从弟翼率其诸弟来降”。诸人皆是北魏孝文帝长弟咸阳王元禧之子。①孝文帝死后,元禧因受命参预辅政而卷入朝廷内争,终以谋反之罪被宣武帝赐死,诸子受到牵连。《魏书·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载元禧共有八子,其中长子元通死。次子元翼“后会赦,诣阙上书,求葬其父。频年泣请,世宗不许。翼乃与弟昌、晔奔于萧衍。翼与昌,申屠氏出。晔,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壮,风制可观,衍甚重之,封为咸阳王。翼让其嫡弟晔,衍不许。……昌为衍直阁将军”。可见北魏孝文帝弟元禧诸子元翼、元昌、元晔等同时南奔入梁,其中元翼与元昌同母,皆“申屠氏出”,梁武帝以其年长,且“容貌魁壮,风制可观……封为咸阳王”。
《魏书·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又载元晔为元禧之嫡子。孝文帝迁洛后,为推进鲜卑上层汉化,为诸弟娉汉族高门女,“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其中“长弟咸阳王禧可娉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元晔字世茂,“李妃所生”,随同父兄元翼等入梁后,元翼欲让咸阳王位给元晔,梁武帝封之“为桑乾王,拜散骑常侍。卒于秣陵”。
《魏书·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又载:“翼弟显和,昌弟树,后亦奔于衍。显和卒于江南。”其中元树在梁颇得重用,影响较大。《梁书》卷三九《元树传》载:“元树字君立,亦魏之近属也。祖献文帝。父僖,咸阳王。树仕魏为宗正卿,属尔朱荣乱,以天监八年归国,封为邺王,邑二千户,拜散骑常侍。”②此外,元树有子元贞,亦长期在梁朝。
元略。《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传附元略传》载元略字俊兴,与其兄元熙皆具文雅气质,“才气劣于熙,而有和邃之誉”。魏孝明帝时,胡太后临朝,宠信孝文帝子清河王元怿,元略与兄元熙皆为元怿所重。后元叉与宦官刘腾合谋,一度幽禁胡太后,矫诏杀元怿并惩处其党羽,元熙在相州起兵反元叉而被斩,元略潜逃经年,南奔入梁:“清河王怿死后,叉黜略为怀朔镇副将。未及赴任,会熙起兵,与略书来去。寻值熙败,略遂潜行,自托旧识河内司马始宾。始宾便为荻筏,夜与略俱渡盟津,诣上党屯留县栗法光。法光素敦信义,忻而纳之。略旧识刁双时为西河太守,略复归之。停止经年,双乃令从子昌送略潜遁江左。”《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追先寺”条亦载元略“神龟中为黄门侍郎。元乂专政,虐加宰辅,略密与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义兵,问罪君侧。雄规不就,衅起同谋,略兄弟四人,并罹涂炭,唯略一身,逃命江左”。元略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入梁,普通七年(526)胡太后复政,元略返归洛阳。
元法僧、元景隆、元景仲父子。《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大通六年正月“庚申,魏镇东将军、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内附”。《梁书》卷三九《元法僧传》载:“元法僧,魏氏之支属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钟葵,江阳王。法僧仕魏,历光禄大夫,后为使、持节、都督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乱,法僧遂据镇称帝,诛锄异己,立诸子为王,部署将帅,欲议匡复。既而魏乱稍定,将讨法僧,法僧惧,乃遣使归款,请为附庸,高祖许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户。及魏军既逼,法僧请还朝,高祖遣中书舍人朱异迎之。”元法僧于梁武帝大同二年(536)死,年八十三,其二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随法僧入朝”。这里所载元法僧家世及其南奔原由较为笼统,《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阳平王熙传》载元法僧“转安东将军、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杀行台高谅,反于彭城,自称尊号,号年天启。大军致讨,法僧携诸子,拥掠城内及文武,南奔萧衍”。这里所载其南奔之由,也不够具体,《北史》一六《魏道武七王·阳平王熙传附元法僧传》则详述其叛魏原委及经过:“后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叉,以骄恣,恐祸及己,将谋为逆。……孝昌元年,法僧杀行台高谅,反于彭城,自称尊号,改元天启。大军致讨,法僧奔梁,其武官三千余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额为奴,逼将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寻改封宋王……征为太尉。卒于梁,谥曰襄厉王。子景隆、景仲。”元法僧本为元叉党羽,元叉专权,引起北魏朝廷内外,特别是元氏宗族内激烈的权力斗争,故元法僧“恐祸及己,将谋为逆”,本图谋“自称尊号”,割据一方,后魏廷剿之而南叛。元法僧入梁,除携带诸子外,举镇南叛,“其武官三千余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额为奴,逼将南渡”,影响很大。
元舒、元善父子。《北史》卷一六《魏道武七王·京兆王黎传附元叉传》载:“叉子舒,秘书郎。叉死后,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可见元舒在乃父元叉被赐死后,处境不佳,于是逃亡入梁。其子元善,又名善住,“少随父至江南”。③
六镇乱起,尔朱荣入洛,擢取统治大权,制造河阴之变,对迁洛鲜卑上层,特别是元魏宗室大加杀戮,一些元魏皇族人物相继南奔。《魏书》卷一○《孝庄帝纪》载武泰元年四月,“是月,汝南王悦、北海王颢、临淮王彧前后奔萧衍,郢州刺史元愿达据城南叛”。《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大通二年(528)四月条亦载:“时魏大乱,其北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悦并来奔;其北青州刺史元世雋、南荆州刺史李志亦以地降。”可见河阴之变后,元魏宗室子弟入梁者甚众。
元悦、元颖父子。《魏书》卷二二《孝文五王·汝南王悦传》载:“及尔朱荣举兵向洛。既忆人间。俄而闻荣肆毒于河阴,遂南奔萧衍。衍立为魏主,年号更兴。衍遣其将军王辩送置境上,以觊侵逼。及齐献武王既诛荣,以悦高祖子,宜承大业,乃令人示意。悦既至,清狂如故,动为罪失,不可扶持,乃止。”《北史》卷一九《魏孝文六王·汝南王悦传》亦载:“及尔朱荣举兵向洛,悦遂奔梁。梁武厚相资待。庄帝崩,遂立为魏主,号年更兴”,又载其“子颖,与父俱奔梁,遂卒于江左”。元悦在梁数年间(528~532),特别在尔朱氏害孝庄帝后,梁武帝一度立之为“魏主”,以求北进,其子元颖则留寓江南。
元颢、元冠受父子。《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上·北海王详传附元颢传》载北海王元详子元颢,字子明,“少慷慨,有壮气”,六镇乱起,元颢出刺相州,“颢至汲郡,属尔朱荣入洛,推奉庄帝,诏授颢太傅,开府、侍中、刺史、王并如故。颢以葛荣南侵,尔朱纵害,遂盘桓顾望,图自安之策。……颢以事意不谐,遂与子冠受率左右奔于萧衍”。《元颢墓志》载:“属明皇暴崩,中外惟骇,尔朱荣因籍际会,窥兵河洛,始称废立,仍怀觊觎。群公卿士,磬于锋镝,衣冠礼乐,殆将俱尽,行李异同,莫辩逆顺。公未知鸿雁之庆,独轸麦秀之悲,而北抗强竖,南邻大敌,事在不测,言思后图,遂远适吴越,观变而动。孝庄统历,遥授师傅,磐石之寄,于焉在斯。”④元颢在梁未久便受命北伐。
元彧。《魏书》卷一八《太武诸王·临淮王谭传附彧传》载其字文若,河阴之变后一度南奔入梁:“是时,萧衍遣将围逼温汤,进彧以本官为东道行台。会尔朱荣入洛,杀害元氏。彧抚膺恸哭,遂奔萧衍。”《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大通二年(528)六月丁亥,“魏临淮王元彧求还本国,许之”,次月便抵洛阳,《魏书》卷一○《孝庄帝纪》载武泰元年七月条亦载:“是月,临淮王彧自江南还朝。”可知元彧在梁前后只有两个多月。
此外,随着北魏乱局加剧,梁朝对北部沿边地带的攻势有所加强,致使一些北魏州镇人物南附降梁,其中主要有:
元罗。《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京兆王黎传》载元叉弟元罗,字仲纲,其父兄在孝明帝时一度执掌北魏中枢军政大权,其本人则“以俭素著称”,出帝时任梁州刺史,“罗既懦怯,孝静初,萧衍遣将围逼,罗以州降”。《北史》卷一六《魏道武七王·京兆王黎传》载元罗“孝武时,位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静初,梁遣将围逼,罗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罗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改封江阳王。梁元帝灭景,周文帝求罗,遂得还。除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少师,袭爵江阳王。舒子善住,在后从南入关,罗乃以爵还善住,改封罗为固道郡公”。
元庆和。《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大通元年(527年)冬十月庚戌,“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以涡阳内属”。《魏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上·汝阴王天赐传》载元天赐孙元庆和为魏东豫州刺史,“为萧衍将所攻,举城降之。衍以为北道总督、魏王”。
元愿达。《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大通二年(528)夏四月辛丑,“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内附,置北司州”。《梁书》卷三九《元愿达传》载其“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乐平王。愿达仕魏为中书令、郢州刺史。普通中,大军北伐,攻义阳,愿达举州献款,诏封乐平公,邑千户,赐甲第女乐。仍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湘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征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将军。大同三年,卒。时年五十七”⑤。
元延明。《魏书》卷二○《文成五王·安丰王猛传附元延明传》载元延明为学术素养最高的元魏宗室人物之一,“延明既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彧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虽风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笃过之”。尔朱荣立庄帝,元延明兼尚书令、大司马,“及元颢入洛,延明受颢委寄,率众守河桥。颢败,遂将妻子奔萧衍,死于江南。庄帝末,丧还。出帝初,赠太保,王如故,谥曰文宣。”《元延明墓志》载其入梁及其学术文化素养曰:“方借力善邻,讨兹君侧。而江南卑湿,地非养贤,随贾未归,忽焉反葬。以梁中大通二年三月十日薨于建康,春秋卌七。公神衿峻独,道鉴虚凝,少时高祖垂叹,以为终能致远,遂翻为国师,郁成朝栋。既业冠一时,道高百辟,授经侍讲,琢磨圣躬,明堂辟雍,皆所定制,朝仪国典,质而后行。加以崖岸重深,风流旷远,如彼龙门,迢然罕入。惟与故任城王澄、中山王熙、东平王略,竹林为志,艺尚相欢。故太傅崔光、太常刘芳,虽春秋异时,亦雅相推揖。”⑥元延明于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9)元颢北伐失败后携妻子南奔入梁,并终于江南。
元斌之。《魏书》卷二○《文成五王·安乐王长乐传》载安乐王元长乐子元鉴弟元斌之,“字子爽。性险无行,及与鉴反,败,遂奔葛荣。荣灭,得还。出帝时,封颍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关,斌之奔萧衍,后还长安”。元斌之在东西魏分立之际一度入梁,后又北归关中,其在梁时间甚短。
由上文考稽,可见北魏后期多有元氏宗室人物南奔入梁。究其原由,根据上述之情形,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因参与北魏皇族内部权力斗争,或受牵连,或在相关斗争失败后流亡江左,其中咸阳王元禧诸子元翼、元树及东平王元略等人便是如此,元法僧之举镇叛魏并最终入梁,也可归入这一类型。二是在北魏发生六镇暴乱之后,尔朱荣擢取政权,残害迁洛元魏雅化上层,导致诸多元魏宗室人物入梁避祸,其中汝南王元悦、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北海王元颢等,皆属此类,此时也是元魏宗室人物流亡萧梁的高潮期。三是北魏末期,梁武帝乘乱攻击沿边之北魏镇戍,致使一些元氏人物降附萧梁,上述魏梁州刺史元罗、郢州刺史元愿达、东豫州刺史元庆和等举镇南投,当皆属此类。当然,流寓萧梁之元魏宗室人物绝非仅止于此,以上仅是能确考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或合家南奔,或举镇南附,也有一些是个人潜逃江左避祸。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入梁之元魏宗室人物,由于南奔之原因与时间不同,他们在梁朝并未形成一个关系紧密的流亡群体,不同支系之间还存在隔阂与矛盾。如元略便轻视元法僧,《魏书·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传附元略传》载其“又恶法僧为人,与法僧言,未尝一笑”。元略之所以“恶法僧为人”,根据相关史实分析,主要在于元略与元法僧原本在魏便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元法僧本是元叉之亲信,而元略兄弟等归属与之对立的清河王元怿集团,自然势如水火,相互敌视,加上元法僧先在北称帝,后叛魏入梁,而元略则因政治迫害潜逃入梁,且仍心系魏室,与元法僧之附梁不同,故心存轻视与敌意。又,《北史》卷一六《道武七王·京兆王黎传附元叉传》载:“初,咸阳王禧以逆见诛,其子树奔梁,梁封为邺王。及(元)法僧反叛后,树遗公卿百僚书,暴叉过恶,言‘叉本名夜叉,弟罗实名罗刹,夜叉、罗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风,事同飘堕。呜呼魏境,离此二灾。恶木盗泉,不息不饮,胜名枭称,不入不为,况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叉为远近所恶如此。”元树在元法僧反叛后,曾致书北魏公卿百僚,以诋毁元叉。如上所言,元法僧本为元叉之党羽,故元树斥责元叉,实际上也暗含他对元法僧的蔑视之意。因此,可以说入梁之元魏宗室流亡人物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部矛盾,难以成为一个具有共同诉求的集团。
“方事招携,抚悦降附”:梁武帝优遇元魏宗室亡人
流亡萧梁之元魏宗室代表人物既如上考,那么,他们在萧梁之境遇如何呢?一般说来,南北朝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对来自敌方的奔亡之士往往多加优宠,以示笼络。可以说,这是东晋与十六国、南北朝的一项基本政策。以北魏为例,刘裕代晋过程中,不少司马氏宗室与士族人物北奔入魏,此后类似情形甚多,北魏对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皆加拔擢,其任用一个突出特点是委以与南朝沿边地域之军政事务,其他还辅之以与北魏上层联姻等笼络手段等。⑦南朝政权屡有更迭,政治斗争残酷,诸皇族宗室与大族朝臣流亡北朝的情况不断发生,其中北朝优遇与安抚政策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之相应,从北魏南奔江左之皇族子弟主要集中在萧梁时期,梁武帝多加优待。
具体而言,从梁武帝与入梁元魏宗室人物的交往情况看,其中文雅化程度较高者尤受钦重。如元略,《魏书·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传附元略传》载其入梁后,“萧衍甚礼敬之,封略为中山王,邑一千户”,历任宣城太守、衡州刺史等。元略“虽在江南,自以家祸,晨夜哭泣,身若居丧”。后梁武帝子萧综叛梁入魏,“综长史江革、司马祖暅、将士五千人悉见擒虏。肃宗敕有司悉遣革等还南,因以征略。衍乃备礼遣之”。可见元略虽不诚心归梁,然梁武帝甚重之,“略之将还也,衍为置酒饯别,赐金银百斤。衍之百官,悉送别江上,遣其右卫徐確率百余人送至京师”。元略是北魏胡太后之亲党,返魏后受封东平王,领国子祭酒,迁大将军、尚书令,“灵太后甚宠任之,其见委信,殆与元徽相埒”。梁武帝如此礼遇元略,当然主要出于感化北人之意,但也与元略之文化素养不无关系。《元略墓志》载其风雅及南渡后所受礼遇云:“游志儒林,宅心仁苑,礼穷训则,义周物轨,信等脱剑,惠深赠貯,器博公琰,笔茂子云。汪汪焉量溢万顷,济济焉实怀多士。……正光之初,元昆作蕃,投杼横集,滥尘安忍,在原之痛,事切当时,遂潜影去洛,避刃越江,买卖同价,宁此过也。伪主萧氏,雅相器尚,等秩亲枝,齐赏密席。而庄写之念,虽荣愿本;渭阳之念,偏楚心目。以孝昌元年,旋轴象魏。”⑧对此,《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追先寺”条亦载:
略生而岐嶷,幼则老成,博洽群书,好道不倦。……萧衍素闻略名,见其器度宽雅,文学优赡,甚敬重之。谓曰:“洛中如王者几人?”略对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摄官;至于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鸳鸾接翼,杞梓成阴;如臣之比,赵咨所云车载斗量,不可数尽。”衍大笑,乃封略为中山王,食邑千户,仪比王子。……孝昌元年,明帝宥吴人江革,请略归国。江革者,萧衍之大将也,萧衍谓曰:“朕宁失江革,不得无王。”略曰:“臣遭家祸难,白骨未收,乞还本朝,叙录存没。”因即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赐钱五百万,金二百金,银五百斤,锦绣宝玩之物不可称数。亲帅百官送于江上,作五言诗赠者百余人。凡见礼敬如此。
元略是北魏宗室中杰出之风雅人物,梁武帝与之文化趣味多有契合,交流深入。
与元略相似的是元彧,《魏书》卷一八《太武诸王·临淮王谭传附彧传》载元彧“少有才学,时誉甚美”,是迁洛元魏皇族文雅化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美风韵,善进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则。博览群书,不为章句。所著文藻虽多亡失,犹有传于世者”,深得汉族士大夫的赞誉。梁武帝甚为礼敬,《魏书》本传载:“衍遣其舍人陈建孙迎接,并观彧为人。建孙还报,称彧风神闲俊。衍亦先闻名,深相器待,见彧于乐游园,因设宴乐。彧闻乐声,歔欷,涕泪交下,悲感傍人,衍为之不乐。自前奔叛,皆希旨称魏为伪,唯彧上表启,常云魏临淮王。衍体彧雅性,不以为责。及知庄帝践阼,彧以母老请还,辞旨恳切。衍惜其人才,又难违其意,遣其仆射徐勉私劝彧曰:‘昔王陵在汉,姜维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彧曰:‘死犹愿北,况于生也。’衍乃以礼遣。彧性至孝,事父母尽礼,自经违离,不进酒肉,容貌憔悴,见者伤之。”萧衍对元彧如此“深相器待”,不仅与其在魏室中之地位相关,更重要在于其雅化风流。特别是元彧与其他入梁之元魏皇族人物“皆称魏为伪”不同,其所上表启,“常云魏临淮王”,这显然不合礼制,然梁武帝“体彧雅性,不以为责”,以显示优待。
当然,入梁之元魏宗室人物成分复杂,风雅之士外,对其他入梁之元氏人物,梁武帝也多加封赏与礼遇。如元悦,《梁书·武帝纪下》载中大通二年秋八月庚戌,“舆驾幸德阳堂,设丝竹会,祖送魏主元悦”。元悦在孝文帝诸子中,不仅品行、才学极差,且神智不清,时有错乱之举,《魏书》本传称其“为性不伦,俶傥难测”,梁武帝之所以如此礼敬,当主要出于通过优遇元魏嫡宗以感召其他北人之目的。
至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元魏宗室人物,梁武帝则委寄尤重。如元法僧父子举镇入梁,深受器重,《梁书》卷三九《元法僧传》载其“既至,甚加优宠。时方事招携,抚悦降附,赐法僧甲第女乐及金帛,前后不可胜数。法僧以在魏之日,久处疆场之任,每因寇掠,杀戮甚多,求兵自卫,诏给甲仗百人,出入禁闼。大通二年,加冠军将军。中大通元年,转车骑将军。四年,进太尉,领金紫光禄。其年,立为东魏主,不行,仍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征为侍中、太尉,领军师将军”⑨。可见元法僧入梁后,“甚加优宠”,除赏赐“甲第女乐及金帛,前后不可胜数”外,还封以尊贵的爵位与军政职位。其子元景隆、元景仲也受优遇,《梁书·元法僧传》载:“景隆封沌阳县公,邑千户,出为持节、都督广越交桂等十三州诸军事、平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征侍中、安右将军。四年,为征北将军、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中、度支尚书。太清初,又为使持节、都督广越交桂等十三州诸军事、征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时年五十八。”又载:“景仲封枝江县公,邑千户,拜侍中、右卫将军。大通三年⑩,增封,并前为二千户,仍赐女乐一部。出为持节、都督广越等十三州诸军事、宣惠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大同中,征侍中、左卫将军。兄景隆后为广州刺史。”又,《梁书》卷四一《王规传》载普通六年,“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诏为侍中”。元法僧父子甚为粗鄙,但元景隆赴广州刺史任,梁武帝召集群臣于文德殿聚会祖饯,以示宠重。
与元法僧类似的是元愿达,《梁书》卷三九本传载其入梁后,“诏封乐平公,邑千户,赐甲第女乐。仍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湘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征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将军”。
梁武帝之所以如此,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安抚归附之元魏宗室人物,以扩大影响,招引更多的归降之人,所谓“时方事招携,抚悦降附”,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因此,在梁武帝这一优待政策下,入梁之元魏宗室人物多获得优越的生活保障及相应的封爵与军政职位,即便对那些决意北归者,梁武帝也多加包容,待遇优厚。不过,必须指出,就江左士族社会及萧梁朝臣之心理而言,他们对元氏流亡人士,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粗鄙武人,依然抱有微妙的种族与文化的歧视。《梁书》卷三九《羊侃传》载:“中大通四年,诏为使持节、都督瑕丘诸军事、安北将军、兖州刺史,随太尉元法僧北讨。法僧先启云:‘与侃有旧,愿得同行。”高祖乃召侃问方略,侃具陈进取之计。高祖因曰:“知卿愿与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还朝,常思效命,然实未曾愿与法僧同行。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今与法僧同行,还是群类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轻汉。’高祖曰:‘朝廷今者要须卿行。’乃诏以为大军司马。高祖谓侃曰:‘军司马废来已久,此段为卿置之。’”南北朝长期分裂,相互歧视,在南朝士众看来,北朝为胡人统治,其民众自为胡虏,归入异类。东晋以来,对晚渡北方士族便加以歧视,羊侃于萧梁南来,自然感受强烈,故言“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江左士族既以晚渡北方士族人物为“虏”,他们对元魏宗室人物自然心存歧视。因此,羊侃受诏辅助元法僧北伐,表示委屈,甚至说“今与法僧同行,还是群类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轻汉”。羊侃作为晚渡汉族士族豪帅,其颇觉南人之歧视,而他本人又轻视元法僧,从中可见当时南人对元魏宗室流亡人士的普遍心态。
当然,随着一些元魏皇族人物长期留滞江左,与萧梁上层交往日益密切,相互理解亦不断加深,其中有人逐渐融入萧梁上层社会。在这方面,元树、元贞父子之表现颇为典型,《北史·魏献文六王·咸阳王禧传》载:“树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贵。每见嵩山云向南,未尝不引领歔欷。初发梁,睹其爱姝玉儿,以金指环与别,树常著之。寄以还梁,表必还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赐死。”《梁书》卷三九《元树传》载其北征谯城,“城陷被执,发愤卒于魏,时年四十八”。这是说元树北征被俘后因决意还梁而致死。此说未必尽是,但就元树的江南观念而言,他年少入梁,在南方成长,前后长达三十余年,故其有较为浓郁的南方情结自不足为怪。又,《魏书》卷八○《樊子鹄传》载元树在谯城为樊子鹄围困,“树既无外援,计无所出,子鹄又令人说之,树遂请率众归南,以地还国。子鹄等许之,共结盟约”。可见元树北伐失利后,其首选方案是“请率众归南”。《通鉴》卷一五五“梁武帝中大通四年九月”条载:“树至洛阳,久之,复欲南奔,魏人杀之。”元树子元贞,当出生于萧梁,《北史·魏献文六王·咸阳王禧传》载元树死后,“其子贞自建业求随聘使崔长谦赴邺葬树,梁武许之。……贞既葬,还江南,位太子舍人”。元贞对萧梁颇为忠贞,太清元年(547),梁武帝以元贞为魏主,送其至寿阳以助侯景北伐,但他发现侯景之异常,于是逃归建康揭发其阴谋。侯景攻建康,元贞受命抵抗,《通鉴》卷一六一“梁武帝太清二年十月”条载“轻车长史谢禧、始兴太守元贞守白下”,战败而弃城。正因为如此,有萧梁宗室人物委后事于元贞,《梁书》卷二九《高祖三王·南康简王萧绩传附萧乂理传》载萧乂理决意反抗侯景,并托后事于元贞:“至京师,以魏降人元贞立节忠正,可以托孤,乃以玉柄扇赠之。贞怪其故,不受。乂理曰:‘后当见忆,幸勿推辞。’会祖皓起兵,乂理奔长芦,收军得千余人。其左右有应贼者,因间劫乂理,其众遂骇散,为景所害,时年二十一。元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萧乂理以为元贞“立节忠正,可以托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元贞虽为元魏宗室之后,但与萧梁上层社会已融为一体。
“数为将领,窥觎边服”:梁武帝扶持元魏宗室降人以经略北方
梁武帝招揽元魏宗室流人,不仅仅给予种种优遇,以作为装饰,而且在南北军事对抗与规划北朝方面,一再扶持其代表人物为“魏王”“魏主”,进而遣师助其北返。
梁武帝在位时间长,且一度内政稳定,国力上升,而北魏则政局动荡,特别在六镇乱起、河阴生变后,纷争加剧,日趋崩溃。天监年间,梁武帝出师北征,主要在于对淮河南北地域之争夺;普通以后,萧梁势力一度拓展至徐州一带。随着北魏乱局加剧,梁武帝甚至图谋用兵中原。在此过程中,梁武帝对北魏鲜汉上层人物采取了“方事招携,抚悦降附”的怀柔政策,委以军旅重任。具体就入梁之元魏宗室人物而言,他们多受命出征。如元翼、元树兄弟,《魏书·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载元翼“后以为信武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镇郁州。翼谋举州入国,为衍所移”。《北史》卷一九《魏献文六王·咸阳王禧传》载元翼出镇郁州,“翼谋举州入国,为梁武所杀”。梁武帝以元翼镇郁州,主要负责梁、魏东部沿边地带的对抗,但察其有谋叛之意,故以迁移之名将其处死。
元树尤为梁武帝信重,参与了一系列军事征伐活动。《魏书·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载元树“数为将领,窥觎边服。时扬州降衍,兵武既众,衍将湛僧珍,虑其翻异,尽欲杀之。树以家国,遂皆听还。衍以树为镇西将军、郢州刺史。尔朱荣之害百官也,树闻之,乃请衍讨荣。衍乃资其士马,侵扰境上。前废帝时,窃据谯城。出帝初,诏御史中尉樊子鹄为行台,率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以讨之。树城守不下,子鹄使金紫光禄大夫张安期往说之,树乃请委城还南,子鹄许之。树恃誓约,不为战备,杜德袭击之,擒树送京师,禁于永宁佛寺,未几赐死”。此次元树北伐,其时在梁武帝中大通四年。元树“有将略”,“数为将领,窥觎边服”,无疑是入梁元魏宗室在相关军事活动中表现最为活跃之人物。其他如元略、元庆和、元罗等人也多参与“窥觎边服”之军事活动。
特别需要重点论述的是,自大通以后,梁武帝一再扶持元魏宗室降人为魏主,出师北伐,以图收复北方。《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大通二年(528)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元颢为魏主,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送还北”;中大通元年(529)正月甲子,“魏汝南王元悦求还本国,许之”;中大通二年(530)六月丁巳,“遣魏太保汝南王元悦还北为魏主。庚申,以魏尚书左仆射范遵为安北将军、司州牧,随元悦北讨”。同年“秋八月庚戌,舆驾幸德阳堂,设丝竹会,祖送魏主元悦”;元悦此次北还未就,《通鉴》卷一五四“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十二月”条载:“魏王悦改元更兴,闻尔朱兆已入洛,自知不及事,遂南还。”《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中大通四年(532)正月戊辰,以“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平北将军、司州牧,卫送元悦入洛”;又载中大通四年二月壬寅,“新除太尉元法僧还北,为东魏主。以安东将军元景隆为征北将军、徐州刺史,云麾将军羊侃为安北将军、兖州刺史,散骑常侍元树为镇北将军”。梁武帝同时扶持元悦、元法僧入北。又载太清元年(547)冬十二月戊辰,“遣太子舍人元贞还北为魏主”。此外,《魏书》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上·汝阴王天赐传》载元庆和入梁后,梁武帝“以为北道总督、魏王。至项城,朝廷出师讨之,望风退走。衍责之曰:‘言同百舌,胆若鼷鼠。’遂徙合浦”。可见元庆和也受封“魏王”而北伐。
在诸次扶持入梁元魏宗室降人为“魏主”的北伐之议中,尤以元颢北伐声势最著、影响最大。关于元颢北伐,《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上·北海王详传附元颢传》载:
颢见衍,泣涕自陈,言辞壮烈,衍奇之。遂以颢为魏主,假之兵将,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于梁国城南登坛燔燎,号孝基元年。庄帝诏济阴王晖业为都督,于考城拒之,为颢所擒。又克行台杨昱于荥阳。尔朱世隆自虎牢走退,庄帝北幸。颢遂入洛,改称建武元年。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号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风政。而自谓天之所授,颇怀骄怠。宿昔宾客近习之徒咸见宠待,干扰政事,又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所统南兵,凌窃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时又酷敛,公私不安。庄帝与尔朱荣还师讨颢。自于河梁拒战,王师渡于马渚,(其子元)冠受战败被擒,因相继而败。颢率帐下数百骑及南兵勇健者,自轘辕而出。至临颍,颢部骑分散,为临颍县卒所斩。
由以上所叙可见元颢北征过程之概略。元颢北还,梁武帝以陈庆之相佐,《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载:“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自拔来降,求立为魏主。高祖纳之,以庆之为假节、飚勇将军,送元颢还北。颢于涣水即魏帝号,授庆之使持节、镇北将军、护军、前军大都督。”自大通二年(528)十月至中大通元年(529)六月,陈庆之转战中原,以少胜众,最终进入洛阳。有关其主要战役,《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中大通元年四月癸巳,“陈庆之攻魏梁城,拔之;进屠考城,擒魏济阴王元晖业”;五月戊辰“克大梁。癸酉,克虎牢城。魏主元子攸弃洛阳,走河北。乙亥,元颢入洛阳”;闰六月己卯,“魏尔朱荣攻杀元颢,复据洛阳”。陈庆之所领仅数千南兵,诸次激战,遭遇尔朱荣与孝庄帝部属之阻截与攻击,皆能克敌制胜,《梁书·陈庆之传》详载其事,其中说:“庆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阳童谣曰:‘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自发钅至县至于洛阳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可见元颢还洛,主要有赖于陈庆之利用当时北方之乱局,采取了乘虚而入的运动战方式,奋勇作战,屠城略地。
不过,如所周知,这一颇具声势的北伐还是以失败告终了,随着尔朱荣的反击,元颢战败被杀,陈庆之则孤身逃回江南。何以如此?根据相关记载,首先在于元颢之军政举措失策,上引文称其“自谓天之所授,颇怀骄怠”云云,可见元颢及其主要辅助者元彧、元延明等人自难有成。其次,元颢称帝后,与陈庆之及南军将校之间各存异心,《梁书·陈庆之传》载:“初,元子攸止单骑奔走,宫卫嫔侍无改于常,颢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乐,不复视事,与安丰、临淮共立奸计,将背朝恩,绝宾贡之礼;直以时事未安,且资庆之之力用,外同内异,言多忌刻。庆之心知之,亦密为其计。”具体而言,陈庆之以为南兵少,建议元颢“宜启天子,更请精兵;并勒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须部送”,而元颢听信元延明所言,以为“陈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增其众,宁肯复为用乎?权柄一去,动转听人,魏之宗社,于斯而灭”,元颢“由是致疑,稍成疏贰”;又“虑庆之密启”,上表梁武帝,以为“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动摇百姓”,梁武帝于是“遂诏众军皆停界首”。当时“洛下南人不出一万,羌夷十倍”,陈庆之军副马佛念进言陈忧,建议说:“功高不赏,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将军岂得无虑?……今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也。”元颢曾有意以陈庆之为徐州刺史,陈庆之亦深惧洛阳危局,“因固求之镇。颢心惮之,遂不遣”。可见元颢入洛称帝后,其内部之元魏宗室亲信与陈庆之等南人间互不信任,不仅无法同舟共济,而且相互敌视,时刻有发生内讧之可能。《通鉴》卷一五三“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闰六月”条则明载:“魏北海王颢既得志,密与临淮王彧、安丰王延明谋叛梁。”确实,梁武帝轻率用兵,具体表现遣兵太少,无法镇服所扶持之元魏宗族傀儡及北人。
对元颢、陈庆之北伐,当时南北人士皆有必败之议论。关于萧梁朝臣士众之异议,《梁书》卷四一《王规传》载:“普通初,陈庆之北伐,克复洛阳,百僚称贺。规退曰:‘道家有云,非为功难,成功难也。羯寇游魂,为日已久,桓温得而复失,宋武竟无成功。我孤军无援,深入寇境,威势不接,馈运难继,将是役也,为祸阶矣。’俄而王师覆没,其识达事机多如此类。”吕思勉先生据此以为“此固人人之所知,而梁武漫不加省,举朝亦莫以为言,怠荒至此,何以为国?况求克敌乎?”北人也有相似预言,《北史》卷一九《魏献文六王·北海王详传附元颢传》载:“初,颢入洛,其日暴风,欲入阊阖门,马大惊不进,令人执辔乃入。有恒农杨昙华告人曰:‘颢必无成,假服衮冕,不过六十日。’又谏议大夫元昭业曰:‘昔更始自洛阳而西,初发,马惊奔,触北宫铁柱,三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败。”这一谶言表达了诸多北方人士之心态。确实,对元颢称帝以取代孝庄帝元子攸,当时北方士族公然反对者甚众。《魏书》卷六六《崔亮传附崔光韶传》载:“及元颢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风靡。而刺史、广陵王欣集文武以议所从。欣曰:‘北海、长乐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独抗言曰:‘元颢受制梁国,称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资仇敌,贼臣乱子,旷代少俦,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齿,等荷朝眷,未敢仰从。’长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张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征士张僧皓咸曰:‘军司议是。’欣乃斩颢使。”崔光韶出自清河崔氏,为北方最显赫之门第,他直斥元颢“贼臣乱子”,体现了北方士族社会的普遍心态。梁武帝招诱元魏皇族,封以魏主之名号,助其部伍以北伐,目的在于利用其特殊身份与声望,趁北方乱局以谋利,但皆以失败告终。梁武帝对于北伐,并无总体的统一战略规划,其扶持元魏降人以北伐,实际上是一种军事投机行为。吕思勉先生一再指出梁武帝根本没有整体的对北战略,至于其乘北魏后期动乱,“则始终思藉降人之力。独不思降人若本无能为,辅之安能有济?若有雄略,又安肯为我不侵不叛之臣?辅而立之,岂非自树一敌邪?”这里明确指出梁武帝“思藉(元魏)降人之力”以规划中原,实难有成。不仅如此,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七“梁武帝”之一九条批评梁武帝在民族纷争之背景下,淡化民族大义,“而委诸元颢,听其自王,授高欢以纳叛之词,忘晋室沦没之恨,恬然为之,漫不知耻。浸令颢之终有中原也,非梁假之羽翼以授之神州也哉?洛阳已拔,子攸已走,马佛念劝庆之杀颢以据洛,而庆之犹不能从,则其髠发以逃,固丧心失志者之所必致也。君忘其为中国之君,臣忘其为中国之臣,割弃山河,恬奉非类,又何怪乎士民之视衣冠之主如寇贼,而戴殊族为君父乎?至于此,而江左之不足自立决矣”。王夫之出于正统的卫道观念,言辞固然不无偏激,但确实深刻地揭示出当时南北民族融合之形势与梁武帝北伐战略失败之根源。
“与贼连从,谋危社稷”:侯景乱梁过程中对元魏宗室人物的利用
侯景乃六镇武人,高欢部将。高欢掌控东魏,委以河南军政之重任。后高欢子高澄执政,侯景与之相争失利而附梁,后渡江乱梁,称帝建康。侯景乱梁过程中,一再利用入梁之元魏宗室人物,以作为其争夺江南统治地位的工具。
其实,早在为慕容绍宗败退守悬瓠时,侯景已有利用元氏人物的想法,《梁书》卷五六《侯景传》载其“遣其行台左丞王伟、左民郎中王则诣阙献策,求诸元子弟立为魏主,辅以北伐,许之。诏遣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须渡江,许即伪位,乘舆副御以资给之”。《通鉴》卷一六○梁武帝太清元年十一月条载之甚详:“壬申,遣其行台左丞王伟等诣建康说上曰:‘邺中文武合谋,召臣共讨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见于金墉,杀诸元六十余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请立元氏一人以从人望,如此,则陛下有继绝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为圣朝之邾、莒,国之男女,为大梁之臣妾。’上以为然。乙亥,下诏以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资以兵力,使还北主魏,须渡江,许即位,仪卫以乘舆副给之。贞,树之子也。”侯景以“河北物情,俱念旧主”为由,请梁武帝立一元氏皇族人物“以从人望”,助其北伐。当时侯景未必决意南向,他与高澄争夺中原,既借重梁朝之力,又假托元氏之名,更与梁武帝一贯的助魏亡人以恢复北土的想法一致。然元贞至寿阳后,发现侯景异谋而逃归建康,《通鉴》卷一六一“梁武帝太清二年七月”条载:“上既不用景言,与东魏和亲,是后景表疏稍稍悖慢;又闻徐陵等使魏,反谋益甚。元贞知景有异志,累启还朝。景谓曰:‘河北事虽不果,江南何虑失之,何不小忍!’贞惧,逃归建康,具以事闻;上以贞为始兴内史,亦不问景。”可见侯景在扶持元氏之人争夺北方无望后,便转而动员元贞附己以偷袭萧梁。
侯景渡江,其士众甚少,原本难以支撑诸多军事攻击与征战,且因其民族与文化之差异,江南士族社会对其怀有强烈的抵制和排斥情绪。为立足江南,他采取了一些新的极端举措,如解放奴婢、罪犯等以及下层社会民众,以扩大其势力,造成了巨大的反梁声势。在此过程中,入梁之元魏皇族人物则因其特殊的身份背景,颇为侯景所重视,成为其拉拢、利用的对象。《梁书》卷五六《侯景传》载其在梁武帝太清三年控制局势后,“至是,景杀萧正德于永福省。封元罗为西秦王、元景龙为陈留王,诸元子弟封王者十余人”;“以王伟、元罗并为仪同三司”;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年)正月,“景以王克为太师,宋子仙为太保,元罗为太傅”。《通鉴》卷一六四“梁简文帝大宝二年正月”条载:“侯景以王克为太师,宋子仙为太保,元罗为太傅,郭元建为太尉,张化仁为司徒,任约为司空,王伟为尚书左仆射,索超世为右仆射。景置三公官,动以十数,仪同尤多。”其中侯景之亲信或“为佐命元功”,或“为谋主”“主击断”“为爪牙”,“自余王克、元罗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从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可见侯景对待元魏宗室代表人物与江左士族名士一样,委以所谓三公之位,是“从人望”而“加以尊位”,目的在于争取人心与舆论,并非视作心腹,授以实权。
当然,除利用入梁之元魏宗室代表人物以争取舆论外,侯景对那些出刺地方且有一定实力的元氏人物也加以利诱或策反。《梁书》卷四《简文帝纪》载太清三年秋七月甲寅,“广州刺史元景仲谋应侯景,西江督护陈霸先起兵攻之,景仲自杀,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为刺史”。《梁书》卷三九《元法僧传》载:“侯景作乱,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诱之,许奉为主。景仲乃举兵,将下应景。会西江督护陈霸先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众曰:‘朝廷以元景仲与贼连从,谋危社稷,今使曲江公(萧)勃为刺史,镇抚此州。’众闻之,皆弃甲而散,景仲乃自缢而死。”《陈书》卷一《高祖纪上》亦载:“(太清)二年冬,侯景寇京师,高祖将率兵赴援,广州刺史元景仲阴有异志,将图高祖。高祖知其计,与成州刺史王怀明、行台选郎殷外臣等密议戒严。三年七月,集义兵于南海,驰檄以讨景仲。景仲穷蹙,缢于阁下,高祖迎萧勃镇广州。”对此,《通鉴》卷一六二梁武帝太清三年所载最详:“西江都护陈霸先欲起兵讨侯景,景使人诱广州刺史元景仲,许奉以为主。景仲由是附景,阴图霸先。霸先知之,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集兵南海,驰檄以讨景仲曰:‘元景仲与贼合从,朝廷遣曲阳侯勃为刺史,军已屯朝亭。’景仲所部闻之,皆弃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缢于阁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镇广州。”可见对广州刺史元景仲,侯景以“许奉以为主”相诱,企图利用他控制岭南,并消灭地方的反抗势力。
此外,从相关记载中可见侯景所任将领中有一些元氏人物,《梁书》卷五六《侯景传》载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四月,“景以元思虔为东道行台,镇钱塘”;又载大宝二年十月,“是月,景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仪同尹思合、刘归义、王晔,云麾将军桑乾王元頵等据东阳归顺,仍遣元頵及别将李占、赵惠朗下据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新安太守元义,夺其兵”。又载十二月,“谢答仁、李庆等至建德,攻元頵、李占栅,大破之,执頵、占送景。景截其手足徇之,经日乃死”。元思虔、元頵、元义诸人具体情况虽不明,元頵、元义在侯景与萧梁之间还有反复,以致被侯景酷杀,但他们确实曾附逆侯景,被委以军旅之任。
由上文考叙可知,侯景乱梁过程中,为了聚集反梁势力,其利用入梁宗室降人的特殊身份,加以任用或利诱,对其名望显著者,皆封为王,其中最突出的当是元罗,他与南朝士族名士一起被授以三公之位;对其中的尚武之人则任为将领,助其攻战;对出刺地方者如元景仲,则加以利诱,以对抗拥梁之敌对势力。从元氏人物而言,其具体情况及其心态也颇为复杂,但作为流亡人士,他们在江南缺乏根底,像元贞这样抵拒侯景的南化人物毕竟是少数,他们大多选择与侯景合作。而元罗这样的名士人物,实际上只是侯景的一个摆设。至于元景仲等粗鄙武人,则企图依附侯景以乱中取利。总之,在侯景乱梁过程中,入梁之元魏宗室人物以其特殊的身份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出南入北,转复高迈”:入梁元魏宗室人物与南朝风尚之北传
众所周知,在长期分裂状态下,南北朝社会风尚与学术文化存在诸多差异。自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随着北方民族融合与南北统一进程的不断推进,南北文化交流也渐趋深入和广泛。在此过程中,就军事征服与政治统一而言,当以北方为主导,而就文化风尚而言,则以南风北渐为突出。北朝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吸收南朝文化,其中士人迁移与流徙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就入梁之元魏宗室群体而言,其南奔正处于南北朝社会渐趋统一、文化交融日益深入的关键时段,一些元魏宗室人物具有良好的雅化背景,他们一度流寓江南,思想观念、文化气质等方面深受南朝风尚的影响,其中有人返回北方,成为南学北传的使者。如元略,《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追先寺”条载:“略生而岐嶷,幼则老成,博洽群书,好道不倦。……萧衍素闻略名,见其器度宽雅,文学优赡,甚敬重之。……略从容闲雅,本自天资,出南入北,转复高迈,言论劝止,朝野师模。”元略是北魏孝文帝迁洛之雅化皇族子弟的杰出代表,其南奔之前已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准,以致梁武帝“素闻略名”。然其以往之效仿江左风雅,毕竟经由转手,未曾亲历与体验。其一度入梁,身临其境,得与梁武帝君臣朝夕相处,其作风自然也深受影响,不知不觉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后返回洛阳,言行举止与精神风貌非同寻常,在当时北方普遍钦慕南朝风尚的时代背景下,元略成为引人注目和竞相仿效的风流人物,所谓“出南入北,转复高迈,言论劝止,朝野师模”,绝非虚言。
与元略相似,元罗入梁前也具有较高的雅化素养,《魏书·道武七王·京兆王黎传》载其“虽父兄贵盛,而虚己谦退,恂恂接物。迁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元)叉当朝专政,罗望倾四海,于时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奖等咸为其宾客,从游青土”。元罗在梁时间较长,自然深受江左玄学风尚之熏染,返北入周后,当在气质风韵上有所表现。
相较而言,元略流寓江左历时未久,其所受南朝文化风尚之浸润主要表现在“言论劝止”之士风层面,而一些年少入梁且长期生活于此的元魏宗室人物,其南化程度自然更为全面、深入,其中有的在吸收南朝经史学术方面颇有成就。如元善,《隋书》卷七五《儒林·元善传》载:“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及侯景之乱,善归于周。武帝甚礼之,以为太子宫尹,赐爵江阳县公。每执经以授太子。开皇初,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伦仪表也。’凡有敷奏,词气抑扬,观者属目。陈使袁雅来聘,上令善就馆受书,雅出门不拜。善论旧事有拜之仪,雅不能对,遂拜,成礼而去。后迁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命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讽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更起朕心。’赉绢百匹,衣一袭。善之博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醖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元善年少入梁,其学术启蒙与研修自然肇自江南,故其后来归周入隋,以经学著名,治经讲学及其言行举止之风格颇为玄化,由所谓“凡有敷奏,词气抑扬,观者属目”,“风流醖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云云,显现出江左名士之流风遗韵。可见元善由南返北,仕历周、隋,不仅颇得统治者钦重,而且以其特殊的文化气质与学术修养,成为“观者属目”“听者忘倦”“后进所归”的名士化经师,在当时南北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①《北史》卷一九《魏献文六王·咸阳王禧传附元坦传》载元坦为元禧第七子,“禧诛后,坦兄翼、树等五人相继南奔,故坦得承袭。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复本封咸阳郡王”。
②《梁书》卷三九《元树传》所载元树之字及其南奔时间等与《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所载不同。《梁书》载其字“君立”,《魏书》载为“秀和”,二字或可并存。《北史》卷一九《魏献文六王·咸阳王禧传》即载元树“字秀和,一字君立”;至于其入梁前在魏之官职及南奔原委,《梁书》载其在魏为宗正卿及以尔朱荣乱而南奔云云,显为讹传。对此,中华书局本《梁书》校勘记于此条下引张森楷《〈梁书〉校勘记》已有考。
③《隋书》卷七五《儒林·元善传》载:“元善,河南洛阳人也。祖叉,魏侍中。父罗,初为梁州刺史,及叉被诛,奔于梁……善少随父至江南。”这里以元罗为元叉子,显然有误,且元罗本为元叉弟,其为梁州刺史及其举州入梁当在之后。故有关元善之家世,当从《北史》。
④⑥⑧赵超辑录:《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92、289、237页。
⑤《梁书》卷三九《元愿达传》载其于梁武帝普通中入梁,与《梁书》卷三《武帝纪下》所载大通二年入梁不同,中华书局本校勘记以为本纪所载准确,传中“普通”当作“大通”。
⑦对此,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北魏用人兼容并包”条有深入论述。清人周嘉猷《南北史世系表》卷一有言:东晋司马氏“自宋受晋禅,宗室凌夷,其北归者,位较荣显”。这也客观上说明了入魏之司马氏人物所受之待遇。
⑨《梁书》卷三《武帝纪下》也逐年记载元法僧父子所受封赏、任命情况:普通六年正月庚申,魏镇东将军元法僧以彭城内附,“甲戌,以魏镇东将军、徐州刺史元法僧为司空”;同年三月己巳,“以魏假平东将军元景隆为衡州刺史,魏征虏将军元景仲为广州刺史”;大通二年正月庚申,“司空元法僧以本官领中军将军”;中大通元年十一月丙戌,“司空、中军将军元法僧进号车骑将军”;中大通三年二月乙丑,“以广州刺史元景隆为安右将军”;中大通四年正月丙寅朔,“司空元法僧进位太尉”。
⑩这里“大通三年”,《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为中大通三年,当从本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