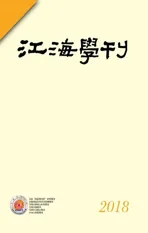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
2018-04-14刘永谋
刘永谋
内容提要 技术治理是当代政治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是迄今仍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近年来,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逐渐成为热点问题。应该加强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深入细致地研究支持和反对技术治理两方面的意见,以建设性的态度重构技术治理的理论和模式。哲学反思技术治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技术治理的思想史研究,技术治理的批评研究,技术治理实践研究和技术治理重构研究。
21世纪之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治理(technocracy)已经成为公共治理领域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可以称之为“当代政治的技术治理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在当代社会运行的科学技术化趋势日益彰显。在社会治理诸领域如公共治理、政府活动、企业管理以及NGO事务中,运用理性化、专业化、数字化、程序化以及智能化的技术原则和方法日益成为主流,“社会技术”“社会工程”和“科学管理”等相关理论术语日益为公众所接受。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加快技术治理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①换言之,技术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和加深的基本趋势,因而对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哲学反思意义重大。
应加强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
技术治理思想的兴起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电力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变革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很自然,欧陆一些学者提出将威力巨大的科学技术用于社会变革和改造活动中,这就是技术治理的基本主旨。
一般来说,可以将技术治理的思想追溯至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和圣西门的《论实业体系》,之后技术治理向全球广泛散播,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理论家。尤其是在20世纪的美国,从贝拉米的《回顾》、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凡勃伦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经由罗斯托、加尔布雷斯、布热津斯基、布尔斯廷、丹尼尔·贝尔,到奈斯比特和托夫勒等人,技术治理的思想可以说形成了明显的美国技(术)治(理)主义(technocratism)传统,已经成为与实用主义并驾齐驱的意识形态支柱。
由于散播太广,具体情况不同,技治主义者观点差异很大,在具体实施层面更是各持己见,但是均赞同“技术治理二原则”,即:(1)科学管理,即用科学思想和技术方法来管理社会;(2)专家政治,即由接受了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包括社会技术专家)来掌控权力。②归根结底,其主旨是社会运行的理性化,尤其是政治运作的科学化。专家治国是技治主义的实践形式,实质是施行科学管理,两者缺一不可。在实践中,常常存在“伪技术治理”现象,即掌权的专家并没有坚持以专业技能实施科学管理,而是打着科学的名号陷入非理性的专制之中。所谓技治主义,就是建基于技术治理二原则之上的系统的技术治理理论。
技术治理并不止于一种观念或理论,而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引发了技术治理运动。比如,20世纪30~40年代,受到凡勃伦等人思想的影响,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中心发生了北美技术治理运动(American Technocracy Movement),由激进派的斯科特和温和派的劳滕斯特劳赫、罗伯等人领导,影响了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政府的施政活动,之后美国的行政活动日益成为某种技术性事务。直至今天,运动的领导机构之一技术治理公司(Technocracy Incorporated)还在坚持。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一经产生,就带动中国当时的民国政府,接受和采取了一些技术治理的措施,为抗战救国服务。③再比如,在列宁时代,苏联就很重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广和运用,出现了帕尔钦斯基和恩格迈尔等著名的技(术)治(理)主义者(technocrat)。④20世纪60~80年代,苏联统治者一直试图推广“控制论运动”,建设全国性的自动化和互联网系统,对整个计划经济进行全面控制。⑤20世纪70~80年代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出现了运用控制论和互联网的技术治理运动,比如智利阿连德政府曾实施的“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⑥。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治理从美国向全球传播,逐渐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但是,与之不相称的是,关于技术治理研究却长期疲软。这种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1)20世纪以来技治主义者虽然不少,但主要精力用于投身实际的实践家多,理论家少。(2)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科学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盛极一时,技治主义遇到诸多总体化、宏大化的批评意见,而技治主义者缺乏对批评意见的必要理论回应,因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偏见,遑论对技(术)治(理)制(度)的深入细致研究。(3)虽然当代中国与技治制颇有渊源,但对它一直持一种“即学即用、活学活用”的态度,许多学人甚至认为技术治理没有什么理论好探讨。可以说,技术治理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均忽视了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仅仅视其为某种因歧义而杂乱的自发性、盲目性实践,甚至根本不能被归纳为统一和一致的思潮和趋势。这应该是全球范围内技术治理研究不尽如人意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当代社会治理的技术化让非专业的普通公众难以理解,如银行利率调控、能源政策和科技政策调整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技术治理的显著影响,因此,加强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势在必行,其中又以加强哲学反思为先。
最近几年,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在国际上成为热门问题,连续有相关专著问世,引起学界关注,如《技术治理的诱惑》⑦、《技术治理兴起:全球变革的特洛伊木马》⑧、《20世纪的科学主义和技术治理:科学管理的遗产》⑨、《美国的技术治理:信息国的兴起》等⑩。西方学者对技术治理的重视,与西方民主制在解决恐怖主义和移民问题的困境、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遭到知识界抗议等相关,这些情况在当前引发了对美式民主制弊端的反思,使得一些学人转向研究有精英制色彩的技治制。
此外,中国过去四十年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让所谓“中国模式(China Model)”或“中国道路(China Way)”研究在国际上成为热门,一些海外学人将中国成功经验归结为某种技术治理实践,即所谓“技治中国论”。如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国模式:精英政治与民主的局限》一书,将“中国模式”归纳为一种“底层民主制、中间实验制和顶层精英制”的兼具明显技术治理色彩和儒家色彩的精英制。虽然这种观点有明显问题,但其中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关注也促使技术治理研究逐渐成为受欢迎的理论问题。
应强调技术治理哲学反思的建设性
在西方国家,技术治理的思想一经产生就引起各种各样的哲学批评。这些批评多数站在怀疑甚至警惕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立场上,反感科学逻辑转化为治理逻辑,带有一种明显的反科学气质,呈现出以价值反思为主导的特点,往往停留在哲学的宏大层面。人文主义者们指责技治主义者把人视为机器或其上的零件,严重束缚了丰富的人性,压制了人的全面发展,把人变成机器的奴隶。自由主义者谴责技术治理试图狂妄地对整个社会进行自主控制,结果只能是侵害个体自由,必然导致专制和独裁,为此,哈耶克专门著有《科学的反革命》一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技术管理并非阶级中性的,而是会加强资本家的权力,帮助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为维护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历史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反对科学优于其他知识的观点,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中的强制应用,主张方法、知识、文化和治理的多元论,试图打破既有的国家与科学的紧密勾连关系。而许多技治主义的批评者都有怀旧主义情结,向往回归前现代的田园牧歌,“回到古希腊”!至于卢德主义者,主要在底层和民间一直存在,主张“停止科学”“砸烂机器”等,传播某种机器毁灭世界的末世情绪。总的来说,这些批评意见值得认真研究,如警惕技术治理滑入专制和独裁的危险,警惕专家权力过于集中等。但是,它们专注于宏大的道德质疑,缺乏实质的深入分析,尤其是缺乏对技术治理在战略和措施层面的各种主张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对当代政治的技术治理趋势的既成事实视而不见,不能在此基础上以一种建设性态度对待技术治理,而是试图对技术治理在思想上彻底拒绝,在操作上彻底根除——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只有正视当代政治的技术治理趋势,深入细致地对技治制加以研究,才能在此基础上对既有的技术治理进行避险、纠偏乃至重构。
除上述宏大批评意见之外,也有少数以实证方法质疑技术治理的批评意见,这种批评集中于政治学的经验研究领域,如J.C.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通过分析一些不同国家的大型社会工程实施情况,得出了大型社会工程必然失败的结论,并给出了四个原因,即:社会管理简单化,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独裁主义以及软弱的公民社会。这种批评意见很有启发性,但显然的再批评是:如果尽量避免这四个原因,是否可以实施一定程度的技术治理呢?并且,经验材料的解读存在不同的观点。比如说,社会工程成功的标准如何设定,他所讨论的工程是否彻底失败了,还是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所有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又比如,何为大型社会工程?规划范围不大的社会工程是否可行?即便是全国施行,新加坡与中国规模上差别巨大,两国的大型社会工程遵循的是否是一样的规律?总之,技术治理的实证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案例、更深入的讨论以及更深刻的反思。
总的来说,对技术治理的总体批评都明显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把技术治理的目标等同于“机器乌托邦(Machine Utopia)”,即将整个社会变成一架严密而总体化的机器,每个人变成机器上的零件。这是一种对技术治理与技治主义的长期以来的偏见,这种偏见在西方非常流行,与激进技治主义者如凡勃伦、斯科特等人的机械技治主义思想更为人熟知因而遮蔽了温和技治主义者的主张有很大关系,也与西方有反科学倾向的敌托邦(dytopia)文艺作品的渲染有很大关系,如《1984》中无处不在的“电幕”几乎成为科技替专制为虎作伥的标志。
凡勃伦的技术治理思想建基于机械论的科学观之上。在他看来,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入以工业系统为主干的工业社会,而工业系统是精密机器式的新型生产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任何一个部分的问题都会导致整个系统运行的问题。因而,必须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才能高效地运转工业系统,只有工程师才有运转它的专业技能,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理想状况是将权力让渡给工程师,让他们组成专业性的“技术人员的苏维埃(Soviet of Technician)”来治理整个社会,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来全社会总体化地配置资源,将工业目标从资本家的利润转向有用商品的生产上。为此,必须发动非布尔什维克式的“工程师革命”,团结底层民众,彻底颠覆资本主义制度,但又不能将领导权交给不具备专业领导能力的工人阶级。凡勃伦主张将权力交给工程师的想法,受到了来自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两方面的批评。总的说来,他的技术治理理论对科学和社会都做了机械性的理解,指向一种全社会无一例外的宏大乌托邦社会工程,并与颠覆性的“革命”相联系,是敌托邦小说所批评的“机器乌托邦”蓝图的典型。
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中的激进派领袖斯科特受凡勃伦影响巨大,凡勃伦不仅积极参与了该运动的早期阶段,他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亦成为激进派的“圣经”。斯科特坚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拒绝与美国政府合作,把与政府合作的温和派称为“叛徒”。他领导激进派为工程师掌权做准备,并试图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契机,在加拿大发起“总征兵”,组建有统一制服的“有纪律的部队”,以致被政府压制和查禁。斯科特等人的行动在北美引发了很多人的反感,也导致北美技治主义者的迅速分裂与运动的快速衰落。
然而,无论是技术治理的理论家,还是技术治理的行动者,激进派只占少数。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关键区别就在于是否全盘推翻既有基本社会制度,其主张可否作为一种改良方案为提升社会运行水平服务。技治主义“鼻祖”圣西门属于温和派,主张由工业家和科学家联合执政,共同维护既有的制度。而凡勃伦之后,基本上有影响的技术治理理论家都是温和派。如丹尼尔·贝尔就认为,技治主义是非意识形态的,是支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在实际发生的技术治理运动中,大多数的技治主义者都是温和的,积极与政府合作,努力用专业技能改善政治活动和公共治理。前述列举的北美、苏联和智利的技术治理运动,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在既有的社会基本政治框架下实施的。技术治理的实践者们提出的许多措施,如社会测量,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成为当代公共治理活动的基本措施,促进了社会进步。在中国,无论是在南京政府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一定程度的技术治理对社会发展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过去40年间,工程师、专家和知识分子活力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增添了强大的活力。总之,技术治理并不只有“机器乌托邦”这一种模式,在历史上有许多其他的不同实施模式,很多都能与具体的社会现实结合得很好,比如源自罗斯福新政(New Deal)的智库(Think Tank)模式。因此,把技术治理等同于“机器乌托邦”是一种未经深思的偏见。当然,必须警惕技术治理走向极端的“机器乌托邦”,该问题应该成为技术治理哲学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哲学反思技术治理的主要内容
总的来说,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属于近年来新兴的科学技术的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 Technology)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科学技术的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该问题的哲学反思,主要有马克思传统、知识社会学传统、尼采-福柯传统和技治-反技治四种传统。因此,对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要在这样一个更广泛的理论视域下进行。
加强对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四个部分的研究内容。
1.技术治理的思想史研究
在思想史上,自称为技治主义者的理论家并不多,但是主张过技术治理立场的却不少。从技术治理的视角梳理思想史,可以厘清不同种类的技术治理思想以及技术治理的不同实施方案和措施,既可以加深对技术治理正反两面的理解,也可以为重构技术治理提供理论素材。
大致说来,技术治理的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包括:(1)早期的技术治理者思想研究,如弗朗西斯·培根“所罗门之宫”的思想、圣西门的“牛顿协会”的思想,还有孔德实证哲学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包含一些技治主义的思想。(2)政治算术学派、国势学派与社会统计学派的技术治理思想研究。政治算术学派主张用观察和数据等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代表作是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国势学派与政治算术学派,同为统计学的早期流派,前者主张以大事与政策记述国家发展,与政治算术学派发生争论。最终,以G.V.迈尔为代表的德国社会统计学派的兴起结束了上述争论,逐渐使得社会统计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3)凡勃伦“技术人员的苏维埃”与“工程师革命”思想研究。他是美国技术治理理论的集大成者,不仅形成了完整的技治主义理论体系,亦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意见。(4)泰勒等人的科学管理思想研究。《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提出以科学和数学方法运转企业,后来被A.V.希尔和E.S.伯法发展为科学管理学派。(5)列宁论泰勒制研究。列宁对泰勒制非常感兴趣,多有议论,并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泰勒制的某些思想。(6)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研究,主要包括纽拉特、卡尔纳普和齐尔塞尔等人的技术治理思想研究。以往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忽视它的社会改造思想,新世纪之交这个问题引起了注意,如卡特赖特等人所著的颇具影响的《奥图·纽拉特: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哲学》。(7)制度经济学派的技术治理思想研究,主要包括罗斯托、加尔布雷斯和布热津斯基等人的观点,重要著作如《新工业国》。(8)操作主义的政治构想研究。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思想影响深远,遍及心理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9)未来学派的技术治理思想影响,主要包括丹尼尔·贝尔的“能者统治”以及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等人的观点。(10)新社会物理学研究。这是社会物理学在当前新的网络和大数据环境中的最新发展。(11)山达基教(Scientology)研究。这是一种与信息通信技术、控制论、人工智能和人体增强技术等发展相关的极端科学主义思潮,主张赋予科学以宗教的内容。
2.技术治理的批评研究
当代许多著名思想家都对技术治理进行了批评,比如哈贝马斯的《技术治理的诱惑》、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无论是对待既有的技术治理思想,还是对待对它的批评意见,都应该采取批判分析的态度,吸收有益的意见,剔除有害的观点。对技术治理的批评意见,很多言过其实,但有些批评意见值得认真对待,并在重构技术治理模式中加以注意。
研究思想家对技术治理的批评意见,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芬伯格等,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利奥塔和罗蒂等,人文主义者如芒福德、波兹曼等,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和波普尔等,相对主义者如费耶阿本德等,以及卢德主义者、怀旧主义者的批评意见。当然,对批评意见必须再批评。
除此之外,还要研究技术治理的乌托邦小说如贝拉米的《回顾》,和敌托邦小说如“反乌托邦三部曲”。研究政治学领域的经验批评,如前述的《国家的视角》《科学阶层》等。并且,在研究批评意见的基础上,勾勒批评者眼中技术治理的形象,该形象可以称之为“机器乌托邦”。
3.技术治理的实践研究
各种技术治理运动均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提出了一些实践措施,如北美技术治理运动提出了社会测量和能量券两项标志性的举措。技术治理理论不是某些理念的集合,而是包括可以操作的战略、制度设计和重大措施的系统性理论。哲学对技术治理的反思不应止于理念层面,而应涉及宏观的战略层面。如前所述,这部分的研究重点是北美技术治理运动、苏联的控制论运动、拉美技术治理运动和民国的技术治理的实践研究。这些研究属于历史案例研究,核心是梳理科技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揭示技术治理在历史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技术治理的重构提供经验素材。
4.技术治理的重构研究
要在理论上避免“机器乌托邦”,发掘技术治理理论和模式的重构问题。对于“技术治理二原则”有不同的理解,这是重构技术治理的理论关键点。对于科学管理原则,什么是科学原理,什么是技术方法?对此,科学哲学百年来的研究已经提出诸多看法,机械论科学观已然不再是社会一般科学观的主流。基于不同的科学观,对科学原理与技术方法的理解就有所不同,实施的科学管理必然有差异。对于专家治国,谁是专家,专家怎么掌权,怎么施政?这些问题并非只有一种答案。比如“专家”一词,在现代中国其实是与传统“士大夫”相对应的术语,是泛专家概念,不仅局限于自然科学专家。专家掌权实际指的是掌握政治权力,并非所有权力,也不是政治权力的全部,可以控制在比如建议权、实施权等环节。专家施政也有不同的模式,可以采用乌托邦的激进方式,也可以采用渐进的改良模式,换句话说,专家政治可以作为目标理想,也可以作为工具手段,服务于不同的社会总体制度。总之,可以对技术治理进行理论重构,防止极端的技治主义观念。实际上出现技术治理派别的原因正是在于对“技术治理二原则”理解有差异。
技术治理的重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基础理论问题,主要包括:(1)重构何以可能?这涉及技术治理证成、证否和重构的基本逻辑的厘清;(2)治理转译问题研究。自然科学知识推不出道德和政治原则,此即为“是”与“应当”的二分问题,但是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是”能不能推出“应当”,而在于“是”在历史中如何推出“应当”,因为“是”在历史中是一直在推出“应当”。这是如何发生的?有哪些模式和规律?此即所谓的治理转译问题。(3)如何选择或建构新的科学论基础?该问题涉及诸多新问题:不同科学论基础会导致何种不同的技术治理理论和模式,如何在不同模式之间取舍,如何在相互冲突的科学论中建构新科学论作为技术治理的基础。(4)专家权力问题。为何又如何赋予专家权力?专家权力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是什么?专家权力如何实施和限制?随着20世纪知识分子人数急剧增长,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分子还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都开始要求政治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治主义是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政治权力表达,而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权力诉求往往围绕言论自由而展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研究和科学社会学对知识分子与权力的问题多有研究。(5)科学审度的技术治理理论。当前,在科技哲学最前沿领域,出现了明显的我们称之为“从辩护、批判到审度”的大趋势,如以苏珊·哈克的批判常识主义、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等为代表的审度论的新科学哲学,以“荷兰学派”的“价值论转向”以及负责人创新(RRI)和设计哲学为标志的过程论的新技术哲学和以柯林斯、林奇等人为代表的互构论的STS(Science & Technology Study)“第三波”。那么,科学审度论政治哲学的推论是什么?换言之,以科学审度论为基础的技术治理模式是什么?当然,作为新科学哲学的科学审度论本身仍需要具体的理论建构,“从辩护、批判到审度”的观点需要进一步阐发。
技术治理的重构研究其次要解决若干重大操作问题,主要包括:(1)“机器乌托邦”批判,即专门就“机器乌托邦”的形成及其防范做出细致的理论研究,反对总体化社会工程,将技术治理限制在工具层面。当然,这种再治理同样要依靠理性和科技。(2)技术治理的再治理问题,即以何种制度设计防范专家权力过大威胁民主和自由。(3)社会主义与技治主义。在思想史上,社会主义与技治主义有相当多的联系,有一些类似的立场。圣西门既是技治主义的“鼻祖”,也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应该说,作为局部的制度设计,技术治理与社会主义是不冲突的,是可以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下推进的。(4)技术治理与当代信息科技的新进展。技术治理与科技最新进展紧密相连,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与AI技术的不断深入推进,对技术治理实践将产生何种影响?应该如何应对?比如时下热点问题:大数据与计划管理的问题。(5)技术治理与当代中国。首先要批判海外的“技治中国论”,一定程度的技术治理并没有也不会改变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其次要哲学地思考:如何有效地让技术治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换言之,如何结合具体国情形成中国特色的技术治理模式?再次,技术治理与中国智库建设。作为技术治理的重要实施措施,智库今天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实践活动。〔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
①刘永谋、兰立山:《泛在社会信息化技术治理的若干问题》,《哲学分析》2017年第5期。
②刘永谋:《技术治理的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③Yongmou Liu, American Technocracy and Chinese Respon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Export Poli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1927~1949,TechnologyinSociety,Vol.43, November 2015.
④樊玉红、万长松:《20世纪20年代苏联“专家治国运动”研究》,《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⑤Benjamin Peters,HowNottoNetworkaNation:theUneasyHistoryoftheSovietInternet, Cambridge, MA, USA: MIT Press, 2016.
⑥Eden Medina,CyberneticRevolutionaries:TechnologyandPoliticsinAllende’sChile, Cambridge, MA, USA: MIT Press, 2011.
⑦Harbermas, J.TheLureofTechnocracy, translated by Ciaran Cronin, Cambridge, UK; Malden, MA, USA: Polity Press, 2015.
⑧Patrick M. Wood,TechnocracyRising:TheTrojanHorseofGlobalTransformation, Mesa, AZ, USA: Coherent Pblishing, LLC, 2015.
⑨Richard G. Olson,ScientismandTechnocracyintheTwentiethCentury:theLegacyofScientificManagement,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6.
⑩Parag Khanna,TechnocracyinAmerica:RiseoftheInfo-State, New York: Create Space,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