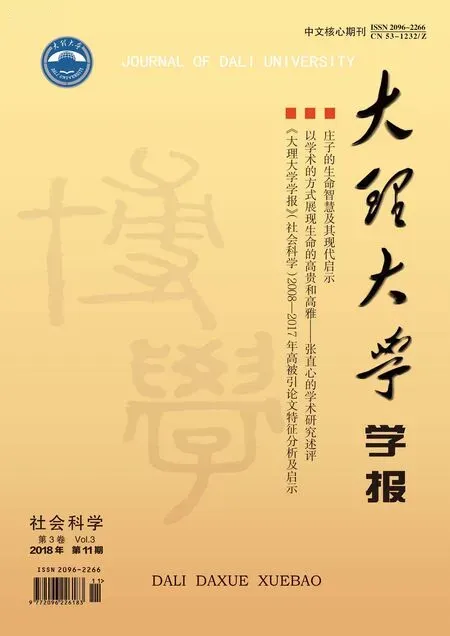论昭通乡土小说中的苦难抒写
2018-04-11张伟
张 伟
(昭通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昭通 657000)
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苦难,打开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即可发现里面记录了战争、瘟疫、饥荒、洪水、干旱、地震等原因造成的大量苦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更是每天都能耳闻目睹各种各样的苦难。“如果从广义上把苦难理解为是人的受苦,那么苦难似乎伴随着历史的整个进程。”〔1〕文学是人学。既然苦难是人类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苦难就无所谓人生,那么它就必然会成为文学关注和表现的对象。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作家如杜甫、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马尔克斯,无一不是苦难的关注者、抒写者乃至亲身体验者。正如有学者指出:“苦难意识是一种总体性的情感,终极性的价值关怀,说到底它就是人类历史和生活的本质。文学经典,它们无不是因为展现了人类的苦难意识而震撼人心。”〔2〕回避苦难的作家不可能成为伟大作家,伟大作家一定会关注并抒写人类的苦难,只不过所抒写的具体内容及抒写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如果没有苦难,以及对苦难的倾力关注,我们的文学或许会失去许多丰富内涵。”〔3〕
自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积贫积弱,屡受列强的欺凌,逐步被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战乱频繁,天灾不断,所以整个中华民族都承受了巨大的历史苦难,以至于柏杨等历史学家感慨说做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是一种最大的不幸。由于现代中国多灾多难的历史背景,所以抒写苦难已经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就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苦难抒写是一种贯穿性的创作现象,大量苦难抒写甚至形成了一种“苦难文学”。这无疑和中华民族经历的现实苦难直接相关。苦难意识在三种“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左翼激进主义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4〕。这一优良传统,应当倍加珍惜并予以传承。我们欣喜地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兴盛不衰的昭通乡土小说始终在关注和表现着人类的苦难,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苦难,表现出了可贵的苦难意识和人文精神。
一、昭通乡土小说中的苦难情怀
昭通不是一片富饶的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它僻处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苦寒的高原地带,乌蒙山深处,贫瘠、落后、闭塞、交通不便,仿佛是被上帝遗弃的土地,也彷佛是被世人遗忘的土地。出了云南省,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叫昭通的地方的人寥寥无几。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当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各大都市以及沿海地区到处呈现出一片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之时,昭通依然是国家仅有的几个成片贫困地区之一,贫困现象触目惊心。一些最偏远的山旮旯里的许多农户除了种几亩土豆、玉米以维持最起码的生存外,几乎家徒四壁。连前后两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温家宝在先后视察昭通时见此情况都心情沉重,语重心长地嘱咐随行人员以及昭通地方官员一定要打好昭通脱贫致富这场攻坚战。尽管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昭通广大乡村要改变千百年来的贫困落后面目却绝非一朝一夕可成,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就注定了昭通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为了生存要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付出更多生活的艰辛,承受更多生活的磨难。何况昭通乡土作家们自身大多出身寒门,从小所经受的磨难丝毫不亚于其他人,因而他们能够对生息于昭通这片贫瘠偏远土地上五百多万各族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这一点只要读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的各种回忆性质的文字即可知之。于是抒写苦难也就成了昭通乡土小说作家自觉且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在无数的昭通乡土小说作家如夏天敏、孙世祥、杨昭、胡性能、吕翼、刘平勇、沈洋、徐兴正、傅泽刚、黄代本、曾令云、潘灵、刘广雄、龙志毅、张仲全、李寿春、轻风、叶听雨等的笔下,均深刻地抒写了昭通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苦难。
这种苦难主要集中在底层人民身上。首先,昭通乡土作家们在一系列作品如孙世祥的《神史》、吕翼的《土脉》、张仲全的《沧桑》、李寿春的《乌蒙雪》、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杨昭的《日蚀》、刘平勇的《一脸阳光》中,描写了农村的破败、落后,描写了农民在权力、暴力、贫困以及自身的种种精神枷锁压迫下,苦难重重的生存状态,描写了他们的劳苦、贫穷、奴性、卑微、麻木、愚昧与窝里斗。受到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极力推崇的《神史》就“写尽了环境的艰难,物质上的贫困,人心的复杂丑陋,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性的爱恨善恶交困矛盾,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和权力暴力,人被异化的阴暗悲剧。”〔5〕149“写出了一个贫困农村社会充满苦难的封闭的家族时代的悲剧。”〔5〕149而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则写出了扶贫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给老实巴交的农民德山老汉一家带来的家破人亡的苦难悲剧,发人深省。
此外,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在许多作品如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吕翼的《土脉》、傅泽刚的《路口》中,描写了进城打工农民这一城市边缘人群体在城市打工的艰辛以及他们所受到的歧视、欺诈和其他种种不公正待遇,他们的被拒、迷惘、孤独、无助、堕落与自暴自弃。与此同时,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在不少作品如吴运强的《香嫂》、龙志毅的《政界》、吕翼的《土脉》、朱镛的《仲熊》中还描写了为了摆脱贫穷甚至仅仅是为了求得起码的生存权而卖身的女性们的屈辱和无奈,写出了她们急欲摆脱贫穷等方面的生存困境,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与内心的伦理道德观念之间的挣扎与煎熬。另外,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对于乡村留守儿童、孤儿、光棍、小贩、流浪者、残疾人、病而无医者、孤寡老人、吸毒人员的苦难也予以了深切的关注。如刘平勇的小说集《天堂邂逅》中就写了失地农民当起了小贩却与城管发生冲突,最后同归于尽的苦难悲剧。可贵之处在于刘平勇没有简单地单方面谴责城管或小贩,作家的良知不允许他偏袒任何一方,他以饱含悲悯的笔墨既写出了小贩在生存压力下谋生的艰辛与痛苦,也写出了城管为了保持市容的整洁付出的努力。如果说失去了其他生活来源的小贩为了一家人的生存的谋生行动具有某种天然的合理性,那么城管为了市容整洁所采取的执法行动未必就没有合理性,毕竟谁都希望我们生活的城市环境整洁优美一些。但在两者各自的合理性中,悲剧却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双方的家庭都陷入了极度的困顿与悲哀之中,作者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双方的处境都表示了深厚的同情,这就不得不让读者更深刻地反思苦难的根源,审视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尤其可贵的是,在抒写沉重的苦难的同时,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也写出了生息在昭通这片古老土地上多灾多难的各族人民真诚善良、仁义宽厚、坚韧不拔、奋发图强、乐天安命、傲视苦难的生活勇气和其他诸多优秀品质。这些品质不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大都市里的人们所能具有的,正因为如此,在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的苦难抒写中,我们不仅读出了深沉的悲悯情怀和凝重的历史沧桑感,也读出了人性的温暖和理想主义精神。
二、苦难抒写中的人文精神
众所周知,虽然人类社会自古就充满了苦难,但并非每一位作家都会关注苦难,有些作家甚至会刻意掩盖苦难。且不说古代文学史中有所谓的花间派,所写的永远是女色、游宴、歌舞、风花雪月等题材,看不到一些一毫苦难的影子。即使是早年曾以“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自许,写出了《卖炭翁》《观刈麦》《上阳白发人》之类针砭时弊同情底层民众疾苦的诗篇的白居易,在经历了残酷的仕途倾轧与宦海浮沉之后,晚年也大写特写其沉醉风月、流连光景、优哉游哉的闲适诗了。现当代文学中亦存在类似的情况。本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分到了土地,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开始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日子过得蒸蒸日上,数亿农民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发自内心的爱戴。但好景不长,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国家的农村政策上出现的一些失误,使得广大农民又生活在天灾人祸引发的极度贫困之中,甚至有许多人因饥饿而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却偏偏出现了诸如《金光大道》《艳阳天》之类掩盖苦难,歌舞升平的小说作品。读了这样的作品,你会误以为中国农村已进入人间天堂。又如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大都市以及沿海地区的繁荣兴旺程度已不亚于欧美国家,于是文学创作中的豪华风、言情风、拜金风、戏说风兴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许多以现代派、后现代派、先锋派自诩的新潮作家们笔下所宣扬的不外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人生观,崇尚的不外乎逢场作戏、游戏人生,过把瘾就死的玩世心态。苦难早就在这些新生代作家们的笔下消失了,呈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是大款富豪、达官贵人、帅哥美女、豪宅、名车、度假村、星级酒店、购物中心、酒吧、咖啡厅、夜总会、健身房、美食、赌博、酗酒、吸毒、偷窥以及淫乱等等,是卿卿我我、花前月下、三角恋爱、没完没了的打情骂俏,争风吃醋与感情纠葛。这种作品固然迎合了一些读者浅薄低级平庸的审美趣味,但人间的苦难失重了或曰被彻底放逐了。
所幸的是,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始终保持了对苦难的关注和抒写。在当今中国,虽然经济已经得到了较大发展,但苦难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依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除非一个作家闭目塞听,否则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既然文学是人学,那么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苦难就永远是文学关注的中心,因为这体现了作家们的良知与社会责任心。只有关注苦难、抒写苦难,让读者们的心灵为人类的困难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而感动颤栗,这个社会的苦难才会被更多人知晓,被更多人思考,人们才有可能采取行动来缓解乃至消除苦难。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对苦难的关注是人最切近的关注,苦难使人严肃地思考自然、社会、历史和人自身。”〔6〕89由此可见,昭通乡土作家们对于苦难的执著抒写,体现了一种异常可贵的人文精神。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对于苦难的关注与形形色色的新潮作家对于所谓“欲望”与“小资情调”的热衷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种不同创作题材与创作风格的背后不是创作观念与技巧的差异,而是良知的比拼。昭通乡土小说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之一夏天敏曾说自己在儿童年代及青少年时代“有过许多沉重、伤感、令人潸然泪下的往事,有过许多难以言喻、难以倾诉的深深的伤痛。”“激越、愤懑的情绪需要宣泄,沉重、伤感的心情需要倾诉。郁结于胸,发而为文,这就注定了我与文学有了不解之缘。”〔5〕97既然这样,夏天敏以及一大批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以极大的热情和悲悯之心来关注和抒写苦难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不是昭通作家们有意要以苦难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是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承载着太多的苦难人生。作家不过是以自己的良知在对人生进行文学的思考与探寻。”〔7〕化用艾青的一句诗来形容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也很恰当:“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及生息于其上的人民爱得太深!”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向执着关注苦难、抒写苦难的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三、苦难抒写中存在的艺术缺陷
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在苦难抒写中表现出了可贵的人文关怀,但他们的苦难抒写中也存在着需要在今后的创作中予以正视并力求克服的艺术缺陷。
首先,昭通乡土小说作家虽然描写了大量的苦难,但他们的大部分作品对苦难的根源的揭示过浅。换言之,他们关注了社会层面的苦难,但对本体层面具有形而上哲学意味的苦难则关注得不够。我们不否认人类有大量的苦难是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比如在黑暗的旧社会里,广大人民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忍受着无穷无尽的苦难,所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多年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封建剥削制度,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新中国的成立给一直生活在长夜漫漫何时旦的各族儿女带来幸福生活的希望,但新中国政权毕竟脱胎于旧社会,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变得很完美,因此,我们社会中依然存在一些由社会不合理因素造成的苦难。应当说,昭通乡土小说作家对此类社会层面的苦难的抒写已比较深入,且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社会批判意识,至于昭通乡土小说中苦难的根源则不外乎贫穷、愚昧以及人际的争斗,官僚主义作风,权力的欺压,金钱对人性的异化与腐蚀等等。如夏天敏的小说集《好大一对羊》、吕翼的小说集《寒门》、傅泽刚的农村题材小说、文坛新秀沈洋的小说集《红裙子的流向》《穿透瓦房的阳光》等作品皆是如此。应当说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笔下的这些苦难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对此类苦难之根源的揭示也真实可信。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人类的苦难并不一定都与社会因素的不合理有关。佛教早已揭示,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人生就是苦海。苦难乃是人生的本质。而基督教也认为,自从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人类从此就注定了祖祖辈辈要在大地上流血流汗,苦难重重。这种苦难来自人类与生俱来,永远无法摆脱的原罪。无独有偶,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尼采也一再指出:“人生是多灾多难的,而且常常是无意义的。”〔6〕15人生就是痛苦,痛苦是人生永恒的本质。但纵观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的创作即可发现,大量的衣食住行诸方面的生活难题构成了他们苦难叙事的主题,他们显然对来自生命本体,具有本源性和形而上意味的苦难关注和抒写得较少,这说明他们对人类苦难之根源还停留在社会的层面亦即停留在表层,因而跟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如曹雪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比,精神境界的差异就太明显了。有学者曾指出90年代农村苦难小说的苦难意识的不足之处:“中国农民承受了无数的苦难,现当代农村小说也着力描写了农民的苦难,但很多小说都停留在描绘现实苦难的水平上,没有上升为伟大的悲剧。”〔7〕这一批评用之于昭通乡土小说身上也是恰当的。
其次,昭通乡土作家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苦难对人类灵魂的净化和升华作用。对于人类而言,苦难并非只有负面意义。别的不说,苦难是人性的试金石,它可以深化我们对人性和人生的认识,春光明媚或和风细雨的环境不是认识人性的最佳环境,只有在苦难的环境中,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卑下、真诚与险诈才会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只有通过苦难,我们才能更深刻地透视人性、解剖人性、理解人性。文学是人学,对于文学而言,还有什么比表现人性更重要的使命呢?而且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言:“正因为人生痛苦,充满了各种坎坷、苦难和不幸,才有世界整体生命的丰盈和永恒,才显现出人生的悲剧美和审美意义。”〔8〕而卡夫卡也说过:“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唯一的联系。”〔9〕对于人类而言,苦难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人在苦难的折磨下沉沦与怨天尤人,有人则在苦难的打击面前变得更加坚强并获得了灵魂的净化与升华。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人类再也没有了苦难。所有人皆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一切愿望皆可如愿以偿,那么人类的生命力、创造力以及审美能力都必将日趋退化、萎缩,甚至枯竭。因此,文学的确应当抒写苦难,但却不是对现实苦难的简单模仿,更不应是对它的复制,而应当将对苦难的抒写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使之成为审美的对象,使之成为展示人性的伟大和崇高的对象,并引导人类的灵魂走向进化和升华。“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野中,苦难既是现实运动的结果,同样也是朝向未来的起点;既具有暂时的历史必然性,又具有必然的历史暂时性;苦难促成了人的狭隘,却生成了人的全面发展。以苦难为中介,人的解放才是可能的。”〔1〕令人稍感惋惜的是,昭通乡土小说作家抒写苦难的作品虽然多,但具有较高美学成就和丰富的美学意蕴,并能真正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者则依然欠缺。就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当我们统观数量不菲的当代苦难叙事文学时,发现能穿越时空而恒久回响于灵魂的作品,能真正带给人们以苦难感悟、理解和升华的作品,并不多见。”〔10〕这一评论,值得具有关注现实、抒写苦难之优秀传统的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