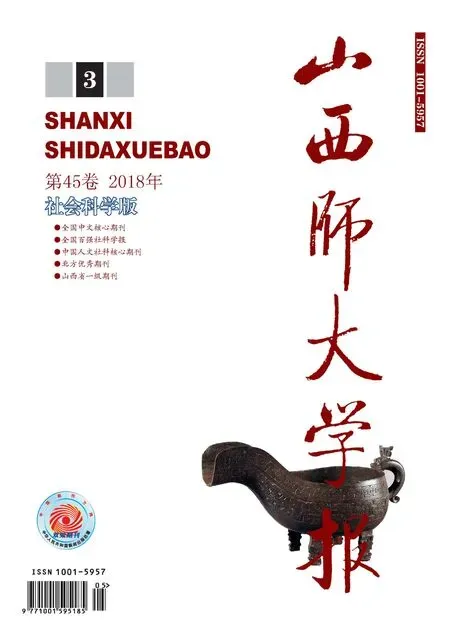论毛泽东建设话语建构的逻辑理路
----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为中心
2018-04-04许冲
许 冲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631)
梳理毛泽东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历史,针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阅读、批注和谈话,是构成其建设话语建构实践的重要组成。一般而论,学术界对此多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称《批注和谈话》)为文本依据,立足于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视域,考察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价值。毋庸讳言,此类历史考察和理论研究意义重大,但从本质层面看,仍未完成对毛泽东话语建构逻辑的基本揭示。事实上,若非经由“历史”的叙述、“哲学”的反思和“政治”的批判,毛泽东是难以仅仅借助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阅读实践,即可完成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话语的课题的。鉴于此,本文拟以《批注和谈话》为分析对象,就该话语建构逻辑加以具体论析,以期镜鉴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建构。
一、以“历史”的叙述为基准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科学是“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1]178由此不难想象,没有“历史”支撑的话语建构,缺失的将不只是话语形式的历史厚重感,更重要的是话语内容的科学性与合法性。毛泽东在评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曾指出“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是该书部分观点“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2]634由此,在1958年至1960年的文本阅读和话语建构实践中,如何经由特定的历史叙述和对比分析,来证实或证伪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规律,就成为毛泽东建构建设话语的逻辑起点。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贯重视运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问题,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采用“古今中外法”。[3]400就其精要之处,该方法不止于要求做到“通贯古今”和“知己知彼”,更重要的是能够做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有赖于此,毛泽东全面以史为据建构建设话语,主要反映在如下方面:
一是基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话语建构。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毛泽东主张“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4]22因此,毛泽东在《批注和谈话》中,既旁征博引又不断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应用,目的就是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公理公例”。如为了溯源商品生产的历史及其存废的客观性,毛泽东以商纣王“经营东南”加以历史佐证;[2]50为了阐明土地所有权变更将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毛泽东以曹雪芹《红楼梦》的总结语进行历史隐喻;[2]102—103为了论证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毛泽东以春秋时期郑庄公注重斗争策略与三国时期董卓盲目杀戮进行历史对比;[2]145—146为了说明文化革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相对价值,毛泽东以张昭、周瑜、吕蒙、鲁肃等人对曹作战的态度作为历史例证;[2]271为了肯定社会劳动中“精神鼓励”的价值,毛泽东以老子“尚贤”思想批判“物质刺激”的片面性;[2]427为了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级差地租问题,毛泽东以萧何“耕三余一”之法予以历史启迪等。[2]600可以说,毛泽东在建构建设话语的过程中,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发展”,[5]708其最直接的效果是将“历史”的“旧言”成功转化为“建设”的“新语”。
二是基于中国革命建设历史的话语建构。鉴于此类历史经验的近因效应,毛泽东据以阐释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意在藉此构筑建设话语的历史合法性基础。如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长期性,毛泽东以中共领导革命战争22年才取得全国胜利的史实,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保持“耐心”的重要性;[2]57为了肯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以大革命时期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分裂及其与中共联盟关系的演变详加论证;[2]288—289为了解释“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毛泽东从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没有获得全国政权、近代化兵工厂和最新武器却能获得革命胜利的事实进行反证;[2]544为了表达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规律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技术发展和手工劳动领域的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现状进行具体例证;[2]415—416为了说明社会主义革命方法需要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获得,毛泽东以三年恢复时期至庐山会议期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懵懵懂懂”、初步明晰、出现“毛病”和遭遇“曲折”的历史进程详加说明。[2]715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可见,中国革命建设历史实际构成了毛泽东“现实底思考”建设话语建构的“现时史”。[6]1269
三是基于苏联革命建设历史的话语建构。毛泽东在《批注和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不过40多年,想写出一本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很难。[2]803尽管如此,却并不妨碍他以“苏联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为“先例”,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话语。[2]30如为了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毛泽东以十月革命胜利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基本内容”进行历史说明;[2]81,87为了阐释“革命的两手政策”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的作用,毛泽东以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列宁的“两手”准备及其具体实践详加阐释;[2]84—85为了言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地位和建设方法,毛泽东基于苏联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而强调两点:一是我国人民还需要“忍受一点牺牲”,二是要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2]180—181为了陈述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合理性,毛泽东以列宁和平赎买构想的破产予以历史昭示。[2]293—294可以说,经由民主革命时期的“以俄为师”,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以苏为鉴”,苏联革命建设的历史经验始终是毛泽东建构政治话语的直接参照和语料来源。而藉此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话语,既因应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轨迹,也符合国人长久以来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期待。
此外,毛泽东在《批注和谈话》中还广泛运用资本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等历史资源,意在借助于更为深远的历史时空和历史内容,来丰富建设话语的历史内涵,此点尤以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历史、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的话语建构最为典型。[2]50,125,297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从历史科学的高度述及建设话语建构的方法论,阐发了一些极具历史哲学价值的观点。如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永久存在的经济范畴,都只是“历史范畴”;[2]17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2]713“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自然更不能从特殊中发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2]158中国编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需要学习《史记》和《三国志》的编撰学问与规范等,[2]453这些内容均是增进毛泽东建设话语历史底蕴的重要支撑。
由此可见,任何历史叙述都不止于叙述历史本身,它无不表征着叙述者的历史理解以及对于历史的二度建构。在《批注和谈话》中,毛泽东为谋划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古今中外”的历史资源和方法论建构建设话语,正是在对上述历史内容的叙述和理解的基础上,才重新建构出既符合中国实际又符合历史逻辑的话语内容。当然,其中也不乏历史理解上的偏误,甚至于功利主义的阐释和运用,并由此将一些主观化和绝对化的思想观点嵌入社会主义建设话语当中,这是当前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需要深刻省察的。
二、以“哲学”的反思为理据
建设话语的建构与经济问题的求解相似,需要“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7]82前者一般寄望于历史的叙述,后者唯有上升至哲学的高度方可揭示话语的本质,进而找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根本路径。其实,毛泽东在建构建设话语的过程中,一方面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讲逻辑”[2]402“没有辩证法”,[2]803另一方面又寄望于依靠“哲学家的头脑”及其掌握的辩证法武器,[2]803深入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规律,据以夯实建设话语的理论基础。
因而,在1958年至1960年的文本阅读和话语建构实践中,毛泽东强调要以“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2]423既不拘泥于具体的经济实践,也没有秉持纯粹“为哲学而哲学”的理路,而是针对现实的建设实践与理论问题,形成具有典型哲学反思意味的话语质疑、批判与重构。事实上,只有借助于哲学才能在更深层次上澄清大跃进以来的“胡乱思想”,[2]3—4如若缺乏必要的哲学反思,毛泽东既难以形成对享有国际权威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清理,[8]30更无法洞悉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以及建构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建设话语。就具体的话语建构实践和内容来说,主要体现为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基于矛盾运动论的话语建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则“对于人类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9]178如何形成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规律的“革命性”认识,进而成功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话语,毛泽东也是从矛盾分析出发的。首先是肯定“共有矛盾”,如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2]175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面临着“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的矛盾;[2]121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矛盾,进而得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也需要不断解决”的结论。[2]215—216其次是批判“不讲矛盾”,主要是(苏联)完成农业合作化后在农村“不讲人民内部矛盾”,[2]237建立国民经济体系过程中不讲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2]268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特点不讲“社会内部的矛盾”,[2]273肯定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没有矛盾,[2]319以及论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时不提平衡和不平衡矛盾。[2]416最后是分析矛盾问题,主要是纠正承认矛盾但否定矛盾是动力的观点,[2]339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2]273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2]340解决矛盾的方法之一是“批评和自我批评”,[2]359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等。[2]634可见,经由上述三个维度的矛盾分析,毛泽东实现了对于中苏两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推求比较,也实现了对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规律的批判、继承和超越,此举对于实现毛泽东建设话语的辩证建构意义重大。
二是基于部分质变论的话语建构。毛泽东在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时强调:“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变的变化都是飞跃”,并且“一切客观过程都如此”。[10]61由此,作为对辩证法根本法则的重要创新,部分质变理论既构成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工作方法,[11]353也成为毛泽东建构建设话语的重要指南。如在批判“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时,毛泽东依据“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质变是通过量变以及“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主观能动性在经由量变和部分质变进入最后质变过程具有重要作用等观点,[2]257从宏观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刻说明。具体包括: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作为一个质变过程,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等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组成公有制,决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将是一个“进一步变化的过程”;无论是建成社会主义还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既不存在“彻底巩固”的问题,也不可否定事物发展阶段的“边”,即都必须承认质变或部分质变。[2]258—259而在微观层面上,毛泽东认为即便是对机器设备新旧部件的更换,抑或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带来的量变,它们也均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农业体系发展中的部分质变。[2]310,568可以说,基于部分质变理论的辩证阐释,毛泽东得以从对立统一关系中发现社会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因,也才从理论与实践相互统一关系中求得建构建设话语的基本方法论遵循。
三是基于认识过程论的话语建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往往会遭遇经典作家的理论构想、苏联建设的权威经验以及本国建设的客观实际三者之间的冲突。这也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建构建设话语过程中的认识难题。基于此点,毛泽东在《批注和谈话》中积极谋求科学认识论与中苏两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结合,希望藉此分析路径来消解上述难题。首先,毛泽东从认识的客观性出发,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必然是无法一眼看透,因为世上没有天生的圣人,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先知先觉”,[2]382因此认识社会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更何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还不成熟。其次,毛泽东从认识的规律性出发,强调“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若不经过“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就希望“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先锋队也不例外”。[2]346最后,毛泽东从认识的可能性出发,强调“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是可以被认知的。正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我国土改政策均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2]153而苏联、中国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规律也证明了此点。其实,上述论述并非仅限于从一般层面阐释认识过程论,其本质是藉此提出二度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命题和哲学依据,而这两者正是毛泽东建构建设话语的内在诉求和方法依赖。
由上可见,毛泽东从矛盾运动、部分质变和认识过程等基本原理出发,将中苏两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殿堂加以审视。此举有助于从哲学高度“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也有利于从中国实际出发“改造”相关理论和实践,表征着毛泽东建设话语建构的核心诉求和路径依赖。但不容忽视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归纳的经验与规律,实际上存有主观化之嫌,而毛泽东的哲学反思也难去绝对化之嫌,两者兼而有之的片面性为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建构话语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这就为当前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提出了进一步实施哲学反思的历史任务。
三、以“政治”的批判为指向
厘定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列宁为此与托洛茨基、布哈林产生过激烈的论争,并认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12]407。然而,对于这一经典论述,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却出现了某种缺失,致使其“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2]66。由此不难想象,对于急切希望借助苏联经验教训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毛泽东而言,仅从教科书科学层面反思该缺失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建设话语重构维度加以消解。
其实,无论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2]407还是“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13]120列宁已就厘清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普遍性解释。而在《批注和谈话》中,毛泽东对于该问题同样做出了符合传统观点的阐释,并且还进行了切近中国建设实际的运用和发挥。若就其核心的“政治”旨趣而言,主要指向了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主要是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阶级)斗争以及需要不断深化的社会革命等问题。毋庸讳言,藉此而建构的毛泽东建设话语,除去具有“既定”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特质外,同时还具有独特的政治辩护性。具体说来,主要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基于上层建筑批判的话语建构。在《批注和谈话》中,作为在“一切社会关系”中与“政治”相对应的“上层建筑”,[2]79其内涵和外延在毛泽东的概念体系中是相对宽泛的,这主要是为了满足建设话语建构的多维需要。究其缘由,“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2]170。基于此点,毛泽东首先借助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判,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无助于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如供给制),更不利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2]66—68其次,毛泽东提出要学习诸如《东周列国志》等文本中有关上层建筑方面的斗争经验,[2]96发挥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借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消除落后和鼓励先进的斗争。[2]358最后,毛泽东将制度建设和社会管理也纳入上层建筑统摄的范围,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发挥主观能动性”,务必要坚持党组织挂帅。[2]400—401与此同时,对于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和物质刺激,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毛泽东批评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2]403,428,431经由上述认识积淀,毛泽东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无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进步,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既要靠技术又要靠政治(也包含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即技术与政治的统一。[2]442,448
二是基于现实政策维护的话语建构。掌握话语权是话语建构的核心旨趣,就其政治价值来看,它是构成现实政策阐释、维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在论及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初衷时,毛泽东直陈“是想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2]40因其既有助于肯定在我国生产资料部分是商品的观点,更有助于为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行权威性的辩护。不仅如此,在论及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其经济制度改造的条件时,毛泽东高度肯定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相关论述,并认为它可以直接为政治挂帅和大跃进提供“辩护”,因为前者印证了我国是如何“提高公民的觉悟程度”,而后者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积极尝试;[2]192在评价第三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首次纳入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既强调“立了案”就不好反对,又批评它未论及我国根据需要和可能而实施的工农业并举的方针。[2]248此外,相关的政治批评也构成毛泽东表达政治和维护政策的重要方式,其核心主要是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以至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无法明确“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2]69而即便是对于“讲政治”的劳动组织改造和社会主义竞赛问题,毛泽东也认为不如我国的土改和合作化政策,因其“政治太弱”而“只讲结果,不讲方法”。[2]461,462,467
三是基于社会革命深化的话语建构。推动建设话语的“革命”建构,在哲学层面抑或实践领域均具有重要价值。事实上,此种建构已经超越对于过往革命历史经验的继承,而是意在新的建设矛盾和发展目标下继续深化社会革命。诚如毛泽东在批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所言,斯大林“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但)不要不断革命”,所以未能从辩证法上看到共产主义运动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作用。[2]70那么,如何才能消解该问题呢?在《批注和谈话》中,毛泽东高度肯定“用革命手段”的“提法好”,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要求;[2]74在论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时,毛泽东强调不能不提镇压敌人和阶级改造问题,而且还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历经反复的斗争才能完成改造任务;[2]97在分析如何消解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时,毛泽东主张从经济、政治、思想三条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121—122在论及以革命手段解决矛盾时,毛泽东认为主要是化解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消除脑体差别、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等;[2]341在分析社会革命是否成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备条件时,毛泽东认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需要,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更替还需要借助社会革命。[2]711—712综上所述,毛泽东最后指出:“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必不可免。”[2]743—744
不难发现,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批判,既是寓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范畴的批判,[2]3同时又极大程度上超越了该范畴而追求着“政治和哲学的实现”。它既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出发,又以现实政策的维护和社会革命的深化为旨趣,兼具革命性与科学性的话语特质。然而,基于复杂条件下的政治批判以及话语建构,在实现其政治辩护功能之余,其中的泛政治化或过度政治化则难以完全规避,由此构成为毛泽东建设话语再度反思,以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过程中亟待消解的问题。
借助于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阅读、批注和谈话,遵循着从历史叙述出发、以哲学反思为据、做政治导向批判的逻辑,毛泽东在1958年至1960年间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重要探索,并藉此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话语。这一话语建构逻辑,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的要求,彰显了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层次。尽管话语建构本身存有一定程度的绝对化、片面化甚至过度政治化的嫌疑,但它确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而形成的阶段性社会主义建设话语建构成果。就其价值而言,它不但兼具历史的和理论的双重意义,而且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尤其是对于当前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而言,其镜鉴、反思和启迪价值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1998.
[3]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朱光潜.克罗齐的历史学[A].蒋大椿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C].沈阳: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 刘洁.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7.
[9]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