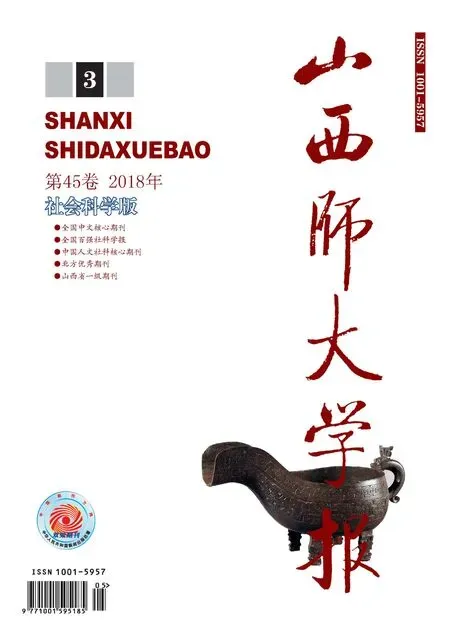英国诗人弥尔顿与《钦定本圣经》
2018-05-07陈桂花王任傅
陈桂花,王任傅
(1.黄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2.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众所周知,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对于《圣经》的知识与他的古典知识一样丰富而全面。弥尔顿研究专家罗森布拉特(Jason P. Rosenblatt)指出:“英国的伟大诗人中,弥尔顿是最博学、最以《圣经》为中心的。”[1]181剑桥大学的科密肯(L.A. Cormican)教授也曾评论说:“弥尔顿与《圣经》的情况如此类似,以致于只有凭借提升宗教精神和拓展宗教经验我们才能够领悟伟大的《诗篇》22(Psalms 22)、《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或是《失乐园》(Paradise Lost)复杂的内涵,才能够清楚地理解那些先前因缺乏宗教敏感而倍感隐晦的东西。……没有宗教经验而阅读弥尔顿最后的三大史诗,就如同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孩子阅读《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一样,只能体会到一些肤浅的意义。”[2]185
的确,纵观弥尔顿的作品,无论是现存最早的、他于15岁时对《钦定本圣经》(the Authorized Version of the Bible)中两首诗歌的改写,还是他丰富的政论散文,乃至他到晚年时创作的、源于圣经题材的三大史诗,弥尔顿都是极具圣经思想和圣经特点的英国作家。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弥尔顿与《圣经》的密切关系已经给予了热情而持久的关注,但是人们仍然感到困惑的是,在弥尔顿所熟悉和掌握的多个版本《圣经》中,有没有哪一版本为其所偏爱?弥尔顿又是如何使用《圣经》以服务其写作目的?对《圣经》的援用赋予了弥尔顿作品怎样的艺术效果?
一、弥尔顿与《钦定本圣经》的不解之缘
作为17世纪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清教诗人和思想家,弥尔顿生活在英国清教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当时的英国,基督教掌控着社会各个领域的绝对话语权,无论是人们的政治诉求还是对道德伦理的要求,都必须首先在宗教上找到它们的神圣合法性,而“所有事物的神圣合法性都必须来源于《圣经》,更确切地说是来源于对《圣经》的阐释”[3]170,因为人们深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4]127。在文学艺术领域,西方作家也大都是在基督教文化的熏染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价值观念乃至文学创作的内容处处都渗透着基督教或《圣经》的影响。对于英国的很多作家来说,《钦定本圣经》就是他们的启蒙读物,是其接触最早并伴随一生的文学教科书。尽管当时的英国人未必对《圣经》抱有明确的文学意识,但《钦定本圣经》在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早已融进了他们的血液。弥尔顿无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弥尔顿被视为“欧洲17世纪进步文化的基石”和“宗教改革的改革者”[5]译本序,他的一生都与《钦定本圣经》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考证,大约4岁的时候,弥尔顿就已经拥有了一部《钦定本圣经》[6]176*据传与弥尔顿有关的英语《圣经》约有7本;但经巴克斯特(Wynn E. Baxter)考证,目前唯一一本确定为弥尔顿所拥有的英文版《圣经》是1612年罗伯特·巴克(Robert Barker)出版的《钦定本圣经》。另有一本《日内瓦圣经》(Genevan Version, London, 1588, 4to.)虽貌似与弥尔顿关系密切,但实为弥尔顿第三任妻子伊丽莎白·明舒尔(Elizabeth Minshull)所有。这本《圣经》中弥尔顿的签名则是有人在他完全失明后从其他文件上剪切下来,黏贴上去的。关于巴克斯特的考证,参见:Harris Francis Fletcher. The Use of the Bible in Milton’s Prose. New York: Haskell House Publishers Ltd., 1970: 21-22.,并且颇为迷恋。那本现藏于英国国家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1612年版小开本《钦定本圣经》中,有弥尔顿亲笔所做的7条记录和多处旁注,其中还有许多标记显示出弥尔顿阅读时的兴趣所在。例如,他在《历代志下》(II Chronicles)14: 11,16: 8 &12和《诗篇》2: 12等这些诗行下面划线以作强调;在《以斯拉记》(Ezra)10: 13和《尼希米记》(Nehemiah)13: 13等诗行边上作旁注以提醒注意。[7]559—561一位弥尔顿的传记作者说,弥尔顿总是以阅读《圣经》开始他的每一天,并将经文中的词句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记忆里。[8]143在15岁时,弥尔顿就曾将《诗篇》里的两首诗歌(第64和86篇)改写成韵文,他所使用的版本就是《钦定本圣经》。弥尔顿早期的世俗诗歌,在其措辞和表达中也显露出了他少年时期学习《圣经》的深刻影响。例如,著名的悼亡诗《黎希达斯》(Lycidas)就包含了常被人们引用的圣经典故彼得(Peter)和他的两把钥匙:“最后来,而最后去的,/ 是加利利湖上的舟子;/ 他带着两把不同的金属大钥匙 / (金的管开,铁的管闭,十分结实)。”[8]142—143*译文出自弥尔顿《复乐园·斗士参孙》(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加利利湖上的舟子指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因为他追随耶稣之前原本是加利利的渔夫。传说他有两把钥匙,掌管着天堂的门,是基督教第一任主教。
有研究者指出,在弥尔顿所熟悉的众多圣经版本中,他把希伯来语《圣经》视为《旧约》(the Old Testament)唯一的权威文本,把希腊语《圣经》视为《新约》(the New Testament)唯一的权威文本;在他看来,《钦定本圣经》则是最好的英文译本[9]90。当代著名圣经文学研究专家谢大卫(David Lyle Jeffrey)在《日常乐章:英王詹姆斯钦定版圣经与英语文学》(“Habitual Music: The King James Bible and English Literature”)一文中详细评论道,约翰·弥尔顿“足可称为参考过众多圣经版本的专家,不仅有英文版,还有最初的拉丁文版、希腊文版和希伯来文版”,“但是,一如威廉·帕克(William Riley Parker)在谈到弥尔顿受钦定版圣经影响时所论,‘它的遣词造句、它的意象、它的韵律,早已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熟悉弥尔顿散文或诗歌的人不难发现钦定版圣经在这个伟大清教徒作家身上的分量:不仅表现在神学方面,也影响到他的文学模式”[10]52。
诚然,弥尔顿大部分的作品都与《钦定本圣经》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著名作家梅尔文·布拉格(Melvyn Bragg)评论说,弥尔顿的主要作品是以《钦定本圣经》为基础的。[11]147我国著名弥尔顿诗歌翻译家朱维之教授也曾说,“论到弥尔顿的语言,虽然丰富而生动,但也有他的缺点,就是大量地运用《圣经》的语言,把他进步的思想、感情都蒙上宗教的外衣。”[12]XXII综观弥尔顿全部的英文作品,不仅他在散文之中对于《圣经》的引用绝大多数来自于《钦定本圣经》[13],伟大史诗《失乐园》所涉及《圣经》之处使用的往往也是《钦定本圣经》的语言[1]12。还有研究者发现,在弥尔顿所有英语作品中,仅有的两处出自《圣经·次经》(Apocrypha)的引文,均与《钦定本圣经》的内容完全吻合。[14]223—224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在英国曾有多种版本的《圣经》流传于世,但从文化影响力的角度而言,《钦定本圣经》在英国社会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该译本于1611年正式刊行,自17世纪中期以降直到20世纪初,曾长时间地发挥了文化主导和宗教权威的作用。从1660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王政复辟时期开始,《钦定本圣经》就真正地成为了英国教会的指定读本[15], 并且“控制了接下来250年的英语《圣经》市场”[1]8。事实上,《钦定本圣经》就是英国人专指的《圣经》。关于这部《圣经》对于英语民族的巨大作用,王佐良先生曾言,“经过在教堂内外不断的诵读,‘钦定本’的内容连同它的文字和节奏早已深入英国人的灵魂”,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部书,而且早已成为英国民族生活的有机部分。[16]259甚至直到20世纪初,该译本一直发挥着教科书的作用,它“是每个人的教育的组成部分,不论他是一般老百姓也好,以至哲学家、革命家”[17]19。正是由于《钦定本圣经》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和英国民众对其熟悉的程度,该译本赋予了弥尔顿作品以其他圣经版本,甚至原文《圣经》都难以比拟的艺术效果。
二、《钦定本圣经》指涉之于弥尔顿散文的艺术效果
美国著名学者、弥尔顿研究专家弗莱彻(Harris F. Fletcher)教授曾经深入地考察了弥尔顿散文与《圣经》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弥尔顿英语散文作品中全部的实际引用,凡是可以辨认出英文《圣经》出处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来自于《钦定本圣经》;并且,如果引文对比参照的是弥尔顿当时所使用的那个《钦定本圣经》版本,那么两者的一致性则更为明显。[9]20弗莱彻教授还以1651年为界,通过具体的数据统计展示了弥尔顿失明前后在英语散文中引用《圣经》的变化情况(见表1)。

表1 弥尔顿失明前后圣经引用之对比
从这份表格中可以看出,失明前在弥尔顿全部的经文引用中,与《钦定本圣经》内容一致的有136处,占引文总数的47.7%。而失明之后,在其全部的124处经文引用中有103处与该译本一致,引用比例高达83%。[9]93—94因此,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7世纪英国史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也说,弥尔顿“是在《圣经》的哺育下长大的;……在早期的诗歌中弥尔顿常常提到《圣经》,在他辩论性的短文当中参引之处则更为频繁”[18]373。
正如前文所述,《圣经》在17世纪的英国社会生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视其为“上帝的话语”,把它作为社会各个领域话语权最神圣的依据。所以,在政论性散文中弥尔顿频繁引用《钦定本圣经》一个突出的艺术效果就是,圣经引文赋予了其观点很高的可信度与权威性,从而大大提升了其政论散文的说服力。弥尔顿对《圣经》内容的使用和援引方法灵活而多样,他最明显的独特做法是,“列举出经文段落所在的书卷、章节或者具体的诗歌,但不实际引用所列举的经文内容”,他这样做的目的通常是“用以支持他自己的观点,或者指明他所讨论的观点所在《圣经》中的位置”[9]14—15。当然,出于同样的目的,弥尔顿时常也会清楚地引用《圣经》中具体的语句,而在这种情况下,其英语引文大多出自《钦定本圣经》。这里,以《建设自由共和国的简易办法》(The Ready and Easy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为例试做分析。
在查理二世复辟前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危机四伏的时刻,弥尔顿撰写了《建设自由共和国的简易办法》这篇政论性散文,向当时控制军权的蒙克(George Monck)将军提出他对改革议会的具体意见,以期阻挡王室贵族复辟的逆流,保住来之不易的共和国政体。在这篇文章中,弥尔顿为了表明和支持自己的观点,指涉和引用《圣经》的内容不下十几处。正文伊始,针对英国残缺议会议员不足且议员可能存在个人操守方面的瑕疵的情况,弥尔顿向蒙克将军大胆提出,“当议会在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时,人民当中那些最有主张、最讲原则的人绝不考虑议会里哪一方人数最多,而是考虑哪一方理由最充分,办法最妥当”;他特别强调,“遇到好的提议或意见时”不必太在乎“表决者的动机”,因为“动机只是一种猜测,或者一时弄不清楚的东西;况且即使动机纯良,这既不能保证行动就是好的,也不能防止坏的结果”。[14]425为了说明这一点,弥尔顿引用《圣经》中关于西门(Simon)和扫罗(Saul)的例子加以佐证,他说,“假使怀有不良的动机却为了善事,那么这善果毕竟是这些居心不良之人做出的,而不是政府里的少数派使然”,这就如同“在教会里,谁不宁愿追随宣传福音的加略人(Iscariot)或西门——尽管他们是出于贪婪的目的,而愿意去追随心地正直却迫害福音教会(the Gospel)的扫罗呢?”[14]425因此,弥尔顿总结说,“按照他们自己的判断来选择更好的建议,纵然是一些心存不良的人提出,这也要比动机高尚的人提出的坏建议更为稳妥。”[14]425
同样在这篇政论散文中,为了反对君主复辟、维护自由共和国,弥尔顿再次反复援引《圣经》的内容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首先,他指出,“上帝为以色列人立王的时候,心里很不痛快,认为他们的要求是一种罪。”[14]428弥尔顿是以《撒母耳记上》(1 Samuel)第八章所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警示英国人,因为人类各族的历史均已表明,人们立王的结果最终必然使自己沦为被奴役的对象。当以色列人请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的时候,上帝就要求撒母耳当严厉地“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19]264—265于是撒母耳告诫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19]265验之以英国人自己的历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撒母耳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那么,从英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现状来看,重新考虑复辟过去的那种君主制度,就无异于是历史的倒退。
除了从历史的经验出发,弥尔顿接着又明明白白地引述《钦定本圣经》的原话,从宗教信仰的权威告诫人们,上帝是从来都不支持人们拥立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王”的。弥尔顿写道:“基督明确禁止他的门徒承认任何这样的异教政府。他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14]428*引文中《圣经》的内容译文出自(和合本)圣经5新约[M]. 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98.弥尔顿这里引用《钦定本圣经》的话语,已经明确地表明上帝对于拥立君王的态度了——“你们不可这样”!很显然,在基督的王国里,没有凌驾于同胞之上的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因此,弥尔顿坚决反对君主,反对独夫。他认为人民需要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政府来维护全体的利益。在这样的国家里,“最大的人物永远是大众的仆人和苦工,他们花自己的钱,耽误个人的事情,却并不高人一等;他们在家里生活俭朴,走在街上也形同常人,谁都可以与之随意而友好地交谈,无需加以崇拜。试问还有哪一种政府比自由共和国更接近基督的规训呢?”[14]428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弥尔顿频繁地在其政论性散文中援引《钦定本圣经》的内容和话语;他的引用也总是有的放矢、入木三分。弥尔顿总能在行文的关键之处十分灵活而自然地引用经文,从而有力地支持自己所阐发的观点,维护人民民主与自由的权利。他的散文是英国进步资产阶级锐利的战斗武器。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最具权威的声音即是上帝的语言,因为几乎任何事情,“如果不能证明它出自受神启示的《圣经》,而只是由人这样断定的,那末不论说过多少遍,这样的说法仍然是毫无权威可言的。”[20]84弥尔顿在其散文中恰恰采用了这一策略,从而大大提升了观点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在实际效果上增强了政论散文的战斗力。
三、《钦定本圣经》指涉之于弥尔顿诗歌的艺术效果
著名弥尔顿研究专家詹姆斯·汉福德(James Holly Hanford)认为,弥尔顿的诗歌“依然光彩夺目,但是在一个缺少古典知识与圣经背景的时代,人们很难立刻、全面地领略到阅读这些诗歌所带来的愉悦”[21]xxx。汉福德的话语清楚地点明了弥尔顿诗歌的两大显著特征:一方面,弥尔顿的思想深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葛学派等古典学者的影响[22],他又潜心学习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著作,因此,在诗歌创作方法上“可说是真正的古典主义方法”[5]15;另一方面,弥尔顿的诗歌与《圣经》有着密切的联系,毫不夸张地说,“弥尔顿的史诗通篇都透着《圣经》的气息”[23]1。我国著名学者朱维之也说,弥尔顿“既继承了希腊、罗马的古代传统,又发扬了希伯来、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他的“古典文学知识和《圣经》文学知识都很丰富,常把希腊罗马的神话与《圣经》的传说交织在一起,结合在一起”[5]5,16。詹姆斯·西姆斯(James H. Sims)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弥尔顿的史诗“在形式上是古典的,而在内容上则是《圣经》的”[23]1。
弥尔顿的诗歌与《钦定本圣经》的密切联系首先表现在,他最著名的三大史诗均选取了圣经题材。三部作品尽管是弥尔顿有感于英国当时的革命形势而作,但它们包含的圣经主题更多于英国历史的内容。正如两位弥尔顿研究专家约翰·拉姆里奇(John Rumrich)和芭芭拉·勒瓦尔斯基(Barbara Lewalski)所言:“《失乐园》从根本上说是一部文学作品,所以作品的语境首先应该是西方文学的圣经文学和欧洲史诗传统。”[24]61我国学者王晓秦也曾经指出,“弥尔顿既是一个革命家,也是一个严肃的信徒,要想较全面地评价这部作品(《失乐园》),既要看到它的革命性,又不能抹煞它的宗教性。”[25]美国神学家、圣诗作家克莱兰·麦卡菲(Cleland Boyd McAfee)则将弥尔顿的头脑生动地比作一个花园,“在那里《圣经》的种子开花、结果”;他还说,弥尔顿的“三大诗歌,按其重要性排列,当然就是《失乐园》《斗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和《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了。凡了解弥尔顿的人都知道这三首史诗,并且知道它们的措辞、典故,还有至少部分思想观念从头到尾都是从《圣经》而来的。”[8]145事实上,弥尔顿的史诗与《圣经》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过去许多主要熟悉圣经文学的读者,习惯上把《失乐园》仅仅当作圣诗来阅读”,“逐渐地,弥尔顿的描述几乎被视为权威经文,他关于驱逐撒旦、上帝造人以及伊甸园中始祖遭受诱惑而堕落的故事已经成为英国人思想观念的一部分。”[26]110
弥尔顿的三大史诗选取圣经故事作为它们的题材,无疑赋予了其作品崇高与庄重的特性。文学作品采用宗教题材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提升作品的主题思想,使作品的内容摆脱偏狭而具有了社会或人性的普遍意义。“在弥尔顿看来,神话、传说、历史,都一样表现时代的精神,英国17世纪时代的革命精神和历史上一切变革时代都有相通之点。撒旦和亚当的失乐园,都是人间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严峻时代的反映,诗人生活的英国历史正是这样的时代。”[5]11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也说,“诗人应当表现的不是特殊的和偶然的东西,而是给他的整个时代添上色彩和意义的共同的和必要的东西”,“弥尔顿的诗歌明显地是他的时代的产物”[27]696—697,因此,“即使作者不是有意在作品中描写一六四八年的革命,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5]11
当然,宗教题材的崇高与庄重感从根本上说是和人们浓厚的宗教信仰分不开的。在英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基督教传统的国家,人们的宗教意识尤其强烈。在他们的心目中,上帝是人与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不容置疑地占据了内心最崇高的地位。这样的社会语境中,一切关于上帝的话题也都笼罩了严肃、权威和崇高的色彩。以《失乐园》为例,这部史诗取材于《圣经·旧约》创世纪的内容,虽然讲述的是撒旦(Satan)与亚当(Adam)分别失去天上和人间乐园的故事,但开篇伊始弥尔顿即表明创作的主旨是“阐明永恒的天理,证明上帝之道对人的公正”[28]44。敢问在一个基督教文化世界还有什么话题比这更有意义、更为高尚呢?诗人自己也说,相比于其他题目,歌颂上帝的主题显然“更为崇高”。在《失乐园》的第九卷弥尔顿称,“自从我最初喜爱这个主题的/英雄史诗时候起,曾用很长的/时间去选择题材,迟迟才开始写作。/英雄史诗的唯一课题似乎是/描写战争,……精雕细琢的技巧,死板的方法,/陈规旧套,并没有给人和诗篇/带来英雄的光彩。何况我连这些/技巧都没有掌握,也没有研究,/留给我的是更崇高的内容,/其本身就足以高扬其名。”[5]295—296可见,选取“更崇高的内容”以驰骋诗才、抒发情志,乃是弥尔顿有意为之。其实,在着手创作《失乐园》之前,诗人原本打算写一首关于“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民族史诗,但考虑到亚瑟王的故事缺少一首史诗所该具备的历史基础,便放弃了这一计划。于是,为了使自己的母语生辉,也为了“凭祖国的名誉和号召提升上帝的荣耀”,弥尔顿重新考虑创作一部“于国更有教义性和典范性的”作品,并最终决定以史诗的形式来讲述“人类的堕落及其所引发的后果”[29]xv—xvi。
从宗教意义上来理解《失乐园》的崇高品质,它还体现在,弥尔顿在对“我们灾难”的叙述中自始至终传达出了一种希望,并以此彰显上帝的慈爱与伟大。史诗一开始就指出,虽然人类因违反上帝的命令而失去乐园,但终将有一位“更伟大的人”来把我们救出灾难——“关于人类最初违犯天神的命令,偷吃/那棵禁树上的果子,将死亡和一切/灾难带到人间,并失去伊甸乐园,/直到一个更伟大的人来/为我们恢复乐土的事,请歌咏吧,/天庭的诗神缪斯!”[28]43而诗歌的结尾一句同样明确地表明上帝始终不会将人类离弃,在他们的苦难历程中总有“神意做他们的指导”——“他们滴下自然的眼泪,但很快就擦干了;/世界整个展现在他们面前,供其选择/安身的地方,并有神意做他们的指导:/二人手拉着手,缓缓移动漫游的脚步/告别了伊甸,踏上他们孤寂的路途。”[28]279除此之外,史诗在叙述过程中也多次描写上帝对人的宽宥与仁慈,并突出了神子基督甘愿牺牲自己,矢志“去救赎人的死罪,用正义救不义”。史诗结构上的这些安排,都从宗教意义上彰显了一种崇高的题旨:诗歌是献给上帝的,它要“证明上帝之道对人的公正”,从而“提升上帝的荣耀”。
除了选择圣经故事作为史诗的题材之外,弥尔顿还在诗歌的描写中频繁暗指《圣经》或引用《钦定本圣经》的语句。詹姆斯·西姆斯曾细致地研究了诸多弥尔顿作品编辑与评注者的记录,从中他发现,弥尔顿在《失乐园》和《复乐园》这两部史诗中对《圣经》的指涉与引用多达1364处;除此之外,西姆斯本人又新发现了816处。[23]368—388例如,《失乐园》开篇宣示长诗创作主旨的13个诗行中,弥尔顿指涉《钦定本圣经》的地方不下15处,所涉内容涵盖了从《旧约·创世纪》(Genesis)到《新约·罗马书》(Romans)等多个不同的篇章。诗文不仅指涉了圣经地点,如伊甸园(Eden)、何烈山(Oreb)、西奈山(Sinai)、郇山/锡安山(Sion)和西罗亚(Siloa);圣经人物,如牧羊人(that Shepherd)、选民(the chosen seed)和更伟大的人(greater Man);还暗指了《圣经》中的一些重要教义,如人类始祖因违反上帝的命令而堕落、亚当和夏娃因不服从上帝而导致的结果——死亡,以及基督的救赎等[23]12,368。从语言艺术层面看,对《钦定本圣经》内容和语句的援引,一个明显的效果就是增强了弥尔顿作品语言表达的真实感与严肃性。
尽管出于诗歌语言表达的特点与需要,弥尔顿在诗歌作品中对《钦定本圣经》的暗指(allusion)较多,然而凡在可能之处他也常常直接引用该译本的语句,以达到触动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以《失乐园》第七卷弥尔顿描述上帝创世第一天的情景为例:
Let there be Light, said God, and forthwith Light
Ethereal, first of things, quintessence pure,
Sprung from the Deep, and from her native East
To journey through the aery gloom began,
Sphered in a radiant Cloud—for yet the Sun
Was not; she in a cloudy Tabernacle
Sojourned the while. God saw the Light was good;
And light from darkness by the Hemisphere
Divided: Light the Day, and Darkness Night
He named. Thus was the first Day even and morn.
(Paradise Lost VII, 243—252)[28]169
不难看出,弥尔顿的行文之中多处引用了《钦定本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中的词句和表达,如Let there be light、God saw the Light was good、divided,以及因诗歌效果需要而颠倒了语序的Light the Day, and Darkness Night / He named.和Thus was the first Day even and morn.等。通过和《钦定本圣经》原文的对比,人们一方面可以领略弥尔顿“会将《圣经》中的一个短语演绎成《失乐园》中的一页文字”[8]145的娴熟技巧,另一方面,对于《钦定本圣经》原文话语的直接引用赋予了史诗强烈的真实感,让人读起来仿佛他是在复述上帝的话语。而且,这段描写的语气,在很多地方也与《钦定本圣经》相应的段落十分相似。试比较: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And God saw the light, that it was good: and God divide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
And God called the light Day, and the darkness he called Night. 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first day.
(Genesis 1: 3—5)[30]1
可见,两份作品描写的语气都是严肃而庄重的,突出了上帝权威和万能的形象。弥尔顿对《钦定本圣经》语气和表达的模仿也使这部分的描写极具真实感,对于深信《圣经》的读者来说,让人感觉弥尔顿的叙述同样不容置疑。以《圣经》在英国社会的核心地位,这些源自《钦定本圣经》的话语无疑赋予了弥尔顿诗歌语言一种严肃的权威性。不可否认,“艺术真实”乃是文学作品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因素。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中就曾提出,“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31]86在一个具有浓厚基督教信仰的国度里,《钦定本圣经》的话语显著提升了弥尔顿史诗的艺术真实和感染力,以致在英国人那里弥尔顿史诗中的描述几乎被当成权威经文,最终逐渐地融入了英国人思想的深处。
综上可以看出,虽然弥尔顿精通古典语言,崇尚原文《圣经》的权威性,但是他的创作与《钦定本圣经》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其政论性散文中,弥尔顿频繁引用和指涉《钦定本圣经》的内容,以提升他观点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在其诗歌创作中,弥尔顿从《圣经》当中找到了他最合适的主题,以赋予作品庄重与崇高的品质;同时,他在诗歌中对《钦定本圣经》语句的直接引用还大大增强了其作品的艺术真实。事实上,不仅弥尔顿本人从《钦定本圣经》中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文学素材,他在创作中运用《钦定本圣经》的方式也为后世作家树立了榜样。在英国,就《圣经》中的某个故事、人物、意象或思想主题展开推衍与叙述,成了诗人与作家文学创作惯常使用的手段;显然这也是《钦定本圣经》发挥其文学影响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约翰逊(R. F. Johnson)在为《世界图书百科全书》所写的《圣经》条目中称,“数以千计的艺术作品建立在圣经人物和圣经故事的基础之上”[32]280,似乎一点儿也不夸张。大卫·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教授在演讲中也曾谈到,“随着教会在17世纪上半叶逐渐用新译本取代了《主教圣经》(the Bishops’ Bible)和《日内瓦圣经》(the Geneva Bible),明显地作家们开始将《钦定本圣经》用作灵感的源泉。弥尔顿即是这样的早期作家之一,他的许多诗行展露出了这一鲜明的影响。弥尔顿有时还精准援用《钦定本圣经》的措辞,如‘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She gave me of the tree, and I did eat.——Paradise Lost, Book X)。毋庸置疑,《圣经》的内容对于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的想象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3]的确,“弥尔顿的作品表现出了《圣经》多么具有启发性,以及人们对其阅读理解的深度。”[11]148他在本质上是一位模仿古典的诗人,又选择《圣经》作为他的资料库。他的作品证明了《圣经》所能赋予伟大诗人的文学潜能。弥尔顿的作品深受《钦定本圣经》的浸润,对于后世的文学和宗教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175—176一言以蔽之,约翰5弥尔顿与《钦定本圣经》的深刻关系堪为宗教与文学互动之典范。
参考文献:
[1] Hannibal Hamlin, Norman W Jones, (eds.). The King James Bible after 400 Years: Literary,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Boris Ford, (ed.). The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Donne to Marvell.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0.
[3] 李勇.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三条释经路径及其社会意义[J].基督宗教研究,2014,(2).
[4] T Harwood Pattiso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ible. Philadelphia: American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894.
[5] (英)约翰5弥尔顿.失乐园[M].朱维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 David Norton.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ible as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Frank Allan Patterson. “Notes on Milton's Bibles”. The Works of John Milton (Vol. XVI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8.
[8] Cleland Boyd McAfee. The Greatest English Classic: a Study of the 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 and Its Influence on Life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12.
[9] Harris Francis Fletcher. The Use of the Bible in Milton's Prose. New York: Haskell House Publishers Ltd., 1970.
[10] (美)谢大卫.日常乐章:英王詹姆斯钦定版圣经与英语文学[J].圣经文学研究,2007,(第一辑)..
[11] Melvyn Bragg. The Book of Books: the Radical Impact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1611—2011. Berkeley: Counter Point, 2011.
[12] (英)弥尔顿.复乐园5斗士参孙[M].朱维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3] Israel Baroway. “Review of the Use of the Bible in Milton's Prose”. Modern Language Notes, Vol. 46, No. 8 (Dec., 1931).
[14] John Milton. “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Divorce”. English Prose Writings of John Milton. Henry Morley, (ed.).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89.
[15] 王任傅.作为文学的《钦定本圣经》接受史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
[16] 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17]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8] Christopher Hill. The English Bible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3.
[19] (和合本)圣经5旧约[M]. 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
[20] (英)马克5帕蒂森.弥尔顿传略[M].金发燊,颜俊华译.北京:生活5读书5新知三联书店,1992.
[21] John Milton. The Poems of John Milton. James Holly Hanford, (ed.).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36.
[22] 崔梦田.论《失乐园》中亚当的正当理性与选择[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23] James H Sims. The Use of the Bible in Milton’s Epic Poem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59.
[24] 申丹,王邦维总主编;章燕,赵桂莲主编.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第1卷5上)——外国诗歌与戏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5] 王晓秦.《失乐园》创作思想试析[J].外国文学研究,1983,(2).
[26] Elbert NS. Thompson. Essays on Milt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4.
[27]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M].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8] John Milton.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Milton.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20.
[29]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Barbara K. Lewalski, (ed.).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30]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Translated out of the Original Tongues and with the Former Translations Diligently Compared and Revised, Commonly Known as the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Nashville: 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 1978.
[3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2] RF Johnson. “Bible”. 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B. Vol. 2. Chicago, London, Sidney, Toronto: World Book, Inc., 1994.
[33] David Crystal. The Influence of the Bible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2011 London Newman Lecture Given at the St. Alban's Centre, Holborn, London (10. 3.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