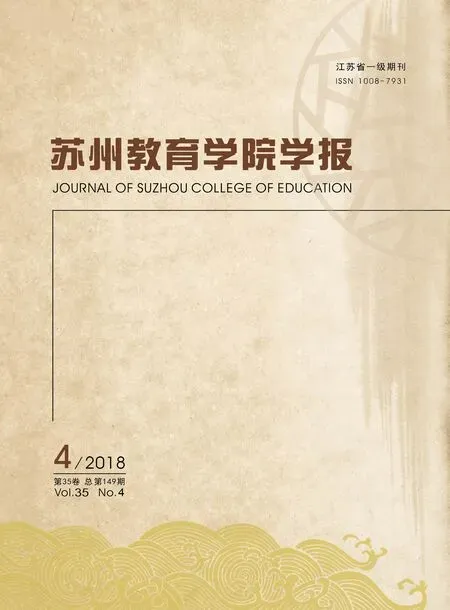陶渊明两次居丧与仕途之关系
2018-04-04李治中
李治中
(周口师范学院 老子暨中原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周口 466001)
陶渊明分别在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和义熙元年(405)居丧,其母孟氏和其妹程氏先后亡故,陶渊明分别是三十七岁和四十一岁。考察魏晋南北朝政界人才成长反映在年龄上的特点,“三十二岁至四十三岁,即建立主要功业的最低年龄段到最高年龄段,为政治上的最佳年龄期”[1]。按照当时的丧服制度,陶渊明在此期间两次居忧,时间合计三年有余,对其仕途影响不言自明。陶渊明丧服前后的东晋时局,正值风云际会、瞬息万变,因政治斗争有褒贬,人物品评亦有贬抑,按照礼制或习俗,陶渊明离职居忧对其仕途,还有人物品评,乃至人生观,均有较大影响。
一、孟氏母卒及陶渊明居丧前后
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记云:“先生以(隆安五年辛丑)七月还江陵,而祭妹文有‘萧萧冬月’之语,则居忧在是岁之冬。”[2]15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从其说云:“先生以辛丑冬月居忧,甲辰服阕,次年乙巳(405)三月,有为建威参军使都诗。”[2]78后学多从之。吴仁杰所依据,是陶渊明义熙三年(407)所作《祭程氏妹文》,其中有“昔在江陵,重罹天罚”[3]191,又有“黯黯高云,萧萧冬月”[3]191,所指为其母孟氏亡故。《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云:“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3]171《诗经·邶风·凯风》有“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4]46,又有“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4]46。陶渊明《孟府君传》表达了其对亡母的思念之情。
陶渊明母亲孟氏亡故,其须离职返还寻阳丁忧。陶渊明父亲早丧,其《祭从弟敬远文》云:“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齿,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3]194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云:“此言己与敬远皆在八岁时丧父,命运既相同,故特别亲爱。”[5]282陶渊明父亲先已去世,按魏晋遵循的丧服制度,《仪礼·丧服》称“父卒则为母,继母如母”[6]564,其当为母亲服“齐衰”,丧期三年,实际是二十五个月,即“三年之丧,十三月而练,二十五月而毕,《礼》之明文也”[7]617,遵照《仪礼·丧服》,其丧服是“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6]563。《礼记·三年问》称:“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8]1559《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265)十二月诏曰:“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7]53以法令的形式把三年居丧规定下来。遵照此制,陶渊明丁忧,必须离职返乡。其曾祖陶侃也曾如此丁忧,“陈敏之乱,(刘)弘以(陶)侃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侃备威仪,迎母官舍,乡里荣之。”[7]1769“后以母忧去职。尝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化为双鹤,冲天而去,时人异之。”[7]1769“服阕,参东海王越军事。”[7]1769单就陶渊明寻阳丁忧的时间而言,如果其母亲孟氏隆安五年(401)孟冬十月去世,则甲辰(403)仲春二月服阕,元兴三年(404)二月当是陶渊明服阕最早的月份,最晚则延至四月。由此推定,元兴三年二月以前陶渊明肯定丁忧在家。
梳理陶渊明寻阳丁忧之前的诗歌,有明确纪年且时间最为接近的是《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这个时间,陶渊明应参镇北将军刘牢之军幕,而不是刘裕或者桓玄。如宋人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云:“先生为镇军非从刘裕,已具去岁谱中。至仕于江陵(桓玄),则又有不然者。”[2]14清人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云:“景文、吴斗南谓先生以庚子(400)作参军,则任于牢之者二年。要之参牢之军,固有年可纪也。”[2]77持有他议的,多对《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理解有别,清人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辨正云:“集韵:‘假,休沐也。’应劭汉官仪:‘五日一假,休沐。’晋书王尼传:‘护军与尼长假。’岂得反以假还为趋职?意必以事使江陵,路出寻阳,事毕,便道请假归视,其辞简,犹曰‘赴假还自江陵’云尔。”[2]78涂口,在今湖北安陆县,介于上游江陵与下游寻阳之间,这首诗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3]74陶渊明经寻阳家中赴江陵甚明,又有“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3]75,可见陶渊明官差在身且事出紧急。因其“怀役”,所以他去寻阳为私为假,去江陵为公为还,以建康为出发地,江陵为陶渊明出使目的地。陶渊明为什么要去江陵呢?就在辛丑(401)岁六月,孙恩起义如火如荼,逼近京都建康,“六月甲戌,孙恩至丹徒。乙亥,内外戒严,百官入居于省。冠军将军高素、右卫将军张崇之守石头,辅国将军刘袭栅断淮口,丹阳尹司马恢之戍南岸,冠军将军桓谦、辅国将军司马允之、游击将军毛邃备白石,左卫将军王嘏、领军将军孔安国屯中皇堂。征豫州刺史、谯王尚之卫京师。宁朔将军高雅之击孙恩于广陵之郁洲,为贼所执。”[7]254与此相应,此时桓玄已经都督“八州及扬豫八郡,复领江州刺史”,“于是树用腹心,兵马日盛,屡上疏求讨孙恩,诏辄不许。其后恩逼京都,玄建牙聚众,外托勤王,实欲观衅而进,复上疏请讨之”。[7]2589辛丑岁(401)七月,时值建康有难,作为被晋廷倚重的北府兵集团和西府兵集团,尽管之间相互提防有加,但必须互通消息以防不测,在这个意义上,身为参军的陶渊明为刘牢之所驱使,前往谒见荆州桓玄就在情理之中。值得一提的是,从陶渊明世居寻阳,以及其亲族与桓玄家族的较好关系,代表北府兵谒见桓玄,陶渊明恐怕是刘牢之军幕中最好的人选。
这一年接下来的时局,如《宋书·武帝上》所载:“(孙恩)寻知刘牢之已还,朝廷有备,遂走向郁洲。八月,以高祖(刘裕)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领水军追恩至郁洲,复大破恩,恩南走。十一月,高祖追恩于沪渎,及海盐,又破之。三战,并大获,俘馘以万数。恩自是饥馑疾疫,死者太半,自浃口奔临海。”[9]3这年冬,时值北府兵用人之际,陶渊明离职返寻阳丁忧,与其相对应,同为刘牢之参军的刘裕在镇压孙恩的战斗中脱颖而出,并且屡建军功。陶渊明此时丁忧,对于深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而志在报效晋廷建立功业的他而言,不能说不是一种打击。事实上,陶渊明此时丁忧,其影响并不局限于此。由于桓玄居江之上游,“自谓三分有二,知势运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7]2590元兴元年(402)“春,正月,庚午朔,下诏罪状桓玄,以尚书令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加黄钺,又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前将军谯王尚之为后部,因大赦,改元,内外戒严。”[10]3589后来,刘牢之叛司马元显,主要因为“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众,惧不能制,又虑平玄之后功盖天下,必不为元显所容,深怀疑贰”[7]2190;但不久,桓玄的篡晋企图,随着其势力的壮大而逐渐明朗,刘牢之继又反叛桓玄,最终导致自己失势而自缢身亡。如果陶渊明不遭母丧而尚在刘牢之军幕,那么就是刘牢之叛司马元显以及桓玄的见证者,陶渊明被卷入以及所受牵累在所难免,刘牢之因为“一人而三反”为时人诟病,陶渊明又何去何从?陶渊明此时丁忧,等于远离政治是非,保全其身家性命及志士节操,实乃不幸之大幸。在这个问题上,所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即皇帝位,贬晋安帝为平固王,远迁寻阳。此时,陶渊明正丁忧在家,桓玄权势如日中天,陶渊明深恐自己曾仕刘牢之而为桓玄嫉恨,故有诗云:“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眄莫谁知,荆扉昼常闭。”(《癸卯岁(403)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3]78陶渊明深入简出,深恐祸及自己。有学者认为陶渊明曾仕桓玄,何以在桓玄日炽之时,陶渊明无有他咎,只因母丧丁忧在家,却避之而犹恐不及?由此诗证,主张陶渊明曾仕桓玄还应商榷。
换一个视角,东晋时儒学仍为士族立家之本,对子弟教育则以儒学为先,以陶渊明为例,“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3]96,陶渊明深受儒学影响,在其居母丧期间,囿于生活贫困,诗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3]77;感于时代诗书不继,遂拟古而咏怀,诗有“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饮酒》其二十)[3]99,内心无比痛苦,故有“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其二十)[3]99。陶渊明生活的东晋社会,倡导以儒学求仕,儒学之孝悌观念备受社会重视,譬如晋武帝泰始四年(268)诏曰:“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7]57居母忧作为孝悌观念的具体表现,在以儒学求仕的层面,我们为陶渊明居丧与求仕找到了心理契合点。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居母丧,失去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似出于无奈,但未必不是一种求仕的策略。换言之,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社会已经形成居丧守礼的世风,客观上能使人以孝出名,进而因名致仕。无论面对与否,陶渊明居母丧时伴有以名求仕的大众心理,正是这种心理,使其在因居丧而失去机会与及时建功立业之间寻找到了心理平衡点。
二、程氏妹卒及陶渊明居丧前后
与陶渊明母丧居忧相比较,因程氏妹卒而居丧在诗文中的记载相对明确。《归去来兮辞》有“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馀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3]159《祭程氏妹文》有“维晋义熙三年(407),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3]191。两相对照,逯钦立注称:“已嫁姊妹,按服制应服大功服,为期九个月。程氏卒于义熙元年(405)十一月以前,至义熙三年五月,约十八个月,即两个九月,故曰服制再周。”[3]192遵照礼制,男子为姊妹、姑母堂兄弟等,应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绖缨,布带”[6]601,服期九个月。细考程氏卒年,义熙三年(407)“五月甲辰”,为夏历五月三十[11],是日“服制再周”,则程氏卒期详细为义熙元年(405)夏历十月三十。因此,陶渊明十一月去武昌奔丧,并写作《归去来兮辞》。就陶渊明与程氏关系,《祭程氏妹文》云:“谁无兄弟,人亦同生,嗟我与尔,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爰从靡识,抚髫相成。”[3]191这里“兄弟”指内外姻亲,《仪礼·士冠礼》云:“兄弟毕袗玄。”郑玄注:“兄弟,主人亲戚也。”[6]29“同生”一词,互见《祭从弟敬远文》:“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3]194程氏妹已经嫁人,虽然“同生”,但属于姻亲,因此称“兄弟”;“百”指百倍,“特百常情”说明陶渊明与程氏妹感情甚笃。“慈妣”何解?释“慈”,《仪礼·丧服》:“传曰: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若是,则生养之,终其身如母,死则丧之三年如母,贵父之命也。”[6]565《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8]161因此,“慈妣”指已经去世的慈母。由《祭程氏妹文》记载可知,陶渊明父亲纳妾但其没有生养,于是命陶渊明与程式妹为其子女,他们称父亲此妾为慈母,只是其在陶渊明十二岁、程氏八岁时就不幸辞世了。父亲命“女(汝)以(之)为母”的时间当在陶渊明幼稚时期,因此,他与程氏才有“爰从靡识,抚髫相成”[3]191,即两人从尚不分辨彼此时改易慈母,朝夕相处走向成熟。
两汉崇奉儒学,强调孝悌,重视礼仪,东晋南朝时期亦然。“江南风俗,凡遭大丧,相近相知的人,三天之内要去吊丧。如果过了三天而不去吊丧,便会被认为是不怜悯丧者的失礼行为,以后即使在路上相遇也不予理睬了。”[12]《归去来兮辞》云,程氏妹卒,时值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就文本而言,陶渊明辞官内因可见于“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3]159。又有外因:“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3]159程氏妹亡故于武昌,因为吊丧事急,才有“情在骏奔”,服期九月,非为三年,因此不合所谓“遣宁终丧”的法令,至于“自免去职”,本是不必要的。由彭泽至武昌,扬帆长江,依照当时船速,需要多少时间呢?东晋王廙性“尝从南下,旦自寻阳,迅风飞帆,暮至都”[7]2004,由寻阳至建康,顺风扬帆需要一天,以此推算,由彭泽至武昌只需半日许。如果说陶渊明因孟母卒“遣宁终丧”是出于无奈,辞去彭泽令则颇出己志,其作《归去来兮辞》,引吭高歌,宋陈知柔《休斋诗话》称“迨今人歌之,顿挫抑扬,自协声律。盖其词高甚,晋宋而下,欲追蹑之不能。”[13]
陶渊明辞去彭泽令的是年三月,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是时(405),刘牢之之子刘敬宣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陶渊明参其军幕。考其时事,三月,“(刘)敬宣为江州,辞以无功,不宜援任先于(刘)毅等,裕不许。毅使人言于裕曰:‘刘敬宣不豫建议。猛将劳臣,方须叙报;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后。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为员外常侍耳。闻已授郡,实为过优;寻复为江州,尢为骇惋。’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职”[10]3638。三月,晋安帝反正,自江陵至京都建康,“乙未,百官诣阙请罪”,“庚子,以琅邪王德文为大司马,武陵王遵为太保,加镇军将军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7]258。晋安帝返回建康重新做皇帝,是国家的大事,又涉及刘裕本人利益,这时的刘裕应当在京都。由此来看,以为陶渊明此次使都为刘敬宣递送解职之表,非为不经之谈,递送的对象就是已经“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刘裕。由此推定《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于三月份庚子之后。刘敬宣自表解职事出刘毅,刘毅曾为刘敬宣宁朔参军,据《宋书·刘敬宣传》记载:“时人或以雄杰许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当别有调度,岂得便谓此君为人豪邪?其性外宽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当以陵上取祸耳。’毅闻之,深以为恨。”[9]1412刘敬宣自表解职的结果是,“于是散彻,赐给宅宇,月给钱三十万。高祖数引与游宴,恩款周洽,所赐钱帛车马及器服玩好,莫与比焉。寻除冠军将军、宣城内史、襄城太守”[9]1412。即刘裕欣然应允,赐其良宅钱帛等,与其数次游宴,以察其有无逆志,其间刘敬宣表现甚恭,刘裕遂除戒心,然后授以冠军将军、宣城内史、襄城太守等。因此,刘敬宣“自表解职”,看似因为其与刘毅个人恩仇,实际是由于刘裕对他的不信任。其中滋味,如《韩非子·奸劫弑臣》辨识云:“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14]由此可见,乙巳岁(405)三月时,刘敬宣尚处危疑之地而不能自保,时任其建威参军的陶渊明自有山雨欲来的惊恐之感,《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故云:“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3]79表达其倦然归与之情。《宋书·刘敬宣传》载:“敬宣宽厚善待士,多伎艺,弓马音律,无事不善。”[9]1414陶渊明所以仕刘敬宣建威参军,他的礼贤下士又多才艺应为原因之一;其二,因为陶渊明始仕刘牢之镇军参军,与刘敬宣有着家世之谊。刘牢之,北府兵集团领袖,犹如其曾祖陶侃,身世寒微但出于军功,陶渊明以为有可托之志,至于刘敬宣,陶渊明亦认其为可托之人,借以兴复晋室。事实上,据《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五》记载,自元兴三年(404)三月“庚申,裕屯石头城,立留台百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造晋新主,纳于太庙”,“壬戌,玄司徒王谧与众议推裕领扬州,裕固辞,乃以谧为侍中、领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谧推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10]3621刘裕已成为北府兵集团的统帅,为众人所瞩目,至义熙元年(405),随着桓玄兵败,刘裕已经成为晋室的实际领导者,晋室复兴已成泡影。刘敬宣“自表解职”事件是一个契机,使陶渊明愈加认清时局。至于后来刘敬宣再度为刘裕起用,辞去彭泽令的陶渊明不再仕刘敬宣,皆因“自表解职”之后,刘敬宣已经屈事刘裕,至于《归去来兮辞》“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3]159,为作者虚托之词。再后来,刘裕西讨刘毅,“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军事,贻敬宣书曰:‘盘龙狼戾专恣,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敬宣报曰:‘下官自义熙以来,首尾十载,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节,常惧福过祸生,实思避盈居损;富贵之旨,非所敢当’。”[9]1415刘敬宣的谦卑姿态得到了刘裕的赞许。刘敬宣气节若此,陶渊明本来失望而去,怎敢再有所托?
乙巳岁(405)三月之后,陶渊明至仲秋始任彭泽令新职,见《归去来兮辞》:“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3]159,然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馀日”[3]159。对于彭泽令一职,陶渊明为何先求之后又轻弃之?陶渊明家寻阳柴桑,距离彭泽百里,是时隶属江州管辖,州治寻阳郡。义熙元年(405),时值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兵集团追剿桓玄残余势力,表现在对江州的争夺上,据《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五》记载,元兴三年(404)四月,“刘裕以诸葛长民都督淮北诸军事,镇山阳;以刘敬宣为江州刺史”[10]3626,又为建威将军;十月,“刘敬宣在寻阳,聚粮缮船,未尝无备,故何无忌等虽败退,赖以复振”[10]3632。刘敬宣任江州刺史直至义熙元年(405)三月,其间有桓玄兄子“桓亮自号江州刺史,遣刘敬宣击走之”(《晋书·刘毅传》)[7]2206。元兴三年(404),“晋大将军武陵王遵承制,以(刘)道规为振武将军、义昌太守”,“与刘毅、何无忌追玄”。及“江陵之平也,道规推毅为元功,无忌为次功,自居其末。进号辅国将军、督淮北诸军事、并州刺史,义昌太守如故”[9]1472。刘毅居功邀赏,方有“闻已授郡,实为过优”之愤恨语,于是刘敬宣辞去江州。据《晋书·何无忌传》记载,直至“义熙二年(406),(何无忌)迁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随义阳绥安豫州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八郡军事、江州刺史,将军、持节如故。以兴复之功,封安成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增督司州之弘农扬州之松滋,加散骑侍郎,进镇南将军”[7]2215。至于义熙元年(405)三月到义熙二年(406)何无忌治江州之间,江州刺史为何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追剿桓玄残余势力之时,“(何无忌)与振武将军刘道规俱受冠军将军刘毅节度”[7]2215,及晋安帝反正,刘道规又“推(刘)毅为元功”,“二州既平,以毅为抚军将军”[7]2207,又联系刘毅居功迫使刘敬宣辞职,江州在此期间应为刘毅控制。刘毅前既已逼迫刘敬宣,陶渊明曾参谋刘敬宣军事,其新任彭泽令新职,寻阳近在咫尺,陶渊明去职的重要原因,应是担心为刘毅嫉恨,有性命之忧,如《感士不遇赋》:“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3]147又如《与子俨等疏》:“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3]187在这个层面,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一职,程氏妹卒仅是一个托辞而已。
三、余论
将吏遭三年丧而“遣宁终丧”,虽为东晋法令,但仍有例外,譬如与刘裕同起义兵的刘毅,“(刘)毅丁忧在家,及义旗初兴,遂墨绖从事。至是,军役渐宁,上表乞还京口,以终丧礼。”[7]2207但是不被允许,“诏以毅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淮南历阳庐江安丰堂邑五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将军、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属。以匡复功,封南平郡开国公,兼都督宣城军事,给鼓吹一部。”[7]2207刘裕初起义兵,彭城同乡刘毅为其心腹,时值用人之际,礼节就不予多虑了。联想陶渊明母丧居忧,刘牢之同样是用人之际,同意陶渊明“遣宁终丧”,可见陶渊明非为其股肱。陶渊明任其镇军参军,仅为文职属吏而已,军功可望而不可即,因此屡生退意,故有诗“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3]71,“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400)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3]74。至于陶渊明居妹丧,时值陶渊明任职彭泽,此时其内心仕与隐的矛盾,随着刘裕成为晋廷实际领导者而逐渐消泯,儒家的建功立业思想已经不再,“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3]159所谓求官,无外乎“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归去来兮辞》)[3]159。陶渊明始求之而轻弃之,非关程氏妹卒,据《晋书·陶潜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7]2461对于这段话,逯钦立考辨之,“所谓‘为五斗米折腰’,同‘事乡里小人’,不是一件事,而是两件不同的事。”[15]后者指束带见邮督。联想到桓玄之乱始平,刘裕乡党刘毅实控江州。“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刺,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魏书·刘裕传》)[16]陶渊明曾祖陶侃事迹显赫,有诗“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命子》)[3]28陶侃之后,寻阳陶氏已成为门阀士族,刘裕等低级士族出身,陶渊明以曾祖为晋世宰辅,而自视甚高,读其激愤语“乡里小儿”,不觉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