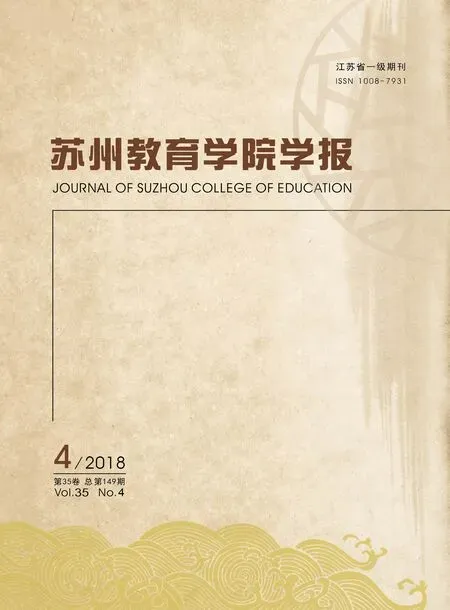怀念与范伯群先生谈话的时光
2018-04-04陈霖
陈 霖
(苏州大学 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范伯群先生去世后,我一直想着写点儿纪念的文字,但每每坐下来准备写的时候,有关先生的点点滴滴就流水般涌现。我不愿它们停下来,让自己沉浸其中,不去用文字捕捉它们。这样的时候,我感到范先生并没有离我而去。他微微笑或者哈哈笑的样子,他说到激动处用指节敲几下桌面的神情,他坚持为我的茶杯里续水时佝偻着的背影,他打开某本杂志把编辑的错误指给我看时的得意和调皮,他在我听了半天搞不懂一个词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只好拿出笔来在纸上写下那个词时的无奈,他上楼时不让我搀扶的坚决的语气,他很“听话地”被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地安排拍照……当所有的一切涌来的时候,我内心很安静,我知道,有一种力量从范先生那里传来,将我与喧嚣而浮躁的空气隔开。
一
2017年年初,我接受了做范先生访谈录的任务,有了与他亲密接触的机会。对范先生,我自认为比较熟悉:读过他写的书,读博时上过他的讨论课,博士论文答辩时他是答辩委员,他的许多弟子是我的朋友,我住的地方离他家很近,经常在小路上不期而遇,站着聊聊天,偶尔去他的小屋拜访……但是,真的开始访谈之后,我感到几乎是重新认识范先生。一方面,面对著述等身的范先生,必须系统地了解他写下的文字才能走近他,才能和他交谈,所以需要“补课”。在阅读中,范先生文字的功力和才情、文字中的气息与思想、文字背后的阅历,都让我时有发现的惊喜。另一方面,在与范先生近距离的接触中,我对他个人的性情、性格有了更多直观的感受,他开放豁达、单纯爽朗,无拘无束之中又包含着敏锐、细致和分寸,他热情、睿智而健谈……与他的交谈让我更为真切地面对一个立体的、丰富的范先生,也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于我而言,访谈的过程无疑是一个学习和体验的过程。
2017年2月1日,我对范先生的访谈正式开始。走进范先生的家中坐下,我拿出了自己带的茶杯。范先生说:“啊呀,你到我这里来还自己带茶杯!”我说习惯了,包里总是带上泡好的茶。他说:“在你到来前10分钟左右,我就把茶泡好了。”这时我才注意到,桌上已经有一杯茶。我赶忙收起自己的茶杯说:“那就喝您的茶。”范先生呵呵笑着,往杯里续上了开水。茶水的清香散出,我们的谈话开始。后来我去范老师家,每次走到楼梯上的时候,便想着桌上有一杯范先生泡好的茶在等着我,心里就滋润开来。
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在前一天跟范先生约好访谈的时间,告知他大体上我想访谈些什么。第二天我去的时候,桌上就有一些资料已经预备好了,说到相关的地方时,范先生便指点给我看;谈话中涉及的时间、人物之类,他都能给出清晰的陈述。有时候在谈话结束之际,范先生会提醒我,下次我们可以谈谈什么啦。在完成每次规定的“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也常常“跑偏”——我忘记了本来的目的,范先生肯定也是这样,我们的话题在某一个节点上岔开去,散漫开来,时间也就拉长了很多。我有些担心说话时间太长,范先生会累,可他说:“这样蛮好,你看你不来跟我说话,我一天里说不到几句话的,甚至好几天都说不到几句话的。”我想也是,陪他说说话也是好的,访谈的任务嘛,慢慢来,不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第一次我带学生摄像采访他,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访谈结束后,学生感叹:没想到范先生这么大年纪精力还这么好,这么健谈,条理也十分清楚;学生的另一个感叹是:范先生谈到的内容都是他们从书上读不到的。我对范先生的访谈,涉及到他生活与学术的各个方面,而逐渐在我的心中形成的一个回旋不已的主题则是:“保住智慧的元气”。
二
我与范先生的谈话时间,一般是在周一的下午三点到五点。有时候,我也会临时去找一本书,找一幅照片,或者去帮他解决一下电脑上的某个小问题 ……范先生都会留我坐下来喝杯茶,聊上半小时到一小时。这样的时候,我和范先生往往都更为放松。
有一次,聊到学界有人做出一些没有底线、匪夷所思的蠢事,范先生很是愤慨和失望,说不知道这人是怎么想的。我谈到某些人挺会混的,将江湖上的一套带到学术界。大概是见我言辞间对“江湖气”颇有些不屑和偏激,范先生似是劝慰似是感喟地说:“你想想看,哪里不是江湖呢?谁不在江湖上呢?关键是得有原则。还有,要有扎扎实实的真东西,否则迟早是混不下去的。”“有原则”和“有真东西”正是范先生做人和为学的标准吧。
有时候,我会在他跟前抱怨现在老师难当,学生难带。我注意到,他对学生难带的抱怨从来就不接茬。我知道,他带过很多“难带”得多的学生,我所说的那些“难带”,恐怕根本算不了什么。倒是对老师难当,他不止一次地感慨:现在的年轻老师压力真是太大了,评职称发文章要有级别,要有项目,还要出国,而且我们苏大的标准比“985”高校的要求还要高。
还有的时候,我驾车带范先生去某个地方,自然比平时开得小心得多,范先生或许是为了让我放松些,车上谈的都是些轻松的话题。有一次,他谈起小时候刚来苏州住的地方,就在天赐庄附近,半夜里会听到运河靠岸上来的人,抬着病人,沿着土路,往博习医院奔跑的声音。还有一次,他谈起20世纪60年代初刚到南京住在西花园里,看林散之写字,傅抱石作画。他说傅抱石画雪花的方式很独特,把电风扇放在那里,笔蘸饱了墨,电风扇一吹,墨飘到纸上就成了雪花了。
范先生与我的谈话,对我说过的往事,让我深受教益或启发自不必说,那种没有戒备、通体透明的氛围,毫不张扬、自然随性的体贴,格外让我难以忘怀,于今想起,备感珍惜,也十分遗憾在他生前没有更多地陪他聊天,听他说故事。
到2017年8月底,我对范先生访谈的主体部分基本完成。我将整理出来的访谈稿交给范先生审阅,过了几天他就叫我去拿。我一看,他对很多有笔误或是听错的地方都做了修改,但内容基本没动,包括很口语化的表达。他说这样保留着谈话的口吻,看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在这之后,我们对一些有遗漏的地方进行了补充性的访谈。
后来,我又提出集中谈一下范先生与国外或境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情况,因为以前虽已有所涉及,但是比较分散,往往被其他主题冲蚀。范先生说:“听你的安排。”于是,2017年10月2日下午,我带着他到坐忘书房做访谈。因为国庆放假,学生回家了,我就请了杜丹老师做摄像和摄影。到了那里,范先生很喜欢那个环境,先由坐忘书房的沈女士领着到楼上看了藏书,然后来到沈女士为我们谈话而安排的主楼外回廊上的一个单间里。访谈开始前,我怕窗外声音吵,准备关了窗子。范先生说:“窗子就开着吧,这地方很有园林的感觉,窗外的竹子很美。”范先生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一叠照片,看得出都是按一定的顺序排好的。他说要一张张指给我看,所以“今天你不能离我太远,你也要出现在镜头里,哈哈!”(这以前我都是坐在他对面访谈的)这次我们谈了将近三个小时,其间杜丹还让我跟范先生拍了好几张合影。以前我还从未跟范先生单独合影过;没想到的是,这第一次,竟然成了最后一次。
三
范先生于2014年获得苏州市首批“姑苏文化名家”称号。当苏州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徐惠女士了解到我在对范先生进行访谈时,提出建立网上“姑苏文化名家范伯群工作室”的动议,并委托我负责建立和维护这个工作室。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可以做起来。范先生起初有点顾虑,主要有两点:一是怕给别人添麻烦,二是自己没有时间。当我和徐惠将公众号的策划案交给他,并详细说明了运作方式后,他表示支持和配合。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和测试,“姑苏文化名家范伯群工作室”微信公众号于2017年9月23日正式开启。适逢全国“第二届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暨武侠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我们就在会议开幕式上举行了一个简洁的开启仪式。在介绍范先生学术道路和学术成就的短视频展播之后,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尧教授和范先生同时按下开启的按钮。我扶着范先生走下讲台时,他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我们工作室的主任陈霖教授。”我当时感到有些意外,后来想到范先生大概是觉得我应该有一个面对公众的身份吧。
公众号开通后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范先生也很快学会了如何在为他专门准备的Ipad上浏览公众号。最初,刊登文章的预览,我都要请他过目。第一次他就指出了文章中的错别字,嘱告编辑要细心校对。公众号转发严家炎、温儒敏、陈思和等大家的文章前,他都要亲自打电话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严家炎先生那段时间在国外,范先生就用电子邮件联系,严先生回复一到,他就告诉我说可以发严家炎先生的文章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将关注人数的增长、后台的留言等情况告知他时,他感到很意外,也很振奋,说没想到这些东西还有那么多人要看。公众号上刊登他为陆文夫的《梦中天地》写的序《小巷散文中的大千世界》时,他还饶有兴趣地在朋友圈里留言,介绍他发表于台湾报纸上的文章如何为“老苏州”做“广告”的事来。
刊登范先生评陆文夫的《美食家》的文章《宏观着眼,微观落笔——评〈美食家〉》时,我做了一个简短的按语,其中介绍了这篇文章1983年在《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时署名“吴越”,是范先生唯一一篇以笔名发表的文章,因为当年他已经在《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了论张恨水的文章。刊发前一天,我把预览发给范先生看了,晚上九点多钟,接到他的电话,说他觉得介绍这篇使用笔名的原委不大好,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文学评论》作为文学专业最高级别的刊物,发一篇有多难啊,而你范伯群一年却在上面发了两篇,说出来恐怕还是会刺激到一些人的”。范先生就是这么凡事替别人着想,宁可谦抑自己。
一般情况下,范先生并不过问公众号编辑事务,只是听我“报备”,但他很愿意听我说说公众号“后台”操作的事,我也给他看过我们微信工作群的一些讨论。11月初的时候,他对我说,知道大家很辛苦,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表示慰问,也认识认识小朋友。我答应了,说等学期结束一定带大家见范老师。他开始时表示同意,但过了不久说,不要等到学期结束了,最近就请吧。我明白范先生的诚意,就答应了。时间排在了11月26日,一个星期天。范先生亲自确定了一家苏帮菜做得很好的饭店,他觉得这样可以让来自外地的学生们品尝和了解真正的苏帮菜。但是11月23日晚,范先生打电话给我,他要住院去了,恐怕没法一起吃饭了。但他坚持那顿饭既然请了,就不要改了,由我替他请大家,等他过些时候出院了,再与大家见面聊。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范先生再也没有机会与小朋友们聚会了。
11月25日,我发短信给范先生说要去看他,很快收到他的短信:“我现在很好,忙的话就不用过来。”我晚上到了医院才知道,短信是他让陪护的研究生罗杰代发的。罗杰说:“范先生咳嗽厉害,血氧较低,医生让少说话。”但当范先生知道我来了,还是对我说:“没事的,你们明天按计划聚,我已经跟饭店确认了。”第二天中午聚餐时,我对大家说了范先生不能来的原委,大家一起祝愿范先生早日康复。就在快吃完饭的时候,接到石娟的电话,说范先生转到ICU了。大家立刻惊呆了。
虽然我感到不妙,但依然相信范先生会回来的。第二天,当祥安兄告知先生状况稳定,应该可以挺过了一劫,我心里松了一下。接下来我就出差到深圳,到深圳的那天晚上,问祥安,祥安说情况变得严峻起来。12月1日,范紫江在微信上跟我谈了好一会儿父亲的情况,还告诉我,父亲在病床上看了公众号新推出的文章。我们对先生的康复还抱着一线希望。可是到了12月2日,祥安告诉我,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12月4日我回到苏州,立刻去医院看范先生。进入范先生所在的ICU,整个房间一片冷灰的色调,只有左边角落的墙上有细碎的光影,那是下午的阳光穿过玻璃和窗帘后投下的。范先生戴着氧气面罩,不方便说话,曾经那么轮廓分明神采奕奕的脸庞,变得如此瘦削、苍白、窄小;裹在被子里的身躯,也显得小了许多。我难以相信,几天不见,范先生竟变成这般模样。我喊了一声“范老师我来看你了”之后就说不出话了,他微微点了点头;好半天我才又开口说:“今晚公众号要推送的是您关于《祝福》的文章,已经编好了。”一丝笑意从范先生的脸上掠过,他还朝我竖了竖大拇指。这是范先生留给我最后的身体语言,也是我与范先生最后的谈话。我一次次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感受到不是一个生命正在远去,而是一个灵魂始终在那里鼓励着生命前行。
四
每次我跟范先生聊上一两个小时的时候,都会问他累不累,他总是说不累。范先生不会对人轻言自己的累:他不服老。一次我跟他很随意地聊天,不经意间说“你老人家……”,他呵呵笑着重复我的话说:“你说你老人家……”我尴尬地意识到自己不小心让范先生不舒服了。“老”及其关联的一切,范先生是不愿轻易触碰的。暑假里,女儿紫江回来探望他,我带着摄像想记录下一些他和女儿在苏州大学本部校园里的一些场景。范先生很不愿意拍他从林荫道上走过,觉得拄着拐杖走路太不好看了。我和紫江都劝他说:“您拄着拐杖走路的样子也很有派头,很有风度。”
2017年下半年,江苏省作家协会作出了为文学大家拍摄系列专访的决定。11月6日,按照事先的约定,范先生下午两点在文学院腾出的一间办公室接受专访。他前一天晚上约我12点半接他去学校,说是书虽然已经运过去了,但他怕别人摆不好,要自己提前去将书摆好。估摸着摄制组快到时,范先生起身走出办公室,拄着拐杖站立着,仿佛一尊雕像,以谦和与谨严的身姿站在文学院办公室的通道上,迎候摄制组的到来。那天的采访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我送他回家的时候问他累不累,他说:“还好,因为早有准备嘛,提着一股气,也就过去了。”
那次电视采访,我让一个学生将经过记下来,其中写着:“采访结束的时候,天已黑了下来。”稿子给范先生审阅时,他改成:“采访结束的时候,已晚霞灿烂了。”
范先生在他2014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后记”中曾经写到:“我觉得‘晚霞’是自然界中最美的景观之一,它甚至比朝霞更舒展与耐看。……但我不喜欢古诗中那歌颂晚景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总觉得‘夕阳无限好’确是无限贴切的写实,而‘只是近黄昏’乃是一声无可奈何的低回的叹惋。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深深感到:‘夕阳无限好,明月正东升。’……太阳与月亮的交接班,就体现了这生生不息的代代相传,真可谓‘复兮旦兮,日月光华’!”[1]
范先生不愿接受黄昏与黑暗,一如他不愿接受衰老和死亡,他以文学的浪漫和孩子般的单纯,以历史的理性和智者的见识,鼓动着生命的风帆,虽历惊涛骇浪,不曾低头屈服,即便死神到来,也无法夺其傲然的尊严。
2018年清明节那天,当我站在小王山上范先生的墓前,抚摸先生的墓志铭,回想着与先生谈话的时光,感受到范先生终生为之并竭力葆有的智慧的元气,从虚空中传递着真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