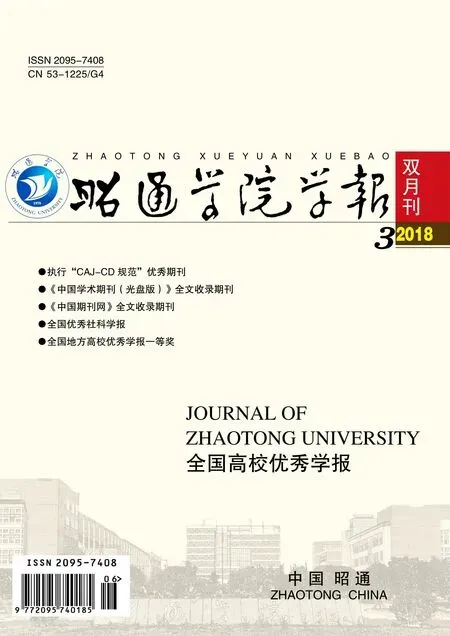话语权力视野下《庄子》“重言”小议
——以《内篇》为中心
2018-04-03徐永东
徐永东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1]941《庄子》“重言”的运用通常被释为借重长者之言以陈己意 。福柯(1926-1984)言:“话语活动(虽然它单调苍白)之下存在有难以想象的权力。”[2]2可以说,话语即是权力。如果从话语权力角度出发,《庄子》的“重言”及其使用本身便无不体现出作者对自身话语权力的积极推尊。在话语权力下移,各方话语纷纭的时代下,《庄子》借助“重言”试图建构以“道”为尊的话语权力体系在所难免。
一、“道术将为天下裂”——话语权力的下移
“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1064《庄子·天下篇》的这句名言常常为人所称引,被用来概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状态。成玄英疏:“儒墨名法,百家驰骛,各私所见,咸率己情,道术纷纭,更相倍谲,遂使苍生措心无所,分离物性,实此之由也。”[1]1066这更为具体地向我们描绘出彼时诸子百家竞起的局面。“幽、厉之后,周室微,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侯,或在夷、狄。”[3]在话语权力视野下,上述这些局面可以看成以周王室为代表的单一话语中心的解体,及其独占话语权力的下移,进而引发诸子对话语权力的争取。诸家建构自身话语权力体系的方式各异,除了道家之外,儒家也具备代表性。
儒家本身“学而优则仕”[4]191的特质决定了其本能地对话语权力采取主动争取的姿态。儒家建构话语权力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4]143
这段话可以看成对“正名”的一般解读。在孔子看来,“正名”的重要性超越语言本身以及具体的事务,而上升为理国治民的首要议题。如果说西周的礼乐制度本身是一个庞大的象征系统,象征并维系着各个阶层的尊卑等级秩序,那么在长期的支配过程中,它已经逐步从最初的由象征而产生的心理力量转变为社会承认的实际力量。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承续这种力量转化的方式,进而试图“借助对名义的规定来确认或迫使社会确认一种秩序的合理性”[5]。这种名义的规定正是话语的规定,及其必然伴随的话语权力的支配。因此,作为规定者,儒者具备了拥有话语权力的可能。
儒家争取话语权力的主要方式之二是述古。“述而不作,信而好古”[4]93是为夫子自道。述古实质上是对过去旧时代的尊崇,而在具体的话语活动层面则表现为对过去知识经验的评论。以孔子为代表的的儒者通过对“郁郁乎文哉”[4]65的西周礼乐文明的反复评说,来阐扬其价值所在。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评说的主体,儒者的话语权力也得到了体现。
可以说,在传统话语权力解体及下移的大背景下,儒者对话语权力的争取和建构是显而易见的。相较于儒者,《庄子》的“重言”表面上看与前者在“述古”上存在相似,但却是不同的机制。
二、道者话语权力的顺承
在《庄子·内篇》中,“重言”的陈述往往围绕述道者和问道者的对话展开,借助彼此之间的问答阐发“道”之要旨。在这一组组的对话之中,相较于后文所要论及的以孔颜、尧舜诸人所代表的他者,更多的述道者可以称为真正的道者之流,即他们无论在历史传统中,还是在庄子所构建的的文本内,始终拥有着对“天道”发声的话语权力。在这些道者之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南郭子綦、老聃以及数位兀者。
南郭子綦的社会地位在三者之中最高,他是“楚昭王之庶弟,楚庄王之司马”[1]48,属于社会的上层。这种身份上的优越性为他获得了天然的话语主体特权——既为其在上流阐发思想提供可能,又为其在下层观点流布提供合理性。而他本人又“怀道抱德,虚心忘淡”[1]48,具备对“道”的自觉性。他“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1]48,在“吾丧我”的状态中游心太玄,在“天籁”的阐发中超然自得。可以说,南郭子綦体现了思想话语的承负者和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两者的紧密结合。而出自身份显要者之口的论道之言,较之他人,往往具备更强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因此,这样的人物无疑是庄子实践其话语权力的最佳对象,寄予了其将关于“道”的话语权力通向上层社会的努力。
相对于南郭子綦,老聃的社会政治地位显然难以望其项背。然而,庄子之所以引用老聃之“重言”,依旧可以从话语权力角度得到解释。首先,类似南郭子綦那种思想和政治权力紧密结合者,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大背景下终究属于小部分,传统的“知识—思想”体系更多地落在新兴的士阶层手中。其突出表现即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招贤纳士之风靡然。这些人,或本是王官贵族衰颓而降为士,或本是下层平民接受教育而成为士,掌握着包含知识与思想的话语权力。而老聃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自然是这种话语权力的突出代表。其次,正如福柯在论述古希腊话语时所言,原本“因其支配力故而人们必须服从的话语,乃是由有权言说之人根据一定仪式来表述的”[2]5,而最高的真理在彼时却转而“不再取决于何为话语或话语所为,而在于它所说为何”[2]5。这对同处于“轴心时代”的中国而言亦然。从这一角度出发,庄子引用老聃之“重言”,正在于后者的“所说为何”。在《应帝王》阳子居问老聃“明王之治”一节中,老聃以为“明王之治”的要义正在于“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1]303。老聃关于“明王之治”的构想,使我们很容易追踪到庄子本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20的论述。可见,对以“道”治天下,突出“道”在治理天下中的话语权力,是两者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促成老聃的“重言”自然地顺承为庄子自身主张的重要辅翼。另外,老聃是士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子》借其“重言”,也从侧面表现出其欲将“道”之话语权力推向勾连社会上下层之士人群体的努力。
“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1]278庄子对畸人的描绘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对兀者群体的叙述尤为突出。成玄英疏云:“刖一足曰兀。”[1]193而刖本身是为古代酷刑的一种。在世俗社会,身受刑罚之人往往为人所鄙,为人所弃。如叔山无趾为仲尼斥以“不谨”而拒绝其学。然而,正是这些被鄙被弃之人,其言却为庄子所取借以醒世。相较南郭子綦,兀者不具备显赫的地位;相较老聃,兀者也非新兴的士阶层。这些似乎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群体何以具备道者的话语权力?闻一多先生曾言:“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体一点讲,一种巫教。”[6]据此可以想见,伴随着神明崇拜思潮的逐渐走低和理性精神的崛起,道家先哲们拈出一个“道”以代替原来的神灵至尊,而庄子更是以“畸人”代替原始的“巫”来作为此时的神即“道”在人间的代言人。要言之,“畸人”在《庄子》的文本中近乎“道”的人格化身。而兀者作为畸人的重要代表自是“道”的权威传达者。例如在《德冲符》申屠嘉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一节中,子产厌恶己与兀者申屠嘉“合堂同席而坐”[1]202,后者以同“游于羿之彀中”[1]204为喻,突出天命的必然性和对内在道德的追求,寄身于天地而遗忘其形骸。从其言论,自然是论道述道之语;从其人论,其人自身的经历处境恰恰是其“道”论的具体呈现。如此,《庄子》借重作为“道”之化身的申屠嘉之言阐扬天道之重可谓渊源有自。而这些畸人兀者在世俗社会中处于下层,《庄子》对他们言论的运用从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其将“道”的话语权力广被下层的愿望——“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1]193或可以看成这种愿望的体现。
综上,南郭子綦、老聃以及兀者之流作为道者话语权力的代表,在体道述道上具备言语主体的特权。这种特权或以其优异身份而突出,或以其道论和合而拔萃,或以其身即“道”而权威,都自然为《庄子》所顺承。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庄子》通过顺承这些流布于不同阶层的道者话语及其话语权力,在彼时社会的上、中、下三个层面传播了其思想主张。
三、他者话语权力的重塑
在《庄子·内篇》中,除了上述所论纯粹的道者之流话语权力的顺承,还存在着他者话语权力的重塑。所谓他者是一批区别于纯粹道者的人物,例如尧舜、孔颜等等,他们或是帝王之类,或是儒者之属,原本并无鲜明的道者立场,甚或具有其反面,而在《庄子》的文本中却为其所用。这种情况一般将其解释为《庄子》借重其身份而不重其言,实质为庄子言说。事实上,这或可从话语权力角度对其进行进一步分析。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提出“话语应用条件限制系统”这一概念,这个系统通过对话语应用的条件予以限定,从而对话语的持有者予以一定的规范,最终达到话语权力的凸显。在这一系统中,首要一条是“话语仪规”(Ritual)。
首先,“话语仪规”“界定言语个体所必备的资格(在对话、询问或记诵中谁必须占什么位置且作出什么样的陈述)”[2]15。通过有意识地对对话双方位置的设定来确认话语主体地位,这是话语约束权力的体现。可以孔子和颜回的一组对话为例予以说明:
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1]290
在《论语》中,孔子与颜回鲜明地体现为师与弟子的伦常关系。在颜回“仰之弥高,钻之弥坚”[4]111的赞美声中,孔子的权威无形中被树立。而上所引之《大宗师》中的这组对话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孔子欲从颜回而师之的情境。师与被师位置的转变体现了话语主导地位的转变,伴随而来的是话语权力的转换。而这种转换的关键和依据在于上文所引的颜回对“坐忘”的陈述。换言之,正是“坐忘”的大通之道赋予了颜回超越世俗之师的可能。从表面上看是孔子尊颜回,实则是尊大道。由此,“道”的话语权力得到了体现。再如《论语》中,尧被孔子称颂:“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4]107其身份地位之高无以企及。而在“尧让天下于许由”中,尧却以布衣隐士之徒许由为尊而“请致天下”。尧与许由在世俗中的尊卑之异被泯灭,进而互换。我们能够从尧的陈述中想见许由作为怀道之士的特殊存在。以上两则例子共同之处在于,在《庄子》所创设的文本中,世俗所公认的地位被有意地倒置,话语的权威伴随着倒置而转变,导向怀天道、抱德行的一方,从而使得“道”的话语权力被突出。只不过前者由“道”之话语权力拥有者的陈述顺向促成互换,后者由对面的他者话语持有者逆向促成。
其次,“话语仪规”“确定言词被假设具有或强加给的功效,其对受众的作用,以及其限制性能量的范围”[2]15。通过突出“道”的话语施加给对象的效果来反映“道”的话语权力是《庄子》行文的典型手法。这种效果突出地表现为他者的赞美之词。在“鲁有兀者王骀”一节中,作为“道”的人格化,兀者王骀的“不言”之言为仲尼所深深叹服,甚至使得后者欲从而师之:“夫子,圣人也,丘也直而未往耳。丘将以为师,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1]194我们能够从仲尼的溢美之词中感受到天道之威。又如前引颜回向仲尼论“坐忘”的情境,后者所表现出的敬服之状正导源于前者的述道言辞。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作为受众的“他者”的表现(评语居多)反观“道”的话语权力所在。
综上,从话语权力角度出发,《庄子》通过“话语仪规”的运用,重塑了他者的话语权力。这种意在突出“道”之话语权威而进行的重塑,其结果一方面表现为话语权力主导方的变化,即由他者导向道者;一方面表现为他者话语权力在“道”的权威下所呈现的“臣服”姿态。而这两种结果在具体行文中又相互交织,如上文两次以颜回仲尼论道为例。但无论如何,相较于传统(尤其是儒者传统)而言,《庄子》文本中的他者所代表的话语实在是被改变了。
四、结语
话语是“一种具有较强隐蔽性但又无所不在的真实权力”[7]。《庄子》的“重言”通过道者话语权力的顺承和他者话语权力的重塑实现其以“道”为核心的话语主导。事实上,这种主导的尝试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8]
“庄子的思想,从其影响于中国士大夫的历史来看,实在不是‘异端’,而是‘正统’。”[9]在话语权力视野下,这种文化脉搏地位的获得与其对话语权力体系的建构是分不开的。
注释:
①关于“重言”的讨论莫衷一是,本文从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