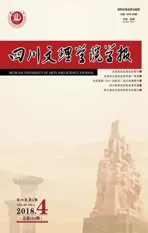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双系统模型
2018-04-03胡春梅曹荣誉
胡春梅,王 蕾,曹荣誉
(重庆文理学院 情绪和心理健康实验室,重庆 永川 402160)
青少年期是个体冒险行为的高发时期,研究者们将该时期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早期(10-13岁)、青少年中期(14-17岁)和青少年晚期(18-21岁),[1]围绕“青少年容易出现冒险行为的原因”展开了研究。过去,有研究者试图将青少年从事不计后果的冒险行为归因于他们的思维过程存在认知缺陷(如简单处理信息、忽视危险等),Spear(2002)认为青少年患有“奖励缺陷综合症”,推动他们通过冒险行为寻求刺激经验来满足奖赏需要;[2]但随着研究深入,这种观点被证明无效。总的来说,15岁及以上年龄的个体已经和成年人具有一样的逻辑推理、信息处理和危险认知能力。[3]
随着发展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研究的发展,对该现象有了新解释。双系统模型(the Dual System Model)是解释青少年冒险行为的观点;自2008年被提出,该模型得到了研究者们的认可、证实和拓展。本文将围绕四个方面阐述双系统模型的相关研究。
一、双系统模型的基本观点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者提出“大脑的发展模式能解释青少年做决定的各个方面”,[4]引导大家从大脑发展的角度探索“为什么青少年易出现冒险行为”。2008年,Steinberg等人(2008) 和Casey等人 (2008)提出了相似的“双系统模型”,解释青少年“为何做出冒险行为决策”。[5-6]该模型认为大脑的社会情绪系统(socioemotional system)和认知控制系统(cognitive control system)的发展过程能够解释“青少年易做出冒险行为”的原因,社会情绪系统会增加个体寻求奖赏的动机,负责该系统的脑区为大脑纹状体(striatum)以及内侧眶额叶皮质(medial and orbital prefrontal cortices);认知控制系统能抑制个体轻率、鲁莽的冲动,负责该系统的脑区包括外侧前额叶皮质(lateral prefrontal cortices,LPFC)、侧顶叶皮质(lateral parietal cortices)和前扣带皮质(anterior cingulate cortices,ACC) 。[5-8]模型提出青少年中期冒险行为达到顶峰,是因为此时已经成熟的社会情绪系统增强了青少年对刺激、新异、危险行为的追求,而成熟较慢的认知控制系统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抑制这些冒险冲动的相应水平。[9]
值得注意的是,双系统模型虽然指出青少年中期冒险行为达到顶峰;但这不仅指青少年中期会出现冒险行为发生的最高水平,也指青少年具有最高的冒险行为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的表达依赖于冒险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在青少年晚期,个体发展更少受到生物因素(青春期成熟)的影响,具有更多进行冒险行为的机会(如,更多经济来源、更少成人监督、更多冒险行为的合法途径——驾驶、饮酒和赌博等),会做出更多冒险行为。[10]因此,双模型系统指出生物成熟因素使青少年中期具有高冒险行为倾向,而社会和法律因素抑制了他们实现冒险倾向的机会。以饮酒、驾驶和赌博为例,如果允许15岁的个体进行这些行为,他们很可能会比20岁初期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酗酒、车祸和赌博成瘾。[1]
二、社会情绪系统的发展
双系统模型指出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增加和情绪唤醒有关,社会情绪系统的激活和反应在青少年中晚期达到顶峰。社会情绪系统的发展与青春期成熟关系密切,[11]随着成熟荷尔蒙分泌增多,大脑的神经结构和功能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增强大脑对奖赏的敏感性。[12-13]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社会情绪唤醒的两种形式“感觉寻求和奖赏敏感”了解其发展。
(一)感觉寻求的发展
感觉寻求是社会情绪反应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个体寻求多变、新异、复杂、强烈的感觉和体验,并且采取生理、社会、法律、经济方面的冒险行为来获取以上体验的人格特质。[14]由于在实验室环境中很难引发个体的感觉寻求行为,因此,现有相关研究多是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进行。众多研究表明感觉寻求的发展遵循倒U型曲线,在青少年中期达到顶峰,在成人期下降;[15-17]这表明社会情绪系统的发展轨迹是倒U型曲线。
感觉寻求与青春期成熟有关,青春期发育成熟水平高的个体会更多地卷入与感觉寻求密切相关的行为中,如物质滥用、[18-19]违法行为、[20]实验室中的冒险行为,[21]这说明社会情绪系统的发展与青春期成熟相关。
(二)奖赏敏感的发展
对奖赏敏感的行为研究还未得到关于其年龄差异的一致结论。部分研究发现14-21岁是个体奖赏敏感增强的时期,[17][22]13-17岁的青少年比6-12岁的儿童、18-29的成年人更难控制快乐冲动,[23]但Tottenham等(2011)却发现儿童、青少年和成人抑制快乐冲动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稳步上升。[24]
研究者们通过神经影像学研究进一步探究奖赏敏感年龄差异的神经机制。Luciana & Collins (2012)发现纹状体腹侧部(ventral portion of the striatum)是计算奖赏的主要区域之一,在青少年期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NAc)的体积(纹状体腹侧的一部分,是奖赏系统的核心结构)上升,之后缩小;[3]在奖赏过程中青少年的纹状体参与程度远大于儿童和成年人。[25-26]这些研究说明纹状体在决策制定中参与增多会导致青少年倾向更多的奖赏选择和冒险行为。
在奖赏过程中纹状体的活跃度会受到具体社会情境的影响。Smith等人(2015)发现在获得奖赏过程中,同伴在场(presence of peers)的情况下青少年完成任务时纹状体活跃程度比单独完成任务时更大;[27]O’Brien等人 (2011)指出,青少年与同伴一起时,完成立即奖赏任务(对照延迟任务)的成绩更高。[28]
青春期成熟会影响纹状体对奖赏敏感的发展变化。[29]Braams等(2015)在对8-27岁个体的纵向研究中发现,对金钱奖励的伏隔核激活在青少年中期比其他时期高;而且,该区域的激活与自我报告的青春期成熟水平更高有关。[30]这为“青少年时期青春期成熟导致社会情绪系统反应的增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三、认知控制系统的发展
双系统模型认为个体的认知控制在青少年阶段增加,持续到20岁早期,在奖赏敏感达到顶峰之后几年才成熟。关于自我调控和冲动性的大部分研究支持、证明了该观点。
(一)自我调控的发展
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通常采用反应抑制(reactive inhibition,指面对外界刺激时完全抑制动机和冲动)任务来评估。反应抑制是个体认知控制的形式之一。相关研究表明自我调控从儿童期到成人期在增加,[31-33]青少年和成人比儿童有更好的自我控制能力。青少年和成人反应抑制的差异与任务具体情境有关,在简单任务中成人和青少年的自我抑制能力没有表现出差异;而在相对复杂、繁琐、需要策略计划的任务中成人和青少年之间的调控抑制能力有年龄差异,成人的调控能力比青少年高。例如, Andrews-Hanna等人(2011)在使用传统斯特鲁普颜色词任务(Stroop color-word task)的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和成人在认知控制上没有差异;[34]而Veroude等人(2013)使用情绪化版本的斯特鲁普任务评估情绪干扰对认知控制的影响,发现从青少年到成人自我调控能力有所提高;[33]Albert和Steinberg(2011)在实验中发现,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完成简单任务(只需1步就可解决问题)的成绩没有差异,而在完成复杂任务(需要5步及以上解决问题)时,从儿童到成人的成绩随着年龄上升而增加。[35]
(二)冲动性的发展
冲动性(impulsivity)(没有计划或没有成熟思考的行动或反应)是用来评估自我调控的常用变量,是青少年的典型特征,它使青少年倾向参加鲁莽、冒险行为。[36]相关研究发现冲动性在人生第二个十年中会随着年龄而下降。[5][15]冲动控制(冲动性的反面)在成年早期发展成熟,20岁初期的个体报告的冲动性比18-19岁个体报告的低,[37]他们做出冲动行为的频率比在青少年期低得多。[5][16]
需要注意的是,自我调控和冲动性的发展都和年龄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持续增长,但是却和青春期发育成熟无关。[5][38]
(三)认知控制的神经机制
神经影像学研究调查了认知控制过程中大脑相关区域的激活程度、方式及联结强度等,为“认知控制能力随着年龄增加而提高”提供了证据。[39]
研究者们通过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 PFC(尤其是前额叶皮质侧面(IPFC))的发展来检验反应抑制的持续成熟;发现在青少年期,随着IPFC持续成熟,IPFC参与抑制任务的程度显著增加,个体完成任务的成绩随着年龄提高,[32-33]这说明了认知控制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的神经机制。
从儿童到成人期自我调控能力的增加和大脑神经联系从弥散到焦点激活的发展有关。[40]研究发现,儿童为了成功控制行动,比成年人更多利用脑前区(frontal regions);[41]这是因为,从儿童期到青少年早期,大脑效率低,需要调动更大脑前区的神经元来成功抑制反应。[42]在青少年期,大脑经历持续的重组,增强必要的神经联系,减少不必要的联系,在抑制过程中引导IPFC区域更加集中参与抑制过程。[1]
在认知控制的过程中,除了依赖大脑相关区域的参与,还依赖于这些区域间神经联结的强度。Hwang等人(2010)发现前额叶皮质和其他大脑皮质之间的联结从儿童期到青少年期增长;从青少年到成人期间,大脑皮质与皮质下区域联结的数量和强度都有所增加。[43]
四、两个系统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作用机制
双系统模型认为青少年期相对于儿童期和成人期,是一个社会情绪系统增强、认知控制系统仍在持续发展成熟的时期;冒险行为在青少年中期达到顶峰,是由于成熟的社会情绪系统激活增加了青少年的冒险冲动,而不成熟的认知控制系统还不足以控制这种冲动。
虽然大部分研究者认同“社会情绪系统和认知控制系统在青少年冒险行为中的作用”,但对于两个系统的作用机制还未达成一致。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1)两个系统是独立发展的,不会彼此影响,分别作用于冒险行为。[44-45](2)青少年晚期认知控制系统开始成熟,其增强会减弱社会情绪系统唤醒水平,降低冒险行为。[6](3)在青少年中期,极度活跃的社会情绪系统渐渐破坏认知控制系统的管理能力,导致青少年出现更多冒险行为。[8]
研究者们通过同时调查感觉寻求和冲动性在青少年冒险行为中的作用来了解“两个系统在冒险行为中的作用方式”。大部分研究发现感觉寻求和冲动性分别与冒险行为相关。Donohew等(2000)发现感觉寻求和冲动决策制定分别和“9年级学生进行性行为、饮酒和大麻使用”的更大机率有关,冲动决策制定和性行为强相关,感觉寻求和大麻使用强相关。[46]Cyders等(2009)在对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除开冲动性,感觉寻求单独预测酒精使用频率的增加。[47]Shulman和Cauffman(2014)发现冲动控制和感觉寻求分别独立地解释冒险选择中的变化。[48]
也有少数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和两个系统相关的大脑区域在冒险行为中同时起作用。Chein等(2011)发现青少年在完成冒险任务(危险驾驶)时,社会情绪系统相关脑区结构(纹状体)激活增加,同时,认知控制系统相关脑区(前额叶皮质)降低了活跃度。[49]但还没有其他研究发现类似结果。
这些研究说明虽然社会情绪和认知控制系统都对青少年时期增加的冒险行为起作用,但仍然需要全面的研究来确认“青少年的冒险行为中社会情绪和认知控制系统是联合作用还是独立作用,以及两个系统相互作用的机制?”
五、问题与展望
(一)实验室冒险行为和真实冒险行为发生情境不同,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实验室冒险行为和真实冒险行为在“情绪唤醒、行为结果可知性、同伴在场”方面有所不同。(1)真实冒险行为发生的情境常常是刺激或惊悚的,能带来更高情绪唤醒;而实验室冒险行为及其发生环境都具有更少刺激性,情绪唤醒程度没有真实冒险行为高。[1](2)大部分实验设计中的冒险行为带来消极或积极后果的几率是已知的;而真实冒险行为带来何种后果的几率通常是未知的。[50](3)真实冒险行为多发生在群体中,有同龄同伴在场;而实验室冒险行为多要求青少年独自做决定。[35]这些差异会影响双系统模型的有效性。
未来,我们要考虑如何设计出“情绪唤醒真实、行为结果未知、同伴在场”等方面贴近真实的冒险行为任务,提高研究的效度。(1)创设“高情绪(刺激、惊悚等)唤醒”情境。通过在完成实验任务前观看视频、阅读故事等方式尝试使被试处于高情绪唤醒状态。(2)创设“结果未知”情境。 如, Tymula等(2012, 2013)在设计冒险任务时,创设了结果“已知”和“未知”情境,通过实验发现,当知道输的可能性时,青少年比成人做出更少冒险决定;而当可能性未知时,青少年比成人做出更多冒险决定。[51-52](3)通过青少年约同伴到场实验,或在实验现场安排同年龄人员等方式,创设真实或虚拟的“同伴在场”情境。如,Kretsch 和Harden(2014)让青少年在完成实验任务时邀请同伴到场,[21]Smith等 (2014)创设情境让青少年相信完成任务时有同辈在观察他们,发现青少年增加了冒险行为。[53]
(二)确认认知控制系统的成熟
关于认知控制系统的成熟,研究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大部分研究认为认知控制系统发展为直线轨迹,发展缓慢,到青少年晚期才成熟;[6][14]也有研究指出认知控制系统在青少年中期达到成人水平的结构和功能,但相对于成人,认知控制的各方面还没有完全成熟、容易被干扰。[8][54]导致这些不一致的部分根源是“如何判断认知控制系统的成熟”。有研究者提出判断认知控制成熟的重点应放在“认知控制系统网络联结的结构和功能发展”上。[55-56]研究表明青少年期控制行为的增加和“增加的纹状体和前额叶区域之间的联结”有关;[57-58]同龄人中,“皮质和皮质下区域之间的联结发展更好”者相对更多参与冒险行为。[55][59]可见,还需要将行为测量、神经影像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确定判断认知控制成熟的操作化标准,更好调查青少年认知控制系统的发展特点。
(三)探究生理因素在青少年冒险行为中的作用
未来,应该深入探究生物因素(如大脑系统、遗传)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1)大脑系统。双系统模型指出了大脑纹状体、前额叶皮质及相关脑区在青少年冒险行为中的作用,但在后续研究中还应该全面探究大脑系统的作用。Ernst’s (2014)提出的三元模型扩展了双系统模型,该模型假设有第三个大脑系统——情绪/回避系统(负责情绪强度和回避,由杏仁核(amygdale)控制)会影响青少年的冒险行为,该系统会通过奖赏感知影响青少年的冲动决定,使其在面对奖赏时会变得极度活跃,抑制可避免的冲动。[60]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三元模型能够解释青少年增高的冒险行为水平,但却启发我们未来应该全面研究大脑系统在冒险行为中的作用。(2)遗传。Harden和Kretsch等(2016)对双胞胎的调查发现,青少年的认知失控与“遗传对智力的影响”之间有强相关。[61]这提醒我们关注遗传因素,未来应该通过多种方法探究遗传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
(四)开展跨文化研究
探究双系统模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验证“该模型是否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 Duell等(2016)发现亚洲青少年和西方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和奖赏寻求、自我调控的关系是不同的。[62]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发生在广泛的文化背景中,不同国家的青少年遵守不同的行为规范,发生冒险行为的机会不同。[63]虽然,青少年的奖赏寻求和自我调控受到生理发展的影响,[64]但也不能忽视社会因素的影响,如穆斯林国家的宗教信仰、[65]一些亚洲国家特别强调自我控制。[66-67]因此,研究者应该立足本国情况对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开展研究,验证和拓展双系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