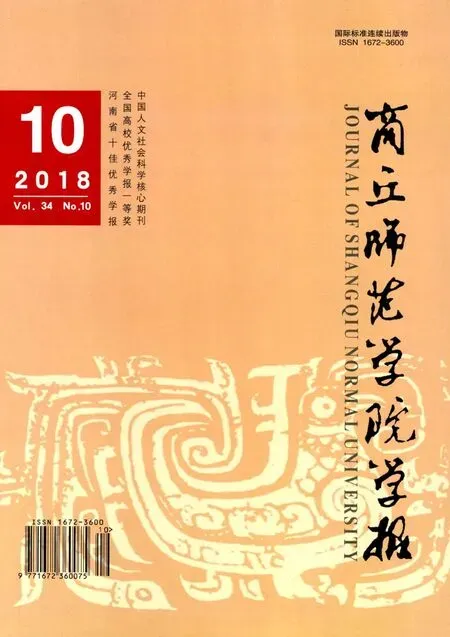论严歌苓小说《芳华》的悲剧艺术
2018-04-03陈学芬
陈 学 芬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严歌苓的新作长篇小说《芳华》甫一问世就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最多的是其中的人性问题,如陈思和的《被误读的人性之歌——读严歌苓的新作〈芳华〉》、刘艳的《隐在历史褶皱处的青春记忆与人性书写——从〈芳华〉看严歌苓小说叙事的新探索》;还有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的文学批评,如岳雯的《好人的故事:长篇小说中的一个伦理问题——以〈芳华〉〈好人宋没用〉〈心灵外史〉为例》;而孟繁华的《芳华的悲歌——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认为,“话语讲述的是曾经的青春年华,但在讲述话语的时代,它用个人的方式深刻反省和检讨了那个时代,因此,这是一部今天与过去对话的小说”[1];亦有研究《芳华》的叙述视角和审美效果的。
《芳华》的主人公刘峰是个好人,标兵模范,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却以悲剧告终;何小曼等的人生也充满悲剧。可以说,《芳华》是一出悲剧。本文拟从悲剧角度分析《芳华》的人物的悲剧类型及其成因,探究《芳华》的艺术特点。关于悲剧,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车尔尼雪夫斯基、尼采等都有过论述。《芳华》以好人的悲剧、英雄的悲剧、婚姻的悲剧蕴含着对荒诞的时代的批判,对人性恶的探讨;但又不令人绝望,因为小说洋溢着善和爱。因此,深入研究《芳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和人性,从而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和人生。
一、好人的悲剧
《芳华》的主人公刘峰是个雷锋式的人物,又因为其名字叫刘峰,被戏称为“雷又峰”,即又一个雷锋。他是被大家公认的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心灵手巧的好人,然而这个好人并没有好报。他深爱的姑娘不爱他,他还因为示爱不当被集体批斗,被迫离开文工团,到作战军队去服役。恰逢中越战争,他在前线失去了一只手臂,成了残疾人。退伍到地方剧团,剧团不景气。为养家糊口,他到海南做盗版书生意,媳妇跟人跑了。他与妓女做朋友,试图感化妓女,也没有成功。后来到北京漂泊,收入不多,又患上了不治之症。
刘峰这个公认的好人一生悲剧,其中有他自身的过失。关于悲剧,亚里士多德持“过失说”:悲剧主角由于犯了错误而导致悲剧。这个主角首先是善良的人,比一般人好,又与一般人相似,他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观众才会同情他[2]55。悲剧借引起怜悯和恐惧使情感得到陶冶。
刘峰深爱着林丁丁,却怕影响到她的前途而不敢表白,几年来一直压制着对她的爱,一直等到她入党提干,政治上允许恋爱结婚了才跟她表白。林丁丁却被他的表白吓哭了,没想到像雷锋一样的标兵刘峰竟然对她有想法,还伸手抱她、摸她。刘峰为她擦眼泪,顺势摸了她的后背,就是这一摸让刘峰成了众矢之的,还被调离了文工团,下放伐木连当兵去了。林丁丁本来不想举报刘峰,可组织上却不肯罢休,林丁丁只说刘峰向她表白,并没有说触摸的事儿,组织上却诱供,让老实的刘峰自己说出了触摸的事儿。
黑格尔“运用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解释悲剧冲突,揭示悲剧的实质”[2]428,“但是他把悲剧冲突的根源看成是伦理性的实体,精神的普遍力量或绝对理念的儿子,而不是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反映;把悲剧冲突看成是伦理性实体的自我分裂和内部斗争,矛盾的双方都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片面性,处于同等的地位;悲剧矛盾冲突的结果,不是真的、善的、美的东西的毁灭,而是理性、‘永恒正义’的胜利,是矛盾双方各自克服其片面性,达到矛盾的和解”[2]429,“只有当一个可敬的人遭遇灾祸或死亡的时候,只有当一个人遭受无辜的灾难或冤屈的时候,我们才特别称之为悲剧”[3]44。
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来看这个触摸事件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批判运动,则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没有错,但都有片面性。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男女授受不亲。20世纪70年代末,刘峰对林丁丁的触摸违反了中国当时的道德观念,是流氓行径,是值得大加挞伐的。组织这么做是为保护女性,是为了纯洁男女作风,似乎没有错。批判者是从中国传统道德的角度、从军队的组织纪律出发把这件事定性为作风问题而加以批判的。而被批判者是基于人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也没有错。但是双方都有片面性,所以引发了悲剧。
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认同黑格尔的悲剧观,他认为:“悲剧人物自身不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悲剧的结局不是绝对公正的胜利”,“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肯定悲剧来源于现实生活,这就批驳了黑格尔严重地与现实妥协的保守观点”[2]590。
如果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来看,刘峰的过失不是造成他悲剧的根本原因,中国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军队的组织纪律、规章制度,人们的盲从、随波逐流,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对好人的苛求,完美主义的追求等才是造成他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今天看来,组织上对这个触摸事件的处理实在是小题大做,没事找事,是荒诞而毫无意义的。可是在那个保守的年代,这深情的一摸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是作风问题。大会小会,批判不断。大多数人都加入了批斗行列,全然不念刘峰平日对大家的好,似乎不加入批斗阵营就非正义,不公道,是思想落后、趣味低下的表现,是包庇罪犯,同流合污。“一旦发现英雄也会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会格外拥挤。我们高不了,我们要靠一个一直高的人低下去来拔高,要靠相互借胆来体味我们的高。为什么会对刘峰那样?我们那群可怜虫,十几二十几岁,都缺乏做人的看家本领,只有在融为集体,相互借胆迫害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个人强大一点。”[4]163批斗刘峰的人们中没有大奸大恶之人,也没有私仇,人们只是由于从众心理而随波逐流,不辨是非。
人们对刘峰的集体批判除了时代的原因、制度的原因、人性的原因外,小说中还提到人们借批判刘峰而自我审视、批判的特别原因。刘峰的犯错让人们认识到标兵模范刘峰也不是完美的,也有他们身上的弱点,让他们对完美人格没有了幻想。刘峰撞见了偷情的淑雯,但并没有揭发她,而是暗地里劝她。当刘峰因触摸林丁丁犯了错时,淑雯竟然随波逐流地在大会上批判他,念稿子时还流了泪,也许是痛心好人刘峰的犯错,世间竟然没有高尚纯洁的人。对刘峰的批判,也是对自我劣根性的批判。在批判刘峰的事件上,显示了传统道德观念的顽固,组织对个人的压制,群体行为的盲目、非理智,人们对完美人格的变态追求,荒诞的时代所激发的人性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斗地主、打右派,而批斗是惯用的手段。在“反右”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被波及,如萧穗子的父亲成了反动文人,何小曼的生父成了“右倾”。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常伴随着夫妻反目,甚至有激进的子女批斗父母的现象,更不要说普通朋友、同事的背叛了。荒诞的时代让人们人性中的恶膨胀到极点,而善被排挤。整个社会伦理道德沦丧,互相不信任,互相折磨,到处都充满敌意,充分体现了“他人即地狱”的哲学。萨特的戏剧《禁闭》表现了这一观点,针对人们对这句话的误解,萨特有过说明,大意就是:如果完全依赖他人,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变质,那么他人就是地狱。
刘峰天性善良,先公后私,即使备受打击,依然不改初心。他在前线受了重伤,被送弹药给养的驾驶员发现了,救上车,但驾驶员迷路了,问他去医院的路,他竟然带路先送补给,后来才去的医院。一条胳膊因此没了。如此英雄行为自然受到组织的嘉奖,给他带来荣誉,但他拒绝参加英模会,做报告。对于荣誉,他早已看淡。在和平年代,很多被遣散的士兵心生不满,聚众滋事。刘峰劝他们回去,被他们打了,看在刘峰也是当兵的,上过战场,失去了一条胳膊才放了他。为了生计,刘峰先到海南谋生,后又到北京打工。刘峰本来就处于社会最底层,离开军队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收入不多,又得了绝症。这个绝症应该属于偶然、意外,是盲目的命运造成的悲剧。但也可以说是必然,因为刘峰这样的好人其实是很难容于世的。
人们对主人公刘峰这个公认的好人的偶然之失大加批判,不是由于仇恨,而是由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当时的社会风气、组织原则。如果悲剧仅仅由于时代环境、政治运动、狭隘的观念导致人性中的恶充分膨胀造成的,那么时过境迁,人心向善,悲剧就可以结束了。只是雷锋式的人物已逝,美好的年华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英雄的悲剧
刘峰是好人,也是英雄。他在文工团时是学雷锋标兵、模范,走上战场后成了英雄。但由于他拒绝演讲,他的英雄事迹并没有广为流传。这是一个看淡了荣誉的真正的英雄。作为小人物,他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在贫病中度过短短的一生。
此外,何小曼因为救人也成了英雄,却很快精神分裂了。何小曼幼年丧父,随母改嫁,早早地体味了人间冷暖,在文工团也因为与众不同而备受排挤,因为渴望大家的温暖而装病,被调离了文工团,做了护士,奔赴前线,因为护送伤员而成了英雄典型,备受赞扬,她却得了精神分裂症。当她康复后,她找到她一直深爱的刘峰,只是刘峰将不久于人世,且并不爱她。两个善良的人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何小曼的一生也充满悲剧。
叔本华认为,悲剧表现人生的痛苦、不幸、灾难等。他把悲剧分为三种:一是恶人作恶;二是盲目的命运,也即是偶然和错误造成的悲剧;三是普通人之间由于地位和关系的不同而引起的相互对立、冲突,互相伤害,但又没有人是完全错误的。这些不幸从人的行为和性格中产生,几乎是人的本质造成的。叔本华最欣赏第三种。前两种稀有,不常见,可以避免;而第三种最多,几乎使悲剧不可避免。每个人都可能既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受害者,悲剧无处不在,人生即悲剧。在经历悲剧的痛苦折磨后走向生命的涅槃,从而得到彻底的解脱。由此可见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导致何小曼悲剧人生的没有大奸大恶之人,是偶然之失和盲目的命运所致,也有普通人之间的相互冲突与迫害。新中国成立后,国贫民困,还有一轮轮的政治运动。何小曼的父亲心地善良、好说话却被打成“右倾”,在外面抬不起头,在家里也毫无地位,众叛亲离。不能明辨是非的妻子随波逐流,不仅没有宽慰他,还雪上加霜,要跟他离婚。由于他工资降了,妻子让他连买个油条的钱都没有,他绝望中自杀身亡,留下四岁的小曼。亲生父亲不堪政治运动的打击和妻子的冷眼而自杀身亡,致使她小小年纪就经历了最亲最爱的人的离世所造成的痛苦。这是时代、社会的谬误所造成的,是偶然的错误,却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这个时候她已经记事,父亲的自杀及在她成长过程中的缺席让她过早地体味到人间冷暖。
她小小年纪就随母改嫁,成了众人眼中的拖油瓶,在继父家低人一等,留下深深的心理创伤。继父没有虐待她,但也不爱她。她也不爱继父,所以她后来又改姓生父的姓。继父没有错,她也没有错。她后来有了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连母爱也变得稀有,只有在生病时才能感受到,这使她很乐意生病。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日益边缘化,成了二等公民。她决定离开家,争取到文工团去做女兵。
但是,新的集体她也很难融入。在她成长的过程中,父爱的缺失,母爱的稀有,在家庭中的无足轻重,世人的冷眼等都严重影响着她的性格,让她形成了某些怪癖,以致被文工团的队友排挤。这些队友都是普通人,没有极恶之人,他们对她的排挤是因为她的另类,也因为人们的不宽容。因为太渴望集体的温暖,太渴望众星捧月的感觉,她装病。装病是一时的偶然的错误,是一个极度缺乏爱和关心的人的下策,事发后她被调离文工团,成了军区护士。她自愿上前线救死扶伤,因为目睹了太多死亡,以致心神恍惚。她本性善良,柔弱的双肩竟然能背起伤员,使她作为一个英雄而受到政府、媒体的关注。就在这关键时刻,她患了精神分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社会为树立英雄典型而故意拔高英雄行为的做法让正直的她无法承受,她不愿意一次次做报告,重复讲述被人添枝加叶了的她的英雄事迹,她想做真实的自己。不顾事实的虚假宣传让她承受不起,她不得不撒谎,她觉得她没有那么伟大,她离英雄差得太远。此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受到的精神刺激;二是由于战争,死尸遍地对她脆弱的心灵造成的冲击。
何小曼的婚姻也是悲剧。何小曼精神分裂不久,她的丈夫阵亡了。她康复后找到刘峰,两个人都是单身,却又并未真正在一起,只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她爱刘峰,但刘峰并不爱她,他一直深爱着他想象中的林丁丁。两个善良的人最终也没能成眷属。
综上,何小曼的悲剧成因是多方面的,父亲的自杀所导致的父爱的匮乏,母爱的稀缺,她的怪癖,队友的排挤,战争的刺激,假大空社会风气的影响等。既有她自身的小过错,更有社会、时代的原因。
三、婚姻的悲剧
小说中的几个人物没有一个婚姻美满的,全都以悲剧告终。刘峰所爱非人,他深爱着林丁丁,结果一表白就被拒绝了,还犯了错误被批斗,被调离文工团,去伐木连伐木。后来结了婚,媳妇跟人跑了。他同情妓女,试图感化妓女,让妓女从良,妓女还是故态复萌,两人分手,他从此孤单一个人。何小曼爱他,他心里敬何小曼,却不爱她。也许他对爱早已绝望,会爱的心已死。何小曼的丈夫结婚没几年就阵亡了,她爱刘峰却只能做他的红颜知己。她的悲剧是爱而不得,缘分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最难捉摸的,爱是无法强求的。
林丁丁的婚姻也是悲剧。还是文工团独唱演员的林丁丁看起来娇滴滴的,一派天真,很受人怜爱。她坦然地享受着刘峰对她的好,却从没想过刘峰爱她,以至于刘峰的表白吓坏了她。没想到像圣人一样的刘峰对她也有情欲,让她一时之间无法接受。她知道刘峰是个好人,一时冲动抚摸了她,在郝淑雯的要求下表示不向外说出去,还是架不住组织的询问招出了刘峰,导致他被调离文工团。她像大多数文工团女兵一样,梦想着给某位首长做儿媳,根本就不会考虑来自社会底层的刘峰。她后来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北京某军区司令的儿子,丈夫还很有出息。她由成都迁到人才济济的北京,就由原来的台柱子、独唱演员变成了小合唱演员;又由于电影的冲击,她们的表演次数日益减少,事业走下坡路,以至无事可干。她没有其他谋生技能,没有文化,也不思进取,天天窝在家里吃零食。她的婆家人——妯娌、小姑子、婆婆由于出身好、受教育程度高,都看不起她,联合起来挤对她,连她丈夫也不帮她,觉得她不给丈夫长脸,使她在家里备受排挤,无人认同。丈夫准备出国深造,婆家人以她没有陪读的资质为理由,逼迫她离了婚。为此,她找了个能带她出国的丈夫,随夫出国开中餐馆,因受不了中餐馆的劳累又离了婚,最终靠给有钱人家当保姆和家庭音乐教师而谋生,成了“劳动人民”。
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林丁丁的悲剧是由她自己的过失造成的。她的悲剧从内因来看,一方面在于她对于权势、物质的追逐,使她忽视了真爱;另一方面则是她的不思进取,不与时俱进,不学无术,不能吃苦耐劳造成的。外因则是时代的巨变、空间的转换使得她的演艺事业走下坡路,她与婆家人的差距拉大;还有等级观念,出身不同所造成的差距,她的不良习惯,她的文化素养等使得婆家人瞧不起她。从黑格尔的悲剧观来看,她婆家人和她的冲突没有对错,双方都有片面性。如果从叔本华的观念来看,她的悲剧是人与人之间基于位置而形成的对立与冲突,没有大奸大恶之人,只是婆家人都看不惯她这个闲人,希望她离开他们家。
郝淑雯的婚姻也是悲剧。她的父亲是空军首长,手下一个师的高射炮兵。郝淑雯本人又香艳性感,追者如云,却嫁了个“军二流子”。这个“军二流子”也是“军二代”,却不务正业,靠着特权,当兵不到部队去,在家开着吉普车到处乱窜。这个“军二流子”是个冒险家,趁着改革开放之机,到深圳闯荡,成了电子厂的老板,赚了大钱。当大家都转战深圳时,他又到海南进军房地产。成了有钱人后,就在外面花天酒地,包养小三,一再背叛淑雯。两人分了合,合了分,最终离婚收场。离婚后的郝淑雯很颓废,家里供佛,烟雾缭绕,像个小庙。依她的家境和容貌,她本来最容易获得幸福的婚姻,但还是婚姻悲剧。他们的婚姻悲剧,“军二流子”丈夫要负很大的责任,是主过错方,但她自身也有过失。她嫁夫随夫,放弃了对事业的追求,在丈夫眼里成了吃闲饭的。丈夫事业有成,而她并没有同步前进。而且身材发福,不再年轻貌美,对丈夫不再有吸引力。她当年择偶不慎,遇人不淑,没有注重对方的品行,以致婚内一再被丈夫背叛,最终落得孤单一个人。
醉酒后的她向萧穗子忏悔,她曾经勾引萧穗子的意中人,并鼓动他把萧穗子写给他的情书上交,让萧穗子被批斗,差点悬梁自尽,幸亏刘峰及时赶到,做她的思想工作,才救了她一命。她们感慨那是个背叛的时代,人们把背叛当正义。小穗子后来成为作家,也经历了婚变,婚变原因不详。
所有这些人最后都成了光棍,没有一个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的。其婚姻悲剧的原因也各式各样,既有自身择偶的盲目,也有时代的巨变造成的差距,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总体来说,就是所爱非人。
四、善与爱永存
小说的主人公好人刘峰以悲剧结局,其他人物也经历了种种挫折,生活不如意。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善良的,没有蓄意要谋害别人的恶人,却造成了别人的痛苦。悲剧似乎与生俱来,不可避免。但小说并不让人绝望,仍然给人以审美愉悦。
“在尼采看来,悲剧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快感,就在于能使人透过悲剧人物的毁灭瞥见那历万劫而不灭的永恒生命力。”[5]84尼采的悲剧理论建立在叔本华的理论基础上,但又与叔本华不同。尼采的悲剧理论与日神、酒神有关,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他认为生命的永恒是建立在个体毁灭之上的”,“现象界里万物变迁,生老病死,一切都被创造出来,又不可抗拒地被毁灭掉,在这不断的创造与毁灭过程之下,潜伏着的却是永恒的生命之流。众多的个体生命毁灭了,隐藏在它们背后的生命力却是不朽的”[5]82-83。
作为个体的刘峰去世了,但生命力永恒,善和爱永存。在荒诞的时代,人性恶膨胀时,人性善也没有泯灭。即使在特殊的年代,恶劣的社会风气下,依然有坚守做人原则的正义的人。当年集体批斗刘峰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有两个人没有参加,一个是萧穗子,一个是何小曼。前者是因为曾经给人写情书,被举报,被批判,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属于思想不健康的,根本没资格批斗别人。而且在她被人批斗心灰意冷,准备悬梁自尽时,刘峰救了她,并好言劝慰。此外,批斗刘峰时已经是1977年了,中国出现了很多新变化,她的视野早已不局限在他们生活的红楼,而关注更广阔的世界。也就是说,很有作家潜质、善于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萧穗子早已超越了那个特殊的时代。何小曼没有批斗刘峰是因为她在这个集体中是个另类,一直备受排挤,而刘峰在她难堪时帮过她,她知道刘峰的人品,她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不肯落井下石,表现了人性善。刘峰走时,只有何小曼去送他,她爱上了刘峰。
即使当年揭发刘峰、批判刘峰的文工团战友,在分开很多年以后,都没有忘记好人刘峰,并对当年批斗刘峰的行为进行了真诚的忏悔。时代在改变,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也在改变,开始反思当年的错误。萧穗子、郝淑雯相聚时就在自我批判,反思她们当年义正词严地对同志的出卖、背叛。当年拒绝并揭发了刘峰的林丁丁始终也没忘记刘峰的好,回国期间,与萧穗子、郝淑雯相聚时回忆刘峰的正直、善良。当年,林丁丁给好色的首长起了个不雅的绰号,传播开来,上级深究此事,人们一个个地把他人招出来,而刘峰宁肯自己担责任,也不愿把林丁丁招出来。何小曼、萧穗子、郝淑雯千方百计地寻找刘峰的下落,渴望与他重聚,郝淑雯借钱给他,萧穗子则是悄悄地送钱给他看病。何小曼找到刘峰,虽然没能成为他真正的女朋友,但至少是知心朋友,尽其所能地照顾他、帮助他,陪他看病,一直照顾他到生命的尽头,还为他举办了追悼会。刘峰虽然远去了,但他播种的善与爱永存。
五、结语
刘峰是个公认的好人、战斗中的英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其一生的悲剧既是好人的悲剧,也是英雄的悲剧,还是小人物的悲剧。何小曼早年丧父、中年丧夫,孤苦一人,是战争中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广为人知的英雄典型,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她的悲剧既有英雄的悲剧,也有婚姻的悲剧。林丁丁、郝淑雯、萧穗子等婚姻不幸。
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这些人的悲剧是由自身的过失造成的。好人刘峰也会犯错,由此造成了一生的悲剧。而何小曼被迫离开文工团也是由于她装病造成的。林丁丁的婚姻悲剧与她的功利的婚姻观有观。郝淑雯的婚姻悲剧是她盲目地选择了有人品缺陷的“军二流子”所致。萧穗子的被批斗是因为她盲目的爱,所爱非人。
如果从黑格尔的悲剧观出发来看刘峰、何小曼等的悲剧,则是无论个人还是组织,还是时代都没有错,但都有其局限性,所以才酿成悲剧。如果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来看《芳华》中人物的悲剧,则是当时的时代环境、激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造成的。从叔本华的观点来看,刘峰、何小曼等人的悲剧由偶然的错误,盲目的命运所致,也由人们之间的位置和关系而导致的冲突和对立所致。而后者是人性使然,所以无可避免。根据尼采的悲剧观,个体虽然毁灭了,但生命力永存。刘峰虽然远去了,但他的精神永存。
综上所述,《芳华》小说中有好人的悲剧、英雄的悲剧、婚姻的悲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自身的过失,偶然的因素,盲目的命运,人与人之间基于位置而形成的对立冲突,人性恶以及由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等所形成的时代的风气等等。但人性本善,爱一直在人们心中,无论有多少悲剧都不能让人们绝望。所以,《芳华》虽然描写了很多悲剧,还是一部充满阳光的、温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