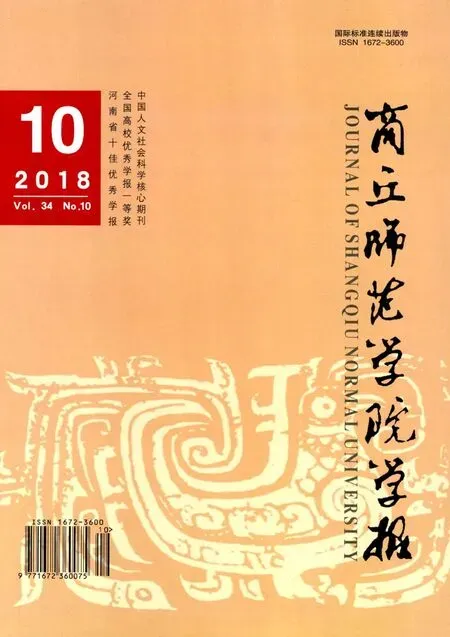论西游武术意境之“空”的美感体验
2018-04-03安汝杰
安 汝 杰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当代美学存在着现代时间美学与后现代空间美学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审美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分裂。应该在时间性与空间性统一的基础上,建设新的美学体系,从而走出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对立格局。”[1]38因此,《西游记》的“美学言说”要向“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中国古典空间美学”汲取灵感,因为“中国古典空间美学还没有发生时间与空间的对立,时间性融合于空间性中,从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1]38。同时,“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其实践基础是艺术活动。中华美学的实践基础是空间性的艺术活动”[1]33,“中国的庙堂不是高耸入云指向天堂,而是以生气灵动通向审美。苏州园林山重水复,在平面上建构了一个审美空间。同样,中国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最终指向审美,具有古典的审美主义倾向,如饮食成为美食(讲求色、香、味),住所成为美居(园林化),书法成为艺术,武术成为舞术,甚至宗教也走向审美,如寺庙多在名山大川,佛像也变成美丽的观音”[1]33。“武术成为舞术”是“中国古典空间美学”进入西游武术的“审美话语”的“契机”,不仅如此,武术本身就具有“空间美学”的质素。《西游记》第五十一回《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中,孙行者赤手空拳对敌“独角大王”:“这大圣展足挪身,摆开解数,在那洞门前,与那魔王递走拳势。……仙人指路,老子骑鹤。……盖顶撒花,绕腰贯索。迎风贴扇儿,急雨催花落。妖精便使观音掌,行者就对罗汉脚。长掌开阔自然松,怎比短拳多紧削?两个相持数十回,一般本事无强弱。”[2]687孙行者迈开拳势,“武步”中有“仙人指路”“老子骑鹤”等招式,这本身就是一幅西游武术的“空间美图”,其中不断生成着美的“武术意象”,是“武术成为舞术”的“典型个案”,是《西游记》中“武术成为舞术”的个中玄机。正如宗白华所说的:“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无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3]310然而,在当今中国小说美学的话语系统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美学言说中,“言说者”仍然久久沉浸于“天人合一”的“唯美妙境”中“喜悦已极”,令人遗憾的是,很少有专文论述《西游记》中武术意境之“空”的美感体验,这正是本文的写作“机缘”。
一、因缘生法与武术意境之“空”
《西游记》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中,孙悟空向菩提祖师学习“筋斗云”的轻身功夫。“悟空弄本事,将身一耸,打了个连扯跟头,跳离地有五六丈,踏云霞去勾有顿饭功夫,返复不上三里远近,落在面前”[2]21,菩提祖师说:“这只能算是爬云,不是腾云。”于是“悟空又礼拜恳求,祖师却又传个口诀道:‘这朵云,捻着诀,念动真言,攒紧了拳,对身一抖,跳将起来,一筋斗就有十万八千里路哩!’”[2]22经过反复操练,“这一夜,悟空即运神炼法,会了筋斗云。逐日家无拘无束,自在逍遥此一长生之美”[2]22。孙悟空的轻身功夫已由“与人家当铺兵,送文书,递报单”的实用技术变成了“武的艺术”,在武之艺术的审美空间中,悟空“去时凡骨凡胎重,得道身轻体亦轻”[2]23,是以能“自在逍遥”,享得“长生之美”。
《西游记》第三十一回《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中,唐僧师徒于宝象国遇难,唐僧被黄袍怪点化为一只斑斓猛虎,使肉眼凡胎的宝象国国王相信唐三藏才是真正的妖魔,紧急关头白龙马与黄袍怪斗法,无奈敌抵不过,于是劝偷懒归来的八戒去花果山请回悟空行者来救师父之难,八戒“义激猴王”,孙行者前来降妖。“这一场在那山顶上,半云半雾的杀哩:大圣神通大,妖魔本事高。这个横理生金棒,那个斜举蘸钢刀。悠悠刀起明霞亮,轻轻棒架彩云飘。往来护顶翻多次,反复浑身转数遭。……猴王铁棍依三略,怪物钢刀按六韬。……猛烈的猴王添猛烈,英豪的怪物长英豪。死生不顾空中打,都为唐僧拜佛遥。”[2]409-410《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到第三十一回《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一连四回讲的是唐僧师徒“宝象国遇难”,遇难开始于唐三藏于黑松林走失,而在悟空看来黑松林的“树林从视觉上看中间是空的,林中可能横着一条小径,也可能根本没有路穿越其间。不过或许用‘空林’一词是因为,即便有路却也是人迹少至,飞禽走兽亦远离了,使人体会到:人禽只是树林的过客,树林本来是‘空’的。如果不是实体空间上的空虚,那么只能理解为是人把林看‘空’了”[4]183-184。作为武之圣者的孙行者是否认为“空林”是“实体空间上的空虚”不得而知,但他至少是把松林“看空”了,以至于空诸所有,因此,悟空与黄袍怪在武斗时进入庄子所谓的“忘”的境界或者说是为慧能《坛经》所称扬的“无住”“无念”“无所系缚”的境遇,“一心西行参佛面,死生不顾空中打”。很显然,在松林的审美空间中,“空”除了有“审美客体”(武术自身)的特征外,更为重要的是“审美主体”(孙悟空)对武术的“本性”由于“无所系缚”而倾注了“诗性观照”,进而催生了西游武术的“美感体验”。
西游武术本性“空”,因为西游武术是假合因缘所成之“法”。“诸法皆因缘而产生、存在、变化、灭亡,自身没有常住不变的自性或主体;没有自性,就是‘空’,或曰‘自性空’、‘性空’。”[5]12西游武术以“舞”的形式活跃于孙悟空修道学艺的“审美空间”,不仅令他掌握了日后保护唐僧西行取经的“实用技术”(降妖伏怪的实用武技),同时也给“紧张”[注]因百回本《西游记》中只一回集中写悟空学艺,因此从孙行者的武艺在取经途中的重要性及学艺所占的篇幅来看,不可谓不“紧张”,若不是有随之而来的西天取经的中心任务,悟空学艺实可以大书特书,不必吝啬笔墨。修武学艺的孙行者带来“美的体验”。孙悟空的轻身功夫来源于第二回中菩提祖师授予他的“真言”,因祖师为花果山天产石猴取名为“悟空”,这真言也必与悟“空”,即悟得“空”的教义有密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是以其为终极目的。孙悟空的武艺就是要“命中注定”地与各色妖魔斗法,因此客观上存在着武技的双向传播,而大闹天宫的壮举无疑给善于降妖伏魔的孙行者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和临敌时的自信心,一时略占上风的武艺高强的妖魔最终落败无不证明唐三藏对于妖魔实力的估计是过高的。而对于难料生死的唐僧师徒而言,紧张后的放松,自然会“月明风清”,也自然会“柳暗花明”,因此也附带有一种独有的“美的体验”,而这美的体验在《西游记》中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西游武术的意境之美从空中而来又终归要到“空”中去。
“万法性空”即“宇宙实相”。西游武术意境的审美空间中并不存在“常住不坏”的“实体”,也没有属于“本体”的“空”的“存在”,“空”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假名”,在“因缘”所生的西游武术意境中“显示”此法的“空性”。大乘沙门龙树持“缘起性空论”,并指出世间万象无不是因缘所生之“法”,本来是“空”的,这种空是“自性空”“本来空”。龙树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6]13“因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6]41“因缘生法无自性,无自性即是毕竟空。”[6]987这就是说,西游武术意境是“缘生诸法”“本来性空”“但存假名”。
二、由虚而空与武术意境之自性
“缘生诸法”的“缘起论”是佛教对空间诸“现象”的根本“识见”,武术意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待缘而起”,本身受到练功场地、当地物候等“空间审美”的诸种条件的“制约”。《西游记》第九十五回《假合真形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中,孙行者识破天竺国公主为妖邪所变,为降妖除魔,行者与妖斗法,妖邪远非孙行者的对手,屡次在对决中化阵清风逃走,于是孙行者唤出当坊土地山神询问妖邪的住处。“寻至绝顶上窟中看时,只见两块大石头,将窟门挡住。土地道:‘此间必是妖邪赶急钻进去也。行者即使铁棒捎开石块,那妖邪果藏在里面,呼的一声,就跳将出来,举药杵来打。’”[2]1279妖邪“主场作战”。初来乍到的孙行者不得不暂时略处下风,被早有准备的妖邪“举药杵来打”。释尊有言:“若有此则有彼,若无此则无彼,若生此则生彼,若灭此则灭彼。”[7]562“若见缘起便见法。”[7]467“诸法的本质是空无自性的,所以本身并没有什么生灭可言,无论是有、无、非有非无还是亦有亦无,最终都要归结到绝对的‘空’上。”[8]24“空宗认为宇宙间纷然杂陈、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是由因缘生起,由此也是空的。这是承认世界上的事物存在着普遍联系,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同时又由此推论出事物无实体、无自性,即空的结论。”[9]59这里的“性”指“自性”“法性”,是不待“因缘”而“自有”的,而西游武术意境是从“因缘”生,故其“自性”不可得,其“自性”也因此为“空”,是为“性空”。
“空”自何来?答曰:由“虚”而“空”。“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10]151-152此即“明自性”。如果西游武术意境的“审美空间”中缺少了“审美主体”(孙行者等佛门弟子)对于“武之自性”的“澄明”就无法“寂照”其“空性”,也难以在习武练艺的实践中产生“美”的体验。《西游记》第八十八回《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母授门人》中,唐僧师徒来到天竺国玉华县,行者兄弟为王子演练武艺,只见沙和尚“双着脚一跳,轮着杖,也起在空中,只见那锐气氤氲,金光缥缈,双手使降妖杖丢一个丹凤朝阳,饿虎扑食,紧迎慢挡,捷转忙撺。……真禅景象不凡同,大道缘由满太空。金木施威盈法界,刀圭展转合圆通。神兵精锐随时显,丹器花生到处崇”[2]1189-1190。玉华王见行者兄弟武艺不凡,央求传授小王子武艺,行者兄弟欣然答应,“就在筵前各传各授:学棍的演棍,学钯的演钯,学杖的演杖。虽然打几个转身,丢几般解数,终是有些着力,走一路,便喘气嘘嘘,不能耐久;盖他那兵器都有变化,其进退攻扬,随消随长,皆有变化自然之妙,此等终是凡夫,岂能以遽及也”[2]1193。然“终是凡夫”的玉华王子虽“师出名门”,但拜师如未拜一般,依旧是“大的个拿一条齐眉棍,第二个轮一把九齿钯,第三个使一根乌油黑棒子,雄纠纠、气昂昂”[2]1188,因其武艺还未融入所授的佛门功夫中来,还未显出“真禅景象”,虽有貌似形肖的“金箍棒”“九齿钉耙”和“降妖宝仗”,也终归是庙堂上的“仪仗”,实不过摆设而已,可谓“诸般兵器在,武未入虚境”。
“虚”如何做到?答曰:“坐忘”与“去知”而至“忘”,忘是精神的逐渐“超升”,旨在达至“自由自在”的“忘境”,“忘”则“虚”。庄子主张要“外求无物”“内求无我”,摆脱“形骸”与“智巧”的“束缚”,此即“坐忘”。“去知”则是要摆脱“心智巧诈”的干扰,祛除违反“自然本性”的“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11]192。由此可知,《庄子》中的“忘”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空掉一切”,不是将“空”置于“顽空”的“境地”,也不是“毫无偏见”地“否定一切”“绝不肯定”,而是始终把“自性”与“境界”作为“实存对象”全身心地加以“求证”,以求在“审美空间”中达到的“忘境”,从而臻于“空”。
《西游记》第六十一回《猪八戒助力败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中,孙行者二调芭蕉扇均未成功,有些气馁,在土地“但说转路,就是入旁门,不成个修行之路”的劝告下,“行者发狠道:‘正是正是,呆子莫要胡谈!土地说得有理,我们正要与他:赌输赢,弄手段,等我施为地煞变。自到西方无对头,牛王本是心猿变。今番正好会源流,断要相持借宝扇。趁清凉,息火焰,打破顽空参佛面。行满超升极乐天,大家同赴龙华宴!’”[2]819这正道出了牛魔王的“本来面目”,“牛王本是心猿变”,因此他也有七十二般变化之功,变天鹅、黄鹰,又变而为人熊,终不离大白牛的原身。孙行者与牛魔王武斗,“惊得那过往虚空一切众神”前来助战,牛魔王用角去触天界救兵李天王父子。“哪吒取出火轮儿挂在那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焰焰烘烘,把牛王烧得张狂哮吼,摇头摆尾。才要变化脱身,又被托塔天王将照妖镜照住本象,腾那不动,无计逃生,只叫‘莫伤我命!情愿归顺佛家也!’”[2]823-824摩云洞“花放一心如布锦,八节四时颜不改”,孙行者、哪吒与牛魔王武斗的场景也是西游武术意境中的奇观,在这诗意的禅境中,牛魔王也终于在其已入佛门的结义兄弟孙悟空的武斗“点化”下,觉知一身“牛力”终归空,于是情愿归顺了佛家。
三、境与象谐与武术意境之美
“空间意味着奠基于身体性存在的整体性世界,虚拟技术所创建的数字空间可以看作是由人与技术之交互作用所指向的一种整体性空间现象,这种空间根源于由人的感知方式和运动方式及主体间的相互关联所产生的具身体验。”[12]128这种“数字空间”的“具身体验”与武术意境的“审美空间”的生成“理为一贯”。同时,“主体、空间和审美三者之间的关系正是以‘体验’的方式连接,对于空间的感悟也正是通过体验的方式赋予主体性的色彩”[13]128。武术意境的“境中藏象”的审美特征决定了其“审美空间”的建构活动是一种主体的“感性实践”方式;武术意境作为“武术之象”的“物化”内在地包含着武者的美感体验;体验以一种“梵我不分”“月印万川”的方式通达“本心”,“审美主体”也在镜花水月般的武术意境中体悟“境与象谐生空境”的美感。
西游武术意境是基于孙行者等佛门弟子等武者习武、用武经验的“武术意象”在审美空间中形成的空灵的“物化之物”;《西游记》中的“武术意境”赖武者、空间等“因缘”而成,是武术的“意象组合”,其“自性”为“空”而具“空蕴”,是名“空境”。其中的“武术意象”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武者”建构“武术意境”的“信息媒介”,它“直觉性”地根据以往的“武术经验”来布置“武术意境”的“细微结构”,把自在的“清风明月”吸收为“武术意境”自身的“空间美质”,把肢体的一动一静“凌空”建成美的“空间造型”。
《西游记》第四十回《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归木母空》中,孙行者向山神、土地问清了红孩妖的来历,“三兄弟各办虔心,牵着白马,马上驮着行李,找大路一直前进。无分昼夜,行了百十里远近,忽见一松林,林中有一条曲涧,涧下有碧澄澄的活水飞流,那涧梢头有一座石板桥,通着那厢洞府”[2]539。唐僧师徒又来到一个“洞天福地”,然“善恶一时忘念,荣枯都不关心。晦明隐现任浮沉,随分饥餐渴饮。神静湛然常寂,昏冥便有魔侵。五行蹭蹬破禅林,风动必然寒凛”[2]543。唐僧不听火眼金睛的孙行者的良言相劝,于此“清明之地”落入红孩儿之手。孙行者在红孩儿的火云洞前,向其讨要师父,无奈红孩妖不与,二者斗在一处,“一个横举金箍棒,一个直挺火尖枪。吐雾遮三界,喷云照四方。一天杀气凶声吼,日月星辰不见光。语言无逊让,情意两乖张。那一个欺心失礼仪,这一个变脸没纲常。棒架威风长,枪来野性狂”[2]545。孙行者的“主体性”已经是完全“物化”在“金箍棒法”的武术意境中,从而形成了“凌空飞行”于武术意象的“审美空间”,西行途中的“辛苦遭逢”“世事沧桑”及曾经的“比武经验”都“遇缘而空”,并且在对“空间”的“审美体验”中通达“神游万物”的“至境”,因此,孙行者与妖斗法的每一次用武均无旧轨可循,便如大诗人灵感到来,作出了一首好诗一般。而诗画同构并通于武,“其绝人处,不在得真形,山水木石,烟霞岚雾间。其天机之动,阳开阴阖,迅法惊绝,世不得而知也”[14]312。
唐代大书家张旭见公孙大娘剑器舞而悟笔法,而“反其意,通其理”的“见画之用笔法而悟剑法”也别有一番“境界”。孙行者看似与红孩妖“斗在画中”,画中但见:“回銮古道幽还静,风月也听玄鹤弄。白云透出满川光,流水过桥仙意兴。猿啸鸟啼花木奇,藤萝石蹬芝兰胜。苍摇崖壑散烟霞,翠染松篁招彩凤。远列巅峰似插屏,山朝涧绕真仙洞。”[2]543实则是孙行者在“以身试武”,也是在以金箍棒劈斩舞动之“象”悟武之“空性”。象者,道之迹。“然道虽有气动,犹是无中生有;有而不以弱养之,则不能反于虚无之天,道又何自而成乎?人第知一阳来复乃道之动机,而不知反本还原,有象者仍归无象。盖有象者,道之迹,无象者,道之真也。”[15]111“当大道未成未盈之时,不无作为之迹,犹有形象可窥,觉得自满自足,不胜欣然。及至大成之候,又似缺陷弥多,大成反若无成焉;大盈之余,又似冲漠无状,大盈反若未盈焉。”[15]124《西游记》中孙行者的武技不是“凡技”,不是“常技”,而是借“象”以入“道”之技,入于“空境”则谓“境与象谐”。
四、即境悟空与武术意境的美感体验
“因缘和合”“刹那生灭”,如何“超脱”,如何“诸缘灭尽”,“空间”如何是“无空间”?空间之中,物无“不变”,无物恒常,空间虽“有”,却非“真有”,空间的“流转”是“境”之“幻相”,甚至空间的“念头”也是转瞬即逝,武者如何“应对”?六祖慧能的《坛经》讲到“无念禅法”时,要求“不染诸境”(“于一切境上不染”“于自念上离境”),要求在一切“境界”上都不起“妄想”,也有“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的要求,可见这里的“境界”即“觉悟境界”,是悟得“空性”的“境界”。“境界”从“诸根”起,所谓“诸根境界”:“身觉种种触,善能分别触,不随分别起,触中得到自在,触中得解脱触尘三昧足。”[16]10(神会《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这即是说,一切“色”对于武者的“清净本性”来说就是“尘”,武者能够在诸种“色”的“包围”中获得解脱,这是一种“自空”的境界,并且“空”也“即此境而空”,而“此境”即“无自性”的审美空间。
尊我斋主人在《少林拳术秘诀》中说:“以入定为功,而后性静心空,脱离一切挂碍,无挂碍则无恐怖矣,无恐怖则神清,神清则气足,气足则应变无方,随机生巧,如是而后明于法而不拘于法,沉其心而无动其气,斯道至此,始可告大成矣。”[17]59西游武术作为孙行者兄弟“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被纳入到学佛修禅的形式中。修习西游武术的主体是禅者,禅心运武,透彻佛性,内心无畏无碍,外现大仁大勇的般若智慧。禅,赋予了西游武术更为丰富的内容,也使西游武术更具空蕴。《西游记》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中,孙悟空向菩提祖师学习腾云的“轻身功夫”,“祖师道:‘凡诸仙腾云,皆跌足而起,你却不是这般。我才见你去,连扯方才跳上。我今只就你这个势,传你个筋斗云罢。’悟空又礼拜恳求,祖师却又传个口诀道:‘这朵云,捻着诀,念动真言,攒紧了拳,对身一抖,跳将起来,一筋斗就有十万八千里路哩!’”[18]18对此,黄周星评道:“才是个心。”[18]18“朝游北海暮苍梧”的轻身功夫的练功要诀是,“心如明镜,性若止水,空诸万物”,否则“腾云驾雾”就会变成“踏尸蹶步”[19]540。如若“心为念缚”,不能“灭诸万缘”“空诸万境”,则只能是身子重如顽石,离地不满半尺即落下,更不能“一筋斗行十万八千里”。
“修炼之士,幻名、幻象、幻景、幻形,须一笔勾销,毫不介意,如此知止知足,常养灵丹,则止于至善,永无倾颓矣。”[15]123“究何状哉?空而已矣。空无不同,一物通而物物皆通;空无不明,一物明而物物俱明。”[15]119“圣人之心,空空洞洞,了了灵灵,无物不容,却无物不照,如明镜止水,精光四射,因物付物,略无成心,何其明也?”[15]133如何悟“空”?“外观其身,身无其身。远观其物,物无其物。空无所空,无无亦无。”[15]170《西游记》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中,孙悟空学艺归来,一日梦到阎罗王差“索命鬼”来勾魂。“美猴王顿然醒悟道:‘幽冥界乃阎王所居,何为到此?’那两人道:‘你今阳寿该终,我两人领批,勾你来也。’猴王道:‘我老孙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已不伏他管辖,怎么朦胧,又敢来勾我?’那两个勾死人只管扯扯拉拉,定要拖他进去。那猴王恼起性来,耳朵中掣出宝贝,幌一幌,碗来粗细,略举手把两个勾死人打为肉酱,自解其索,丢开手,轮着棒打入城中。唬得那牛头鬼东躲西藏,马面鬼南奔北跑。”[18]29-30美猴王轮棒将“勾死人”打为肉酱,其所用的招式不得而知,从其“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说辞来看,此次轮棒是将幽冥界、森罗殿等幻名、幻象、幻景、幻形,一笔勾销。之所以能够“一笔勾销”,这不仅是由于幽冥界对于悟空而言是“虚设”,是“空无”,也是因为他成功阻止冥府索魂的手段即武艺本身是空的,而唯独曾拜菩提祖师的美猴王悟得此“空性”,此即“悟彻菩提真妙理”,这也无怪乎“‘隐身化形’‘飞行绝迹’等技艺更为其所擅长”[20]65。
“朱子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此言道心人心,瞥眼分明,于此持志养气立教,割断牵缠,诞登彼岸。”[15]186朱熹所说的“鉴”就是用来“鉴照”境的,而《西游记》中的境典型的如第二十回《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中的“花尽蝶无情叙,树高蝉有声喧。野蚕成茧火榴妍,沼内新荷出现”[2]255;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中的“焰焰斜晖返照,天涯海角归云。千山鸟雀噪声频,觅宿投林成阵。野兽双双对对,回窝族族群群。一钩新月破黄昏。万点明星光晕”[2]175;第十五回《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中的“涓涓寒脉穿云过,湛湛清波映日红。声摇夜雨闻幽谷,彩发朝霞眩太空。千仞浪飞喷碎玉,一泓水响吼清风。流归万顷烟波去,鸥鹭相忘没钓逢”[2]187;等等。“‘境’是习武修禅者体验世界的诸多‘窗口’,而真实不妄的‘境’是对空的‘寂照’。”[21]30“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原来共一家。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断除烦恼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世事随缘无挂碍,涅槃生死等空华。”[15]191“唯清中有光,净中有景,不啻澄潭明月,一片光华,乃得清净之实。若有一毫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之意,便是障碍。所以学道人,务使心怀浩荡,无一物一事,扰我心头,据我灵府,久久涵养,一点灵光普照,恍如日月之在天,无微不入焉。”[15]65
五、结语
意拳宗师王芗斋在其散佚的《拳意正轨》中论“桩法换劲”时道:“欲求得技击妙用,须以站桩换劲为根基,所谓使其弱者转为强,拙者化为灵也。若禅学者,始于戒律而后精于定慧,证于心源,了悟虚空,穷于极处,然后方可学道。禅功如此,技击犹然。盖初学时桩法频繁,如降龙桩、伏虎桩、子午桩、三才桩等。兹去繁就简,采取各桩之长,合而为一,名曰浑元桩,利于生劲,便于实搏,精打顾,通气学,学者锻炼旬日,自有效果,亦非笔墨所能表其神妙也。”[注]见其弟子姚宗勋1963年于北京兴盛胡同二十八号西屋整理的未刊本《拳意正轨》第40-41页。“拳”在“意”中,“道”在“心”中,拳法、桩法皆因悟起,对于孙行者等武者而言,在“非笔墨所能表其神妙”的“妙悟”的状态中,“心境都空”“触目皆缘”,“黄花观”“演武堂”“翠云庵”无不是“法身般若”,在此“审美空间”中“武之自性”自在“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