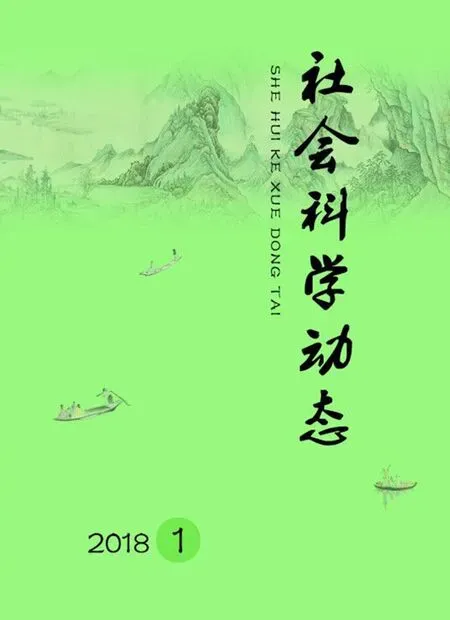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研究
2018-04-03江国华庞羽超
江国华 庞羽超
引言
法律制度的 “设计者”或 “立法者”通常聚焦于制度设计的任务是否完成,而较少关注其所设立制度的实施效果。法律制度作为强制性偏多的刚性制度,其废立、变动、发展,不仅需要上位者的认可,也有赖于全社会的支持,故而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检验、测评,理应是法律制度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其在实际中却处于缺位状态。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阶段是整个过程的源头,也是关键,其成功与否、效能如何直接影响到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质效。现行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触发方式复杂多样、紊乱失序,亟待规范、整合。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触发既不应是权力主导者凭主观意志或稳定需要临时性、刻意地、有选择地挑选某一方面法律制度进行的 “试验”,也不应是民粹主义者将个人利益与体制需要 “捆绑”,而应当是以制度完善为前提的常态化反应,以了解、获知法律制度运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效校正制度性障碍。
目前,直接以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为课题的研究在域内外均处于空白状态,但与其相关的 “立法后评估”、 “法律评价”、 “立法评估”等近似、类似的综合研究却不少见。英美等国的国家制度具有十分浓厚的行政主导特点,各项法律制度往往通过 “行政法案”、 “总统法令”、 “地方政府条例”等形式执行,故域外国家类似研究也往往以 “公共决策”、 “公共政策”、 “政府绩效”等为切入口,通常为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综合性论述,例如尼古拉斯·亨利的 《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①、伊维特·韦顿的 《Public Policy and Program Evaluation》②、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的《Regulated Industry in a Nutshell》③均是以公共政策、行政规章为切入口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及其触发、启动过程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论述。我国类似论述则兼具综合性和过程性,最为常见的是以 “法律实施效果评估”、 “立法后评估”、 “法治评估”为切入点的研究,如钱弘道等人的 《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④、陈书全的 《论我国立法后评估启动的常态化》,他们从评估依托、启动过程、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环节对立法后评估、法律实施效果评估等类似概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论述。
直接以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为课题的研究一是可以丰富立法学研究的视野,将法律制度相关立法学研究置于一个更完整、更开阔的视野中;二是亦可为域内法治实践提供借鉴,通过概念解析、实例引证等方法,综合判别过往、当今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当前实际提供可资借鉴的意见,进而建议制度设立者结合国情、社情进行调整和修改法律制度。
一、基本概念之诠释
“法”作为一个秩序性概念,时常被作多种解释,且其颇具包容性的范畴又衍生了众多差异性概念,作为承载其主要意义的 “法律”以及衍生的“法律制度实施”与 “法治”、 “法律实施”等概念看似一致,却又存在不同。厘清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概念边界,对于探究其触发模式、摸索其触发机制十分重要。
(一)“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解释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概念衍生于 “法律制度”,其与 “法律制度”存在着天然的因果关系,在梳理其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其前置词语作比较辨析。
1.“法律”与 “制度”的概念
“法律”是指由国家确立的行为准则,是对全社会普遍约束力的规范⑤,在成文法国家其最明显的特点即有国家机关认可或确立。 “制度”原指具有相对刚性的、具有规范社会状态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有目的的建构状态,也是相对于法律更为宽泛、松散的概念。
2.“法律制度”的概念
“法律制度”将 “法律”与 “制度”两者组合在一起,其意义却更加宽泛,通常指国家或地区所有法律原则、规则及其衍生政策的总和。从宏观而言其可以指一个政权架构的基本制度的方式及其核心执政理念,以及其希望形成的社会制度基本模式,例如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即是执政党希望建立的法律制度架构。从微观而言, “法律制度”可以指某一系列或某一项法律及其衍生政策所形成的系列行为准则⑥,既可以指宪法方面的法律制度,例如政权的组织形式、法律废立方式等;亦可指经济方面的法律制度,例如盈利性法人的建立准则、市场规制方式等;也可以指诉讼法律制度,例如审判机构审级设置、司法从业人员准入要求等。
3.“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概念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顾名思义就是法律制度的执行结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制度亦不外如是,虽然其执行的出发点始终围绕制度设立的目的,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部分风险因素的不可控性,可能导致法律制度实施结果与设立目的不一致,其结果虽然较大概率是与设立目的相吻合,但却有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二)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解释
“评估”,从语义上讲与 “评价”、 “评定”、“评议”等词接近,有学者曾主张将其理解为 “测量”和 “评价”⑦,这样既有定量的梳理、也有定性的分析,最终得出综合的结论。从这个语境理解“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就可以将其视作根据必要的标准或要求去判断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重点考察其与设立目的、社会需求的符合程度,及制度内部诸要素和环节的功能状态。
1.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内容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内容主要针对合目的性、合社会需求性两方面。就和目的性而言,是考察法律制度实施效果与法律制度设立初衷的相符程度,即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而不考虑这一设立目的性质;就合社会需求性而言,是考察法律制度施行效果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程度。此外,法律制度内部的和谐性、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非结果性的负面因素也应纳入评估的内容。
2.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时间
通常,法律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即便是设定了 “试行期”、 “考察期”,其评估时间也不可能提前至制度实施前,否则就是预评估、拟制评估,而非对实施效果的评估。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法律制度尤其是以政令或类法律政策为主要实施依据的法律制度 (如全国人民法院、检察院系统的司法体制改革),在最开始 (如上海、重庆、湖北等第一批司法改革试点省市)选择了边实施边评估的方式⑧,仍然需要勘察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的状态,只不过这 “一段时间”较短罢了。
3.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成果
就评估结果而言,可能会引起法律制度的变化。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并不必然引发回馈,即对制度的修订或更新,而从评估的初衷不难发现,问题导向是评估的核心意义所在,设定评估就是假设某一法律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可能存在问题。例如政权更迭之后,新政权通常会对旧政权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如北洋政府对 《大清新刑律》《法院编制法》等法律制度进行评估,并修改后予以沿用。
(三)“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解释
“触发”是一切事物启动的源头,对于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而言,由谁触发、以什么样的方式触发都直接关系到触发的效用和意义。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就是触动法律制度实施效果开展的具体路径。
1.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具体内容
就具体范畴而言,触发机制应当包含触发主体、触发时间、触发条件、评估对象等几个方面。触发主体是指由谁来触发整个评估,而触发主体应当是在整个触发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主体,而并不非得是对评估启动有最终决定权的人;触发时间是指评估过程最终启动的时间,其可能是通过 “条件预设”等方式确定,也可能是因突发事件而随机启动;触发条件是指达到什么标准启动评估;评估对象是指评估的标的,可以是某项法律法规及其衍生的法律制度,也可能是一系列法律法规支撑的一整套法律体系,甚至有可能是整个制度框架体系。
2.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触发动因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决然不是因 “立法后”时代来临而有的新鲜事物,而是自法律制度产生那一刻就常伴其左右的事务,其触发、启动往往伴随着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放大、扩散,这些问题即为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触发动因。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不合政治需要。政治层面的变革往往会带来局部或整体性的国家制度更迭,在这一过程中执政主体必然会根据政治需要对法律制度进行审视,对其执行、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回望,符合当前执政需要者就予以保留,不符合者予以废弃。如民国初期,时任司法总长的伍廷芳、法律编查会副会长兼署大理院院长的董康等人对 《大清新刑律》实施效果进行的评估⑨。(2)不应社会现实。法律制度在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现实时,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在法律制度继续实施的过程中被放大、扩散,引起执政主体对其的关注和重视,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3)偏离设立目的。法律制度施行、发展过程中会因各类因素而影响法律制度设定目的的实现,进而需要对法律制度一定时期内的实施效果进行重新审视。如汉武帝时期设立的 “刺史”、“巡抚”等职本为中央政府出刺各地的巡视、巡察官⑩,目标是澄清吏治,但因中央集权的弱化,这些巡察官最终都演变成为地方最高长官,进而触发后继政权对监察官制度的重新审视和评估。 (4)引发法律冲突。任何法律制度都会经历一个由少到多、由缺位到完备的过程,在法律制度确定、实施过程中,总会出现因修订不及时,设立时考虑不周而出现的法律制度间的冲突,或是上下位之间的冲突、或是同位阶的冲突。就目前的 “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⑪而言,法律制度制定主体数量众多,从全国人大直至较大市的政府都有一定立法权限,不同部门间所确定的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这种矛盾和冲突一旦出现,就会大概率引发立法主体或其上位机关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审视,触发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
3.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演变趋势
法律制度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也不外如是。近年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触发机制逐渐规范化并走向制度化,其演进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触发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从上海、山东、云南各地的实践⑫不难看出,早期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很大程度上由立法机关触发,触发主体较为单一。而2012年以后,大至对单项现行法律制度的评估、小至对某单一性法规的评估,都引入了更为多元、广泛的主体,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党组织的参与,这一方面以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为标志,将统揽包含法律制度改革在内的改革引导权移交给党委。另一方面,民众日益提高的政治参与热情也让他们成为了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的主体,逐渐破除了 “权力惯性”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的垄断,当这种热情上升为对当前法律制度不满的群体性意志,评估触发就呼之欲出了。 (2)评估对象:由特定向非特定转变。2000年,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托其法制委员会对 《山东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权益保护条例》⑬等地方性法规进行了评估并在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2012年至2013年,中共中央政研室会同中央政法委针对当时审判工作体制、检察工作体制进行了评估,进而开展了饱受争议的司法体制改革;2013年底至2014年,中共中央政研室又会同中央纪委研究室对当时纪检监察体制进行了评估,进而又启动了以 “压紧各级党委反腐主体责任”、 “派驻机构权力上收”、 “巡视全覆盖”为重点内容的第一轮纪检监察体制改革⑭。纵向比较不难发现,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对象由地方性法规扩延到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又由单项法律及其衍生的法律制度扩延到某项由多个法律架构成的法律制度,评估对象的范围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 (3)触发时间:由不规律向规律转变。从最初的以修改法律为目的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看,触发时间在某项法律实施数年后、乃至十几年之后,例如《云南省邮政条例》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其面临的首次实施效果评估在2004年。之后多次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虽然施行与触发之间的时间差日益缩短,但因评估触发体制的缺位,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性。而近年来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时间基本稳定,大多采用了边试点、边评估,或先试点、后评估的触发方式,其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添加了更多的 “预设”的色彩,目的性更加明确,也更具规律性。例如2013年后,浙江省相继开展的 “登记制度改革”、 “审批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均在改革方案下发的同时设定了评估的方式和方法。 (4)触发条件:由合法性向合科学性转变。2000年以前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触发条件多以合法性为主,即主要审查是否违法,这多数是因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而引起了上位法、同位法的变化,而评估对象尚未作出适当调适,如 《山东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权益保护条例》修改的目的是对应1999年宪法修正案对经济制度界定的调整。随着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发展,其触发条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对象是否科学,即是否符合社会需要、公众期许、内部和谐等标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 (白皮书)⑮,展现了非常明显的 “公众倾向”,其对实施效果的评估主要以 “是否从回应人民群众最迫切的司法需求做起”、 “是否从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改起”、 “是否解决了 ‘执行难’‘立案难’等群众关注的问题”为标准,既与社会公众日益期盼的司法公正相契合,又与执政党认同的 “人民利益”价值观契合。
二、政府主导型的中国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
纵观域内外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实践,其触发主体或主导方多为以立法、行政机关为代表的制度内决策机构,演进和发展离不开官方的推动。在我国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规范化、制度化及触发机制建立的过程中,由政府主导的特征更为明显,上海、福建等地的地方立法机关都曾尝试以单项地方性法规及相关法律制度为切入口进行实施效果评估。
(一)触发方式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立法主体、行政主体在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方面具有一定主动性。而从动因来看,通常离不开以下三个元素:“面临的体制外危机对其长期低效率构成的压力”、 “体制内观念的转变,不再将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视作制约,而是改进制度的方式”、 “制度发展的必然需要”,上述动因也让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在触发方式上呈现出多样性。
1.因立法监督而触发
此类触发方式在当前法治实践中被最为广泛地应用,具体而言,触发主体为立法机关或其代表(国内主要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触发动因较为多样,主要关注法律制度是否符合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否符合上位法律规定、是否符合现实需要;触发时间主要为立法机关履行职责时期,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具体而言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类: (1)因批准生效而触发。一定的立法主体制定的法规性文件、法律制度需经特定立法主体予以批准后才能生效,而在批准生效前,该项法律制度却极有可能已经通过政府令、政策性文件的形式存在,故而批准过程必然引起对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触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以下简称 《立法法》)第72条规定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上述规定即为部分拟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固化的法律制度设立了批准的程序,批准的过程就是对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合法性、合目的性进行评估。 (2)因备案审查而触发。法规备案是指法规、规章及相关法律制度生效后供相应机关被查的程序制度, 《立法法》第98条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应当在公布后的三十日内依照下列规定报有关机关备案……”,第100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研究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单纯的备案并不必然导致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触发,但如在备案审查中发现其存在与其他法律制度冲突的可能,则必然会引发更深层次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随着立法权意识的增强,法规备案已由传统的 “被动性审查”转向 “主动性审查”,从通常的 “应要求、请求进行”转变为 “随机、定向抽查”。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对 “一府两院”报送的30多件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逐件进行了审查研究,有重点地对地方性法规开展了主动审查,同时也针对92件公民提出的认为违宪违法的审查建议进行了处理。上述数字还不包括以 “请示汇报”为形式的非正式审查,例如2015年广东省人大法工委在制定《广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 (草案)》⑯的过程中,曾就 “电梯伤人物管先陪”的条款向全国人大法工委请示汇报,全国人大法工委给予了 “立法条件既不成熟,也超出了地方立法权限”的答复,广东省人大法工委在随后的第一次审议草案中删除了上述条款。此类 “请示汇报”是典型的制度外循环,但其制度依托为法规备案的法律规定,以此种形式触发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仍未离开因备案审查而触发的范畴。 (3)因法规清理触发。法规清理是指法定有权的国家政权机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按照一定的方法,对现存的规范性法的文件进行审查,是解决这些规范性法的文件是否继续沿用、是否需要变动的专门性立法活动。⑰从 “清理”二字可见,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调整、梳理现行法律制度,在调整、梳理前需要从整个层面对该法规及相关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具体而言,有较有规律的定期清理模式,如1985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提及的国务院各部门、地方人民政府每年对法规清理一次⑱;有大范围、大规模的集中清理,如1979年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效力问题的决议》即是对1949年以来所有制定的法律、法令进行清理;也有针对某项部门法律及法律制度的清理,如1996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以下简称 《行政处罚法》)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并于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 (4)因立法提案而触发。立法提案是指立法机关认可的立法机关代表依法、依程序向立法机关提出的关于修改某项法律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通过特定主体的提案活动,有关立法主体就需要对相应提案进行回应,就必然会伴随着对相关法律及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审查、评估。 《立法法》第14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第15条规定:“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甘肃省代表团先后提出了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当竞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建议;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工会界别的50多件提案建议中,涉及法律制度调整的占三分之一,明确提及修改现行法律的有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建议》 《关于修改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建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建议》,其极有可能触发对上述法规、条例及相关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 (5)因人大执法检查而触发。执法检查是立法机关或立法主体对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的制度。自1992年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至2006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执法检查活动日益强化,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曾在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作报告中毫不讳言地指出,要 “把加强执法检查摆在突出位置。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常委会把保证法律严格实施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强和改进执法检查工作。”有观点认为,执法检查本身就是一次对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但执法检查偏重于法律制度的执行情况,更类似于一个问题发现机制,而非一个完整的评估机制,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执法检查,主要检查监督法律实施主管机关的执法工作,督促国务院及其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组不直接处理问题。”故因人大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而衍生的对问题和响应法律制度的审视、评估才是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人大执法检查只是触发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渠道和方式。
2.因司法适用而触发
具体而言,触发主体为审判机关,即法院。触发动因比较单一,为法律制度的不合秩序,即上下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冲突,审判机关依据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新法优于旧法”等原则选择适用符合法律秩序的法律及相关法律制度,客观上让相冲突的法律制度处于“虚置”状态,迫使立法机关对其进行效果评估;触发时间主要为审判活动后。审判权的被动性及审判活动的具体性决定了司法监督对触发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局限性和限缩性,此类触发方式在当前体制内较为少见。在美国、英国等英美法系国家中,法官如遇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之间相冲突,可以主动选择其认为合适的法律进行适用,在判例形成后让不合适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制度成为 “摆设”,进而引起对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评估。在国内亦有类似的做法和案例,将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工作的触角延伸至诉讼领域⑲:2003年1月,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伊川县种子公司诉汝阳县种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认为, 《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第36条规定的 “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内统一价格,不得随意提价”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种子价格应有市场决定”的立法精神相悖离。⑳之后,该案件几经波折,引起了各级立法、审判机关对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经营管理制度的关注和评估。2003年7月15日,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向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就该案中种子经营价格问题发出一份请示,10月13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室发文答复表示 “《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关于种子经营价格的规定与 《种子法》没有抵触,应继续适用。”2004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中表示, “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2004年4月1日,河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同时废止《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不再规定种子经营统一定价事项。
3.因 “日落条款”而触发
该类触发模式是指在到达某一时间或法律制度实施一定时间后,假定某项法律制度已不合现实需要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国内的 “日落条款”设置散落于各类制度中,如 《行政许可法》第20条规定: “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政许可进行评价;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十三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青岛、郑州等地建立的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均对具有一定法律制度性质的规范性、政策性文件规定了2—5年的有限期,如青岛市的 《关于建立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和定期清理制度的通知》就规定 “规范性文件应当规定有效期,有效期自规范性文件施行之日起一般不超过五年;有效期届满,规范性文件自行失效。” “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前六个月,规范性文件起草机关认为规范性文件有必要继续实施的,应当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重新修改……”。
(二)优势与缺陷
“官方缺少主动发起实施效果评估的动力,这就是评估与管理的逻辑悖论。”㉑这种论断立意于社会组织不愿将自身的不足暴露的天然特性,虽存在一定片面性和单向性,但却也间接引出了政府主导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优势与缺陷,这种优缺点使其始终难以离开权威性的特点。
1.政府主导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优势
这一优势主要依赖于政府的威权优势及其掌控的资源,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点:(1)评估触发权威性强。政府主导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属于制度内的正式评估,或至少是被制度主体所认可的正式评估,其触发均有据可循,或法律、或规定、或政策,故而触发机制也具有严格的程序性。不论是备案审查、法规清理,还是司法适用、精英动议均会遵循体制内的规定或 “潜在规则”,如备案审查需遵循 《立法法》 《法规规章备案条例》。这种权威性、正式性能在制度主体间达成一致,触发效果较好。 (2)评估触发回应性强。因为此类触发机制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正式性,其会对法律制度的立、改、废产生直接和明显的影响,评估触发的回馈性较高,很少出现触发后不启动实施效果评估的情况。例如2003年安徽省政府法制办应人大立法提案的要求对 《安徽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实施办法》 《安徽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规定》等该省计划生育法律制度进行了评估,提出了 “取消育龄男性办理婚育证明”的建议,并在后续立法中被采纳,得到全国人大的认可㉒。 (3)评估触发成本较低。依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政府主导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其可以获取远比民众等初级行动团体成本低得多的资源来提供制度服务㉓,亦可以利用国家机器的 “暴力权力”降低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触发成本。一方面,其对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情况有着更为详尽的了解和认识,也可以轻易地获取户籍、住房、资产、经济、健康、教育、环境等方面的数据档案,更容易发现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而知晓何时触发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国家强制力可以更容易吸纳专业技术人员,其通常比民间或第三方组织吸纳的专业技术人员更具备立法、执法经验,也掌握更科学、更合适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方式,触发的质效更高。此外,政府主导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还有以国家财政资源为依托的经费保障,令评估触发更有保障。
2.政府主导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缺陷
具体而言亦可分为以下三点:(1)触发社会参与度低。此类评估触发机制将触发动议紧束于制度内渠道,触发主体局限于体制内部,都属于公权力内部层面的集体、组织,相对不重视社会公众的参与,导致动议表达及利益诉求表达的主体内部化。一旦这种内部化倾向存在,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就不可避免地招致 “评估触发困境”㉔,即当法律制度的设立主体和触发主体处于同一阶层内时,触发主体会为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辩护,或回避问题的存在及评估触发的必要性,或以 “执行偏差”、 “不可抗力影响”等理由为问题开脱,甚至产生反面效果。 (2)触发适用存在局限性。此类评估触发机制对象、触发标准通常都具有一定法定性,例如备案审查、批准的对象都有一定的范围限制等,因而此类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方式适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带有浓厚的 “官方”色彩。这就极有可能导致与社会公众需求的不一致,造成制度供给的扭曲与错位,一方面触发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难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意愿和方向也难以反馈,造成各种制度内主体的“一厢情愿”、 “一意孤行”的局面。 (3)触发公正性易受质疑。要求法律制度设立者触发对自己订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至少会引发设立者两个维度的考虑:其一,触发评估即意味着对自己设立、执行法律制度等行为的审视乃至批评,也是对自己设立法律制度乃至自己的质疑;其二,触发评估往往意味着以另一种观点、甚至是与设立时相悖的观点来审视某项法律制度。因此,此类触发模式就必然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且这种主观色彩很大程度上是偏向于法律制度设立主体的,其触发与否及后续评估结果如何的公正性易受质疑,社会公众易于从负面的角度解读触发的目的。
三、社会促动型的中国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
政治事务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几个阶段,其参与主体也日趋多元,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民众等各类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共同推进了政治事务的发展,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亦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促动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也日益完善,这意味着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触发主要由制度外主体引起或起主要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外主体掌握了启动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绝对主动权,也不意味着制度内主体将触发权让渡给了社会主体,仅仅是指社会主体在触动中起了主要或重要作用,促使或迫使制度内主体启动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
(一)触发方式
各国因文化背景、政治传统的差别,社会促动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方式也各有所别。例如在美国,民众主要通过选举投票、民意调查左右当政者施政倾向及对法律制度的态度等侧面促动方式影响决策主体触发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在英国,民众主要通过诉讼、告诉等行为触发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机制。我国民众则更倾向于以直接、甚至对抗方式影响决策主体启动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
1.因诉讼而触发
此类触发方式系社会公众或社会组织因某一具体诉讼案件影响的发酵、扩散,而引起的对裁决该类诉讼案件的法律及相关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就触发主体而言,主要是涉案当事人及关注该案的社会群体,但其并不局限于涉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在案件影响面日益扩散的进程中,触发主体促使公权力决策主体最终启动对涉及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决然不可能是一个或若干个个人或集体的意见,而是一定层面的群体性倾向,故而此类触发主体应当是一个团体。就触发动因而言,主要为涉及法律制度的不合现实,即在诉讼结果呈现后,涉案当事人即社会公众认为该结果及所依托的法律制度与现实需要不符,与社会公众需求不符,其动因的切入点往往是某一具体诉讼案件中涉及的个人利益,但这种个人利益所带来的问题却又往往具有共性且易引起共鸣。就触发时间而言,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时间点为案件获得关注以后,既可能在案件诉讼结果呈现后,又有可能在案件诉讼结果呈现相当长时间之后。此类触发方式较为典型的就是,近年来对冤假错类刑事案件的重新审视以及由此带来的 “以审判权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自2005年的湖北京山佘祥林杀妻案、2010年的河南商丘赵作海杀人案始, “冤假错”案逐渐唤起社会公众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的地方政法工作体系和刑事法律制度的关注和审视。2012年至2014年间,司法机关先后对河北保定赵艳锦雇凶杀人案、北京常林锋杀妻焚尸案、浙江杭州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福建福州念斌投毒案等重大冤假错案进行了纠正㉕,其背后是涉案人家属短则几年、长则数十年的再审申请和公益律师等密切关注人的呼吁,以及逐渐暴露在公众面前的 “刑讯逼供”、 “疑罪从有”、 “政法委定案”、 “办案难以独立”等诸多制度弊病。如在佘祥林案㉖中,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总结材料中提及 “佘祥林案件结果经过当时市、县两级政法委员会协调,并有 ‘一审拉满,二审维持原判’明确意见。这种 ‘先定后审’的做法是导致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如在张辉、张高平案中,张辉曾称其在狱中受牢头狱霸的暴力逼供;张高平亦称原审供述系因其遭到了公安部门以 “特别”方式对待而形成,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在二张出狱的次日对该案作出回应, “该案侦查机关违法使用狱侦耳目获取张辉有罪供述,直接导致了这起冤案。”又如在念斌案中,该案自2006年进入司法程序以来,虽曾被最高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先后经三级法院七次审判㉗,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在2011年11月24日第三次对念斌判处死刑,直至2014年方才由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宣判念斌无罪,这无疑体现了“有罪推定”观念的根深蒂固。上述诉讼个案中制度性弊病的呈现,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地方政法工作体系和刑事法律制度的关注和审视,进而触发了执政党对当前刑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审视和评估,开始了包含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司法事权上收至省一级”等内容的司法改革。
2.因告诉而触发
此类触发方式系因社会公众或社会组织对某一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相应问题的申诉、告诉等行为而引起对涉及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情况。就触发主体而言,主要为利益相关人和利益共同团体,告诉的利益诉求颇具个性,因而利益相关人习惯性地将与自己利益诉求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实现“抱团效应”;就触发动因而言,主要为涉及法律制度的不合现实,即与社会公众切身利益不相符合或在实施过程中会影响、损害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实际利益;就触发时间而言,也存在较大的不固定性,时间点为诉求获得关注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自然也包含对法律制度设立、修订的批评和建议权,实践中这种批评和建议权又演化为信访、抗议游行、群体性事件等具体方式。信访是一种被制度内主体认可的告诉方式。以我国中部某县为例,2010年至2014年间,该县分别办理信访件7875件、7929件、10095件、8589件、7252件,其中社会公众的告诉行为占到了绝大比例㉘。信访根据是否涉及司法案件又可细分为涉诉涉法信访和普通信访,涉诉信访诉求大多针对个案裁决结果,其诉求人大多穷尽或不信任正式司法程序内救济渠道,转而求助于党委、政府等决策机关、行政机关主导的信访救济渠道,以期获得更多关注。与因诉讼触发不同,此类型的关注点仅仅是个体的利益诉求,而非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故而很难触发对案件涉及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评估。普通信访则大多针对包含具体利益的诉求,如拆迁补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这些诉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共性特征,故而有条件引起相关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触发。国家信访局 《信访事项内容分类》将信访件分为农村农业、国土资源、城乡建设、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计生、教育文体、民政、经济管理等十七大类,每一大类又可细分为若干小类,每一小类都有对应的法律制度,如 “劳动和社会保障”大类中的 “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对应的是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相关法律制度, “卫生计生”大类中的 “计生执法”对应的是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相关法律制度,各地信访部门会按照上述目录分类梳理信访件主要内容并形成数据分析报告,以供制度内决策机构参考。例如2015年,决策者在制定 “全面二孩”政策中就参考了各地因计生执法而形成的信访件统计报告;又如2010年、2011年,中央纪委、国务院根据拆迁补偿类信访件统计报告相继下发了 《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并对现有征地拆迁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了评估,随后发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废止了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改了征地拆迁相关法律制度。相较于正常信访,非正常上访、群体性事件等告诉的几种极端行为就很难被官方主体认可,但仍能触发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机制,且因上述极端行为的影响力远高于正常信访,其触发评估的概率也高于普通信访。2011年9月,广东省陆丰市(县级市)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对该村土地、财务、选举等问题不满而聚集至陆丰市政府进行非正常上访,部分村民在当日下午打砸、毁坏周边企业财物并冲击围困了村委会,村民诉求直指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组织自治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 “治理不公开”、 “选举程序不严格”等问题㉙,进而触发了广东省委、省人大对村级治理相关法律制度的评估和审视,进而于随后制定 《加强村级基层组织建设五年行动计划》,并于2015年将上述行动计划中的“两议两公开” (“两委”会商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做法以地方性法规——《广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重新确立了村级组织建设相关法律制度。
3.因监督而触发
此类触发方式系因社会公众或社会组织对某一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相应问题的关注、评论、建议而引起的对涉及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情况。就触发主体而言,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和不固定性,其主体可以是官方以外的任何主体,但较少出现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是个体如某一网民,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如对某一事物看法相同的群体。就触发动因而言,其为涉及法律制度的不合现实,即法律制度实施效果与社会公众预期存在较大差距;就触发时间而言,其也存在较大的不固定性,时间点为对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相应问题的观点获得广泛认同以后。社会监督是社会公众在制度外的一种建议表达方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信访、告诉都属于社会监督的方式,但舆论监督因其参与主体的中立性、非利益相关性和载体的便捷性,更容易发酵、扩散,进而触发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例如,收容遣送、劳动教养等制度的废立、改进进程中均受到了明显的舆论影响。收容遣送制度废止的直接动因为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17日,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孙志刚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 (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后孙志刚由于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殴打而致死。2003年4月25日, 《南方都市报》以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㉚为题,首次披露了该事件,文章当天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这一方面推动了对涉案人员的处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关注和评估,进而促使制度内主体对该项制度实施效果进行评估。2003年6月18日,在对该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草案)》,废止了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 《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劳动教养制度废止的直接动因则为任建宇事件、唐慧事件,2012年8月3日,唐慧因多次上访而被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 “扰乱社会秩序”为由进行劳教㉛;2011年9月23日,重庆市郁山镇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2011年4月至8月多次发表 “负面言论和信息”被公安机关处以两年劳动教养。上述事件被媒体曝光后迅速发酵,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存在“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 “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 “处罚过于严厉”、 “程序不正当”等问题,进而唤起了制度内主体对劳动教养制度实施效果的审视和评估。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正式废止了实施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
(二)优势与缺陷
2000年以后, “公民社会”这一历史范畴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与这种关注一同诞生的是社会公众对政治事务参与热情的提高;与之所相对应的另一个名词——“民粹主义”亦同时兴起,同时伴随的则是社会个体所希望实现的利益。从这两个角度出发,不难解读社会促动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优缺点。
1.社会促动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优势
具体而言,该优势可分为以下三点:(1)制度弊病导向性强。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对象是法律制度,但并不是所有法律制度都存在实施效果评估的需要,即便是需要也存在先后缓急的区分,政府主导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内部性致使其难以全面掌握解决各项法律制度存在问题的不同紧迫程度,而社会推动恰好能弥补这一不足。公众反映大、社会影响大的法律制度相关问题往往更加紧迫,也往往具有优先评估的必要性。官方决策主体可以根据各类社会主体反应的强烈程度进行评估触发的次序排列,进而参考这一次序进行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 (2)评估触发的客观性高。政府主导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内部性,会影响评估触发的客观性。 “只要是来自决策主体本身,不论其身份如何,属于哪一级哪一类部门,很难避免利益牵连,也很难真正站到社会公众的角度,结果也难让社会公众信服。”㉜而法律制度实施效果如何,作为法律制度服务对象的社会公众有最直接的感受。 “作为公共服务的顾客,社会公众能最真切地感受到服务水平的高低。”㉝社会公众等决策外主体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触发过程的促动和参与可以让决策者站在更客观、更中立的立场,促使触发结果和评估结果的真实可靠。 (3)易于促成公民需求与制度建设的耦合。对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效果的意见、建议、评价反映了社会公众的需求,但从触发评估到进入评估进程,从评估进程到对法律制度进行修改、形成实际的法律产品供给则是较为复杂的过程。而在体制外循环的公民需求往往处于 “虚置”状态,是一种意愿的法律需求,且难以最终触发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社会促动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则能将公民需求转化为有效的法律需求,促使官方决策主体关注、评估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结合公民的有效法律需求对涉及法律制度进行调整、修改。
2.社会促动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缺点
该缺点可细分为以下三点:(1)触发主体观点易受个体利益影响。社会促动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触发主体较为复杂,多数为松散的非组织团体,其发起者和引导者往往为因涉及法律制度实施造成个体利益受损的参与者。这导致其难免受个体利益的影响,夸大法律制度相关问题的阴暗面,甚至有可能对法律制度采取全盘否定等极端态度,进而让整个意见团体陷入 “民粹”的怪圈。 (2)难以掌握触发回应的主动权。社会主体如要促动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最终仍要依靠制度内的官方主体。换言之,如果官方对社会主体形成的触发意愿缺少回应,评估机制就难以最终触发。例如至1995年始,各类社会主体就相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以下简称 《草原法》)及相关法律制度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官方决策主体对当时草原资源利用制度进行实施效果评估,然而直至2001年, 《草原法》修改才通过 “2002年第457、1184号议案”被正式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㉞。 (3)触发缺乏必要支撑。成熟的社会促动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离不开成建制、成规模的专业力量的介入。此类专业力量或以组织或以机构的形式出现,一方面可以让社会公众对某项法律制度及相关知识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也能让触发动议更中立、客观。各国都比较重视在触发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时引入专业力量,例如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研究所,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但国内在这一方面仍处于起步、萌芽状态,致使社会促动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后劲不足、动力不够。
四、中国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完善之路径
政府主导和社会促动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均有一定利弊,其核心在于两者不同的利益倾向导致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观点的不一致,这就需要在两者之间架构均衡的桥梁,在官方意愿和社会动议之间达成平衡。在威权体制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建立政府与社会合作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不失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合理假设。政府主导、包容并蓄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是指,制度内的官方主体作出启动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决定与社会主体意愿相吻合,或社会主体提出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动议得到了官方的积极回应,两者在是否启动对某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方面达成一致,进而触发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开展。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触发 “共意”的形成,也尽可能规避了政府主导、社会促动两种法律制度的缺陷。
(一)政府与社会合作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构想
罗杰·柯比将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等制度内主体与社会公众共同决策的过程分为三种类型㉟:政治动员型——由权威政治领袖提出决策意向并推动进入决策议程;内在创始型——制度内团体和个人提出决策意向并推动进入决策议程;外在创始型——由社会主体推动进入公众议程并在取得决策主体认可后进入决策议程。政府与社会合作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亦可参照上述理论进行类型区分。
1.内在创始型的触发模式
“内在创始型”的触发模式是一种由内至外的触发模式,即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等制度内主体动议、社会公众认同的触发模式。 “政治动员型”的触发模式亦可归入这一类。其与政府主导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不管是否符合社会需求、不顾公众认同与否径行发动其认为有必要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即便有社会公众的有限度参与,也难以左右公权代理方的决策意向;而公权代理方动议、社会公众认同的触发模式则是直接将社会公众作为决策主体的组成部分,在综合考量其意见后形成最终是否触发的决定。这一模式又可根据公众参与时间的早晚和介入程度分为以下两类:一类为制度内主体动议时已有明确的动议对象——拟触发评估的法律制度已了解该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只动员公众响应该动议并配合触发。在这一模式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通过各类渠道发现、掌握了某项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主动发起对某项具体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动议——如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2005年进行的首次法律绩效评估时将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等法律制度列为评估对象㊱,并以公众咨议、公开听证等公开、开放的方式向各类社会主体征求意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综合各方意见后作出最终决定。这一模式实则是制度内主体主动设定议题,并让议题获得公众认同进而达成合意的过程。另一类模式为制度内主体动议时尚无明确动议对象,仅有动议方向——某一领域的法律制度,需要根据社会公众的意见来形成最终动议并触发评估。此类模式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制度内主体拟触发对某一方面的法律制度进行实施效果评估,但并未掌握该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未明确对哪项法律制度或某一法律制度的哪些部分触发评估,而是将拟触发评估对象确定的主动权移交至社会公众手中并根据公众意见作出决定,通过更为开放的公众议程确定是否触发、如何触发、对谁触发实施效果评估。
2.外在创始型的触发模式
“外在创始型”的触发模式是一种由外至内的触发模式,即社会主体动议、制度内主体认同的触发模式。这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公共决策议程,其对法律制度相关问题的发现、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进行触发的动议纯粹是由社会公众等制度外主体完成。其触发过程与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十分相似,均会经历个体或集团动议、社会认同扩散、引起制度内决策主体关注、制度内决策主体触发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等过程。但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在社会促动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中,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制度内决策主体对社会动议的关注是被迫的、不情愿的,且其关注往往还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冲突——非正常上访、群体性事件、舆论发酵,这种被迫代表其不愿意与社会公众共享触发权力的态度,也不愿意与其就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相关问题达成合意;而在社会主体动议、制度内主体认同的触发模式下,制度内决策主体对社会动议采取的是主动接纳的态度,主动促成决策与社会动议的耦合。这一模式与制度经济学派归纳的制度创新模式十分相似。制度经济学家曾将制度创新归纳为如下五个步骤㊲:(1)形成的 “第一行动集团” (发起者)预见到潜在利益的存在,认识到只要进行制度创新就能获取潜在利益; (2) “第一行动集团” (发起者)提出创新方案; (3) “第一行动集团” (发起者)在若干创新方案中作出决策,确定发起方案; (4)形成“第二行动集团” (实质上的决策主体); (5)“第一行动集团”与 “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创新目标。套用上述理论来解释外在创始型的触发模式, “第一行动集团”即为准备发起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社会主体, “第二行动集团”即为对评估触发有决策权的官方相应机关,其触发过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法律制度实施相关问题的产生,某一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大部分人或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人的关注;第二步,社会主体对法律制度实施相关问题的确认,在发现问题后对问题的界定、描述、影响扩大的过程;第三步,制度内主体吸收社会公众的相关意见建议,并在触发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方面达成一致;第四步,制度内的决策主体触发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
(二)政府与社会合作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环境基础
促成上述两种触发模式的形成与发生,离不开较为完整的制度土壤。
1.民主观念需要培育
“民主”是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因意识形态、利益分配的差异, “民主”在各国、各地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通常意义上讲, “民主”的实践方式或为 “选举”,或为 “投票”,但不论哪种形式,其都应当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顾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在官方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中也是按照这一标准来设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 “民主”供给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意愿:一方面,制度内精英政治的固化,且其继续对社会意见抱有排斥、怀疑的态度,社会公众的动议、意见难以被吸纳;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因对个体利益分配的不满而产生对公共决策参与的热情,且这种热情日益增长,并在未得到有效反馈和关注的情况下逐渐酿成 “民粹”等对抗性较强的行动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公众难以和制度内的决策主体就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触发达成一致。应从原理、原则、途径三个层面在制度内强化 “民主”的供给则是达成上述触发一致的基础条件。其一,重申 “民主”的原理体系:人的尊严原理、平等原理、自由原理、主权在民原理等,引导决策内制度主体正视其决策权力的来源及其权力行使合法性的来源,转变对社会动议的排斥、怀疑态度。其二,强调 “民主”的原则体系,即讨论原则、妥协原则、多数原则等,让制度内外的各类主体回归合议、讨论等和平的分歧表达方式。其三,扩容 “民主”的参与途径,重点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循序渐进地放开政治壁垒和偏见,在制度内吸收意见、中和矛盾、消解偏见。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公众会以更为平和的态度来看待关于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动议,官方主体则也以更为开放、正当的态度来看待关于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动议,进而为两者对此达成一致创造条件。
2.制度内动议渠道的优化
将各类非官方、制度外主体关于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的动议最终转化为触发的行为,依赖的还是官方的决策。要在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方面获得制度内外的一致,既离不开官方决策主体积极、开放的态度,也离不开对现有动议渠道的优化。前文所述制度内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动议渠道主要有立法监督、司法适用等几类。在立法监督方面:制度外主体可通过推选人大代表、要求人大代表转达等方式引起决策主体对社会意见的关注,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构成一般为 “党政干部为主,商人名流为辅,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华人华侨、少数民族为补充”格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具有 “党政干部”身份代表仍占39.4%㊳,一线基层代表比例虽有提高,但却仍处于少数,且其意见和建议难有独立性,往往受其他基层代表影响,故社会公众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等公共决策的意见建议实则并未在立法机关内得到有效表达。在司法适用方面:制度外主体主要通过充当人民陪审员的方式来参与审判,进而影响审判机关的法律适用和裁判,而人民陪审员 “陪而不审”、“陪而不议”㊴的现象让整个陪审员制度沦为摆设,遑论体现社会公众对相关法律制度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不论哪一种渠道,都难以有效表达社会公众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触发意愿,这类意愿长期徘徊、游荡于制度渠道外,最终可能会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等对抗性冲突。从制度层面优化现有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动议渠道是促成制度内外主体达成合意的必要条件。要提升对社会公众代表的吸纳程度,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政议政参与主体中增加民众代表的比例,在 “人民陪审员”、“执法监督员”等司法过程参与主体中增加随机代表的比例,让制度外主体直接参与到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相关决策中。提高社会公众代表参与制度内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注重发挥 “意见领袖”引导社会公众形成对法律制度的理性意见和建议及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的动议,并愿意从现有制度渠道发起这种动议。要落实社会意见反馈机制,注重从公开听证、意见征询、网络舆情等方面收集社会公众对相关法律制度的意见建议并予以回应,完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闭会期间听取公众意见机制;适时设定量化指标,确定官方吸纳社会意见的标准和条件,畅通由制度外向制度内的动议表达渠道。
3.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培育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中的 “第三方社会组织”是有别于立法主体、执法主体、公共服务对象等法律制度实施直接参与者的法律制度专业评估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促成、开展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触发及施行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中具有中立、客观性,一方面其不会受官方主体的干扰,另一方面也不会受个体利益和民粹主义的束缚,超然于法律制度的设立者、执行者及服务对象之外。现存的第三方社会组织或长期受制度内主体支撑,如行政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下属各类事业单位;或与境外意识形态组织密切关联,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态度或倾向㊵;或自身专业力量不足,难以摆脱仅代表小团体利益的束缚,既不客观、也难中立,更不能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触发起到促进、推动的作用。因此,培育第三方社会组织并引导其良性发展是促成制度内外主体达成合议的有力支撑。要激活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发展动力,推动法学教研实力较强的高校、学术团体、律师事务所成立、发展、整合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机构,激发现有第三方社会组织有序参与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的意愿。以专业性和独立性为重点强化第三方社会组织促成、开展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能力,鼓励制度内外的法学理论专家、应用法学专家加入第三方社会组织。规范第三方社会组织介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的流程,明确介入时间、介入标准、介入内容等具体细节,为制度内外各类主体提供合理、科学的参考,让其促进、推动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触发和开展。
(三)政府与社会合作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比较优势
政府与社会合作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是基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分离又协调一致的内在关系而提出的。国家产生于社会,受制于社会, “国家应当承认社会的独立性与自治性,为社会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从而使社会具有一个合法的活动空间;国家应当培育出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集团,使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政治上表达它们的意志。”㊶这也让这一模式均衡了政府主导型、社会促动型两类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优势,回避了两者的缺陷。
1.更具效率性
如前文所述,社会促动型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缺乏后续进程的主动权和触发最终的决策权,进而影响实际效率。与之相反,政府主导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虽然掌握了后续进程的主动权和触发最终的决策权,但因其内部性和单向性,整个触发过程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会引起社会公众的质疑和阻扰,客观上也会影响触发的效率。打破这种效率僵局的最佳路径就是在制度内主体与制度外主体之间达成合意,即政府与社会合作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仍让制度内决策主体有限度地掌握了触发的最终决策权,但又兼顾了公众、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主体的不同意见,既不必担心在触发过程中遭受太多阻力,又可具备与单纯由政府主导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一样的制度内优势,其完成触发进程的时间短,客观上也提高了整体效率。
2.更具公平性
政府与社会合作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并不局限在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 “政府”本身就是一个泛指名词,涵盖了各级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等官方机构,故而这一模式囊括了各类官方与非官方主体之间的各种博弈、协商和合作,其既不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过程,也不是社会主导的纯粹的自下而上的意见发泄过程,而是多元主体之间对话、竞争、妥协、合作,最后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㊷。这一模式下,各方意见都能通过较为正规的制度内渠道进行纾解,最终达成各方均认可的触发倾向或动议,这种动议超然于各主体意见之外,打破了各主体间的利益边界,以共同合意的方式表现出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的动议和建议,一方面不会因统治集团的要求单方面触发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另一方面也不会受个体利益或小团体利益对某些法律制度偏见的影响而触发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就触发对象而言更具公正性、客观性。
3.更具回应性
日本学者曾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有过如下论述:“在既有的政策中选出国民关心度高的题目,对其实施与效果的相关性以及根据外部原因实施的决策所获效果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价,是对政策进行修改和重估的继续。”㊸触发只是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起步和开始,触发后的评估、反馈等进程才是检验触发效果的关键,政府与社会合作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兼容了各方观点和意见,更容易进入实质性的评估程序乃至评估后的反馈程序,触发的效果也更容易展现。
结语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在国内随着 “法治”理念的重拾,日益朝着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其触发既有国家层面的推动,也有社会层面的促动。但不论是 “自上而下”还是 “自下而上”,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仍呈现出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难免显露出以偏概全、难以中立等缺点,对其研究既是必要,也是客观需要。法治中国的建设离不开法律制度体系的日益完善,而法律制度体系的日益完善则离不开相应的评估及其触发机制,作为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第一环节”——触发机制完善与否,在整个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机制中备受瞩目。本文通过对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相关模式、实践的介绍,从探究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概念入手,在比对域内外较为典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基础上,对当前较为普遍的政府主导、社会促动两类主流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政府与社会合作型的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以期对今后的法治实践有所裨益。但由于本文所涉课题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应文献也并不多见,使得本文写作依据较为匮乏、所引文献不够丰富,致使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受到一定局限,但仍希望本文能为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触发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一些参考。
注释:
① [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项龙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② Evert VEdung,Public Policy&Program Evaluation,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7.
③ Ernest Gellhorn,Regulated Industry in a Nutshell,Minnesota: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0.
④ 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⑤ 杜飞进:《论法治力》, 《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3期。
⑥ 崔晓燕:《论法律制度安排与法律实施成》,重庆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 张大伟等:《论法律评估——理论、方法和实践》, 《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⑧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
⑨ 商昌国:《董康与北洋政府 〈暂行新刑律〉的两次修订》, 《兰台世界》2013年第30期。
⑩ 万孝行:《“异体”监察与西汉刺史制度》, 《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⑪ 廖健、周发源:《中央与地方立法机关相互关系辨析与重塑》, 《湖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⑫ 郭光辉:《〈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立法后评估工作追记》, 《中国人大》2007年第8期。
⑬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山东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权益保护条例》, 《山东政报》2001年第1期。
⑭ 李春晓:《十八大以来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⑮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 (白皮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
⑯ 2014年5月21日,广东省政府发布了 《关于印发广东省电梯安全监管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其中规定“当电梯事故或故障造成损失时,使用管理权者对受害方承担第一赔付责任”。2015年,为推进该项改革的制度化,广东省人大法工委在起草 《广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草案)》时直接将 “电梯伤人物管先陪”的条款列入其中,引发广泛争议。
⑰ 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62页。
⑱ 李步云、汪永清:《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⑲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文化研究室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制度和监督工作》,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
⑳ 杨世建:《法制统一的反思: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界分及冲突解决——以 “洛阳种子案”为例》,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6年第2期。
㉑ [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项龙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㉒ 何聪:《安徽:“立法后评估”让规章更管用》,《人民日报》2005年9月29日。
㉓ 刘自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经济学分析》,《行政与法》2007年第12期。
㉔ [美]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彭勃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291页。
㉕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 (白皮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页。
㉖ 陈卫东:《“佘祥林案”的程序法分析》, 《中外法学》2005年第5期。
㉗ 熊秋红:《以念斌案为标本推动审判中心式的诉讼制度改革》, 《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
㉘ 陈柏峰:《信访制度的功能及其法治化改革》,《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
㉙ 郑晶:《村民自治权的法律保障——以广东乌坎事件为切入点》, 《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16期。
㉚ 陈峰、王雷:《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5日。
㉛ 汝绪华、汪怀君:《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政府执行力与舆论话语权——以湖南永州唐慧事件为例》,《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㉜ 周凯:《政府绩效评估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㉝ 齐二石:《公共绩效管理与方法》,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㉞ 布小林:《立法的社会过程——对草原法案例的分析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63页。
㉟ Roger W.Cobb and Charls D.Elder,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Opinion,New York:Alfred A.Knopf,1971,p.30.
㊱ 郭光辉:《提高立法质量的成功探索——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对一地方性法规开展立法后评估》, 《中国人大》2006年第11期。
㊲ 傅殷才:《制度经济学派》,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㊳ 徐理响、黄鹂:《人大代表结构与代表身份选择合理性问题探析》,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㊴ 胡媛、胡杏:《陪审制度事实评议机制研究》,《人民司法》 (应用)2016第34期。
㊵ Wang Shizong,Song Chengcheng,Xu Lu,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Multi-layered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6,(4).
㊶ 吴家清:《国家与社会:法治社会的价值选择》,《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
㊷ 王名、蔡志鸿、王春婷:《社会共治: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2期。
㊸ 龚深弟:《日本时事政策评价工作——〈城市铁道建设应有状态〉评论概要》, 《现代城市轨道交通》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