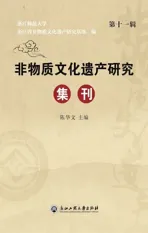村落传统节日的复兴与地方社会再生产
2018-04-03陈映婕
陈映婕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一、背景:中国乡村的传统复兴
“传统”概念的出现,基于现代性的整体出现和有力刺激。所谓的“复兴”是一个侧重历时性的术语,具有过去—现在、理想—现实的二元思维模式,一般被认为是经历了中断和裂变后得以重构的文化回溯过程与结果,其中依然没有脱离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言说范畴。作为现代性的伴生物和一类文化变迁与转型现象,传统的复兴既是文化主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试图建立新的文化秩序的自觉实践,同时也是该时期文化自身存在矛盾与危机的潜在表征。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传统的复兴伴随着人们对传统的进一步反思与实践,以及对传统的再创造与新发明。正如吉登斯所说:“传统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像启蒙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消失。相反,传统以不同的形式到处继续繁荣发展,但是以传统方式存在的传统越来越少。”[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从宏观的角度看,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地方文化或弱势文化的文化自觉。这类社会文化实践经常被看作是对“全球化”的抗争与抵制。但是,“具体到近年来国内出现的各种‘传统’的‘复兴’,无疑还有国内本身的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在许许多多的后一种‘实践’(指地方或弱势文化的复兴),与其说是传统的复兴,不如说是传统的再创造”。[注]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1页。这对于认识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变迁与发展尤为关键。
中国近现代的发展是伴随着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紧张、矛盾、纠葛和选择,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场二元博弈。“对于近世中国,如果想快速地勾勒出其全貌的话,她似乎是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并在这两极中间不停地摇摆,即在左和右、新和旧、现代和传统、进步和落后、革命和复辟、城市和乡村、拆除和建设等的对立概念之间摇摆……”[注]赵旭东:《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复兴的二律背反》,《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54页。这种“摇摆的极端化”与中国在变迁中的复杂情形有关,也与现代性自身的困境有关。
自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中国乡村的民间传统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复兴与繁荣阶段,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发展不容小觑。民间组织、伦理道德、宗族制度、宗教信仰、节日仪式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根据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丁荷生(Kenneth Dean)的实地调查和估计,到1992年整个福建省重修的民间神庙多达三万个,每个县有三百到上千个神庙被修复,同时多数的家族村落已经恢复它们的祠堂。[注]Kenneth Dean, Taoism and Popular Cults in Southeast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4-6.美国汉学家肖凤霞(Helen Siu)从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的角度,认为近年汉人社区传统社会与仪式的复兴是由官方提倡所引起的。[注]Helen Siu,“Recycling Tradition: Culture,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 of South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90 (4),pp.766-794.人类学者王铭铭通过对福建塘东村的田野调查,提出民间传统与现代化是交织着发展的,地方宗教仪式起到了联络地方社会关系与操演社会竞争的功用。[注]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6页。学者王加胜从经济学的角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民间传统自身具有非制度性的经济调节与补偿功能,农村经济体制的变化与市场化进程为传统制度(如家庭组织、婚姻等)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使其对地方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参见王加胜:《民间传统的复兴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3期,第97页。人类学者周大鸣通过凤凰村信仰与仪式的复兴个案,从民间信仰与现代化的角度去分析传统复兴的原因,认为宗教复兴来自五种动力,即信仰生活的缺失、文化教育的普及、商业活动的推销、大众传播的普及、传统生产方式的恢复。[注]周大鸣:《传统的断裂与复兴——凤凰村信仰与仪式的个案研究》,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252页。国内学者侧重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发展模式,去寻找民间传统复兴的可能性。
对于乡村传统的复兴,不仅可以归因于基层社会对政治理想的幻灭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松弛,还应归结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发展出现的不平衡现象,以及传统力量尚未消失的潜在生命力。现代性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悖论与双重性,为传统的再度发育留下了长足的生存空间。文化的发展是多种力量的消长、竞争与中和,所谓的传统与现代有时表现出对立矛盾的一面,似乎水火难容,有时则泾渭难分,甚或联袂登台。
二、村落传统节日的当代复兴
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文化复兴的组成内容。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当下学界关注较多的“传统节日”是民族—国家视野中的、具有传统意味的现代公众节日。基于西方节日具有普适性的现实背景,知识精英们成功地推动了国家有关新的法定节假日政策的出台,使得某些影响力较大的民族传统节日得以纳入其中。有的学者将此视为是传统节日在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复兴,并强调其在现代化语境中促使民族文化自觉与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意义。[注]高丙中:《对节日民俗复兴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再生产》,《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7—11页。在这类文化运动中,国家和知识精英成为主要代理人。
在基层社会,许多村落节日的复兴经历了一个地方式的复兴过程,也包含了更为复杂的话语力量与权力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农村社会史无前例地、毫无保留地卷入到国家生活的疾风骤雨中去,地方社会生活成为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微缩胶片。新的权力话语将沿袭了数代的乡村传统贴上“迷信”“落后”的认识论标签,农民也被看作是一个在经济与文化上处于消极和被动状态的庞大群体,成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对象。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试图扫除乡村在实现社会理想过程中的历史障碍,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以及由外部力量重创的“共产主义新传统”[注]该术语来自魏昂德教授(Andrew G.Walder)在1986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Communist Neo-Tradition)一书,即将拥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的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类独特的社会形态和新的文明传统。转引自郭于华:《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第10页。。在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与经济改革之后,正如W.R.葛迪斯所说的那样,“总的来说,农民正逐渐变得不太像‘农民’了,而更像中国人民这个整体中,在乡下的一个部分”[注][澳]W.R.葛迪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见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附录”部分,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页。。
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一定力度的调整,并尝试新的经济改革内容,文化上的社会控制也有所松弛。中央政府甚至允许一些地方适度地恢复一些与促进经济发展有关的传统节日。云南大理白族的传统节日“大理三月街”,是滇西北具有民族特色的物资交流集市和文化艺术盛会。由于受“破除旧俗”和经济衰落的影响,1977年初次恢复的传统“三月街”,不足千人,卖出的商品还不如城里一家小百货商店多。[注]杨盛龙:《少数民族节日文化的复兴》,《瞭望》1991年第18期,第12页。因此,这个时期此类传统的复兴基本上是体制内部、自上而下式的,来自民间社会的文化复兴动力不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正式确立,由资本主义导向带来的社会变革冲击着国家与大众的经济文化生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文化。伴随着社会运动式改造的结束与乌托邦式国家理想的幻灭,诸多乡村社会的村落家族制度、民间互助组织、宗教信仰、草根艺术在由商品经济主导的大众文化语境中纷纷得到再度发育。由于节日是具有狂欢性质的、特殊的时间生活,具有综合性与程式化的特点,能够集中展演村落的生活结构,因此这些再兴的传统事项借助节日的时空,能够得到一个整体展现的契机,或者说,正需要这样一个汇演的文化舞台。
传统节日的复兴,也是文化主体对文化要素自行选择的过程与结果。在形式上,许多意欲复兴的村落节日首先选择了农耕社会中以年为周期的岁时节日时间,如春节、元宵、二月二、春社、清明、秋社等,因循了传统社区的节日时间观念。笔者曾经在位于浙北地区的桐庐县南乡一带,调查过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复兴起来的村落群节日,地方上称之为“时节”。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在乡村的持续推进,当地人的生计更多地依赖工商业,而非传统的农业,并且时节的内容和功能已经与以往有了本质性的区别,但是在复兴的过程中,每个村落的时节日期都不约而同地采纳了传统夏历中的“吉日”。这样能让他们感觉节日具有“传统感”,如同历代祖先延续下来的那个时节一样。[注]陈映婕:《饮食消费与人际关系的生产》,《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第222—232页。
在内容上,村落节日的语境中包含诸多仪式活动,如起始仪式、净化仪式、竞技仪式、服饰或饮食的展示、祭祀仪式、表演仪式、结束仪式。[注]王娟:《民俗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74页。许多当下复兴起来的村落节日,在总体上也并没有脱离这些仪式过程,依然保留和遵循着传统的一定形式。但是,这些节日的仪式功能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村落内部或村落之间的实际生活需求,而是在更大的话语空间中寻求更多的社会资本或象征性资本,以期实现有目标的地方社会再生产。
三、地方社会再生产与现代性资本
马克思唯物论中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使社会能够得以延续下去的、生产力与人口的再生产。现在这个概念已经从经济领域被引入文化范畴,并被广泛应用,指的是社会主体通过自觉的行为使得观念和价值传递下去,以维持社会既有的规范与秩序。法兰克福学派使用“文化再生产”的概念,表示国家所支持的文化制度,使人们在观念内制造出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继而使得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被再生产出来。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借鉴了经济领域中的“资本”这一概念,将之运用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去。他将“资本”分为四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根据物质性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形式的资本,一类是非物质形式的资本。各种资本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比如将地方文化当作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如名人故居、家族遗址,就是以国家教育制度认可的精英身份作为一类文化资本的象征符号,从而将其合法有利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主要是一种社会声望、知名度及其占有文化象征和经济资本的数量程度。“所谓象征性资本,是用以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资本的积累策略等象征性现象的重要概念。……它是通过无形和看不见的方式,达到比有形和看得见的方式更有效的正当化目的。”[注][法]高宣扬:《布尔迪厄的象征性实践和权力运作》,《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7页。在布尔迪厄看来,任何文化知识体系都有一种把社会权力体系引入并使之合法化的特性,而象征性资本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实现资本的正当化与权力分配的过程。拥有不同的象征性资本,就拥有不同的文化符号支配与被支配的可能,并且总是将客观的等级制度、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再现成合理且合法的社会秩序,以实现社会的再生产。因此,“通过文化再生产和权力再分配过程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中,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成功而有效地建构和维持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相互协调的同质关系”[注][法]高宣扬:《布尔迪厄的象征性实践和权力运作》,《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9页。。
以上这些文化政治学的概念,将有助我们从理论的角度较深入地阐释当下村落传统节日的复兴现象。
笔者曾经调查过浙南泰顺县一个名为“百家宴”的节日。该节其实是当地的元宵节,节日内容有祭祖与祭春、戏曲表演、祭祀地方神灵(陈靖姑)与巡游、烟火表演和集体宴席。其中的宴席,在传统社会中是宗族村落内部或与邻近村之间的集体会餐,以前并无特定称呼。直到近几年,随着节日规模和影响力的增大,媒体帮助当地为该宴席起名“百家宴”,使得社会大众通过电视、电台和网络对“泰顺百家宴”这一地方文化品牌广为知晓。为了配合电视在元宵那天能够及时地向观众播放该节日,“福首”(从家族中推选出来的节日组织者)甚至事先率领族人为其预演了一遍节日的开幕仪式。[注]《关于浙江“泰顺百家宴”的调查报告——以三魁镇元宵节为个案》,见浙江师范大学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234页。大众媒体作为一类新的社会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能够迅速地将复杂的问题以象征符号的话语形式加以简单化,实现信息传递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当“百家宴”的社会名声与威望达到一定程度,获得了公众对其独特性的广泛认可以及全球化下地方文化的正当性时,它就形成了一类象征性资本,并有可能转换化为有形的经济资本,节日中蜂拥而至的各地游客即是有力的说明。持有经济资本的商家也介入到新兴的节日中去:他们在举办百家宴的道路中间,挂起了醒目的红布横幅和充气横幅,上面写有“某某厂家祝三魁百家宴圆满成功”和“某某啤酒祝三魁百家宴隆重举行”的字样。商业广告以消费一定经济资本的代价,给人以支持文化事业的感性印象,增加了公众的好感与消费意愿,目的在于换取更多数量的货币资本,并炮制出有关“品牌”的社会资本。知识专家们借助其来自教育背景和资源的文化资本,对节日的运作方式和未来发展提出规划与建议,并借助大众媒体的声音,强化自身的文化权威与社会资本。地方行政权力以文化监管的身份介入节日,组织和安排了各级和各类媒体的有效参与,并密切关注节日中的社会秩序。因此,这个依托当地村落家族的复兴得以重构的、具有传统意味的元宵节,成为一个权力与资本密集互动的复杂“场域”,当地人的行为、形象与仪式只是整个节日表演场中的一项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义。这个元宵节并非仅仅满足当地村民的现实文化需求(如家族认同、休闲娱乐、精神抚慰),而是还以一个节日的场域去建构地方上各类资本周期性的扩大再生产。
借助复兴的节日去谋求现代性资本的文化再生产的情形,并非是个别案例。人类学者潘蛟在2002年调查了一个为配合州庆而举行的火把节,他意识到,“举行火把节庆典更像是一种文化生产,然而,在不同时期,这种生产的性质是不同的。在过去,这种生产基本上是‘自足’的,即旨在满足当地消费,在当地促发家庭、社区团圆、欢聚和交流,祛除灾害、祈盼丰年等意义和快感。然而,如今这种生产更像是一种商品生产,它的目标不仅在于满足当地社会需求,而且在于对外流通、吸引外地游客”。[注]潘蛟:《火把节纪事:当地人的观点》,中国民俗学会编:《节日文化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页。所以,实现现代性资本的再生产,成为现代性语境下复兴起来的传统节日的重要文化功能之一。新兴的现代村落节日早已不再只是满足于农耕社会中村落内部或村落之间的社会互动,许多节日仅仅依托了村落作为举行的地点(place),继而发展起一个充满不同话语形式与权力结构的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
另外,国家权力的地方性演示,是当下传统节日复兴运动的重要特征。掌握各种资本的、体制内外的精英(政治、经济、文化),成为节日的资源支配者和仪式主角,当地的村民在节日场域下的权力结构中居于边缘位置。浙江省缙云县的仙都在2008年举行了“戊子(2008)年中国仙都民祭轩辕黄帝大典”。这个节日是在近几年由当地政府正式命名的。首先,名称中的“戊子年”是以传统的天干地支计时法计算出来的,其次才以辅助说明的形式出现了现代公历时间,在节日的时间表述上保留了传统的形式。其次,作为县属景区的“仙都”直接跨过省与市的行政单位,居于“中国”之后,而其中的“民”也主要指的是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人民”的政治概念。最后,“轩辕黄帝”既是地方节日的信仰对象,同时也是中央集权政治生活中民族—国家的重要象征符号,其信仰的复兴有着地方和国家的双重需求。
该清明节的节日主体,在历时上总体经历了国家精英—普通村民—地方精英的发展模式。东晋成帝在此地设立祭拜黄帝的场所;唐玄宗时期成为江南官员祭黄帝的地点;宋代皇帝曾派大臣去仙都祭祀轩辕氏;至明代,渐废,转为民间祭祀;近代,民间多集中在村落祠堂和院落中堂自行祭祀,先祭轩辕氏这位国家神灵,再祭各家祖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断,于20世纪70年代末渐兴;1998年由缙云县人民政府组织重修“黄帝宇祠”。2008年的清明节,节日主体由一个主祭团和六个陪祭团组成。其中主祭团中主要是当地的政府官员、赞助单位负责人以及港澳台代表,共26人;陪祭团一与陪祭团二分别是浙江兴城房产与浙江雅仕寝品的工作人员,两者是主要赞助单位,共有90人参加;陪祭团三为中国港澳台侨胞,共50人,其中以台湾同胞为主;陪祭团四是当地的畲族村代表团,他们身穿经过特别设计的民族服饰参加,共50人;陪祭团五是仙都景区各村村民,由他们进行表演活动,仅有24人;陪祭团六是游客与民众,近千人。[注]《浙江缙云仙都清明节的调查报告》,参见浙江师范大学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251页。这份节日人员的名单,揭示了节日的资本来源与权力结构。通过此次节日,体制内的地方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体制外的政治—经济精英强化了他们的合法性身份与资本的正当性,使地方的权力模式和既有秩序得到再生产。正如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兹所说,精英们“根据一系列要么是继承的,要么是在更革命的条件下他们自己创造的故事、庆典、徽章、仪式和附属物,来使他们的存在正当化,并赋予他们的行动以秩序”[注]C.Geertz,“Centers, Kings and Charisma: Reflections on the Symbolics of Power.” in Local Knowledge: Future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1983,pp.121-146.。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地方普通民众在仪式中居于权力的边缘结构,他们似乎只是因为“表演节日”才被允许进入陪祭的行列中去的,不过,正是通过这一认可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合法仪式,当地的村落民众才能拥有长期稳定地进行祭祀的权力与可能,那么,以后的家祭与庙祭都可能成为合法和公开的民间信仰活动。因此,他们也是仪式的受益者,在不触及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重新塑造了自身的民间传统节日,使其得以再生产。“人们在开展民间文化的复兴活动时,有时候越是能够成功规避国家的力量,就越是容易顺利地开展活动;有时候越是能够成功地利用国家的力量,就越是容易发展。”[注]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325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传统的复兴也可以说是国家与地方、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一场文化共谋。在传统节日复兴的过程中,地方文化的意义在突显国家话语力量的节日仪式中,被明显地非地方化(deindigenization)了。
结 语
在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中,以村落社区为基本单位开展的岁时节日是农业文化的必要产物,节日的性质、内容和功能无一不与处理与完善人—自然的关系这一农业主题有密切关联。传统的村落节日由于其凝聚社区团结、传承地方知识、增强道德教化、娱乐身心等重要功能,是周期性农业生活的必要环节,在村落民众中具有自在与自发的生存机制。
然而在逐步走向商品化、工业化、城市(镇)化的现代社会中,即便是在乡村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得间接与隐晦。农村的年轻一代不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向往城市生活,更乐于从事工商业;城市扩大化使得许多农业耕地处于各种开发商的包围之中,使得传统农业无以为计;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涌向城镇与都市,他们在市场中艰难地寻找一席之地。我们正面临一个日益远离土地与农耕的“新乡土中国”。“现代节日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没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它已经较少有时间坐标的意义,也不再有与民众生命息息相关的力度……”[注]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0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地方社会复兴起来的节日往往只是具有传统形式的现代性节日。新的语境中复兴起来的地方性节日,有时在形式与仪礼上还保留着传统的意味,但其文化象征意义与社会功能都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强化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地方与国家之间的现代关系,并且已经超越了传统村落和地方性的地理—文化边界,以实现对人际关系、权力结构、象征性资本和国家符号的地方社会再生产。而这些,都是现代性的结果与需求。传统文化的复兴是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它一头联系着过去的传统,一头连接着当下的现代,其真正的价值在于文化主体对于历史和现实关系的再理解、再阐释与再生产,从而完成文化历史性的更新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