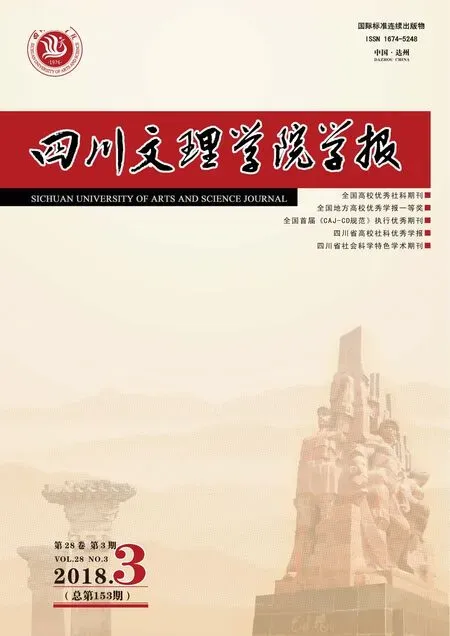略论达州闪小说作品里的人物众生相
——以《川东文学》达州闪小说群体联展为例
2018-04-03钟钦
钟 钦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四川 达州 635000)
字数在600字内的闪小说,源自英文“flash fiction”,“flash”意即“闪光的、闪耀的、一闪而过”,“fiction”意为“小说,虚构的文学作品”。顾名思义“flash fiction”即为一闪而过的微短小说,其具有小说特质,且易于信息时代多渠道传播。西方的“flash fiction”,前有伊索寓言,后有契诃夫、欧·亨利、卡夫卡。汉语闪小说在先秦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搜神记》《世说新语》《笑林广记》《聊斋志异》里俯首可拾。据云,世界上最短小说仅三个字:神垂死。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弗里蒂克·布朗一篇25字的科幻小说:“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堪称闪小说绝世经典。闪小说应运而生是因为它最适应当下生活节奏、情绪宣泄、传播方式和阅读需求,其特点自然是篇幅超短,立意新奇,构思精巧,一针见血,杯中兴波。在今天人们的文学观念中,所谓小说,它是一种以创造虚拟世界为方式、以诉说生命体验为重心、以情节为元素、以反讽为基调的语言艺术。小说情节的安排大致的两种方式:一曰叙事的相对集中,或曰情节的戏剧化;二曰叙事的相对扩展,或曰情节的内在化。闪小说在这些方面,无疑语言更精粹,选材更严格,开掘更深入,在情节上更为戏剧化。
《川东文学》2017年夏季号的达州闪小说群体联展,展出了达州籍且目前大都生活工作在达州的智若愚、杨祚华、黎凡、唐端、侯文秀、廖维、王大举、李柯漂、卢贵清、胡兴雄、谭帅、李佑伦12位作者的闪小说。唐端、黎凡、侯文秀、廖维四名女将尤为可贵,这无异使小说创作女作家寥若晨星的巴山作家群里,迎来更璀璨的星空。
纵观达州的闪小说创作,可谓是底层作家书写着底层人物的生态百相。这些闪小说作者,几乎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工人、农民工、护士、乡村干部、小学教师等,“作家以艺术的形式观察生活现实,这种艺术形式已成为他们表现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这就注定了他们的闪小说创作,眼光向下,书写底层人物,关注小人物的命运遭际。他们的闪小说,也就书写着农民、普通小市民、退休职工、残疾儿童、被拐卖的妇女、精准扶贫对象、乡村干部等这些生活在底层的草根阶层普通百姓,最大的官员(其实压根就算不上官员),无外乎是乡上的公职人员。以情节的戏剧化手法,高度凝练生活,通过凡人琐事杯中兴波,反映底层的喜怒哀乐,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机智、敏感,对现实生活的某个场景、某个瞬间的瞬间把握,使其方寸之地积聚起巨大的爆发力,彰显艺术魅力、显现艺术高度,深刻地表现出对人性,特别是对底层文化里的人情世故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的洞察,进而引起读者心弦的颤动,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
一、“苦”的霸凌与温馨
现实生活“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2]智若愚(本名唐自勇)是乡村干部,他的《全频道》写妻管严的全频道耳朵张老二,他老婆的招牌动作,就是一生气,不管什么场合,嘴里不停叫骂着,伸手揪住张老二的耳朵,或左或右地使劲扭动,就像扭黑白电视机的频道一样。所以张老二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全频道”。张老二在临死前,几次张嘴要说什么,却没发出声。他老婆的手照例在张老二的耳朵上,以为他想吃什么,“张老二摇了摇头”。老婆又以为他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张老二又轻轻地摇了摇头”。以为他还有什么事没有做完,“张老二张了张嘴,缓慢地举起右手,伸向老婆的耳朵”。他老婆如梦初醒,“我知道了,我扭了你一辈子的耳朵,你都没有扭过我一回,是不是也想扭扭我的耳朵?”张老二点了点头,马上又摇了摇头,“抓住老婆的手,慢慢地举到自己的耳朵边”,“一字一句说道,你,你,再扭,一扭,我的,耳朵,我这,一走,你,你就,你就,再没有,没有耳朵扭了”。他老婆一下子抱住张老二,把他的手放在自己耳朵上,哭着要一辈子也“没有扭过我的耳朵”的张老二“你扭哇,使劲扭哇,把我也扭成个全频道”时,可是张老二已经断气了。写出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苦”的夫妻情深:苦涩而甜蜜,蛮横而温馨,隐秘的施虐与受虐等,业已成为了习惯的奇妙心理。这种“苦”,是一种中国底层文化语境中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但其内在包含了底层社会里夫妻间深厚的爱和包容。读来令人潸然泪下。巴尔扎克说:“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无足取了。”[3]《全频道》以“扶质立干”细节聚焦的手法,刻画人物,突出主旨。其细节堪称典范,与严监生临死前伸出的两个指头,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为乡村干部杨祚华,同样写乡场文化的《下棋》,则是写老年男人的霸凌与宽仁,写了象棋的常胜将军张老头,和他屡战屡败的对手王老头,两个人都很较真而且固执,一个赢得高兴得胜不饶人,一个输得郁闷“愤愤地丢下棋子,掉在地上”,“输了心情,比输啥子都重要!”便推枰不下。“于是,俩老头背对背,各抽各的烟,各喝各的茶。”算是“友尽情灭”,真个是老小老小老来还小。但他们毕竟不是小孩,而是黄土埋了半截的老头,明晓老来友伴的来之不易,更需要包容,需要宽仁大度,当王老头在瞎溜达多时,看到“张老头兀自枯坐在黄桷树下”,就主动上前和解,继续下棋。张老头也不是一根筋的人,下棋虽说是娱乐,不输钱输命,到底关乎心情,便借坡下驴。两人“与先前不同的是,张老头赢一盘,让王老头赢一盘”,最后一盘下和棋,“不分输赢,笑呵呵地跨进了小酒馆”。
二、“爱”的迷失与弥补
侯文秀的《粉红色内裤》,写了一种我们的父母那一代的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深。酷暑天,父亲从乡下来到城里接放假的孙子到乡下小住,晚上父亲洗澡换下衣服,“我”看见父亲的内裤“凸现无数个小毛球,并裸露着粗白线缝补的线头”,几乎无法再穿了,遂带父亲进商场买内裤。当“我”在收银台久候不到父亲去找他时,才发现父亲居然在琳琅满目的女士内裤处,试穿一条粉红色内裤,顾客们都对他“窃窃私语,指指点点”。“我”自然觉得分外丢脸,粗暴地拉走父亲,不再买内裤。但父亲固执地返回去,认真地和“服务员一条条试大小”,“最后父亲选了一条蓝色和一条粉红色。”昂起头,理直气壮到试衣间“换上新内裤”。并从垃圾桶里捡起了“我”随手扔掉的旧内裤,宝贝似的抱在胸前。“内裤有你妈缝的荷包,把钱搁里面保险哩。现在你妈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使了,没法再为我缝制新荷包了……”父亲被小偷偷过几次钱,母亲才在他的每条内裤里缝上装钱的口袋。而那条粉红色的内裤,是父亲专门“给你妈买的。这里的内裤摸着柔和,不像我们小场镇卖的,穿在身上扎肉……”我们的父母,他们的精神层面他们的心灵内核,都在彼此依恋着彼此搀扶着,一步一步实实在在走着人生的路。闪小说作家需要有一双慧眼,擅长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创作素材,侯文秀《粉红色内裤》,就慧眼独具,生活琐事中看到爱的密码。真是一花一菩提,一沙一世界。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说:“在一粒沙中,看到全世界,在一朵野花中,见到天堂,将无垠,握在掌中,见永恒,于一剎那。”
李佑伦的闪小说《肇事者》则是写的“回来了被留下”的故事。小说构思巧妙,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不断设悬。从前挂在裤腰上的BP机,戏称为“裤腰门铃”,现在的手机则被戏称为“牵狗绳”。“一个电话,儿了回来了,风驰电掣。又一个电话,儿子又走了,烟消云散。电话里,儿子召之即来;电话里,儿子呼之即去。”父亲想留儿子在家多呆一下,真是煞费苦心:先是儿子的车子轮胎没气了,儿子换上备胎,转身又没了气,反而瘪了两个轮子,于是补胎。父亲从镇上请回补胎的师傅,补到了午饭时分,儿子不得已留下来吃了午饭。饭后,又要走了的儿子的车轮胎又瘪了。父亲装作不知情,假意打骂拴在车旁守车的狗,真不知情的母亲骂人不骂狗,骂到了“肇事者”的祖上八代和重孙千代。“父亲瞪她一眼,哪个放的气,你骂哪个就行了,关他祖宗儿孙干嘛。母亲仍不改口,父亲就扬起手来,准备朝母亲盖过去。”此时此刻,聪明的儿子终于明白,这三次轮胎瘪了,都是父亲的杰作。“爸——”儿子“眼泪花花”,“今晚不走了……”“父亲身子一抖,手臂慢慢垂下,扭过脸……”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人人都在奔波不息,快得连灵魂都跟不上脚步,当父亲的多么希望在外打拼的儿子回到家,多呆那么一阵,而悄悄让儿子的轮胎瘪了三次,儿子也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而留了下来。广西作家鬼子的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主人公李四的子女们都在瓦城工作,李四时时望着他们回来,李四的妻子说子女们“不回来就又是忙”。李四六十大寿,儿女们都忘了回家,李四于是到城里找儿女们给自己过生日,结果导致妻亡夫死。儿女们“就都把原因归结为太忙了,实在是太忙了,整天都在忙,忙得人的脑子都热哄哄的,像被火烧着了一样。可不忙行吗?不忙怎么活下去呢?你不忙,别人忙呀,别人就会当着你的面,把所有的好东西,一样一样地抢走,最后会把你碗里的饭也抢走,你说你不忙你怎么办?”可是,各种忙的结果,真的是我们的灵魂所需要的吗?诚如耶稣所说:“赢了全世界,却丢掉了灵魂。”
心中有阳光,才会有大爱,也才会有充满阳光的生活,也才会用这阳光去照耀他人。廖维的《阳光的约定》写“我”在写作过程中,被一个见过面没说过话的双腿瘫痪坐轮椅的邻家小男孩,用镜子反射阳光有意干扰,不得不停下写作,走出屋去,小男孩见到“我”有些胆怯:“阿姨,我就是想用镜子里的太阳光反光,把你从屋子里面引出来”,“我爸爸妈妈天天去干活不在家,我想让你陪我玩”。无疑,这个小男孩是异常孤独忧伤的,“我”弯腰抱起孩子,并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告诉他什么时间想“我”陪他玩,什么就用镜子将阳光打进“我”的窗子。看似简单的动作与话语,却充满了温馨的大爱,温馨的力量。小男孩的心温暖了,“非常兴奋”,与我“拉钩”,定下不反悔的“死约定”。一件很小的事情,廖维娓娓道来,字里行间都是盈盈的爱的终极关怀。她将阳光洒向每一个角落,带给人以温暖和爱,使这个残缺的世界完美一点,使这世上的人多一些快乐。《阳光的约定》以小见大,诠释了大爱这个文学作品的根本目的。
三、“痛”的悲怆与彷徨
“小说不是现实的写照,而是独立的存在。”[4]255被拐卖后成为山村女教师的郜艳敏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艰辛与无奈,我们被一点点伤害侵蚀,磨去所有的棱角,我们只是活着却没有了生活,却又于绝望中去寻获萤火虫般的希望,并让我们的生活尽量有一抹亮色。唐端的《樱桃树》写了类似这样一个十分悲催的热点问题,与娘一起在院内栽了樱桃树的南方的小丽被拐卖到了北方,多年逃跑失败后,男人应许她挖来一棵樱桃树栽在这北方的院内,小丽每天给这棵“樱桃树浇水,陪樱桃树说话”,“喊娘,喊娘的时候泪水湿了衣襟”。樱桃树越长越大,小丽在樱桃树下的时间越来越久,梦里也全是家乡的樱桃树,娘在樱桃树下成了雕像。“丽——丽——丽,娘在这里。”小丽心如针扎。最终小丽被解救回家,在南方家乡的樱桃树下,小丽扑入了白发老娘的怀中,可是回乡的小丽,夜夜梦见的是北方的那棵樱桃树。怎么办?小丽可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薇拉。在这块土地上,不知道有多少个“小丽”永远生活在这种无边无际的“痛”中。小丽可以被拯救,但这种“痛”,怎么弥补?《樱桃树》构思精巧,写出了生活异端的爱恨交织的痛苦。
四、“怨”的烦恼与痴愁
唐端的另一篇《爱》,写爱上男同事的慧,春节期间因为见不到所爱的人而觉得时间慢得像蜗牛。但当她妆容精致提前到单位,见到爱了多年的男人时,看到的则是“他牵着一个女人的手。他们面前有一个小小的水坑,慧看见他双手一绕,便抱着女人轻松跨过水坑。”慧的心坍塌在了那个“在众人眼里养尊处优,连饭都不会做的”女人“温婉的笑容中”。“你样样都好,样样都比她强,你只有一个缺点——你不是她。”怎么办?慧的故事不是小丽的故事,自然也不同于薇拉。慧怎么办呢?小说撷取生活中的一朵小浪花,采用相对扩展的叙事手法,写出了当下社会的另一类说不得的“痴苦愁怨”。
王大举的闪小说《难吃的面条》与唐端的《爱》题材类似,视角不同,切入点不同,老婆从丈夫老郁落下的手机上,发现老郁有小三的蛛丝马迹,进而轻描淡写旁敲侧击,老郁谎称那里有家面馆,味道挺不错。两人都暗藏机锋,老婆“轻描淡写地问,吃碗面要三四个小时?”老郁也不正面回答:“老郁偷偷地斜了一眼老婆,装着若无其事地说,吃面人多,三四十分钟还是要的。”三四十分钟和三四个小时,相去何止一星半点,但老婆也不深究,“还是轻描淡写地说,明天带我去吃吃那个面条,我尝尝什么味?”老郁做贼心虚,饭后主动帮老婆打下手,这实际上欲盖弥彰,自欺欺人趁上洗手间做善后工作。翌日,老郁带老婆找到那家面馆,装出很好吃的样子,老婆尝了两口,依然“轻描淡写地说,这面也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呀?”老郁也觉得难吃,但不得不“吃得津津有味,把汤都喝得干干净净。”老婆掏出纸巾给老郁“这面条难吃,以后还是不要来吃了。”老郁“擦干嘴上的汤汁,笑笑说,“今天的面条确实没有原来好吃了。”夫妻二人真如说禅一般,处处在在都是机锋,大道无形,大音希声,不眈与形,不逐与力,不持与技。“老郁从面馆出来,回头朝世纪城小区那扇窗飞快地望了一眼,窗口,那个美丽的少妇探出半个头也在看他。”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怨”而不得。小说针砭世相,力透纸背,内涵丰富,耐人寻味。
五、“俗”的常态与反讽
杨祚华的《诨名》则是讽刺了总爱给别人乱取诨名乱喊诨名的乡村文化恶俗。以博戏谑一笑的乡调解办老汪汪善绪,把财政所长的家属(妻子)“何佳苏”故意喊成“我家属”,从而插科打诨,一图口舌之娱,结果被一个小学二年级学生把“绪”字认成了“猪”,而获得了“汪骟猪”诨名,真个是一饮一啄,吐丝自缚。毫无疑问,越是阳春白雪的地方,诨名绰号越少甚至没有。小说其实写出了下里巴人的乡场文化的一种“俗”的常态,诨名绰号是人们生活的调节器,多少宏大严肃的主题,就在诨名绰号里,逐步消解。这已浸润于每个底层人心中,成为日用而不觉。这也是乡间文化贫瘠精神寂寞的一种表现,间接地反映了建设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文化软实力的不易。浙江大学的殷企平先生在《小说艺术管窥》中说:“反讽即是预期的东西与发生的事情处于不调和的状态,通过表层意义使真正意义隐藏起来相互发生矛盾。”概略地说,反讽的实质即是存在层面和现实层面的不相协调。小说的反讽其实是一种智慧的提问与冷凌的观察。但它不叫嚷,不回答,小说中的反讽其实是一种文体意义上的规避与克制。
六、“恶”的延续与变异
李柯漂在500来字的《大姑》里,刻画了大姑这个特别势利的小市民形象。她没有文化,却极有前瞻性眼光,虽“扁担般大的‘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既不认识更不会写,然颇有头脑异常精明。俗话说:“就是做条狗,也要做城里的狗。”农村的穷困使大姑嫁不到城里,也要嫁到城镇边上去。看中并嫁给大姑父,“是因为大姑父家在小镇旁边。”她种菜养猪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后来的城镇化占用了大姑家老房子,大姑更富有了。可是大姑越富裕越吝啬,与亲戚也越生疏。真个是人情薄如纸,亲情寒似冰。小说在这里揭示了当下转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人越富人情越生疏。”在大姑的眼里也只有钱,当我打工十多年自认为混得不错去拜望大姑时,大姑一边炫富一边讥嘲我一边笑呵呵接过我妻子给她的红包,“谁说我什么都不认识?这钱我可认得真真的。”小说首尾照应,结尾更凸显了大姑的守财奴形象。因为过去穷怕了,现在有了钱就悭吝到了无法理喻的地步。大姑这类人物在当下乡村走向城市的转型过程中,类似城市里的“碰瓷”族,可谓是“恶”的延续与变异,但这样的“恶”当如何消弭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呢?
七、“欲”的焦虑与困境
王安忆指出:“小说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之外的心灵世界。”[4]277《华严经》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不忘初心即是不要忘记人最初的时候那颗本心,那颗与生俱来的善良、真诚、无邪、进取、宽容、博爱之心。对文字颇讲究的作家温瑞安有个小说人物名字就叫做初心,是四大名捕的追命崔略商的母亲,有个章节的标题就是《初心的粗心》,还有个章节标题叫《追命的命》,人物名字与标题,饶有趣味。黎凡的《初心》则是写的“我”(艾小姐)要求发明了“变脸”整容新仪器的吴博士,依照扫描“我”提供的出道前的照片而变回出道前的模样,这是“我”第五十次变脸,也是最后一次变脸,“这次变脸,是公司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由于“我”提供的出道前的照片上的女孩太普通,系统不但拒绝识别,而且根据我前四十九次变脸的大数据自动优化,给了我一张美若天仙无与伦比的美丽容颜。然而,“我”要的却是出道前“我”的本真模样,“我以不同的美丽脸蛋叱咤于各种场合,我累了”,“我回不去了”。小说杯水巨澜,以小见大,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深刻主题,我们奔着宏大的目标而去,到头来,我们却想回到原点,可又回不去了。不是我们左右生活,而是生活的洪流生活的漩涡挟裹着我们,掌控着我们。共同焦虑是今日社会转型变革的背景下,底层的普遍心理,蔓延出来的就是混沌的各种生存状态下的众生百相。其原因是“对日常秩序的偏离、对传统价值的叛逆”,[5]是生活“荒漠中的人性畸变、现代性语境下欲望的唤醒及再压抑……真正成为了个体的底层、暧昧的底层、充满悖论的底层、去价值化的底层。背后折射出时代普遍的精神困境”。[5]
八、“梦”的骨感与丰满
对底层生存窘境下生态百相的书写,容易使读者得出展示冷色的结论。但是,我们这个急剧变革风起云涌的时代,是有温度、有梦想、有情怀,有使命的时代,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提供着巨大的保障。卢贵清的《变卦》就写了精准扶贫中的一则小插曲,因贫困数十年都建不起房的牟大娘,住在年久失修的危房里,看到别人家的新房艳羡不已,但又由于贫困缺钱而坚决不改造危房,碰巧赶场回来,坐上了派往村里精准扶贫的第一书记小邓的长安车,小邓宣讲了精准扶贫脱贫奔康的政策和措施,牟大娘于是“我家房子马上拆旧建新,再也不得往后拖了”。她老伴李老头便要急匆匆去找风水先生来看地择期,不过,当知道小邓书记大学学的建筑专业,毕业后在建设局工作了五年,明天要来帮他们规划设计新房时,担心风水先生与小邓说的不一样,遂决定“那就只请小邓第一书记!”小说写了两次变卦,牟大娘由不修房子到转变为积极修房子,由请风水先生看地择期到请小邓书记规划设计,虽是小小的两次转变,却见微知著地反应了农村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新气象新变化,现实虽然骨感,然梦想毕竟丰满,而且在逐步实现美梦成真。卢贵清的《卖鱼》、李柯漂的《立冬》、侯文秀的《幸好不收礼》、谭帅的《送礼》,同样写出这种新气象新变化,读来令人倍感欣喜。
诚然,达州的闪小说创作近些年颇有佳绩,获奖甚众,作者和作品都接地气,有情怀,篇幅微短,短而不缺,简而不淡,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的底层人物形象,书写了底层的生态百相。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也达到了相对的高度。但不能否认,精品意识不强,思想容度上不够深邃,思想大于形象,观念远胜艺术。在题材多样化上,没能广阔地反映当今纷繁复杂的转型期社会生活。描写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刻画的人物层次单一,几乎见不到系列人物的系列闪小说,人物性格不鲜明,人物形象脸谱化现象严重,更未能通过塑造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命运,情节设置上还不能很好地做到“表现出人物行为的矛盾冲突,由此揭示人物命运变化的过程”。[6]不少作者的作品数量虽然多,但称得上精品的却不多。“文章得失不由天”,心血和艺术品的价值是成正比的。同时,在艺术表现上,闪小说最重要的欧·亨利手法尚不娴熟。此外,巴尔扎克说:“艺术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7]小说创作的根本仍然是语言,闪小说不仅要锤炼语言,也要擅用留白艺术。达到以小见大,以微显著,言约意丰,片言百意的艺术效果。达州闪小说的语言,大都说不上像邵雍所言:“炼辞得奇句,炼意得余味”,一些作者的语言也仅仅是做到了文从字顺,谈不上语言的美化。有的行文比较浮躁,这种浮躁,使得创作的文本都有不少谬误。作家的职责是要消除人们潜意识中的邪恶隐性,纯洁净化社会空气和人的魂灵,使那些假丑恶受到揭露而彰明,使正义、善良、爱和美德永存于天地之间,光耀千秋,从而“为世界贡献出原创的而又具普遍性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匈)巴拉兹.电影美学[M].何 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8:15.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0.
[3] (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G]//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73.
[4] 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课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5] 李 壮.青年作家与“新底层”[N].文艺报,2014-11-17(04).
[6]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261.
[7] (法)巴尔扎克.论艺术家[M]//巴尔扎克论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