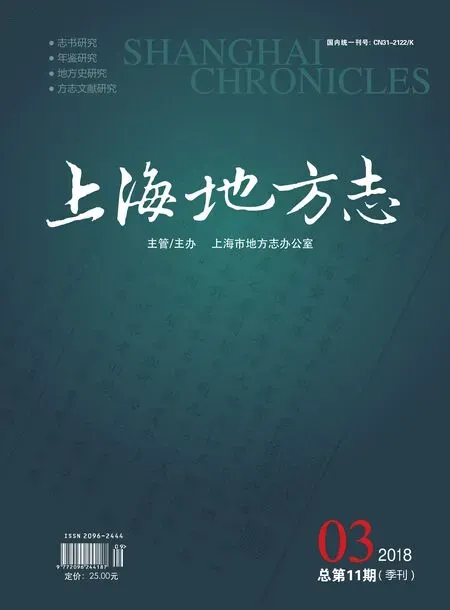乾隆《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考略
——兼及清乾隆前期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
2018-04-02赵心愚
赵心愚
在清代西北地区修纂的地方志中,杨应琚所纂乾隆《西宁府新志》是清代前期成书较早的一部府志。此志共四十卷,不仅分别记载了西宁府及所属西宁、碾伯二县等沿革、疆域、山川、风俗、物产、户口、盐法、兵制等诸多方面,而且涉及明塞外四卫、青海、西藏等地,由于编纂整严有法,体例周密,方志史研究者评价甚高,被列为著名方志。①张维赞此志“整严有法,而议论驰骤,高瞻远瞩,多经世之言。”见其著《陇右方志录》第18页,大北印书局1934年;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将此志列入著名方志,见辞典第121—122页,黄山书社1986年。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宁府新志》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有关论文已发表多篇,有的从此志内容分析杨应琚当时的民族关系思想,有的还涉及此志体例及编纂方法。②毛文炳:《清代西宁道杨应琚》,《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3期;陈亚艳:《从西宁府新志看杨应琚的民族关系思想及其实践》,《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4期。应指出的是,有学者已注意到此志中涉及青海藏区的记载并存在西藏篇目,故将此志作为藏区地方志收入藏区方志汇编之中。③张羽新:《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三十三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还有的学者在讨论清代西藏地方志产生时,明确将此志中的西藏篇目视作首批西藏方志之一,但对这一篇目及内容、资料等未进行全面分析。④肖幼林、黄辛建、彭升红:《我国首批西藏方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中国藏学》2009年4期。笔者以为,《西宁府新志》中的西藏篇目确为一成书较早的西藏简志,在清代西藏方志史的讨论中应对其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乾隆《西宁府新志》的纂修及西藏篇目的内容、记载特点
西宁元代为州,明代改为卫。清初沿明旧制仍为卫,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升西宁卫为府,并置西宁县为治所。次年,清又在当地设“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通称西宁办事大臣)。杨应琚,字佩之,号松门,辽海汉军正白旗人,乾隆中期已为著名封疆大吏之一。杨应琚雍正末年赴西宁,上任即重治边并倡办学,乾隆初年请准将贵德改隶西宁府。①《清史稿·杨应琚传》记其赴西宁上任时间有误,见汪受宽《清史稿杨应琚传笺校》,《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4期。明代西宁卫在嘉靖、万历年间曾两次修志,但嘉靖年所修志书清初已佚,万历年所修志书乾隆初年也仅部分尚存。进入清代后,顺治年间修有《西宁志》(又称《西镇志》),为清代西宁首修志书,但仅为初创,繁简失驭,材料亦显有限。久仕西宁,杨应琚了解当地民情、地情以及当地旧志情况,为西宁及周边地区的治理,同时也为《一统志》编纂提供资料,于是决定自纂一部新志。在《西宁府新志·序》中杨应琚言:“国有史,郡有志;志者一郡之史,史者天下之志也。然志为史之先资,贵详而有体。”“余承乏兹土十有余年,……于乾隆丙寅秋七月握管,至丁卯夏五,历十一月而脱稿”。②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序》,四川大学图书馆藏乾隆十二年刻本。本文所引《西宁府新志》材料,皆引自此版本。序中所言,表明其对地方志性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并明确纂修《西宁府新志》的具体时间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七月至次年五月。此序后署衔为“陕西分巡抚治西宁道按察使司佥事”。佥事在副使之下,《西宁府新志》的纂修即是杨在此任上完成。
杨应琚所纂《西宁府新志》乾隆十二年(1747年)成书,当年即刊行。此志为两级分目体,即先分大的门类,各门类之下再分目。全志总四十卷,卷首有杭世骏序、杨应琚序及凡例、目录,卷一为舆图,从卷二起为星野志、地理志、建置志、祠祀志、田赋志、武备志、官师志、献征志、纲领志、艺文志等十志,各志之下再分设百余目。此种体例,目以类归,层次清楚,所以张维赞其“整严有法”。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十志中的武备志。“武备”一词本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南宋时则成为地方志门目名。《西宁府新志》中,从卷十八至卷二十一均为武备志,其下再分设十余目。卷二十一即此志中之西藏篇目,具体设“西藏”“附国”并附“赴藏路程”,后两目实际上也与西藏相关。为何要将有关西藏的记述归入武备志?杨应琚在此志凡例中言:“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况西宁为极边之郡乎。逼介青海,环拱诸番,径通准夷,南达三藏,自古为用武之地。故特纂武备一志,凡兵制、戎器、驼马以及番族无不具载,并青海之始末,防范准夷之要隘,西藏之疆域、山川、风俗、户口、天时、人事亦附列焉,使守土握兵者知肯启之。”③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凡例》。这样的认识,武备志前后的小序及论中也有表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杨应琚突破不可越境而书的修志惯例,编纂西宁志时专设西藏篇目并将其归入武备志中。尽管西藏篇目未成为一级门目,但在《西宁府新志》中实际上仍单作一卷,为武备志的四分之一,这反映出杨应琚纂修此志时对西藏的重视以及当时对相关材料的把握程度。
《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主要内容见于“西藏”目。为记西藏自然、社会诸多方面情况,杨应琚在此目之下再分设“疆域”“形势”“山川”“古迹”“土则水利”“风俗”“物产”“关隘”“户口”“贡赋”“人事”“天时”“兵防”“寺庙”“剌麻”(即喇嘛,后皆同)等十五细目。“疆域”之前,还有一大段文字,从西藏分野写起,接着简要记西藏地区从唐代至清乾隆初年的历史沿革,最后记载的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封颇罗鼐次子珠弥纳木劄为长子。④珠弥纳木劄,《西藏志》译为朱米纳木查尔,《清史稿·傅清、拉布敦传》记为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郡王颇罗鼐的次子。此处称封珠弥纳木劄为“长子”,应是立其为“世子”,《西藏志》记其时间在乾隆九年,指确定由其袭爵位。见《西藏志·封爵》,吴丰培整理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这一大段内容前有“西藏”二字,应是目名,但也可视作细目名,其后这段内容实际上类似《西藏志·事迹》。若将其也视作一细目,总就十六细目。
“疆域”目中,除记西藏与西宁、成都的路程距离外,又分别记其东至、西至、南至、北至于何地。“形势”目在各细目中文字最少,仅“环山拱合为势,百源集流成江”两语。“山川”中,仅记有布达拉山、甲里必洞、牛魔山、东噶尔山、浪党山、甘丹山、禄马岭、瓦合一柱剌山、过脚山、阿里山、克里野山及乳牛山等近十余座山和大河、怒江两川。“古迹”目从布达拉寺塔、琉璃桥开始记,在记拉萨大诏门外唐碑时,照录其全部碑文,最后以古纪功碑文结束。“土则水利”目文字较多,记西藏水旱田地及江河船筏济渡与蓄水为圩等。“风俗”目文字仅多于形势,简要记信佛崇僧与婚丧等。“物产”目所记明显不分类,笼统记西藏多种矿物、植物与动物,有松蕊石、青金石,也有茜草、藏枣,还有牦牛、犏牛等。“关隘”目所记内容不多,只记藏东、藏西的汤家古索、东噶尔关等五处关隘。“户口”目所记较详,分为藏王颇罗鼐所管、雍正十年分归西藏管辖及赏给达赖剌麻三部分记,除记户数、人口数外,还记寺庙数及剌麻数。“贡赋”目文字亦不多,贡、赋划分也不太明确,但数量具体,分西藏辖下和赏给达赖剌麻辖下两部分记。“人事”目先记官多世袭,然后从藏王之下噶隆开始记各级官员,一直记到各地头人,但之后又记农事、工匠、贸易、医药卜筮、交接礼仪、居室、衣冠、刑法等,诸多内容归于此目,显得多且杂。“天时”目内容分三部分,先记西藏星象,再记西藏历法,最后记西藏一年四季气候及变化特点。“兵防”目记载较细,先记西藏马兵总数及驻拉撒(即拉萨,后皆同)等地马兵数,次记阿里及后藏步兵总数及各地马步兵作战能力、甲胄、兵制等。“寺庙”目内容不多,仅记大诏寺、小诏寺及甘丹寺等十座寺庙。为何如此?著者在此目后言:“西藏寺庙甚多,不能尽载,择其名尤著者录于右”。①杨应琚:《西宁府新志·武备志·西藏》“寺庙”。这清楚地反映出,编纂时杨应琚对材料是有所选择的。“剌麻”一目在各细目中文字最多,材料也十分丰富。此目从何为剌麻写起,又简要介绍其服饰与佛书,然后就以大段文字纵向记元明时期剌麻被中央政府封为法王的情况,尤以明代的记载最详,从洪武到万历各朝均有涉及。最后,以“自西宁剌麻宗噶巴抵藏甘丹寺坐床设教,戴黄帽,禁其徒妄作,以静坐修禅为本,谓之黄教,其教今大盛云”结束。②杨应琚:《西宁府新志·武备志·西藏》“剌麻”。
以上各细目所记即为西藏篇目的主要内容。其后为“附国”目,文字较短,记有后套、后藏及巴尔布、布鲁克巴距诏或藏的里程及当地简要情况。“附国”目之后又附“自西宁至藏路程”,实际上亦为一目。这两目所记,亦是西藏篇目的内容。再其后,为以“松门杨氏曰”五字开始的志论。值得注意的是,论中明确说:“……乌斯藏疆域、山川、古迹、关隘、户口、兵防、天时、人事,亦备细附列焉。欲莅兹土者,知地利而为之防范也”。③杨应琚:《西宁府新志·武备志·西藏》“论”。论中此语,再次强调其编纂西宁志时专设西藏篇目的用意。
分析《西宁府新志》西藏篇目的内容,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记载特点。
1.所记内容地域范围非常清楚,即明确记雍正年间川滇藏与川青藏划界之后的西藏。在西藏目之下所设十五细目具体内容及疆域之前类似《西藏志·事迹》那段文字中,不论是自然方面还是社会方面的记载,均只记划界后西藏之内的情况,川滇青藏区情况则不纳入记载,“疆域”细目中还明确记西藏与四川、青海分界。附国目所记也只与西藏相关,实际上仍反映了编纂者确定的志书记载地域范围。自西宁至藏路程虽然涉及青海及西宁,但编纂者将其明确定位为“附”,也反映出编纂者确定的记载地域范围。方志编纂应明确所编志书地域范围,并在内容中始终注意。杨应琚纂修此志时对西藏地域范围的明确及始终加以注意,反映出自雍正年间划界至乾隆十年左右,人们已清楚西藏的地域范围。
2.既较全面记载西藏各方面情况,又注意突出西藏的文化特点。通过“疆域”“形势”“山川”“古迹”“土则水利”“风俗”“物产”“关隘”“户口”“贡赋”“人事”“天时”“兵防”“寺庙”“剌麻”等十五细目及疆域之前类似历史沿革的那段记载,《西宁府新志》在乾隆初年的条件下仍比较全面的记载了西藏与中央王朝关系及西藏自然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但编纂者注意全面性的同时又注意在内容中反映西藏的特点。读此志可看出,纂修此志时杨应琚首先在细目设置时设有“寺庙”“剌麻”等细目,之后又设有“附国”目及所附“自西宁至藏路程”,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藏的特点;其次在“山川”“古迹”“土则水利”“风俗”“物产”“关隘”“户口”“贡赋”“人事”“天时”“兵防”等细目的内容中,又通过具体材料反映西藏在各方面的特点。
3.在具体记述中注意反映相关内容为《西宁府新志》所记,即在一些细目内容中有意识提及西藏与西宁、青海的关系。如“疆域”细目中,就首先记西藏在西宁南三千六百七十里,之后又记北至木鲁乌苏噶尔藏胡叉交青海番族界。“山川”细目编纂者只记有布达拉山、甲里必洞、东噶尔山等近十座山,其中后面几座山是有选择的记入,在过脚山之后的双行小字注中明确注明:北通青海,乃屏藩之区。关隘目记有木鲁乌苏河口,其双行小字注中亦明确注明:在藏东北二千九百里,与西宁番属交界。这样的情况在其他一些细目中也有,即使在“剌麻”一目,最后也有“自西宁剌麻宗噶巴抵藏甘丹寺坐床设教,戴黄帽,禁其徒妄作,以静坐修禅为本,谓之黄教,其教今大盛云”语。
4.各细目内容有详有略,篇幅不求一致。前已言及,《西宁府新志》中“形势”目在各细目中的文字最少,仅“环山拱合为势,百源集流成江”两语,但“剌麻”一目材料十分丰富,在各细目中篇幅最长,达2000字左右,其余各细目,长短也不一。分析各细目所记内容,可看出编纂者对材料是有整理、鉴别及选择的,各细目的内容多少及篇幅长短是根据其编纂需要再采择材料确定。因此,编纂者首先考虑的是记载清楚与说明问题,并非篇幅长短的一致。
二、乾隆《西宁府新志》的资料来源
资料是地方志编纂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没有资料的广泛收集与整理、鉴别,志书的编纂不可能真正得到落实,更不可能编纂出一部能得到后人肯定的名志。《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共9300余字,涉及西藏历史与现状诸多方面,没有较多的资料占有是难以完成的。分析此志自序及凡例的内容,可以认为杨应琚决定修此志时已在注意相关资料的收寻。在《西宁府新志·序》中杨应琚言:“湟中旧志久失,而见存者荒谬不雅训,……文献无征,是西宁郡志作者为尤难也”。①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序》。在《西宁府新志·凡例》中又言:“按旧西镇志(即《西宁志》),仅寥寥二本,重刊于顺治丁酉”,还提到“陕甘旧志”“历代史志”及“采谚征谣”等等。②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凡例》。新志编纂时,其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为史志。李泰棻在其著作中专门用一章讨论方志的资料问题,“记录的资料”为一大类,其中“属于史书者”与“属于志书者”即为这一大类中的两类。③李泰棻:《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作为新志编纂者,杨应琚深知这一重要资料来源,故在自序及凡例中有以上所言。《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与此志其他部分不同,专记西藏地区历史与现状的诸方面,西宁旧志或陕甘旧志中可利用的相关资料必然很少,尽管自序及凡例中未谈及其具体资料来源,但分析、比较之后可知,除了较为有限的调查材料外,未到过西藏的杨应琚修志时应掌握了多部西藏地方志及记有西藏历史的史籍。这些西藏地方志及记有西藏历史的史籍,即《西宁府新志》西藏篇目的主要资料来源。为了解其资料的来源及资料的选择、运用情况,下面对几个细目(包括相当于细目者)的部分内容作简要的比较、分析。
首先是“疆域”之前类似《西藏志·事迹》那一大段文字,前已指出,这段内容也可视作一细目。与《西藏志·事迹》比较,其中可发现一些相同相似之处,但又存在不少不同点。如,此段带总体记述性质的内容开始即言:“藏地,于天官井鬼之分野也。历为图伯特国,诸史多未及载。考其地,即西吐蕃也。唐孝德皇帝于大诏寺立有甥舅联姻碑记。元世祖以其地之大剌麻八思巴为大宝法王,赐玉印。前明为乌斯藏。又称为康、卫、藏,康即今之叉木多,卫即今之西藏,藏即今之后藏扎什隆布,总谓之唐古忒。”①杨应琚:《西宁府新志·武备志·西藏》。比较之后就可看出,这一段文字中有不少异同。首先,“藏地,于天官井鬼之分野也”语在《西藏志·事迹》中虽有,但并不在此段之前,并多“藏地”二字,而且“天官”作“天文”;其次,从“历为图伯特国,诸史多未及载”起,到“藏即今之后藏扎什隆布”止,不少语句虽也多见于《西藏志·事迹》中,但其中的一些内容又不见,而且语句先后亦不同;再次,“总谓之唐古忒”语,《西藏志·事迹》中因前已言“今曰图伯特”故有“又曰唐古忒”语,这段内容中的“总谓之唐古忒”是就康、卫、藏而言,二者也存在不同。②《西藏志·事迹》,吴丰培整理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本文所引《西藏志》各目材料,皆引自此版本。出现异同可能是因改写,但有的文字也可能参考了另一部早期西藏地方志——雍正《四川通志·西域》。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一《西域》在“疆域”之前亦有一大段文字,开始即言:西藏“在工布江达以西,为图伯特国,又称为康、卫、藏,康即今之叉木多,卫即今之西藏,藏即今之后藏扎什隆布”。③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一《西域》,四库全书本。本文所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材料,皆引自此版本。这一段文字除前面七字不同外,后面可说完全一致。接下来在记吐蕃历史时,又有“其唐公主所下嫁者为苏隆藏干布,其祖为纳礼布,乃额勒特莽固礼之后,马克扎巴之子,传数世至苏隆藏干布,其势始大”语。《西藏志·事迹》中则记为:“自唐孝德皇帝以公主下嫁蕃王和亲后,始于中国通往来。其国之始为君者,乃额勒特莽固礼之后,马克已之子纳礼藏布,传数世至苏隆藏干布,其势始大”。可能因脱误造成人名有所不同,语句也有明显改动,但比较之后仍可看出二者基本一致。“疆域”前类似《西藏志·事迹》那段内容共千余字,尽管删改较多,后面又有明显的补充,但通过以上比较,可肯定成书于雍正末及乾隆初刊印的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及《西藏志》抄本是《西宁府新志》西藏篇目的资料来源。
相对而言,《西宁府新志》“山川”“古迹”“寺庙”等细目的资料来源较为清楚。前已言及,“山川”目仅记有布达拉山、甲里必洞、牛魔山、东噶尔山、浪党山、甘丹山、禄马岭、瓦合一柱剌山、过脚山、阿里山、克里野山及乳牛山等近十余座山和大河、怒江两川。比较其具体记载,可发现所记山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中西藏“山川”目及《西藏志·山川》目的部分内容基本相同。其中,从布达拉山到甘丹山这六座山山名与排列顺序及小字注,均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中西藏“山川”目相同;从禄马岭到克里野山,山名与《西藏志·山川》目所记东方之山、西方之山及北方之山中的几座山同,尽管只选择了几座山,其小字注也明显有增删,但也明显利用了其资料。“山川”目仅记两川,其中大河及小字注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中西藏“山川”目中所记大河基本同。另一川为怒江,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中未记此川,《西藏志·山川》目所记南方之川中有怒江,但其小字注也仅“即外夷界,不可渡”一语。比较之后发现,编纂者是利用《西藏志·疆圉》“西藏南至珞瑜茹巴之怒江为界”这一段内容中的大部分材料,丰富了怒江的小字注。“古迹”目从布达拉寺塔开始记,在记拉萨大诏门外唐碑时照录其全部碑文,最后以古纪功碑文结束。其中,布达拉寺塔、琉璃桥、水阁凉亭、花园、宠斯岗等名称与排列顺序及小字注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中西藏“古迹”目所记同。此目中的经园、海中寺、唐公主遗像等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古迹”目无,编纂者是利用了《西藏志·寺庙》中疏日岗(小字注中误为疏目岗)、多尔吉拔母宫及大召中相关材料,名称亦为编纂者所加。此目中的唐碑,其注基本利用了《西藏志·寺庙》大召中相关内容,碑文则照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所附“唐德宗御制西藏碑文”。此目最后的古纪功碑注及碑文,均照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所附相关内容。西藏寺庙很多,但“寺庙”目仅记大诏寺、小诏寺及甘丹寺等十座。比较之后可看出,从大诏寺到桑鸢寺这前七座寺庙名称与顺序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中西藏“寺庙”一致,但部分寺庙小字注文字有压缩或改动;其后的仍仲宁翁结巴寺、撒家寺、热正寺三寺则利用了《西藏志·寺庙》中三寺的记载,但将热正寺误为执正寺,小字注亦有增删。
与以上三目资料来自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及《西藏志》不同,《西宁府新志》“物产”“关隘”“贡赋”等目的资料几乎全部摘自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中西藏所记相关内容。“物产”所记前三十九种名称与顺序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中“物产”一致,只是将最后的马骡改为六畜并加注,再加奇松一种。“关隘”目内容不多,只记汤家古索、东噶尔关等五处关隘。比较其记载,这五处关隘名称、顺序及小字注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中西藏“关隘”所记完全相同。“贡赋”目内容亦不多,比较后亦可看出,所记西藏辖下和赏给达赖剌麻辖下两部分认纳钱粮、贡品及数额也均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中西藏“贡赋”内容相同。
通过以上简要的比较、分析,可看出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及乾隆《西藏志》两志是以上各目的主要资料来源。除所举几目外,其他一些目的资料也多有这样的情况,由于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但以下几目资料来源有所不同,需要再作比较、分析。“天时”“剌麻”等目从具体内容看,其资料与最早成书的清代西藏地方志《藏纪概》及乾隆初成书的《西藏志考》应存在某种关系。“天时”内容记西藏星象、西藏历法及西藏一年四季气候与变化特点。其开始为:“自木鲁乌苏西一路至乌斯藏,每晚日落见星,仰观经星及星象,觉光芒闪烁较中土为更大,历夏秋冬三季,并不见北斗七星”。这一段与《藏纪概》卷之尾“藏天异”开始一段文字相似。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基本照录《藏纪概》卷之尾内容,但略有修改。《藏纪概》卷之尾“藏天异”中有“历春夏秋冬四季”语,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中改为“历夏秋冬三季”。但其后的“夜亦见露,秋季终有薄霜”语,雍正《四川通志·西域》改为“夜亦有露,秋冬有薄霜”,把关键时间“秋季终”改为“秋冬”。“天时”目中,作“秋终有薄霜”。从“天时”目所记看,资料出自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可能性较大,但仍可能参考了《藏纪概》卷之尾“藏天异”。①李风彩:《藏纪概》,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吴丰培先生认为,《藏纪概》成书“远在雍正五年以前”,并称此志为“藏地志乘之首”。吴丰培《藏纪概·跋》,《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此外,还有可能参考了乾隆四年刊印的《雅州府志·西域》中的“藏天异”,因《雅州府志·西域》也基本抄录了《藏纪概》卷之尾的内容。②乾隆《雅州府志》卷十二《西域》,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光绪补刻本。需要注意的是,“天时”目又有“亦有闰月,但其闰月不同时耳。如,壬子年闰五月,其地闰正月;乙卯年闰四月,其地于甲寅年闰七月……”语。对此《西藏志·纪年》记为:“仍有闰月,但其闰月不同时耳。如,雍正十年壬子闰五月,其地闰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闰四月,其地于甲寅年闰七月……”。另一早期清代西藏地方志《西藏志考·属相纪年》则作:“仍有闰月,但其闰月不与同时耳。如,壬子年闰五月,其地闰正月;乙卯年闰四月,其地于甲寅年闰七月……”。③《西藏志考》,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抄稿本方志从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三者比较,资料摘自《西藏志考·属相纪年》可能性大,当然可能也参考了《西藏志·纪年》。前已指出,“剌麻”目在各细目中字数最多,达2000字左右。分析、比较其内容,除开始的“(剌麻)即中国之释子,其僧家内典皆自番经译出,然惟西藏为甚多,凡出家者,不娶妻,著红黄衣”语外,基本抄录了《明史·西域》(三)中“乌斯藏大宝法王”的材料,一直到“不复能施其号令矣”止。④《明史》,《西域》(三),卷三三一,列传二一九,中华书局1974年。值得注意的是,此目主要内容之后,列出著名楞布气、呼图兔多名。“剌麻”目所列名称、顺序为:“西都楞布气、多尔吉拔母、扎什楞布气、三巴呼图兔、噶尔吗呼图兔、阿吗记仲呼图兔、阿里竹孙呼图兔、阿噶仲吉、地母呼图兔”。《西藏志·寺庙》中也有相近记载,前三者基本一致,只是“扎什楞布气”作“扎萨楞布气”,但“呼图兔”皆作“呼图克图”。《西藏志考·寺庙名色》亦有记载,但前二者无,“扎什楞布气”作“扎撒楞布气”,其后也均作“呼图兔”,不作“呼图克图”。分析、比较后可以认为,“剌麻”目资料除基本抄录了《明史·西域》(三)中“乌斯藏大宝法王”材料外,摘自《西藏志考·属相纪年》可能性很大,但同时又应参考了《西藏志·寺庙》的相关记载。
三、《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与乾隆前期西藏地方志的发展
有清一代,至雍正年才出现了具有方志体例的西藏地方志。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李凤彩所纂《藏纪概》成书在雍正五年以前,为私人编撰的最早清代西藏方志。雍正《四川通志》开局于雍正十一年,两年后成书,乾隆元年(1736年)正式刊行。此志卷二十一为“西域”,为目前已知的官方编纂的最早清代西藏地方志,而且从体例看更具方志特点。这部官方编纂的最早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出现,开了清代官方修西藏地方志的先河。①何金文:《西藏志书述略》,第9页,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在雍正时期成书的这两志之后,又先后出现《西藏志考》与《西藏志》。这两部西藏地方志均单独以方志著作形式出现,成书时间比前二者稍晚。《西藏志考》,无名氏纂,清代、民国时期只有抄本流传,人们过去将其视为是《西藏志》的一种抄本。《西藏志》,无名氏纂,乾隆前期、中期也只有抄本流传,乾隆末年和宁将其刊刻印行。将《西藏志考》与《西藏志》的篇目、内容及行文风格一一比较后可发现,《西藏志考》并非《西藏志》的抄本,实际上《西藏志》当是在其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由于存在这样的关系,《西藏志考》与《西藏志》可视为是内容相近的两部方志著作。②有研究者认为,《西藏志考》是抄自乾隆元年成书的《西域全书》,而《西藏志》则是在《西域全书》修补本基础上编成。这一发现有重要意义,也证明《西藏志考》与《西藏志》内容上的确存在关系。见刘凤强:《〈西域全书〉考——兼论〈西藏志考〉、〈西藏志〉的编纂问题》,《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从其内容材料下限看,《西藏志考》成书时间在乾隆元年(1736年)下半年或次年初,这一时间只比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晚一至二年;《西藏志》的成书时间虽比《西藏志考》又稍晚一些,但也在乾隆初年成书。在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这四部西藏地方志之后,乾隆前期先后还出现了乾隆《雅州府志·西域》、萧腾麟纂《西藏见闻录》、张海纂《西藏纪述》及陈克绳纂《西域遗闻》等几部官方、私人编纂的清代西藏方志。乾隆《雅州府志·西域》成书刊印时间前已谈及。陈克绳纂《西域遗闻》长期只有抄本流传,其成书时间在乾隆十八年或稍后。③赵心愚:《乾隆〈西域遗闻〉的编撰及其缺陷、价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萧腾麟纂《西藏见闻录》与张海纂《西藏纪述》两志,其成书时间虽较早,但刊印时间前者为乾隆二十四年,后者为乾隆十四年,刊印前未见流传,亦无人摘引其资料。④萧腾麟自序写于乾隆十一年冬月,故其著成书当在此年。萧腾麟:《西藏见闻录》,张羽新:《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二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有研究者认为,张海乾隆六年丁忧前已完成《西藏纪述》文字部分,即成书较早。见赵长治:《〈西藏纪述〉考略》,未刊稿。从以上比较可看出,《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乾隆十二年(1747年)成书并刊行,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成书、刊印的时间均较早。可以认为,《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的成书与刊印,在时间上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当时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继续发展。
从本文以上的分析、比较来看,《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成书之前,《藏纪概》、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西藏志考》《西藏志》及乾隆《雅州府志·西域志》等西藏地方志已问世,这五部方志或以抄本流传,或已刊印。讨论乾隆前期西藏地方志的发展首先需要指出,在《西宁府新志》西藏篇目之前,从编纂方法与资料来看以上五种方志著作实际上分为两个体系:一是《藏纪概》、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及《雅州府志·西域》中的西藏篇目,一是《西藏志考》与《西藏志》。《藏纪概》不同于清初已出现的与西藏有关的纪程著作,首次设置了“藏天异”等六目,已具方志体例。这些篇目名称及内容在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乾隆《雅州府志·西域》的西藏篇目中仍然可见,这说明几种方志著作在编纂方法及部分资料上有着一定的承袭及辗转相传的关系。尤其在编纂时,后二者显然参考了前者的方法,并沿用了前者在篇目名称及设置上的某些做法。当然,后二者不仅细目、资料有增加,更重要的是体例上已更具方志性质与特点。对比后即可发现,在篇目设置及资料上,《西藏志考》《西藏志》与《藏纪概》及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乾隆《雅州府志·西域》中的西藏篇目均不同,实为另一体系。杨应琚纂《西宁府新志》西藏篇目时,已有条件查阅、参考以上五种志书。翻阅《西宁府新志》西藏篇目可发现,其细目设置与名称已有《藏纪概》的某种影响,当然,从细目名称与设置以及所摘资料来看,更有可能主要是参考并摘录了雍正《四川通志·西域》或乾隆《雅州府志·西域》西藏篇目中的细目及资料。同时,又在细目名称与设置上参考了《西藏志》及《西藏志考》,并从这两志中摘抄了资料,而且量也比较大。因此,杨应琚所纂《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的出现,其篇目设置及内容实际上反映或代表了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中的一种态势,即两个体系及其资料开始合一。这种发展趋势是从杨应琚开始的,与其编纂中的大胆探索分不开。这种趋势出现后,所纂西藏地方志可更为全面地记载西藏各方面的情况,资料也更显丰富。笔者几年前曾言,《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所反映的已有西藏方志两种体系的合一趋势,也很有可能使几年后陈克绳纂《西域遗闻》时受到启发。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①赵心愚:《乾隆〈西域遗闻〉的编撰及其缺陷、价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其次,《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在大量摘录已有西藏地方志资料的同时,还摘抄了一定数量的乾隆初才正式刊印的《明史》中的资料。在清代西藏地方志编纂中摘录《明史》资料,《西宁府新志》西藏篇目为最早,这也反映出杨应琚为纂新志广搜资料时已注意到刊行不久的《明史》。尽管最后采用的摘自《明史》资料的量并不太大,但仍表明杨应琚纂新志觅资料时有着更广阔的视野。第三,对已有西藏地方志资料加以整理、鉴别后再使用,并非一概照抄照录。《西藏志考·历代事实》中有一段记大召前廊有唐三藏师徒像及猪八戒招亲高老庄即蔡里的材料,《西藏志·事迹》中亦有相同一段内容,只是将“蔡里”改为“采里”,并在后加“其真其诞,俗传如斯”语。②《西藏志考·历代事实》,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杨应琚编纂时将这一段内容全部删除,这反映出其对资料的审慎态度,也说明其对已有西藏地方志资料摘抄后是进行过整理、鉴别的。
编纂《西宁府新志》西藏篇目中杨应琚使已有西藏地方志两种体系合一,注意利用新的资料源,并在摘抄中对已有方志资料加以整理、鉴别,不仅决定了《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在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乾隆前期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最后应指出,杨应琚虽然后来在云贵总督任上被赐死,但其对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应给予应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