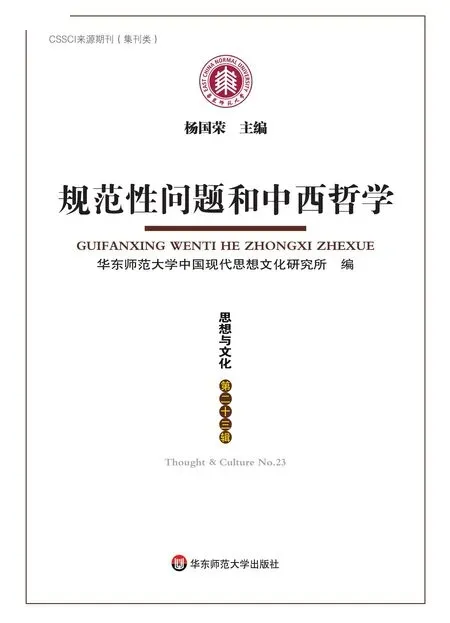论《人间词话》中作为诗人与世界相互生成的“境界”
2018-04-01
●
“境界”是《人间词话》[注]本文所有引文都摘自王国维: 《人间词话》,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后文只在括号里列出所引篇目,不再另注。的思想主题。一百多年来,学界对《人间词话》的研究,都集中于对字词意义的诠释与梳理,并通过儒道禅三家各自的文本分别进行释义,或者综合三家文本进行相互释义,或者侧重对王国维的生平、思想学术背景等资料的整理与梳理。[注]沈文凡、张德恒: 《王国维〈人间词话〉百年研究史综论》,《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9辑,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这些工作,为深入研究《人间词话》,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还谈不上对其思想本身进行研究,也不能替代思想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一方面用唯物与唯心、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王国维的艺术理论,另一方面开始注重王国维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渊源关系及其比较研究[注]程国斌: 《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的世纪考察》,《学术交流》,2005年第2期。,但毕竟还处于研究初期,显得不够成熟。郭勇健从现象学角度把王国维的境界还原为胡塞尔意义上的意向性客体[注]郭勇健: 《王国维境界说的现象学诠释》,《中国美学研究》第3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年。,还未脱离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虽有创建,尚需更为本源地思考。本论文从生成角度阐释王国维的境界说,把他的境界思想还原到境界自身生成的过程中进行考察和阐释,希望借此把境界作为境界本身显现并揭示出来。基于此,从《人间词话》文本整体出发,然后深入到境界自身显现和敞开的语义中,按照境界自身指示的道路行进,最后找出境界的边界,这些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一、 境界的语义
日常意义上的境界,主要有四个意思: 一是边界,疆界,国界,国与国的分界线,即土地的界限;二是境况,情景,处境,如[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 “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三是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亦特指诗词、书法和绘画等构成的意境;四是指人在精神与思想上,异于其他人的东西,如气质和品格等修养,并表现为言说和行动符合某种较高的道德规范,也表现为思想具有某种透视与洞见事物的高度和深度。因此,境界在日常语言中首先是作为判断的标准。在人们常说的有境界和无境界中,无境界还处于混沌之中,而有境界虽然看似很明晰,其实也缺乏相应的规定从而显得模糊不清。其次,境界有高低之分,它表明层次、阶段、水平、范围等不同的状态。
境界一词来源于佛教并主要在佛教理论中使用。日常意义中的境界本身是佛教中的境界的继承或变式,前者的第一、二和四种意思,还保存在佛教的境界语义中。但佛教的境界的意义更为本源,它指的是在人的心灵界限内构成的独特境况。佛教境界中的“境”,是“心之游履攀缘处”。此心不是作为肉团心的心脏,在此是指作为思之官能。思想能够去游履攀缘,即能认识它能够认识的事物,其前提是能够找出与区分什么是能认识的和不能认识的。这虽是心境,但主要是思想对事物的思考。在此思考中,它又有“所观之理曰境,能观之理曰智”的区分,而“能观一切境界智”,指的是在各种境界中能有所指引和道说的智慧。“界”首先是指,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差别与区分,其次是一事物自身固有之本性,第三又指事物之名相,如六界和十八界等。但佛教的境界,一般指心走出自身去体验外在事物,经过训练和修行又返回到自身后所达到的觉悟程度。这种觉悟,主要有佛圆满极境、菩萨大乘境、缘觉中乘境和声闻小乘境等不同涅槃境界和表现。这些境界的区分看似是对觉悟的分别,其实是对觉悟的肯定,因此它属于不分别的分别或分别的不分别,超越了分别和不分别的区分,达到了分别和不分别的本源。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继承了佛教境界说[注]詹志和认为:“‘境界’原本是一个会通‘内’‘外’、综合‘根’‘境’的佛学名相,移用于诗学,便是强调‘心’与‘物’的互摄、‘意’与‘境’的浑通。唯其如此,‘境界’二字才足以承当王国维的诗学‘元范畴’。也是因此,‘境界说’诗学在两大问题上表现出了与中国佛学的深刻联系: 第一,强调心识对境相的充注性和能动性;第二,强调审美对象的具象性和直观性。此二端正是王国维‘境界说’诗学的宏旨所在。”参看詹志和: 《王国维“境界说”的佛学阐释》,《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也强调境界的独特性和最高规定性,这种独特性和规定性是一种区分和划界。他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一)“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九)“兴趣”是《沧浪诗话》的核心语词,严羽主张以禅喻诗之悟,言说不可言说的和表达不可表达的,通过语言表达语言之外的东西。“神韵”表达的是形象之外的东西,也即属于心灵或精神的东西。但王国维认为“兴趣”和“神韵”只是表现了所表达事物的表象,并没有道出诗之为诗的根本,只有他自己提出的“境界”才道出了诗的本性,并把“境界”作为诗的最高规定和最后根据。对于境界的种类,王国维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为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六)由此可知,境界由心和物构成,即主客合一、情景合一,它包含了一切景物和诗人自己对景物的情感。同时,王国维认为描写景物和抒发情感是境界产生的基础,描写真景物和抒发真情感才算是境界的实现和完成。[注]周祖谦和张连武认为:“王国维的境界之‘真’是一个取烙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与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美学、艺术观念,兼具本土韵味和时代特征而又内涵丰富、别传新声的诗学概念。……它是优秀诗人基于对宇宙人生的独特感受、深切体验及对特定对象(景物或感情)的审美领悟,在某种自由的精神追求(王称之为‘势力之欲’)的驱策下,经由匠心独具的艺术构思与传达而呈现于诗语形式中的主客浑融的高品位的艺术世界(或以景物为主,或以情感为主)的存在状态或属性。其要点有三: 一是自由;二是可以直观;三是独异性。首先,自由是指诗词作品所写‘世界’的那种摆脱了一时一地的社会政治兴味、传统的道德观念、世俗的陈规陋习、自私的名利计较以及单纯个体存在的种种局限的束缚,本乎天然而祈向超越之域的属性。其次,可以直观,即《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不隔’。……第三,独异性乃指有境界的诗词作品以诗人特有的生活感悟为前提而在艺术构思、艺术传达上的独出机杼与自铸新词。”参看周祖谦、张连武: 《管窥王国维的境界之“真”——〈人间词话〉“境界涵义论”献解之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所以,从根本上说,真才有境界,而假没有境界,规定诗词为诗词的本性是“真境界”。在《人间词话》中,与境界相邻近的其他语词,主要有: 妙境(六三)、品格(三二、四八)、格调(三八、四二)、意境(四二)、性情和气象(四三)、无题(五五)等。这些语词的语义,或者是对诗人所表现的世界的模糊的感受,或者是用自然景物来进行类比和描述诗人内心的情感状态,或者认为无法用概念来涵盖和表达诗词所呈现的世界。从这些意义上讲,王国维的境界[注]彭玉平认为:“简而言之,所谓境界,是指词人在拥有真率朴素、超越利害之心的基础上,通过寄兴的方式,用自然明晰的语言,表达出外物的真切神韵和作者的深沉感慨,从而体现出广阔的感发空间和深长的艺术韵味。格调是其精神底蕴,名句是其表现形式,自然、真切、深沉、韵味则堪称是‘境界’说的‘四要素’。”参看彭玉平: 《“境界”说与王国维之语源与语境》,《文史哲》,2012年第3期。所涉及的,要么是思想中的事物,要么是思想外的事物,要么是思想自身。
二、 境界的要素
由上述可知,境界之发生,是人与世界相互生成的事件,是在诗人经验与体验世界和万物中形成的。在境界的发生中,诗人是世界中的诗人,世界是诗人的世界,两者相互同属。从这个意义上讲,境界的构成要素,主要是诗人、世界和世界中的万物。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认为豪杰之士、大家和诗人,有能力去创造作品的境界。王国维眼中的豪杰之士,主要是苏东坡和辛弃疾。
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三)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捧心也。(四四)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四五)
作为豪杰之士,能够超越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分,既能够写有我之境也能够写无我之境,甚至能够综合二者之优点。苏东坡词风旷达,辛弃疾词风豪放,根源于二人都有博大的胸襟,这种博大的胸襟表现为雅量高致。但胸襟是什么?它是一种灌注全身的宏大气势和强劲生命的力量感。这种气势和力量感,来自于词人自身对生命的独特体验。这种独特的体验是与生俱来的,别人无法模仿。苏东坡和辛弃疾能体验这种胸襟并把这种胸襟表达出来,呈现于他们的词中。
大家,是王国维推崇的能创造出伟大作品的另一类人物。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五六)
大家的作品,不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能让人感受到神清气爽和耳目一新。写景是写世界和世界中的万物,言情是言诗人自己对世界和世界中的万物的感受。诗人能够把写景与言情之词脱口而出,在于他们能够洞见到事物的真相以及体验到能触动人心最深处的细微情感,并具有相当强的语言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注]叶嘉莹也认为:“一个作者必须首先对其所写之对象能具有真切的体认和感受,又须能具有将此种感受鲜明真切地予以表达之能力,然后算是具备了可以成为一篇好作品的基本条件。”参看姚可夫: 《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155页;或参看叶嘉莹: 《迦陵文集(二)》,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能够把这种情与景的自由状态在作品中如实表达出来。王国维认为,纳兰容若就是这样的人。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五二)
王国维看重纳兰容若的词,理由在于纳兰容若的真切,即纳兰容若真真切切地把想要表达的景与物,如这景与物自身所是那样传达出来。而纳兰容若之所以能够做到真切,在于他如物自身所是那般观看它,并如所观看到的那般去思考它和表达它。
王国维这样写道:
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只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境界有二: 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附录·一六)
豪杰之士和大家,虽然都是诗人,但诗人是比豪杰之士和大家更杰出的杰出者。诗人见于外物者是悲欢离合和羁旅行役的场景,呈于诗人之心的是悲欢离合和羁旅行役的感受。不管是场景还是对场景的感受,都是具体时空中的物,即须臾之物。诗人能够把这种时空中的须臾之物,用文字保存下来,使之变成非时空或超时空的永恒之物。而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诗人能够感受到常人不能感受到的事物和感受、能够言说和传达常人不能言说和传达的情感。这是诗人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即诗人能洞观世界和万物的神奇与奥妙,体验人生的最深邃和最高远的地方,把观看和体验到的境界在作品中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否定常人的境界,肯定诗人的境界,因为他认为只有诗人才能创造境界,只有诗人才能创造真正意义上的真境界。
世界和万物是构成境界的另一要素。世界和万物如果不存在,人就不能去经验它们,人的思想也就不能触及它们,因此也不能去言说它们。世界和万物存在和显现自身,是人得以去经验世界和万物的前提,也是思想得以思考的前提,也是言说得以言说的前提。在此前提下,人才能去经验世界和万物,然后才能去思考与言说世界和万物。世界在此有两个意义: 一是就世界自身而言,它是包括矿物、植物、动物和人等在内所有存在者整体;二是从人的角度而言,世界是作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周围世界、周围性在此。[注]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论: 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境界作为诗人观世界的产物,它是由诗人视域所及的范围构成的。诗人从他自己站立之点看去,形成一个观看的区域,在此视域内,事物被诗人看见,显现出事物的真相;超过此视域,事物不被诗人看见,显现的就是假象甚或幻象。观世界的观,作为看,有看与被看的不同,还有外观和洞见的差异。看是诗人去看事物,被看是被诗人所看的事物。外观看到的是世界事物的假象或者表象,洞见看到的是事物如它自身所是的显现自身,即真理。但不管是看与被看,还是外观和洞见,都依赖于事物自身的敞开和显现,我们才能观看到该事物。
三、 境界的生成
由上述可知,境界由诗人、世界、诗人和世界的关系等要素构成。生成的境界,不仅存在于此,还生成、敞开、显现自身,它包括世界如其自身所是地呈现的世界和世界如诗人所观那般显现的世界,还包括世界自身和诗人所观世界交互生成的世界。这交互生成的世界,在《人间词话》中,就是艺术世界,也即王国维谈论的境界,它是前两种真理在艺术作品中的生成和显现。因此,境界的生成,首先是各要素的各自生成,其次是各要素的相互生成。
首先是诗人的生成。诗人在世界中存在,并在世界中生成和保存自身。王国维认为,诗人要成为诗人,必须经历三个阶段: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二六)
大事业和大学问,是众多的事业和学问中之大者,即根本的事业和学问,在中国思想中主要是性命之学,即关于人的规定的学问。“昨夜西风凋碧树”,悲秋作为寒秋的感叹,感叹的是生命的短暂和易逝,以及世界的变迁和轮回,即前述的忧生和忧世情怀。“独上高楼”和“我”,体现着悲秋中的孤独,诗人与自身和世界,甚至与自身以往历史相分离。“望尽天涯路”,体现出一种期待和向往,这成为诗人从此处走向将来的开端和起点。“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爱智慧的“爱”是奉献和给予,奉献自己并给予他人,但王国维这里的“爱”却是对自己的追求锲而不舍,追求与追求的事物同在,并与之同喜悦或同悲伤。“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是“回首”,即缅怀过去并回到其本源,非迎面而去与之在一起,也非看到自己存在命运的辉煌处,而是阑珊处。阑珊处,是光明与黑暗交替的地方。在这里,世界和万物都在其中隐约闪现,即生命和存在在此处既显现又遮蔽,它们不是全然可见,也不是全然不可见,而是在偶然中遇见。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的第一境是悲秋,但开始了追求,设定了目标;第二境是始终不渝,无限地给予,而非索取和占有;第三境强调目的的实现具有偶然性和随意性。这三种境界不是一个平面,也无高下之分,但有序列,是境界的开端、展开和完成的三个阶段。诗人的这种关于存在与命运的境界的生成,始终与看相关,它始终追求一个目的,即成为大词人。这三种境界,王国维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即形象性、自然性的语言来类比和描画。但是,由于形象大于思想并规定思想,王国维以一形象来解释另一形象,中间缺少对思想的精确限定,产生以此形象遮蔽和覆盖彼形象的问题,从而对思想本身造成遮蔽,也对真正的境界造成了遮蔽。
其次诗人与世界、万物的相互生成。它包括诗人观世界和体验人生。诗人如何观世界和万物?王国维认为可以通过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的方式去观世界和万物。[注]周祖谦认为:“所谓‘以我观物’,不过是‘有我之境’创作过程中必经的一个环节,即诗人怀着激动的情感去观察外物,给外物染上情感的色彩。在此环节之后,诗人还要把由观物获致的以情感为内核的观念意象作为一个整体给以审美的观照。”参看周祖谦: 《情景分列: 王国维之“境界”创造对象观——〈人间词话〉“境界涵义论”献解之一》,《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王国维认为: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三)
王国维“境界”的核心,分为“有我”和“无我”两种境界。总体而言,“有我之境”是以主体作为客体的规定性,“无我之境”是以客体作为客体自身的规定性。但王国维的“我”不是西方思想中作为自我意识的“自我”,因为“我”没有像“自我”那样成为万物的根据和规定。“无我”中有“物”的存在,这实际上是清除了物和我的区分和差别;“有我之境”浸透了“我”的情感,但却不是欢乐之情,而是“不淫”,即符合道德规定的情感。“无我之境”没有“我”的阴影,而是诗人融化在天地自然之间,山水自然成为诗人的主导,成为诗人的家园并显露其自身。同时,“我”在“南山”的呈现中,体悟空间和时间、有限和无限的瞬间转换,而所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禅宗的超过自然达到心灵状态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无我之境”中,我隐退和不在场,消融在物之中,体现了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在另一个地方,王国维提出了另一种观看世界和万物的方式,他说: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六〇)
内外观,即观内外;内观即观诗人与他人自身的人生,外观即观宇宙、世界和万物。这种观,王国维认为应该从诗人需具备的能力来探讨,即诗人必须深入到世界的内部和人的内心深处,去体验自然之造化的伟力和人内心的神秘而不可言说的感受,才能写出真实的、有生命力的文字。同时,诗人还要跳到世界之外,站在宇宙整全的高度,才能认识和经验世界整体,才能把握世界,使作品达到既深邃又高远的境界。这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观看视角与体验,还有整全的视域,超出了有我之境的情感浸透于客体和无我之境的主体消融于客体的区分,可以说走向了诗人与世界双向关涉和交互生成的境遇。
因此,诗人在世界中经验世界并体验人生。体验,与我们的身体相关,是我们身体的某种行为,并始终相关于人的生命。在激动、欢乐和痛苦等情绪体验样式中,世界和万物向人敞开和显现自身,同时人也向世界和万物敞开自身。在此敞开和显现中,万物在世界中发生、生成、持存、衰减和死亡,人也概莫能外。从这个意义上讲,站立在生死之间的诗人,能够触摸到万物与人自身的命运。诗人听从这种命运的召唤与指引,一方面赞美大自然的神奇与造化,另一方面忧生与忧世。而经验,超出了作为个人身体性的体验,是对世界整体的存在经验和把握方式。诗人的职责或者说任务,就是把这种相关于人的生命的体验上升或转换成对世界和自己的存在经验构造并传达出来。在文本中,王国维把体验称为阅世,他说: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一七)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一五)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弛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二五)
诗人多阅世,不仅能扩大诗人的视界,积累感性材料和写作素材,还能增进认识,提升认识世界和事物的能力,并从这种认识中反观诗人自己,诗人才会“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在这个意义上,阅世,就是经验与体验万物,并思索人生百态,诗人才会产生忧生忧世的情感。忧生侧重于忧自己的生命,担忧生命的无目的和无归宿状态;忧世则侧重关怀人世的疾苦,而自己却痛苦于没有解脱的门道。“瞻”、“望”在这里就是追求,但忧生本身却看不到和求不得,以此否定了看,使看失去了对象和目标。“所问津”、“谁家树”亦看不到,没有看的对象,所看和所思的对象皆被否定,相关联的仅只是看与能看、思与能思的空洞。李后主为人君时,未与外在世界接触,未体会人间百姓疾苦,后遭遇国破家亡,既伤国家灭亡之痛,又伤自己境遇之悲惨,因此他后来的词,才会有“感慨遂深”的境界。王国维认为,李后主伤身世之痛和国破家亡的主题,是士大夫忧心天下和百姓疾苦等题材的源头和滥觞。尽管此话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至少我们能够从中获知,阅世与历世是诗人创造作品的素材和境界产生的基础。
最后,作品境界的生成。前面说到豪杰之士、大家和诗人能够创造作品的境界,但关键是他们如何创造作品的境界?王国维主要谈到三点。
第一,作品的境界在打破理想家和写实家的界限处生成。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五)
王国维认为,创造作品的境界分两种,即理想与写实。理想是表现诗人心中体验的事物或情感;写实则是摹写或复制自然世界的本来面目。理想与写实看似彼此对立,但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与写境和造境相关联。自然事物处于相互关联中,也即彼此作为对方存在的条件而显现出来,它们相互制约并相互生成。诗人创作的作品,就要把这种关联和限制打破并与之分离,使诗的境界尽可能扩大。诗人虚构的境界,是从无到有的生成,但王国维不称之为创造,而是称作构境,认为它必须承载世界和万物作为内容。同时,诗人构造境界须遵从自然法则,否则就显得空洞而不真实。但是,王国维在这里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艺术创作规律来探讨,而是力图为“境界”的区分寻找根据,他把自然和心灵作为境界的规定。尽管这样,王国维却忽略了自然是有限的,不能成为完全的境,而虚构也必须有虚构的对象。因此,不论是写境还是造境,境界都是心灵和自然相结合的产物,也即理想与写实相结合的产物。
第二,作品的境界在诗人主动支配与统握外物中生成。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六一)
不管是写景(风月)还是言情(忧乐),诗人都必须处理好视(观看)与外物的关系。轻视世界和万物,成为世界和万物的奴仆。重视世界和万物,成为世界和万物的主人,能主动支配万物,与花鸟在一起,感受到它们的忧愁与快乐,从而写出真境界。
第三,作品的境界在血写的文字和赤子之心中生成。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一八)
尼采所谓的“血”是生命之创造、生命力意志的表达,不是王国维认为的血泪的悲伤。李后主的悲伤的血泪,类似于尼采所谓“女人的美学”,而不是“男人的美学”。李后主与赵佶虽然不同,但用基督和释迦牟尼的差异来比附却并不切中,因为李后主只是沉溺于自身的感伤,并没有基督拯救世人罪恶的博爱精神,李后主也没有释迦解脱世人疾苦的悲悯和智慧。况且,把基督和释迦的行为都归结为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愿,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基督教的逻辑前提是人本性是罪恶的,而释迦的前提是世人处于生老病死的现实状况中,两者的逻辑前提有根本的差异。尽管王国维误解了尼采“血写的文字”的真正意思,但他认为类似于李后主这种悲伤的血泪,是诗人真性情的流露,是创造境界的必备要素,无疑也有可取之处。在文中,王国维认为李后主这种真性情产生的根源,在于李后主具有赤子之心: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一六)
赤子是儿童,赤子之心是童心。儿童未与外部世界接触,尚未体验忧生与忧世的烦恼和痛苦,故具有纯而不杂之心灵。李后主一生短于人君之谋,却长于真性情,这使他有可能具有赤子之心。
四、 境界的形态
境界的生成,是作品中生成的境界,它呈现出有我与无我、隔与不隔和大小优劣等形态。
(一) 有我与无我的境界
众所周知,诗人观世界与体验人生的方式,就是作品的生成方式。作品生成的境界的不同形态,也就是作品呈现的不同类型。中国古典诗词的境界类型大都是写景与言情,其中景与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要么是借景抒情,采用类比或象征的方法,把情感寄托于类比或象征的事物中;要么融情于景,走向情感与自然的合一;要么境由心造,以心灵创造出世界。与这些不同的是,王国维把此类境界划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注]钱剑平认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指当人们存有‘我’的意念,因而与外物有某种对立的利害关系时的境界。这不是指感情强烈个性鲜明的境况,而是当‘外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威胁着意念的状况下观物所得的一种境界。……所谓‘无我之境’是审美主体‘我’‘无丝毫生活之欲’,与外物无利害之关系,审美时心情宁静,全部沉浸于外物之中,达到了与物俱化的境界。”参看钱剑平: 《〈人间词话〉“境界”说新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肖鹰认为:“王国维是主张‘境界’中必须‘有我’的,而所谓‘有我’与‘无我’两种境界的区分,只是对‘境界’中表现的‘物’与‘我’的不同关系的区分。”肖鹰在文章后面接着说:“王国维所推崇的‘有我之境’,不仅要求作者以沉痛强烈的情感投入到对象中,而且要求诗人自觉成为人类情感和理想的承担者、表现者。……王国维的‘无我之境’是自然与理想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王国维接受席勒的人本主义诗歌美学,主张诗歌境界要实现自然与理想的统一,从而表现完整的人性。当诗人在现实中直接感受到这种统一的时候,形成‘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的‘无我境界’——优美的诗境;当诗人在现实中不能感受到这种统一的时候,他就用理想来映照自然,把自然从有限提升到无限——理想,形成‘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崇高的诗境。”参看肖鹰: 《“有我”与“无我”: 自然与理想的结合方式——论王国维“境界”说的诗境构成原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在对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关系的研究中,彭玉平认为:“王国维在美学文学理论中都强调直观的观物方式,只有以有我之境为基础,而以无我之境为目标,两境之间不仅有前后之分,也有高下之别。”参看彭玉平: 《有我、无我之境说与王国维之语境系统》,《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由前述可知,有我之境反映的是诗人内心的创造体验,无我之境显现的是诗人摹仿自然世界及万物自身的形态。王国维把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产生归结为造境和写境。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二)
在这两种境界[注]钱剑平认为:“社会生活中物物互相牵连,又互相限制,作家在创作时受其制肘,然重要的是面对现实,作家应排除错综复杂的‘关系、限制之处’而加以典型化。”参看钱剑平: 《〈人间词话〉“境界”说新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中,“造境”是创造之境,“写境”是模仿之境。“造境”反映的是艺术与心灵的关系,是心灵所创造的境界,即有我之境。“写境”反映的是艺术或者说诗与现实的关系,现实就是“合乎自然”,合乎自然给予诗人的尺度和规定,即无我之境。但是,在这里王国维基于主客二分来区分理想和现实,还限于唯物和唯心的对立,他所说的境界被境界之外的东西即心灵和现实所规定,境界还没有自身的根据。
(二) 隔与不隔的境界
如前所述,诗人在世界中观世界和体验人生,他感受的深浅程度受到他的视域范围的制约,诗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世界及万物自身的是其所是,诗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把这种感受显现出来,王国维把它称为隔与不隔。[注]彭玉平依据意与境的关系把王国维隔与不隔的境界分为四种形态。他认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其实包含着不隔、隔之不隔、不隔之隔、隔四种结构形态,大体分别对应意与境浑、意余于境、境多于意、意与境分四种意境形态。不隔而深被王国维悬以为审美理想,文学的常态是隔之不隔与不隔之隔两种中间形态。”参看彭玉平: 《论王国维“隔”与“不隔”说的四种结构形态及周边问题》,《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 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四〇)
春草生在池塘边,燕子把泥弄丢在横梁上;晴空万里连云,忧愁与苦痛都写在旅人的脸上;姜夔感叹和赞美萋萋芳草与白云黄鹤,并与天地一切游戏。所有这些情和景,就如在眼前那般一览无余,没有阻隔和遮蔽。相反,浦畔被江河所淹没和遮盖,虽然具有朦胧之美,但毕竟是遮蔽的显现或显现的遮蔽,这就是隔。隔,不仅仅是单纯的隔,它还包括不隔中的隔,王国维认为姜夔就有此类作品: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三九)
姜夔的这首写景作品之所以是隔,在于没有完全把想要表达的体验表达出来。“无声”,虽然宽阔与辽远,但略显喑哑与沉闷。“清苦”,虽然情态逼真,但情感略显低沉,也不舒畅,更不如前述苏东坡和辛弃疾词那般豪迈和激昂。既然这样,哪种情感才是既不低沉、也显得舒畅的不隔呢?王国维认为: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批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四一)
“忧”,忧的是时间,生命短暂和昼短夜长给诗人造成痛苦,但一个“游”字,却显现出自由自在的状态,诗人瞬间把痛苦转化为快乐,情绪随即也变得坦荡和豪迈。“求”长寿,却让药“误”了变成短命。因此,追求的方法和目的都显现为错误,而一个“饮”字和一个“批”字,把这种追求的方法和目的全都否定,同时肯定身心快乐在当下人生中的重要性,情感由悲转乐没有丝毫障碍。上述两种都是写情,下面这两种属于写景。南山如其自身所是那般显现出悠然自在,诗人体验到这种悠然自在,然后把南山的悠然自在完全表达出来。天与四野,即天空、大地和草原,空旷辽阔,甚至掩没在草中的羊群,随着风吹草动,也一览无余。这些显现出的境界之所以不隔,王国维认为是在遣词造句尤其是在词类活用上完成和实现的。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七)
枝头的红杏和破云而出的月亮所照亮的花儿,它们的存在状态即是它们的生命显现状态。诗人在对这种显现的生命情态的描画中,著一“闹”字和一“弄”字,把动词作为动词运动起来,使要描写的景物自身鲜活的生命状态在纸上跃然欢腾,从而使死境变成了活境,境界呼之欲出甚至喷涌而来。
(三) 境界有大小无优劣
王国维认为境界有大小的区分,但不能以境界大小评判作品的优劣。
境界者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八)
细小的雨线和跳跃于水面之上的鱼儿,微微的轻风和风中斜飞的燕子,是小境界。落日余晖照在大旗上,风萧萧般呼啸混合着马的嘶鸣,是大境界。这两个作品的境界虽有大小的不同,但它们都是好作品,因为王国维认为:
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一)
王国维认为有境界即是好作品,无境界则不是好作品,但他仅仅以有无境界来区分作品好坏,略显粗糙和简单。由前述可知,作品的境界作为诗人与世界相互生成的事件,其大小是被诗人观世界的视域范围和诗人的情感体验的深浅所规定的。作品境界越大,则越具有普遍性,作品境界越小,则越趋向于个人性。以诗词而论,若越具有普遍性,则倾向于哲理诗和玄学诗,若越趋向于个人性,则越具有独一性。在文学艺术史上,大家都推崇个人化的诗词并贬低带有普遍性的哲理诗和玄学诗,主要原因就在于诗词的价值和魅力就显现在个体的这种具有独创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重复性的体验中。
五、 境界的边界
综合而言,王国维试图把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的思维结合起来,拎出“境界”一词来重新定位和评价中国的传统诗词。王国维借用的西方思维主要是席勒的美学[注]肖鹰在他的论文中,经过论证和分析,得出:“‘境界’说的精神实质是王国维提出了以人本主义理想为核心的诗歌理想——‘境界’。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是‘境界’说的思想资源。”参看肖鹰: 《被误解的王国维“境界”说——论〈人间词话〉的思想根源》,《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肖鹰在另一篇论文中再次指出:“王国维‘境界’说的核心内涵是‘自然与理想结合’的命题。这个诗学命题(‘自然与理想结合’),是席勒的人本主义诗学的宗旨,它表达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美学的最高理想。王国维追随席勒,主张‘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以自然与理想统一为诗歌的理想境界。”参看肖鹰: 《自然与理想: 叔本华还是席勒?——王国维“境界”说思想探源》,《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叔本华的悲观思想[注]唐小华在他的论文中,经过分析与论证,认为“忧生忧世思想也受到了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是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经验总结。王国维天性忧郁,在思想还未完全定型的青少年时期,一接触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就被吸引,认为:‘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并成为叔本华哲学的最早鼓吹者和奉行者。”参看唐小华: 《忧生忧世——王国维“境界”说核心思想之一》,《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梁涓也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受叔本华的人生哲学、艺术直观说和超功利说以及天才说等思想的影响最为明显。参看梁涓: 《王国维“境界说”及其与叔本华美学之关系》,《江汉论坛》,2001年第11期。和尼采关于生命力创造的学说,并以之来解读唐诗和宋词中的“情景合一”的境界。在西方思想中,王国维以理想与自然(造境和写境)、主体与客体(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等二元对立概念来评论中国古典诗词,这表现在他从主客关系和情景关系来分析“境界”,但他论述的最终目标却是强调诗人在世界中对生命的体验。王国维推崇西方的悲剧(希腊意义的悲剧是英雄对不可知的命运的抗争),但他主要言说的却是“忧生忧世”的感伤情怀,而不是对不可抗拒的命运对英雄人物造成的毁灭,或者人物性格中的不可改变的因素对人物造成的巨大痛苦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基于西方近现代思想的背景来构建“境界”说,但又始终关联于并回归于中国传统思想,因此王国维的“境界”说是西方思维和中国思想的混合物。[注]对于此结论,姜荣刚认为:“对王氏‘境界’说的概念使用特点与理论建构予以深入探究,则可发现采用的是典型的‘六朝人所谓格义之法’,或者说是中西观念的互相参证,这种理论表达方式是西学东渐下晚清西学翻译与文论建构的基本特点。”虽与我论述的视角不同,但可以从另一视点看到相同结论的事实。参看姜荣刚: 《王国维“造境”、“写境”本源考实——兼论“境界”说的概念使用特点及理论建构模式》,《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