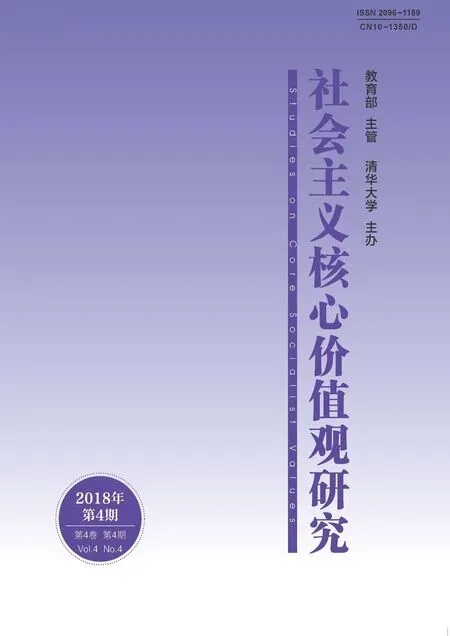保罗·柏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构建及其当代启示
2018-04-01殷逸枫
殷逸枫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维度。对此,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柏克特依据马克思的文本,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生态学阐释,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生态内涵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亲生态性,拓宽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路径,诠释了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但是,柏克特过度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忽视了原本在马克思主义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关系维度。尽管如此,其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构建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和借鉴。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1]230伟大实践需要科学理论加以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其必然成为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学习马克思,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早在19世纪,马克思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所爆发的诸多环境问题时,就已经展开了对生态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不是散落于其著作的某个角落的只言片语,而是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构建这一问题,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诸多探讨。
较之于此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保罗·柏克特①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1956—),又译为伯克特、柏格特,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和发展理论。柏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构建主要集中在1999年出版的《马克思和自然》(Marx and Nature: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和200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两本著作之中。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构建路径具有开创性。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对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形成的,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教条化。从理论的历史发展来看,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转向后的新形态,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范式,将其等同于狭隘的“经济决定论”,主张马克思主义缺失生态维度。因此,此前的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要么从未意识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内涵,试图借助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然异化现象,例如,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源,威廉·莱易斯将之归因于控制自然的观念,而本·阿格尔则归结为满足虚假需求的异化消费;要么断言马克思主义本身即是反生态的,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并将生态维度嫁接其上,以此来保证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问题的有效性,例如,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两个重大方面是存在缺陷的。马克思倾向于把他对社会劳动即劳动分工的讨论从文化和自然中抽象出来”[3]436,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3]7,因此,生产条件概念被奥康纳嫁接到马克思的积累模型和危机理论上[4]7,以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与这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同,柏克特开创性地从马克思的文本著作出发,“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重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态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在他们的思想中再次融入生态维度”[5]10,以期“发展出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机联系的生态学唯物主义,目标是赋予它革命性的实践意义”[5]10,进而充分呈现出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柏克特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阐释路径,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借鉴,同时对于反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捍卫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现实的个人: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向度的彰显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之前所有历史理论,关键在于其将历史的主体和前提从抽象的概念转向“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进而以此为逻辑起点研究历史的演进过程,实现逻辑性和历史性的统一。柏克特在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构建中承认了这一哲学革命,并且以此为理论出发点来论证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生态内涵,为构建马克思生态思想奠定理论基础和前提。正如柏克特所分析的,“要了解马克思是如何将自然条件融入到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有必要首先了解自然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的地位”[6]25。
柏克特因循马克思对历史前提的分析,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论证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生态内涵。在柏克特看来,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分析是以财富的生产,即使用价值的生产为立足点的。换言之,作为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进一步,柏克特认为,分析自然和劳动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生产中的共同作用,是打开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向度的重要环节。正如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所指出的,“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去对自然进行解释,这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对自然的漠视”,“这种自然观愈是使自然脱离人的生动的实践,就愈是受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批判”。[7]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208,为了生产出符合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人必须“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8]208,因此,人在没有自然、没有感性的外在世界存在的情况下无法创造使用价值。柏克特引用马克思的论述:“劳动并不是它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8]56他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必然联系的重视,由此说明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对于财富生产的作用时,并不贬低自然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柏克特将马克思作为历史前提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或财富的生产等概念作为自然和劳动、物质性和社会性紧密结合的整体,从而保证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和自然概念间的统一性。如此,一方面避免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如技术决定论或自然主义,将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由自然决定的机械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又不至于陷入片面的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形式对于塑造人类历史的作用,而忽视社会形式的物质内容,即作为自然条件对人类生产和发展的限制[6]17。由此,柏克特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下,赋予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即人与自然的物质交往活动以“社会—自然”双重属性,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生态向度。
二、“价值—自然”矛盾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
商品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柏克特认为,“当我们思考内在于商品、货币和资本中的价值形式和自然之间的对立时,资本主义环境危机趋势的社会根源才能被完全揭示出来”[6]79,因此他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思路,将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构成——商品之中,揭露出商品所内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内在的“价值—使用价值”矛盾向外扩大化为“资本—自然”矛盾的路径,并以此为基础阐发了资本对于劳动力和自然条件的支配和剥削与生态危机的关系。
第一,商品内含“价值—使用价值”矛盾。柏克特根据马克思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分析,总结出使用价值和价值在生态层面的矛盾。在《资本论》“商品”章中,马克思揭示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异性,即“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8]50。也就是说,“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8]50,“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8]51。柏克特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交换过程时注意到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抽离的现象,揭示出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但是,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必然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8]51,它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其实可以看作是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自然属性具有质的差异性,它代表的是特殊性和有限性;而价值作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质上是同一的,因而只具有量的差异性,相应的,它代表的是普遍性、社会性和无限性。因此,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同质的价值和异质的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
第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交换价值统治使用价值可以看作是二者同时被作为更具一般性的社会形式的价值统治。[6]80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此时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起支配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生产和交换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获得货币,以满足资本增殖的内在需求。在柏克特看来,从使用价值占主导地位到交换价值或价值占主导地位,实质上是社会性的价值逐渐统治自然性的使用价值的过程,进而,价值在量上的无限性也必然会同使用价值在量上的有限性之间发生矛盾。简而言之,自然条件的稀缺性在由价值和货币控制的生产体制下被忽视了,生产陷入对自然的剥削之中。货币对于自然的物质差异性的抽象,是与生态相矛盾的。因此,柏克特总结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与自然有明显的矛盾性,主要反映在对自然条件的轻视,而这种轻视正是反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的基本形式。”[6]19
第三,“价值—自然”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具体地表现为资本对包括非人自然和人类自然在内的社会条件的全面控制和掠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目的是实现“价值增殖”,这就必然要求扩大再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地进行。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9]因此,资本在增殖目标的驱动下,一方面不断消解非人自然的多样性和联系性,另一方面逐渐割断劳动者同自然生产条件之间的联系,导致人成为远离自然和背离人类精神的异化存在,从而将非人自然和人类自然简单化、同一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和手段。此外,资本对自然和人的统治从经济领域扩张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化身为统治人们的工具理性,迫使人沦为单向度的人,无法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而加剧生态恶化的程度。
三、基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构建马克思的生态危机理论
一般而言,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我们将其理解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一些生态批判者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同于经济矛盾,将资本主义历史危机归结为经济危机,从而否定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其他可能性。针对这一理解,柏克特认为马克思从未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仅仅限定为经济层面的矛盾,相反,它具有多重维度,并且这种多重性能够为我们阐释现今所遭遇的环境危机提供理论依据。
柏克特首先承认马克思本人的确从未将环境危机与资本主义历史危机联系起来,尽管他分析了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共产主义的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确未能将环境问题纳入到其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考察之中,但是,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出发,资本主义环境危机趋势不仅符合而且可以大大丰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危机的预测。因此,与奥康纳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引进“生产条件”概念,然后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三者关系出发来阐释环境危机不同[3]257-259,柏克特根据马克思的文本,从未经修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分析了环境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出现的必然性。
在柏克特看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是指经济层面的矛盾,而且包括更基础层面的为私人利润而生产和为满足人类需要而生产之间的矛盾。否定马克思主义包含生态维度的生态批判者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危机的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10]278——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是理解为经济层面的矛盾,将资本主义危机简化为单一的资本积累危机,从而作出“马克思任何形式的危机理论日益与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潜在矛盾无关”[6]175-176的论断。柏克特反对这种狭隘的理解,认为生态批判者只关注了引文的前半部分,而忽略了紧随其后的更为重要的后半部分,即“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10]278。也就是说,生态批判者的错误在于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只是从狭隘的经济层面来理解[4]285-286。在柏克特看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两个方面,不仅是指生产对利润的追逐而导致经济危机,还包括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增加未能成为扩大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反而成为导致生产者及其共同体同生产条件之间日益分离的原因,进而引发资本主义的新的危机。所以,在柏克特看来,“为利润而生产和为需要而生产之间的矛盾,生产条件同生产者和他们的共同体之间的分离,社会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立,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同等表述”[6]182。换言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只是反映为积累危机,而是包括积累危机在内的这些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就表明资本主义仅是一种过渡的、历史性的生产形式,“甚至没有利润率问题出现,原则上,由于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出现问题,资本主义也会经历一场历史危机”。[6]181-182
所以,根据柏克特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解,环境危机也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历史危机的表现。在柏克特看来,“马克思虽然未直接将环境危机融入到他对资本主义历史界限的设想中,然而他的框架使这种融合成为可能,因为它将资本主义历史危机作为生产条件社会化这一特定阶级剥削方式的危机”[6]190。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控制着自然社会化的过程,将私人占有下的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变为社会生产下的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尽管这种转变扩大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为更少限制且更加持续的人与自然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由于这种自然社会化过程沦为资本积累的手段,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割裂了人类生产同生产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之间的统一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此消失,引发普遍的环境危机也就成为必然。
此外,柏克特根据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多重理解,界定出两种类型的环境危机——狭义的、就资本积累而言的环境危机和广义的、就人类发展而言的环境危机。[6]113可以看出,这两种类型的环境危机都包含自然环境的恶化,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立场的差异,前者是站在资本积累角度而言的,是由于资本扩张对原材料的需要而导致的自然条件短缺;而后者是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出发,站在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发展角度而言的,因为资本主义城镇和农村的工业划分所引起的物质和生命力量流通的不协调,导致了人类社会发展质量下降的危机。可以说,在以人与自然全面发展为理想的马克思看来,人类发展的环境危机更为根本,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题中之义,而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只是表现。[6]107-108
四、人的解放与通向共产主义的新契机
柏克特基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解,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的内在缺陷。在此基础上,柏克特从人的解放出发,论证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共产主义的亲生态性,丰富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论内涵。
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必然引发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一些生态批判者们看来,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信奉实际上陷入普罗米修斯主义或生产力中心主义,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前提的,因此必然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所以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包含着人类控制自然的反生态伦理观。柏克特承认马克思的确有对资本主义的高度赞扬,也有过对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生产力的增长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论述[11],但是马克思对此作出评价或判断的依据不是基于狭隘的工业主义视角,而是基于广义的人类发展视角。在柏克特看来,马克思基于广义的人类发展视角,断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在于它发展生产并将其社会化,使得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的普遍发展。但是,这种普遍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始终无法实现,相反,自然和社会条件的社会化反而为资本自由地使用自然和社会条件提供便利,并将它们转化为剥削生产者的条件,同货币积累一起限制工人和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被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所窒息。因此,资本同社会化的自然条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同追求普遍发展的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直到环境问题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进而导致无产阶级的反抗,成为通向共产主义的新契机。
探索共产主义的生态内涵,构建亲生态的和谐社会。柏克特认为,马克思对未来人类发展的设想,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步和由此出现的物质财富量上的增长和自由时间量上的增加这一反生态的标准,相反,马克思基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自然的亲生态和亲人类转变而预见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发展是质上的充足。[6]224也就是说,那些生态批判者基于狭隘的工业主义视角将共产主义物质化、片面化,而马克思则是基于人和自然全面发展的视角将共产主义设想为超越资本主义的亲生态和亲人类的社会。共产主义亲生态性的根源在于联合生产原则,它消除了生产者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社会分离,实现二者的重新联合,清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剥削形式——包括人对自然条件的剥削——存在的前提,联合生产的手段和目的始终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联系。
树立广义的共产主义革命观,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径更为多元。柏克特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打破了在它之前的阶级社会对人类发展的束缚,因此也同时创造了‘迈向(与资本主义)不一样的新社会的历史前提’。”①译文参考: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6.[6]199。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使得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路径更为多元化。具体而言,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资本更容易获得对社会生产条件的控制权,进而达到对无产阶级的全方位剥削。因此,柏克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已不再像19世纪那样,是单纯的经济剥削,而是包括政治、文化、生态在内的各方面剥削。同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观也不能再局限于狭隘的工业主义视角,而应该转向更广义的人类发展视角,必须从纯粹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层面的斗争;阶级斗争的目标也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或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是包括了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要求。所以,柏克特认为广义的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观恢复了片面的工业主义视角所放弃的对生产条件的控制,从而为经济斗争和文化、生态等多方面斗争的联合创造了可能性,一方面真正将共产主义指向一个将财富变为公共财富的社会,另一方面拓宽了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
五、柏克特构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启示
柏克特依据马克思的文本,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马克思生态思想进行阐释,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生态内涵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亲生态性,拓宽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路径,从而呈现出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当然,柏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构建存在着过度阐释等问题,过度强调人与自然关系在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原本在马克思主义中起重要作用的社会关系维度。但是,不可否认,柏克特构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尝试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而言,柏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构建,超越了此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延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理解,主张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现实的变化而将重点转向意识形态批判,由此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中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统一关系,制造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空场。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发起反对实证主义的无情战争为特征,这使它不幸地付出了一个沉重的代价:倾向于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制造裂痕,由此导致对关联生态学和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所有存在方面的忽视”[12]。进而,在构建马克思生态思想时,此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求助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非整体理解,将“现代”生态尺度嫁接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上[13],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与之不同的是,柏克特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之中,基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解——这一整体性不仅包括社会和自然,而且包括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成熟时期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对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整体理解——来挖掘马克思生态思想。甚至在科沃尔看来,柏克特的这一路径为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纯正性而达到了神化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如果柏克特—福斯特的纯正马克思(pure Marx)是试金石,那么他只能从最开始被触动: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足够专业,清除掉所有偏离的解释,简而言之,是一种统治阶级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眼中坚定地聚焦于19世纪伟大的文本。”[14]反对者尖锐的批判恰好从反面说明了柏克特对于马克思文本的重视。
其次,柏克特依据马克思的文本著作构建马克思生态思想,反驳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反生态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论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生命力。如前所述,此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大力鼓噪历史唯物主义反生态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或对其进行“修正”。但是柏克特从马克思的文本著作出发,“绝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环境主义的一个选项而已,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特别形式的环境主义,这种环境主义是从阶级关系和人类解放的立场出发来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6]preface,不仅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生态问题阐释的有效性,而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正如福斯特所赞扬的:“马克思对生态学的贡献之所以在如今被广泛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柏克特的著作和受其著作影响的极少的思想家。”[15]此外,在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社会主义被普遍唱衰之时,柏克特论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联合生产的基本原则)内在地包含着更人道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必然性”[6]256,证明了我们“有理由憧憬历史唯物主义在阶级概念下永不妥协的革命本质,为更加彻底的新世纪社会主义设想重建创造潜力”[5]14。
再次,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资本与自然的关系。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自然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这是柏克特构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阐释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和完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中资本和市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资本的无限扩张逐渐越过了生态红线,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因素。限制资本扩张的趋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30这生动诠释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二者之间的主次关系,彰显了我们党和政府对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最后,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必须时刻保持人民性这一根本底色。正如柏克特在批判马克思是生产中心主义者这一论断时所指出的,必须摆脱狭隘的工业主义视角——以物质增长为评价标准,转到以广义的人类发展视角来看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也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16]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必须始终坚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普遍发展为标准,而不是为了物质财富的增长,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环境保护成果直接惠及于民。这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显著特征和优良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政治本色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