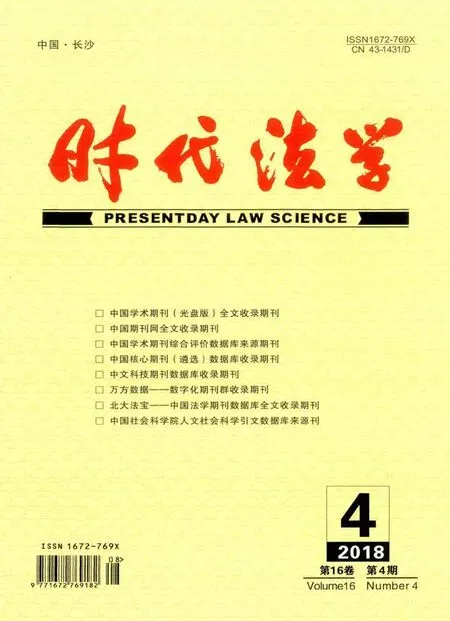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跨界破产中的适用与启示*
2018-04-01黄圆圆
黄圆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29)
一、问题的产生
公共政策例外条款(public policy exception)是国际私法领域的重要机制[注]在2012年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和判决执行的第1215/2012号(欧盟)条例》中,第45条和第46条明确规定,如果此种承认(或执行)明显违背被请求承认国的公共政策,该判决得被拒绝承认(或执行)。1958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会议通过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又称“《纽约公约》”)第5条明确规定,如果承认或执行该项裁决将和这个国家的公共秩序相抵触,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的管辖当局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 在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注]《跨界破产示范法》第6条规定,本法中任何规定概不妨碍法院拒绝采取本法范围内的某项行动,如果采取该行动明显违反本国的公共政策。《欧盟跨界破产条例(第2015/848号)》第33条规定,任何成员国均可拒绝承认在其他成员国启动的破产程序,或拒绝执行由该破产程序产生的判决,如果承认或执行的效果将明显违背本国的公共政策,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或宪法性的权利和个人自由。。 作为接案国法院对外国破产程序进行承认审查的最后一步,该条款为接案国法院权衡本国国家利益与国际跨界破产合作要求提供了司法空间。如果承认或救济某外国破产程序将明显违背接案国的公共政策,即便该破产程序符合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一般审查标准[注]这里所指的“一般审查标准”,包括管辖权审查、条约关系审查、互惠关系审查、正当程序审查等。,接案国法院也可依据该条款,拒绝对该外国破产程序予以承认和救济。换言之,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对于一国是否能够参与国际跨界破产合作具有决定性作用。
然而,由于“公共政策”的概念通常以国家法律为基础且国别规定各异,《跨界破产示范法》(下称“《示范法》”)和《欧盟跨界破产条例》均未对“公共政策”的内涵进行明确界定。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跨界破产示范法颁布及解释指南(2013)》(下称“《指南》”)的说明,“公共政策”这一措辞虽然具有较为广泛的内涵,但多与各国强制性法律规定相关。在许多国家,公共政策被解释为仅限于法律的根本原则,特别是宪法规定的各项保障[注]参见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工作组.指南[Z].维也纳:联合国维也纳办公室,2014.。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在跨界破产案件中限制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基本原则[注]《指南》第104段指出,“明显(manifestly)”一词意在强调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应当作限制解释,并强调只在涉及到对颁布国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时才援引第6条。,因此,最终援引该条款以拒绝国际跨界破产合作的司法实践非常有限。但随着影响各国跨界破产审判的因素愈来愈多,国际社会对该条款的适用似有扩张趋势,究其扩张适用的基本路径,有学者认为以债权人保护条款为代表的某些跨界破产规则为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扩张适用提供了便利[注]See Elizabeth Buckel, Curbing Comity: The Increasingly Expansive Public Policy Exception of Chapter 15, Geo. J. Int’l Law, 2013, p.1294.。考虑到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中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在现有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该条款与相关条款的逻辑关系进行厘清,以明确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司法适用,同时为中国跨界破产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完善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二、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司法适用
在跨界破产司法实践中,虽然法院最终认定应当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案例屈指可数,但不容否认,当事方围绕该条款发生争议的个案不在少数。本文根据已有司法实践,对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适用进行比较分析。
(一)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情形
从目前的国际司法实践来看,不符合程序性要求、侵犯宪法性权利以及违背跨界破产核心机制和宗旨等情形,均有可能导致接案国法院以公共政策例外为由,拒绝对外国破产程序予以承认和救济。
2012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区法院在审理一起跨界破产案件时,明确如果外国程序无法满足正当程序及告知要求,将有可能触发《美国破产法》第15章中的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注]See in re Sivec SRL, 476 B.R. 310 (E.D. Oklahoma 2012).。该案的债务人于2008年在意大利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11年债务人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请求美国法院中止其债权人正在美国进行的诉讼活动。经查明,该案涉及的主要债权人是一家美国公司,由于未收到意大利程序的启动通知,导致债权人错失了申报债权的期限,从而无法在意大利重整程序中行使表决权等法定权利。美国法院认为,该意大利程序剥夺了债权人受美国立法保护的被告知及出庭听审的权利,考虑到这两项权利是最为基本的程序性权利,最终美国法院援引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拒绝对该意大利程序予以承认和救济。2006年欧盟法院在审理“欧洲食品公司破产案”时[注]See in re Eurofood IFSC, 2006 E.C.R. I-3813.,也曾强调“被告知权和出庭权在一项公正的司法程序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就破产案件而言,债权人或其代表人能否依据平等武装理论参与到破产程序中,对于评价该破产程序的程序公正至关重要。虽然在不同国家的破产程序中,告知或出庭听审的程序要求各异且其具体内容根据个案紧迫程度可能有所变化,但必须保障当事方具有相应的抗辩权”[注]“平等武装”(equality of arms)这一概念,最早为欧洲人权委员会所使用。现阶段,“平等武装”一词已被广泛用来描述控辩双方之间对等的程序权利义务关系。参见冀祥德. 控辩平等之现代内涵解读[J]. 政法论坛,2007,(6):90.。
2011年美国纽约南区破产法院在审理一起涉及德国程序的跨界破产案件中,强调侵犯隐私权会成为援引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法律基础[注]See in re Toft, 453 B.R. 186 (S.D.N.Y. 2011).。该案中的债务人在德国进入破产程序,随后德国程序中的外国代表人请求美国法院承认并协助该德国程序。该案主要的协助请求是外国代表人希望美国法院批准其进入债务人的两个电子邮箱(邮箱的主服务器位于美国境内),以了解债务人在美财产情况以及债务人变卖破产财产的具体信息。审理该案的艾伦法官(Allan L. Gropper)认为,德国代表人请求的救济措施涉及债务人隐私,而隐私权是美国众多法律规定的基础性权利,同时也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众多州宪法力图保障的基本权利[注]该案中,美国法院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查询了《窃听法》(Wiretap Act)和《存储信息保护法》(Stored Communications Act)两部法案。《窃听法》中规定对故意截获他人电子通信的行为予以刑事或民事处罚。法院认为,如果允许德国代表人秘密截获债务人的电子邮件,将对债务人的隐私权构成侵害。随后,法院将本案情况与德国代表人提供给美国法院的判决先例进行对比,认为其提交的司法先例与本案情形不符,对本案的审理不具约束力。最后,美国法院查询了《破产规则》中的相关条款,按照规定,只有极少数情形才可以在不通知目标对象的情况下即采取截获行为,而本案不属于“极少数情形”。综上,援引《美国破产法》第15章1506条。。最终,艾伦法官以承认德国程序并予以协助将明显违背美国的公共政策为由,拒绝对该破产程序予以协助。
2009年美国纽约东区破产法院在审理一起涉及以色列程序的跨界破产案件时,提出如果承认或救济某外国破产程序将明显违背《美国破产法》第15章的核心机制及宗旨,美国法院可以援引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注]See in re Gold & Honey, 410 B.R. 357, 373 (E.D.N.Y. 2009).。该案的债务人于2008年7月在以色列进入接管程序(receivership proceeding),并于同年9月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重整。随后,美国法院发布自动中止(automatic stay)命令,强调该命令适用于债务人所有的破产财产。然而,该案的债权人仍在以色列继续推动接管程序,并选任接管人,之后该接管人向美国法院提出《美国破产法》第15章项下的破产保护请求。美国法院认为,一旦承认该以色列接管程序,美国最基本的国家政策和破产法机制将受到严重腐蚀,因此应当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以拒绝承认和协助[注]2011年,美国破产法院审理过一起涉及意大利程序的跨界破产案件。该案中,意大利程序选任的代表人不顾美国法院发布的自动中止命令,继续采取违背该中止令的行为。最终,美国法院拒绝承认和救济该意大利程序。虽然美国法院并未强调拒绝承认和救济的理由是意大利程序违背美国核心的破产法机制,但足以说明外国程序在违背《美国破产法》第15章核心机制的情况下,很可能无法获得美国法院的承认和救济。See in re Think 3 Inc., Case No. 11-11252.。
(二)不应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情形
相较于法院最终援引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司法实践,关于是否应当适用该条款的司法案例更为丰富。围绕该条款发生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清偿额差异、实体法差异、法律适用差异以及承认前行为认定等方面。
首先,关于清偿额或清偿率差异的争议[注]在破产案件中,清偿额(或清偿率)是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跨界破产案件中,经常出现由于各国破产实体法内容差异等原因,导致针对同一债务人的破产清偿额(或清偿率)有所差异。实践中,这一事实也成为债权人请求法院启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主要理由。。在“KDI破产案”中,债务人在加拿大进入破产程序,并请求美国科罗拉多州破产法院予以承认和协助。但争议方请求美国法院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理由是较之美国本地的破产程序,美国投资者在加拿大程序中的受偿额较少,且加拿大程序的成本明显偏高。最终,法官认为上述理由不足以构成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基础[注]See in re Pet. of Ernst & Young, Inc., 383 B.R. 773, 774 (D. Colo. 2008).。针对这一争议,英国霍夫曼公爵(Hoffman)认为,“(修正的)普遍主义是英国法院自18世纪以来审理跨界破产案件所遵循的黄金规则。普遍主义要求英国法院与债务人主程序所在地的法院进行合作,以确保债务人破产财产的统一清偿,即便这样可能会使英国债权人的受偿额受到不利影响。”[注]See in re HIH Casualty & General Insurance Ltd., [2008] 1 WLR 852.
其次,关于实体法差异的争议[注]从本质上讲,关于实体法差异的争议,是指基于不同程序间的实体法差异导致当事方权益变动,从而引发的争议。而这里所引发的争议,归根结底是关于清偿问题的争议。。在“曼斯菲尔德破产案”中,涉及一项加拿大程序中的第三方豁免问题,而《美国破产法》第11章并不认可该类豁免,除非该类豁免对于债务人重整计划的成功通过具有必要性。有争议方主张,基于加拿大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实体法规定存在实质差异,法院应当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拒绝承认该案中的加拿大程序。最终,美国法院就这一主张给出了否定评价[注]See in re Metcalf & Mansfield Alternative Invs., 421 B.R. 685 (S.D.N.Y. 2010).。类似的,在“OAS破产案”中,争议方认为该案巴西程序中的清偿方式与《美国破产法》项下的清偿方式存在实质差异,且该差异是对《美国破产法》的明显背离,应当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予以拒绝承认,但美国法院并不认同这一主张[注]该案的债务人是一家巴西企业集团,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巴西法院发布实质合并(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命令,这意味着集团间的内部债务抵消。争议方认为,根据《美国破产法》的规定,美国法院在同等情形下并不会对债务人进行实质合并,这意味着债权人可以自由追讨债务人内部进行的欺诈转移。See in re OAS S.A. et. al., 533 B.R. 83 (S.D.N.Y. 2015).。同时,外国破产法对债务人保护程度的差异,也不足以构成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适用基础[注]在“ABC教育破产案”中,与《美国破产法》对债务人的保护程度不同,待承认的外国破产程序对债务人给予了更大程度的保护,即便如此,美国法院认为这一差异不足以导致法院启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See in re ABC Learning Ctr. Ltd., 445 B.R. 318, 336 (D. Del 2010).。
再次,关于法律适用差异的争议。在“帕玛拉特破产案”中,债务人首先于意大利进入破产程序,后向美国破产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阻止其债权人正在纽约进行的诉讼行为[注]帕玛拉特是意大利一家著名的跨国食品加工企业,于2003年申请破产保护。See in re Parmalat, 394 B.R. 696 (S.D.N.Y. 2008).。债权人主张争议的适用法律应为纽约法律,意大利程序中的禁止令对其不具有约束力。虽然该案争议方没有直接援引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但美国法院坚持法律适用差异不足以违背正当程序以及公共政策等最基本的概念[注]“帕玛拉特破产案”发生于2003年,该案的美国程序开始于2004年。由于当时美国尚未采纳《示范法》,美国程序的审理依据是《美国破产法》第304条。See Scott C. Mund, 11 U.S.C. 1506: U.S. Courts Keep A Tight Rein on the Public Policy Exception, But the Potential to Undermin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Remains,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0, pp.345-346.。同时,美国法院对于法律适用问题的立场,也在另一个非破产案件中得以强化。当法律适用争议发生时,美国法院更倾向于尊重国际礼让原则,积极进行国际合作[注]在2008年发生的一起涉及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台湾公司申请美国法院禁止被告正在中国北京进行的诉讼行为,理由是双方明确约定关于合同所发生的一切法律争议应当适用美国加州法律。原告认为,被告在中国北京进行的诉讼程序意在逃避美国加州重要的公共政策。但加州当地法院最终并没有支持原告的主张,而是倾向于礼让和国际合作。See in re TSMC North America v. Semiconductor Mf’g. Int’l Corp., 161 Cal. App. 4th 581, 586 (2008).。
最后,关于法院承认前各方行为所引发的争议。在美国法院于2007审理的一起跨界破产案件中,债务人首先在日本进入接管程序,日本程序中的代表人通过公司法规则罢免原董事,且在债务人其他董事的配合下对其破产财产进行出售等处置行为。随后,日本程序中的代表人向美国法院提出破产保护申请,请求美国法院承认该日本程序为外国主要程序(foreign main proceeding)。争议方认为,由于外国代表人罢免董事的行为并未取得美国法院的允许,如果获得法院承认,将明显违背美国的公共政策。但其主张并未获得美国法院的支持[注]美国法院在该案中强调,第15章的性质基本上属于程序性,其存在并不构成对美国法律的实质改变。换言之,第15章并不能改变美国法律尊重的礼让原则。且从第15章功能的角度分析,如果外国代表人不需要美国当地法院的协助,其完全没有必要申请第15章项下的承认与救济。考虑到第15章立法史及《示范法》的有关评述内容,美国法院严格坚持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限制适用。See in re Iida, 337 B.R. 243, 248 (9th Cir. 2007).。同时,弗吉尼亚州破产法院在一起个人跨界破产案件中,再次重申了“在外国代表人向美国法院提出破产保护申请之前,其所采取的正当行为并不足以构成法院援引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基础”这一观点[注]该案中的债务人是一名持美国临时签证的英国人,其早先已在英国进入破产程序,其所有破产财产已被依法接管。随后,接管人请求美国法院承认英国程序。债务人主张接管人在从事任何法律行为前,应当提前获得美国法院的允许。最终美国法院对这一主张给予了否定评价。See in re Loy, 380 B.R. 154 (W.D.Vir. 2007).。
三、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与其他条款的关系认定
虽然国际社会对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司法适用普遍坚持限制适用的立场,但就该条款与主要利益中心条款、额外救济条款和债权人保护条款的内在关系、以及上述条款是否为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扩张适用提供路径等问题的争论却不绝于耳[注]Elizabeth Buckel认为上述条款为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扩张适用提供了便利。但Michael A. Garza则认为,上述条款是保障公共政策例外条款限制适用的配套机制。See Elizabeth Buckel, Curbing Comity: The Increasingly Expansive Public Policy Exception of Chapter 15, Geo. J. Int’l Law, 2013, p.1294. See Michael A. Garza, When Is Cross-Border Insolvency Recognition Manifestly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Fordham Int’l L. Journal, 2015, pp.1623-1627.。明晰该条款与相关条款的内在逻辑,有助于避免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扩张适用,这对国际跨界破产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注]此处的分析以《示范法》为参照。。
(一)相关条款在跨界破产规则中的功能定位
主要利益中心(center of main interest, 下称“COMI”)是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核心规则。根据《示范法》第17条的规定,当外国程序发生于债务人COMI所在地时,应被承认为外国主要程序;当外国程序发生于债务人营业所(establishment)所在地时,应被承认为外国非主要程序。当某外国程序既非外国主要程序,也非外国非主要程序时,“贝尔斯登破产案”的审理法官给出了拒绝承认和救济的回应[注]See in re Bear Stearns High-Grade Structured Credit, 389 B.R. 325 (S.D.N.Y. 2008).。该案中,债务人虽然注册于开曼群岛,但却从未在该地从事经常性管理活动且第三人对该地难以查明,同时该地也不存在债务人的营业所,法官认为开曼程序既不是外国主要程序,也不是外国非主要程序。至于是否应当予以承认,本案法官强调外国主要程序与非主要程序的存在是一个定义问题,而非自由裁量问题,对于不符合二者定义的外国程序,即不应当予以承认和救济[注]该案对于美国法院明确债务人COMI规则的司法适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前,在“斯芬克斯基金破产案”中,审理法官认为,当外国程序无法满足外国主要程序和外国非主要程序的定义时,考虑到将其认定为外国非主要程序不会导致不利结果,法官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认定案件中的外国程序为外国非主要程序。See in re SPhinX, Ltd., 371 B.R. 10 (S.D.N.Y. 2007).。
额外救济条款(additional assistance)是《示范法》救济体系的补充条款。考虑到各国在采纳《示范法》时,可能已经存在对外国破产程序予以协助的立法,为了补充和协调跨界破产合作的途径与形式,额外救济条款明确采纳国可依据其他法律向外国管理人提供进一步援助。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接案国法院既无法依据《示范法》中的自由裁量救济条款对某外国程序予以救济,也无法依据本国其他法律提供救济时,接案国即可以无法提供额外救济为由,拒绝对外国程序予以承认和协助。
与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制定意图类似,债权人保护条款的制定也是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虽然《示范法》并没有试图对条款中的“债权人”进行界定,但通常被采纳国解释为“本国”债权人[注]参见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工作组.指南[Z].维也纳:联合国维也纳办公室,2014.。在跨界破产司法实践中,接案国法院可以“承认或救济外国程序将严重损害本国债权人利益”为由,拒绝参与国际合作,从而间接达到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适用效果。相较于COMI条款和额外救济条款,债权人保护条款与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关系最为密切,被视为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扩张适用的主要路径。
(二)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与相关条款的争议关系
如前文所述,关于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与相关条款的内在逻辑关系,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即“替代机制说”与“配套机制说”。
1.替代机制说
“替代机制说”认为,相关条款有为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提供扩张适用路径的趋势。考虑到公共政策例外条款限制适用的基本要求,接案国法院为了实现拒绝承认和救济外国程序的司法意图,便会援引相关条款间接达到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司法效果。这一观点在债权人保护条款与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关系问题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萨阿德破产案”中[注]此处属于音译。See in re Ackers v Saad Investments Company Ltd., [2013] FCA 738.,债务人是一家注册于开曼群岛的投资公司,主要从事国际投资业务,于2008年在开曼进入清盘程序。根据澳大利亚《跨界破产法案》(Cross-Border Insolvency Act 2008)的规定,债务人的COMI位于开曼群岛,因此,债务人在开曼群岛进行的破产程序被澳大利亚法院认定为外国主要程序。2012年,开曼程序的外国代表人请求澳法院将债务人位于其境内的资产返还开曼程序,以统一清偿债权人。该案中,债务人在澳的主要债权人是澳洲税务局,考虑到外国税收债权人无法根据开曼群岛的法律在开曼程序中申报债权,澳法院最终作出了有利于澳洲税务局的判决,命令中止返还债务人位于澳境内的所有资产。该判决指出,虽然《示范法》坚持普遍主义的跨界破产合作理念,以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牺牲当地债权人的权益为代价。考虑到澳洲税务局无法在开曼程序中申报债权,为了维护其利益,澳法院认为其发布中止债务人财产转移的命令是恰当的,且有利于公正、平等对待所有债权人。澳法院的上述立场在“泛洋海运破产案”中同样得以体现[注]See in re Yu v STX Pan Ocean Co Ltd., [2013] FCA 680.。该案的债务人是一家韩国航运企业,韩国程序中的外国代表人向澳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澳法院颁布禁令,以禁止澳境内债权人针对债务人船只采取扣押行为。虽然澳法院承认该案中的韩国程序为外国主要程序,但澳法院并没有批准外国代表人的上述请求,其认为通过扣船实现海事优先权是海商法中的特有机制,禁止扣押船舶是对全体海事优先权人利益的损害。最终,外国代表人未能从澳大利亚程序中挽回任何债务人的破产财产。
在上述案件中,作为《示范法》采纳国的澳大利亚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展现友好积极的跨界破产合作立场,而是通过宽泛解释债权人保护条款等途径,保守地应对某些跨界破产法律问题[注]See Sandeep Gopalan and Michael Guihot,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Law: A Proposal for Judicial Gap-Filing, Vand. J.Transnat’l Law, 2015, p.1235.。从目前国际跨界破产司法实践来看,税收债权无法在外国程序中受偿几乎已成惯例[注]See Jonathan M. Weiss, Tax Claims in Transnational Insolvencies: A “Revenue Rule” Approach, Virginia Tax Review, 2010, p.261.,澳法院出于保护本国税务机关利益的目的,拒绝参与国际合作的做法明显欠妥。对“泛洋海运破产案”而言,该案属于典型的涉海跨界破产案件,如何救济该类案件中的海事优先权问题,目前仍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议题[注]See William Tetley, Conflicts of Law Between the Bankruptcy Courts in Admiralty: Canada,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Tul. Mar. L. Journal, 1996, p.258-288; See Anselmo Reyes,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nd Shipping Companies, 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2016, p.520.。从近期发生的“韩进海运破产案”来看,虽然各国法院对该问题的立场存在分歧,但都给予了韩国程序不同程度的救济[注]石静霞,黄圆圆.跨界破产中的承认与救济制度——基于“韩进破产案”的观察与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2):34.。比较而言,“泛洋海运破产案”中澳法院的做法有待商榷。
2.配套机制说
“配套机制说”从《示范法》整体结构的角度,认为相关条款共同服务于公共政策例外条款限制适用的宗旨。换言之,只有在无法依据相关条款予以拒绝承认的情形下,接案国法院才可能考虑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适用。目前,美国巡回法庭已在两起涉及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上诉案件中,明确表达了“配套机制说”的观点。
在2011年由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法院审理的“奇梦达破产案”中,债务人是一家总部位于德国的半导体设备公司,2009年于德国进入破产程序[注]See in re Qimonda AG, 433 B.R. 538 (E.D.Va. 2011).。由于债务人在美国拥有大量专利,德国程序选任的代表人向美国法院提出破产保护申请,请求美国法院对德国程序予以承认并对债务人位于美国的专利进行救济,以实现债务人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注]债务人总共拥有约1.2万项专利,其中至少包括4000项美国专利。债务人通过专利交叉许可协议与美国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电子公司合作。根据协议,债务人与电子公司就成千上万的专利享有永久的、不可撤回的交换专利权。See Michael A. Garza, When Is Cross-Border Insolvency Recognition Manifestly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Fordham Int’l L. Journal, 2015, pp.1620-1621.。美国法院认为,德国程序对债务人专利的救济措施与美国专利法存在显著不同,且《德国破产法》对专利许可无法给予有效的保护,这明显违背美国支持科技创新的国家政策,故援引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以拒绝承认和协助德国程序。在上诉审阶段,美国第四巡回庭认为,考虑到初审法院已就债权人保护条款进行了正确解读,在充分衡量本国债权人利益和破产合作的基础上,本案更适宜以债权人保护条款为基础作出判决[注]See in re Qimonda AG, 737 F.3d 14, 29 (4th Cir. 2013).。在2012年审结的“比特罗公司破产案”中,美国法院再次阐述了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同相关条款的适用关系。该案的债务人是一家墨西哥控股公司,于2010年在墨西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注]See in re Vitro S.A.B. de CV, 455 B.R. 571, 575 (N.D, Tex. 2011).。随后,墨西哥程序中的代表人向美国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其承认墨西哥程序中的重整计划。由于该重整计划彻底消灭了债务人的非破产子公司对债权人的保证义务,美国法院认为,在破产案件中保护第三方的请求权是一项最为基本的国家政策,墨西哥程序中的重整计划极端地豁免了非债务人的担保义务,根据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规定,该重整计划不应得到承认和救济。在上诉审阶段,美国第五巡回庭回避了对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讨论,着重分析《美国破产法》第15章有关救济条款的适用问题[注]See in re Vitro S.A.B. de CV, 701 F.3d 1031, 1070 (5th Cir. 2012).。第五巡回庭认为,救济条款的适用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要求,即相较于额外救济条款,对外国非主要程序的救济条款和债权人保护条款等救济条款更为具体,应当予以优先适用。考虑到该案中的墨西哥程序无法依据额外救济条款得到救济,换言之,《美国破产法》第15章中的救济条款无法适用于该案,故对该程序予以拒绝承认。
可以看出,“配套机制说”的观点是从逻辑解释的角度出发,俯瞰跨界破产法律规则的内容结构,通过分析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与其他相关条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探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合理适用。虽然上述两个案件的审理结果均导致外国破产程序的拒绝承认与救济,客观上与援引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结果无异,但“配套机制说”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公共政策例外条款限制适用的基本原则,符合跨界破产合作的根本宗旨。
纵观上述争论,作者更倾向于“配套机制说”。从《示范法》文本的角度来看,包括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内的文本条款均服务于《示范法》的立法宗旨,即“为处理跨界破产案件提供有效机制,以促进达成本国法院及其他主管机构与外国法院及其他主管机构之间涉及跨界破产案件的合作”[注]参见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工作组.指南[Z].维也纳:联合国维也纳办公室,2014.。为了保障立法宗旨的实现,《示范法》各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紧密有序,并不存在条款功能的重叠现象。换言之,“替代机制说”忽略了法解释方法中的体系解释对于阐明规范意旨的关键作用[注]体系解释方法具体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地位,即依其编、章、节、条、款、项之前后关联位置,或相关法条之法意,阐明其规范意旨之解释方法。其主要功能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之关联,探究其规范意义;其二,采纳体系解释方法,以维护法律体系及概念用语之统一性。梁慧星.论法律解释方法[J].比较法研究,1993,(1):49.。同时,从国际跨界破产立法与司法实践发展的角度来看,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观点的对立,主要是由于各法域在司法实践中对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解读有所偏差,而这种偏差往往与各法域所处的跨界破产法制发展阶段及其国际合作立场密切相关。虽然前文提及的澳大利亚和美国均属于《示范法》的采纳国,但两国在跨界破产立法与司法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较之美国体系化的跨界破产立法以及普遍主义的合作立场,澳大利亚在《示范法》基础上颁布的《跨界破产法案》(Cross-Border Insolvency Act 2008)与本国已有法律出现多处重合,亟待改革[注]See Gerard McCormack and Anil Hargovan, Austral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Paradigm, Sydney Law Review, 2015, p.390.; 司法实践方面,澳大利亚法院在其审理的数个跨界破产案件中,均呈现出一定的地域主义倾向,从而为“替代机制说”提供了论证土壤。目前来看,“替代机制说”既不符合国际跨界破产立法宗旨和要求,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对跨界破产合作的客观需求,且有悖于国际跨界破产合作的主流趋势。
四、中国的立法选择与借鉴
由于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是平衡国际跨界破产合作需求与国家利益的核心条款,将该条款纳入本国跨界破产立法体系是各国在进行跨界破产规则构建时的必然选择[注]以《示范法》为参照,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各国立法中的表现形式略有不同。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毛里求斯、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将《示范法》第6条完整纳入本国的跨界破产立法中;加拿大、希腊、墨西哥、塞尔维亚、黑山、韩国、英属维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在采纳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时,去掉了《示范法》第6条中强调该条款限制适用的副词——“明显地(manifestly)”;日本则采用“公共秩序(public order)”一词替代原《示范法》第6条中的“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一词。See Michael A. Garza, When Is Cross-Border Insolvency Recognition Manifestly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Fordham Int’l L. Journal, 2015, pp.1595-1599.。现阶段,中国的跨界破产立法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如何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合理纳入并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值得各界予以关注和研究。
(一)“八步认定理论”的提出与实践
近期,有学者从平等武装理论的角度出发,总结出有序审查外国破产程序的八个步骤,这为接案国法院认定是否应当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提供了思考路径[注]See Bob Wessels,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Law Part Ⅱ: European Insolvency Law, Deventer: Wolters Kluwer 2017, para. 10118ff.。具体而言,第一步审查外国破产程序是否给予了当事方充分、公平的机会以陈述案件事实及法律问题;第二步审查外国破产程序是否给予了当事方充分、公平的机会以评论涉案证据和对方当事人作出的法律论证;第三步强调,只有在迫切需要外国法院发布裁决的紧急情况下,接案国法院才可对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审查要求予以宽限;第四步要求第三步中提及的外国法院发布的裁决,必须具有“首日命令(first day order)”的性质或命令中的措施“绝对(absolutely)”不可延迟[注]“首日命令”的术语源自《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司法实践。从字面意思来看,在破产案件审理首日的几个小时之内,美国破产法院即会面临大量刻不容缓的紧急救济请求。这些救济请求多数属于行政性质的请求,可能对当事方的权益造成实质影响。在个别情况下,申请法院发布“首日命令”的动议(motion)并不会告知第三方。为了保障程序正义,美国法院要求必须将该动议告知可能受此影响的当事方。See in re Center Wholesale, Inc., 759 F.2d 1440, 1448-1450 (9th Cir. 1985).; 第五步强调,如果外国法院发布了首日命令,则不论是当事方还是外国法院,均应尽最大可能将案件的紧迫性合理性告知主要的非担保债权人、任何受此影响的担保债权人以及相关的政府监管机构;第六步审查外国法院是否针对其所采取的紧急措施给予了各利益方程序上的保障,即允许其对法院采取的紧急措施进行抗辩;第七步审查外国法院采取紧急措施的期限及范围,任何法院采取的紧急措施应当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且仅出于维护债务人日常经营的需要或管理人保全破产财产价值的需要;第八步审查外国法院的后续程序措施,法院必须在程序上为其他利益方提供进一步的额外救济措施[注]这里所指的“其他利益方”包括债务人和受紧急措施影响的债权人。,以确保所有利益方均能充分、无条件地享有平等武装理论的保障[注]2011年,英国高等法院在审理一起个人跨界破产案件时,明确强调了维护平等武装理论的重要性。该案中的债务人是一家跨国企业集团的董事长,考虑到债务人此前已在北爱尔兰申请破产,英国高等法院认为有必要为北爱尔兰程序中的官方接管人(official receiver)提供参与英国高等法院程序的机会,以保障正在英国高等法院进行的破产程序满足“八步认定理论”中的前两项审查标准。See in re Seán Quinn et al., [2011] IEHC 428.。
作者认为,“八步认定理论”主要是从程序公正的角度,试图为接案国法院审查外国破产程序的正当性提供审查路径。较之跨界破产层面的公共政策审查,“八步认定理论”的审查范围及审查对象均较为局限。在审查范围方面,“八步认定理论”重在讨论正当程序审查。虽然已有的司法实践表明外国程序的正当性问题极易导致接案国法院启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但公共政策审查还会涉及到程序以外的事项,如外国代表人提出的救济请求是否有悖于接案国的根本法律原则等问题。在审查对象方面,“八步认定理论”的审查对象是包含紧急措施的外国程序,虽然审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可适用于一般外国破产程序,但审查要求较为笼统,无法体现破产案件的特殊性。因此,“八步认定理论”与跨界破产语境下的公共政策审查并不能完全等同,且其对合理适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指导有限。
(二)中国立法对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吸收与借鉴
《企业破产法》第5条第2款明确提及“如果承认或执行外国破产裁决将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法院将不予承认和执行”。该条款虽看似与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具有一定共性,但二者依旧存在较大差异[注]本文认为,《企业破产法》第5条的上述规定与跨界破产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企业破产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并未采用“明显”一词或类似措辞,考虑到该条款尚无司法适用先例,因此无法从字面意义探究该条款是否存在限制适用的立法意图;第二,《企业破产法》第5条第2款中关于“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用语及其变形,多次出现在我国不同的部门法中,在缺乏进一步解释的情形下,该条款无法体现出其在跨界破产语境下是否具有特殊内涵。较之《企业破产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虽然《示范法》正文对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表述也较为简洁笼统,但《指南》等相关配套文件为该条款的内涵及适用提供了详实的指导,体现出了跨界破产语境下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特殊性。。因此,在中国未来的跨界破产立法改革中,有必要纳入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或在保留上述原条款的前提下,融入如下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内涵与理念:
首先,明确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跨界破产案件中应当限制适用的基本原则。对于“公共政策”的具体内涵,应当明确区分针对本国事务的公共政策和适用于国际事务的公共政策。一般而言,针对国内事务的公共政策内涵较为广泛,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解释》”)第10条的规定,凡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食品或公共安全卫生的、环境安全的、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反垄断与反倾销的情形,因与中国社会公共利益直接相关,均属于中国法律强制规定的范畴,可被视为中国国内法规定的公共政策。但在跨界破产语境中,建议中国立法明确限制上述针对国内事务的公共政策援引,通过采用“明显违背”等类似措辞,强化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限制适用,减少实践中针对国内事务的公共政策对国际跨界破产合作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注]2006年欧盟法院在审理“欧洲食品公司破产案”时,即强调公共政策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内涵可能千差万别,但跨界破产领域的公共政策应当限定在与宪法所保护的最基本的权利和与自由相关的程序性及实体性的公共政策范围内,且各国法院在特定情形下应当对本国公共政策的内涵予以限制。See Scott C. Mund, 11 U.S.C. 1506: U.S. Courts Keep A Tight Rein on the Public Policy Exception, But the Potential to Undermin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Remains,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0, p.338.。
其次,重视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司法适用的灵活性。作为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的控制阀,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援引通常会导致接案国法院拒绝申请方提出的破产保护请求。因此,在立法中不仅要坚持限制适用该条款的基本原则,还应特别关注该条款的灵活适用问题。换言之,如果完全承认或救济外国破产程序将明显违背接案国的公共政策,是否存在部分承认或救济的可能。近年来,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基于诉讼经济和促进国家间判决流通的目的,国际条约或国内法层面开始引入可分割制度,即排除对外国判决中有违接案国公共政策或存在争议性的判决内容,对判决的其余部分予以承认和执行[注]可分割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指的是外国判决中包含数项可分割的内容,当事人只申请承认和执行部分判决内容或被请求国法院依据其国内法就其中部分或数部分,独立予以承认或执行。连俊雅.可分割制度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适用及其启示[J].时代法学,2016,(6):104.。受此启发,建议中国立法在吸收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同时,给予其灵活适用的司法空间。即中国立法应当允许本国法院在应当援引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特殊情形下,评估分割承认和救济外国破产程序的可能性,以寻求保护本国权益与迎合跨界破产合作需求的利益平衡。
最后,明确正当程序要求与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之间具有直接关联[注]从前文提及的司法实践来看,如果外国破产程序无法满足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接案国法院将很有可能以程序正当要求为基础,拒绝对该外国破产程序予以承认和救济。在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示范法草案》中,第7条“公共政策的例外”已将程序公正写入条款正文。。与公共政策的界定相似,正当程序要求也存在国内法层面和国际条约层面的区别规定[注]在国内法层面,对正当程序予以规定的典型是英美法系国家。英国1933年《外国判决(互惠执行)法令》对当事人是否得到有效送达和公正审理的机会等程序公正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1986年《第三次对外关系法重述》第482节规定,如果判决是在一个根据正当程序不能提供公平审理或程序保障的国家作出的,则美国法院可能不会承认该外国法院的判决。在国际条约层面,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先后通过的《民事诉讼程序公约》《外国民事或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以及《协议选择法院公约》都对正当程序要求进行了规定。乔雄兵.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正当程序考量[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98-100.。显然,在跨界破产立法中,应当采纳国际层面的正当程序审查标准[注]在“劳合社与阿申登案”中,阿申登主张美国法院不应对该英国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理由是涉案的英国程序并不符合美国伊利诺伊州承认与执行法案中的正当程序要求。审理本案的皮斯纳法官(Posner)认为,针对英国程序公正性的评价问题,不应以美国某一具体的正当程序条款为认定基础,而应当将之置于文明国家最基本的公正程序的角度予以审查和认定,而这种最基本的程序要求即国际意义上的正当程序要求,其必须与美国立法中具体的程序正当规定相区分。See in re Lloyd’s v Ashenden, 233 F.3d 473(7th Cir. 2000).。关于国际正当程序要求的界定,189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希尔顿案”时,首次做出了“在能够确保司法公正的法律体系中作出的判决具有止争效力”的表述[注]See Audrey Feldman, Rethinking Review of Foreign Court Jurisdiction in light of the Hague Judgments Negotiations, NYU Law Review,2014, pp.2241-2227.。随后,有学者将“希尔顿案”审理法官针对国际正当程序要求的表述进行了总结,即“国际正当程序要求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应当是有管辖权的法院,且该法院能够为当事方提供完整、公正的审判机会,不论是对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均应提供充分的告知及公正待遇,以保障不存在歧视或欺诈”[注]该学者还对违背国际正当程序要求的情形进行了形象的表述,认为希特勒时期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即不符合国际正当程序的要求。See S.I. Strong,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U.S. Courts: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Rev. Litig., 2014, p.108.。2016年新加坡高等法院在审理“韩进海运破产案”时,也充分论述了对外国破产程序予以程序审查的步骤及要求[注]在“韩进海运破产案”中,新加坡高等法院强调对外国破产程序的程序审查应主要关注债权人待遇和正当程序两个方面。在债权人待遇方面,其主要考察外国债权人在待承认的破产程序中能否获得公正、公平的待遇,任何偏向于本国债权人或特定债权组别的外国程序均有可能被拒绝承认;在正当程序方面,其主要关注重整计划的制定是否以适当交流、债权人实质性参与为基础,以及外国程序是否能够保障国内外债权人具有充足的时间及资料考虑重整计划。See in re Taisoo Suk (as foreign representative of Hanjin Shipping Co Ltd), [2016] SGHC 195.。考虑到程序要求与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跨界破产规则中的“控制阀”角色,建议中国立法借鉴《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示范法草案》第7条的规定,将国际正当程序要求直接纳入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正文当中,以强化正当程序对于国际跨界破产合作的保障作用。
在跨界破产规则中,相较于其他颇具争议的条款,国际社会对于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司法适用已达成普遍共识。因此,长期以来围绕该条款产生的争议相对较少。然而,随着跨界破产法制与实践的发展,针对公共政策例外条款与COMI条款、债权人保护条款以及额外救济条款的关系认定问题,国际社会提出了两种完全相悖的释义,即“替代机制说”和“配套机制说”。其中,“替代机制说”认为跨界破产规则中的上述相关条款为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扩张适用提供了路径,这一主张从根本上撼动了公共政策例外条款限制适用的基本原则,动摇了国际跨界破产合作的理念与精神。考虑到目前中国各界对本国跨界破产立法改革的呼声日益迫切以及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跨界破产规则中的关键作用,本文结合有关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跨界破产司法实践,在对上述问题予以回应的基础上,探讨《企业破产法》第5条第2款的改革方向,以期能够为中国跨界破产立法与实践提供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