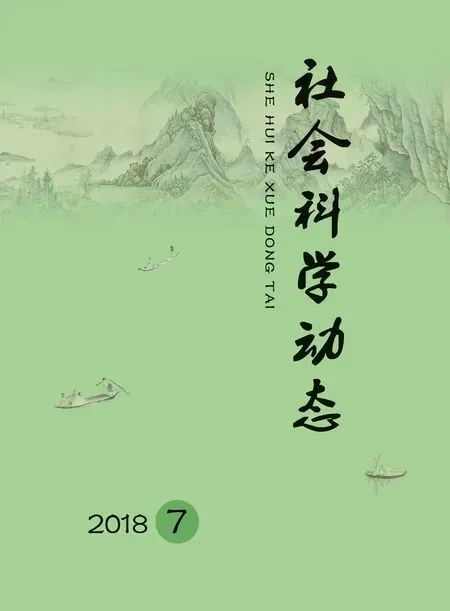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读《舒芜胡风关系史证》
2018-04-01彭林祥
彭林祥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所有对该事件的叙述都不可能绕过他。绿原在《胡风与我》中曾认真提出:“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①然而,现有的研究中,要么完全“不研究舒芜”在“胡风派”中的历史作用,要么一味地从“道德”上对其进行苛责,似乎离绿原的期许甚远。吴永平先生的《舒芜胡风关系史证》则有所不同,这是一部把着眼点放在舒芜与胡风关系的演变上,并把“胡风派”其他成员及同时代相关人物一并纳入视野,以重新审视“胡风事件”的力作。
该著以时间为序,从1943至1955年,分为上下两部。前有《引子》,后有《尾声》,正文64章。书前有朱正先生的《序》,书末除《后记》外,还有一篇《舒芜胡风关系简表》作为附录。全书共48万字,结构相当完整。
笔者认为,该著初步驱散了笼罩在“胡风事件”上的历史迷雾,基本实现了史、证、辨的有机结合,略述如下:
一、舒芜和胡风关系史的细致梳理
该著以舒芜和胡风的关系为主线,围绕舒芜与胡风的初识、亲密携手、产生裂痕、关系冷漠、逐渐疏远、舒芜自我检讨,以及“胡风问题”的形成、定性和上纲过程展开叙述,详略得当,首次完整梳理了两人从结识到对立长达13年的纷繁史实。
1943—1955年间,中国政治形势巨变频仍,抗日战争、国共和谈、解放战争、新旧政权的更迭;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兴无灭资等一系列运动,思想上从多元向一元的转变,文艺和文艺人被纳入体制化的进程,等等。这些历史波澜在知识分子身心上的投影,通过舒芜和胡风的关系演变,在该著中都有相应反映。
解放前,舒芜的职业是大学教师,与胡风结识后,在“文艺—文化”领域中崭露头角,成为“胡风派”核心成员。他们共同亲历了不少政治事件,如乔冠华等人发起的“广义启蒙运动”、中共南方局的内部整风运动、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等等;也共同接触了大量历史人物,如资深学人黄淬伯、顾颉刚、台静农等,本流派成员路翎、阿垅、何剑熏、绿原等,以及中共文化圈子成员陈家康、乔冠华、冯雪峰、聂绀弩、何其芳等。解放前后,“胡风问题”一度惊动中共高层,周恩来甚至毛泽东都曾过问,胡乔木、周扬、林默涵、郭沫若、茅盾都曾参与处理。这些事件及人物都被纳入了著者的视野,使得全书既有纵的历史梳理,又有横向的四、五十年代中国政治、文化、文学领域中各种复杂关系的揭示。
通过对舒芜和胡风交往史的描述,著者勾勒出了舒芜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逡巡的心路以及胡风从“文艺”而涉足“文化”的波谲云诡的历程。舒芜和胡风的结识,在他们各自的生命历程中都是一个重要的结点。有了胡风的邀约,舒芜得以走出纯学术研究的书斋而踏入“现实问题”的战场;有了舒芜的加盟,《希望》杂志得以超越《七月》而在“文化”领域独标一格。尽管舒芜始终怯于与政党政治分庭抗礼,但有胡风的勉力扶助,他尚能跌跌撞撞地同行。但随着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浪潮迫近且日益具象化,舒芜和胡风对“真的主观”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根本分歧。舒芜欲逃离文艺与政治的漩涡,回归纯粹的学术研究;而胡风却迷恋于文艺政治化的愿景,渴望成为最高意旨的权威解释者;道不同言不合,舒芜与胡风只得分道扬镳。不幸的是,舒芜终未能逃离欲逃离的政治是非,而胡风亦最终丧失了全面指导文艺的可能性。著者似乎对政治化的文艺环境及政治化的文化人啧有烦言,并从另一角度对知识分子的命运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独特的反思。
综上所述,该著对舒芜和胡风关系进行梳理时,并未孤立地对他们的关系史进行勾勒,而是把他们放置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并连缀起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述评,形成了该著鲜明的个性特色。
二、基于历史事实的辨正、辩驳和论证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平反,当事人、亲历者、研究者有大量的著述问世,由于各自立场不同,认识也有差别,加之时间过去多年,误记的情形甚多,以讹传讹的情况也不少,导致一些基本事实成为了“历史的迷雾”。概而言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诸多“史料”已经芜杂到了需要甄别考证和需要去伪存真的地步。著者在梳理关系史的过程中,基于基本的历史事实,对“历史的迷雾”进行了澄清。
著者对上述“史料”中的相关历史细节进行了辨正。如舒芜与胡风初次见面的时间,胡风在《胡风回忆录》中将初识的时间确定为1943年11月下旬,著者根据舒芜回忆与胡风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文协所在地张家花园)而推导出他们见面的时间大约可以确定为1943年4—5月间,并认为胡风起初对舒芜并不看重。此外,著者在引用《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晓风编)、《舒芜口述自传》 (舒芜)、《关于乔冠华》 (胡风)、《回忆与思考——关于“胡风事件”的补充》(黎之)、《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 (林默涵)等文章中的相关文字时,对其中的错讹之处都一一加以辨正。尤其应该提到的是,著者对胡风1954年撰写的“万言书”也重新进行了审视,并对其中的失实之处进行了匡正。
对某些研究者耸动一时的观点,著者也持审慎态度。如林贤治在《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 中认为毛泽东将胡风作为当时全力击刺和解剖的主要对象,主要是由于思想的对立。著者则认为“全力”说与毛泽东对胡风问题的关注情形不合,“对立”说也与胡风的文艺实践活动情况相违。著者指出,解放初的几年里胡风多次向毛泽东表示其对兴无灭资战略思想的理解和追随的愿望,其创作实践所显示的并不是背离主流的企图,而是趋奉、迎合的努力和渴望。此外,著者对李中《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论著中的一些观点也提出了异议。著者极其重视历史细节的真实性,往往通过具体史实的考证来辩驳对方的误解或偏见,而自己的观点也得以呈现。
著者对“胡风事件”中一些重要结点进行了考证。如《论主观》的历史公案,该论文的写作和发表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是引发抗战文坛上“主观论批判”运动的导火索,也是解放前夕胡风与“港方”笔战的焦点之一,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运动,甚至间接地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定性中起过作用。由于该论文事关“胡风问题”的要害,胡风和舒芜对其文的发表初衷各执一词。著者通过对南方局内部整风等历史事件的缜密考证后提出:舒芜《论主观》的写作,是为了声援在党内受到批评的陈家康等人,主旨是对政党的思想统一运动及思想控制手段提出质疑,胡风非常清楚该文的锋芒所向,并对该文及后续诸文的写作和修订给予了非常具体的指导和督促。因此,无论胡风后来提出的“为了批判说”、“双簧说”还是“失察说”,都是意图推卸责任以“彻底甩掉舒芜及《论主观》这个历史包袱”的巧辩。再如,著者对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的发表经过、发表时的政治形势、文章具体内容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中央对“胡风小集团”的注意并不起自舒芜这篇发表于当年5月底的文章,而是起自胡风当年5月初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封信,胡风在这两封信中向中央正式提出“讨论理论问题”、“安排工作”、“移家北京”等要求,中央随即指示中宣部拟定了处理胡风问题的方案。总之,著者在涉及舒芜和胡风关系演变的一些重要节点上,依据各种文字材料,致力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三、基于事实基础上对舒芜的辩诬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中,胡风及其成员是受难者,自然赢得了道义上的同情。舒芜因其在批判文章中引用胡风的信件,促成胡风集团从“反党集团”上升为“反革命集团”,似应负有重大责任。“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以后,许多人对舒芜在该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都比较反感,谴责舒芜为“卖友求荣”“出卖耶稣的犹大”,等等。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 《舒芜口述自传》中曾自我辩护,但随即遭到“集团”中人的非议和反击。学者林贤治甚至在《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中专门辟“舒芜与犹大”一节来探讨这一问题。可见,这样的说法至今在学术界、读书界仍不乏认同者。《舒芜胡风关系史证》梳理舒芜与胡风自1943至1955年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还原历史,为舒芜辩诬。
著者认为,指责舒芜“卖友求荣”者大多出自对舒芜与胡风的关系演变缺乏了解。早在1950年底胡风即已单方面与舒芜绝交,1952年更向中宣部检举舒芜为“破坏分子”(内奸),1954年又向中央举报其为“叛党分子”,他们之间不仅早就无复“友”情,谁“卖”谁也须另说。至于“求荣”云云,著者认为这个断言也失之草率。解放初舒芜在南宁颇受重用,不仅担任着重点高中的校长,还兼任着南宁市人民政府委员、南宁市中苏友好协会筹委会副主任、广西省教师联合会宣教部部长、广西省文联筹委会常委和研究部部长、南宁市文联筹委会副主任、广西省人大代表等多种职务。1953年舒芜调京后的职位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一名普通编辑。据此可见,“求荣”之说亦不能成立。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指责舒芜在文章中“摘录胡风信件”不仅违反了宪法,而且超越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针对此,著者分列三条理由进行辩驳:第一,如果知识分子真有这条道德底线,那么早在1952年便在致中央报告中摘录过舒芜信件的胡风也应受到谴责,独责舒芜,是道德的双重标准。第二,“五四”进步知识分子在辩难时从不忌惮引用他人的书信,尤其在非引用不能说明问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第三,胡风和舒芜都是“尊鲁迅的”,都倡言“爱爱仇仇”而反对“宽恕”,忽视他们的这个“共同点”而探求底蕴,无异于缘木求鱼。
不可否认,舒芜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形成过程中应该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一点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中已公开承认。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此案发生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以及最高层对政治形势的判断。著者认为,胡风问题于1954—1955年间受到中央的严重关注,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舒芜写于1952年的那两篇文章,而在于胡风1954年在“万言书”和“批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清君侧”的强烈诉求、指导文艺运动的炽热欲望及排斥一切的强烈的宗派主义情绪,正是这些不寻常的表现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因而,一味地指责舒芜,或夸大舒芜“交信”一事在铸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作用,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著者对舒芜和胡风的交往史有这样的总结:“舒芜与胡风关系演变的决定因素在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素养及文化追求,舒芜只希望在文化哲学方面有所独立建树,而胡风则有借助政治之力而施展文化抱负的远志。他们在处理政党政治的要求及宗派内外部矛盾的方式上也有所不同,建国初期舒芜力图通过公开的的途径消解矛盾、填补裂隙,却不被本流派成员所理解。他的批评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都是独立写成而且公开发表的,而胡风等对舒芜的批评和揭发都是私下商议且秘密呈报的……”著者力图在书中证明:舒芜既不是“犹大”,胡风也不是“耶稣”,他们都是时代祭坛上的牺牲品。
著者在其2006年出版的《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一书的《后记》中自述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曾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某些方法。文化人类学,即注重研究对象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与位置,注重研究对象与周遭环境的关系,并以一种“参与对象化”的方式贴近研究对象。著者在20世纪90年代曾两度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师从保尔·巴迪先生,深受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的影响。著者把这种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概括为“文本细读和文化社会学分析”。《舒芜和胡风关系史证》一书无疑继续运用了这个方法,其致力于具体展示相关人物关系的演变契机、过程及结果,以揭示“胡风派”之有别于其他现代文艺社团的特质。通过对“胡风派”内部运动状态及矛盾状态的细节描述,从另一个侧面揭示“胡风案”形成的主客观因素,进而把握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特点及建国初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某些特征。除此之外,著者对中国传统治学方法(朴学方法)也有借鉴和继承。我甚至认为,《舒芜胡风关系史证》一书无疑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学风而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取得成功实践的代表性著作。
学者萧功秦在《我和高华的交往》中对高华的历史研究著作曾有这样的评价:“高著所用资料几乎都是公开出版,作者能够从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资料中爬梳鉴别,点滴归拢,并发掘其新意。书中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严实的资料的基础上。高对史料的真伪也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据事言理,而非凭空想象,对自己所作的论断,他还采用不同的资料加以佐证。他整整十年的如此洗磨,我常常在想,未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可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或补充该著的论断,而难以推翻其整体观点。”②笔者认为,把这段话用来评价《舒芜胡风关系史证》也颇为恰当。
注释:
① 绿原:《胡风与我》,《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② 萧功秦:《我和高华的交往》,《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