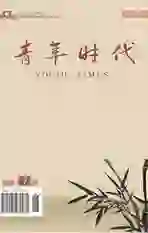中学生家庭环境、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情绪的关系研究
2018-03-31詹勣新
詹勣新
摘 要:目的:探讨中学生家庭环境、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情绪的关系。方法:采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修订版FES-CV、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以及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对92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本研究中的中学生抑郁情绪的检出率约为41.3%,总体平均分为17.80±10.16,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抑郁情绪水平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学习成绩上没有显著差异,不同抑郁情绪水平在核心自我评价上差异显著(F=21.060,p=.000<0.01),家庭矛盾性在核心自我评价上差异显著(F=6.095,p=.000<0.01),在家庭控制性上不同抑郁水平差异显著(F=3.896,p=.000<0.05)。家庭环境和核心自我评价无显著相关,核心自我评价和抑郁情绪呈负相关。结论:核心自我评价、家庭环境中的矛盾性和组织性对于抑郁情绪有预测作用。
关键词:中学生;抑郁情绪;家庭环境;核心自我评价;预测作用
一、研究背景
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抑郁情绪是一个需要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学阶段是人生极为重要的时期,但多方面因素又有可能引起中学生的抑郁情绪,如其心理不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健全,判断力较低、意志脆弱不稳定等。加之心理健康尚未大范围普及,人们对心理健康问题没有科学而正确的认识,容易对自身产生误判,强加一些子虚乌有的病症进行一些消极暗示。家长教师也对抑郁症等高中生高发心理问题知之甚少,认为不高兴就是抑郁症,或是“孩子只是心情不好,过段时间就没事了”,对高中生的成长添加了很多不利因素。研究表明,中学生的生理、心理都具有青春期特有的敏感性,并且正接受着来自家庭、学习、人际交往等各方面不同程度的压力或刺激。由于自身心理调适能力难以适应变化且缺乏正确疏导,中学生更容易发生情绪障碍等问题,而抑郁正是中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Auerbach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抑郁可能导致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认知功能损害等现象出现,青少年患上抑郁更可能引起人际交往困难、学习障碍等,影响人生发展。
导致中学生抑郁的因素很多,本研究主要关注家庭环境和自我评价。中学生的生活很单纯,一般来讲,学校和家庭是中学生待得最久的两个地方。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可见抑郁问题与这五个方面有着紧密联系,而对于自我的认知和评价始终贯穿于这五个层次。素质—压力理论认为,压力因素和素质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青少年抑郁的产生,其中压力因素来源之一就是家庭环境,研究结果也显示抑郁和家庭环境具有一定关系。刘宁等的研究显示,青少年如果缺乏有效的家庭支持易引起抑郁;尼格拉等研究显示家庭中父母控制的不同形式对青少年抑郁具有不同的影响。而素质因素之一为自我认知和人格特质因素,研究者提出以核心自我评价来研究人格特质,将核心自我评价定义为人们潜意识所持有的最基准的评价。任志洪等研究显示核心自我评价在竞争与抑郁关系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王静研究显示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负性情绪呈负相关,因此,本研究推测中学生抑郁可能与家庭环境和自我评价的共同作用有关。
纵观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虽然研究得出中学生家庭环境、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情绪存在着潜在联系,但目前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还有所欠缺。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对高中生进行相关调查,探讨家庭环境、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情绪三者之间的关系,希望有助于家长、教师等一切与高中生成长相关的人及青少年自身对抑郁情绪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以便及早地发现并解决抑郁问题。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某高中5个班,共150人发放调查问卷,回收问卷104份。个人信息不完整及有个别题未作答视为无效问卷予以剔除,共回收有效问卷92份。被试人口结构见表1。
(二)方法
1.研究工具
第一,家庭环境量表中文修订版FES-CV。该量表共有10个分量表,分别考察10种家庭特征:亲密度(Cohesion),评价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承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2)情感表达(Expressiveness),鼓励家庭成员公开活动,直接表达其情感的程度;(3)矛盾性(Conflict),家庭成員之间公开表露愤怒、攻击和矛盾的程度;(4)独立性(Independence),家庭成员的自尊、自信和自主程度;(5)成功性(Achievement Orientation),指将一般性生活(如上学和工作等)变为成就性或竞争性活动的程度;(6)知识性(Intellectual-Cultural Orientation),指对政治、社会、智力和文化活动的兴趣大小;(7)娱乐性(Active-Recreational Orientation),参与社交、娱乐活动的程度;(8)道德宗教观(Moral-Religious Emphasis),对伦理、宗教和价值的重视程度;(9)组织性(Organization),安排家庭活动和责任时有明确的组织和结构的程度;(10)控制性(Control),使用固定家规和程序来安排家庭生活的程度。本研究采用FES在国内的第三次修订版(FES-cv),经检验内部一致性克隆巴赫α系数为0.506,信度水平一般。
第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该量表主要用于测量抑郁情感或心境。全量表共有20题,涵盖抑郁症状的主要方面。项目反映了抑郁状态的6个方面:抑郁心情、罪恶感和无价值感、无助和无望感、精神运动性迟滞、食欲丧失、睡眠障碍。填表时,受试需要说明最近一周内症状出现的频度。答案包括:“偶尔或无(少于1天)”“有时(1-2天)”“经常或一半时间(3-4天)”“大部分时间或持续(5-7天)”,每个答案依次被赋值0,1,2,3。有4道反向计分题目。经校正后,总分越高代表出现抑郁的频度越高。判别标准为,总分<16分:不抑郁;16-19分:可能抑郁;>20分:确定有一定程度的抑郁。在本研究中,其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21,信度水平较好。
第三,核心自我评价量表。该量表是一个单维度的自评量表,由10个项目组成,采用五级计分法,从1到5分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总分的范围为10-50分,分数越高说明被测者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38,信度水平较好。
2.施测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发放调查问卷,由学生匿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填写问卷,当场作答并回收。
(三)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使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抑郁情绪及核心自我评价在不同性别、学习成绩差异方面采用t检验;抑郁情绪与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采用Person相关分析;抑郁情绪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回归采用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中学生抑郁的基本情况
(二)不同性别中学生的抑郁情绪、家庭环境和核心自我评价差异分析
对不同性别中学生的抑郁情绪、家庭环境和核心自我评价进行t检验,结果如下:
表3结果显示:高中生家庭环境中的情感表达成分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男生受家庭环境中情感表达的影响更大,性别对其余成分的影响都不显著。
(三)是非独生子女的中学生的抑郁情绪、家庭环境和核心自我评价差异分析
对是非独生子女的中学生的抑郁情绪、家庭环境和核心自我评价进行t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四)不同学习成绩的中学生的抑郁情绪、家庭环境和核心自我评价差异分析
对不同学习成绩的中学生抑郁情绪、家庭环境和核心自我评价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结果显示,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家庭环境、抑郁情绪在学习成绩上无显著性差异。
(五)不同抑郁情绪程度的中学生的家庭环境和核心自我评价的差异分析
对不同抑郁情绪程度的中学生家庭环境和核心自我评价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结果显示,不同程度抑郁组在家庭矛盾性、控制性及核心自我评价上差异显著,具体为有一定程度抑郁组在核心自我评价上显著低于无抑郁组和有可能抑郁组(F=21.060,p=.000<0.01),并且无抑郁组的核心自我评价最高;有一定程度抑郁组的家庭矛盾性显著高于无抑郁组和有可能抑郁组(F=6.095,p=.000<0.01),并且可能抑郁组的家庭矛盾性最低;在家庭控制性上,可能抑郁组的家庭控制性最高,并且三组差异显著(F=3.896,p=.000<0.05)。
(六)家庭环境、核心自我评价和抑郁的相关分析
对家庭环境、核心自我评价和抑郁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中学生家庭环境、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情绪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情感表达和矛盾性显示出与抑郁情绪的显著正相关。
(七)中学生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以抑郁情绪评分为因变量,以核心自我评价、家庭环境、性别、学习成绩及是否独生子女等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上述结果发现,核心自我评价、组织性、矛盾性作为显著变量依次进入了回归方程,可累积预测“抑郁情绪”为54.7%的变异量。同时,在运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时,诸多自变量中,核心自我评价首先被选入回归模型,由核心自我评价可解释抑郁情绪47.3%的变异量。核心自我评价高,家庭组织性好,则抑郁危险性降低;家庭矛盾越高则抑郁心理加重。
四、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的抑郁情绪检出率约为41.3%,低于李雷雷等在2010年调查的重庆市中学生抑郁检出率(58.4%),这可能与研究所选用的样本量和对象群不同有关,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为高一学生,相比于其他几个年级课业任务相对轻松,且也可能与所使用的量表评分标准不同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和抑郁情绪水平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及学习成绩上均无显著差异。在性别上不显著,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性别刻板印象逐渐弱化,社会、学校及家庭对男女的重视程度愈加一致,男女平等的主张越来越推广,中学生在性别上并没有体验到区别待遇带来的不适应感。而在是非独生子女上,抑郁情绪水平也无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独生子女拥有的亲密的同伴关系,让其和非独生子女一样,享受到了所需要的关心和陪伴,使其在核心自我评价和抑郁情绪水平上显示出无明显差异。在学习成绩上,抑郁情绪水平无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现在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所感受到压力和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所感受到的压力并不能被较好地区分,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可能更有压力。郑睿智等的研究发现学习压力对抑郁情绪影响尤为突出,因此研究者认为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进一步研究学习压力对于抑郁情绪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核心自我评价越高显示抑郁存在的可能性越低,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情感表达和矛盾性显示出与抑郁情绪的显著正相关,家庭矛盾越多,形成一种压力氛围,使中学生抑郁存在的可能性越高,但亲密度和情感表达越多抑郁存在的可能性越高,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不符。研究者认为,现代父母和孩子的相处模式更倾向于平等的朋友关系,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度越来越高,情感表达也越来越轻松,而在青春期孩子需要的个人独立自主的空间可能得不到满足,在心理上对父母的依赖较严重,一旦离开家庭,比如长期住在学校等,那么在应对危机事件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抑郁情绪。
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核心自我评价、家庭环境中组织性和矛盾性对于抑郁情绪有预测作用,并且核心自我评价的预测作用最为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首先要重视核心自我评价,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情緒呈负相关,且相关性高。家庭成员应适当引导高中生对自身形成客观及适度乐观的认识,培养高中生具有自我认知的能力,使高中生不因旁人的看法动摇自己、怀疑自己从而导致抑郁。高中生自身应当重视对自我的认知,通过平日对自己的观察、反思及他人的客观评价形成正确的认识自我的方法,不偏信旁人,将别人的话作为参考,不过分注重他人的眼光,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给予恰当肯定。其次,重视家庭环境对高中生抑郁情绪的影响,特别是家庭环境中的矛盾性和组织性。高中生和家庭成员都应形成正确观念,不怨天尤人。先天条件如性别、兄弟姐妹、家庭所在地等既无法重新选择,也对抑郁情绪的形成作用不大,不应着眼于这些先天条件,反而应该更重视提高家庭成员亲密性、情感表达、组织性等。可以组织家庭集体活动,开设家庭会议,固定时间共同分享最近的收获和经历,形成约定共建良好家风,关注高中生身心健康等。
五、結论
由以上研究数据可知:(1)高中生核心自我评价、抑郁情绪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学习成绩以及家庭所在地上都无显著性差异;(2)家庭环境中的亲密性、情感表达、组织性和抑郁成正相关,矛盾性和抑郁情绪成负相关;(3)核心自我评价和抑郁情绪呈负相关,并相关性高,核心自我评价越低,抑郁情绪程度越深;(4)家庭环境对抑郁情绪的回归作用并不理想,仅矛盾性和组织性有预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对抑郁情绪的回归作用理想。
希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能更加关注高中生的心理健康,防患于未然,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一代主力军建好身心健康的保障,同时对心理健康给予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李雷雷,汪洋,王宏,等.重庆市中学生抑郁状况及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10(10):1071-1073.
[2]刘虹.中学生完美主义、家庭环境与抑郁情绪的关系探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3]刘宁,陈锡宽,闻增玉,等.上海核心家庭亲子沟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05(2):167-169.
[4]尼格拉·阿合买提江,夏冰,闫昱文,等.父母控制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和间接效应[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3):494-497.
[5]潘露.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探析初中学生厌学心理以及教育策略[J].考试周刊,2014(59):162-162.
[6]任志洪,叶一舵.核心自我评价量表的中文修订[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57-163.
[7]任志洪,江光荣,叶一舵.班级环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与调节作用[J].心理科学,2011(5):1106-1112.
[8]王静.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班级环境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D].武汉:湖北大学,2011.
[9]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10]周学山.中学生班级环境、核心自我评价与心理和谐的关系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5.
[11]郑睿智,董永海,李杰,等.中学生抑郁与家庭环境及应对方式关系[J].中国公共卫生,2012(10):1280-1282.
[12]Abela,J.R.,Aydin,C.M.,Auerbach,R.P. Responses to depression in children: reconceptualizing the relation among response styles[J].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2007(6):913-927.
[13]Auerbach,R.P.,Eberhart,N.K., Abela,J.R.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in canadian and chinese adolescents[J].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2010(1):57-68.
[14]Hankin,B.L., Fraley,R.C., Abela,J.R.Z. Daily depression and cognitions about stress: evidence for a traitlike depressogenic cognitive style and the predict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 prospective daily diary study[J].J Pers Soc Psychol,2005(4):673-685.
[15]Judge,T.A., Erez,A.,Bono,J.E.The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J].Personnel Psychology,2003(2):303-331.
[16]Monroe,S.M.,Simons,A.D. Diathesis-stress theories in the context of life stress research: implication for the depressive disorder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1(3):406-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