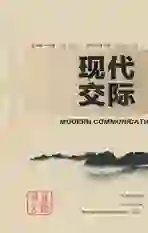当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度解析与艺术书写
2018-03-30刘晓燕
刘晓燕
摘要:当代韩国作家尹大宁的作品大多审视人的精神世界,以其长篇小说《美兰》为例,这部作品反思韩国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将“美兰”作为人性异化和人格分裂的象征符号,揭示当代人的自我认同障碍和生命存在危机;运用了聚焦人物灵魂的叙事艺术,设置内涵丰富的新奇意象,采取日常化的叙事立场,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作深度解析与生动呈现。
关键词:韩国文学 尹大宁 《美兰》 精神困境 叙事艺术
中图分类号:I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24-0106-03
韩国学者赵润济在《韩国文学史》中宣明“韩国民族之历史是悠久的”,指出韩国文学史“同民族史同样久远”[1],呼吁韩国文艺界人士“调和东西,兼摄新旧”,从而“对世界文学有所贡献,有所推动”。[2]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90年代的韩国文学更倾向于题材、风格和手法的多样和转换”,作家们力求“忠实地表现他们新的感受和内心的苦闷”,积极尝试“将心理分析和意识流手法与东方传统的寓言式隐喻相结合”。[3]在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其中包括“后起之秀”尹大宁。[4]本文选取尹大宁的长篇小说《美兰》进行个案分析,探究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
一、人格分裂与身份迷失
尹大宁擅长“创造性地展现受到创伤的人们的心灵,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5]其长篇小说《美兰》刻画当代人的心灵创伤和精神危机,深受中国读者之青睐,200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2009年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以《少女的肖像》为名出版,足见其魅力。
《美兰》讲述韩国青年成彦宇与两位同名女性(吴美兰和金美兰)的情感纠葛和婚恋经历。成彦宇入伍之前“是一个没有目标或希冀的无为青年”,到了退伍之际,又“陷入了极度的倦怠之中”,他“早已对人世与自我失去了兴趣”。[6]由于种种偶然性,精神空虚的成彦宇博得两位女士的好感,吴美兰为之献出初恋和初夜,金美兰与他携手组建家庭,但他始终无法确定真爱对象。
小说借男女性爱体验来审视两性之间的情欲纠缠。成彦宇与吴美兰云雨之后便劳燕分飞,不免感叹:“我二十四岁时,从一个二十一岁的女人那儿,学到了女人的一切。往后从别的女人那里学到的,只是残饭剩菜而已。”[7]他对吴美兰怀有“不尽的思念”,每次喝醉之后“眼前便浮现出吴美兰的身影”,让他“痛苦不堪”。[8]对于“为人伶俐而精干”的金美兰[9],成彦宇向她表白:“在新罗宾馆相见那天,我在修车场看到了你的背影。我看到你心中的空洞,孤独造就的空洞。它像黑洞霎时把我吸了进去,吸到你的孤独里去。”[10]与金美兰的肉体结合,让成彦宇觉得:“仅仅一次做爱,就让我们两个人的肉体和谐交融,从而我意识到我再也离不开她。”[11]成彦宇对吴美兰和金美兰都怀有欲罢不能的爱恋。
成彦宇对于吴美兰和金美兰的情爱混乱反映了他的人格分裂。吴美兰让他感受到生命本能释放的浪漫激情,金美兰使他体验到现实人生促成的安稳和谐,两者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冲突,正如他所说:“我是一个首先需要和谐秩序的人。如果我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我就会随时分崩离析,而美兰称此为背叛。”[12]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成彦宇无法将“本我”与“超我”整合为健康的“自我”人格。
成彦宇的自我形象是模糊不清的。《美兰》多次出现“镜子”意象,成彦宇一边注视镜子中的脸一边反思:“镜子里的人确实是我吗?那是一张我真不想认同的脸。”[13]成彦宇的朋友朴允载也指出“镜中的面孔”实际上“跟原貌并非一模一样”。[14]金美兰将离世的母亲当做自己的“一面镜子”。[15]作者本人也提出:“每天早晨,当我起床照镜子时,总感到困惑不已:我是谁?又在哪里?” [16]拉康强调:即使儿童心理已经成熟,他们“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样子并不是就有了自我意识”。[17]《美兰》中频频闪现的“镜中人”与“镜外人”构成陌生者的关系,表明当代人无法识别自我形象,自我的扭曲又折射出当代人身份的紊乱,因为“自我是身份结合形成的”[18],身份迷失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人格分裂。
成彦宇的自我与身份问题还暴露于职业态度上。他对法律事务兴趣不大,却最终选择了律师职业,但有时“连律师的身份也忘了”[19],甚至反省自己“钻了法律的空子”而“心怀不安地过着日子”。[20]这种心态反映了当代人的心理“焦虑”,即“社会人格分裂为各种对立的角色”,导致“自由”也“分裂为各种不连续的行为”。[21]《美兰》真实地记录了当代人自我意识紊乱的心理症候。
二、人性异化与生命衰颓
尹大宁的作品大多与人性反思和生命观照密切相关。有人认为“对生命不可抗力的省察是尹大宁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22],也有人指出尹大宁的某些小说“反省宿命和人间孤独”[23],还有人阐明尹大宁的作品“充满对缺乏社会关系的存在本质的探讨”[24]。《美兰》中的人物心理障碍,源自当代社会发展失衡所滋生的人性异化之弊端,人性被扭曲和压抑,生命便呈现衰颓之相。
《美兰》中的男性人物都有性格缺陷。青年成彦宇“一直像条蚕,过着作茧自缚的生活”[25],结婚之后的成彦宇“满足于自己拥有几个幸福的客观条件和单薄的既得利益”,陷入毫无生气的生活沼泽,“总有一阵虚度年华的战栗”[26]。未老先衰的朴允载“受着长期倦怠乏力的折磨”[27],摆脱不了平庸、市侩的习气。金学友实质上是一个偏执狭隘、自私自利的轻浮之徒。成彦宇的小叔长期保持独身状态,他“坚持认为第二次恋爱绝不可能纯洁无暇,第二次就意味着对自身的背叛”[28],但后来与金美兰的母亲秘密恋爱,“背叛”了理性。吴美兰的父亲患有忧郁症,被迫接受精神治疗,后来为了保护女儿而自当罪名,远走异国他乡,强烈的乡愁几乎摧垮了他的内心。《美兰》中的男性人物都具有消极厌世、空虚疲顿的形象特征。
《美兰》在批判男性人物病态人格的同时,也未赋予女性人物完美无瑕的精神品格。吴美兰十岁逝母,金美兰五岁丧父,她们自幼形成了抑郁反常的人格心理。吴美兰被继母虐待到近乎自闭的境地,杀死继母之后便堕入无尽的罪恶感和恐惧中,以自我折磨和放浪人生等方式不断挣扎,最终“没剩下任何情感”。[29]金美兰父亲早逝,母亲自我封闭,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极度孤独,缺乏安全感,又不善于关怀他人,常常“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习惯于“顽强地保护自己”。[30]金美兰的母親为了“跟虚无和情欲苦斗”,经常“赤身裸体一连几个小时坐在温室里”。[31]朴恩子“性格呈中性”[32],拙于情感表达。
《美兰》中的男性和女性都是被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压抑了自我人性的悲剧人物。成彦宇对金美兰倾诉自己的精神重负,谴责“世风日下、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社会”[33];小说有一章以“失去的家”为标题,有不少内容讽刺和批判当代韩国社会某些不正常的生活现象,展现部分韩国人见利忘义、纵情声色、勾心斗角的病态人格。叙事者对韩国儿童天性被学业所害的状况感到无奈,对酗酒市民“充血的眼睛”流露出悲哀之情。[34]《美兰》揭露的社会文化弊病并非韩国独有的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平衡式发展,社会对人性维度的关怀相对不足,人性被异化,人们的情感关系遭到破坏,精神需求亦被剥夺,个体生命走向衰颓。随着《美兰》故事情节的演进,人物的生命存在发生了变化:成彦宇形同槁木,吴美兰形神俱灭,金美兰心如死灰,成彦宇的小叔遁世隐居,金美兰的母亲悄然自尽……唯有回归现实、拒绝变异的医生朴允载变得温和、圆润,说明人性和谐对于生命健康的重要意义。
三、聚焦灵魂的叙事艺术
《美兰》揭示当代人的人性压抑与异化、人格分裂和身份迷失,需要突破外部空间的局限和现实关系的束缚,采用特殊的艺术手段。
《美兰》中多次出现“金虫”“包”“鹿”等具有丰厚心理内涵的意象。作者用“金虫”指涉男性,首见于小说“引子”,它“来自一个遥远的世界”或者“一个万劫不复的岁月”,飘忽不定且处于失重状态,“飞到阳台上”立即“摔在瓷砖地上”(《美兰·引子》)。成彦宇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倒放的金虫拼命挣扎”[35];金美兰渴望找到“生活里失去的东西”,想抓住“窗檐上”的“金虫”[36],当她对丈夫行为感到不满时,要把“飞进窗里”的“金虫”猛然“翻倒在桌面上,还折断它的腿”,警告丈夫:“金虫一旦翻倒,就很难自己翻过身来。”[37]《美兰》以虫喻人的艺术手法,很像卡夫卡的《变形记》。《美兰》的两位女主人公随身携带的“包”均给成彦宇留下深刻印象,吴美兰手中提着的“白包”对他颇具诱惑力,金美兰故意留下的“皮包”让他形成难以释怀的记忆,借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带有容纳性和接受性、有待外物填充的“包”与女性性别特征有关,暗示男性的性欲望和潜意识。“鹿”被寄寓独特的含义,成彦宇在与吴美兰发生一夜情的当晚,听到发情的鹿群不停地叫春;当成彦宇的小叔与金美兰的母亲第一次相遇时,成彦宇看见一头流血而死的鹿,男女相互吸引并以女方的自杀告终,“鹿”成为情欲的隐喻。
《美兰》使用超现实的描写手法。当吴美兰在成彦宇的陪同下来到她当年谋杀其继母的新罗宾馆时,眼前产生种种幻象,小说写道:“艇里有着我认识不过一周的女子,以及洗手间镜子里面目不清的我自己,还有红珊瑚与鱼类在我眼前乱晃。我不是在做梦吧?”继而又提到:“五月清新的晚风吹过池面,吹过曾漂浮一具穿白外套女尸的水面上。”[38]这些语句刻画了吴美兰的恐惧感和成彦宇的错乱感。和金美兰一起度蜜月的成彦宇在印尼旅游期间又见吴美兰,吴美兰说自己经常在雨夜看到形如成彦宇的幽灵,而成彦宇也看到了那个“雪人似的白色幽灵”[39],灵魂出窍的神秘现象折射出男女双方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美兰》还穿插了成彦宇的梦魇、朴允载的感应等内容,表现当代人焦灼不安的情感心理。
《美兰》采取日常化的叙事立场,利用偶然性的巧合事件诠释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以不可靠的叙事者表达当代人的空虚与迷茫。女主人公取名为“美兰”,本意源于中国古城“楼兰”,说明小人物身上也包含着历史神圣感。小说将重大政治事件与个人生活事件置于同一时间维度:成彦宇与金美兰结婚之年,韩国发生“最后审判和韩中建交”“金泳三当选十四届总统”等事件,国外发生“南斯拉夫内战”以及洛杉矶“黑人暴动”等事件,叙事者声称:“乍看来,上述事件与我们没一点干系。其实,却有着出乎意料的直接关系……世界的事情,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相互影响。”[40]小说叙述成彦宇听到吴美兰随父返回韩国时,介绍南北首脑举行峰会的盛大场面。在“后记”中,作者自述“本小说的灵感来自南北关系”。[41]在作者眼里,与政治运动和历史事件相比,个体的生命历程和日常生活并不逊色。男主人公成彦宇还充当了不可靠的叙事者,他在婚后与别的女性保持性关系,竟然轻描淡写地宣称“没什么需要特别记忆记叙的事情”,自称这种行为“只是一种酷:一个月见两次面,吃顿饭、做次爱,仅此而已”[42],这种言行是对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文明病”的反讽。
四、结语
文学是文化交流的渠道之一,以中韩文化交流为例,诚如郜元宝教授所言:“如果韩国当代文学也能和韩国饭菜一样进入中国读者和普通市民的视野,那么,中韩之间的交流就必将超越‘韩流而进入实质性层次,我们相互之间似乎不可消除的陌生感和神秘感,也就很容易因为心灵的相通而消于无形。”[43]郜元宝称赞尹大宁的小说“对当代青年人心理的准确把握,流畅而近于推理小说的叙述笔法”。[44]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尹大宁及其作品的研究。
本文对尹大宁的长篇小说《美兰》进行文本细读和理论分析,发现《美兰》颇能体现当代韩国作家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深度解析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当然,《美兰》也有可议之处,如:小说情感主题的正向价值指向不够明晰,对韩国社会环境的描写不够开阔,等等。孙正聿先生告诫我们:“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是人的生命的枯萎与否定”,在寻求精神家园的征程中,当代人应当“显示自己的尊严、力量和价值”,仍需发扬“英雄主义精神”。[45]任何一部作品都很难做到完美,相信尹大宁先生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艺术成就!
参考文献:
[1][2][韩]赵润济.韩国文学史[M].张琏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3]曹中屏等.当代韩国史:1945—2000[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4][43][44]郜元宝.小批判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文钟哲,严英爱.尹大宁及其短篇小说《光的脚步》的写作[J].世界文学评论,2010(1).
[6][7][8][9][10][11][12][13][14][15][16][19][20][25][26][27][28][29] [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韩)尹大宁,美兰[M].朴明爱,具本奇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7]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18]趙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1][法]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M].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22]金寿铁.现代人际关系的实验室——谈韩国作家尹大宁短篇小说的魅力[J]. 博览群书,2014(12).
[23]安南日.2000年以后韩国小说的影像[A].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朝鲜—韩国文学与东亚[C].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492.
[24]金英今.朝鲜—韩国文学史(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45]孙正聿.人生哲学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