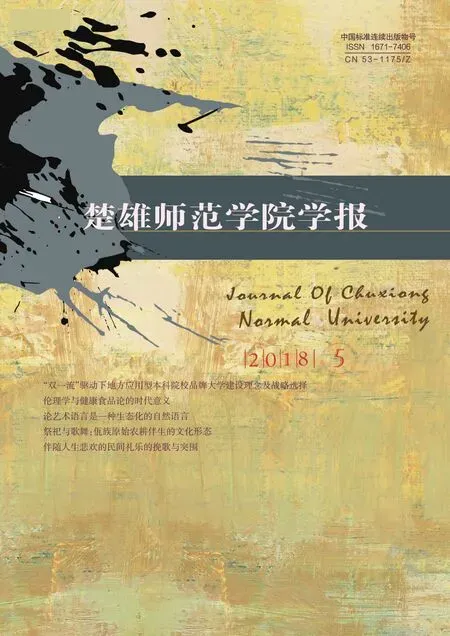简论彝族民间信仰中的龙崇拜*
2018-03-30殷鹰
殷 鹰
(巴黎国际商业拓展学院,法国 巴黎 92600)
“龙”的概念,广泛存在于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中,龙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文化认同的核心符号,对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作用。一首《龙的传人》在华人世界中传唱不衰,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精神里对龙文化的认同。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龙也是其文化中重要的文化认同符号。
彝族对龙的崇拜源远流长,彝族的族源与上古崇龙部落有密切关系。对彝族来源问题,前人已有诸多探讨,学界众说纷纭。彝族的民族形成,在《彝族简史》中认为:“彝族在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自称和他称,直至解放前夕……有三十来种不同的自称和他称。但在这三十来种的自称和他称中,以‘诺苏泼’‘纳苏泼’‘聂苏泼’作为自称的彝族,即占彝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1](P2)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人们抛开部分侮辱性的称呼,自愿统称为“彝”。今天“彝族”的称谓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民族称谓。因此,彝族是一个支系繁多、构成复杂的民族。《彝族简史》中认为更能被广泛接受的彝族起源观点是:“彝族是以从‘旄牛徼外’南下的古羌人这个人们共同体为基础,南下到金沙江南北两岸以后,融合了当地众多土著部落、部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1](P10)易谋远先生在《彝族史要》中则认为“彝族是众多古代民族共同融合而成的”[2](P155),“彝族先民与分布于中国四川的旄牛徼外以黄帝为始祖的蜀山氏后裔早期蜀人、以古东夷颛顼族为祖先的昆夷以及炎帝为始祖的楚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2](P1)根据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文中的考证结果,古羌族和黄帝部落皆为龙族,以龙为图腾。因而彝族从族源上来说就具有崇龙的文化基因,在彝族民间信仰中,龙是十分重要的神灵,龙具有多重神格,既是图腾祖先,又是创世之神,还是带来祥瑞的神灵和司水之神。在彝族地区,流传着许多有关龙的神话故事,至今保存着隆重的祭龙仪式,龙成为彝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符号,也是彝族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文化桥梁。
一、作为图腾祖先的龙
在彝族的图腾文化中,龙是普遍崇拜的图腾祖先。图腾(Totem)这一词汇原本的含义是“它的亲属”或“标记”,人们通常将所信仰的图腾当作自己的祖先以求获得庇佑,涂尔干认为始祖的名字就是一种图腾,同一部落的原始图腾元素会被之后分散开来的部族继承持有。彝族族源复杂,故而图腾较多,有竹、葫芦、虎、蛇、龙、鹰等,但龙图腾仍然是较为普遍的一种。
彝族支系“诺苏坡”是主要生活于四川和云南大小凉山一带的彝族支系,人口众多,在这一支系中广泛流传的神话英雄史诗《支格阿龙》(彝文中“龙”的发音为“Lu”,故又有版本名为《支格阿鲁》)中描述道,彝族先祖支格阿龙是其母有感于被掉落的三滴龙鹰血所生,是龙鹰的后代。阿龙是龙把他养大,能够听得懂龙语,也能说龙话,自称“我也是条龙”。支格阿龙诞生故事属于父系始祖来源的感生神话,故事中将“龙鹰”看作是祖先,因此可推论彼时该部族图腾应为“龙鹰”,或者说“龙”和“鹰”,至今龙和鹰的神话意象依然活态地存在于彝族民众的信仰生活中。彝族族源与崇龙的黄帝后裔和崇凤(鸟)的炎裔楚人都有密切联系,可猜测“龙鹰”形象彼时可能为该两个氏族后代移民融合而产生的混合式图腾。《支格阿龙》中描述支格阿龙被龙抚养长大的情形:
“饿时吃龙饭,渴时喝龙乳,冷时穿龙衣。支格阿龙啊,生也龙日生,年岁也属龙,行运也是到龙方,名也叫阿龙。”[3](P283)
与支格阿龙的神话母题相同的故事在西南彝族地区流传甚广,版本众多,如在云南楚雄元谋小凉山的彝族中,支格阿龙的故事被翻译为《阿鲁举热》(“阿鲁”为龙,“举”为“鹰”,“热”为“儿子”),而在贵州地区的彝族中这则神话被称作《支嘎阿鲁》。支格阿龙故事在彝族聚居地区的广泛存在,证明了龙图腾在西南地区的彝族民众中是被普遍认同的。
在彝族的龙图腾神话中,比较著名的神话还有《九隆神话》,该神话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南中志》《蛮书》等史籍中均有记载。下面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内容来进行简要分析。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男子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而‘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九隆死,世世相继。”[4](P27)
学界认为哀牢夷为彝族先民之一,活动范围大致为今保山至大理一带。上面这则神话也是一则明显的龙图腾感生神话。沙壹有感于沉木而怀孕,而沉木实则是龙,因而生出的九隆是被龙认定的龙子,龙则是父系始祖。哀牢夷将自己认为是龙的后代,除了神话叙事中的神龙感生外,史载哀牢夷也有在身上纹龙和在衣物上加尾饰的习俗,明确体现了其“以龙为祖”和“龙生夷”的龙图腾崇拜特征。
二、作为创世神的龙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民族间的交流逐渐增多,彝族和汉族的接触日见频繁,西南地区的各民族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形态。彝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长期处于混居状态,文化相互影响,尤其是汉族文化对彝族文化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彝汉文化交流过程中,在涵化(culture-contact)作用下,彝族文化中龙崇拜的边界日渐扩大,龙的属性逐渐泛化。龙作为一个虚拟文化符号,比之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牛、狗等动物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人们对龙的敬畏恐惧感因其虚拟性而被无限放大,龙在彝族的信仰观念中不再是一个单纯获得笼统保佑的图腾祖先意象,人们对龙有了更多更具体的诉求和期待,龙在彝族的民间信仰和相关神话叙事中,被赋予了多重复杂的神性,拥有了多变的形态和多重的意义。龙从单纯原始的图腾祖先崇拜中衍生出了神灵崇拜的内容,龙转换为彝族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灵。
在彝族的创世史诗中,龙成为重要的创世神。楚雄地区的彝族中影响较大的创世史诗《查姆》描述了龙神参与创世的情节。龙神罗阿玛受命于天神,费尽心力找到万物之源的种子,并在天上种下了梭罗树,之后,梭罗树长大了,开出花,上面就结出了日月星辰,散出了风霜雨雾,长出了动物草木,形成了世界最初的样子。而初创的世界不甚清明,天神又派龙神罗阿玛降下大雨清洗山川丘陵,水龙罗塔纪挑来海水清洗日月辰星,从此世界才得以昼夜清晰,四季分明。[5](P10―13)在这一整个复合创世系统中,世界不是由单一创世神创造成型,而是由多位神灵参与,创世的过程也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修改打磨,其中,龙不仅扮演了驱动世界形成的角色,还扮演了世界的维护者和改造者这一角色,在创世过程中不可或缺。
流传于红河地区的《诺谷造人神》则有着神龙诺谷创世造人的故事。“在远古时代,绸拍吾喉羔,有座龙王府,龙王罗塔纪,他是海中祖,生个独儿子,取名叫诺谷。”[6](P26)这位龙子诺谷出生第四天便已长大成熟要离开龙宫游玩。诺谷不断在大海中遨游,直到入水口的源头,跃出水面一看,世界却像一个鸡蛋一样,天地之间除了两个进水口,两个落水洞外只剩一片混沌,没有日月,未见行人。于是诺谷挥起铁扫帚打破混沌,并用其扫出了山川河谷,然后又拿起竹筛,筛出了日月星辰和江河湖泊。此后诺谷继续扫出花草树木,筛出飞禽走兽。一切完成后,地面依旧没有人烟,诺谷决定用泥造人,捏出了独眼人,这便是传说中的第一代彝族人。这则神话中神龙创世的过程描述得更为详细,龙子诺谷作为创世神包办了除开天辟地外的几乎所有创世环节,而且还用泥捏出了人类祖先,既是创世神,又是造人神,这也是该地区彝族一直保持着祭龙习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流传于该地区同一故事的异文版本则描述“很早的时候,有一条老龙,住在汪洋里,龙名叫俄谷,这是造天龙,这是造地龙。老龙生小龙,小龙叫诺谷。”[3](P28)诺谷则是造日月,造星辰的神龙。造出日月星辰后,诺谷又接着造出江河山川,飞禽走兽。而后造出男人女人,指定其二者结为夫妻繁衍后人,并为夫妻俩造出五谷和家畜,从此人们过上有谷栽有畜养的生活,而大地上有了万物活动的生机。不仅如此,这对龙父子还赐予所有彝族人民福禄,让男女老少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人们有感于龙父子的恩情,所以每年到二月二都要举行盛大的祭龙仪式来还恩,并继续向龙父子祈求来年的顺遂。这则神话的叙述中,老龙开天辟地,龙子造物造人,龙作为核心贯穿了创世造人的全过程,完成了整个创世神话的综合性释源。而此二则神话细节虽然不同,但都讲述了神龙诺谷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情节,可见神龙创世造人应是该地区彝族民众的共识,龙是彝族民间信仰中及其重要的创世神。
三、作为祥瑞之神的龙
由诺谷造人故事中龙为彝族人送来福禄可以看出,龙被彝族人看作是驱邪佑吉的祥瑞神灵。杨正权先生在《西南龙文化》一书中记述道:“滇南石屏等地彝族有祭龙习俗,并且认为龙能驱除百怪。……只要阿龙出现,任何精灵鬼怪都不敢作祟。”[4](P108)而楚雄永仁地区的彝族流传着的《开年歌》中唱道:“开年是龙头,龙头开年来,带着你的腰,带着你的尾,带着你的四肢。家里的龙头开,开的财神门,开的吉利门,开的兴旺门。”[6](P107―108)同样是把龙看作是吉祥的象征,是保佑家族兴旺的祥瑞之神。
四、作为司水之神的龙
彝族与崇拜龙的黄帝部落有渊源关系,黄帝在神话叙事中具有主雷雨的神性。彝族民间信仰中龙也是司水的“水神”。在彝族的神话叙事中,水不仅是生命之源,也是万物之源,对水的崇拜即为对生命的崇拜。彝族属于山地民族,大多数生活在山区或半山区之间,生产方式以耕种为主,兼有部分的畜牧和狩猎,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用于支撑生产生活的资源,而在山地的地理环境中获取水资源并不容易,所以人们对水非常渴求。在彝族先民的原始思维中,很容易将降水过程前后出现的雷和虹等自然现象与图腾中形态相似的龙(蛇)发生联想,再加上雷雨前蛇通常会离洞活动,人们会在此时见到多于平时所见数量的蛇,所以认为是龙神降临导致降雨,从而将龙当作司水之神。
彝族神话中,龙神作为水神出现的场合不少。如弥勒县的彝族中流传的洪水神话描述了洪水来源是由龙的争斗造成的:天地间原本有十二条天龙和十二条地龙,天龙执意要下雨,地龙不服要干旱,二龙相争斗,斗第一回合地龙胜,因而三年大旱,斗第二回合天龙胜,九年下大雨,从此洪水滔天。可见龙在彝族神话体系里是作为水神掌管晴雨干旱的存在。而《查姆》中洪水神话部分关于洪水降下过程的描述“四道水门都关上,龙头摇一下,雷声隆隆响,龙身抖一抖,雨点如鸡蛋,龙尾摆一摆,风雨一齐来”[2](P59),也可佐证龙神能够招引雷电、呼风唤雨,带有“水神”的属性。
五、对龙的祭祀仪式
彝族文化中的“龙”,从图腾崇拜到神灵崇拜,其文化内涵不断增加,从图腾祖先、创世之神到祥瑞之神、司水之神等,龙与彝族人民的生老病死都有了密切的关联,也就产生了相关的祭祀仪式。
祭龙是彝族一年中非常重要的祭祀之一,大部分彝族地区都有祭龙仪式或是祭龙节,楚雄山区的彝族祭龙时间为正月初二,而红河地区则以二月二为祭龙的时节,基本都在春耕前夕。祭祀龙旨在乞求神通广大的龙神保佑这一年中雨水丰沛、粮食获得好收成。如楚雄州大姚县境内流传的《祭龙经》节选《鲁捏底》中说:“今天来祭龙,祭品已齐全。人们需要水,树木需要水,花草需要水。望你行好事,降下雨和水。龙水快快出呀!蛇水快快喷呀!”[6](P78―79)这段经文表达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在农业生产的季节到来时,乞求龙神能够降下充足的雨水,以满足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分,在此处人们更看重的是龙能司雨水的水神属性。
对龙的祭祀仪式在形式上大致是相同的,尤其是春耕前以祈雨为主的祭龙仪式,在云南省滇中南片区的彝族里基本以“祭龙树”为主。流程一般分为三步:请龙——祭龙——接龙。人们认为龙神住在天上,所以要通过请龙仪式将龙神请下凡间,下凡后龙神的“灵”附着在指定的龙树上,由此开始在龙树下摆祭品来祭祀龙神,毕摩在祭祀过程中通过念祭辞与龙神沟通,祭祀完成后就可将龙神迎到村中,以保佑今年生产的风调雨顺。
“龙树”通常会由毕摩在村子左边的山上选一棵特定的树,在该树未死亡的情况下一般不能随意更换。彝族民众认为龙神平日住在天上的龙宫中,但它的灵可以短暂地寄居在树上,祭龙时要先把龙请到龙树这棵指定的媒介上再进行祭祀。龙树生长的树林被称为“龙林”,龙林大多位于村子的左边山上,因为彝族风俗里同样有“左青龙右白虎”的观念。
有学者提出彝族“祭龙树”的习俗实则为“树崇拜”的结果,祭龙的本质是祭树,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彝族祭拜龙树,虽然形式上是在祭拜树,而树崇拜也确实是彝族民间信仰中的重要内容,但在该仪式中其实质仍是祭拜龙,即“龙树”是龙的化身,而非一个被祈求的对象。从祭龙词可以看出,彝族祭龙的主要诉求是祈求雨水,而树或树神并不具备降雨这一功能,也就是说树和这一祭祀行为的出发点是无关的,降雨实质上是龙的工作。树是祭龙仪式所希望获得的成果的受益者,而不是拥有被期望的超能力的被崇拜者,也不是完成祭祀需求的执行者,树在祭龙仪式中仅仅是龙的“载体”。因为“龙”本身是一个虚拟形象,未曾出现在生物界中,在祭拜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具象的载体或者说偶像来承担接受传达信息的功能,让祭拜者观念中的神灵具象化。
选择“树”这一形象可能与雷电有关,先人常认为雷电现象是神龙降世的缘故,而看到闪电劈到树干这一现象自然认为是龙灵附身。当然也可能与彝族神话中龙王创世时种下梭罗神树有关,但树只是彝族祭龙仪式上“龙神”寄寓其中的一个最常见的载体(部分地区也有祭龙潭、祭龙山或祭龙柱等形式),而不是这一祭祀活动的本质。所以“树”在祭祀龙的仪式中不是对树的崇拜,祭祀龙树其根本是祭祀寄寓其中的龙灵,祭祀龙以祭祀树的形态表现出来,仍然是彝族“龙崇拜”的一种体现。
六、多变的龙形象
由于龙的虚拟性,“龙”更多的是以一个抽象的意象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被人们赋予各种超能力和神性,所以当龙性投射到现实世界时,就会有不同的形象被称为龙,也就是何星亮先生所提出的“龙泛化”的结果。
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中的龙形象多种多样,没有形成像汉族那样被文献记载且得到大家普遍认同的龙形象:“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7](P356)。民族文献记载中很少出现对龙形象具体的描写,而是更多着墨于龙的神性功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龙形态,十分多元化,一直保留着各自的特色。如苗裔后代的苗族、侗族、瑶族等视为图腾的“龙犬”,便是犬身龙头,但身上具备远超犬类的超能力;如彝族“龙马”的传说,龙马其形为马,能日驰千里而到必要时刻又可化龙腾飞。这是人们将“龙性”投射到了狗、马身上的结果,或者说是龙“名”与物“形”的有机结合,并非狗、马本身就是龙。
所谓“龙性”的投射,被视作龙的物体首先应保持其自身基础特点,即被投射物自身原属的生物特征,而同时该被投射物又具备“龙”的某种超能力。有学者使用楚雄地区正月初二祭龙仪式上接龙这一环节所唱的《祭龙词》中对龙的描述,认为彝族文化中存在一些包含龙性投射的多种动物龙形象,诸如鼠龙、羊龙、兔龙、牛龙等。但此说法依然值得商榷,该篇《祭龙词》以甲乙双方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对唱:
“甲:一年十二月,每月有两节,每月有一龙。正月有两节,不知什么节?正月有条龙,不知什么龙?
乙:正月这个月,立春雨水节。正月这一龙,嘴巴十分大,胡子长又长,它为兽中王,它是老虎龙。
……
In following years, many of the original colonists celebrated the autumn harvest with a feast of thanks.
甲:一年十二月,腊月有两节,不知什么节?腊月有一龙,不知什么龙?
乙:腊月有两节,小寒大寒节。腊月这一龙,人们饲养它,喂草它也吃,喂粮更喜欢,请问这条龙,是不是真龙?
……
甲:腊月这一龙,它是条牛龙。人们种庄稼,不能少了它,这是条好龙,把它请回来。”[6](P79―85)
全篇总共唱了十二个月的十二条龙,分别是一月的老虎龙,二月的小兔龙,三月的真龙,四月的蛇龙,五月的马龙,六月的山羊龙,七月的猿猴龙,八月的鸡龙,九月的狗龙,十月的猪龙,十一月的鼠龙和十二月的牛龙,与此同时,每个月的唱词除了对本月这条龙的描述,也同时对应了两个历法中本月的节气。
在该篇歌谣中,有对部分月份的某条龙进行具体特征的描述,如正月的老虎龙长着大嘴并留着长须,二月的兔龙住在松树林里有着红色的嘴,三月是真龙身子长冠子大,四月的蛇龙同样身子长但是没有手脚,五月的马龙身量高而且尾巴长,十月的猪龙全身上下都是宝,十一月的鼠龙会偷吃粮食而且不是条好龙,腊月的牛龙既吃草也吃粮并且是条好龙等等。但歌谣中间部分对六月的羊龙,七月的猿猴龙,八月的鸡龙和九月的狗龙缺乏任何描述性的语言,仅直接点出了本月是条什么龙。而带有具体描述的月份和龙,描述的只是本月这一动物本身的特征,并没有显示出其与龙性有关的超能力。因此,这篇《祭龙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龙”这一形象的多变,在彝族的观念里龙不拘泥于一个固定形象,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名”,而他的“形”则是可以在其龙性的基础上变化万千,但并不能作为龙性投射的佐证。
此篇《祭龙词》对十二个月龙的唱法,是该地区彝族祭祀歌谣的习惯性唱法。唱词中十二个月不同动物的龙相对应的是彝族历法中的十二兽,而以十二兽为序编写祭祀歌谣是该地区彝族祭祀歌谣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方式。如与这篇《祭龙词》流传于同一地区(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南华县)的另一则巫师(当地称为香通)在祭祀仪式上唱的《跳十二属神》很相似:
二月属兔学兔跑,小兔前脚短又短,上坡容易下坡难,双耳摆动就开跑。
三月属龙要学龙,学龙就是会行雨,金龙治水行下雨,某氏门宗庄稼好。
……
腊月属牛要做牛,耕田犁地不离牛,驾起牛来要犁地,哇哦哇哦来回犁。”[6](P103―105)
这首《跳十二属神》属于日常祭祀仪式上的表演性曲目,而《祭龙词》则属于祭龙仪式上歌手的演唱曲目(有时由毕摩演唱),二者同属表演性曲目,使用了同样的叙事结构和表达方式,即月份加属相特征的结构。《祭龙词》作为以祈雨为主的祭龙仪式上的表演性唱词,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同时唱到了纪日十二兽和二十四节气,其内容应与历法更为相关。彝族历法惯用十二兽(或十二属神)来纪日和纪年[8],楚雄地区彝族十二属神按顺序排列即为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跳十二属神》正是以这样一个顺序排列,而《祭龙词》以同样的顺序安排每月龙的属性和形象,这可以理解为何《祭龙词》中唱到三月才是真龙,因为从十二兽记日的顺序来看三月的属相为龙。所以笔者认为这相当于是按照每月的属神为龙安排了一个属相特征,而非将龙比作该动物。
在彝族民间信仰中,龙的形象因龙的虚拟性和龙性的复杂性而呈现多样化的特点,“龙泛化”和“龙名化”成为常态,对于彝族文化中龙形象的多元特征还有待于更多的文化考古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来进行佐证。
综上所述,彝族不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龙的民族,龙崇拜更是在彝族民间信仰中生根发芽,开出了独特而绚烂的花朵。龙在彝族文化中的文化意蕴丰富多彩,形象多变,既是普遍认同的图腾祖先,也是部分彝族支系认可的创世神和祥瑞之神,更是彝族神灵崇拜中最主要的司水之神。彝族对龙的崇拜使祭龙仪式至今仍然广泛存在于彝族的民俗文化中,龙一直“活在”彝族人民的信仰生活里,是彝族民族文化中广泛认同的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是彝族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文化桥梁。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建设中文化认同的标志性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