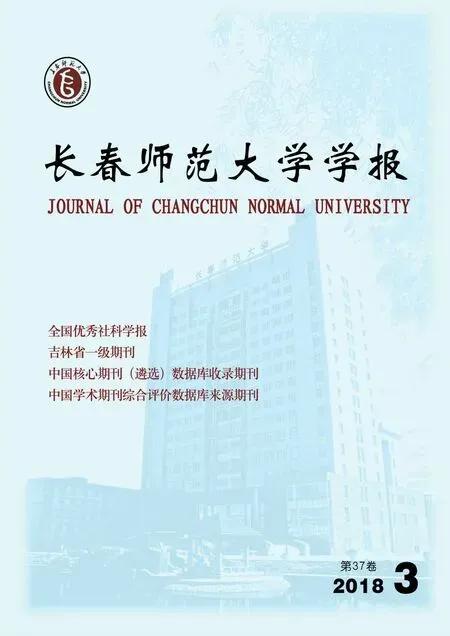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影响下大学生国家意识的培育
2018-03-30钱逍
钱 逍
(徐州工程学院 党委宣传部,江苏 徐州 221018)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本质并非真正地去除意识形态,而是要去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是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争夺的理论工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断渗透,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传播与泛化的主要受众无疑是青年一代,而青年大学生作为思想最为活跃的社会群体,在“不自觉”中很容易成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追随者。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所倡导的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的政治倾向和价值立场,影响着大学生对国家意识的思考与判断。所谓国家意识,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热爱、期待、维护、坚守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它体现着一个国家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发展的源泉,是复杂形势下维系国家信念、国家情感、国家意志与国家行为的根本。面对形势与挑战,我们不仅要认清其实质,更要深入分析其对大学生国家意识建构的作用机理,消除其对青年学生国家意识培育的影响,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教育对大学生国家意识培育的引领。
一、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本质
非意识形态化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来已久,并以政治思潮的面貌在20世纪上演了两次影响高潮。它的提出迅速迎合了反马克思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社会思潮的胃口,它们相互融合、互相支撑,演化为一股在西方社会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并逐步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传播之迅速、范围之广泛,源于其内在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诉求。我们必须深刻透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本质,才能对大学生的国家意识培育进行正确引导。
首先,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对除西方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僭越。贝尔认为,“整个世界已经走向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融合、互为补充,产生了同质化的趋向。”[1]在他看来,西方国家在解决其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时,往往不将意识形态作为主要因素考察,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失去了感召力,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划分失去了意义。“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2]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未来社会唯一的统治形式。可以看出,无论是意识形态终结论还是历史终结论,抑或文明冲突论,都将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不同的其他一切国家制度排除于整个世界体系之外,是为论证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永恒性服务的,充分印证了其冷战思维的政治倾向。
其次,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黑格尔认为,“意识发展所经历的一系列形态就是意识自身不断向科学发展的历史,而世界精神经历从东方到西方的漫游后,最终停留于日耳曼,意识形态的进化也就走到了终点,德意志就成了世界精神与意识形态的最终体现者。”[3]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奉行者们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将历史唯心主义提出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否认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非科学历史观作为其哲学依据,断定意识形态已经被民主制度、科学技术或者文明冲突等形式替代,其目的就是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推广至一切国家和地区,实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去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而消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
再次,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西方学者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淡化论、文明冲突论,甚至是“普世价值论”等,形式虽然多样,但其本质与西方国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是一致的。所谓的“非意识形态化”,却恰恰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是具体的、历史的,它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也不会因为科技的发展变化而失去其存在价值。一切淡化、否定意识形态的观点皆是谬论妄言,企图以西方国家主导世界是西方国家意识霸权的表现。
二、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大学生国家意识培育的影响机理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大学生国家意识培育的影响机理很特殊:一方面,它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打着去除意识形态的旗号传播西方国家意识,迷惑性非常强。因此,其作用机理是多方面的,既对我国国家意识认同构成消解,又对大学生国家意识的培育构成阻碍,而其去除意识形态的迷惑性极易导致青年学生对我国国家意识培育的抵制。
首先,非意识形态化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论,将政治制度和国家意识终止于资本主义,构成了对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我国国家意识认同的消解。众所周知,国家认同决定着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决定国家的稳定与繁荣。而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一直宣扬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20世纪,俄国、亚洲、阿拉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精英们引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它们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以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垮台,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获得持续发展,现在已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人们同时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唯一最新的世俗上帝失败了。”[4]这种宣扬的结果是破坏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国家认同呈现出消解与重构的态势,导致青年学生国家意识的弱化。
其次,通过宣扬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将意识形态驱逐出社会生活,并将科学技术、文化心理、生活方式等作为未来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加以论证,降低人们对国家意识的关注,阻碍大学生国家意识的培育。他们认为,“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5]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制度也许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任何其他的政治制度都不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冲突将终结。在此基础上,鼓吹未来世界将以文明的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冲突。宣扬意识形态淡化论、终结论,其目的都是妄图将西方国家制度和意识推行到一切可以推行之处,阻碍社会主义国家意识的培育。
再次,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鼓吹者们在宣扬意识形态终结的同时还极力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合法性。这种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不断美化的高扬特别能迎合思想尚未成熟的大学生的特点,从而使大学生失去对我国国家意识培育的兴趣。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鼓吹者极力宣扬资本主义的成功,而极力放大社会主义的问题。大学生是思想最为活跃的社会群体,同时又是思想观念极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的群体。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与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网络社会的结合,很容易使青年学生陷入一种所谓的世界主义的思维模式中,从而走向国家意识的反面。国家意识的弱化将会导致青年学生政治敏锐性和正确性的弱化,进而在无意识中对国家意识培育产生抗拒。
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影响下大学生国家意识培育的必要性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国家政治、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等多方面为我国国家意识构建带来了诸多影响与挑战,这种影响本身恰恰说明了大学生国家意识培育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冷漠的危机。在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那里,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科技的比较、文明的冲突或是心理的因素,总而言之,国家、政治已不再重要。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大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谈政治“显得太空”,不如谈经济“来得实在”。这种不良风气也弥漫至高校校园,使部分大学生忽视了人格品性的锻炼与塑造。二是信仰缺失的危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似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多元世界的大门,在这个时空中,“全球化”“地球村”“网络社会”“消费心理”等充斥其中,将信仰这一人的精神力量肢解,各种信仰缺失的论调如藤蔓般缠绕着学生的思想,影响大学生身心发展。三是价值共识的危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解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目标,淡化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精神力量的重要作用,使传统国家意识受到巨大冲击,以达到颠覆价值共识、实现西方社会主导世界的目的。
四、大学生国家意识培育路径
当前,国内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国家意识教育的内容主要为爱国主义教育,缺乏对国家意识的整体性、系统性教育。当代大学生面临着一元主导、多元思潮相互影响的局面,由此产生了复杂的观念意识,亟需进行培育和引导。面对包括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培育大学生的国家意识需要把握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进行学理批判,揭示其实质。恩格斯说:“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新的内容。”[6]这个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原则,指导我们对待问题要具有批判的眼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限。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宣扬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是完全违背历史和现实事实的。即便在当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家民族性这一范畴仍无法消解,且在与全球化浪潮的较量中愈发坚定。当代社会是由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等错综复杂的因素组成的,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终结只能是一场镜中月水中花式的空想。那些主张非意识形态化的人本身也无法脱离意识形态而生存,其实质不过是为了打着终结意识形态的旗号推行西方国家的意识和制度而已。
第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教育对大学生国家意识培育的引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通过对国家形态的历史性叙述,彻底暴露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虚假性。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历史进程决定了国家形态变迁的历史必然性。”[7]而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正如前文所强调的,其实是暗藏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霸权主义的。分析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影响下大学生国家意识培育的必要性可以得知,对大学生进行国家意识培育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教育。高校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国家意识培育中的主体性作用,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向大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念,培养青年学生正确的国家意识,使之具备完整的国家意识结构,让国家意识成为大学生价值判断的标准和自身行动的指南。
第三,创新大学生国家意识培育的形式。青年学生一般不会从学理上对包含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进行探讨与批判,也不会从政治制度的架构上得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孰优孰劣的结论,而往往根据自身接受和获取各种社会信息的途径和感受进行判断。因此,创新大学生国家意识培育的形式便成为引领学生思路、实现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探索启发式、互动式、体验式教育,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新颖形式,既教化又感化,使学生知情意、相融通、相吻合,真正领会国家意识的结构与内涵,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坚守国家意志的过程中实现崇高的人生理想。一方面,要善于运用现代媒体,尤其是各类新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可以说,当下谁赢得了新媒体,谁就赢得了青年。将国家意识培育与大学生关心、关注的现实问题和自身利益相结合,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大学生对国家观念的肯定与认可。另一方面,将社会实践活动纳入国家意识培育环节。通过社团活动、志愿服务、参观访问等方式,或采取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等社会机构联合探索的方式,让大学生在生动的实践中锻炼与学习,使其国家意识在实践与思考中得到升华。
[1]刘海龙.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影响及其应对[J].理论导刊,2014(3).
[2]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M].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梁建新.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想——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评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5]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胡承槐.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当代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J].哲学研究,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