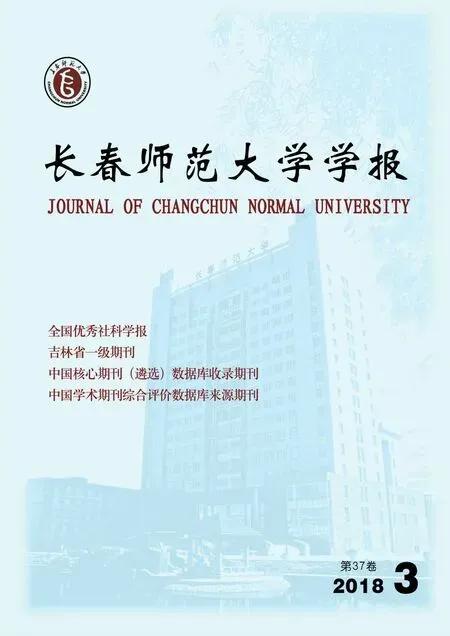论《于湖词》中“吴楚”的情感内蕴
2018-03-30张硕
张 硕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芜湖 241000)
《于湖词》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张孝祥所作,现存唐圭璋所编《全宋词》共收其词作228首,聂世美校点的《于湖词》共收其词作223首,宛敏灏笺校、祖保泉审订的《张孝祥词笺校》收其词作五卷139首,拾遗一卷36首,辑补一卷49首,总计224首。这些词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词学、美学等方面展现出较高的造诣。张孝祥的经历与际遇、流连与兜转以及其士大夫的豪迈、进取、无奈、喟叹等都融入到词体之中,使得《于湖词》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与文化意义。
张孝祥出生于宋高宗绍兴年间,在年少时期就经历金兵屡次南下侵扰,江淮之间多起战乱的状况,因此迁居于湖即今之芜湖。这是吴楚衔接之地,具有浓烈的江南吴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张孝祥仕宦之地如江州、建康、荆州等均在吴楚之间,其因就任、离任而游历的兴安、潭州、黄州、池州以及洞庭、湘江、金山等处多是吴楚文化特别是楚文化浓郁之地。词人所处南宋的时代之感、出世入世的思愁忧怀以及个人生平的交友恋情都在遇到“吴楚”之时一触而发,并与其千百年来所蕴含的情感内蕴高度融合。
以《张孝祥词笺校》为准,《于湖词》中明确将“吴楚”一并提出的有9首,分别是【水调歌头】中的“吴山楚泽”、【念奴娇】中的“楚头吴尾”、【水调歌头】中的“楚云吴钩”、【浣溪沙】中的“楚竹吴船”、【念奴娇】中的“平楚吴中”、【鹧鸪天】中的“楚雨吴霜”、【满江红】中的“吴波楚山”、【转调二郎神】中的“楚馆吴溪”和【浣溪沙】中的“楚缆吴粧”。此外,提到“吴”的还有9首,提到“楚”的有22首。这些词作充分展现出词人丰富多样的情感。
一、“吴楚”与乡思客愁
据宛敏灏先生考证,于湖当时的地理位置是楚与吴之间,而张孝祥已将“楚尾吴头”的于湖视为自己的家乡,当其在远仕时便常常在词作中以“吴楚”为家寄托自己的乡思。如其作【念奴娇】:“朔风吹雨,送凄凉天气,垂垂欲雪。万里南荒云雾满,弱水、蓬莱相接。冻合龙冈,寒侵铜柱,碧海冰澌结。凭高独啸,问君何处炎热。家住楚尾吴头,归期犹未,对此惊时节。忆得年时貂帽煖,铁马千群观猎。狐兔成车,笙歌震地,归踏层城月。持杯且醉,不须北望凄切。”[1]16此时词人正任职静江,面对风雨下的南荒景象,其难以抑制的思乡之情便与家之所在的“楚尾吴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楚尾吴头”的于湖是张孝祥的家乡,但“吴”与“楚”在词人的作品中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于湖以及离于湖较近的建康、临安等吴地各处对词人而言更多的是家的代表。相对来说,楚地以其历来远宦不遇的文化底蕴寄托了词人的客愁。
古荆楚大地既包括今湖北地区,也包括今湖南等地区。宋朝当时的治地辖区划分主要将其分为荆湖南路(治所为潭州,今长沙)和荆湖北路(治所为江陵府,今荆州)。“楚”有潇水湘江,有洞庭岳阳,是被贬远地、辗转不遇臣子的伤心地。这一历经多年的文化底蕴与每一个来此的词人都会产生巨大共鸣,韩元吉即在《张安国诗集序》中提出:“楚之地富于东南,其山川之清淑,草木之英秀,文人才士,遇而有感,足以发其情致”,“浮湘江,上漓水,历衡山而望九疑;泛洞庭,泊荆楚,其灌愉感慨,莫不什于诗”[2]。正如张孝祥著名的【念奴娇·过洞庭】一词,处处紧扣楚景,深刻地表达出其常年在外漂泊的复杂客愁。又如【鹧鸪天】:“人物风流册府仙,谁教落魄到穷边?独班未引甘泉伏,三峡先寻上水船。斟楚酒,扣湘弦,竹枝歌里意凄然。明时合下清猿泪,闲日频题采凤笺。”[1]99这是张孝祥在荆州送别陈倅之作,“人物风流册府仙,谁教落魄到穷边”正是词人的心声,楚地的酒、楚地的竹枝歌等与词人凄然的客愁融于一体。
二、“吴楚”与忠愤吊怀
吴楚大地自古就孕育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其间历史古迹、人物传说等数不胜数。同样,吴、楚又都是战火四起、英雄频出之地,国家的兴衰、人物的成败造就了此处的文化底蕴。张孝祥亦生在战争时代,其以身救国之志与“小儒不得参戎事”的忠愤与“吴楚”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如其作【水调歌头】:“濯足夜滩急,稀发北风凉。吴山楚泽行尽,只欠到潇湘。买得扁舟归去,此事天公付我,六月下沧浪。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 制荷衣,纫兰佩,把琼芳。湘妃起舞一笑,抚瑟奏清商。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莫遣儿辈觉,此乐未渠央。”[1]8湘楚是屈子之乡,其“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3]的忠臣精神给楚地注入了经久不灭的文化底蕴,这使同样怀抱一腔报国热情却难以尽展的张孝祥嗟叹不已,忠愤之情借以抒发。又如其作【水调歌头】:“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胜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犹在,功业故优游。赤岸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1]9词人此作正逢金主完颜亮大举侵送,直捣长江北岸,而宋将虞允文大败金主完颜亮于采石之时,其“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4]与“中流击楫”的忠愤豪情与吴楚这古今战场相得益彰。
吴楚之地多忠臣志士,其忠义之情与张孝祥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不得志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使其忠愤之感得以寄托。因此,《于湖词》中也多次借“吴楚”抒发了词人的吊怀。如其作【水调歌头】:“淮楚襟带地,云梦泽南州。沧江翠壁佳处,突兀起红楼。凭仗史君胸次,为问仙翁何在,长啸俯清秋。试遣吹箫看,骑鹤恐来游。 欲乘风,凌万顷,泛扁舟。山高月小,霜露既降,凛凛不能留。一吊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横槊,兴废两悠悠。此意无尽藏,分付水东流。”[1]5这是张孝祥自桂林罢归路过黄州时所作,“无尽藏”之名本于苏轼之文,其谪居黄州时写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作,对“赤壁之战”进行了多番凭吊。张孝祥罢归来此,自然也要借楚地发生的这段兴废之事抒发自己的情绪。
三、“吴楚”与友情爱情
张孝祥多居住和辗转于吴楚之间,其相交的友人多在吴楚之地,类似的经历、相同的志趣、共同的追求使《于湖词》中“吴楚”承载了词人与同道之人的友情。如其作【浣溪沙】:“射策金门记昔年。又教藩翰入陶甄,不妨衣钵再三传。 粉泪但能添楚竹,罗巾谁解系吴船,捧杯犹愿小留连。”[1]87这是词人饯别刘珙之作。刘珙字共父,曾在建康、潭州、荆南等地任职,与张孝祥之任职时有继替,且其多有政绩,与张孝祥在抗金政见上高度一致,是张孝祥为官期间相交的非常重要的友人。除此之外,张孝祥在外为官之时与其相交唱和的还有张栻、朱熹、朱元顺、王倅等人,他们之间也多借楚天楚地抒发惜别之情。
“吴楚”因与词人及其交往友人的仕宦和游历的紧密关系,成为其真挚的友情寄托,而“吴楚”乃多情之地,其水乡梦泽所体现出的阴柔忧伤的文化氛围与词人的爱情交相辉映。
关于张孝祥的爱情经历,宛敏灏有较为详尽的考证。主要涉及到两位女子:一位是词人十五、六岁时交往的李氏。张孝祥的父亲拒绝了秦侩一党中曹泳的结亲提议而入狱,因此张孝祥无法将与其有夫妻之实而无夫妻之名的李氏之事公开,最终只得将李氏送回原籍居住。这是词人一生中特别痛苦无奈的事,这种愧疚心疼和无奈自责的情绪也一直存在其词作之中。另一位是送归李氏后娶的正室时氏。二人因词人常年为官漂泊在吴楚之地而聚少离多,因此张孝祥内心的思念愧疚也多寄情于此。如前文提到的【浣溪沙】下阙:“粉泪但能添楚竹,罗巾谁解系吴船,捧杯犹愿小留连。”词人以写爱情来表现惜别之情。楚地盛产竹子,楚竹又常被称为斑竹、湘妃竹。张华《博物志》记载:“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5],可见楚竹承载着忧伤的爱情。“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6],来来往往的东吴行船,其间也不可避免地承载着情人离别的伤感。又如其作【转调二郎神】:“闷来无那,暗数尽残更不寐。念楚馆香车,吴溪兰棹,多少愁云恨水。阵阵回风吹雪霰,更旅雁一声沙际。想静拥孤衾,频挑寒灺,数行珠泪。凝睇。傍人笑我,终朝如醉。便锦织回鸾,素传双鲤,难写衷肠密意。绿鬓点霜,玉肌消雪,两地十分憔悴。争忍见、旧时娟娟素月,照人千里。”[1]115这是张孝祥乾道三年冬在长沙怀念李氏所作,词人的愁与恨和记忆中的欢与乐相反而相成,深情与无奈均寄于吴楚之间。
“吴楚”的山水、舟馆、楼台、花月、传说、故事和吴楚间发生的事、吴楚中友人们的经历等都对张孝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一生多辗转于吴楚,其作词时自然而然地将自身乡思客愁、忠愤吊怀和友情爱情都寄托于“吴楚”之上,从而形成了《于湖词》的一个重要特点。
[1]张孝祥.张孝祥词笺校[M].合肥:黄山书社,1993.
[2]宛新彬.张孝祥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
[3]汤漳平.楚辞[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198.
[4]李贺.李贺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0.
[5]张华.博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4:93.
[6]杜甫.杜甫诗选注[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