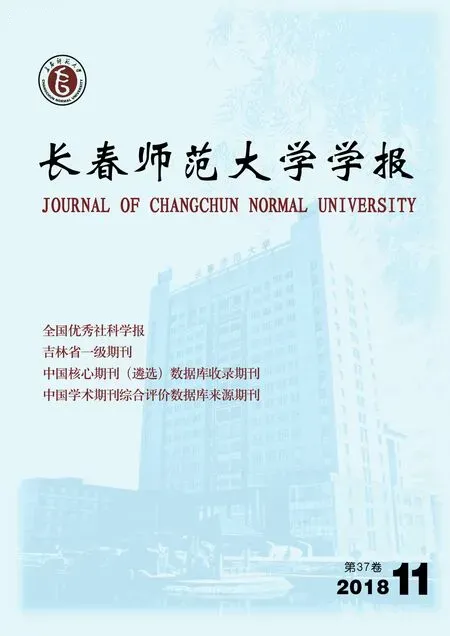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的话语转向
2018-03-29李宗双
李宗双
(通化师范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0)
五四文学革命中,文言向白话的话语转向,蕴含着服务于社会、时代的历史背景。欲了解这种变化与转向,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在于厘清文言与白话的源流及关系。五四时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其蕴含的内容是多面的:传统与现代的论争,古体与今体的变革,时代与历史的发展,文言与白话的转向。其中文言向白话的话语转向,是语言自身话语方式的变革。文学话语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会呈现出一定的不同步性。这种不同步性既体现在文言向白话的过渡当中,又外化为启蒙者与反对派的论争。反对派有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派,也有以梅光迪、胡先骕、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更有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其中反对派与学衡派的论争最值一提。学衡派的代表人物都曾留学欧美,学贯中西,在论争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对白话文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一、文言与白话的渊源及其关系
谈及20世纪的中国文学,首先要对文白之间的渊源及关系进行梳理。1915年胡适在美留学时,便已主张使用白话文。随后,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大幕。文言与白话的论争是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应资产阶级的变法运动而生的。虽然我们不能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简单地理解为“活白话”与“死文言”这两种文学话语方式的交锋,但在五四文学革命背景下,这种交锋代表着时代的变革、权利的转向。其中文白的交互关系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文言文在中国文学中有根深蒂固的物质基础,存在一定的相对性。一方面,文言文对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有重要的传播作用;另一方面,文言文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提供了现实可能。举一简单例子,在白话文运动中无论是梁启超、陈独秀还是胡适,皆具有深厚的文言功底,因而他们能站在比较高的起点上审视文言本身的不足与缺陷。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文言与白话的交锋,不仅体现了文学话语自身的变化,更是一种可以折射时代变化的价值转向。正是文言自身的变革与优化,才能为白话文的发展创造先决条件。“死文言”虽陈腐,却是“活白话”发展的重要基础。白话文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得以登上历史舞台。这既是一种时代的巧合,更有其内在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二者是一种互相补充、推陈出新的关系。
其二,文言与白话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与创新。与文言相比,白话文与时代的变革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一是白话文继承了文言中的妙用之法,循理而举事。二是白话文打破了八股文的固定模式,更具创造性。只有明确二者的渊源,才能于用中见体,获得新的变革与发展。当然,这既需要通畅豁达的继承,又需要简洁明了的创造。这既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滥觞于世的原因,更是二者关系的微妙之处。
其三,文学话语的转向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因而在“死文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活白话”更具社会化价值。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文言与白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当然这种转化是建立在二者渐趋融合而白话已然成为话语主流基础之上的。对于20世纪初文言与白话的内在转化,我们不能仅将其理解为文言与白话的相互杂糅。它既是一种生不离死、于死中见活的话语转向,更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内在变革。所以,对“活白话”与“死文言”内在关系的考量,既表现为文言与白话发展的内在张力,又内化为文白变革的根本动力。
二、“活白话”取代“死文言”的原因
白话文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主流话语,与晚清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体运动有必然联系。我们不妨抛开时代和政治因素不谈,单从文学革新与语言发展的角度分析为什么白话文能取代文言文。
在五四文学革命前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文学革命家就在晚清白话文报刊上开始了这种实践。据史料记载,晚清以来直到1918年,各地创办的白话报刊多达170余种,较有影响的有《演义白话报》《平湖白话报》《无锡白话报》《通俗报》《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等,其中以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最具代表性。梁启超等人最先提出“新文体”写作,他的《少年中国说》虽然被人认为是“近代文言散文”,但这种新文体在当时已经起到启蒙大众的作用。无论是晚清文人的倡导还是白话期刊的创办,对白话文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使白话取代文言成为必然趋势。
五四文学革命中期,陈独秀、胡适等人又将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与固步自封的文言文相互对照,彰显出白话文内在的发展活力。当然这并非对传统文言的全盘否定,白话文发展本身也没有尽弃文言文的优势。白话文是启蒙思想、教化民众的工具,追求的是语言的革新与文学观念的转变。从文学革新角度看,传统的文言文缺乏创新精神,而白话文除却宣传作用外更有利于展现复杂的社会生活与丰富的人文情感。白话文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实际,抒情叙事自然贴切,相较于文言文受到的束缚更小。
从中国语言发展角度来看,文言文日趋僵化、保守,个别字句纷繁复杂,不易理解,传承下去存在一定困难。虽然晚清文言文逐渐过渡到新文体,但也难以跟上语言发展的实际步伐。语言本身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每时每刻都需要填充与创新,因而适应这一需要的白话文应运而生。它既可启迪民智,又可传承语言,具有很好的情感表达作用。可以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三、对“死文言”与“活白话”的现实考量
文言与白话固然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骨子里也有一种相生相克的弊端。文言与白话的矛盾关系在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随着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深入,文言与白话已然形成对立趋势,即文言的发展已无力回天,而白话的发展蒸蒸日上,这是文言与白话在发展形势方面的对立。同时,它们在叙事方面存在对立。文言在变革前拥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压抑了人们的现代性需求。
白话想要发展,就必须摆脱“死文言”的束缚。在五四文学中,“死”不再是人生最大的恐惧。鲁迅先生主张藐视苟活的古训,认为苟活是人们恐惧并极力淡化死的一种自我意识。五四时期,作家开始在新的层面上对白话文进行肯定。当然,这种肯定是双面的:一方面,文言的“死”代表了一种历史的终结,是任何人也无法超越或否定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对白话而言,是一种“循理而举世,因资而立权”的引导。文言的“死”,迫使白话文尽可能地以有限的发展空间创造无限的文学价值。“死文言”本身是与白话文相对存在的,任何外来的推力都取决于其内在的现实需求,更来自时代发展的客观趋势。“死而后生”是这代人身上所具有的共同品质,也是时代赋予他们的重要使命。
四、结语
文言的积淀与整合使白话文有了新的发展空间。二者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辩证联系促进了中国近代白话文学话语方式的形成。二者既融合又创造,在五四文学浪潮中进化演变,成为文学革命中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