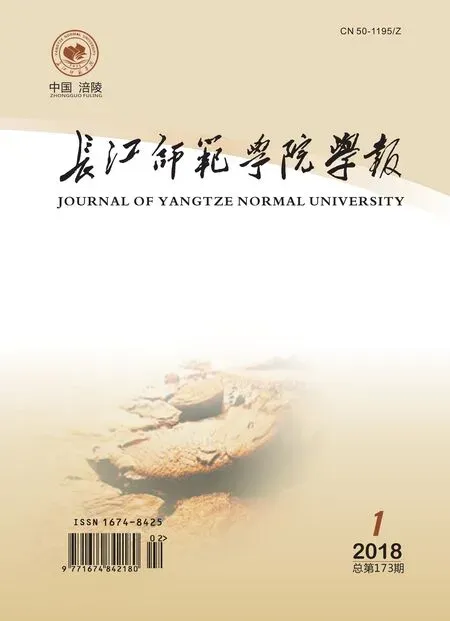浅谈宋代金陵怀古诗中的“异端之说”
——以《瀛奎律髓》金陵或六朝的怀古诗为例
2018-03-28秦霁月
秦霁月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总共选了刘禹锡、周贺、李商隐、梅尧臣、许浑、罗隐、杨亿、钱惟演、刘筠、李宗谔、王安石、刘攽、王珪、刘克庄等14个人的23首与金陵或六朝有关的诗,其中周贺的《送康绍归建邺》侧重写景送别而非感叹历史兴亡(纪昀:“此非怀古,误入此门”[1]83),故只选另外13人22首诗。这其中只有刘禹锡、李商隐、罗隐和许浑4人为唐朝人,无论是诗人的数量还是诗歌的数量,都远远少于宋朝,且主题较单一,多为借古讽今、以史为鉴,这大概是因为金陵对于唐人来说只是一个承载繁华危机、兴衰成败的历史符号。而对于宋朝文人,金陵所承载的意义则更为复杂,吞并南朝的历史经验使得宋人对金陵产生了其他朝代文人所没有的丰富感受,南唐成为宋人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从而产生了一些对历史兴亡的不同看法,故而宋人的金陵怀古诗不仅数量上多于唐人,而且主题也更加多样化,亦有一些不同于前代的声音,甚至方回所谓“异端之说”。
一、分类及唐宋比较
方回在怀古类的序言中言道:“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可以为法而不之法,可以为戒而不之戒,则有益悲夫后之人也。齐彭殇之修短,忘尧桀之是非,则异端之说也。有仁心者,必为世道计,故不能自默于斯焉。”纪昀亦言“此序见解颇高”[1]78。这里指出了怀古诗中的“异端之说”,即指不论时间长短(“齐彭殇”)、功过是非(“忘尧桀”)单纯以有一种变化无常的自然规律来评价历史,将人为因素排除在外,不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与之相对的则是以“兴亡贤愚”为戒的历史责任感,此当为怀古诗的主流。如果宽泛一点来说,在怀古类诗中,不强调“贤愚”,不出于“为世道计”的作品,大致都可归为“异端之说”。
按理金陵乃是六朝古都,频繁迅速的朝代更替和江南的纸醉金迷都应引起诗人“可以为戒”的兴亡感慨,出于“为世道计”的抱负借古讽今当为主流。然而,事实上,这22首作品中,此类主题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则为方回所说的不论是非、不以为戒的“异端之说”,且尤其在宋朝为甚。
首先将这22首作品大致分类,从内容上,明确提及金陵或南唐的有:刘禹锡、许浑、王珪、刘攽、梅尧臣的《金陵》,王安石的《金陵怀古》《和微之重感南唐事》《次韵微之高斋有感》,刘克庄的《雨花台》等,16首;侧重感慨六朝兴衰之事的有:李商隐的《陈后主宫》,罗隐的《台城》,杨亿、钱惟演、刘筠、李宗谔的《南朝四首》等,6首。从主题上分类,则侧重以六朝荒淫兴衰为戒,借古讽今的有:刘禹锡的《金陵怀古》,李商隐的《陈后主宫》和杨亿、钱惟演、刘筠、李宗谔的《南朝四首》等6首;表达“齐彭殇、忘尧桀”的“异端之说”或以胜利者的心态发豪言壮语或伤感故国不复、繁华不在等的有:许浑、王珪、刘攽的《金陵怀古》,罗隐的《台城》,梅尧臣的《金陵》,王安石的《和微之重感南唐事》《次韵微之高斋有感》,刘克庄的《雨花台》等,16首。感慨六朝之事的内容与以六朝荒淫兴衰为戒,借古讽今的主题有较多重合,且均在数量上较少;而以金陵景物或南唐为内容的则与异端之说等其他主题有较多重合,且数量上较多。而且,前者多为唐人所作,后者多为宋人所作。
二、以史为鉴之作
唐朝两首以六朝荒淫兴衰为戒的诗都是中晚唐的作品,“唐代士人功名心特重,安史之乱后,虽有所变化,渐至晚唐而渐见纤弱,但积极入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2]169,故而作者都以进取的心态,抱有以史为鉴可以对当时的政治产生积极影响的希望。刘禹锡的《金陵怀古》将六朝之亡的原因归结于“《后庭花》一曲”,明确指出“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既有统治者莫要依仗地形而荒淫无度的告诫之意,又含兴亡的原因在人,可由人的行为来左右的进取精神和历史责任感。李商隐的《陈后主宫》少了几分事在人为之意,而是罗列意象、典故来极力描绘陈国荒淫无度的生活,何义门将其比作宋徽宗的《艮岳记》[1]85,足见其所状之繁华,以此暗示陈国灭亡之由,表达借古讽今的劝诫之意,“借陈事刺当时耳”[1]85。
这一主题中还有宋朝初期以杨亿为首等所作的《南朝四首》,这几首诗不但借古讽今的主题与李商隐相同,就连表现这一主题的方法也都是极力描写南朝繁华奢靡的生活画面,运用典故,场景众多,所感慨的也主要是六朝兴衰而未涉及五代之事,可以说是直接承接唐朝而无宋朝的特点。故而这4首诗与宋朝其他这类作品内容主旨大不相同,虽表达的是主流的思想,但在宋朝的金陵(六朝)怀古中却是异数,这或许与模仿李商隐有一定的关系,使得这些亲历北宋灭亡南唐之人所言均未超出前人,就连钱惟演这个南朝降臣所作之诗都没有独到的思想体悟。
三、“异端之说”及其他思想感情
唐时许浑和罗隐所写已不再是“为世道计”、以史为鉴的主题。许浑和罗隐所处的时代已是藩镇割据,罗隐甚至曾依附吴越钱氏,战乱割据自然使诗人产生了不同的感触,情调也由事在人为的积极进取转为相对悲观。许浑的《金陵怀古》前两联描写了当年繁华的金陵的衰败景象,颈联则以“石燕”将“晴”变“雨”,“江豚”引起“风浪”喻英雄人物左右时代的发展,然而诗的重点却不在英雄人物的豪情,而是“英雄一去豪华尽”的末世悲凉感。而罗隐的《台城》重点则在于朝代不断兴替不过历史规律,为此相争不过徒劳争夺无用之物,为此伤感亦是不必。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思想深度,实则不然,这种情感其实是看多了“深谷作陵山作海”的沧桑变换而生的漠然,与之前的唐诗的劝诫和事在人为比起来更多悲观情调,虽说“莫伤情”实则是一种无奈或是故作超然。《台城》的这种情感基调,应该说开启了宋代金陵怀古的“异端之说”。
南宋刘克庄的《雨花台》与《台城》的思想最为接近,前3联写景却不涉及与南朝王宫、历史有关的景物,而是写雨花台、寺院等乡间山中之景,但表达的亦是物是人非之意,末句“登临不用深怀古,君看钟山几个争”也是表达这种物是人非、朝代更迭不过是世间常景,不必为此投入太多感情。方回评价此句为“终俗”而纪昀更谓“通身皆俗”[1]147,由此评而看,作者若非故作超然,就是未曾真正理解物是人非的凄凉。
梅尧臣的《金陵》亦含这一思想。首句“恃险不能久”承接刘禹锡的“山川空地形”,却并非如刘禹锡一样表达“兴废由人事”之意,反而更强调人的无奈,即使地形险要也不及天意所向。又描绘六朝繁华已尽,宫阙荒凉,却不必将此放在心上,言“莫挂一毫芒”。所表达的意思虽与刘克庄相近,但气势却要好得多,前面所写之景视野开阔宏大,承接“莫挂一毫芒”的旷达之语才不显得突兀,不似刘克庄所写不过山间景物,却要承接“登临不用深怀古,君看钟山几个争”,衔接难免不太自然,给人做作之感。而承接梅尧臣的“莫挂一毫芒”,将“齐彭殇、忘尧桀”的“异端之说”发挥到极致的,则是刘攽的《次韵金陵怀古四首》其一,全诗不谈兴衰之因,但言兴替之实,不仅“忘尧桀之是非”,更含有“齐兴衰变换”之意,“虎踞群山带绕江,为谁为国为谁降”当真不执着于一朝一代,更不论是非功过之意。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的末句也含此意,“黍离麦秀从来事”一句不含任何是非的评价,虽然前面提及“逸乐”乃祸因,但此句却将朝代的兴替比作季节更替般的自然之事,仿佛一个没有原因的更加令人无可奈何的自然局面。然而“黍离麦秀从来事”“为谁为国为谁降”虽是对历史最为真实、准确的概括,但这也实在是一个充满无奈的现实,其中所包含的沧桑兴衰的悲凉早已超过梅尧臣的《金陵》,对此,诗人却能做出“且置兴亡近酒缸”“笑数英雄尽一缸”的旷达豪迈之举,其很大程度上当缘于作为吞并南唐的胜利者的骄傲豪情。
以胜利者的姿态发豪言壮语当然是宋人的特权,而王安石此类作品尤多。王安石的《和微之重感南唐事》及《金陵怀古四首》其二、其三、其四,以及刘攽的《次韵金陵怀古四首》其二、其三,均属此类,刘攽之诗虽用往事之典,但亦是言胜利者之感。而王安石诗中尽是“天移四海归真主,谁诱昏童肯用长”“兵缠四海英雄得,圣出中原次第降”“将军谈笑士争降”之语,“山水雄豪空复在,君王神武自难双”更是将“山川空地形”和“恃险不能久”归结为宋君的英明神武,将宋君视为左右历史潮流的英雄。这些,虽然难免歌功颂德之嫌,却也体现了一种自信豪迈的情怀。而刘攽之诗为和王安石之作,情感上自然有所应承,然而其在“齐彭殇、忘尧桀”方面虽比王安石表现得更加明显自然,也更加超脱,但在胜利者的豪情抒发上却不及王安石的气势。
宋朝还有一类金陵怀古之诗,既非方回所谓“异端之说”,也没有什么“为世道计”之心,只是单纯抒发朝代兴衰而故国却无人问津的凄凉伤感之情。刘攽的“唯有鱼盐城下市,樯乌相对集瓶缸”隐隐含有物是人非之意,却没有伤感之情,但言兴衰变化而已,但是王珪的两首《金陵怀古》则都极具故国无人问的伤感之情。《依韵和金陵怀古》前三联均写惨淡萧瑟之景,末句以“故国凄凉谁与问,人心无复更风流”极尽凄凉往事无人问津的伤感;而《金陵怀古》则通篇都在言欲寻旧迹而不得,反复渲染陈迹不在,故人已逝,甚至当年的极尽悲凉亦被人忘却的更深的悲凉感,“十年重到无人问,独立东风一怆情”。无论是否套语,所表达的是一种个人的人生感悟,其情感是高于颂圣和劝诫的。钱惟演这类降臣所作之诗都不出借古讽今的劝诫之意,王安石等人更是大发胜利者的豪情壮语,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亦言“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并赞圣朝和平,金陵的繁华陈迹和国破家亡的悲痛早已为人遗忘,当真只有王珪一人为之怆情,其中凄凉伤感自可见矣。
四、宋人金陵怀古诗与其时史学观的差异
由上文可以明显看出《瀛奎律髓》中金陵怀古之作大多都为方回所谓的“异端之说”,而作此说者又多为宋人。然而,宋人的史学观念甚至文学观念却绝非如此。宋朝注重理学教化,自建国之初便强调“以资世教”的经世致用史学观,而文人士大夫亦多持兴亡由人事的观念,重视历史的借鉴意义。自宋之初,修史以作借鉴就是宋代编修史书的重要目的,赵匡胤在下诏编修《旧五代史》时,就已指出“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3]4611;真宗朝官修《册府元龟》,亦取舍史料,整理君臣善迹美政,“以资世教”[4]264;仁宗朝奏请重修五代史时,亦有“安危之迹,亦可为鉴也”之说[4]254;《资治通鉴》之名亦明显体现出了修史的目的。
通过对新、旧《五代史》的褒贬,可以明显看出宋人重视历史以资世教的作用。宋初编订《旧五代史》本来就有以史为鉴避免五代之乱的目的,然而时人对其就有“褒贬失实”之评[3]4615,以至在宋仁宗时便引起君臣极度不满而提出重修[4]254。通过《新五代史》的编订理念,不难看出,宋人甚至在史实记载和历史的劝诫教化作用间更重历史的劝诫教化作用的。欧阳修认为五代乱世,其礼乐文章不足法,所以在典章制度方面,《新五代史》只作《司天考》和《职方考》两篇;《旧五代史》则被欧阳修评价为“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5]347。尽管在保存史料和史实记载方面,《旧五代史》是优于《新五代史》的,例如,《新五代史》比之《旧五代史》的残本缺载之人尚远远超出[6];周世宗攻打南唐之时,清流关唐军的守备人数,亦当以《旧五代史》为确[7]90,等等。然而宋人对《新五代史》的推崇却远胜于《旧五代史》,乃至后来《旧五代史》几乎失传[3]4620。足见宋人的史学观远非其金陵怀古诗中所体现的“忘尧桀之是非”。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异端之说”缘于“金陵”对于宋人有不同于唐人的特殊意义。宋吞并南唐,南唐的灭亡对宋人来说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是历史功绩,而宋朝重文轻武,文人士大夫得到极大的尊重和重用,形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故而宋代文人有很强的自尊心、自信心,与此同时,宋朝对文人的优待也带来了文人的真诚服膺和对宋朝的真心颂扬[8]210,故而王安石诗中充满了胜利者的骄傲和豪情,并由衷地称赞了宋君的英明神武,无论是地势险要还是荒淫误国,都不及天意要让四海归于“真主”,诗中以史为鉴的情感自然就淡化了。
另外,南唐的兴衰对于宋人来说是一个并不遥远的经历,金陵作为南唐的都城对宋人的意义也就超出了单纯的繁华衰落、奢靡误国的符号,而成了一种能够引发更加切身的对沧桑变化的慨叹的意象。而宋人对南唐故事也是有兴趣的,欧阳修就曾在《丰乐亭记》中提及对滁州旧事的寻访;王安石也曾读徐铉的《江南录》而大发感慨写下一篇《读〈江南录〉》等。然而近在眼前的南唐繁华、亡国之痛早已被“盖天下之平久矣”的繁盛之音所掩盖,故国不在,人心不复,怀念故国、伤感故国凄凉之人更再难寻觅,此时对历史变迁无常的悲叹早已盖过了以荒淫为戒的“世教”,“故国凄凉谁与问,人心无复更风流”尽显当年的沉痛早已无人问津的苍凉感。
五、结语
方回《瀛奎律髓》中所选的与金陵或六朝有关的怀古诗中,宋诗的数量远多于唐诗,“齐彭殇、忘尧桀”的“异端之说”又远多于“为世道计”的正统观念,而前者亦多为宋人所作。
金陵的纸醉金迷和朝代的频繁更替,使得相关的怀古诗本最易表达“逸乐安知与祸双”的以史为鉴的劝诫,然而不同于宋代“以资世教”的史学观念,宋人对金陵这一意象发出了既不合于自身亦不同于前代的感慨。宋人以其时代历史经验的优势,除了昆西派4人所作,大多加入了对灭亡南唐的体会,或“黍离麦秀从来事”的旷达超脱,或“天移四海归真主”的豪迈自信,或“故国凄凉谁与问”的凄凉伤感,表达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丰富情感。
[1]方回.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欧阳修.新五代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6]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5.
[7]顾宏义.天衡:十世纪后期宋辽和战实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8]崔际银.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