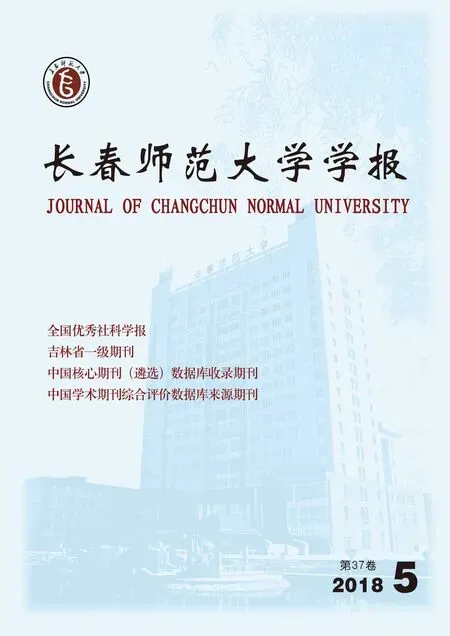《文选》撰者及成书时间刍议
2018-03-28邹德文
高 博,邹德文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一、“不录存者”说
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第二十李善注《文选》条载,“窦常谓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盖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然则所录皆前人作也。”[1]1054历代学者多从此说,而以《文选》收录作家中亡故最晚者陆倕之卒年(普通七年,526)作为研究《文选》成书时间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以笔者管窥所见,王立群先生首先对此说提出质疑,并作出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考证。在其名作《<文选>成书研究》一书的第一章中,先生写道:“率先应用此说而研究文选成书的是何融……何融在实际考察生前诗名极盛且卒年在陆倕卒年之前的何逊未能入选时,已发现‘不录存者’说无法对此进行解释……且何融个人考定的《文选》收录梁代作品作年最晚者为刘峻在天监十五年(516)所著的《辩命论》,至此,窦常所谓‘不录存者’的这一观点可以宣告寿终正寝了”,又以“魏晋南北朝典籍真正提出这一观点并身体力行者唯有钟嵘《诗品》”,“据刘勰所言,魏晋南北朝文论家并非均如钟嵘那样‘不录存者’,因为‘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本身即是古今兼论”[2]9-10等语作为佐证。笔者以为,王立群先生对窦常说的质疑,其要点在于:若《文选》录“不存者”,则当收录何逊的作品,以及与何逊情况类似(死于陆倕之前,如柳恽、吴均)的一些文学家的作品。然而,考虑到《文选》编撰过程中其他选录标准存在的可能性,不收录何逊的作品似乎不足以作为质疑“不录存者”说的理论依据。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反面来思考:若《文选》“可录存者”,则不论从哪方面看,与萧统关系极好而文名又极盛的刘孝绰都应当有作品被收录。按此,依笔者拙见,“不录存者”说依然可以作为研究《文选》成书年代的重要依据,即《文选》的最终成书时间不应早于陆倕亡故的普通七年(526)。另据周绍恒先生《何逊卒于萧统<文选>编成之前说质疑》一文所考,何逊“不仅在天监十八年(519)左右未卒,而且迟至中大通五年(533)八月还活着,甚至有可能是卒于大同元年(535)四月之后至大同三年(537)正月之前”[3]575,即其死亡或在陆倕之后。此说与《文选》编者及《文选》编撰年代关系密切,期待海内外各位专家学者作进一步考证。
二、“《文选》为再选本”说
“《文选》为再选本”之说,古时已有。唐代刘良注《文选》时,于《答何劭》作者张茂先名下注云:“何劭所赠华诗,此诗之下是也。赠答之体,则赠诗当为先,今以答为先者,盖依前贤所编,不复追改也”[4]1512。
1986年10月,已故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三十八集发表《<文选>的编撰实况与当时对它的评价》一文,提出《文选》乃是“由先行诗文选集再度编撰而成的选集”[5]88一说,并对此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述。2004年4月,王立群先生为其著作《<文选>成书研究》撰自序文,指出“《文选》并非先成长编而后删节成书,而是依据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刘义庆《集林》等前贤总集进行二次选编的再选本”[2]2,并在书中对此作了极为详细的考证。我国已故学者曹道衡先生称王先生与冈村先生“异地同符,可谓美谈”,然此二说之间似尚有一些差异。冈村先生根据《隋书·经籍志》中书名排列方法推断《集林钞》《集钞》《集略》等书皆为“依据《集林》而来的同类选集”,并以“沈约《集钞》十卷、丘迟《集钞》四十卷以及昭明太子与刘孝绰自编的《诗苑英华》等”为《文选》选文时所依据之“先行诗文选集”[5]88;而王立群先生所提出的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刘义庆《集林》等皆为“前贤总集”,此或因王先生以《隋书·经籍志》之分类为准,将《集林钞》《集钞》《集略》等书并归入总集之列,且又以《集林钞》等书皆是依据前人总集而编撰的选集所致。此二说总体上已十分接近。
曹道衡、傅刚两位先生认为,“普通七年以后,《文选》的实际编纂时间只能是大通元年(527)末至中大通元年(529)底这两年之间”。“很明显《文选》是在萧统原先编纂的诗文总集基础之上进行的”,而《文选》中的赋类,“是依据了萧衍所编的《历代赋》”[6]225-226。清水凯夫先生则认为,“因为以往昭明太子集团已编完了《古今诗苑英华》、《古今文章英华》,所以在这基础上完成《文选》选录该是容易的吧”[7]220。俞绍初先生亦曾在文章中指出:“《文选》的编撰不需要新起炉灶,可在已成的几部总集的基础上进行。赋类,已有梁武帝《历代赋》十卷……诗类,当以《诗苑英华》二十卷为基础”[4]3981。
近年来,“《文选》为再选本”说,已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接受。
按《隋书·经籍志》所载,当时存世之别集共437部,总集共107部[8]721-726,则可供编撰《文选》所使用之书亦当不在少数。然据王立群先生考证,“《文选》中部分作品的篇题与该作家别集之篇名有别”,故《文选》“非据作者别集选录”。此外,由“《文选》为再选本”说所引发的一些新问题,如《文选》中哪些时代中的哪些诗文是经过“二次选编”而被收录进来的,哪些时代中的哪些诗文没有经过“二次选编”而被直接选录进来,《文选》编撰时所依据的“前贤总集”具体是哪几部书等问题,尚待进一步考证。
三、“萧统独撰《文选》”说
据《梁书》《南史》《隋书·经籍志》等诸多史料记载,《文选》为昭明太子萧统所独撰。
按“《文选》为再选本”说,则其编撰工作完全可能由萧统一人独自完成。
1976年,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清水凯夫先生在《<文选>编辑的周围》一文中首先提出“《文选》的实质性撰录者不是昭明太子,而是刘孝绰”[9]45一说,此后又多次撰文重申这一观点。清水先生认为,“梁代的总集,在一般情况下,正如《梁书》、《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那样,把下编纂命令的帝、王作为编者并把名字作为‘撰者’记录下来。而实际上这些总集,可以说绝大多数是有力的文人作为中心而被编纂出来的”[7]201-202,并以此作为推断《文选》实际撰者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其名作《<文选>编纂实况研究》一文中,先生举出了多个梁代总集编纂的实例:
(1)简文帝编纂总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委任以近臣庾肩吾、徐摛为首的“高斋学士”而完成的(见《南史·庾肩吾传》)。
(2)据《梁书·简文帝纪》载,简文帝著《法宝连璧》三百卷。然据《南史·陆罩传》载,此书乃是由萧子显等37名文人完成的,萧纲本人并没有参加实际的选录工作。对这件事,湘东王萧绎的《梁简文帝法宝连璧序》更详细举出了编者的具体名字。
(3)《隋书·经籍志》载,“《长春义记》一百卷,梁简文帝撰”。但正如《南史·许懋传》所言:“皇太子召与诸儒录《长春义记》”,实际上是太子萧纲招聘许懋和其他文人一起参加选录。
(4)元帝萧绎有碑文总集《碑集十帙百卷》,据它的注记“付兰陵萧贲撰”可知,是元帝让萧贲作为中心进行选录工作,绝非萧绎自己直接从事编纂工作。
(5)《西府新文》,《颜氏家训》记为“梁孝元在藩邸时,撰《西府新文》”;而《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西府新文》十一卷,梁萧淑撰”,则《西府新文》乃是侍臣萧淑等选录的,绝不是元帝亲自参加了编纂工作。
(6)昭明太子的叔父安成王萧秀在编纂总集《类苑》时,“召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见《梁书》卷二十二《安成康王秀传》)
(7)嫌恶刘孝标的梁武帝为了阻止《类苑》流传,编了一本总集《华林遍略》。武帝本身并未参加编纂,依然是命令臣下诸学士撰写的(见《南史·刘峻传》)。
(8)《隋书·经籍志》载,“《通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但《梁书·吴均传》载:“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从中可以看出,实际撰者是吴均等人。[7]198-201
以上,清水先生列举出梁代总集编纂的多个实例作为佐证,皆是为了证明《文选》的实际编纂者为刘孝绰。
此外,据萧绎《金楼子·著书篇》载,《梁书·元帝纪》和《隋书·经籍志》中萧绎本人的著作可分为五种类型:金楼(元帝号)自撰,金楼撰,金楼付某撰,金楼自为序付某撰,金楼为序。这一记载亦受到清水先生的重视。在1984年发表的《<文选>撰者考》一文中,先生“以《梁书》和《隋书·经籍志》记述的元帝撰著为中心,将《金楼子·著书篇》与之对应的记述制表明示”,认为“既然有明记‘自撰’的,则单记作‘撰’的大概是‘自撰’以外的撰著,可能是由他人协助的撰著。如果‘撰’是这种意义的话,则‘金楼付某撰’、‘金楼自为序付某撰’、‘金楼为序’的撰著当然是金楼完全没有实际参加的撰著”[9]6。
然正如力之先生所说,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萧氏兄弟于著书立说,未见乾没他人之功”,“整部《梁书》以及《南史》相应部分亦没有半句涉及孝绰或者其他什么人参加文选的选录工作”,《文选序》全文“也没有一处谈及他人参加文选的选录工作”[10]。史载昭明太子生平宽和容众、品格高尚,故清水先生举出的诸多例证只能从反面证明《文选》为昭明太子撰。
另据《文选序》中“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等语,亦可见《文选》总体上应为昭明太子所独撰。
四、影响《文选》成书时间研究的几个重要因素
有几个重要因素,历来为研究《文选》成书时间的专家学者们所重视。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据《昭明太子集》卷首所载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一文中“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载”等语,可知《昭明太子集》当成书于普通三年(522)。按萧统所作《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一文中没有提及《文选》,则《文选》的成书时间应在普通三年《昭明太子集》(即湘东王所求文集)成书之后。
(2)据《文选序》中“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日《文选》云耳”等语,可知《文选序》应为《文选》的编纂工作接近尾声时或基本完成后所作。且《文选》的编纂时间必在天监十四年正月昭明“行冠礼”“加元服”“省万机”之后。
(3)按普通七年(526)十一月,丁贵嫔(萧统生母)“有疾”,“太子还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带”。及其下世,萧统更是悲痛欲绝,“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则恸绝”,“虽屡奉敕劝逼,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11]112。冈村繁先生认为,“昭明太子这种极度的厌食以及急剧的身心衰竭并非一时小恙,其病状并非仅由于奉侍病母和服丧哀劳所致。它恐怕与当时太子已经患上的不治之症有关”[5]80。此后,昭明又因“埋蜡鹅事件”大失梁武帝欢心,并“迄终以此惭慨”[12]876-877,则以《文选序》中所透露出的萧统闲适愉快的心情来看,此文不太可能作于丁贵嫔“有疾”之后。即在普通七年(526)十一月丁贵嫔“有疾”之前,《文选》的编纂工作应已接近尾声或基本完成。
(4)按《文选》“不录存者”,其最终成书时间当不早于收录作家中亡故最晚者陆倕之卒年,即普通七年(526)[11]276。
按俞绍初先生据《艺文类聚》卷四十九引梁元帝《太常卿陆倕墓志铭》一文中“日月往来,暑流寒袭。东耀方远,北芒已极。坠露晓团,悲风暮急”等语所考,陆倕应卒于普通七年秋,而史载丁贵嫔卒于普通七年十一月。[13]312-313又按《梁书》记载,丁贵嫔所患之病乃是急症,从得病到死只在一月之间,此前萧统或许并未因此耗费太多精力,则《文选》最终成书时间似乎应在普通七年陆倕死亡之后,丁贵嫔“有疾”之前。
五、文选成书过程中的“补录”现象
依据“不录存者”说,若《文选》最终成书于普通七年陆倕死亡之后,丁贵嫔“有疾”之前,即《文选》最终成书的时间距离陆倕死亡的时间极短,则在其编撰过程中极有可能存在一个将当时新近死去作家的作品补录进来的步骤。
若《文选》最终成书于丁贵嫔“有疾”之后,结合前文所述《文选序》写作的时间和背景来看,则在《文选》的编撰工程初步完成后,几乎一定存在一个将当时新近死去作家的作品补录进来的步骤。
此外,若《文选》最初确定所录作家之下限就是陆倕去世之普通七年,则正如力之先生所说:“由于陆倕去世距丁贵嫔‘有疾’至多仅三个月,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文选》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完成的”[14]。
关于文选成书过程中的“补录”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国内已有多位专家学者发表过自己的见解。王立群先生在《<文选>成书研究》一书中写道:“普通三年至普通六年,为部分现代《文选》学研究者最为看好的编纂之时。普通七年(526)下世的陆倕入选《文选》,以《文选》入选作家卒年为研究视点的研究者只能认定陆倕是初选后的补入者。”[2]137
俞绍初先生认为:“及至普通七年……《文选序》已经写成,自梁天监以前的作家作品也大体甄选就绪。剩下来要做的,一是对已完成部分进行必要的修订加工,二是增补普通时期的作家作品,以使符合古今兼收的体例要求。所以昭明太子一俟心丧期满,大约在大通二年(528)末,便立即重理旧业,把远在荆州的刘孝绰召回,让他重新担任太子仆,去共同完成尚未完成的工作。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刘孝绰进京不久,关系昭明一生命运的‘蜡鹅事件’暴露了……几乎与‘蜡鹅事件’暴露的同时,刘孝绰也因母亲亡故而去职,加上一些东宫学士相继凋零,要想继续从事《文选》的编撰已不再可能了,于是便匆匆补进普通间刘孝标、徐悱、陆倕三家诗文,算是完成了使命,这便是今天所见的《文选》。”[4]3981-3983
力之先生在《文选》成书时间考说一文中写道:“佐公(陆倕)去世时只要《文选》还没有编定,就自然没有不收之理;甚至刚编纂好,还可以入之。此类钟嵘《诗品》之后入休文。”[14]
六、“刘孝绰补录《文选》”说
据《梁书·刘孝绰传》载,“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11]332
1983年1月,清水凯夫先生发表《<文选>中梁代作品的撰录问题》一文,将“在考察《文选》的编辑情况时值得提出的齐梁时代作品(共29篇)整理出来”,分成六类,详细考查了这些作品的选录与刘孝绰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对其中的《头陀寺碑文》《刘先生夫人墓志》两篇作品进行了分析。清水先生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文选》的实际编者是刘孝绰”这一观点虽然并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其对《头陀寺碑文》等具体作品的分析亦曾遭到力之、顾农等国内专家学者的质疑和反对,但从清水先生的研究过程可以看出,刘孝绰应在《文选》成书的后期参与甚至实际主持了《文选》的撰录(主要是梁代作家作品的补录)工作。仅从《文选》中所收录卒年最晚的三位作家的六篇作品来看,其中就有四篇被清水先生认为是根据刘孝绰的意志而被收录进《文选》的,《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诗》一诗因作者徐悱是刘孝绰的妹婿而被列入“根据亲戚或同族关系撰录的作品”之列;《广绝交论》一文因“对道洽的报复”而被列入“刘孝绰作为一种报复措施撰录的作品”一列;《辨命论》与《重答刘秣陵沼书》因“均与刘孝绰的狷介性格酷似刘峻以及与所敬爱的刘瓛有关系”而被列入“其他,因与刘孝绰的关系撰录的作品”一列。[9]28-29清水先生在《<文选>编辑的周围》等文章中亦曾对《文选》中梁代作品的撰录问题作过颇为细致的分析,因本文篇幅所限,于此难以详述。此外,从刘孝绰现存最长的诗作《酬陆长史倕诗》中“分悲宛如昨”“度君路应远,期寄新诗返”“相望且相思”“平生竟何托,怀抱共君深”[15]1833-1834等语,亦可看出他与陆倕之间既是诗友,又有颇为深厚的同僚之谊。故陆倕亡故之后,刘孝绰将其被载入《梁书》的两篇名作《石阙铭》和《新刻漏铭》补录入《文选》亦在情理之中。正如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在《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擬测》一文中所总结的那样:“《文选》中对天监后期至普通中逝世的作家,其取舍似都与刘孝绰的爱憎有一定关系。所以,推测刘孝绰对《文选》的编定曾起过重要作用,应该是合乎情理的”[16]347。
据《梁书·到洽传》记载,普通六年(525),(到洽)“迁御史中丞,弹纠无所顾望,号为劲直,当时肃清”[11]277。又据《梁书·刘孝绰传》载,“及孝绰为廷尉卿,携妾入官府,其母犹停死宅。洽寻为御史中丞,遣令史案此事”,刘孝绰“坐免官”[11]332,则刘孝绰“免官”当在普通六年。据《梁书·刘孝绰传》载,“孝绰免职后,高祖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11]333。另据《梁书·武帝本纪下》载,“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书左仆射徐勉为尚书仆射”[11]47,则刘孝绰在大通元年(527)正月时依然处于被“免官”期间。因此,有刘孝绰参与的《文选》后期的补录工作,不可能完成于普通七年(526)陆倕死亡之后、丁贵嫔“有疾”之前。而据史料记载,自普通七年起,东宫文士集团日渐凋零,陆倕、到洽、殷芸等太子身边的著名文人相继去世。又据《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免职后”、“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后为太子仆,母忧去职”等语,可知刘孝绰于大通元年春正月之后,曾再次回到萧统身边做“太子仆”。再结合丁贵嫔“有疾”之后萧统急剧的身心衰竭以及此后发生的“蜡鹅事件”对其造成的严重影响来看,萧统在此期间将《文选》后期的编撰工作移交给经验丰富且深受他本人爱戴的刘孝绰是完全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选》成书后期的补录工作是由刘孝绰或以刘孝绰为首的文人集团来完成的,而《文选》最终成书的时间与刘孝绰“后为太子仆”的时间密切相关。
七、《文选》最终成书时间考
天监七年(508),梁武帝定安北将军为武职二十四班中的二十一班,定骠骑将军为武秩二十四班。[17]418-912
据《梁书·简文帝本纪》载,萧纲于普通五年(524)“进号安北将军”,“(普通)七年,权进都督荆、益、南梁三州诸军事”,“(中大通)二年,(被)征为都督南扬、徐(疑为扬、南徐之误)二州诸军事、骠骑将军、扬州刺史”[11]69。
据《梁书·武帝本纪下》载,“二年春正月戊寅,(武帝)以雍州刺史晋安王纲为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11]49。
据《梁书·刘孝仪传》载,“刘潜字孝仪,秘书监孝绰弟也”,“晋安王纲出镇襄阳,引为安北功曹史,以母忧去职”[11]413。按刘孝仪在“安北功曹史”任上“以母忧去职”,则其“去职”的具体时间应在中大通二年(530)正月萧纲晋升为骠骑(大)将军之前。
据《梁书·简文帝本纪》载,萧纲于中大通三年(531)五月被立为皇太子。[11]69
据《梁书·刘孝仪传》载,“王(萧纲)立为皇太子,孝仪服阙,仍补洗马,迁中舍人”[11]413,则刘氏兄弟“服阙”(丁忧期满)是在中大通三年五月萧纲被立为皇太子之后。
按梁代制度,丁忧期为二十七个月(一说二十五个月)。[17]8可以推算出刘孝仪“以母忧去职”的具体时间应在中大通元年(529)二月之后。
综合上述两点来看,刘孝绰(与刘孝仪同)“以母忧去职”的具体时间应在中大通元年(即大通三年)二月之后,中大通二年正月之前。而其“服阙”之时,萧统已薨,故《文选》成书后期的补录工作只能完成于刘孝绰“以母忧去职”之前。
据《隋书·礼仪志三》所载,“沈洙议‘至如父在为母出适后之子……心丧以二十五月为限’”。“唯王俭《古今集记》云,心制终二十七月,又为王逡所难。何佟之《仪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案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月为断”[8]105-106。则丁贵嫔死后,萧统须守“心丧”二十五个月。即从普通七年(526)十一月开始到大通二年(528)十二月为止是萧统守丧的“时期”。按“心丧”之制,《文选》后期的编撰工作亦不太可能在萧统守丧期间进行。俞绍初先生认为,“昭明之免丧当在大通二年十二月,其招孝绰为太子仆殆在此时后未久,似欲以续成《文选》故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选》最终成书的时间应在中大通元年(即大通三年,公元529年),萧统“心丧”期满之后,刘孝绰“以母忧去职”之前。
八、结论以及笔者对几个相关史料的理解
依笔者拙见,《文选》应初步成书于普通七年,丁贵嫔死亡之前,其主体部分当为萧统一人独撰。《文选》成书后期的补录工作则是由刘孝绰(或以刘孝绰为首的文士集团)来完成的,其最终成书时间应在中大通元年(大通三年,公元529年),萧统“心丧”期满之后,刘孝绰“以母忧去职”之前。
按《梁书》《南史》《隋书·经籍志》等正史资料所载,《文选》为昭明太子撰,此当是就《文选》编纂的总体情况而言。刘孝绰所做的仅仅是《文选》成书后期的补录工作,且以其身份地位而言,不被正史列入《文选》作者之列亦在情理之中。
据屈守元先生《跋日本古钞无注三十卷本<文选>》一文中所述,日本古钞无注三十卷本《文选》中第一卷《文选序》的题署上方有一标记云:“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屈先生据此认为“《文选序》出于刘孝绰之手”,但“刘孝绰是受萧统之命而作的,他不能因此而取代萧统的《文选》主编权;这篇序的观点也是萧统的”[18]443-444。笔者以为,“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标记在《文选序》题署的上方,其含义极有可能与《文选》成书后期萧统将《文选》的补录工作移交给刘孝绰等人有关。
《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载,“或曰:晚代诠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19]1539。罗根泽、潘重规等学者认为,“或曰”后面的这段话出自唐人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序》。其说距离《文选》编纂的年代不是很远,故历来为选学届诸多专家学者所重视。另据《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文字下之的注解所载,《文选》为萧统“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20]1066。笔者以为这两个史料上的记载正好印证了《文选》由萧统、刘孝绰等人共同完成的情况。而对于何逊曾参与《文选》的编纂工作这一说法,目前大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其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考证。
据俞绍初先生《<文选>成书过程擬测》一文所述,“在敦煌遗书中有一部类书叫《杂钞》,里面有一个书目,其中提到《文选》说: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谓之《文选》”[4]3983。笔者以为,此当是据《文选》成书后期刘孝绰“后为太子仆”,萧统将《文选》的补录工作移交给刘孝绰等人的情况而得出的说法。
[参考文献]
[1]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
[3]周绍恒等撰,王立群主编.第十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4]萧统选编,吕延济等注,俞绍初等点校.新校订六家注文选[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
[5]冈村繁.冈村繁全集第二卷:文选之研究[M].陆晓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清水凯夫著,周文海编译.《诗品》《文选》论文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8]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9]清水凯夫.汉魏六朝论文集[M].韩基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0]力之.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J].文学评论,1999(1).
[11]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14]力之.《文选》成书时间考说[J].钦州学院学报,2011(2).
[1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曹道衡等撰,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7]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8]屈守元等撰,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9]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0]王应麟.合璧本玉海[M].东京:中文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