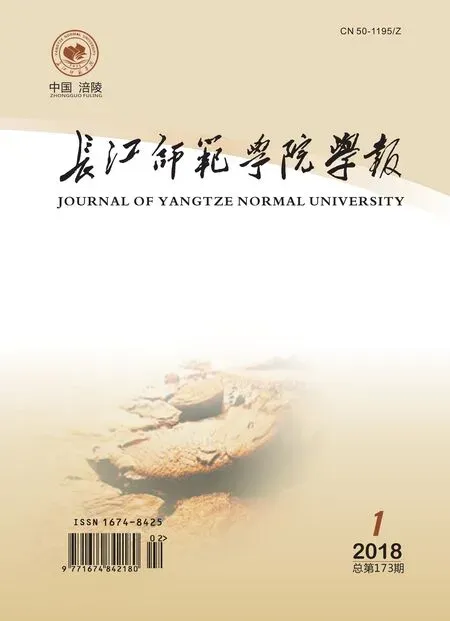鄂西南土家族传统婚俗变迁研究
2018-03-28李兴军
李兴军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对传统婚俗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从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看,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其一是侧重传统婚俗文化调查和资料收集的研究;其二是对婚俗中的某个片段进行专题研究;其三是注重解释婚礼仪式象征意义的研究。以上3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完全展示传统婚俗的全貌,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土家族人民生活的水平不断提高,其婚俗也相继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较为明显的是,鄂西南土家族传统婚俗在外来文化的传播和介入下发生了急剧的变迁。这里选取湖北省来凤县“舍米湖村”为研究个案,对舍米湖村婚俗变迁问题进行专题探讨,采用历时性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讨论舍米湖村土家族传统婚俗变迁的现状及原因。这有利于土家族婚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有助于提高土家族的文化自觉意识,树立文化自信观念。
一、土家族的传统婚姻观念
第一,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土家族传统婚姻最重要的一条是需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至于选婿,祖父母、父母主持之下,不必问女子之愿否。”①乾隆《鹤峰州志》卷10《风俗志》。在一般情况下,男子年龄到了十三四岁,父母需要为他们筹划婚事,并请媒人为孩子说媒。说媒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说媒。此种情况是男方家父母已经看中了某家女孩,便会央求媒人直接说媒。另一种是请媒人介绍。此种情况是男方家没有寻觅到合适的女孩,便请媒人介绍具备“门当户对”“男女般配”等条件的女孩作为参考。在请媒的过程中,男方家需要提前准备“礼物”②礼物,多为酒肉、糕点。,做好酒菜,毕恭毕敬地邀请媒人到家中吃饭喝酒,并由家中公婆、父母、伯叔等长辈告诉媒人关于孩子的具体情况,之后媒人开始起步动身说媒。在整场婚事当中,媒人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媒人能力的大小会影响婚事的成败。
第二,讲究“生辰八字”。在土家族传统婚姻中,当媒人说成亲事后,在订婚当日要请算命先生或者是风水先生看生辰八字,通过看生辰八字来决定这一桩婚事是否真的合适。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一环节在土家族传统婚姻中极为重视。在土家族人看来,“生辰八字”关系着婚姻当事人的幸福。关于“生辰八字”的相关研究,亨利多在《关于中国的迷信》一书中有过完整的叙述。
第三,注重“吉日”择定。“吉日”择定是继“生辰八字”确定后的重要一环。“吉日”由风水先生根据婚姻当事人的“生辰八字”推算确定。一般而言,“吉日”要考虑婚礼仪式的每一个时辰,若有一个时辰与“生辰八字”相冲突,则需要另择“吉日”。此外,“吉日”的选择通常有一个时间范围,土家族婚礼“吉日”的挑选多在农历腊月或来年正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时期土家族人一年粮食储备最为丰富,且正值农闲,筹办婚礼劳力较为充足。
二、土家族的传统婚俗
(一)婚姻习俗
1.传统时期的血缘婚。目前,可以从土家族兄妹成婚的神话及土家语的亲属称谓来探寻血缘婚的遗存。兄妹成婚的故事在土家族聚居的许多地区都有流传,如《马桑树的变迁和百家姓的由来》《孙猴子上天》两个故事集中讲述了渝东南地区土家族人兄妹成婚的故事;《佘氏婆婆》讲述了鄂西南土家族谭姓始祖的由来[1];《布所雍尼》讲述了湘西与酉水流域土家族人布所和雍尼兄妹结婚生下肉坨坨,用金刀把肉坨砍成120块,从此世上有了土家、苗家和客家的传说;《傩神爷爷和傩神婆婆》记录了黔东北土家族人是傩神爷爷和傩神婆婆的后代。尽管上述土家族兄妹成婚的故事不具有科学性,但它们集中表达了人类对血缘婚的拒绝及反思过后的一种文化自觉。
此外,从土家语的亲属称谓中也可对其血缘婚略知一二。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普遍存在姑母、岳母同称,姑父、岳父同称,舅父、公公同称,舅母、婆母同称,祖父、外祖父同称,祖母、外祖母同称,等等。此称谓不论族内族外,只有性别、年龄之分,没有亲疏远近之别,所有的同辈人均用同一称呼。这种“类别式”的称谓制度即为“血缘婚”存在的反映。
2.土司统治时期的“骨种婚”。“骨种婚”又称为“姑舅中表”婚,即“姑家有男,舅家有女,姑家可优先遣人说定舅家之女,舅家因此不敢嫁女于他家。反之,舅家之男对于姑家之女亦有优先权,因是舅姑两家的儿女属于互相婚配的关系”[2]45。此类婚姻形态也可以查找到相关的历史文献证据,如雍正八年永顺知府袁承宠在《详革土司积弊》中云:“土司旧例,凡姑氏之女必嫁舅氏之子,名曰‘骨种’,无论年之大小,竟有姑家之女年长十余岁,必待舅氏之子成立婚配。”①民国《永顺县志》卷6《风俗志》。即土司统治时期的土家族严格实行血缘婚制度;王伯龄的《禁陋习四条》反映了乾隆七年永顺县存在骨种婚姻形态;曹学佺的《蜀中广记》记载了明代土家族地区存在骨种婚习俗;甘明蜀的《酉属视察记》记述了民国时期土家族人地区存在骨种婚的旧习。
可见,自明代以来,土家族地区就存在骨种婚习俗,且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骨种婚在土家族地区盛行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保证舅家“种”的延续,在婚姻上具有绝对优先选择权。这种优先选择权既表现为舅家之子对姑家之女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也表现出舅家对姑家不用支付太多的彩礼钱。在现实中也因不能正常“还骨种”而带来一些弊端,影响了双方关系的发展,如舅家与姑家都是儿子,舅家与姑家都是女儿,舅家之子与姑家之女年龄相差较大的情况。以上3种情况都会引起双方之间纠纷,造成骨种婚的中断。
其二是土司时期土家族聚居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使“骨种婚”发展得以存在。实行“骨种婚”对土司时期的土家族发展具有两大优势:一方面,骨种婚是一种保住劳动力的方式。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农耕文明中,土家先民为了不让女性劳动力外流,实行骨种婚可以减少女儿外嫁造成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骨种婚是一种保证“种”延续的社会机制。土司时期的土家族男子奉土司之命出征,时常面临死亡的危险,通过骨种婚可保证“种”的延续。
因此,骨种婚的存在不是土家族婚姻发展的偶然,而是土司统治时期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婚礼习俗
1.抢亲。关于土家族“抢亲”的婚礼习俗,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云:辰、沅、靖州蛮,男方在娶亲之前,多埋伏在路边,等到女方从那里经过时,就将其绑缚,带回自己家成亲,女方在此过程中会呼叫求救,这其实都是男女双方事先商量好的,具有表演性质[3]124。显然,这是一种表演意义上的抢亲。然而,土家族的抢亲更是一种仪式。这在杨昌鑫的著作《湘西土家风情》一书中介绍得较为详细。随着时代的发展,土家族的抢亲仪式由兄弟背负的方式逐渐演变为“拦门礼”或“背亲带”。清改土归流以前,“兄弟背负”的土家族婚礼抢亲既是一种增添气氛的方式,也是土家族人对野蛮时期掠夺性婚姻的心理反映及其历史回顾。改土归流以后,土家族地区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更加重视伦理道德,注重以“礼”的方式来延此旧习,“拦门礼”在鄂西南等土家族聚居地区逐渐成为主流。
2.哭嫁。土家族“哭嫁”分哭姊妹、哭父母、哭哥嫂、哭祖先、哭哥哥、哭媒人等,每一种哭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一般而言,哭姊妹预示婚礼的开始,新娘哭姊妹或者姊妹互哭都表示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哭父母既表达了新娘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怀念,也流露了父母对女儿远嫁他乡的不舍之情;哭的内容多以教育和鼓励为主,如孝敬公婆、遵从夫君、爱护幼小、勤俭持家等。哭舅父母既体现了新娘对舅父母的不舍和依恋,也受传统时期土家族“姑舅中表”婚姻遗存的影响。哭哥嫂既体现了一种兄妹之情,也体现了新娘与哥嫂之间一种美好的寄托和期望。整个土家族婚礼的哭嫁表面看似是一种悲伤,实则是土家族人“喜事丧办”的自然流露,喜事中的哭不仅具有隆重的仪式感,而且能体现土家族人重视亲情关系维系、知恩图报的光荣传统。
土家族哭嫁习俗极为盛行的因素有三:其一是社会历史原因。改土归流以后,原来“以歌为媒”的自主婚姻完全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所取代,女性地位一落千丈,在感受到极大的压抑之时,哭成为宣泄压抑情绪的较好方式之一。其二是土家族女性自身拥有的悲剧心态。传统时期土家族女性受到夫权压迫,往往会产生对往昔自由生活的怀旧感,在无力改变现状的前提下,哭成为一种无形的抵抗方式。其三是对亲人的不舍之情。新娘知道出嫁后,不能像往常一样侍候父母,想起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哭便成为情感的自然流露。
三、舍米湖村土家族婚俗文化变迁现状
其一,反对父母包办,主张自由恋爱。改革开放以来,土家族婚姻发生了变化。随着新《婚姻法》的颁布,年轻人婚姻主张独立自主,反对父母包办。与传统婚姻相比,土家族普遍存在“先恋爱,后结婚”的形式。谈恋爱(无论是否真正有热烈的爱情)是结婚的必要程序,而不是年轻人青春期的儿戏和冲动[4]53。舍米湖村民A说:
以前父母对后辈的婚姻有着无上的权威,尽管有些年轻人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却没有多少争取婚姻自主的愿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好多年轻人的对象,要么读书时候就认识了,要么出去打工的时候就找好了,根本不需要老人操心。
显然,在现在的土家族婚姻中,恋爱型婚姻已占据主导地位。
其二,择偶形式发生了变化,出现自主选择与父母参考相结合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土家族年轻人择偶自主权由父母完全包办转变为年轻人自主选择与父母参考相结合,很少出现完全自由和完全包办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择偶需要两代人的同意,进行双重的批准与否决,很少出现年轻人被迫结婚的现象。当然,也有个别年轻人不考虑父母意愿而结婚的,但毕竟是少数。择偶方式的变化使年轻人在婚姻中处于主导地位,一桩婚事的成功与否多半是按照年轻人的意愿行事。父母在一桩婚事中多充当从属地位,对孩子的婚事以提供参考性意见为主,很少出现直接干涉的情况。事实上,自主选择与父母参考相结合的婚姻,同样存在传统婚姻体制下的弊端。一桩婚事很难达到父母与子女双方都满意的理想状态。比如,年轻人选择的对象,父母却不看好;父母认为合适的对象,却迎合不了年轻人的口味。在此情况下,往往会出现父母与子女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但为了保证婚事的顺利进行,父母多半遵从年轻人的意愿。
年轻人婚姻自主权的膨胀主要是男女结识方式多样化所导致。随着男女平等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女人同男人一样可以平等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广泛参与各类型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男女平等政策不仅为女人争取了各项权利,而且也扩大了男女之间的交际范围。如今,通过学习、职业、社交媒体等途径结识,最终走向婚姻殿堂的例子并不罕见。
其三,仪式简化,形式多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土家族依旧延续传统的结婚仪式。但该时期已舍弃抬“花轿”的传统,认为“花轿”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大胆摒弃。1958—1962年,处于人民公社化时期,提倡“勤劳节俭”的生活作风,婚礼中的“铺张浪费”行为被遏制。加上3年自然灾害,土家族人民的生活面临窘迫的境况,婚礼被迫从简。“文化大革命”期间,土家族领取结婚证时需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随后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宣告结束。21世纪以来,土家族婚礼和汉族差异不大,更多的是模仿城里时尚的结婚礼俗。例如,舍米湖村D村民说:
现在的土家婚礼喜欢走流行化,把以前的规矩改了。以前办喜事,酒席女方家要办3天,男方家要办4天。现在只吃一顿饭,至亲留下来陪同就可以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鄂西南土家族婚礼传统文化特质(元素)逐渐减少,仪式简化的同时更趋向于现代化发展的潮流。近年来,婚礼形式也随之多样化。既有延续传统的家庭婚礼,也有另辟蹊径、融入诸多现代元素的集体婚礼、旅行婚礼和校园婚礼等。婚礼形式的变化和婚礼场所的变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人们往往根据结婚人的意愿选择不同的结婚场所。整体而言,家庭婚礼仍然是鄂西南土家族婚礼的主要形式,但在全球化和都市化背景下,土家族传统婚俗文化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仪式简化和形式多样的出现多受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其四,通婚范围逐步扩大。20世纪50年代以后,土家族的通婚范围呈现出由寨内结婚(只允许本社区内人的结婚)向寨外结婚(突破本社区范围的外人结婚)的现象。据杨建平的研究,外出务工是引起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因外出务工的增多,出现了外省女青年远嫁土家族村寨和土家族村寨姑娘远嫁外省的现象。目前,鄂西南土家族村寨社区不乏有外嫁到湖南、浙江、广东、重庆等地的女青年,也有向湖南、重庆等地外娶的男青年[5]。
从整个鄂西南地区婚俗文化变迁的现状来看,主要呈现出以下3个特点:其一是婚姻的“法制性”逐渐加强。婚姻必须符合法定结婚年龄,符合法律规定程序,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婚姻都将得不到法律保护。其二是婚姻的“科学性”不断普及。即结婚不再是同姓或联宗。越来越多的土家族人逐渐意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提倡非近亲结婚,扩大配偶选择范围,主动进行婚前检查,并意识到注重婚姻的“科学性”有助于保证家庭的幸福及子女的健康。其三是婚姻的“社会性”不断体现。一方面,地方政府关心群众的婚事。结婚人须到民政局登记,领取结婚证;孩子出生则及时进行户口登记。另一方面,组织筹办婚礼的社团不断增多。在传统社会,婚宴主要在家庭进行。现在越来越多的酒店、宾馆开始承担起筹办婚礼的职责,婚礼显得更加自主和多元。整个鄂西南土家族传统婚礼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系列的文化变迁。
四、舍米湖村土家族婚俗文化变迁的原因
美国学者奥格本说:“文化变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的,由社会的内部的变化引起;另一个是外部的,有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文化的的变迁,如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引起。”[6]1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舍米湖村土家婚俗文化变迁的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一)内部原因
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和社会的结果。舍米湖村土家族传统婚俗的变迁就是舍米湖土家族人适应文化的结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土家族人自然选择的结果[7]。过去土家族存在“血缘婚”或“骨种婚”的习俗。随着科技的发展,土家族人民逐渐意识到近亲婚姻的弊端,诸如“体质不强壮、智力不发达、某些疾病通过遗传因子蔓延,这不仅害己,而且害人、害家、害国”[8]53。为了革除这一陋习,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直系血亲结婚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鄂西南土家族人民顺应了这一政策的号召,果断放弃了这一陋习。
同时,这也和土家族人“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的社会心理因素有关。过去土家族人实行父母包办婚姻,整体上和汉族一样受儒家“三纲五常”“夫唱妇随”等伦理观念的影响。未出嫁以前,土家女子的命运掌握在父母手里;出嫁以后,命运多被“夫权”主宰。土家女子表示对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不满,结婚时以“哭嫁”的形式来诉说自己内心的悲痛和无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妇女权益保障措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保障权益法》等,这些法律法规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维护了妇女的主体地位,“男女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传统婚姻在良好的社会风尚引导下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性,为了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鄂西南土家婚俗文化出现变迁在所难免。
(二)外部原因
第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打工者与日俱增是造成土家族传统婚俗变迁的主要动因。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舍米湖村与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土家人走出寨子,到周边县、市打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已经成为舍米湖村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据调查,外出打工者年龄多在18~50岁左右,这一群体思维活跃、身体适应能力强。他们到新的生活、工作环境后,面临的是不同地方的人们,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群体之间要达成一致,必须各自做出改变,按照城市的主流文化行事。此外,不同地方的人到一个新的社区里生活,组成一个新的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文化上的交流、切磋,先进总是不断战胜落后。当舍米湖村民在这一群体中出现文化不适应时,他们会竭力做出改变,不断融入新的环境。对于打工者而言,适应一套新的文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起初表现为文化的渐变,随着量的积累,就演变为质的突变。因为人类文化史的演变,不仅表现为渐变,而且表现为突变[9]398-403。这一变迁一旦发生,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对于已婚男女来说,他们把自己在城市里习得的新文化带到村里,向家人(老人、小孩)、村民传播。其二,对于未婚男女来说,他们的婚恋观会越来越接近城市的操作方式,不管是择偶的方式、标准,还是通婚的范围,传统的观念体系直接被打破。这两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促使生源地村寨婚俗文化体系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户籍制度的改革和人口流动政策的不断放宽,这一变迁趋势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
第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随着电视、网络、媒体、报刊、电话的普及,“地球村”的出现使舍米湖村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封闭的状态,它与中国乃至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以前,鄂西南土家族人民主要通过报刊了解外面的信息,如《人民日报》《湖北日报》《恩施日报》《来凤日报》等。报刊是促使鄂西南土家族本土文化变迁的首要原因,如今也依然在发挥作用。整个20世纪,电视对人类的影响意义重大。毕竟电视作为20世纪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伟大发明之一,它是一种综合性、多功能的信息传播工具,以数字化的形式向人们传播新闻、广告、综艺、电视剧等影像记录。通过收看电视节目,村民不断模仿、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元素,随着量的积累,外来强势文化逐渐成为主流,本土文化开始不断渗透和融入到现代文化(强势文化)中,促使本土文化的变迁。因此,电视是促使鄂西南土家族本土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
然而,网络媒体是促使鄂西南土家族本土文化变迁的又一重要原因。21世纪以来,网络媒体开始成为主流,与电视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网络是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为一体的新型传播媒介,具有超越时空、快速便捷等特点。随着“网络全球化”或“信息全球化”时代的来袭,鄂西南土家族人也开始打网络电话,上网络电脑,玩网络游戏、QQ,刷网络微博、微信等,如今的鄂西南土家族人已进入全网络化时代。比如,舍米湖村村民E通过网络电话每两天与深圳打工的丈夫联系;村民J每天用微信与在武汉上学的女儿聊天等。可以看出,网络交际在村民中已逐渐常态化。此外,媒体成为宣传鄂西南土家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平台。在舍米湖村,先后有来凤电视台、恩施电视台、湖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记者采访和宣传土家族传统文化。通过媒体,舍米湖村民与外界在文化上有了互动,不管是土家族摆手舞、过赶年,还是土家族传统婚礼都在时代发展过程中发生变迁。
总之,这里通过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力图阐释鄂西南土家族传统婚俗变迁的全貌。通过文献研究,我们发现:第一,土家族存在诸多古老的传统婚俗,但对今天仍有影响的是以神话传说流传的“血缘婚”和土司统治时期的“骨种婚”或“姑舅表婚”,它们在鄂西南土家族婚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二,土家族婚礼仪式隆重,而“抢亲”和“哭嫁”最能反映鄂西南土家族女性地位和婚姻性质,二者表面上具有表演性质,实质上反映出土家族历史上普遍存在“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的社会心理,以及“包办婚姻”笼罩下的婚姻常常伴有压迫、奴役的色彩,这两种仪式反映出新娘普遍存在对社会现实不满的现象。此外,通过田野调查,以1949年前后为时间节点,对“舍米湖村”土家族婚礼进行前后的比较研究,发现以“舍米湖村”为代表的鄂西南土家族传统婚俗在婚恋、仪式以及通婚范围等方面都出现了急剧的变迁,且这一变迁多为鄂西南土家族人自然选择和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我们认为,传统文化变迁多含有进步的因素。在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应持辩证的态度,积极肯定和弘扬传统文化变迁中的合理因素,也要大胆否定和摒弃其消极的一面。
[1]彭林绪.土家婚姻习俗的嬗变[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42-50.
[2]林耀华.凉山夷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45.
[3]陆游.老学庵笔记[M].杨立印,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24.
[4]闫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53.
[5]杨建平.鄂西土家族民俗文化变迁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1.
[6]威廉·费而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与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
[7]赵情学.鄂西南舍米湖村土家族传统婚姻仪式当代文化变迁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09.
[8]陈廷亮,彭南均.土家族婚俗与婚礼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53.
[9]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398-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