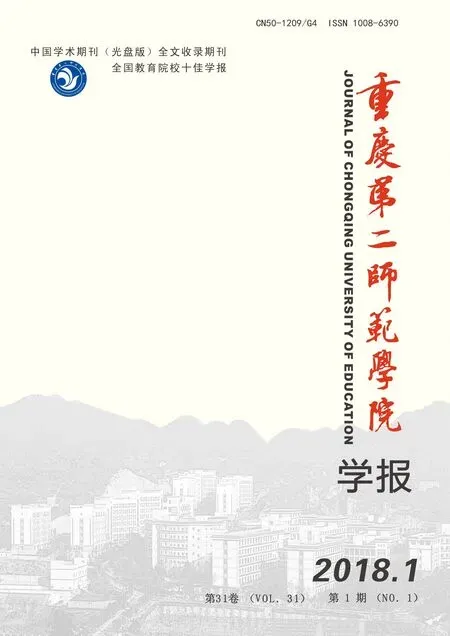从文学史书写看《西厢记》的接受史
2018-03-28陶文晔
陶文晔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1,同理,我们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史”。文学史书写者在对大量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建构出书写者视域下的文学史。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书写者不仅会有强烈的还原和再现文学发展历史的愿望,而且会试图认知与评价历史上的文学现象。正如新历史主义学者海登·怀特所认为的,“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如何组织一个历史境况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事件相结合”[2]。由于书写者身处不同的历史时代,其认知与评价历史现象的价值要求,必然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而作为各个时代文学史的书写者,其对文学的接受史也自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本文借鉴秦军荣《文学史书写与〈窦娥冤〉的经典化》中的分期法[3]61-67,通过梳理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轨迹,考察其中有关《西厢记》叙述话语的演变,从而发掘作为文学接受者的书写者对于《西厢记》的独特接受史。
一、1904年至新中国成立前
(一)1904—1914年
我们先看文学史书写的前十年,这一阶段文学史的代表性版本有:1904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11年黄人《中国文学史》、1914年王梦曾《中国文学史》。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书写对于戏曲持有三种态度。
首先,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视为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由于处在文学史书写的初期,林传甲对文学的定义仍有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印迹,其文学史的编排体制,仍循“籀篆音义之变迁,经史子集之文体,汉魏唐宋之家法”[4]1。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主要指的是文章,对于小说、戏曲则持贬斥的态度。 “金元之杂剧,宋元之南戏,发展到明清时期的传奇所唱的北曲、南曲,虽都曾有幸进入过宫廷,但在清代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尚被贬为‘南北曲非文章之正轨,故不录其词’。”[5]因此,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受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其十四篇十六节之标题就是“元人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并认为“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4]148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并未直接提及《西厢记》,只是在贬斥戏曲时有“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4]148的说法。由此可见林传甲对《西厢记》一类戏曲的态度,即认为它们是“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4]148。
其次,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虽未对戏曲表现出刻意贬斥的态度,但从其叙述中仍然不难发现尊文抑曲的倾向。例如,其文学史的编纂以文为主,将小说、诗词、戏曲等作为附庸。王梦曾认为,曲之兴盛是由于“金元以蛮族入据中原,不谙文理,词人更曲意迁就,雅俗杂陈而曲作矣”[6]72,即曲之产生与兴盛是由于“蛮族”文理不通,词人不遵守文理规则而刻意迁就,使文体陷入混乱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他又提及“金末董解元作《西厢记》,为北曲开山”[6]72,并将王实甫列入元代擅长作北曲且最有名者。由此可见,王梦曾虽然仍恪守以文为主的传统文学观,但在对戏曲的态度上则体现出不同于林传甲的一面。
再次,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也孕育出更具开放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一例。在这部文学史著作中,黄人“‘破成格而广取之’,远远超越传统文学的藩篱”[7]6,戏曲这一经常被忽视的文体得到应有的关注。但囿于历史与文学分野,“然历史所注重者,在事实不在辞藻”,[7]2黄人对于文学史的叙述更偏重于对文学历史真实的叙述,绝少自己论说的部分,《西厢记》也只是在“金元人乐府目”一节中存目。
综上,在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国人于探索自强的道路上踽踽独行,反映在思想史上,传统经史子集式的学科门类已无法适应大量涌入的新知识的分类。“学者们在传统与现实的双重焦虑和紧张中,对经典进行着重新诠释试图重新发掘属于自己的知识和思想资源。”[8]490而这种回应所带来的后果则是“在某种意义上引起了后来知识与思想的巨变,并促使传统之学向现代学科体制中的文学、史学和哲学转化与分化”[8]490。
(二) 1915—1949年
这一时期文学史著作大量涌现,其中关于戏曲的评论与认知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1915年出版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将元杂剧作为元代的代表文学样式,认为杂剧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峻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1。这就从内容和文辞上给予元杂剧以高度评价,对后来的文学史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傅斯年说:“必此类书出于世间,然后为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与社会史者,有所凭借。”[1]164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版),葛遵礼的《中国文学史》(1921年版),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1926年版),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1928年版),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年版),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版)等,在编写体制上皆按时代进行文学分期,明显受到王国维的影响。谢无量在《中国大文学史》中认为,“宋画元曲千古无匹”[9]卷九第十八章14;刘毓盘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戏曲“虽出于文人游戏之所为而粉墨登场贤不肖皆有所惩劝,季札观乐而知其国之盛衰即此意也”[10]50,故戏曲亦有观盛衰、美教化、厚人伦、移风易俗之作用;顾实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认为,“使元之文学见重者,杂剧传奇小说之轻文学,确为中国文学开一生面者也”[11]254;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更是认为,“因这种杂剧的产生,在中国的戏曲史上,成立了一个新纪元”[12]445。这表明文学史书写者对戏曲的态度已发生巨大的改观,以《西厢记》为代表的杂剧开始被认定为元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
其一,基本确立了《西厢记》在元代杂剧中的扛鼎地位。顾实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认为,“元之传奇,北曲有《西厢记》,南曲有《琵琶记》,此外无甚著闻者焉,然以此二者,而元之传奇可谓九鼎大吕之重矣”[11]257,元曲之所以见重于世,是因为有《西厢记》和《琵琶记》这样的经典作品。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将王实甫列为元曲五大家,称“他的《西厢记》,声誉在一切元曲之上”[13]142。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亦称“《西厢记》是元曲里面最伟大的作品”[14]227。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将王实甫列为元代百余位作者中地位较高的六家之一,并指出其作品“以《西厢记》为最”。
其二,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书写者对《西厢记》的作者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在之前的文学史中,书写者并未过多在意《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如王梦曾认为“王关足成《西厢记》”,[6]72即《西厢记》是由王实甫和关汉卿共同完成的;黄人则将《西厢记》列在王实甫名下,并未深入讨论。但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中,《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主要观点有:一是王作关续。如赵景深、郑振铎、胡云翼就持此观点。二是王实甫作。如谢无量、葛遵礼、刘毓盘、顾实、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均持此种观点。他们对王作关续之说进行辩驳,认可涵虚子《太和正音谱》所谓“王实甫十三本以《西厢记》为首,汉卿六十一本不载《西厢》”[9]19,认为所谓的关汉卿续补《西厢记》之说实际上是明清之际被窜改的,并非事实。
其三,提出《西厢记》的主题乃写 “男女离合”之说。这一主题呼应了五四之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中的感伤情调。“感伤”作为五四之后个性精神解放的一种形式,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这类作品大都以男女之间的恋爱为主题,情爱在作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种感伤情调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中,而且形成了一种文学思潮,因此在文学史书写中也必然有所体现。就《西厢记》而言,一些文学史认为《西厢记》的主题就是表现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如顾实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提出,“作者之意,写男女离合之情绪”[11]261-262。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西厢记》以五剧二十折的大篇幅写一个“恋爱的喜剧”。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认为,《西厢记》所写乃“苦于恋爱困于环境的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的浪漫故事”[12]445。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史书写者对这一主题仅仅是一笔带过,并未进行深入剖析。此时的文学史围绕男女之情的主线提出《西厢记》的主题说,与今日之观念并不相同。
其四,关于人物形象之分析。顾实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认为,张生不过一“轻薄少年”,不足为莺莺配偶,而莺莺则是“出生贵家”、“服从严格道德之意志”的女子,老夫人是常夸门第之高者,红娘是生成贱骨而颇有侠气之风的侍婢;郑振铎版文学史将莺莺看作久困于礼教之下由沉默不语到热情奔放的少女;刘大杰版文学史则将红娘看作句句话都入情入理且经验丰富的婢女。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文学史书写者对《西厢记》人物形象的多样化解读,显示出其书写态度的自由。文学史书写者对《西厢记》女性形象的关注,体现了在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传入之后,中国思想界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以及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寻求女性解放的依据所作的努力。
其五,对《西厢记》文辞的肯定。《西厢记》的文辞虽历来为世人所重,但是在初期文学史书写者中仍持贬斥态度,认为是浓艳夭丽之至的淫亵之词。这一时期文学史书写的关注点则聚集到了《西厢记》的文辞上,将其从淫词艳曲的小道之流提升到了雅文学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或引述《太和正音谱》道实甫之词“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9]19,或称其为“一纸绝妙的抒情诗曲,非出之于一位大诗人之手不办”,或以宋词人喻实甫,认为实甫乃“晏几道秦观之流亚”,[15]211其风格“雅艳婉媚”等,充分肯定其婉约风格。
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书写对《西厢记》的态度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的变化。在西方文学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交互影响中慢慢探索出自身的道路,由此也体现出这一时期自由之思想影响下文学史书写的多样化。不过,也正是由于受西方观念的影响,文学史书写常常比附西方之观点,突出强调所谓自由精神之追逐和个性解放之努力,未免使《西厢记》的人物与主题抽象化,未能发掘中华文化所具有的深刻内涵。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书写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向。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和实践占据主导地位,“它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6]78。在这种大环境下,文学史书写与政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增强。其中,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主要有: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57年版),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1964年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中国文学史》(1979年版)等。
(一)矛盾说的明确与发展
这一时期,文学史书写者紧紧抓住“矛盾”这条线索,以文学反映各种社会矛盾为切入点分析和解读文学作品。
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57年版。这一版本与1932年的版本不同,正可作为反映不同时期文学史书写转向的最佳例证)认为: “元代的杂剧……大多能正确反映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也真实写出了当时人民的苦难,和他们英勇不屈的斗争。”“历史上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相互关联着,在元代他们结合得更为紧密,而种族矛盾显得突出。”[17]171陆、冯据此提出,作者以矛盾来推进《西厢记》高潮的纵向演进,“崔母悔婚是封建与反封建的矛盾初次爆发,是全剧的第一个高潮”,而“书斋幽会及拷问红娘是矛盾的再度爆发,是全剧的第二个高潮”,[17]180作者通过把握矛盾的发生和发展结撰全篇。而游国恩版《中国文学史》进一步提出,《西厢记》的两条线的矛盾冲突同时且交错进行:“崔张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有两条相互关联的情节线索,一是崔、张、红对老夫人的矛盾斗争;一是崔、张、红三人之间的误会冲突。”[18]209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中国文学史》中提出,《西厢记》这部以爱情为题材的杂剧的主要矛盾就是崔、张二人“出于自由意志两相情悦的爱情”与“封建婚姻制度”之间的矛盾。[19]741由此观之,《西厢记》无疑就是以矛盾的产生、发展、激化和最终的调和为主线来创作的。
与前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矛盾说”无疑是新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深刻影响。此一时期文学史对《西厢记》的分析与解读体现了其宏观性,即从总体上把握文本,在纷繁复杂的故事情节中提取线索和矛盾,对整个文本的解读更加全面。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文学史书写以“矛盾说”结撰全篇,把人物形象简单地图解为某一阶级利益的代表,将原本相互交错的人物关系简单对立起来,减损了人物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有其不足之处。
(二)反封建主题的确立
与前期文学史将《西厢记》的主题定位于“叙写男女离合之情”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书写确立了《西厢记》的反封建主题。
陆侃如、冯沅君1957年版《中国文学史简编》提出,《西厢记》的思想性在于:“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反对借金钱或势力强迫成功的婚姻,反对扼杀青年男女真挚的爱。”[17]179这一表述虽不足以见到其中强烈的反封建思想,但是却开始体现出反对一切不合理事物的倾向。而游国恩版《中国文学史》则明确提出,从《董西厢》到《王西厢》,“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也更鲜明了”[18]202,认为王实甫是“以同情封建叛逆者的态度”“歌颂了莺莺和张生为自由结合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18]202可见《西厢记》反封建主题在游版文学史中已经得到确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中国文学史》,进一步将《西厢记》的戏剧冲突归结为“维护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封建势力和要求自由表达爱情、自由结合的青年一代的冲突”[19]742,从而充分肯定了追求自由的青年一代反对封建制度的系列努力。
可见,鲜明的反封建主题在这一时期占据了《西厢记》文学史书写的上风。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主题解读是在用20世纪的观念揣摩元代社会的现实,脱离了王实甫创作《西厢记》所处的历史时代,缺乏一定的历史感。
(三)红娘形象的突显
在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切文学活动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目的”[16]79。突显人民群众的力量显然成为文学作品中所要关注的重点,而红娘在促进崔张二人的美满结合中所作的努力无疑是人民群众力量的彰显。由此,红娘不仅成为本剧的主要人物,同时也被看作正义的化身。
陆侃如、冯沅君版文学史认为,红娘“富于正义感和斗争性”、“在她身上看不出礼教的痕迹”[17]179;游国恩版文学史认为,“红娘是剧中另一主要人物……有着一种受压迫受奴役者的是非标准和从这种是非标准出发的正义感”[18]205;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版文学史认为:“作者出色地刻画了她身上某些劳动人民的品质……从而使她成为剧中最吸引人、光芒四射的人物形象。”[19]746
如果说从《会真记》到《西厢记》的人物重心在转移,那么世人对人物的兴趣亦在转移,这种转移实际上代表着某个时代的观念。唐、宋、元各有其代表性的文学样式,从诗词曲产生的趋势来看,其受众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下层,而创作者上至文人士大夫下到混迹于勾栏瓦肆的文人士子,他们关注的视角也由家国天下转向了底层民众,而所使用的语言也逐渐趋向于通俗白话,并逐渐增加了市民趣味,反映下层民众的勇敢智慧、乐于助人的美好品质。这一时期对于红娘形象的突显,不仅呼应了当时提倡人民大众之文学观念,同时也呼应了历史洪流中文学观念转型的必然趋势。
无论是矛盾说、反封建主题还是红娘形象的突显,均体现出文学史书写的鲜明时代特征,对《西厢记》的评价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作为过渡,以此观照20世纪70年代后的文学史书写,不难发现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既有延续性又有创新性。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
改革开放迄今,“对审美的理想诉求,加上外来观念的冲击,最终促成了文学史标准的重大变革”[20]65, “重写文学史”一度成为最响亮的口号。“他们主张文学是审美的而不是社会的、政治的,呼吁文学观念的变革。”[20]65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文学史书写在新时期出现了新气象。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以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1996年版),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1998年版),袁行霈《中国文学史》(1999年版),袁世硕、张可礼《中国文学史》(2006年版)最具代表性。
(一)对文学史书写传统的延续
所谓对上一阶段传统的延续,主要体现在对矛盾说和反封建主题说的延续。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西厢记》的矛盾说开始确立。各版文学史均认为,《西厢记》是以矛盾推动和展开故事情节的。游国恩版文学史还总结出了两条相互关联的矛盾线索。20世纪80年代至今,袁行霈和袁世硕、张可礼版文学史延续了这一说法,即老夫人与张生、莺莺、红娘一条,崔、张、红三人之间一条共两条矛盾线索。反封建主题的延续则主要表现在郭预衡版和袁世硕、张可礼版文学史中。如袁、张文学史认为,王实甫《西厢记》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更突出了它的反封建主题”,[21]565同时两版文学史都将崔、张二人为自由结合所作的努力视为封建叛逆者对以崔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反抗。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文学史书写是对传统的延续。
(二)对文学史书写的创新
进入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思想界开始从过去单一的阶级斗争观念中解放出来,进入了比较自由和开放的环境,换言之,原先带有浓郁时代特色的思想界单一的阶级斗争观开始被多元的语境所取代,这也为重新解读《西厢记》提供了更多话语空间。
关于《西厢记》主题的解读更加丰富了。除了反封建主题,章培恒、骆玉明版文学史提出,《西厢记》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作者很少从观念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22]39。如果细细品味书写者此处的态度,我们不难感受到,原本辞色锋利的主题已经被书写者策略性地融化为温和的面目,没有此一阶级对另一阶级金刚怒目式的反抗,而是人性生活化的表达,也就是书写者所说的“把反封建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22]39袁行霈版文学史则提出了“情”的主题,指出《西厢记》“愿天下有情的终成了眷属”,男女之间只要有“情”,就应该同偕白首,“而一切阻挠有情人成为眷属的行为、制度,则应受到鞭挞”[23]227。在这里,崔、张二人所作的种种努力无疑成了对他们之间的“情”的养护,而此前的反封建主题也让步于此处的“情”。
关于红娘形象的分析也出现了新意。此前,红娘被认为是《西厢记》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之一,是突显劳动人民力量的出色代表,受到高度赞扬。章培恒、骆玉明版和袁行霈版文学史则提出不同看法。如章培恒、骆玉明版文学史认为,作为婢女的红娘能将周公孔孟讲得头头是道,显示出人物形象理想化的成分;而袁行霈版文学史则指出“王实甫让红娘经常把道学式的语言挂在嘴边”[23]235,同时延续他提出的“情”的主题,认为红娘“不仅是见义勇为,而且是缘情反礼”,“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情’的自觉追求的态度”[23]236,均显示出这一时期的创新性。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体现了书写者在反思传统的基础上,开始理性地面对文学,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
四、结语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史书写,无不受到书写者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审美思潮的影响。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中,关于《西厢记》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以及遣词造句等方面的解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中的一些解读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文学史书写应该将文学作品还原到其作者所处的时代,紧密结合各时代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进行审美观照。就《西厢记》而言,其作者王实甫处于民族矛盾突出的元代,面对理学萧条,世俗伦理错乱的局面,他试图以作品中的人物为载体,以主人公对情感的执着追求、突破与超越来突显情的主题,并以人的情感为依据重建混乱的社会伦理。这是我们立足于当代的文学史书写者所应当关注的课题。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643.
[3]秦军荣.文学史书写与《窦娥冤》的经典化[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61-67.
[4]林传甲.中国文学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5]时白林.黄梅戏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2.
[6]王梦曾.中国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2.
[7]黄人.中国文学史[M].杨旭辉,点校.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
[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30.
[10]刘毓盘.中国文学史[M].上海:古今书店,1924.
[11]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1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13]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14]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M].上海:北新书局,1947.
[15]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M].上海:开明书店,1932.
[16]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7]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18]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19]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0]管才君.文学史书写:从政治向审美的历史变迁[J].泰山学院学报,2015(2):64-69.
[21]袁世硕,张可礼.中国文学史: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2]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2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于 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