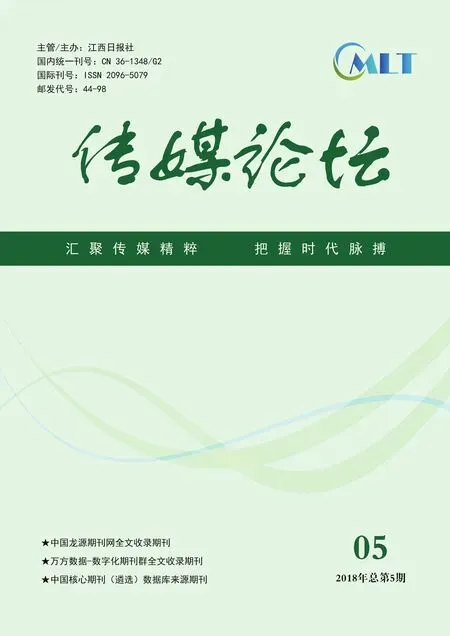电视纪录片创作技巧和价值的探究
——论《人生七年》与《零零后》的关联与不同
2018-03-28孟悦
孟 悦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江苏 扬州 225100)
2017年8月20日至24日,五集电视纪录片《零零后》每天晚上在央视播出。十年的跟踪拍摄,摄像机里孩子的成长在带给观众感动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关于诸如个性与制度、应试与素质、留守与留学、青春期与亲子关系、独生子女与二孩政策等话题的探讨。这部纪录片与1964年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公司历时近50年拍摄并播出的八集电视纪录片《人生七年》相比,既有关联,也有明显的不同。
一、创作理念
《人生七年》(Up Series)由麦克·艾普特(Michael Apted)执导,这部纪录片的创作灵感来自于耶稣会的一句格言“孩子七岁后就是一个大人了”。这部纪录片从1964年开始拍摄,拍摄的对象选取了14名来自英国不同社会阶级的孩童,这些孩子有的来自于贵族学校,有的来自于只有一间教室的乡村小学,有的是黑人,有的是白人。拍摄历时长达近50年,每七年拍摄一次,每次拍摄一星期,一直到2012年播出了这群孩子的56岁篇。这部纪录片历时之久让人震撼,但是这部片子却不是为了感慨年华易逝,它的创作理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揭示、批判英国的社会阶级固化现象,探讨阶级出生对人的成长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英国的社会阶级是一直存在的,这也一直影响着英国的社会结构。在艾普特看来,所存在的社会阶级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出身于底层的优秀的人才不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机会,所以出现“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的现象。艾普特的社会阶级理念一直贯穿于整个系列片的拍摄过程中,参加拍摄的英国小孩背景各异,这就与中国的《零零后》完全不一样,在《零零后》中的十来位主人公,都是来自北京的中产阶级家庭。艾普特用他几十年的追踪拍摄证明了他当初的社会学命题。在14个背景各异的孩子中,像约翰和安德鲁这样的富人家庭的孩子,在七岁时被问及以后的理想时,就很明确要求就读英国最好的学校和进入上流社会,几十年后,他们进入了剑桥、牛津,并且成为了律师和政客,没有偏离富人该有的人生轨迹;而像西蒙、杰西这样的底层孩子,按部就班的经历了辍学、离婚、失业。当然,中间也有一位孩子是个例外,成为了打破自己命运天花板的底层社会漏网之鱼。
(二)揭示除了阶级以外决定人生的重要因素
《人生七年》的初衷是为了揭示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但是该纪录片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七年的拍摄以后,对于阶级的探索逐渐淡却,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浓厚的人文情怀,这从纪录片后期越来越关注主人公个人的故事可以看出,导演在探索生命的意义。从出生、教育、事业、家庭、婚姻这几个角度出发,艾普特试图去探究是什么造就了一个人的人生。最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影片来感受导演的探索结果,那就是:婚姻和教育。唯一的命运漏网之鱼,从社会底层到最后能够当上大学教授,就是因为他在学业里的不懈努力。
《零零后》的总导演是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的主任张同道。该纪录片共有五集,拍摄历时十年。最早决定拍这部片子是因为自己家的孩子。张同道在孩子四岁的时候开始拍摄他,在一次和孩子的互动中他忽然明白也许自己的教育只不过是凭借经验在对孩子进行粗暴的干预,于是他很想打开孩子与成人截然不同的世界。《零零后》的创作理念:引起社会关于个性与制度、应试与素质、留守与留学、青春期与亲子关系、独生子女与二孩政策等话题的探讨:这是关于一群中国“00后”孩子的成长故事,或许也是关于中国未来的寓言。片中的主人公都是来自于北京中产阶级,也许有人说选择的样本没有做到全方位覆盖,但是其实从这些孩子成长的过程是可以看出现阶段“00后”在关于教育问题上面的普遍问题的。
这就引起了我们关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思考。在放养天性和规范约束的二元对立中,我也曾迷信自由的力量。但问题的核心在于孩子并非二元对立的两种模式,而是星斗一样个个独立,熠熠生辉。也许,错的并不是某一种教育模式,而是这种教育模式与儿童性格是否匹配。不管学校课堂还是培训班上,性格外向的孩子总是受到嘉奖,乐观开朗、具备领导力被界定为优秀儿童的典范。导演张同道原本坚持自由放养的教育观,在这十年里,同样发生了变化。每个孩子的基因和生长环境不同,所以适合的方法也不同,没有最好的教育方法,只有最合适的教育方法。
二、创作手法
(一)两部片在创作手法上的相同点
1.向未知取材、截取生活片段与尊重生活原貌
这两部纪录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导演是生活,在导演选取了主人公以后没有人知道故事的走向和孩子们人生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有的只有一个理念。导演有一种超前的思维去策划和拍摄,也许零散的对生活的记录在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时间慢慢累积,这些记录都成了宝贵的资料。编导的慧眼穿透力、超前的思维决定了片子可以走多远。在拍摄时,导演也是相对克制,尽量不去干预和介入,而是忠实于生活的原貌,这是两部纪录片相同的地方。
2.冷静客观叙事,注重细节把握
《人生七年》整个纪录片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在扮演“上帝之眼”客观叙事的同时,艾普特十分注重细节的把握。同样的,在《零零后》中也存在着很多细节,当锡坤还在读幼儿园的时候,他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被记录了下来,他的调皮和恶作剧的细节,这些细节的记录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他长大后那么喜欢探究“物”的空间,包括他的妈妈在他进考场以后脸上的每一个神情,都做了细节的记录,把中国式家长对孩子的爱刻画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思考当代中国的教育问题。
(二)两部片在创作手法上的不同点
1.叙述手法
《零零后》更加体现出一种人文的关怀,分别讲述每一位主人公的故事,每一位主人公单独成为一集,在一集里面叙述十年来主人公的变化与成长,透露着对主人公的人文关怀。但是《人生七年》的叙述手法并不是一直这样,从纪录片一开头,艾普特采用的是对位的形式剪辑孩子们的故事,将不同的孩子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反应和不同回答剪辑在一起,从而凸显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阶级的差异性。在这一阶段,编导的焦点聚焦在了社会上,主人公只是导演为了验证他当时关于人类学的一个假设,直到到了《人生28年》才开始发生转变,艾普特开始分开关注每位受访者的故事,人文气息越往后越浓厚,逐渐以个人故事为主,因而更加打动人心。
2.拍摄时间间隔
《零零后》从2006年开始连续拍了十年,中间没有一年是间断的,这就让观众对于一个主人公性格的了解比较全面,不会出现断层。但是《人生七年》每个七年拍摄一次,每次拍摄七天,这就导致我们无从知道这七年间发生了什么,而对于仅仅通过那七天来判断一个人的生活,这样就比较片面。这也是关于《人生七年》价值意义受到争论的所在之一。
3.是否存在开放的话语结构
《人生七年》弹性包容各种批评质疑,不刻意回避,在那群七岁的孩童长大后对于他的问题的反感和抱怨如实呈现。最具代表性的画面是杰西在49岁时对于导演组的指责,艾普特谦虚地承认她说得没错。而《零零后》历时十年的镜头中竟然没有这样的镜头。
三、 价值意义
正如巴拉兹赋予纪录片的伟大使命“用画面记录人类历史的使命”,《人生七年》和《零零后》让我们感受到:
(一)唯有纪录片能够记录时光
人类是唯一一个知道自己生活在时间里的生物,但是时间却又来无影去无踪,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以后,我们拿什么证明自己曾经经历过那些时光——唯有纪录片。而在别人的影像里,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在《零零后》播出以后,很多70后和80后会跟着镜头去思考自己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得与失。
《零零后》打开我们了解孩子的窗子,像镜子一样映照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是在帮助还是在伤害。这也是纪录片的意义所在。我们从《人生七年》看到谁通过努力成为中产阶级,谁在破旧的社区里生养儿女,谁在慈善中寻找生活的意义,谁在自我否定中不断流浪……从幼童到少年,从少年到婚姻,从婚姻到育儿,又从儿辈到孙辈,隐含着每个人生命中的缺憾和挣扎,在自己的轨道上努力生活,安心老去。人生的足迹如此逼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些孩子的人生足迹,其实也是我们的足迹。没有比从别人的影像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生命中那些逝去时光的美好或忧伤更令人百感交集的了。
(二)知识和舆论导向
《人生七年》告诉我们,决定我们人生走向的有很多因素,除了阶级还有婚姻、教育等,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也是可以冲出束缚的,同样也让我们看到社会阶级的存在无疑不利于国家的发展,社会资源被浪费……这部纪录片传达了很多诸如此类的知识。
《零零后》让我们在别的孩子成长影像里面思考我国目前关于教育和关于社会存在的问题,就像一场风暴引起社会的反思。让我们对现有的教育模式提出拷问,引起社会关于个性与制度、应试与素质、留守与留学、青春期与亲子关系、独生子女与二孩政策等话题的探讨,让我们反思真正的教育应该从尊重开始。
四、结语
纪录片就像“镜子”一样,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还是还像锤子一样,主动干预现实,这一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笔者通过分析《人生七年》和《零零后》之后,发现中外纪录片在很多方面存在很多的不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纪录片呈现出记录理念“多元融合”的情态,这表明我国的纪录片发展态势越来越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