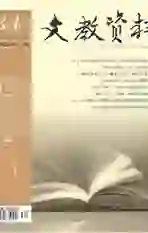在沪高校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状况调查
2018-03-27杨军红
杨军红
摘 要: 该研究在Horwitz等(1986)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基础上编制在华留学生汉语课堂学习焦虑量表,以此作为研究工具调查在沪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焦虑状况,并探讨有效的课堂教学辅助措施,创建在沪留学生汉语学习支持体系。调查发现,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来华时间长短等个人因素与外语学习焦虑没有显著相关,但是不同文化群体留学生的汉语课堂学习焦虑表现呈现明显的文化差异。中国教师的课堂教学风格和汉语课堂活动设计影响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焦虑。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构建学习者共同体,降低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焦虑和不适感,同时对外汉语教师要提高跨文化交际敏感性,注意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汉语学习中的特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的的自信心。
关键词: 汉语学习焦虑 社会支持网络 同伴压力 学习者共同体
1.外语焦虑的研究现状
1.1外语焦虑的概念界定
外语焦虑(foreign language anxiety)在外语课堂上很常见,指在学习或使用第二种语言或外语时感到的不安、忧虑、紧张和恐惧。Horwitz(1986)等学者将外语课堂焦虑定义为:“一种与课堂语言学习有关,产生于语言学习过程中的独特而复杂的自我认识、信念、情感及行为。”
Horvitz等人(1986)观察到,当人不得不使用另一种自己不擅长的语言时,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沦落到一种孩子气的状态,这是一种令人尴尬的状况。外语焦虑可能会造成类似于大脑短路(short-circuit)的情形,处于焦虑状态的学生会“学不进去”,会的也忘记,难以正常发挥应有的水平。Young(1992)提出:“语言焦虑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结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研究。”
1.2外语焦虑分类
对于学习者来说,语言焦虑是对自我表现的恐惧。在同龄人面前从事外语练习活动,有可能会出错或出现尴尬,给他们带来不适感。Horwitz(1986)将焦虑分为交际焦虑(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考试焦虑(Test anxiety)和负评价焦虑(Negative evaluation)。交际焦虑,也译为沟通焦虑,指“对与他人的交际或尚未发生但预期会有的交际的忧虑和恐惧”(钱旭菁,1999;Yukie Aida,1994);考试焦虑是一种表现焦虑,指“测试时对自己的表现可能不符合要求的忧虑和恐惧”(Yukie Aida,1994)。钱旭菁(1999)研究发现,考试焦虑方面美国人和日本人没有显著差异。在大学里,美国人注重成绩、等级和平均积分点,因此美国人对考试表现出较强的焦虑。负评价焦虑是担心导师、同学或其他人可能会对他们的语言能力进行负面评价,害怕显得笨拙、愚蠢或无能。“负评价”不仅会造成学习者语言上的自信心下降,而且自我概念有可能受损(Tsui,1996),抑制学习者自信地努力交流。还有学者(Alpert& Haber)把外语学习焦虑分为促进性焦虑(facilitating anxiety)和障碍性焦虑(debilitating anxiety)。促进性焦虑能使学习者产生学习动力,对学习有促进作用。一些研究表明,一定程度的焦虑可能对学生是积极的。Hadley,Terrell和Rardin(Young,1992)认为学生应该经历一些紧张以产生学习的欲望,因为如果焦虑的程度没有给学生带来任何挑战,那么他们学习上的进步就很可能会变慢或没有进展。
1.3影响留学生汉语课堂学习焦虑的因素
长期的外语学习焦虑有可能造成学生注意力分散、健忘、反应迟钝、学习兴趣降低,自信心下降等。从目前看,影响外语课堂学习焦虑的因素主要有个人因素、教师因素和文化环境因素。
1.3.1留学生的个人因素
Tallon(2009)指出,外语学习者的个人差异,包括个性特征、认知能力、学习风格、元认知差异、学习者所在的社会情境和学习者个人的情感因素对外语学习者的学习过程都有影响。钱旭菁(1999)运用“外语课堂焦虑等级列表”详细调查了留学生汉语焦虑感与学习者的性别、年龄、国别、学习时间、自我评价、期望值、是否为华裔、学习成绩等指标的关系。钱的研究发现焦虑感和学习者的性别和年龄及汉语成绩都没有明显的关系,与口语成绩呈中度负相关。即焦虑感越強,口语成绩越差。关于焦虑感和学习时间的关系,MacIntyre和Gardner认为,“随着学习经历的增加和水平的提高,学习者的焦虑感会有所减弱”(Yukie Aida,1994)。但是钱旭菁(1999)的研究发现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其焦虑平均值并没有显著差异。她认为学习时间有长短,汉语水平有高低,但焦虑感没有显著差别。
张莉、王飙(2002)的调查发现留学生的焦虑值与被试的口语成绩、HSK听力成绩和HSK总成绩的相关性显著。研究发现被试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的焦虑感越强,其口语、听力及语法水平越低。本项研究发现上汉语课时,多达81%的被试感到焦虑不安,79%的被试注意力不能集中。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大部分更重视汉语听说能力,但焦虑感阻碍了他们这两方面能力的提高。这项研究只是笼统反映了留学生的汉语课堂学习状况,对留学生的个性差异、课堂教学风格、教师的教学方式等没有进行研究。
1.3.2教师作为课堂学习环境的主要决定因素
教师的教学目标不能仅仅提供可理解的语言信息输入,还要扫除学生的各种心理障碍。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人的认知活动总是伴随着一定的情感因素,当情感因素受到压抑甚至抹杀时,人的自我创造潜能就得不到发展和实现,只有对学生的内心世界持尊重和理解的态度,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陌生或意想不到的教学方法和教师行为会引起学生的焦虑。来自一种文化(或区域亚文化)的学习者认为“理所应当”的做法可能会给来自另一个文化群体的学习者带来压力和焦虑。作为引起课堂焦虑的关键因素,Cohen& Norst(1989)认为课堂发言极易使学生面临“威胁”,因为学生被要求用还未掌握好的语言当众表露自己的观点,需要冒险挑战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旦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就会产生挫败感和焦虑感。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教师的纠误活动是造成学生外语课堂学习焦虑情绪的重要因素。教师苛刻而生硬的纠误方式会引发学生的焦虑感。许多中国教师认为,在课堂上学生对教师有一点畏惧感有助于强化课堂教学效果。这种观念势必使他们的教学态度比较严厉,教学要求比较严格。这会给学生带来比较大的压力, 增加学生的焦虑感。
1.3.3文化环境因素
正如Oxford(2005)所指出的,焦虑总是在一定的语境和文化规范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文化的课堂对学生的期望不同。例如,上课时不说话可能表示对老师的尊敬,但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会被理解为是学生焦虑的一种反应。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国语境中,知道如何回答老师问题的学生可能会因为害怕被同伴认为是炫耀而选择不回答问题。在进行外语学习焦虑研究时,要考虑广泛的语境因素,如关于课堂情境的文化规范和行为,理解和确定正常的行为和相对焦虑的行为。
Kirmayer(1991:22)指出日本人的社会化过程被灌输强烈的相互依存和为了别人的感情的责任感。相反,在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具有首要地位,不怕得罪或者冒犯他人,自我的社交表现较少关注他人,焦虑也较少。宋萌萌(2012)在教学中发现,日本留学生在课堂上听讲认真、学习刻苦,但比较谨慎、课堂活动参与度低。相比欧美留学生,日本留学生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张(2001)研究了两组在新加坡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的焦虑水平。研究发现,不太熟练的学习者“对自我更敏感(ego-sensitive),更关心面子(saving face)。Nguyen(2002)研究发现,个别越南学生在发言之前,希望确保他们得到同龄人的认可。如果出了差错,69.3%的人感到“害羞”和“非常害羞”,会有“丢脸”的焦虑。
1.4目前的研究局限
以往研究(张莉,2002)发现被试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的焦虑感越强,其口语、听力及语法水平越低。但是,是焦虑感导致口语听力水平低,还是因为口语、听力、语法水平低而导致焦虑,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教师如何管理外语课堂焦虑这一点未得到充分的探讨。大量研究结果发现外语焦虑在不同文化的外语课堂学习中都存在,但文化因素对学生焦虑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
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的问世给外语焦虑研究提供了一个量化的研究工具,但现有的研究主要是西方文化视角,特别是英美学者的经验。由于语言背景、文化背景、课堂教学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外语学习的焦虑状况和影响因素也有不同。量化的考察难以兼顾教学的文化情境,也没有对学习者以往的学习经历和教师的影响进行考察。鉴于这个世界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外语课堂学习焦虑还需要更多的跨文化视角的质性研究。
2.研究设计与实施
2.1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首先使用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调查留学生汉语课堂学习的焦虑状况,获取相应的数据。采用Likert量表计分,从“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5分)的五级量表形式。为了避免系统误差,对其中一些反方向题采用反向计分。将全部33题的得分相加,得到一个焦虑值,作为衡量学生焦虑感的尺度,得分越高表示焦虑越严重。
在量化研究基础上研究者进行了质的研究。研究者本人是对外汉语老师,和留学生非常熟悉,获取学生的信任,有进行深度研究的便利。设计半结构化访谈,选取汉语学习中度和高度焦虑的学生进行访谈,了解他们汉语课堂学习经历,是否体验焦虑,如何管理自己的焦虑,及他们如何看待老师在汉语课堂焦虑管理方面的努力和行动,并探索引起汉语课堂学习焦虑的原因。同时选取一些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了解他们对外语课堂焦虑问题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管理学生的课堂焦虑,参与课堂观察,随时收集资料和信息,并进行教学反思。
2.2参与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从上海市高校选取留学生进行调研,参与本次调研的学生140人,回收有效问卷123份,其中男生62人,女生61人,空缺1人。年龄分布:18岁—20岁学生48人,21岁—24岁学生62人,25岁以上学生8人。其中语言生48人,本科生65人,硕士生10人。因为无法进行汉语水平测试,因此关于参与调研者的汉语水平情况的描述,只能让受访者按照自己目前的HSK成绩自填。HSK1-3认定为汉语初级水平,HSK4-5为汉语中级水平,HSK-6级为汉语高级水平。参与本次调研的学生有20人是汉语初级水平,中级水平91人,高级水平12人。參与本次调研的留学生来华时间不到半年的有30人;在华大概一年的有35人;大概两年的有21人。参与调研的高校是上海合作组织司法培训基地,留学生主要来自前苏联的中亚及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俄语国家,多数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如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还有少数留学生来自韩国、希腊、尼泊尔、泰国、柬埔寨、孟加拉、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不同国别的留学生混合编班,由于语言不通,汉语成为不同国别学生日常交际沟通的唯一工具。本调查样本中没有日本留学生和欧美发达国家留学生。
2.3研究工具和研究实施
调查问卷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学习者个人背景情况及汉语学习情况。第二部分是Horwitz(1986)等人设计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FLCAS)。第三部分设计一些开放式问题如当你对学习汉语感到焦虑时,你通常做什么?为了使受试者准确无误地了解问卷内容,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采用汉语、英语、俄语三种问卷。首先由研究者将量表英文版其翻译成汉语,让有翻译资格证的同事进行校对,然后进行预测,对学生感到有异议的汉语词语进行简化处理。由于参与调查的许多留学生来自俄语区,看不懂英文和中文,研究者又让既懂俄语又懂英语和中文的留学生对照英文版和中文版将问卷翻译成俄语。问卷修订好之后让任课教师在班级中进行问卷调查,当场作答,结束后立即收回。
研究者按照“非常不同意为1分;不同意为2分;既不同意又不反对为3分;同意为4分;非常同意为5分”进行数据整理,为了保证调查的信度与效度,FLCAS问卷设计了一些正反相对的调查题。在上述两个方面,互为正反的调查题,一道调查题焦虑值高,则与之相对的调查题焦虑值低。第8,12,28题为逆向计分。理论得分范围是33分-165分,分数越高,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焦虑越严重。
2.4研究发现与结果分析
本项研究的重点是探索留学生的焦虑具体状况,找出哪些群体的焦虑值比较高。根据所收到的完整样本统计结果显示,参与本次调查的样本的焦虑总值平均是90.75。在33道选题中,焦虑值最高的五项陈述是:
测试焦虑:对“汉语考试时我感到紧张”的同意程度平均值3.28。
课堂焦虑:对“当我迟到或缺课后的第二天,我会感到紧张”的同意程度平均值3.13;对“当汉语老师无法解释这堂课时(知识点),我感到紧张和困惑”的同意程度平均值3.13。
沟通焦虑:对“当我不能用汉语写作或表达自己时,我感到紧张”的同意程度平均值3.06;对“当我不理解老师用汉语说的话时,我感到焦虑”的同意程度平均值3.05”。
研究者筛选了焦虑总值最高的12位参与调查者的数据,对他们的个人统计学信息进行描述如下:
在这12位学生中,18岁-20岁5人,21岁-24岁5人,25岁-28岁1人,28岁以上1人;来自中亚国家的有5人,另外7人来自泰国、韩国、越南、尼泊尔等国家;焦虑总值平均分123分,焦虑均值为3.73,考试焦虑均值3.8分,负评价焦虑均值3.8分,交际焦虑均值3.67分。在汉语学习经历上,有5人来华之前学过汉语;有7人是汉语零起点的学生;汉语水平分布上,这12位焦虑值最高的学生中,初级水平(HSK1-4)的学生有4位;中级水平(HSK-5)的1位;高级水平(HSK-6)的2位;在学习困难中,有7位同学认为最困难的是听力;其次是写汉字。
2.4.1不同性别留学生焦虑值比较
不同性别留学生的焦虑值差别不大,男留学生(N=51)焦虑总值平均数89.8分,女留学生(N=50)焦虑总值平均数89.4分;从图1看出,男留学生样本的考试焦虑和负评价焦虑高于女生,但交际焦虑女留学生略高于男留学生。
2.4.2不同文化群体的留学生的汉语课堂学习焦虑表现呈现明显的文化差异
因为参与调查人数较少,一些国别的留学生的人数只有一两个人,难以进行样本比较,所以本次调查只抽取了参与调查人数较多的国别的留学生做比较。调查发现焦虑值呈现明显的文化差异,来自同一国家或者文化群体的焦虑感接近。
在本次参与调研的留学生中,平均焦虑值最高的是泰国学生群体。参与调查的六位泰国学生平均焦虑值114,其中有一位焦虑值97,其余四位焦虑值均在100分以上,无论是交际焦虑还是负评价焦虑和考试焦虑,均为最高。其中两位已经通过HSK6级,两位通过HSK5级。虽然通过了HSK6级考试,但是感到“跟中国人交流,说话特别谨慎,怕语法错”。还有一位汉语中级水平的泰国学生,害怕“考试不及格,学习没有进步,考HSK不及格”。调查发现,泰国学生认为最困难的是中文阅读,不习惯教师的教学方法,“这里的老师很害怕的样子”。儒家文化圈的留学生(越南和韩国)的焦虑值均高于中亚留学生。三位参与调查的韩国留学生的焦虑指数分别是121,111,131,呈重度焦虑。这三位韩国学生来中国不到半年,汉语表达非常吃力,听不懂,感到自己的汉语水平不好,课堂上倍感焦虑。巴基斯坦学生的焦虑程度有较大差异,一位呈现较低焦虑,另外两位的焦虑程度较高。巴基斯坦学生在开放式问卷中提到在班上不敢说汉语,在班级之外可以进行流利的漢语表达。“In class I feel nervous and I cant speak anything, outside of class I can speak well”,呈现典型的课堂焦虑;另一位同学谈到无法理解汉语语法”。
相对而言,焦虑感最低的是中亚留学生群体。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留学生的焦虑均值2.98,低于总体的焦虑平均值。中亚留学生的焦虑感很低,首先是这些学生在该校人数较多,文化习俗相近,彼此之间用俄语交流,而且多数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俄语、英语、主体民族语言,有的还会西班牙语或者土耳其语,外语学习经历丰富,学习外语的时候常常显得很自信,不太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不认为说不好外语是一件丢面子的事。再加上来华的中亚学生普遍年龄小,性格散漫外向。多数在华中亚留学生都有中国朋友,和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互动很多。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尤其是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学生如来自韩国和越南的留学生,面子作为约束行为的一种手段,是极其重要的。他们的性格偏向于文静保守,上课害怕出错,焦虑感很强。
2.4.3来华时间长短与外语学习焦虑没有显著相关
我们普遍认为,留学生初来乍到,连基本的生存汉语都不会说,听不懂,无法交流,当然会处于重度焦虑中;但本项调查,在华时间长短与焦虑指数没有相关性,并不是在华时间越长,汉语水平越高,焦虑感就越低。本研究发现,焦虑感最低的是在华一年的学生。焦虑感最高的是在华两年以上的学生。样本中的两年以上的留学生多数是泰国留学生,所以焦虑值可能产生偏差,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样本调查。来华一年的学生基本的会话和交际汉语都已经掌握,焦虑感降低。两年以后,尽管汉语的日常交流没有问题,但是在华两年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学历生,要和中国学生一起用中文学习,参加各种专业课,还要考试,其焦虑感并不比初来乍到减轻多少。反而是来中国一年的语言留学生,感觉最好。
2.4.4留学生的汉语水平与课堂焦虑表现没有显著相关
调查发现,汉语水平高低与汉语课堂焦虑表现值没有相关。因为没有得到留学生的汉语成绩单,所以问卷只是区分了HSK1-6级,让留学生按照HSK1-6级自己填写目前的汉语水平。本项调查只能大致描述不同汉语水平的留学生的汉语焦虑状况。从图4可以看出,汉语水平高的留学生比汉语水平低的留学生的焦虑值高,其中水平较高学生的交际焦虑值和考试焦虑值均高于汉语水平低的留学生。
2.4.5汉语学习困难
本项调查设计了一个问题了解学生的汉语学习困难:在您的汉语学习历程中,您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我们把学生填的信息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并设计了一个开放式问题让学生描述汉语学习中最困难的是什么。从上图可以看出,学生最焦虑的是口语表达,特别是书面表达和学术汉语表达。有的写“我的发音不准,声调发不准,害怕开口”;有学生说“跟中国人交流,说话特别谨慎,怕语法错”;有的学生害怕老师让自己到讲台前进行口语表达,“把自己当作老师,站在黑板前给学生们讲课”。有的已经通过HSK5级甚至6级的留学生仍然担心自己的汉语表达;“虽然我知道很多词汇,有的时候写或者说话的时很难来用”。有的学生反映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进行有效表达:“Forget right word right time.”听力也是学生反映最难的事情,学生认为听懂老师用汉语上课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
参加汉语考试也是学生倍感焦虑的事情,害怕“考试不及格,学习没有进步”,害怕期末考试,怕考不过HSK;另外,学生反映汉字很难,有的汉字看上去很像,但是意思却不同,这让他们非常迷惑。学生在开放式问卷中填“To confuse the similar characters in Chinese, because they look alike but meanings are different.”有的学生甚至说“写某一汉字万遍以后第二天忘记”,感到很沮丧。有的汉字是多音多义字,更让学生难以掌握。
另外,教师的课堂风格对学生的汉语学习也有影响。同伴压力也是造成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的主要因素,“跟汉语比我好的学生聊天儿时感到不自信”。
3.思考和建议
3.1构建“学习者共同体”
合作学习理论认为:合作学习在减轻学习焦虑、促进交流、加强学习动机、增强学习者的自信心、提供可理解的语言输入输出等各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留学生教学管理者应当有意识地进行班级团队建设,特别是初级汉语课堂教学的班级成员流动不要过大,采用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加留学生间的接触与了解,让学生彼此熟悉,营造相互了解和信任的班级氛围,降低学习者之间的竞争压力。这种友好互助的班级氛围有助于减轻学习者的焦虑感,提高语言熟练程度,打破语言焦虑的恶性循环。
3.2努力营造没有威胁的课堂气氛
面对文化因素导致的群体汉语学习焦虑状况,确实要求教师具备对学生的焦虑症状的理解与诊断的能力,教师要努力构建没有威胁、团结互助的课堂气氛,让大家在这里感到“出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在课堂教学活动设计中要避免让焦虑感较强,比较顾及面子的学习者在课堂孤独地进行自我呈现,减少学习者在面对全班时的心理压力。鼓励小组练习,采用合作的方式减少学生的焦虑和压力,让学生,特别是初学者能够在一种宽松的环境中进行练习。不喜欢登台进行口语表达的学生,可以引导其通过记录、写作等学生个体喜欢和擅长的方式来完成学习任务。这不仅有助于降低不同个体的心理焦虑,还可以让学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在教学中,老师应该尽一切努力减少学生的焦虑感。教师在课堂上应特别注意保护好学生脆弱的自尊,在课堂上多使用积极和肯定的评价,及时赞扬他们取得的点滴进步,采取鼓励的态度纠正他们出现的错误,“鼓励冒险”,“建立学生的自信”,使学生经常获得成功、快乐的体验,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学习。“促进合作学习”和“让学生自己意识到他们的错误(Brown,2002)。
在练习语法点时,教师对学生的错误应立即予以纠正,以强化学生对正确语法形式的印象;而在课堂交際过程中,特别是在学生进行成段表达的时候,不应随时纠正错误、以免打断交际,制造紧张心理。另外,教师纠错要区分错误类型,分清全局性错误和局部性错误,严重错误和一般错误、经常性错误和偶然性错误,不必每错必纠,选择合适的纠误方式,掌握纠误技巧,尽量诱导学生自己发现错误并自行纠正,而不是简单地直接改正(Lyster &Ranta,1997)。延迟纠错,容忍学生的错误,教师对学生学习汉语的能力表示满意甚至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
3.3强化情感因素对语言学习影响的意识
重视学生情感的释放和情绪的表达,以真诚、接受、理解的态度对待学生,以合作者的身份平等地与学生进行思想交流。可以让学生把自己的焦虑都说出来,或者写在纸上,大家分享学习经历和体验。告诉学生,学生都缺乏自信,都认为别人强于自己,通过这种同伴间“自我披露”的方式减轻汉语学习焦虑。性格内向的学生在语言输出遇到障碍时,一定要帮他们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对此,教师一方面要鼓励他们大胆表现自己,另一方面不要过多强求,以降低其焦虑感,松弛其神经系统,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参考文献:
[1]陈劼.英语学生课堂焦虑感与口语水平的关系[J].国外外语教学,1997(1).
[2]侯莹.国外外语焦虑研究述评[J].语文学刊,2011(8).
[3]钱旭菁.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时的焦虑[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2).
[4]孙永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外语课堂焦虑问题的实证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17(12).
[5]王才康.外语焦虑量表(FLCAS)在大学中的测试报告[J].心理科学,2003(2).
[6]张家强,郭丽.本科生课堂焦虑研究: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的信效度再检验[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7]张莉,王飙.留学生汉语焦虑感与成绩相关分析及教学对策[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1).
[8]Horwitz E. K., Horwitz M. B., Cope J..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86(70):12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