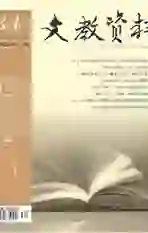谈《唐律疏议》体现出的“惩教结合”观
2018-03-27张煦琳
张煦琳
摘 要: 《唐律疏议》作为《唐律》的注解,是唐朝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儒法典”。无论是刑名的制定或是刑罚的成规,无不体现出其“德主刑辅”的特色。由此,因德生出的教化、因刑体现的惩训,共同交错构成了极具人文精神与教育意义的“惩教结合”观。与当今惩罚、教育分离的现状不同,《唐律疏议》中所体现出的“惩教结合”具有共时性,这对当今法律的制定与完善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唐律疏议》 德主刑辅 惩教结合
《唐律疏议》,唐长孙无忌所撰,是对《唐律》的逐条注解。全书以《唐律》为蓝本,按照原书顺序,对五百多条律文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和诠释。全书都在解释律文,但又不囿于此。《唐律疏议》不满足于字面上的解释,也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对律文的随意解释。而是引经据典、追源溯流,通过对历代法律条文、思想的引证考据,使读者见微知著,大大丰富了《唐律》的内涵。“在总结吸收前朝历代优点的基础上,《唐律疏议》成为古代中国法律儒家化的集大成者,并对后世的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唐律疏议》为政府组织修撰,又通过诏令形式下颁,其正规性与权威性不言而喻。因此,其虽属注释,但实际上与律文无异。唐律规定的刑名仅有五种,为历代最轻。纵观近现代法制,惩教二者显然是呈分离状态的:惩罚归惩罚,无论是经济惩罚或物理惩罚,都只是单纯的惩罚行为。教育则经常处于次要的地位,或是呈缺失的状态。就《唐律疏议》刑名制定中所体现出的惩教的高度结合,本文将介绍其现象,探究其原因,并做出相关思考。
一、“惩教结合”的制定背景
首先,“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唐律疏议》实施的伦理依据:天生善质的“圣人之性”和天生恶质的“斗筲之性”毕竟只是少数,占据绝对数量的是有善有恶的“中民之性”,因此要以德启善,以刑去恶。但如果将德育与刑罚分开实施,那么没有刑罚的震慑,德育往往不被重视;或是没有德育的引导,则刑罚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二者是一个有机、统一的过程,唐朝统治者正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其次,唐初统治者深感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故积极采用儒家所推崇的宽刑轻罚,使法律与道德相结合,以安定民心,恢复生产。他们继承了西汉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阳尊阴卑,故道德尊崇于法律,阴阳相合方能成岁,故道德与法律相配才成政教。”“德主刑辅”的思想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惩教二者的紧密结合。具体表现为“刑中显德”与“出德入刑”两种层次,也即“惩中有教”与“违教必惩”。
最后,“虽然唐朝采取的是‘儒治世,佛治心,道治身的统治手段,但道教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佛教‘戒杀的教义客观上起到了减轻刑罚的潜在效果。”[2]宗教对政治的影响虽然细微,却也不容忽视。
二、“惩教结合”的具体表现
(一)“刑中显德”的刑名制定
《唐律疏议》规定的刑罚有笞、杖、徒、流、死五种。虽然只是刑罚的名称,但长孙无忌在进行注疏时,明显有意渗透进“惩教结合”的理念。具体叙述如下:
(1)笞刑
笞刑下有注释:“笞者,击也,又训为耻。言人有小愆,法须惩戒,故加锤挞以耻之。”[3]唐人用荆条鞭笞有过之人,以示惩戒。在施加肉体折磨的同时,也实施了精神的拷问。荆条每落,便是对受刑之人道德的质问:做人应有的道德哪里去了,你现在觉得羞耻吗?每有笞,便思耻。还好属于小错,切记知耻而后勇,笞刑毕后,望思耻进取,勿要再犯。
(2)杖刑
汉景帝时,往往出现笞刑未毕而受刑者已然亡故的情况,因此把之前应笞三百的改为二百,二百改为一百。“今律云‘累决笞、杖者,不得过二百,盖循汉制也。”[4]唐循汉制,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法律条文的制定中。刑罚可减,这同时也是对受刑之人道德上的点化:法律尚有怜人之心而自减,难道人能没有怜惜之心、顾忌之意吗?
(3)徒刑
徒刑有五等,受刑者被剥夺自由,在牢内生活一定时间。“徒者,奴也,盖奴辱之。”[5]这与笞刑教化的方式相似,都是以刑罚名称本身的含义来惩教有过者。被判徒刑,则是被判为奴。奴在唐朝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这种“临时为奴”正是对受刑者的道德拷问,使其一边面临失去自由的监禁生活,一边反思自己缘何沦落至此?正是因为道德的缺失,行了失德之事,才会失去为人的资格。唯有在出狱后追求道德,行有德之事,做有德之人,方能不复为奴。
(4)流刑
“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6]流,即流放。不杀且流,原因只有一个“不忍”。这一个“不忍”,便是对受刑者良心的拷问。法律尚有不忍,故弃刑杀而流远,人在做违法之事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不忍之心吗?法律将有过之人流于远方,人自然应当将失当之举流于不再犯。
(5)死刑
“死者,澌也。消尽为澌。”[7]现代虽也有徒、死之刑,但显然少了包裹于刑名之中的教化意义。在《唐律疏议》里,死亡并不单纯地指死亡本身,它也有十分深刻的道德内蕴。正是因为受刑者罪无可恕,所以要剥夺他的生命权利,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殆尽。他的失德已无可挽回,所以他的一切都要尽数消散,自此在世间不留一丝痕迹。德行是存在的基础,倘若有违,便只能消失。世道是由人们的德行尽数组成的,不属于就只能被抹去。
《唐律疏议》废除了腰斩、枭首、夷三族等酷刑,仅保留“惩教结合”充分融合的五类刑名。严刑峻法的废止并非是时代的倒退,因为唐朝统治者深知,德化往往比纯粹的惩罚要行之有效。无论是先教后罚,亦或是先罚后教,都不及惩教结合来的有效。五种刑名的确立,正是惩罚与教化的有机结合,二者贯穿于同一个过程中,时间跨度完全一致,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二)“出德入刑”的法律成规
除去“刑中显德”的刑名制定外,《唐律疏议》还有不少法律成规体现着“出德入刑”的思想,这是“惩教结合”观的另一层体现。当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礼節教化不足以规范人身行为时,便要对其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出于礼者入于刑,接受刑罚即是存在失礼之举,这会使受刑者在接受惩罚的过程中反思自己的无礼之举,达到立法者“惩教结合”的目的。
(1)不孝
“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8]不孝作为“十恶”之一,刑罚之重令人惊异。当今子女不孝,判处超不出民事的范畴,但《唐律疏议》中对不孝的处罚就没有那么宽宥了。责骂、诅咒祖父母、父母去死的,以谋杀论处;父母身故却密不举哀的,判处流刑;守丧期间行嫁娶之事的,判处徒刑三年。不孝即无礼,无礼便受刑,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惩教结合”。
(2)悔婚
在女方知道男方真实情况后,如接受聘礼答应婚约,则悔婚须受杖刑六十,婚约依然有效。接受聘礼而另许他人,杖一百。事成者,处一年半徒刑。婚姻大事必须慎重,若视为儿戏轻易允毁,那么这一失礼举动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3)轻妻
《唐律疏议》有言:“妻者,齐也。”妻之于夫,就像秦之于晋一样般,是一种平等的、势均力敌的关系。妾则是一种货物,买价即是其价值所在。至于婢女,则属卑贱之流。因此以妻为妾,以婢、妾为妻者,须判处一年半至两年徒刑。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人皆平等的思想,但也是出于维护封建家庭秩序的需要。
此外还有对同姓成婚、强嫁寡妇、迎娶逃女等出礼之举的惩罚,兹不详述。总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律疏议》所规定的礼法关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结果上来看,便是“惩教结合”。逾礼之人在受到惩罚之时,会自然而然地回溯到自己的失礼之举上,从而在接受肉体折磨的同时进行深刻的精神反思。
三、“惩教结合”的借鉴价值
(一)“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
《唐律疏议》篇首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9]这清楚地告诉我们,惩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在实施惩罚时毫无德礼方面的暗示与引导,那么惩罚便会流于表面,变得毫无价值。
“伦理道德与封建律法的融合,最终使礼成了法律的灵魂和统治阶级意志的精神内核。”[10]今天的我们固然不能大力倡导封建伦理道德的重建,但道德层面的许多东西古今皆然。我们只需汲取其中有益的成分,做到古为今用。刑罚的设置不是以暴力或权利威吓有过之人,而是要使其在受刑的过程中主动反思。惩罚的施加只能成为“药到病除”的“药引”,德化才是治病的良方。
(二)“惩罚教化”的同时同步
“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的,两者相辅而行。”刑罚的实施与德礼的宣扬,二者本是互为表里的存在,可纵观当下的法律惩戒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德育的缺失。法律逐渐理性的同时,其人性的色彩也在黯然褪去。“中国古代法上颇具特色的,不是西方式的个人自由和平等权利,而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原则。”[11]随着法律中人道色彩的逐渐消失,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遗憾。
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规避徒刑、死刑等刑罚,亦或是赔偿金的支付而选择不去触碰法律底线,与之相伴的是,道德方面的考量彻底缺失了。虽然起到的效果看似相同,但道德约束的有效性与时效性,无疑是惩罚约束所无法比拟的。就像在前文中所述的那样,单纯的德育宣讲很难唤起服刑人的注意力,没有德化引导的惩罚实施反而会激起服刑人的反动情绪,这也是当今为何越来越多的服刑者“二进宫”的主要原因。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惩戒结合”,这二者的结合并非是缺一不可的关系,而是同时同步的关系。将服刑人受刑与德育的过程结合起来:受刑即德育,用有教育意义的惩罚手段使其反思主动自己的失德之举;德育即受刑,受道德引导的反思过程即是自我向精神施加惩罚的过程。
(三)“出礼为刑”的理念引导
当今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始终无法令广大民众放心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民众法律意识的淡薄。法律很难普及界定,但道德却容易把握运用。现阶段虽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但基本的道德共识还是存在的。因此,违背道德即是犯罪这一思路,值得当下社会去借鉴。很多人认为犯罪太遥远,是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样的人往往对法律一窍不通,有朝一日触碰法律底线,方叹为时已晚。
因此,加强德育教育,是减少违法案件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理念已经被教育界所认可。可有种现象值得我们瞩目:“不道德”作为犯罪的“警报器”,往往被忽视。广大民众倾向认为,失德和犯罪八竿子打不着,因而稍加注意便好,没有必要特别重视。殊不知,在古代,失德就是犯罪,出礼便要受刑。因此,立法机关需完善立法工作,不要把所有看似“无足轻重”的事情,都交给道德去解决。
参考文献:
[1]姚奕.从《唐律疏议》看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J].科教导刊,2010(9).
[2][11]朱丽娟.论《唐律疏议》的人权意识[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18).
[3][4][5][6][7][8][9]长孙无忌.岳纯之,点校.唐律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0]李忠建.《唐律疏議》法律伦理思想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