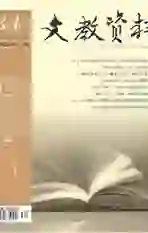《珊瑚鞭》评点简析
2018-03-27邓嫣
邓嫣
摘 要: 袁于令评点徐石麒《珊瑚鞭》,表现出鲜明的文人、友人式评点特质:以圈点、眉批、夹批为主要形式,内容多漫谈、随感、注释,与作者、读者、剧中人物同时展开对话,赞誉多而批评少,重案头而轻舞台。这种特质,是评点者身份、评点者与作者关系、清初戏曲评点风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徐石麒 袁于令 《珊瑚鞭》 戏曲评点
顺治旧钞本《珊瑚鞭》传奇,卷首署名“坦庵徐又陵填词,幔亭仙史袁令昭评阅”。《焦循论曲三种》载,“吾里中徐坦庵作《珊瑚鞭》传奇成,邀袁箨庵观之”,说明袁于令评点《珊瑚鞭》,是应作者徐石麒之请,属于朋友间的戏曲创作、交流行为。这使袁于令的评点,区别于金圣叹评《西厢记》、毛声山评《琵琶记》之类的“以今批古”,又不同于明代戏曲评点中的“李评”“汤评”“陈评”系统,而具备更多文人的、友人的、清初的戏曲评点特征。
一、评点的形式与内容
袁于令的评点,以圈点、眉批、夹批为主,偶见批注结合圈点,还有少量出批,形式上是比较自由的。这些批语字数简短,与作品内容紧密结合,或提示情节,或夸赞曲白,或评点人物,或注释文义,或结合其他戏曲作品直抒己怀,内容上也是比较自由的。这种漫谈、随感式的评点,使得评点分布也比较自由,密集处一句一评,稀疏处一出不过两三评。袁氏批语视角多变,预设的交流对象也不是固定的。有些批语,是直接与作者对话,有些是与剧中人物对话,有些是与《珊瑚鞭》其他可能的读者对话,甚至有感而发自言自语,唯独缺乏与观众、演员的对话,缺乏关于舞台演出的见解。这说明袁于令评点《珊瑚鞭》,是案头的而非场上的评点,关注点更多放在文本层面。下面结合具体批语,分别说明这些情况。
袁于令在《珊瑚鞭》卷首目录“返金陵”下夹批“二难并”,“悲失偶”下夹批“连环操”,“两团圆”下夹批“双乔醋”,并在各出标题下有对应的出批。第二十出《返金陵》,标题下批“此折标题颇不惬意。鄙见,现改为‘二难并何如?”这一出讲的是卢夫人携女避难至金陵胞兄白元处,卢梦梨与白红玉相见,两家都被杨廷昭陷害,两家女儿都在为择婿犯愁。结合剧情,二女最后都与苏友白结缡,此处改“返金陵”为“二难并”,不仅提挈本出剧情,还关照全剧情节走向,比原标题实现了更多的表意功能。第三十一出《两团圆》,讲的是苏友白同一天内先后迎卢梦梨、白红玉进门,二女假装吃醋,戏弄苏友白。袁于令在标题下批“此折易之曰‘双乔醋,似亦新奇”,也有相同的效果。第三十二出《承天寵》,眉批“全出何不易名曰‘双栖凤?”《珊瑚鞭》的主线剧情,就是白红玉、卢梦梨二女与苏友白历经波折终成良缘,这几处批注中的改动,表明袁于令十分看重出名的扣题与呼应。这种对作品的修改意见,显然是给作者看的,也展现出袁于令作为曲坛老手的高明。但这类批注总量很少,显示出袁于令评点友人作品时不愿喧宾夺主的谨慎态度。
与意见相比,袁于令批语中有大量夸赞作者才华的内容。开篇《作者意》“聊借他缘,塑我擎花手”一句,夹批“必有此才,乃许自夸”,就已经奠定了评者与作者知音相惜的基调。正文批注中诸如“趣绝”“奇语”“妙句”之类相对笼统的赞誉俯拾皆是,结合曲白内容,具体夸赞也非常多。第三出《闹东篱》,末、净唱【节节高】,袁于令圈“你选婿时开绛纱窗。解围又入青绫帐。”眉批“对偶亲切,天然入韵。”这是对曲辞技巧的赞赏。第四出《辞婚怨》,杨芳的一大段白,讥刺时人不学无术,靠权荫上位,袁于令眉批“作者目空一世,那个知者特借此以泄其不平耳。”“摹写曲尽。”肯定作者对人世观察入微、表达刻至的才华。第七出《误辞鸾》,生唱【簇御林】,袁于令圈“则被他无情唤起多情怨。为多情转做的无情面”,眉批“情辞交至,声色双清。”夹批“说开说合,煞之活之,均无不可,真才笔也。”这里谈到了曲辞与声情的结合问题。第十七出《美人题》,生唱【罗袍歌】前腔,袁于令圈点全曲,眉批“忽自疑,忽自信,摹写痴情入微,词更奇矫,真是文生于情。”这是赞美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生花妙笔。第十八出《暗抛情》,标题下批“读全出若离若合,似隐似现,全在迷离惝恍中求之。仙乎,仙乎,余观止矣。”这是赞美作者的制曲风格。可以说,袁于令对徐石麒《珊瑚鞭》的肯定,涉及戏曲创作的方方面面。
除此之外,袁于令还有不少评价剧中人物或与其对话的批语。第二出《女传书》,旦唱【黄莺儿】,袁于令圈“柳腰轻载不起你图书架”,眉批“真是不栉书生”,又圈“怕传胪姓氏,唱不到女娇娃”一句,眉批“娇艳中颇饶幽愤。”这是高度评价白红玉的学识才华,认同她的可爱性情。后文旦白“卢家妹子诗格清高,果在孩儿之上”,夹批“论才似亦在卿卿之上。”这已经把白红玉当作真实存在的亲切人物,在跟她说体己话了。第九出《新柳吟》,旦白“可奈命薄缘悭,终成画饼”,夹批“也不尽然”,这是已知剧情的局外人对剧中人的善意揶揄,眉批“我欲分忧少许”,把白红玉当作真实存在的人物在疼惜;后文旦唱【步步娇】,袁于令圈“我妆罢懒登楼。怕东风染遍青青柳”,夹批“是可怕也,孰不可怕也?”第十四出《怜同调》,贴白“我小姐眼也不差”,夹批“真个眼也不差”;贴白“我小姐怜才之心,可白天日”,夹批“真个可白天日”。第三十一出《两团圆》,生唱【高阳台】,袁于令圈全曲,夹批“我妒其人。”这种与剧中人物的对答,非常活泼有趣,显示出袁于令以幻为真的赤子之心。须知,这种对虚构世界的真感情,是文艺创作、感受与审美的前提。
上文列举的批语,是戏曲评点中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不论评点人身份如何,都能做出类似的鉴赏。而袁于令作为戏曲作家,在曲学及戏曲创作方法上,有自己的专业见解,这也体现在《珊瑚鞭》的评点中。曲学方面,如第五出《叹遐征》,【沽美酒带太平令】,袁于令圈“耐尽了猿嗥虎咆,听尽了乌嘈雁嗷”,眉批“今乐府一句两韵,名曰‘短柱,极不易作。”短柱体不易作,这是同样填过曲的人才能有的感叹,只看不写的人是很难有这种体会的。第十三出《青衣诧》,旦唱【尾犯序】,袁于令圈“都与那寒郊荒茸一样老成蒿”一句,眉批“茸字、老字俱用上声”,后文贴唱【前腔】,袁于令圈“你鬓云修整莫待晚来搔”一句,眉批“四曲音律甚协,真可叫绝。”这些批语从曲学角度切入,既是为了引导读者鉴赏《珊瑚鞭》在曲律方面的严整匠心,也是袁于令作为戏曲作家的专业性的体现。
这种专业性还体现在袁于令对《珊瑚鞭》创作法及结构法的关注上。第七出《误辞鸾》,生白辞婚事,眉批“文章只恐喧宾夺主,只得将瑞庵女一笔扫却。”第九出《新柳吟》,贴白“小姐,你往常时,一味拈花折柳,只是戏耍,如今怎便十分不同了”,夹批“极意写得,画家背染法,情态可想。”第十出《乞鞭阻》,生唱【出队子】【前腔】【神仗儿】三曲,袁于令圈【神仗儿】“看杏花风里。飏青帘几字。那更歌楼女子。喁喁啧啧,说南朝国事。犹唱着后庭枝。犹唱着后庭枝”数句,眉批“前二曲写情,此一曲当写景。说歌楼女子,须知不是说歌楼女子。细想风光入画,此为不脱不粘,妙境。”后文生白“奇甚,奇甚,这先生果然是神仙了”,袁于令点此句,眉批“口中似答,心中是想。文章一笔作两笔用者,视此。”第十八出《暗抛情》,小旦唱【南乡子】前腔,袁于令圈“敢是楼下书生,猛撞入罗浮岸”一句,夹批“即从对面写,极妙。”第二十二出《两谈心》,小旦白“若非男子,必当见案”,夹批“是逆逗法”。第三十出《争附炎》,张轨如一段白,眉批“铺叙不可少。”诸如此类对戏曲文法的指点,在戏曲理论及创作指导方面,是有建设意义的。
戏曲结构的重要性,在明末清初进入曲家视野,王骥德、万树、李渔等人都强调过关目之间的连贯和关照。袁于令在评点《珊瑚鞭》时,也在此处着眼。第十出《乞鞭阻》,末白“那先生说相公此行,也是为姻缘事”,夹批“此句逗得好,文心之灵,一至于此。”后文生唱【神仗儿】,夹批“读至此方知逗句之妙,真无缝天衣也。”第十六出《诗场笑》,白元出和新柳诗原稿,识破苏有德、张轨如诡计,眉批“回顾藏过之稿,密甚。”第二十二出《两谈心》,旦、小旦唱【川拨棹】【前腔】,眉批“回顾前文。”这种数次强调,表明这一时期,结构严整已成为戏曲届评、创双方自觉实践的共识。
还有一类评语,是袁于令结合其他作品对《珊瑚鞭》进行阐释。第七出《误辞鸾》,末唱【啄木儿】,袁于令圈“写芙蕖红晕疑深抹,杨柳绿痕微浅”,眉批“较《洛神赋》又另开生面,只是无人克当斯语耳。”第八出《返鸾舆》,乜先一段白,欲送驾回南朝,眉批“《尤西堂乐府》有云,今日宰牛,明日宰马,送君还归……然词也。”第九出《新柳吟》,旦白写诗传世一段,眉批“才人胸中,岂肯作印板文字?故欲袭《牡丹亭》故套而卒易之,神味则与《牡丹亭》一般酸楚。”第十四出《怜同调》,旦唱【解三酲】前腔,袁于令圈“泼春愁不顾莺花见,恨不得噙一字告青天”,眉批“从‘泼残生除问天句脱化而出。”后文生唱【解三酲】前腔,中有“抓不住日影窗前”一句,袁于令圈全曲,眉批“‘猛教人抓不到梦魂前,‘抓字从此生出。”后文嫣素、友白对话,眉批“嫣素可人,似较红娘更为灵慧。”夹批“此两婢子,意似有齐桓晋文之判。”袁于令在这类批语中,指出《洛神赋》、《桃花扇》、《西厢记》等经典作品对徐石麒及其《珊瑚鞭》的滋养,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作品。
除了上述与作者对话、与剧中人物对话的批语,袁于令还有一些注释、提示类的点评,是专为读者而设的。注釋类的批语,如第二出《女传书》,【琥珀猫儿坠】唱词“和他买遍长安,百幅松花”,夹批“松花笺也”。第二十七出《悲失偶》,【剔银灯】“衠一味诗骚唱酬”一句,夹批“衠,真也,不杂也”。这类批语显然不是给作者看的,文化水平高的读者也用不着,是为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服务的。提示类的批语,如《女传书》外唱【琥珀猫儿坠】,“若共你三春批点上林花。由他十八登瀛,也让才华。”眉批“伏。”后文外白“待我挂冠时节,接他到家,与你同住几时。”眉批“伏笔。”第五出《叹遐征》,【侥侥令】“旌旆悠悠征尘盖”一句,夹批“有脱误”。第七出《误辞鸾》,生白“只为这一场扯淡,倒打动我无限情思”,夹批“逗下出。”第九出《新柳吟》,旦白“不如拈诗一首,流布人间。倘遇世外知音”,夹批“着眼”。这种批语显然是给其他读者看的,袁于令在评点《珊瑚鞭》时,考虑到了这个批本传播于世的可能。这说明,袁于令给徐石麒的评点,虽然是知音式的,但并非排外、私密的文学活动。作者与评点者,都希望《珊瑚鞭》能够传播出去,为广大读者、乃至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所见。
二、评点的特质及原因
上文分类讨论了袁于令评点《珊瑚鞭》的形式与内容,下面谈谈袁氏评点的特质及形成原因。
首先,袁于令评点《珊瑚鞭》,继承了中国文学评点的一贯传统,涉笔成趣,不拘一格,随意性是很大的。这些评点与文本内容紧密结合,评点与剧情同步推进,或评价人物,或提示情节,反映在读者眼中,评点内容客观上参与了作品的叙事进程。由于袁于令与徐石麒是同时代人,评点行为发生在双方都还在世的时间段,袁于令又是戏曲创作方面的前辈,则袁于令的评点,很有可能影响了《珊瑚鞭》文本的形成,钞本中的修改痕迹也可以佐证这一点。评点系统既依附又独立于文本,在指导创作与引导鉴赏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袁于令评点《珊瑚鞭》区别于《西厢记》《琵琶记》等跨朝代名剧评点的重要特质。
其次,袁于令的身份及与徐石麒的关系,部分决定了《珊瑚鞭》的评点风格。袁于令出身名门,少年成名,一部《西楼记》天下皆知,当属一时曲坛巨擘。其人年轻时洒落不羁,不曾仕进,明亡后仕清已是违身违心,又以“侵盗粮款”罪被参劾罢官,可以说是很失意的。但这个人“声伎游酒,至老不衰”,活到八十一岁的高寿,可见性情是很通透放达的。这样的一个人,有丰富的戏曲创作实践,经验和心得已非寻常评点者可比,在评点中既能至情至性,又因历世甚深而眼光独到老辣,创作力虽已衰竭,感受力与鉴赏力却丝毫不减,且能借此一吐胸中块垒,这是袁于令在人生暮年仍兴致勃勃地应邀评点了《珊瑚鞭》,且评点质量相当高的原因。至于作者徐石麒,一生布衣,入清后避世隐居,只跟少数朋友唱和往来,却邀请袁于令评点自己的《珊瑚鞭》,可见是以知音视袁,不以其仕清为污点的。袁于令既是应朋友之邀,又是曲坛前辈,这决定了《珊瑚鞭》的评点,一定是以褒扬为主的。
最后,袁于令的评点风格,自觉融入了清初戏曲评点的潮流当中。戏曲评点由明入清,评点主体渐趋文人化,评点主体与创作主体为同时代人的比例大幅增加,评创关系渐趋紧密化,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清初的戏曲评点,不再能像明代李卓吾那样具备强烈的批评意识,也不能像金圣叹评《西厢记》,毛声先评《琵琶记》那样自说自话,“六经注我”,也不像明代以舞台演出为指向的戏曲评改,而必须关注戏曲作者的创作旨趣,同时更多着眼曲辞、文法,而少涉及曲律、演出。评点要更多地承担阐释、引导职能,同时又不好逾越评、创主体间的界线。这也就意味着,特别张扬主体意识的评点,在这一时期,除非以今批古,否则是很难实现的。袁于令评点《珊瑚鞭》,始终恪守自己的“特殊读者”身份,多谈案头而少涉及场上,既是自觉,也是清初戏曲评点风尚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徐石麒填词,袁于令评点.《珊瑚鞭》[M].顺治旧钞本,《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
[2]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5.
[3]张勇敢.清代戏曲评点史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4]李艳辉.徐石麒及其戏曲创作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
[5]王琦.袁于令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