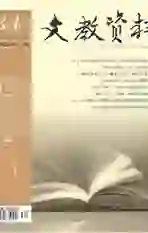报告文学“虚构”的理论发展
2018-03-27赵禹平
赵禹平
摘 要: 中国报告文学的“虚构”,形式上雷同于纪录片的“摆拍”,且由于近年来对非虚构文学的重视,研究者们逐渐重新审视“虚构”这一创作技巧。实际上,围绕真实性、特写、镜头感等理论,国外乃至国内理论都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成果。国外的报告文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步被引入中国,由30年代开始的强调真实性、讽刺性、新闻性到50年代“特写”的提出、作者对想象力的肯定,再到80年代“非虚构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国外的报告文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笔者所作的就是历时性的对“虚构”研究的理论梳理。
关键词: 报告文学 “虚构” 理论发展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出版的程光锐等主编的《报告文学》中指出,报告文学的发展是随着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产生,那些取材于现实的旅行日记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报告文学的特点;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之后,积极的革命者则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对社会时事进行报道述评,获得学者公认。
从18世纪中叶报告文学的初具雏形,到2015年白俄罗斯记者兼报告文学作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报告文学近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报告文学研究也取得众多理论成果。国内外对报告文学的研究,从报告文学的定义到报告文学的写作,都离不开对真实性的探讨。国外的报告文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步被引入中国,由30年代开始的强调真实性、讽刺性、新闻性到50年代“特写”的提出、作者对想象力的肯定,再到80年代“非虚构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国外的报告文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国外研究
(一)20世纪30年代各国“拒绝虚构”的报告文学理论:真实性、讽刺性、新闻性。
20世纪30年代,国外的报告文学研究有重要文献如中野重治(Nakano Shigeharu)《德国新兴文学》,安德尔·马尔克劳斯(Andre Malcross)的《报告文学的必要》,以及川口浩(Hiroshi Kawaguchi)《报告文学论》和皮埃尔·梅林(Pierre Merlin)的《报告文学论》等。此阶段的报告文学,在二战背景下,研究者们更注重的是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批判性、新闻性特征。要求报告文学家以批判者的身份,对社会时事进行揭露和讽刺。以日本学者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为例,作者对报告文学的特性、存在方式都做出分析,认为报告文学的近代性和传播性把报告文学与其他文学类别很好地区分开来,同时也强调了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性和讽刺效果;[1]
另一日本学者山田清三郎写有《通讯员运动和报告文学》,文章标题即标明:报告文学与通讯员运动一致,是通讯员进行运动结果报告的一项武器,需第一时间明确其新闻意义。马尔克劳斯著《报告文学的必要》中肯定现实真实直接关系报告文学的价值,“报告文学‘实际的力量,在乎全面地拒绝现实的逃避,即所谓最进步的报告文学形式”。[2]安德尔·马尔克劳斯(Andel Marcrous)认为报告文学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拒绝现实的逃避,并且人物如果破壞真实,报告文学则毫无意义。
法国梅林(Merlin)著的《报告文学论》,加博尔(Gabor)的《“报告文学”的本质与发展》等,侧重点各不相同,虽在本源、特质等方面各抒己见,但一致地肯定报告文学的三个研究特性:真实性、批判性和新闻性。综上可见,真实、新闻、时事批判,是报告文学之初就已经坚持的写作准绳。
(二)50年代——“特写”理论。
20世纪50年代初,基希(Kisch)写的《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和T·巴克(T. Buck)所作的《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等相关报告文学理论家研究,一度受到中国众多作家的追捧;在这些作家的理论当中,尤其应注意,作者想象力和“特写”的鼓励、提倡,使得报告文学“文学性”得到加强。苏联报告文学家基希,首先认为报告文学作为“危险的样式”,应当在适当的时代背景下以其充分的真实性,发挥报告文学的战斗力;其次,报告文学要在作者的大量调查和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写成,应兼具真实性、战斗力和讽刺性;同时,基希也强调,报告文学写作离不开作者的想象,这是针对细节回放而言的;叶圣陶就曾评价基希的报告文学是“在真切的事实上进行抒情诗的想象”[3]。塞尔维亚巴克写的《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中,也肯定了报告文学对社会现实真实性地反映效果和报告文学的批判、警醒作用。
另一苏联学者波列伏依(Boris Polevoy)《论报纸的特写》,研究“特写”在报告文学写作中的运用:在高尔基的理论观点基础上,认为“特写”是很好地突出事件局部,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和文学性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最佳方式。报告文学家想象和报告文学“特写”的提倡,对报告文学写作和研究而言,都具有相当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报告文学的想象和特写,标明报告文学需要依赖“略有虚构”去对细节、局部进行想象、完善,构成完整的叙述场景和作者观点;但也并不是“粉饰生活”的虚构想象。
(三)80年代——“非虚构”文学理论。
“非虚构”的文体相对于“虚构”文体而为另一文体类别,其特殊的写作要求,集结了一批文学理论家对“非虚构”理论的关注。首先,“非虚构”作为一个文体类别,是众多文学类型的几何,常常包括新新闻报道和各类非虚构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散文、游记等亦可纳入非虚构文学文体之中。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的非虚构文学理论盛行。譬如约翰·霍洛韦尔(John Hollowell)的《非虚构小说的写作》、诺曼·西姆斯(Norman Symmes)的《文艺型记者》、雪莉·艾利斯(Shirley Ellis)的《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等。
美国理论家把报告文学作家纳入文艺型记者范畴,诺曼·西姆斯道:“文艺型记者不同于小说作家,但作品中人物也如小说中人物,其感情和戏剧性时刻均具有特殊力量,文本的文学价值在于它反映不同环境的冲突,或同另一种真实文化象征的冲突。”[4]也就是说,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还是在于它的真实性、非虚构性。受美国“非虚构文学”的影响,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实际在纪实文学的研究讨论内展开,其中不乏“拿来”因子,也有本土研究学者对纪实文学的前瞻性考量。
二、国内研究
国内的报告文学研究大抵随国外研究步伐、结合本土报告文学创作特色,粗略地分为五个报告文学发展及研究发展阶段。
(一)对“真实性”探讨的萌芽期(20世纪40—50年代)。
中国报告文学发展脱胎于西方报告文学,始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凸显的近现代文学开端时期。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家们,着重讨论报告文学的定义,对报告文学和其他散文、小说类文学做区别分析,尤其强调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基调,而此时对报告文学真实性基调的理解,在于真实写作、类似报导写作,在基希提倡的“亲身躬为”基础上,强调用生活的眼光理解真实。
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具备报告文学的基本形态之后,赵超构、丁玲、孙犁、杨朔等是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写作的代表作家,这时期的报告文学类似报导写作,写一个地区一群人物,就以介绍和说明的口吻来写。中国报告文学在实践及研究初期,中国作家们热切地融入历史、投身报告文学创作,报告文学加入中国文学发展史,呈现新的文学方向,同时,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基调、定义、特征定框架,使得这一文类从散文、小说、新闻中抽离出来,独自发展。赵超构文艺创作中要求作家不能隔绝生活,要对百姓(写作对象)充分熟悉和了解,不能有隔膜;并且要求“弥补缺陷的方法,就是‘学习,老作家向群众学习生活语言”[5],群众亦是报告文学真实材料的见证者。
周立波对报告文学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的作用极其重视,在《谈谈报告文学》中,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报告文学在萌芽阶段的发展仍有许多问题,提出观点可归纳为:1.报告文学不是速写;2.报告文学写作必须要全面、宏观地带入历史思考中。周钢鸣在周立波之后,对报告文学和速写、报导等新闻类稿件做了区别分析,在《怎样写报告文学》一文也强调报告文学既不能和速写等同,也不能向小说靠拢;报告文学的基调是真实性,就应当真实写作。而周立波、周钢鸣的“真实性”等的要求,其实是对基希等人的报告文学理论的移植创新发展。
“五四”运动受国外思想的影响,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们鲁迅、谢冰莹、梁启超等人在不断学习提倡域外报告文学写作的同时,自己进行报告文学创作;他们尤其重视这种具有真实性特征的文类,在报导事实和启蒙人心基础上的积极意义。
(二)“可虚构”“绝不虚构”两大派别的争论期(20世纪50末—70年代初)。
在经历了初期发展阶段对报告文学文类界定、定义明晰之后;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阶段的报告文学理论,较多受到苏联报告文学理论的影响。对报告文学理论分析逐渐发展为两大派别,分别为“绝不虚构”派别和“可虚构”派别。而“绝不虚构”和“可虚构”的界定标准,不难从学者的论述中得出标准即为是否运用想象;想象式“虚构”的重点在主观地架构故事细节,学者对虚构与否的支持、反对,实际是对此种方法的认同与否。
秦兆阳、魏金枝、刘白羽、茅盾都对报告文学的可“虚构”做出论述。秦兆阳《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承袭上一阶段对报告文学真实性的讨论,率先拉开了文学界对报告文学真实性是否受虚构影响的论题,魏金枝的《先从报告文学特写入手》认为报告文学写作中涉及到了虚构、想象成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作者想象的影响,也就存在某些虚构描写;两位学者都认为报告文学的“虚构”是在所难免,作家及理论研究者都不应当排斥报告文学对“虚构”的运用;在处理报告文学中发生在真实人物的真实事件时,“我们要提倡艺术真是的塑造法”[6]。
刘白羽曾在《新闻战线》上发表《论特写》,着重阐释虚构的可能性,指出报告文学就是材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合体;虚构是为了艺术性地塑造作品,而真实写作又是对现实生活材料的加工。茅盾则趋向于关注人物事件典型与全真实的矛盾,也作文并以一系列苏联的报告文学作品为例,肯定典型和真实人物、事件是可以通过艺术构造共存的,报告文学对真实性的要求绝对不会因为人物典型性的塑造而受到干扰;换角度而言,茅盾认同适当合理的想象有助于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发展,迎合了人物、事件典型性的要求,而虚构的艺术加工正离不开想象力的推动。
冰心则从自己的作品出发,用“虚构”手法创作报告文学作品,以行动来回应报告文学可以虚构的号召;《咱们的五个孩子》《颂“一团火”》《神圣忧思路》都是用质朴的文学笔法来诉真人真事。袁殊认为:“报告文学,是把心灵安置在事实的报告上;但不如照相写真样的,只是机械地摄写事实”;李广田说:“表面上看起来,报告文学只写已然的事实,也许无需‘想象”[7],但实际作者用材料例证报告文学各素材之间需要想象将其串联结构起来。
而以夏衍、井岩盾为代表的主张“绝不虚构”者对“可虚构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里程碑式代表作《包身工》作者夏衍认为,“报告文学绝不能虚构”,“夸张也是绝不允许的”。[8]井岩盾推崇写作的“不虚实”、“不虚美”,认为文学作品就是在掌握了真实材料之后加工构造而成的,纪实性作品文学性特征因而生成。
在《真实和虚构》这篇文章当中,井岩盾并未指明对象地对奥维奇金“报告文学可以虚构”的观点进行抨击,明确说明包括回忆录、传记之类的文学作品决不允许虚构;他认为,作者和读者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契约,读者要理解作者的意圖,作者也要倾向于真实地展现需要描写的生活。郭小川也认为,真人真事是报告文学的基本特点,在宣传上具有独有的威力,不能被虚构的故事所代替,并赞同报告文学不应存在合理想象的观点。60年代的报告文学理论发展,实际是报告文学理论发展中争论开始的一个起点,伴随着报告文学的发展,对报告文学“绝不虚构”“可以虚构”的讨论一直继续。在报告文学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中仍然突出。
(三)真实性原则的再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
进入新时期后,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开始恢复,对“真实性”“政论性”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黄钢《报告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必须严守真实的党性原则》中,将“真实性原则”作为报告文学的首要原则加以提倡,《一个新闻工作者谈报告文学》胡绩伟则专门从新闻性的角度来谈报告文学的写作等。
而对“真实性”的要求,则从上一阶段的报告文学应“绝无虚构”和报告文学可以“适度虚构论”的激烈争论,到达新阶段上对报告文学可以“适度虚构”的更多肯定。“绝不虚构”的支持者夏衍,从报告文学文体的性质出发,仍然坚持对“适度虚构论”者进行反驳,坚守真实就是完全真实的观点。认为报告文学不应该有任何的虚构成分,如若要虚构,就应当直接作小说。支持报告文学“完全真实”的黄钢,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过大量特写报告文学写作经验,并承认报告文学“绝对真实”的穆青,在建国后报告文学的写作中仍体现“虚构”的想象性描述,并且在理论上还提倡作家在报告文学写作中要运用想象去塑造真实。
事实是,越来越多学者如徐迟、罗荪、林帆、萧乾都纷纷对运用想象进行报告文学的“适度虚构”或“略有虚构”表示赞赏。70年代初写出《歌德巴赫猜想》的徐迟在《再谈散文》这篇文章中说:“速写,或称特写,或报告文学,就完全是实况的写照了。但也允许略有虚构,不离真实的虚构。如果有了较大的虚构,它就变成了小说。”[9]徐迟还对“略有虚构”做出解释,以陈景润收苹果再三推辞的对话为例子,说明事件细节的虚构也是在所难免;这种虚构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在不失真实的情况下,尽量还原人物特征。由“略有虚构”而生的“适度虚构论”,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萧乾、李延国、钱钢等的努力下,报告文学的形势不仅朝着中长篇发生变化,还突出了报告文学可以全景式、宏观式写作的新特征。
罗荪1977年在《解放日报》发表《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战斗作用》中再倡报告文学的文学叙述,应塑造人物典型,反对因曾受江青和张春桥的“反真人真事”,坚决强调可以细节虚构,突出真人真事;林帆又在罗荪之后《是报告,也是文学——谈报告文学》中补充罗荪观点,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赞赏胡绩伟“有些加工和虚构”的观点,紧随而来的报告文学小说化长篇潮流,更是得到了萧乾的盛赞,萧乾在《当代》中发表的《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曾形容报告文学如插上了翅膀一样,正在一展宏图。正是越来越多理论家对“适度虚构论”的支持,使得报告文学在新闻性和文学性兼具的情况下,对时事进行报导,对生活原貌描写的同时引入对生活的思考;也引导着更多读者的理解与思考。
(四)理论创新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末
19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末,报告文学理论研究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1.发展“可虚构”理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理论家中,以继续支持“可虚构”的李炳银先生为代表。李炳银在两本小说研究专著之后集中研究报告文学写作及理论。李炳银被称为“报告文学的账房先生”,他的研究特征是“多向度”和“实证研究”。聚焦点包括报告文学文体定位、报告文学价值和责任,以及传统的研究命题“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之辩证关系。
李炳银反对将两者对立,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是以虚构为手段;而报告文学不应因真实性而反对虚构。李炳银还一反传统对报告文学批判性或赞美性的单向认知,认为报告文学不仅可有虚构,且文学就应当以审美为追求,再综合其他效用。正如他所言,“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独立的理性评判是报告文学的灵魂,文学艺术的表达是报告文学的翅膀”[10]。李炳银对真实的强调,是赞同文学性丰富报告文学的“原汁原味”,正如他在《报告文学的文学不等式》所说“报告文学可以依赖作者自己的社会经历感受和阅历体验而更多主观的去虚构想象表达。”[11]李炳银、王晖等学者对“可虚构”的支持、西方“非虚构文学”的发展等,将报告文学可否“虚构”再一次拉回读者视野。
2.多元西方理论的渗入:丁晓原则尝试将文化学理论与报告文学相结合研究,其专著《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中对报告文学的话语空间、叙述形式等诸多内容进行开放性分析。王晖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事模式》从经典叙述学角度出,总结了19世纪报告文学作发展、研究概况。实际也是对报告文学“略有虚构”肯定的基础上,对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等进行分析。《新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事模式》在对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梳理的基础上运用了热奈特的叙事理论,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的角度进行报告文学的科学分析。
同样,《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研究》将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叙述距离、叙述聚焦、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功能、民族叙述、叙述话语与非叙述话语逐一分析。《论十七年报告文学的叙事话语》和《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者叙事》也都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各个时间段报告文学写作的叙述特征。《报告文学叙事视角分析》阐释各种不同叙事视角如何生成不同的视觉审美艺术,诸如此类的分析。
叙述学理论由80年代的传入,随着报告文学研究者的不断探索,直到21世纪,仍占重要位置。特别是在网络技术发展、影视传播发展的背景之下,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熠熠生辉,报告文学因此与纪录电影的联系更为紧密。可以说,国外理论的引入,不论是强调文化的文化批评研究,还是强调形式的叙述学研究,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国内作者一道,使得国内报告文学同世界报告文学样也呈现多元状态。
3.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章罗生专著《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和一系列学术论文,都持续关注着报告文学界的“审美新变”。章罗生的观点总结起来大致有三:其一,章羅生肯定了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受中国传统文化、国外文学和思潮影响下东西兼并的艺术门类;其二,他认为报告文学兼具了中国传统小说、戏剧等民族文化特征和西方理性、新闻性追求,是新闻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而当今中国的报告文学发展正朝着中西、新闻与文学融合的道路发展,越来越趋于成熟和细致。其三,章罗生同李炳银同样,并不赞同报告文学单纯的“批判、讽刺”功能。
另外,龚举善也在报告文学研究方面做出贡献。他是在历史的背景下,以当前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主题、体裁以及发展方向研究为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转型期报告文学论纲》中,龚举善对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径和导向,报告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动力有着独到分析。尹均生、王晖、周政保、周森龙和张立国等学者都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研究者的代表,在各自的着重点上各有建树。
第二阶段:网络形式转型阶段(21世纪——至今)
21世纪以来,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随时代科技的发展也异彩纷呈。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的进步,为报告文学的网络转型提供动力。报告文学同纪录片一样,也受电脑科技的带动,引起了学者研究的精细化和新颖性。丁晓原对报告文学的研究,就是以文化生态视角为切入点;而网络娱乐化的发展,势必会引起群氓文化的泛滥;如何引导报告文学的正向发展,如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等多角度的理论视野来掌握转型后的报告文学,也成为学者的研究突破口。2012年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报告文学艺术论: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理论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当中就收录了40篇报告文学相关的研究论文,从作家个案角度进行理论阐述与探究。
龚举善专注于报告文学的转型之路,结构方式、叙述方法、主体意识以及报告文学的形式创新、传播路径、接受主体的变化等都在龚举善的研究范围之内。《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正是龚举善对转型之路上的报告文学的一次过渡性总结,分析阐述了报告文学是如何介于“两种真实”之间存在,报告文学如何改革发展,报告文学题材的新拓展等重要问题。随着电视文学的提出,让更多学者转向于报告文学新世纪发展之路。王金洲《电视报告文学新闻性真实性和艺术性新探》、景国真《电视报告文学的表现特色》、吴戈《论报告文学与电视纪录片的互补共构》等研究论文着手探讨电视文学的表现艺术、电视与报告文学的互构性关系,两者的关系研究也是本论文的实践之一。
“虚构”作为报告文学的特殊创作技巧,经历了理论家较长时间的争辩,报告文学也在当代发展中经历着转变和新发展;电视报告文学的突起,也吸引了更多人对报告文学和电视纪录片的整合性研究。对报告文学“虚构”的理论研究成果之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非虚构作品研究的基石,意在期待无远弗届之效。
参考文献:
[1]川口浩.报告文学论[J].北斗,1932(1).
[2][7]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M].武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57,160.
[3]李光荣.基希——中国报告文学的乳母[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3).
[4]诺曼·西姆斯.文艺型记者[J].交流,1986(1).
[5]余仙藻.赵超构和他的《延安一月》[J].新闻和传播研究,1981(5).
[6]丁晓原.论五六十年代报告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J].学习与探索,1998(3).
[8]夏衍.报告文学的几个要求[J].新闻业务,1963(5).
[9]徐迟.再谈散文[J].湖北文艺,1978(1).
[10]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4.
[11]李炳银.报告文学的文学不等式[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