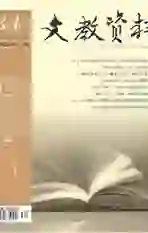来路与归途
2018-03-27向明媚
向明媚
摘 要: 《世间已无陈金芳》自发表以来颇受好评,小说将焦点放在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女子陈金芳身上,提出了底层人民在都市的生存问题,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底层文学与底层人民的出路问题。将精神和灵魂寄托在故乡或许是在都市挣扎的底层人民保存自我的一个良方,而作家深入底层人民的程度也关系着底层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 《世间已无陈金芳》 底层人民 都市的生存 底层文学
底层文学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城市的快速发展导致其对乡村挤压越来越严重,农村的低收入和都市的诱惑使得更多的农村人涌入城市,然而阶层的固化、机会的不平等种种原因导致他们的奋斗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作家们适时地关注到了这些问题,怀抱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信念,将底层人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以他们在城市的遭际作为小说的故事情节,写出他们的艰辛与挣扎,以此呼吁社会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其中不乏用心。《世间已无陈金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给广大的读者留下深刻地印象,与其言说方式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一、贴合与分离:小说的双重叙述视角
《世间已无陈金芳》这部小说是以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我”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堕落的少女的故事,并时常以“我”的认识对陈金芳予以评价,小说虽然没有写出“我”的名字,但是有心的读者可以将“我”和石一枫《恋恋北京》中的主人公赵小提进行关联。《世间已无陈金芳》这部小说虽然以“我”为故事讲述者,但我们知道,小说讲述者的观点并不代表作者的观点,叙述者的观点和作者的观点可能相同也可能相反,相同的时候便是作者借用人物之口发表自己的言论,不同的时候则存在多种情况,或表达反讽之意,或强调某一观点等等。这篇小说就很好地处理了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在让主人公尽情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又将作者本人的想法渗透在文本之中。
作者赋予叙述者“我”的论调是较为客观疏离的。少年时,陈金芳于“我”而言仿佛世间一粒普通的微尘。她的突然出现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她独特的“饮食习惯”更是为“我”所不解,她被同学围攻,与家人发生矛盾,“我”一直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没有给予她安慰,甚至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同情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疏离的态度也保持了某种客观性。在同学因为她的虚荣攻击她的时候,“我”则觉得虚荣心人人都有,还提出了“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的观点,揭露了最普遍的人性。
然而,当“我”音乐会再遇陈金芳时,原先的“事不关己”的情感好像已经转化为一种轻蔑的讽刺。她的叫好声在“我”眼里是“欧式装逼范儿”,“我”认为她想从和“我”的谈话中“忆苦思甜”,甚至她精致的衣着和妆容还有改过的名字在“我”看来是“内外兼修”的变化!是否在这里,叙述者口中所说的“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已经发生在他身上了呢?当别人在某个方面低于自己的一级时,我们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同情或无视;但当他们试图追赶或者超越我们的时候,我们则觉得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甚至置疑她的能力和资格。赵小提是不是在这里好像已经成为了他口中的那种人。
以上都是叙述者“我”的观点,那么在作者眼里是不是也是如此认为呢?随着小说故事的发展,可以发现其实作者并不是与讲述者持同样的观点。在讲述者保持冷漠疏离的态度讲述陈金芳家的吃食,她异常强烈的虚荣心,还有与家人发生争斗,作者其实表达了自己潜藏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每当讲述者沉入自以为是的猜测时,现实情况就发生反转并予他迎头痛击。陈金芳用宽厚和爽朗的微笑回应“我”原本想象中的“忆苦思甜”,陈金芳与豁子分手也打破了“我”原本的想法。透过这种反转,似乎可以稍微透视作者的本意。
还有在男女主的感情上,小说没有明确地指出两人之间有着爱情的关系,以“我”的主观视角来看,“我”从没想过陈金芳是否喜欢“我”,无论是她听“我”拉琴的时候,“我”与豁子打架的时候,还有两人再次相遇,在我眼里“我”就算与陈金芳有点什么关系也是能算是“露水姻缘”,她与我而言最终成了像初恋又不是初恋的人。但是作者传达给读者的却与赵小提的自我认识不同,“我”因为陈金芳的倾听弹出了有“人味儿”的琴声,陈金芳的解围,陈金芳想要买钢琴,以及陈金芳对“我”的了解等等,还有“我”因为陈金芳的两次喝酒,无论“我”对陈金芳是什么感情,陈金芳对“我”确乎是存在着爱情了。
因此,这篇小说始终贯穿着的两种情感维度是不容置疑的。在表象的文字層面,作者以叙述者之口,使读者了解到陈金芳的基本故事,这包括不同阶层之间的不理解,包括“我”年幼时的无视和成年后的轻蔑;而在情感深层,作者却时时刻刻表达了对陈金芳的关注,表达了对陈金芳被人误解的同情。
石一枫是抒情的,在这一方面,《世间已无陈金芳》不像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那样做现实图景的还原。但他又时刻做到了感情的节制,例如陈金芳在反抗家人的时候说:“你们把我领到北京,为什么又让我走?为什么又让我走?”此处作者特意强调陈金芳是用“普通话”说的这一句,然而又仅限于此,不做过多的情感表露,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双重叙述视角其实一直贯穿在小说中,作者借漠然的赵小提之口表现自己某种程度上的“零介入”,又在叙述上故作巧思呈现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二、互换与对峙:“我”与陈金芳的奇异关系
赵小提一直以一种淡漠的态度看待陈金芳,但是对于陈金芳来说赵小提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存在。如果深入地观察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其实有一种曲折的“对峙”与“互换”关系,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将从前的“我”和陈金芳以及现在的“我”和陈金芳做一个比较。
首先,表层身份地位的置换。这部小说采用倒叙的手法,先讲了“我”和陈金芳的再遇,然后追溯到陈金芳的来历及其他相关的事情。在当时生活优渥的“我”看来,从乡下来的陈金芳就像一个“桌子”或者“板凳”。“我”原本有着很好的条件,少年时拉得一手好琴,最终却艺考失利,只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后也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只是一直晃荡着混日子,“我”本来还有一个不错的妻子,但是却用一再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终结了这段婚姻。相较之下,陈金芳来自农村,她生活贫寒,家里还有理也理不清的琐事,她学习不好也无法继续学习,她与家人闹僵并以出卖自己身体的方式获取生活的必需品。小说将成年后的陈金芳塑造成一个美丽动人、颇富交际手段的人,而且有着充足的金钱。这样看来他们的身份好像有一个置换。
其次,心理情感的对峙。相较于陈金芳的光鲜亮丽,碌碌无为的赵小提只是一直在混生活而已,站在这样的人面前,“我”好像是低她一头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虽然表面赵小提觉得“我不如她”,内心里还是觉得她“配不上我”。陈金芳也看到了赵小提的不屑,自嘲说自己挺土的。此外,小说虽然以赵小提为故事的讲述者,但是趙小提对陈金芳的认知却少得可怜。他不知道她陈金芳的钱从何而来,不愿意谈起她的过去也不愿问她的现在。他用一种自以为是的世俗观念看待所有陈金芳,自以为了解并“看破”了她的所有,然而却发出了两次毫不准确的猜测,在这些猜测里包含的是嘲讽与恶意。陈金芳对“我”的认知十分清楚,她两次说中了“我”的本质:“表面赖不叽叽的,其实骨子里傲着呢”;“优点在于敢贬低自己,这显得很有自知之明;缺点则在于你总是觉得贬低完自己,就有资格去伤害别人了。”
这种身份上的转换与心理上的对峙其实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底层人民奋斗的艰辛,他们通过努力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金钱和地位,打破了固化的阶层,却并没有获得原有阶层的心理认同。将这一现象抽离文本,好像也可以用其说明现在的底层写作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作为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市民阶层的代表,对陈金芳的认识和理解十分有限,这不仅是由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导致认识的困难,还由于“我”根本没有想要走进她了解她的意愿。因此,“作家能否真的为底层群众代言”[1]一直都是底层写作探讨的一个问题,对于一些并非出生于底层的作家来说,他们能不能真正的理解对底层人民,言说底层人民,也是底层文学应该关注的问题。
三、来路与归途:底层文学和底层人民的去处
陈金芳是一个接受了城市文化,想要趋近现代文明而不得法的典型,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要为陈金芳走上末路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若是从生命个体本身探寻她堕落的原因,恐怕要归于心灵上的“假充实、真空虚”。她通过接触城市文明,貌似部分地充实了原本来自乡村的她自以为的贫瘠的内心,这种“充实”使她获得了相应的快感,也改变了她原有的价值观念,因而她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种“充实”最大化,但可悲的是,她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换来了本金却又丝毫不懂生意场上的经营,最后又以非法集资和投机投资换来满盘皆输。她年少时的生命体验:夜晚的琴声,偷穿的衣服,烙铁烫的头发,鲜艳的口红等等,那些所谓的“充实”,只不过将一种“空虚”置换成了另一种“空虚”。
如果联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好像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生活在别处”最早由诗人兰波写出,他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诗人的理想生活永远都在别处,而不是此处,这就像陈金芳一生的追求一样。但是,当“别处”变为“此处”之后,那些曾经追求“别处”的人又当作何打算。当陈金芳跨越了所谓的阶层差别,跨越了城乡界线,成为像“我”一样地道的城市人,那么生活上是不是也向现在的“我”靠近,那么“我”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出生在北京,在生活上衣食无忧;在人生选择上,父母早已为“我”选择了拉小提琴这一道路。“我”的生活好像“一丝不苟”,然而实际上,“空虚”从生活的缝隙巧妙地钻进,“我”被认为是过度开垦的煤矿,连原本因为陈金芳聆听变得有“人味儿”的琴声也不复存在。成年后,事业上的不求上进,婚姻的草率态度,究其本身,未免不是心灵上的“空虚”。有人把石一枫笔下的这种人物类比于王硕的“顽主”,或将其归结为具有“犬儒”性格的人,这都具有合理性,连石一枫自己也称笔下的人物的犬儒主义者。[2]“犬儒”是一个具有宽泛内涵的语词,徐贲的《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就为犬儒找出了多种特征,因而与其用犬儒来形容赵小提,我更愿意用犬儒的一个特征来形容他,那就是“看穿”。虽然徐贲在书中说“将犬儒只是限定为悲观绝望的那种‘看穿或只是‘知与‘行的分裂,便有可能将犬儒的范围规限得过于狭隘”,但是这恐怕是赵小提犬儒性格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他所有的其他性格和人物行动都是基于“看穿”这一特质的,正是由于这种看破,使他无视了人生的意义,就获得了于他而言的一种“空虚”。因此,对于陈金芳和“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双重失败。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并不是在否定人们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和肯定消极的人生态度,追求理想是有价值的,问题的症结在于“空虚”。
那么对于“陈金芳们”来说,人生的出路到底在何处?他们应该怎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作者显然没有给出这个答案,社会也不可能提供一个完美的方案。但是在有些类似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有曲线地提出一些意见。既然问题的症结在于“空虚”,那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消除这种“空虚”。李凤群的《背道而驰》讲述的也是从农村到城市打拼的青年男女的故事。小说中的女子,有不满家长包办婚姻逃离乡村的(田园),有为了追求物质享受出卖肉体的(白雪)等等;小说中的男子,有单纯向往城市生活的(小弟),有一心一意想在城市扎根的(康志刚)等等。但是,当他们在城市饱经风雨之后,这些人都有了部分地精神向乡村的“回归”。田园消除了与父母的隔阂,在城市生活多年的康志刚突然想要回家去看看,白雪说给养父买了衣服,诸如此类。李凤群为奋斗在城市的人提供了一种自我保存的方法:从乡村获得精神安慰。
李佩甫的《生命册》讲述的是从农村到城市的青年吴志鹏的故事,他进入城市后先后做过教师、枪手、商人等。当老师的时候,他不满别人总是说他是“新来的”,继而因为不想受到农村乡邻一次次的委托,所以选择辞职,去往北京发展。他本以为到了北京将有编纂古籍的宏图大业等着他施展,却不料这个计划却并没有实现,他只能成为一个枪手,浑浑噩噩的混日子。后来,他和好友骆驼终于在股市和生意场上一展身手,捞到了不少好处,但是长期以来经商所采用的不正当的手段被人揭发,好友骆驼生意失败跳楼自杀,他因为脱身较早侥幸躲过一劫。吴志鹏离乡多年,终于借着为姑父迁坟的事重返家乡,这是的他已然有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的心境,“在我,原以为,所谓家乡,只是一种方言,一种声音,一种态度,是你躲不开、扔不掉的一种牵扯,或者说是背在身上的沉重负担。可是,当我越走越远,当岁月开始长毛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惟一能托住我的东西。”[3]这部小说也以这种“离乡——进城——还乡”的模式构成,在某种程度上替那些执意想要逃离乡村奔向城市的人预演了一次人生的奋斗旅程。
然而,这种“精神的回归”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于好不容易从农村中逃离出来的像陈金芳一样的人来说,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剪断與农村的所有关联,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无情而决绝的。所以,在他们从乡入城的初期,是不可能产生这种想法的。此外,在经历也风雨之后,他们的精神究竟还能不能回去也是一个问题。就如《生命册》的的结尾处吴志鹏所说的话:“可我说不清楚,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还能不能再长回到树上?”“也许,我真的回不来了。”[4]对于已经体验过城市生活的人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还有千千万万个正在从乡村奔赴城市的人,就像《背道而驰》中的小弟,对于他们,可能在历经了城市生活的艰辛后,才能有所悟,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避免自己被“空虚”所占领。
对于底层写作来说,显然与时代紧紧结合在一起,它言说的是对整个时代和社会发展给底层人民带来的冲击。底层写作尽管有着不俗的成就,但是还是存在着不小的问题。王晓华曾将底层写作分为三个层次:指向底层的文学,为了底层的文学和底层自身的文学[5],而为他所肯定的也是至少进入到第二个层面的底层文学。然而,正如上文已经提到过的,作家是否能够真正地了解底层人民并且为其代言,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无法得知,作者在言说这些群体时,是否将其作为“他者”。另外,广义的底层文学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文学史上从不缺乏对底层人民的书写,但是在新世纪以来,在社会环境和政治政策的影响下,这类文学作品变得越来越多,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底层文学之于当代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显然,底层文学能否以一种文学类型进入文学史是任何人都无法断言的事情,就目前的底层文学写作来看,想要进入文学史,其实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四、小结
《世间已无陈金芳》以一种油滑而不失严谨的笔法揭露了这个时代的问题,无论在艺术表达上,还是在人物塑造上,都大大超过了同时期同类型的小说,在底层文学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文学界较高的评价。这进一步引起了学界对底层人民和底层文学的关注。从众多相似的小说来看,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尽管想要转换他们的身份,但他们精神的依托只能在乡村,这也是在城市奋斗的他们自我保存的方法。而对于底层文学而言,作家则承担着尤为重要的责任。
参考文献:
[1][5]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J].文艺争鸣,2006(4).
[2]石一枫.我就是一个传统作家[J].芳草,2015(5).
[3][4]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