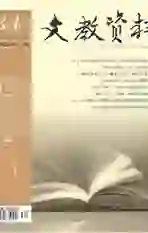《一座城池》中的叙述反讽
2018-03-27程儒珺
程儒珺
摘 要: 韩寒的作品一直以幽默简洁、辛辣明朗见长。而反讽作为韩寒作品中的常见手法,往往在指此言彼和正话反说之间,造成一种颠覆嘲弄的否定效果。分析把握《一座城池》中的叙述反讽,从其表现形态、社会意义以及内核力量出发,来领略韩寒的价值谱系和个人成长,更重要的是透过韩寒的作品,来体会出一代青年,在特定时期内的文化认同、价值选择和精神风貌。
关键词: 韩寒 叙述反讽 《一座城池》
韩寒自初渉文坛起,便引发轩然大波。“当代鲁迅”“问题少年”“文化英雄”的称号接踵而至,褒贬不一的评论、是非蜂起的论争纷至沓来。而《一座城池》,被韩寒自己称为“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作品”。它延续了以“反讽”作为主要修辞艺术的韩式风格。其中的叙述反讽,既是一种文学创作的手段,更是作者对话外界的窗口。在看似幽默的叙述反讽背后,凝聚着青年一代的精神气质,以及作者韩寒对现实最深的思考和期待。
一
《一座城池》主要讲述了一群青年因一次打架斗殴事件而从学校肄业,从此过上了亡命天涯的流浪生活。他们随心所欲、目中无人,这座陌生的城池成了他们的乌托邦,一切都只为了自由地活着。作者借这群漂泊流浪的少年之眼,目睹了各式各样的传奇经历,在诙谐简洁的叙述之中,展现了复杂丰富的反讽姿态。
其一,幽默风趣、插科打诨的语言反讽是作品中叙述反讽的主要结构。首先,在《一座城池》里随处可见嬉戏、幽默、夸张和拆解,形成简明硬朗又略带讥诮的话语风格。“这点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那些明明都是下流的人,为什么凑一起就叫上流社会呢?”[1]“大学里怎么会有学生要当二奶?”“你这么想当然想不通了,你就当人家二奶有上进心来上大学就行了。”[2]作者借助这种言此指彼、正话反说的方式对社会现象进行反讽式的拆解,从而将个人与历史相关联,加深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除此之外,这种语言反讽也表现在粗俗与崇高、严肃与调侃的二元融合上。作者往往在表达某个严肃的观点和看法之后,紧接一个幽默、粗鄙的调侃,在这一雅一俗之间,不言自明的讽刺效果已跃然纸上。例如“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要把这些所谓的安全感托付在一些身外之物上,比如房子或者在银行的存款。这地球是如此不可靠地悬在宇宙之中,地震、战争、经济崩溃等等随时会把我们的身外之物夺走。”对此主人公在经过一番认真地思考、咨询后得出结论:“当然是安全套能带给我们安全感啦。”[3]上一秒还在感叹现代人对身外之物的追逐,下一秒则用玩世不恭的调侃来化解正经严肃的作品氛围。在严肃话题与粗鄙词汇的不协调之间,形成一种嘲弄式的反衬。值得注意的是,在语言反讽里,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作家与叙事人的不同。“作家通过反讽设置一个与他本义相反的叙事人。叙事人传述了表层涵义,但叙事人具有明显的虚伪标志,令人难以相信;于是,人们越过了叙事人,沿着一个相反的方向看到了作家所欲表现的潜台词。”[4]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背道而驰,构成了文本的张力结构,表层辞令和深层内涵既相互排斥,又相互独立,二者在相互作用的同时造成一种嘲弄的否定效果。
其二,除了表层的言语反讽外,《一座城池》中的叙述反讽也表现在更深层次的情境反讽上。按照米克的观点,在言语反讽时,人们往往站在反讽者的角度,而情境反讽则让人们位于观察者的立场上,人们冷眼旁观着事态的演变,因而更具哲理性和悲剧性效果。在《一座城池》的故事开头,作者先用戏谑的笔调描写了“我”在车站打公用电话、打出租车等一系列从被骗到被威胁直到不得不从的讽刺场景。在这其中作者不再使用不正经的词汇,严肃的白描与尖锐的嘲弄之间形成令人捧腹的喜剧效果。又例如文中写道“我”、健叔等人因走投无路而心怀愧疚地把一个坏了的取暖器以1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个老头,可三天后发现老头在原地卖取暖器,且旁边立了个牌子“全新取暖器,儿子送,家中已有,200元。”[5]此时的老人已不满足于原价卖,而是已经吃亏了还想再赚点。人性中的自私贪婪、转嫁灾祸的心理在情境反讽里被一览无余。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寒的小说中,情境反讽的形成往往是一种对荒诞普遍性的认同。他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平凡到似乎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世界是荒诞的,每个人都自愿地或被迫地参与其中,这样就在故事内外都形成了令人自省的讽刺情形。
《一座城池》在语言反讽和情境反讽两方面展现了复杂的反讽姿态,它延续了韩寒一贯的简洁明了、幽默辛辣的作品风格,而其中的叙述反讽与韩寒的其他小说相比,又有着不同之处。
在韩寒以往的作品里,无论是《三重门》《像少年啦飞驰》还是《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我们虽可以透过文字体会出作者的言外之意,但韩寒往往采用局外人的俯视视角,他不带感情、冷眼旁观地俯视着人们的一言一行,在毫不留情地嘲讽之余却并不会明白显现地流露出自身的价值批判和个人立场。而在小说《一座城池》里,作者不再游离于故事之外,而是在反諷的同时直接表现出自身对事态的看法和评价。例如在小说最后,描写到城市居民借着爆炸的契机而抢砸商店,甚至不惜互相侵犯、大打出手时写道“我觉得这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已经暂时不是人了。随着天色渐渐昏暗,路边开始出现头破血流昏迷不醒的人。我觉得周围有很多野兽看着,不过幸运的是,我也是其中的一头,而且奔跑的速度大家都差不多。”[6]在这里韩寒不仅批判了人性的异化和兽性的显现,且对于叙述者“我”也开始有着自我反思。一直以来,韩寒作品中的主人公“我”都是叛逆少年的代表,他们玩世不恭、放荡不羁,是现行文化秩序和价值符号的反叛者。作者往往借助这些反叛者来表现对社会现象的思考,他们身上留有韩寒自身的影子,因而对于他们出格的言行作者往往采取默认、包容甚至赞许的态度。而在《一座城池》里,作者在批判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自身,这种双重关照使得其小说在思想层面呈现出更加成熟、圆融的姿态。
二
戴锦华曾指出:“如果说新中国的第一代艺术家是为革命战争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所造就;那么此后的几代人则是在反叛自己的生长年代,反叛‘喂养自己的文化的过程中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彼此间的指认。”[7]作为青春文学的代表作家,韩寒的言行和作品在青年一代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作品中的叙述反讽是一种价值符号,具有普遍的时代印记和社会意义。
其一、《一座城池》中的叙述反讽映衬出青年一代的叛逆心理,成为青少年寻找共鸣和宣泄情绪的出口。逃离学校的问题少年、浑浑噩噩的日常生活、同甘共苦的哥们儿义气、令人向往的美好女性,诸此种种成为韩寒作品中的共同母题。作为“80后”的一代,韩寒的作品映衬出一代青年的叛逆心理。青年有青年的烦恼,他们不愿不顾一切地“呐喊”,也不愿就此悄无声息地“彷徨”,无法毫无忌惮地“释放”,也不愿一味迁就地“压抑”,敏感而又细腻的他们在韩寒的作品里找到了情绪宣泄的出口。例如在《一座城池》乃至韩寒的其他作品里,粗鄙调侃的用语随处可见,如“装逼”“二奶”“妓女”“手淫”等等,但如此大胆犀利的用词非但没有受到指摘,反而备受青年的追捧。这种用粗俗简洁的词汇来谈论公共话题的方式,满足了大众的心理需要。青年们在韩寒身上看到了偶像的影子,韩寒身上也映衬出青年一代的精神气质。于是韩寒成为广大青年的代言人,故事主人公的叛逆生活让他们好奇向往,他们在韩寒的叙述反讽中找到了共鸣,放松著被长久压抑的自我。
其二、《一座城池》中的叙述反讽也引发出对一系列公共话题的反思。在《一座城池》里,有不少片段涉及对权力体系的嘲讽。例如媒体虚假宣传、医生宣称“救死扶伤”而并非“免费救死扶伤”等等,引发民众对公共话语尤其是权力体系的反思。对于这个时代,似乎每个人都有话要说,但又不知如何表达或不敢表达,欲言又止的他们在韩寒那里得到了排解。敢言他人之所想,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这种幽默辛辣的讽刺,因其所指渉对象的权威性而更有大快人心的效果。例如对于报纸上说,市民爱去图书馆或者博物馆,居民的精神面貌有了巨大的改善。作者紧接着反讽道“这篇报道很有前瞻性,因为市图书馆和博物馆还没落成。当然也能理解为市民们按捺不住期盼的心情,纷纷自带书籍在图书馆工地上阅读,或者在博物馆工地上参观施工过程中挖到了一些文物。”[8]一方面,这种叙述反讽是大众自我宽慰的独白和缓解焦虑的途径,面对权势的强梁,大多数人都没有公然面对的勇气,于是这种幽默诙谐、冷嘲热讽便成了他们对自身境遇的安抚。另一方面,这种叙述反讽更映衬出一种扭曲变形的反抗,这一点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80年代的王朔、90年代的王小波、新世纪十年的韩寒,他们是不同阶段的代表。‘戏谑美学的深刻之处,正在于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抵抗策略,应对着‘脱历史的疏离与分裂。”[9]此时的叙述反讽颠覆着主流话语系统,它在反思公共问题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参与了社会道德的建构。人们在反讽里看到了“意见领袖”和“社会公知”,叙述反讽也成为民众眼中的利器,以此来对抗着社会的不公。
《一座城池》中的叙述反讽,既映衬出一代青年的叛逆心理,更因其涉及到对公共问题的思考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韩寒以一种去精英化的形态介入社会生活,人们在作品的叙述反讽里,看到了自己不敢表达的切实想法,此时的韩寒不再是作家韩寒,而是他们内心里最真实的自己。
三
反讽是一种否定、一种拆解,但拆解的背后必定有其潜在的内核力量。而韩寒叙述反讽的精神内核,则是一种对人生的怀疑和生命的漂泊之感。
黄平曾称韩寒的杂文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游击战。“这里的‘游击,不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更是游击的本义,在没有找到自己‘根据地情况下的游荡、回击。”[10]但这种游击不仅限于杂文,其小说也整体呈现出一种虚无主义的氛围,在其叙述反讽的背后,是对世界的怀疑和游离之感。韩寒作品里的主人公始终是漂泊着的,例如在《一座城池》里,第一个出现的场景是火车站,故事中我和“健叔”自认为是杀人犯,因而一路游击、一路逃离。而在《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全文以“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作为第一句话,从此开始了主人公沿着“318国道”从上海到西藏的漂泊之路。除了故事主人公的颠沛流离之外,其作品中的叙述风格也给人一种漂泊、游击的印象。在韩寒的小说里,一般没有紧密的逻辑结构,故事发展也无太强的前后关联。他多通过主人公的对话、回忆来推动叙述进程。这种片段化、破碎化的文本内容和叙述方式,其根本指向是一种怀疑人生的虚无、漂泊的情绪。他们一路漂泊、一路游击,却也不知道该去向哪里。他们反叛着现行的文化秩序,却也构建不出自己的心灵根据地。因为内心的虚无和漂泊,所以怀疑生活的意义。作品中的叙述反讽是漂泊、空虚之感的外化,他们在叙述反讽中来获得一种自我的身份认同。
这一点在韩寒自己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少年成名的韩寒,在高中时便因频频挂科而选择退学,他高扬“七门红灯照亮我的前程”,大肆抨击教育制度。“现如今的大学像妓女一样,只要有钱,全国所有大学都乖乖排成一排随便你点,想上哪个上哪个,愿意多花点钱甚至可以几个一起上。”[11]曾经的韩寒是那样的锋芒毕露,但而今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愈发的成熟圆润,此时的他也开始反思年少时的言行。例如他在《我所理解的教育》中坦言“现行的教育制度包括高考制度,肯定无法照顾到方方面面,也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但没有一个制度是可以照顾到所有人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有着基本的公平。”[12]在十年前,我们很难想到这是出自韩寒之手。从以前的叛逆少年,到现在的已为人父,叙述反讽依然是韩寒作品中的重要特征,但已褪去了早期的伶俐尖锐,这其中的深层原因便是随着年岁的增加,其对人生的虚无和怀疑之感的自我排遣。现如今的韩寒已不再模糊自己的价值立场,而是对公共话题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态度,因而他在保留以反讽作为发声的途径的同时,而换以更加宽和包容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
综合而言,作为“80后”的代表作家,韩寒始终在青春文学的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从韩寒的成功来看,在某种程度上,韩寒自身的符号价值远远大于其文学价值。“韩寒”似乎成为一个代名词,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特立独行、亵渎权威、蔑视名流,符合人们在一个阶段内的心理需要。而“韩寒热”的出现,实际上也映衬出一代人在特定时期的文化认同和精神面貌,光凭这点,韩寒就是值得被纪念的。
参考文献:
[1][2][3][5][6][8]韩寒.一座城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141,58,35,148,209,44.
[4]南帆.反讽:结构与语境——王蒙、王朔小说的反讽修辞[J].小说评论,1995(05).
[7]转引自徐世强.通往现实的“三重门”——论韩寒及其小说创作[J].文艺评论,2008(6).
[9]黄平.反讽、共同体、和参与性危机——重读王朔《顽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7).
[10]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J].南方文坛,2011(3).
[11]韩寒.杂的文[M].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08:25.
[12]韩寒.我所理解的教育[EB/OL].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94692043550866,2018.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