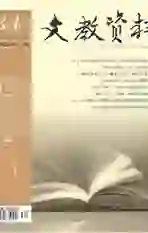“爱”与“忏悔”意识
2018-03-27左凡
左凡
摘 要: “五四”先驱者们作为“历史中间物”,在新与旧的夹缝中成长,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承担者,鲁迅、郁达夫、郭沫若、丰子恺、许钦文、庐隐等人开启了中国现代童年母题文学之风,他们对童年时期所受的创伤书写充分肯定了儿童的独立意义与价值,表达出对个性解放的诉求,而他们对记忆中人物的刻画更多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爱人”之心,同时,他们也在在文学的精神向度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在反观童年时表现出了忏悔与自救的反思品格,为完整的“人”的觉醒走上历史舞台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童年创伤 自爱 爱人 忏悔人的觉醒
“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是新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突破口,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成为了“五四”作家共同的特征,他们往往从自身经历出发,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独特感悟与对社会的现实诉求。“人”的发现也包含了对儿童的发现,正是“五四”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创作主体才得以将童年时期获得的心理体验纳入现代性的思想意识体系中加以观照。在此之前,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根深蒂固的“老者本位”观念深入人心,儿童不具有个人的独立性,只是作为一个“缩小的成人”[1]被封建礼教禁锢着。二十世纪以来,大量的西方文学(包括西方儿童文学)被译介到中国,“五四”作家们一方面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关注儿童世界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在“人的解放”思潮下,儿童的独立性得到了众多作家的重视,他们意识到只有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儿童也觉醒了,才可能实现完整的“人”的觉醒。
周作人提出“儿童本位”的文学观念,将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来看待,为中国现代的儿童观开辟了道路,此后,鲁迅在1919年提出了“幼者本位”[2]的观点,表现出了对儿童独立性的高度关注。周氏兄弟对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关注为现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对自我童年的反观成为了“五四”作家新的的创作题材,自此开创了现代文学童年叙事的母题。“五四”时期的作家在对童年创伤经验的书写中抒发了童年的经验与感悟,不仅有儿童自己经历的创伤,也有他人的悲剧给儿童心理留下的烙印,在童年创伤书写中,一个人的故事往往凝结了一代人的经历,关心作家们的童年创伤书写不仅有助于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也是以回溯的方式重新审视过去的伤痛的心理重建过程。
一、哀:天性的扼杀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说到“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天性,不使他自由发展”[3],而童年又是人的一生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接触的人事都会耳濡目染地影响儿童。童年期儿童的智力发展与概念增长极为迅速,在这个阶段,游戏对儿童的发展具有无法忽视的作用,对儿童天性的扼杀最大程度体现在对儿童游戏行为的剥夺上。鲁迅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清醒,以冷峻的笔调谴责对儿童天性的扼杀行为,此后冯雪峰、李广田、邹韬奋、萧红等人都沉痛地批判了传统礼教给儿童精神上的负担。兒童天性的被扼杀给他们带来的心理阴影使他们在追忆往事之时不约而同地将尖锐的批判锋芒指向了封建制度。
鲁迅在创作《野草》与《朝花夕拾》前陆续翻译过很多涉及儿童心理的文章,他了解成人对于儿童游戏天性的扼杀会造成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表现出对传统教育方法的憎恶,《二十四孝图》是对“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鲁迅是喜爱图画的,但是这类行为却被“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他们要求儿童遵守社会的普遍秩序,完全不顾儿童自我的情感喜恶,扼杀了儿童的游戏天性,这自然会造成儿童精神力量的萎弱。在《五猖会》中,“我”本来对这次罕逢的盛事充满了期待,但是父亲却让我背完书才能去看会,父亲对“我”的天性的扼杀使得“我”对期待已久的五猖会都失去了兴趣,成年后的“我”对五猖会的场面已经完全忘却了,却只对父亲叫“我”背书一事印象深刻,说明了父亲对鲁迅的游戏天性的扼杀带给鲁迅的心灵创伤不仅仅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这件事所遗留的情感一直潜伏在鲁迅的潜意识中。
鲁迅对其童年创伤的反观意在强调“幼者本位”的观点,希望“让孩子们象孩子那样生活着”[4],很多作家在“痛定”之后对童年创伤的叙事也表达出对传统礼教的批判与对儿童独立性的呼唤。李广田在《悲哀的玩具》[5]中写道,“我”将麻雀作为玩物却惹得父亲的勃然大怒,虽然“我”成年以后理解了父亲由于生活的重担无法顾及孩子的无奈,但是“我”的没有欢乐的童年又有谁能理解呢?当时对父亲的“恨”以及父亲的行为在“我”幼小内心留下的创伤永远也无法抹去了。郭沫若出于孝心为了治疗母亲的晕病而去采摘别人家的芭蕉花,却被母亲严厉批评,这是对他的自信与勇气的摧残,在其幼年受到的“体罚”与“诗的刑罚”都表现出他对传统教育方式的批判,这种教育方式牺牲了儿童本该有的天真稚趣与快乐;郁达夫回忆上学情形时,孩子们被关在“笼中”背诵《三字经》,竟把上厕所当做是享受与娱乐;苏雪林的《童年锁忆》哀叹自己童年时期接受的都是有毒的精神食粮:成人向儿童灌输的荒谬的迷信和恐怖万分的鬼怪之谈;庐隐在《童年时代》中也以痛苦的笔调回忆了自己贪玩不小心弄坏了别人的怀表,被母亲痛骂并关在小黑屋中惩罚,使得庐隐回想自己的童年“只有可笑和叹息”[6];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讲到小时候不被母亲允许与其他孩子玩耍,虽然有学习音乐与图画的机会,但不是被反对就是被打骂,使得童年时期的胡适只习得读书与写字;邹韬奋在《我的母亲》[7]因为背不出书被父亲拿着板子毒打,母亲不忍心地流泪,但是嘴上却说着“打得好”,儿童正是这千百年来传下来的“野蛮的教育”的受害者;萧红年幼时学着乡下人的姿势蹲在洋车上,乡下人的本意是善良又体贴的,但是她却遭到了母亲的苛责。长辈们以“爱”的名义对儿童实施的是封建式的毒害,并且都在孩子们的心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朱自清的《择偶记》[8]则是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儿童的压迫,哀叹作为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就成为了包办婚姻的牺牲品。童年时期的创伤对于作家而言自然而然的会成为他们的写作资源,但是“五四”及以后的作家对童年创伤经验的书写的主题与意义深度的揭示明显还是受到了鲁迅“幼者本位”思想的影响,使得童年创伤的书写不同于一般性的回忆,达到了社会批判与重塑国民性的高度。
作家在成年后对童年创伤的反观往往表现出对童年时期的儿童天性被扼杀的叹惋,充满了哀凄。费孝通说:“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痛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9]家长长期的专制统治会造成儿童的奴隶根性,作家们在几十年后仍然清晰地记得这些童年经历,甚至是当时的心理状态,这就证明了童年的经验,特别是创伤性的经验对作家的影响是极大的,阿德勒说过:“在所有心灵现象中,最能显露其中秘密的,是个人的记忆”[10],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他们选择这些回忆进行反观绝不是偶然的,只有那些对他的处境有重要性的事物,才会留在他的记忆中,并且在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后“旧事重提”,作家们对童年天性被扼杀的书写都是对“幼者本位”思想的呼应,希望儿童能够成为独立的个体,儿童的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一部分,充分表现出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色彩。
二、情:“爱”的缺失
作家们隔着时间距离对童年的审美观照也伴随着情感记忆,对儿童有重要意义的人会一直留在作家的童年记忆中,对他们而言,祖辈、父母、仆人、同龄人往往是他们接触最多的人群,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自爱”与“爱人”的意识逐渐形成,“五四”先驱者们对童年时期所受的压迫经历的书写充分肯定了儿童的独立意义与价值,表达出个性解放的“自爱”意识,他们对记忆中人物形象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刻画更多地凸显了人道主义的“爱人”之心。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促成了“五四”时期的“人”的觉醒。
在童年叙事中,文本中的“我”即是作家自己,直接又真切地表达作者的个人体验。“五四”时期的童年书写几乎都把家人纳入了作品中,一类是书写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这种丰富性的经验给他们的生命增添了温馨与快乐,作家们的书写集中在对和谐的家庭关系与幸福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上,如冰心;另一类则多书写童年时期的缺失性经验[11],即物质匮乏与精神创伤,他们从父辈、朋友、仆人那里获得的“爱”是有缺失的,一方面在对这些人的描写中透露出作家们对腐朽现实的控诉与对“爱”的渴望,另一方面作家们能从自己的苦难身上看到他人的苦难,从而又在批判中体现出了深深的悲悯情怀。
“五四”作家们在回忆童年的作品中展现出的父辈形象常常和摧残与压抑联系在一起,他们以爱的名义对孩子们实施的封建教育方式对儿童天性的压抑实际上是一种伤害,中国的儿童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对他们的长辈只能顺从而不敢反抗,对他们又敬又怨。鲁迅、李广田、郁达夫、郭沫若、庐隐等人对父辈教育与责罚的描写都体现出了他们与父辈在精神上的疏远。苏雪林在《童年锁忆》中回忆了自己黯然无光的童年,因为出生于旧时代的大家庭,家长专制制度束缚了人的自由本质,又因她是一个女孩更受限制,她认为儿童没有得到应享有的关切与爱护,父母将全部心灵费在侍奉尊上上,“已无余力及于儿童”了[12]。只有摧毁现有的制度,才能从“高墙”里解放,做一个完整的儿童,自由的人。
除了过于严苛的教育使得作家们感受不到家庭和谐的温暖外,也有些作家自幼没有体验过父母的疼爱,他们的童年书写中对封建思想的抨击力度减弱了,“爱”的渴望与“爱”的缺失带来的悲哀是他们极力抒发的情绪。庐隐在《童年时代》中回忆往昔时,认为自己的内心是“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的[13],导致了她很多的作品都采取了日记、独白的方式,她的《海滨故人》便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与感伤的情调。郁达夫在《儿时的回忆》中也提到了自己“悲剧的出生”,三岁丧父使得他与母亲饱受邻居与亲戚的欺凌,对于饥饿的恐惧与父爱的缺失养成了郁达夫抑郁又乖僻的性格,《沉沦》《茫茫夜》等自叙传小说中的“我”“他”很大程度上就是郁达夫本人的写照,这些作品都有着浓郁的悲哀气息,正是由于父母亲情的缺失之痛在他的心里的深刻烙印,给他的作品都蒙上了一层沉郁悲哀的色调。作家们以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叙事方式共同写下了童年时期的创伤经验遗留在他们心中的哀凄,展现出了作家们孤寂而又敏感的内心世界以及儿童对于“爱”的渴求。
“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都是在仆人照料下成长的,仆人与他们不处于平等的地位上,他们在儿时感受到了仆人对他们的关怀与底层人民生活的不易。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中的关爱“我”的长妈妈、郁达夫《悲剧的出生》中的照料自己的翠花、王西彦《义父》中孤凄的老人、臧克家《老哥哥》中上了年纪被无情驱逐的长工都在作家的心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弥补了作家们“爱”的缺失,然而他们的生命力的陨落或是精神力的堕落又使得作家们更为沉痛地控诉这个黑暗的社会与封建的制度。与童年时期的作家们相伴的还有儿时的同伴,作家们不吝笔墨地描绘童年时期同伴间纯真的感情,然而这些人物的悲苦命运却能带给作家心灵上更大的震颤。鲁迅的《故乡》中儿童时期的闰土机灵活泼,却在多年以后变得像“木偶”一样麻木,王鲁彦《童年的悲哀》里教我拉胡琴的阿成哥死后带走了我的欢悦,郁达夫《悲剧的出生》里家乡的大多数人贫苦又麻木,像蟑螂似的在那里生长、繁殖,唯一给“我”带来生命的活力的阿千,他的死亡“也带去了我的梦,我的青春”[14],朱自清《择偶记》中表现了自己对表妹的美好情愫,却被包办婚姻制度扼杀。“五四”作家回忆这些底层人民的往事,也是对他们作为“人”的价值的肯定,他们的被侮辱与被损害控诉了黑暗腐朽的社会对他们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戕害,表现出了作家们对底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但是,启蒙者们也意识到了他们精神上的不觉悟,即由于精神上的奴役而缺乏“自愛”的个性解放精神,“五四”作家着意刻画他们的悲剧,就不仅表现出了“爱人”的意识,又隐蔽地表达出了他们对个性解放思想的呼吁以及反求诸己的思考。
三、思:忏悔与自救
“五四”时期,在急速变动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先驱者们都面临着精神出路的选择,但是由于中国精神渊源中上帝的缺席,使得中国缺少罪感文学,缺乏灵魂审判的意识,部分作家对童年时期经历的反观当做是精神避难的途径,冰心、废名、汪曾祺等人复现的儿童世界蕴含着他们对生命浪漫化的体悟,他们用诗意性的笔调建构起一个回不去的乌托邦,而童年创伤经验叙事则与之相反,它们在本质上是反乌托邦的,作家们直面内心的苦痛与现实的残酷,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回顾中渗透了时间沉淀后的个体生命体悟。“五四”一些作家将童年创伤的矛头对准封建文化、思想、制度,而缺乏灵魂自省的深度。但还有一些作家们的童年创伤书写体现出了以个性解放为内核的启蒙文学精神,在文学的精神向度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鲁迅作为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的开风气者,不仅在主题模式的选择上有前瞻性,他对于自我灵魂的审判意识也极为沉痛深刻。《风筝》借由它灵魂审判的深度表现出了在创伤经验书写基础上的升华。“我”在成年后的自省一部分是对自己损害了儿童的天性的自责,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的虐杀”的原因追根溯源。“我”的心“很重很重地堕着”,不仅在于“我”意识到了自己行为对小兄弟的伤害,更是鲁迅惊异于自己深受封建礼教的摧残,在不知不觉中竟由一个“被害者”成为了一个主动的“迫害者”。鲁迅清醒地意识到封建礼教对人们精神的腐蚀,他在自责与忏悔中体现的自省意识是对自我心灵的深层解剖,更是对封建力量的传承性感到震惊,意在揭示封建思想对心灵的腐蚀而被毒害者却毫不自知的现实。罪应当获得救赎,但必须通过忏悔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救赎,没有罪感,没有忏悔意识,文学就只能充当受害者和审判者的角色,负罪者很容易把罪责外化,推向他人。《风筝》的意义远不止在于记叙了一件忏悔的故事,作为受害者,把罪责推向封建礼教并开展对旧社会的讨伐这是很容易的,而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鲁迅决定了忏悔的最终走向是寻求救赎,并且走向的是自救之途。“我”试图对自己“精神的虐杀”进行“补过”,但是被害者却“什么也不记得了”,只有施害者自己认为过去的行为是一个错误,受害者却不以为意,努力赎罪的结果竟然是虚无,这一结果更让人感到鲁迅自我解剖的锋利与残酷。但在绝望之后“我”却选择“躲”进“严冬”,“严冬”是残酷的现实,是刻满了血痕的真实,鲁迅选择了“严冬”是正视了现实的残酷与挣扎的虚无并且选择承担的反抗精神,鲁迅将自己对自身与对社会的悲凉的认识转化成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因为绝望而选择反抗比为了希望而反抗的精神要更加可贵,这是一个“精神界之战士”内心的丰富与宽广。
作家在书写童年创伤时通常也寄寓了浓厚的忏悔与自省,而与这种反思意识联结起来的是他们对压抑儿童天性的自责与对幼者成长处境的关注。李广田1936年写作的《成年》与鲁迅1925年所著的《风筝》都表现出由“被害者”到“受害者”、由醒悟到忏悔的精神历程,“我”将自身受到的错误教育施加于弟弟身上,呵斥他、责打他,向他无理由的发怒,在“我”接触到“人”的观念时,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深深的自责。鲁迅将忏悔转化为了直接行动,希望向小兄弟请求宽恕,而李广田在忏悔后没有实施赎罪的行为,只是醒悟过来,将罪责化为内心的忏悔意识,也就缺乏了鲁迅反抗绝望的力度了。丰子恺在《忆儿时》中也回忆了儿时养蚕、吃蟹、钓鱼三件事情,童年时期的他经常压死幼蚕,吃蟹与钓鱼吃,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生灵的无辜,成年后的丰子恺笃信佛教,对于万物都持有悲悯情怀,这使得作家在若干年后回忆起对“生灵的杀虐”时,一方面是回忆童年的温情,另一方面又是杀生取乐的忏悔。作家们的忏悔并不是感情的冲动,而是经过了深刻的理性思考与内省,在时间的积淀下对自我行为的反思。“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文学来唤醒国民“沉睡的魂灵”,以此进行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文学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拯救社会,而在于自救”[15]。鲁迅对童年时期行为的自省书写揭示出了人们都未尝察觉的民族文化的心理遗传,促进了后辈的理性思考。
“五四”先驱者们作为“历史中间物”,在新与旧的夹缝中成长,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承担者,即使一生都在批判封建传统,但是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封建思想的刽子手,他们清醒地自觉着自己“中间物”的地位,回忆过去,但执着于当下,不是“源发于任何一种外在的权威和意志,而是源发于一种自觉自愿的主观需求,不是源发于对作品中一再提及的‘真的人的憧憬,而是源发于面对现实的自觉态度”[16]。对于童年创伤的书写是与心灵的直接交锋,这是他们抗争现实的方式,是作家们主动、自由的选择,这一选择正是源于他们对于现实的深刻体认。尼采说:“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作家们对童年创伤的书写正是一次“自救”的行为,通过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反观,“五四”作家从被压抑的自我中呼吁完整的儿童,完整的“人”的诞生,应和了五四追求自由的个性解放精神,同时以儿童视角对他人生命进行回顾时又渗透了先驱者们人道主义的悲悯之心。在“自爱”与“爱人”的感性体悟后,“五四”作家们对自我人格生成历史的反思与理性思索后的忏悔体现出了一个个精神探寻的历程,“爱”与“忏悔”两种意识贯穿于作家们对童年创伤的回忆中,展现出了新文学的先驱者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们对自我灵魂的重新拷问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学者们,真正促进了沉睡的魂灵们作为完整的“人”的觉醒。
参考文献:
[1]周作人.儿童的文学[J].新青年,1920,8(4):55.
[2]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A].鲁迅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1:134.
[3]胡适.易卜生主义[A].胡适文集[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5.
[4]谭桂林.论鲁迅对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的历史贡献[J].鲁迅研究月刊,1990(8):21.
[5]李广田.李广田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74.
[6][13]庐隐.庐隐自传[M].北京:第一出版社,1934:91.
[7]鄒韬奋.韬奋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1955:28.
[8]朱自清.朱自清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189.
[9]费孝通.生育制度[M].商务印书馆,1999:10.
[10]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0:64.
[11]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54.
[12]苏雪林.苏雪林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320.
[14]郁达夫.郁达夫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352.
[15]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415.
[16]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