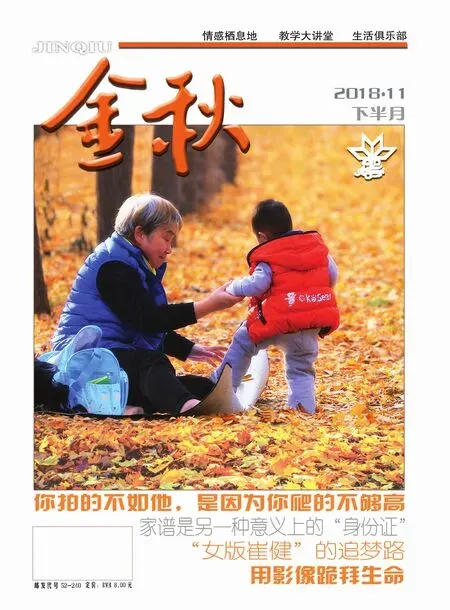撷影随想
2018-03-25姚泽芊
◎文/姚泽芊

和夫人在斯里兰卡旅行
爱为吾师
这一生断断续续一直做着有关艺术的事,编导、编剧、美术、文学……但最终感觉真正适合自己的,可能还是摄影,因为惟有摄影虽未做专业,却让我长久地乐此不疲,保持着旺盛的热情。
七十年代末辗转从兵团、部队回到西安,一心就是想拿相机,无奈找不着机会,才就着过去的经历做起了群众舞蹈工作。因不甘心“群众”的工作性质,又尝试写小说,也获了奖,又被抽调到杂志社作编辑,但是对摄影的热爱却从未从心中减退,那时,摄影还是个高成本的事情,个人承担不起费用,有时借着工作之便,便狠狠地“挥霍”一阵子,过一把摄影瘾。

后来,退休了,自由了,照相的成本也降下来了,可以像专业摄影师那样到处跑跑,拿相机像机关枪一样扫射了,但是金色的年华也过去了。摄影绝对是一个需要金钱、体力和时间的事情。在第一点不是问题,第二点还基本不是问题的时候,第三点,时间,就成了绝对的问题。因为,摄影的本质功能是记录,记录就需要时间,需要规划,需要积累,需要认准方向扑下身子去弄。照片所记录的生活的价值,往往是数年或多年后才能显现出来。
功夫在“诗”外
因为有过舞蹈艺术的实践,我最初是从舞蹈摄影中感觉到了自己的优势。之前看过许多舞蹈摄影作品,总有隔靴搔痒之感,摄影者因为不是真正懂得舞蹈,所拍的影像往往抓不住要害,触动不了情绪的G点。当时我就想,我要弄肯定比这个好,因为我知道舞蹈的本质。几千年前《诗经》中对舞蹈就有这样的论述:言之不足而嗟叹之,嗟叹之不足而咏歌之,咏歌之不足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表现人类最强烈的情感,这也是一切艺术的初衷和落脚点。舞蹈,又是地域文化和地域性格的集中体现,因而,舞蹈摄影的最高境界,是要能表现出舞者举手投足间那种特定的、微妙的情绪和韵味。这样的作品,绝不是唾手可得。这其中,需要体味、需要感悟,在此基础上还要敏锐地捕捉。
在这样的理论支持之下,我在舞蹈摄影领域小试牛刀,果然出手即受好评。摄影圈反响不错,在舞蹈界更被青睐。舞蹈专家们对我作品的评价是:这个摄影师知道演员那口气儿提在哪儿了。算是对我劳动最专业的褒奖。一时间,省舞蹈家协会、职工舞蹈家协会都邀请我做舞蹈大赛的专职摄影师。由我的作品而受启发,他们感叹,过去摆拍舞台照的方式应当改变了。省总工会还出资,为我给全省职工舞蹈决赛专场抓拍的摄影结集出版了画册,题名《舞动的心灵》。

诗歌界有句行话,叫“功夫在诗外”。这句话非常适应摄影艺术的状况。摄影的门槛似乎很低,不需要基本功训练,谁上手都能弄。但是真正要搞好,靠的也是镜头以外的东西,那就是,丰厚的、全面的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的素养。
何谓“毒”眼
摄影圈里有一句行话:某某人的眼睛“毒”。
所谓眼睛“毒”,就是善于发现,在混乱中发现秩序,在平凡中发现深刻。
眼睛“毒”的基础,我感觉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较高的美术素养,无论什么样的场面,总能够在里面发现符合美术构图法则的结构,捕捉到比较均衡、舒服的画面。另一方面,就是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文学是人学,有文学素养的人,观察敏锐,出于职业习惯,看人往往会透过表面直抵灵魂,从而挖掘出比较深刻的东西。
有了这两种素养,摄影师就会如虎添翼,拍摄任何日常的东西,出片都会具有一种“文化感”。这是深入到骨子里的东西,骨子里有了这种素养,拍出照片,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文化感”。
这一方面,我在实践中也是有所体会。前两年,到斯里兰卡去旅行,这个印度洋上的岛国风光绮丽,风俗独特。在慕名去拍摄已成为该国文化标志的海上独木垂钓时,那些安排得天衣无缝的人文美景并没有怎么打动我,倒是在经过一个叫尼甘布的小镇时,海边一些渔民的实地劳作使我倍感震撼。他们衣衫不整,形容疲惫,在海风的吹拂下紧张地劳作,还有人在为什么事在激烈地争论,斯里兰卡的神鸟——乌鸦在他们身边翱翔。我被这一切深深吸引,立即频频按动快门。
在整理这组照片时,我在一些著名的摄影网站上搜了一下拍摄地尼甘布小镇的图片,竟然全部是海景和海鲜,没有人去关注这些渔民。
我把这组照片放在国内比较权威的photofans摄影网站,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网站总部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对这组片子充分肯定,并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写了专访文章,发在了网站的人物版,同时还邀请我做了网站的签约摄影师。
事后我想,到底是什么吸引了我?应当不是美丽的场景,不是造型独特的渔船,而是他们独特的生存状态,是他们的情绪和情感,触动了我的所谓人文情怀,使我有深入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记录他们的冲动。
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似乎是一个政治名词,但是一切艺术,尤其是摄影艺术,却与此密切相关。原因很简单,因为生活是日新月异的,而艺术的经典是持久恒定的。在摄影艺术中,一味去玩味经典,企图复制经典,那就是刻舟求剑。这个问题在风光摄影中最为突出,以至有人断言:风光摄影已死。对于摄影艺术来讲,求新最难,却至关重要。
求新有多种路径,可以在技法上在形式上创新,但那只是表面上的标新立异,触及不了艺术的本质。
最根本的求新,我感觉还是要忠实于生活。生活每天都是新的,还愁以记录生活为宗旨的摄影新不了吗?
这个问题,我在实践中也有所体会。在少数民族地区拍摄,我原先总是企图拍出最纯粹的民俗风情,要避开一切现代信息的干扰,如电线、广告、汽车等,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生活的真实,拍出来的只能是过去生活的木乃伊。
还有一次,在四川拍摄老茶馆,由于摄影人很多,我费尽力气回避开这些外来者的介入,拍出了一些光影很好,很纯粹的风情片。但是回来后,发现这类片子拍的人太多,拍得再精致,也只沦于把玩光影,已没有了时代的生命力。经过思考,我没有再回避现实,把摄影人也作为茶馆发展的一个因素概括进来,搞了一组照片,反映了老茶馆从兴盛,到衰落,再到因摄影人的介入而再次兴盛,建立“摄影创作基地”的过程。有了这个主题线索,原来的片子就活了起来。有了鲜活的现实生命力。后来这组作品还以“沧桑老茶馆”为名,被一些刊物采用。

风景在路上
从年少时借相机玩,到年轻时小说在电台广播获奖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部华山牌照相机,再到近些年来长枪短炮齐全,断断续续也有几十年了。要问为什么摄影?回答只能是:因为爱。这个回答似乎少了点文以载道的崇高,却是最实在、最靠得住的动因。任何艺术,首先是有了爱,有了做,才有了后来社会赋予它的种种使命。
几十年写字照相,文学也好,摄影也好,都是在记录着自己的时空轨迹。我微信上的公开号“泽芊行吟”,功能栏的介绍里写着这样的文字:这多年且行且吟,风雨兼程,行不止,吟不绝……这正是我经历的写照和心境的真实剖白。
任何搞作品的人都希望作品被社会认可,因为那样,你就会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但是,能有这个结果除了才能和努力外,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可遇而不可求,我感觉大不必为这个事情去破坏我们澄明的心境。人生苦短,能与三五好友在一起上路,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个过程才是最宝贵的。诚如斯汤达墓志铭上所镌刻的:活过,爱过,写作过。有了这些,便应当满足了。曾和一些好友出版了一本摄影合集《我眼中的新疆》,我撰写的后记,题目就叫:我们在路上。
路上有最好的风景,需要自己去发现,这个发现的过程其乐无穷;路上行人众多,而我们自己,也是这路上的一道风景。